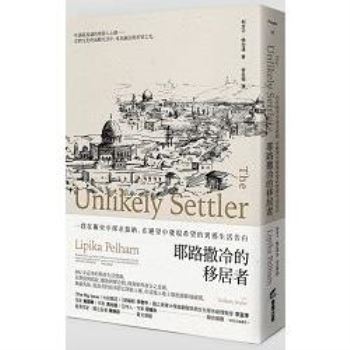母親不是猶太人
那日在倫敦,一個昏暗的贖罪日(Yom Kippur),夜晚里歐從猶太教堂回家,即將結束為期二十四小時的禁食。在這寒冷的秋夜裡,我也剛從BBC國際頻道(BBC World Service)位於布希大樓(Bush House)的新聞編輯室值了十二小時的班回來。我手指刺痛、背部痠痛,而長時間暴露於霓虹燈光下的雙眼,此刻正在適應家中廚房的柔和黃光。我把包包跟外套扔在廚房,泡了杯茶坐在餐桌前。我們六歲的兒子基朗正在畫著圓臉火柴人,還有他最拿手的圓圓大眼。我對里歐打招呼,他正站在兒子後方看著他畫畫。
「今天還好嗎?」
「還不錯。」
「你看起來好蒼白?」
「有嗎?」
「葛力克祭司還好嗎?」
「他很好。」
「要喝些茶嗎?」
他沒回答。從我剛進屋到現在他始終繃著臉,他開始整理餐桌上的雜物,迴避我的眼神。我這才意識到是怎麼回事,心裡想著我是否該道歉。我不夠敏感,沒有意識到他正處於贖罪日禁食,在我找到適當詞彙清楚表達我的歉意之前,他先開口了,以他獨有的沉靜而堅定的語氣說道,「今天是猶太曆最神聖的一天。我知道妳對宗教不感興趣,但妳至少可以試著尊重我。」
「你這話什麼意思?我當然尊重你的信仰。你不在家的時候,我甚至還帶兒子去猶太教堂參加星期六的祁福式(Kiddush),我很喜歡葛力克祭司跟他家人。」
「那妳怎能在我禁食的時候在我面前喝茶?妳大可再等上半小時左右,禁食就快結束了。」
「拜託,不要找我吵架!我工作了一整天,壓力很大。你可能會有興趣知道以色列正不分青紅皂白地砲擊黎巴嫩(Lebanon)南部……」
「妳怎麼可以在贖罪日去上班?妳明知道這對我有多重要。」
「你在說什麼?我不敢相信你會這樣講。我不是猶太人,你奉行你的宗教我沒意見,但我為什麼要禁食?我又為什麼不該去上班?你怎麼可以這麼霸道?」
「妳根本不懂。我一整年都在壓抑自己,唯有這一天我一想到我的孩子永遠不會是猶太人,就會從睡夢中驚醒。」他聲音顫抖地說。我害怕那每年至少得吵上一回的話題又要來了。我們總是在爭論該不該讓孩子成為猶太人,每逢贖罪日這個議題就會被掀起。若要讓孩子成為猶太人,我就得先皈依猶太教。
「就因為我不是猶太人?所以你要我怎麼做?戴頂假髮,吃符合猶太教規的食物,不吃海鮮,進行為期三年的轉化過程?你瘋了嗎?我一直以為我們是很棒的一對;我們想要證明縱使我們來自不同的大陸,有著不同習俗,但我們還是可以共同生活,用健全自由的價值觀教育孩子。我一直寧願相信我們之間的一切,是一個偉大的跨文化愛情故事。」
「但是每當贖罪日我的感受就會不一樣。﹂他說,一想到我永遠不可能轉化成猶太人,他的語氣難免有些沮喪。但此刻他正全神貫注看著兒子,我決定趁勢離開這個話題,朝臥室走去準備更衣,好前往他父母位在倫敦漢普斯特德區(Hampstead)的家,一起迎接禁食告終。」
「我從來沒要求你歸化,但如果妳愛我,妳就會知道什麼對我最重要。」當我聽見他這番令人瞠目結舌的言論,我在樓梯口停下腳步。
我的「以色列」女兒
我去幼稚園接瑪亞時遲了些。園裡只剩幾個孩子,匆忙趕來的家長把汽車隨處暫停,因為基督教青年會跟這所和平幼稚園所在的大衛王街此刻正對外封閉,好護送一些達官顯要通行。等著我的瑪亞手裡拿著許多藍白圖畫。以色列獨立紀念日就快到了,孩子們畫的每幅畫都是根據此主題描繪出以色列代表色。我甚至收到學校通知,說紀念日當天所有孩子都該穿白色T恤跟藍色牛仔褲到校,好揮舞藍白旗幟跟大衛王街的慶祝隊伍打招呼。整座城市都以藍白色妝點,從私宅到檢查哨塔,國旗四處飄揚。幾乎每兩部車就有一輛在收音機天線插上以色列國旗,隨風飄揚。
瑪亞走回座位要從抽屜拿她忘記帶走的東西。她回來時,我驚訝地看見她手裡拿著一根迷你英國國旗。
「誰要妳畫這個的?」
「我的老師。每個小朋友都要畫自己國家的國旗。我根本不知道這是英國國旗。我老師給我看一張圖片,我就照著畫。妳喜歡嗎?這是給妳的喔,媽咪,妳想家的時候可以用這個。」
「所以他們是刻意想讓這一切看起來正常。只要畫個聯合傑克(The Union Jack),那就算畫上一整天的以色列國旗都沒關係囉?那巴勒斯坦國旗呢?」我對我四歲的女兒這麼說,隨即意識到這話聽起來有多蠢。
「什麼是聯合傑克?」
「這個,就是妳手上拿的這個。」
「噢,我不知道英國國旗叫這名字。」
「那妳手上這些圖畫要怎麼辦?也是要給我的嗎?」
「這些是獨立紀念日的裝飾。我會掛在我房間。」
我從未見過有哪個地方對國旗如此執著。這裡不只可以在陽臺跟窗戶上看見國旗,健行者也會頭戴國旗圖樣的棒球帽,我甚至看過有男子戴著織成國旗上藍色星星與兩道藍色條紋圖樣的無邊禮帽。當我跟瑪亞走出優雅的基督教青年會大樓,她用希伯來語高聲喊道,「Degel shel Israel(以色列國旗)!」同時指著大衛王街上飯店外頭約一打在旗竿上飄揚的國旗。
「Degel shel Israel」成為她接連幾個月最喜歡的詞彙之一,儘管我苦口婆心勸她無論畫國旗或揮舞國旗都是不正確的行為,但她就是不聽勸。她拒絕理解原因,也不想知道為什麼她不該在她臥室牆壁或是我工作筆記本畫上以色列國旗。她甚至開始配戴一枚上頭有國旗的以色列博物館徽章,這讓她巴勒斯坦派的哥哥非常惱火。然而只要試圖從她身上拿下那枚徽章,場面都會變得一發不可收拾,要不大發雷霆、要不涕淚縱橫。我決定忽視她對國旗的偏執,我認為她很快就會失去興趣。但對里歐來說這可沒那麼簡單,他擔心他的巴勒斯坦朋友會發現他不但是猶太人,而且還有個「以色列」女兒!這又是一件至今我仍無法接受的事:只要我對任何人提起我們會奉行安息日習俗,並且在週五夜晚點起蠟燭,里歐就會勃然大怒。抵達耶路撒冷沒多久,我們就有過幾次劇烈的爭執,正是因為我公開談論我們的半猶太孩子,還有我們之所以會來到這裡,主要是因為他與這片土地及猶太教之間的關係。
「妳也不會希望我到處去跟人說妳有可能是印度教徒,但妳親近的家人又是穆斯林吧!」里歐憤怒地說道。我回覆他,「你當然可以這麼跟別人說,但我跟你狀況不同。你知道我的背景不是那麼簡單好懂,我沒有信仰任何宗教。我是無神論者,那才是我真實的身分。此外我們不是在印度,我們人在耶路撒冷,就我看來我們之所以會來這裡,正是因為你是猶太人。」
「我不想被任何刻板印象影響。再說,要是我的巴勒斯坦同事知道一個猶太人竟然想告訴他們該如何與以色列維持和平,這可能會讓他們對我留下壞印象。」
「但如果你連這麼重要的事都要隱瞞,他們又為什麼要信任你?如果某天你的猶太人身分曝光,他們又作何感想?」
「我報告裡所有建議都是根據我與人們開會結果而擬定的;我只是不想讓他們對我有先入為主的印象。我怕如果他們發現真相,一切就毀了。」里歐說。
「不好意思,我不懂你在說什麼。」我繼續說。「如果你擔心阿拉伯人發現你的信仰後,會因此反對你的提議,那你在這裡根本就是浪費時間。和平提議應該由屬於這片土地的人來擬定,否則這跟殖民事業有什麼兩樣?他們為什麼要聽局外人指揮?經過了六十年的協商之後,這些局外人替這片土地帶來了什麼?」
「總之我就是不希望妳到處宣傳我的猶太身分,就這樣。」我從他聲音聽見他對我有所不滿時,才會出現的那股嚴厲。
「我才沒有到處宣傳什麼!但我認為你必須告訴他們你的身分,如果他們因此質疑你的公平性,那錯的是他們。」
我當下感到失落迷惘。如果他持續否認自己的出身,我看不出有何必要待在耶路撒冷。我之所以會同意搬來,正是因為他與這片土地的連結。看著許多外國人打著西方自由主義的旗幟行殖民之實,有意無意地剝削以巴衝突,我拒絕成為他們的一份子。歐莉說里歐是自我厭惡的猶太人,這說法總會觸怒里歐。他真正想傳達的是,以色列假猶太教之名所犯下的行徑是如此駭人,他不想背負此罪名。然而除了隱藏身分以外,一定還有其他方式可以表達。
「你這樣言行不一會讓孩子們無所適從。」我說。
好吧,瑪亞除外,儘管她父親對以色列以及非猶太人卻奉行猶太教規這兩項議題存有異議,但我們的女兒對於自己應當歸屬何處沒有絲毫困惑。瑪亞愛死以色列了。
合法異鄉人
通過機場安檢最簡單的方式,是一開始就先提出自己與猶太人的親屬關係,當然前提是你確實有。當時以色列安檢單位會以不同顏色的貼紙作為暗號替乘客分類,但每隔幾個月各顏色所代表的類別會更換,如此人們便猜不到自己在以色列的機密檔案裡被歸屬於那一類。然而在以色列的第一年期間,我旅行了幾次之後便摸索出這些顏色的意義,我想至少在那一年裡,各個顏色所代表的意義如下:
粉紅色:猶太人或是有猶太親屬,例如我們一家人。
綠色:支持猶太人的正當異教徒。
白色:其他不構成安全威脅的外國人。
紫色:在巴勒斯坦領土工作,有潛在安全威脅的外國人。
橙色:姓名帶有阿拉伯文或是聽起來像阿拉伯文,可能會造成安全威脅的外國人,當中可能包括阿拉伯基督徒。或是護照上蓋有﹁敵國﹂的戳章,例如敘利亞、伊拉克、黎巴嫩、蘇丹。(有一回孩子們跟我拿到最安全的粉紅貼紙,但里歐不但只拿到橙色,而且還被盤問了好幾個小時,因為他的護照上有黎巴嫩的出入境章。當時他還沒去辦另一本出入以色列專用的護照。)
紅色:巴勒斯坦人。所有巴勒斯坦人都被認為是以色列國家安全的主要威脅。
這意味著即使是娶了英國妻子的巴勒斯坦參謀總長,每回要經由本—古里安國際機場去英國此探視妻兒,都得被脫衣搜身。
「既然我跟你們歐麥特總理(Ehud Olmert)進行和平協商會議時,都可以不用脫衣搜身就進入他的官邸,那我確定你大可不必讓我經歷這番折騰才讓我上機吧?」時任巴勒斯坦參謀總長的拉斐克.阿爾—胡賽尼(Rafiq al-Husseini)每回僅著內衣褲站在隔間裡時,總會如此告知負責質詢他的海關人員。他說他時常從安曼飛往倫敦,這樣一來便能免去這些羞辱。
每當輪到我們通過機場安檢時,通常由瑪亞負責多數談話,如此一來安檢會在幾分鐘內就結束。但有時候,我就是忍不住挑釁這個國家有如卡夫卡小說劇情一般荒謬的安檢流程。好比說,有一回我們要飛回英國過猶太新年那次就是一例。
那位年輕海關官員有著明亮雙眼與一副職業笑容。我們是人龍隊伍裡最後一組旅客,而我們的班機再過四十分鐘就要起飛了。為了加快流程,他走到我們身邊問了一句,「Ivrit ou Anglit?」
他是在問我們,他該說希伯來文還是英文?
我女兒用她完美的腔調回答道,「Ivrit.」
這位年輕官員臉上專業嚴肅的表情頓時轉為一抹溫暖的笑容。
「Bemet? 真的嗎?」他說。「妳的希伯來文是在哪裡學的?」
「在我學校。我們要去倫敦看我的saba ve safta。」
「妳爺爺、奶奶住在哪裡?」
「在修伊緒(Huish)。」
「那是在哪裡?」
「在倫敦。」
對瑪亞來說,倫敦等於英國的同義詞。我跟這位官員解釋修伊緒是位在威爾特郡(Wiltshire)的一個寂靜村落。他轉向我並開始專心問起更具體、更標準的「安全」問題。
「所以妳的家人住在英國?」
「是的。」
「他們叫什麼名字?」
在本—古里安機場出入多次之後,像這樣針對家庭背景進行侵略性提問已不再令我意外,因為我知道這位官員想知道些什麼。我躊躇了一會兒,猶豫著是否該拖慢整個安檢過程,故意不告訴他想要的資訊,稍微逗弄他一下?最後我對他說了家人的名字卻故意省略姓氏,如此一來,說了等於沒說。
「Shem Mishpakha?」他們的姓是?
我故意說了他們戰後的姓氏,從這姓氏完全看不出猶太血緣。
我欣賞著他的表情變化。他嚴肅了起來,先前放鬆的臉部肌肉再度緊繃,好找出以色列安檢單位一心想查出的「真相」。每一位質詢官都得問出盤查對象的種族與宗教背景。我已經知道下一個問題會是什麼,我不但沒有說出他想聽的答案,還準備了更言不及義的回答。我知道這麼做會拖慢進度,但我無法剝奪自己進行這個小遊戲的機會。
「妳的公公、婆婆或是妳和妳先生有屬於哪個社區嗎?」
「我們當然都屬於我們住的社區。」
「不是,我的意思是他們有參加什麼集會嗎?」
「我不懂你的意思。」
但其實我完全明白他在問什麼。他想知道我們是否為某間猶太教堂、基督教堂或是清真寺的教徒。
……
我環顧四周,巴勒斯坦旅客們看著我蓄意與這個種族歧視的系統作對,臉上幾乎藏不住笑意。要是我向海關官員說出我們「恰如其分」地虔誠信奉猶太教,他會立刻心滿意足地停止盤問。但我不能讓這位有著銳利明亮雙眼的以色列海關安檢人員打擊我的自尊。我身邊圍觀的這些臉孔,讓我無法說出他想聽見的答案,這些已排隊等上數小時的旅客大多是阿拉伯人,有些則是來自菲律賓與斯里蘭卡的家庭幫傭。要是我此刻直接答出真相,他們會認為我是投機份子,縱使那麼一來,我便可以順利通過安檢。
那日在倫敦,一個昏暗的贖罪日(Yom Kippur),夜晚里歐從猶太教堂回家,即將結束為期二十四小時的禁食。在這寒冷的秋夜裡,我也剛從BBC國際頻道(BBC World Service)位於布希大樓(Bush House)的新聞編輯室值了十二小時的班回來。我手指刺痛、背部痠痛,而長時間暴露於霓虹燈光下的雙眼,此刻正在適應家中廚房的柔和黃光。我把包包跟外套扔在廚房,泡了杯茶坐在餐桌前。我們六歲的兒子基朗正在畫著圓臉火柴人,還有他最拿手的圓圓大眼。我對里歐打招呼,他正站在兒子後方看著他畫畫。
「今天還好嗎?」
「還不錯。」
「你看起來好蒼白?」
「有嗎?」
「葛力克祭司還好嗎?」
「他很好。」
「要喝些茶嗎?」
他沒回答。從我剛進屋到現在他始終繃著臉,他開始整理餐桌上的雜物,迴避我的眼神。我這才意識到是怎麼回事,心裡想著我是否該道歉。我不夠敏感,沒有意識到他正處於贖罪日禁食,在我找到適當詞彙清楚表達我的歉意之前,他先開口了,以他獨有的沉靜而堅定的語氣說道,「今天是猶太曆最神聖的一天。我知道妳對宗教不感興趣,但妳至少可以試著尊重我。」
「你這話什麼意思?我當然尊重你的信仰。你不在家的時候,我甚至還帶兒子去猶太教堂參加星期六的祁福式(Kiddush),我很喜歡葛力克祭司跟他家人。」
「那妳怎能在我禁食的時候在我面前喝茶?妳大可再等上半小時左右,禁食就快結束了。」
「拜託,不要找我吵架!我工作了一整天,壓力很大。你可能會有興趣知道以色列正不分青紅皂白地砲擊黎巴嫩(Lebanon)南部……」
「妳怎麼可以在贖罪日去上班?妳明知道這對我有多重要。」
「你在說什麼?我不敢相信你會這樣講。我不是猶太人,你奉行你的宗教我沒意見,但我為什麼要禁食?我又為什麼不該去上班?你怎麼可以這麼霸道?」
「妳根本不懂。我一整年都在壓抑自己,唯有這一天我一想到我的孩子永遠不會是猶太人,就會從睡夢中驚醒。」他聲音顫抖地說。我害怕那每年至少得吵上一回的話題又要來了。我們總是在爭論該不該讓孩子成為猶太人,每逢贖罪日這個議題就會被掀起。若要讓孩子成為猶太人,我就得先皈依猶太教。
「就因為我不是猶太人?所以你要我怎麼做?戴頂假髮,吃符合猶太教規的食物,不吃海鮮,進行為期三年的轉化過程?你瘋了嗎?我一直以為我們是很棒的一對;我們想要證明縱使我們來自不同的大陸,有著不同習俗,但我們還是可以共同生活,用健全自由的價值觀教育孩子。我一直寧願相信我們之間的一切,是一個偉大的跨文化愛情故事。」
「但是每當贖罪日我的感受就會不一樣。﹂他說,一想到我永遠不可能轉化成猶太人,他的語氣難免有些沮喪。但此刻他正全神貫注看著兒子,我決定趁勢離開這個話題,朝臥室走去準備更衣,好前往他父母位在倫敦漢普斯特德區(Hampstead)的家,一起迎接禁食告終。」
「我從來沒要求你歸化,但如果妳愛我,妳就會知道什麼對我最重要。」當我聽見他這番令人瞠目結舌的言論,我在樓梯口停下腳步。
我的「以色列」女兒
我去幼稚園接瑪亞時遲了些。園裡只剩幾個孩子,匆忙趕來的家長把汽車隨處暫停,因為基督教青年會跟這所和平幼稚園所在的大衛王街此刻正對外封閉,好護送一些達官顯要通行。等著我的瑪亞手裡拿著許多藍白圖畫。以色列獨立紀念日就快到了,孩子們畫的每幅畫都是根據此主題描繪出以色列代表色。我甚至收到學校通知,說紀念日當天所有孩子都該穿白色T恤跟藍色牛仔褲到校,好揮舞藍白旗幟跟大衛王街的慶祝隊伍打招呼。整座城市都以藍白色妝點,從私宅到檢查哨塔,國旗四處飄揚。幾乎每兩部車就有一輛在收音機天線插上以色列國旗,隨風飄揚。
瑪亞走回座位要從抽屜拿她忘記帶走的東西。她回來時,我驚訝地看見她手裡拿著一根迷你英國國旗。
「誰要妳畫這個的?」
「我的老師。每個小朋友都要畫自己國家的國旗。我根本不知道這是英國國旗。我老師給我看一張圖片,我就照著畫。妳喜歡嗎?這是給妳的喔,媽咪,妳想家的時候可以用這個。」
「所以他們是刻意想讓這一切看起來正常。只要畫個聯合傑克(The Union Jack),那就算畫上一整天的以色列國旗都沒關係囉?那巴勒斯坦國旗呢?」我對我四歲的女兒這麼說,隨即意識到這話聽起來有多蠢。
「什麼是聯合傑克?」
「這個,就是妳手上拿的這個。」
「噢,我不知道英國國旗叫這名字。」
「那妳手上這些圖畫要怎麼辦?也是要給我的嗎?」
「這些是獨立紀念日的裝飾。我會掛在我房間。」
我從未見過有哪個地方對國旗如此執著。這裡不只可以在陽臺跟窗戶上看見國旗,健行者也會頭戴國旗圖樣的棒球帽,我甚至看過有男子戴著織成國旗上藍色星星與兩道藍色條紋圖樣的無邊禮帽。當我跟瑪亞走出優雅的基督教青年會大樓,她用希伯來語高聲喊道,「Degel shel Israel(以色列國旗)!」同時指著大衛王街上飯店外頭約一打在旗竿上飄揚的國旗。
「Degel shel Israel」成為她接連幾個月最喜歡的詞彙之一,儘管我苦口婆心勸她無論畫國旗或揮舞國旗都是不正確的行為,但她就是不聽勸。她拒絕理解原因,也不想知道為什麼她不該在她臥室牆壁或是我工作筆記本畫上以色列國旗。她甚至開始配戴一枚上頭有國旗的以色列博物館徽章,這讓她巴勒斯坦派的哥哥非常惱火。然而只要試圖從她身上拿下那枚徽章,場面都會變得一發不可收拾,要不大發雷霆、要不涕淚縱橫。我決定忽視她對國旗的偏執,我認為她很快就會失去興趣。但對里歐來說這可沒那麼簡單,他擔心他的巴勒斯坦朋友會發現他不但是猶太人,而且還有個「以色列」女兒!這又是一件至今我仍無法接受的事:只要我對任何人提起我們會奉行安息日習俗,並且在週五夜晚點起蠟燭,里歐就會勃然大怒。抵達耶路撒冷沒多久,我們就有過幾次劇烈的爭執,正是因為我公開談論我們的半猶太孩子,還有我們之所以會來到這裡,主要是因為他與這片土地及猶太教之間的關係。
「妳也不會希望我到處去跟人說妳有可能是印度教徒,但妳親近的家人又是穆斯林吧!」里歐憤怒地說道。我回覆他,「你當然可以這麼跟別人說,但我跟你狀況不同。你知道我的背景不是那麼簡單好懂,我沒有信仰任何宗教。我是無神論者,那才是我真實的身分。此外我們不是在印度,我們人在耶路撒冷,就我看來我們之所以會來這裡,正是因為你是猶太人。」
「我不想被任何刻板印象影響。再說,要是我的巴勒斯坦同事知道一個猶太人竟然想告訴他們該如何與以色列維持和平,這可能會讓他們對我留下壞印象。」
「但如果你連這麼重要的事都要隱瞞,他們又為什麼要信任你?如果某天你的猶太人身分曝光,他們又作何感想?」
「我報告裡所有建議都是根據我與人們開會結果而擬定的;我只是不想讓他們對我有先入為主的印象。我怕如果他們發現真相,一切就毀了。」里歐說。
「不好意思,我不懂你在說什麼。」我繼續說。「如果你擔心阿拉伯人發現你的信仰後,會因此反對你的提議,那你在這裡根本就是浪費時間。和平提議應該由屬於這片土地的人來擬定,否則這跟殖民事業有什麼兩樣?他們為什麼要聽局外人指揮?經過了六十年的協商之後,這些局外人替這片土地帶來了什麼?」
「總之我就是不希望妳到處宣傳我的猶太身分,就這樣。」我從他聲音聽見他對我有所不滿時,才會出現的那股嚴厲。
「我才沒有到處宣傳什麼!但我認為你必須告訴他們你的身分,如果他們因此質疑你的公平性,那錯的是他們。」
我當下感到失落迷惘。如果他持續否認自己的出身,我看不出有何必要待在耶路撒冷。我之所以會同意搬來,正是因為他與這片土地的連結。看著許多外國人打著西方自由主義的旗幟行殖民之實,有意無意地剝削以巴衝突,我拒絕成為他們的一份子。歐莉說里歐是自我厭惡的猶太人,這說法總會觸怒里歐。他真正想傳達的是,以色列假猶太教之名所犯下的行徑是如此駭人,他不想背負此罪名。然而除了隱藏身分以外,一定還有其他方式可以表達。
「你這樣言行不一會讓孩子們無所適從。」我說。
好吧,瑪亞除外,儘管她父親對以色列以及非猶太人卻奉行猶太教規這兩項議題存有異議,但我們的女兒對於自己應當歸屬何處沒有絲毫困惑。瑪亞愛死以色列了。
合法異鄉人
通過機場安檢最簡單的方式,是一開始就先提出自己與猶太人的親屬關係,當然前提是你確實有。當時以色列安檢單位會以不同顏色的貼紙作為暗號替乘客分類,但每隔幾個月各顏色所代表的類別會更換,如此人們便猜不到自己在以色列的機密檔案裡被歸屬於那一類。然而在以色列的第一年期間,我旅行了幾次之後便摸索出這些顏色的意義,我想至少在那一年裡,各個顏色所代表的意義如下:
粉紅色:猶太人或是有猶太親屬,例如我們一家人。
綠色:支持猶太人的正當異教徒。
白色:其他不構成安全威脅的外國人。
紫色:在巴勒斯坦領土工作,有潛在安全威脅的外國人。
橙色:姓名帶有阿拉伯文或是聽起來像阿拉伯文,可能會造成安全威脅的外國人,當中可能包括阿拉伯基督徒。或是護照上蓋有﹁敵國﹂的戳章,例如敘利亞、伊拉克、黎巴嫩、蘇丹。(有一回孩子們跟我拿到最安全的粉紅貼紙,但里歐不但只拿到橙色,而且還被盤問了好幾個小時,因為他的護照上有黎巴嫩的出入境章。當時他還沒去辦另一本出入以色列專用的護照。)
紅色:巴勒斯坦人。所有巴勒斯坦人都被認為是以色列國家安全的主要威脅。
這意味著即使是娶了英國妻子的巴勒斯坦參謀總長,每回要經由本—古里安國際機場去英國此探視妻兒,都得被脫衣搜身。
「既然我跟你們歐麥特總理(Ehud Olmert)進行和平協商會議時,都可以不用脫衣搜身就進入他的官邸,那我確定你大可不必讓我經歷這番折騰才讓我上機吧?」時任巴勒斯坦參謀總長的拉斐克.阿爾—胡賽尼(Rafiq al-Husseini)每回僅著內衣褲站在隔間裡時,總會如此告知負責質詢他的海關人員。他說他時常從安曼飛往倫敦,這樣一來便能免去這些羞辱。
每當輪到我們通過機場安檢時,通常由瑪亞負責多數談話,如此一來安檢會在幾分鐘內就結束。但有時候,我就是忍不住挑釁這個國家有如卡夫卡小說劇情一般荒謬的安檢流程。好比說,有一回我們要飛回英國過猶太新年那次就是一例。
那位年輕海關官員有著明亮雙眼與一副職業笑容。我們是人龍隊伍裡最後一組旅客,而我們的班機再過四十分鐘就要起飛了。為了加快流程,他走到我們身邊問了一句,「Ivrit ou Anglit?」
他是在問我們,他該說希伯來文還是英文?
我女兒用她完美的腔調回答道,「Ivrit.」
這位年輕官員臉上專業嚴肅的表情頓時轉為一抹溫暖的笑容。
「Bemet? 真的嗎?」他說。「妳的希伯來文是在哪裡學的?」
「在我學校。我們要去倫敦看我的saba ve safta。」
「妳爺爺、奶奶住在哪裡?」
「在修伊緒(Huish)。」
「那是在哪裡?」
「在倫敦。」
對瑪亞來說,倫敦等於英國的同義詞。我跟這位官員解釋修伊緒是位在威爾特郡(Wiltshire)的一個寂靜村落。他轉向我並開始專心問起更具體、更標準的「安全」問題。
「所以妳的家人住在英國?」
「是的。」
「他們叫什麼名字?」
在本—古里安機場出入多次之後,像這樣針對家庭背景進行侵略性提問已不再令我意外,因為我知道這位官員想知道些什麼。我躊躇了一會兒,猶豫著是否該拖慢整個安檢過程,故意不告訴他想要的資訊,稍微逗弄他一下?最後我對他說了家人的名字卻故意省略姓氏,如此一來,說了等於沒說。
「Shem Mishpakha?」他們的姓是?
我故意說了他們戰後的姓氏,從這姓氏完全看不出猶太血緣。
我欣賞著他的表情變化。他嚴肅了起來,先前放鬆的臉部肌肉再度緊繃,好找出以色列安檢單位一心想查出的「真相」。每一位質詢官都得問出盤查對象的種族與宗教背景。我已經知道下一個問題會是什麼,我不但沒有說出他想聽的答案,還準備了更言不及義的回答。我知道這麼做會拖慢進度,但我無法剝奪自己進行這個小遊戲的機會。
「妳的公公、婆婆或是妳和妳先生有屬於哪個社區嗎?」
「我們當然都屬於我們住的社區。」
「不是,我的意思是他們有參加什麼集會嗎?」
「我不懂你的意思。」
但其實我完全明白他在問什麼。他想知道我們是否為某間猶太教堂、基督教堂或是清真寺的教徒。
……
我環顧四周,巴勒斯坦旅客們看著我蓄意與這個種族歧視的系統作對,臉上幾乎藏不住笑意。要是我向海關官員說出我們「恰如其分」地虔誠信奉猶太教,他會立刻心滿意足地停止盤問。但我不能讓這位有著銳利明亮雙眼的以色列海關安檢人員打擊我的自尊。我身邊圍觀的這些臉孔,讓我無法說出他想聽見的答案,這些已排隊等上數小時的旅客大多是阿拉伯人,有些則是來自菲律賓與斯里蘭卡的家庭幫傭。要是我此刻直接答出真相,他們會認為我是投機份子,縱使那麼一來,我便可以順利通過安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