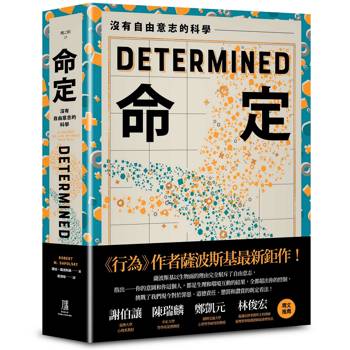14 懲罰的愉悅
正義得以伸張之一
歷史學家塔克曼(Barbara Tuchman)在1987的經典著作《遠方之鏡:動盪不安的14世紀》(A Distant Mirror)中,把14世紀描述為(雷同於現在的)「多災多難」而聞名於世。不論是不是一面鏡子,不管從什麼人的標準來看,那個世紀真的爛透了。其中一個悲慘根源是法國和英國的百年戰爭於1337年開始,沿途只留下毀滅。天主教會分裂出好幾個對立教宗,把基督教搞得一團亂。但最大的災難還是從1347年開始橫掃全歐洲的黑死病;在接下來幾年裡,將近一半的人口會在淋巴腺腫大的痛苦中死去。以倫敦為例,這場疫情嚴重到要花兩個世紀才能讓人口回復到疫情之前的規模。
甚至在該世紀更早先時,情況就夠糟了。以1321年為例,當時普通農民不識字、全身上下都是寄生蟲,為求生而辛苦掙扎。他們的預期壽命大約是二十五年;三分之一的嬰兒在第一個生日之前就死去。被迫把十分之一的收入繳給教會讓人更加貧窮;英格蘭有10-15%的人在一場飢荒中餓死。此外,每個人都還努力從前幾年的事件中復原;前幾年,牧羊人十字軍(Shepherds’ Crusade)宣稱要去殘殺西班牙穆斯林,最後反而跑去法國肆虐。但至少沒人覺得某個外團體在井裡下毒。
1321年的夏天,法國各地的人們認定,某個外團體――這次是痲瘋病人(醫學上稱「漢生病」)――正在井裡下毒。這種陰謀論很快就擴散到德國,然後從農民到王室的每一個人都接受了。在嚴刑拷打下,痲瘋病人很快就坦承說,是的,他們成立了一個發誓要在井裡下毒的公會,用的是蛇、蟾蜍、蜥蜴、蝙蝠以及人類糞便那一類的東西做成的藥水。
假設痲瘋病人真有下手的話,他們幹麼這麼做呢?有一種《活死人之夜》(Night of the Living Dead,喪屍電影的始祖)風格的說法是,人們認為那些毒會造成痲瘋病――也就是說,那是一種增員的手段。有些人感同身受地提出了另一種解讀,他們猜測說,痲瘋病人遭受缺乏同理心的對待而怨恨不已,因此做出這種報復行為。但一些有先見之明的人,對於資本主義之腐敗的理解領先了好幾個世紀,因而察覺到一種獲利動機。很快地,在更多「強化審問」下,答案浮現了――拷打後的痲瘋病人推卸責任,在痛苦尖叫間宣稱,他們的好搭檔猶太人付錢要他們在井裡下毒。完美。人人都認為猶太人不會得痲瘋病,所以他們才能平安地跟痲瘋病人搞陰謀。
但接下來猶太人又進一步推卸責任。儘管猶太人靠著唯利是圖的高利貸以及綁架基督教幼童賣去行血祭而暴富,但雇用那麼多的痲瘋病人還是花了他們一大筆錢。很快地,在死亡輪上被打斷骨頭(譯注:古代酷刑,將人綁在巨輪上打斷骨頭,然後放置至死)的猶太人公開宣布,他們也不過只是中間人――資助他們的是穆斯林!更具體來說,是格拉納達(Granada)的國王以及埃及的蘇丹,他們密謀要打倒基督教世界。但很不方便的是,暴民抓不到那兩個人。暴民們退而求其次,在法國和德國一個鎮又一個鎮地把痲瘋病人和猶太人燒死,死了幾千幾萬人。
在把後世稱作「痲瘋陰謀」的這件事處理完後,人們又回歸日常的艱困求生;正義獲得了伸張。
那些爛好人自由派
改革不是人人都喜歡。或許你正在梵諦岡養尊處優,然後來了個粗野的德國僧侶,喋喋不休地講著他那個什麼《九十五條論綱》。或者,如果你的品味是期待「事情變好之前得先變糟」,即無產階級掙脫頸上鎖鏈的那種路線,那麼改革只會削弱革命。如果改革當真接受了一個徹底荒謬到難以忍受、粗暴到難以捍衛的體制,那麼改革似乎不是一條出路。你應該看得出來我們會往哪邊去。
對啦對啦,刑事司法制度的確有很多要改革的。監獄容易造成犯罪,培訓著頻繁進出的累犯。暗藏的偏見對客觀審判和陪審團的概念予以嘲笑。體制提供了各種用金錢就買得到的正義。這些全都需要改革。至於在戰壕中試著做出改革的人──清白專案(Innocence Project,非營利法律組織,試圖為錯判有罪者平反、證明其清白,同時改革刑事司法系統,避免同樣的事情再次發生 )、從內部進行改革的地方檢察官候選人、無償幫助弱勢者的律師――實在是很不可思議。我如今有機會和多位公設辯護人共同處理大約十來件謀殺案,而這些人實在激勵人心――不但報酬過低、工作過量,與企業圈的有錢人錯身而過,還要為了那些通常在娘胎裡待了半年就注定未來會失敗的坎坷人辯護,而大部分的案件都敗訴。
然而,如果沒有自由意志,就沒有任何改革可以給予哪怕只有一絲道德善意的報應性懲罰了。
刑事司法改革看起來可能會像這樣:16世紀的歐洲有各種用來指認女巫的測試,全都糟糕至極。在良性一點的辦法裡,有一種是念《聖經》中吾主釘於十字架上的記事給嫌犯聽。如果沒有感動落淚,那麼她們就是女巫。1563至1568年間,荷蘭醫生維耶爾(Johann Weyer)試圖改革女巫審判制度,因此出版了一本《論惡魔幻覺,並論咒語和毒藥》(De praestigiis daemonum et incantationibus ac venificiis)。維耶爾在書中計算,撒旦有支由7,405,926名魔鬼和惡魔組成的大軍,1,111個師裡各有6,666名成員。可見維耶爾完全相信這套制度。這本書提出了三個改革建議。首先,不是女巫的人顯然會因為被打到體無完膚就什麼都招認,甚至承認自己是個女巫。第二點則讓維耶爾被視為精神病學鼻祖,那就是,有些人可能只是看起來像女巫,但其實是精神失常。第三點則提到了那個落淚測試。維耶爾呼籲,這方法想用盡管用,但不要忘記淚腺常常到了老年就會萎縮,所以聽了釘上十字架故事卻沒掉淚的老女人可能是器官受損無法哭泣,而不是女巫。
當你試圖改革一個純粹以胡扯為根據的制度時,情況就會像是這樣。當改革派人士試圖讓刑事司法制度更平等的時候,其實也是如此。這就等於是,試圖讓現實中的「施加正義」更符合柏拉圖式的理想樣貌,但那種理想樣貌其實沒有科學合理性或道德正當性。因為才剛開場,所以這邊先輕描淡寫一下……
正義得以伸張之二
在法國路易王族漫長的世系中,路易十五確實感覺不怎麼樣。他沒推行多少政策,也起不了什麼作用,又遭到人們鄙視,認為他是敗壞法國經濟軍事、貪圖逸樂的腐敗國王;1774年死後,法國公民大肆慶祝,預示了十五年後法國大革命的到來。1757年,一名刺客用基本上是摺疊刀的東西捅了他,刀子在穿透好幾層衣物(事發於隆冬戶外)後,造成了一點皮肉傷;但巴黎的大主教為了幫助嚴重受傷的君王,下令為了祈求龍體迅速痊癒而進行四十小時的禱告。
關於行刺未遂者――因連續偷竊雇主財物而多次遭解雇的家僕達米安(Robert François Damiens)――的動機為何,歷史並沒有說明白。有一種解讀是,他神經錯亂,精神有病。其他解讀則和當時的宗教爭議有關,達米安屬於遭到路易壓迫的敗北那一方,因此決心復仇。國王格外擔心達米安屬於更龐大陰謀的一環,只不過達米安在刑求時並未給出任何人的名字。動機先放一旁,唯一的相關重點就是他企圖刺殺國王;因此達米安被判有罪,注定成為法國最後一個被五馬分屍(quartered)的人。
這場發生在1757年3月28日巴黎一座公共廣場上的處決,留下了非常詳實的紀錄。達米安的雙腳先是被一種稱作「靴子」的刑求工具壓爛。接著,當初持刀冒犯國王的那隻手,被灼熱的鐵鉗燒焦;接著,將熔鉛以及滾燙的油、樹脂、蠟再加硫磺混在一起的液體倒進他的傷口。接著,他被切除生殖器,然後滾燙的混合物也從那邊倒進去。
這些舉動,以及達米安的哀號和求死呼聲,讓廣場以及(以高過頭的價錢租給有錢人當包廂的)上頭公寓裡擠滿的大量觀眾歡呼聲不斷。
但這些折磨都只是為重頭戲暖場而已,而所謂的重頭戲就是「五馬分屍」――將受害者的四肢各綁在一匹馬上,然後四匹馬兩兩往相反的方向走,把那人的肢體撕扯開來。達米安顯然擁有比預期中更堅韌的連結組織;儘管馬匹試了又試,他的四肢依然完整。最終,負責監督的行刑者把達米安四肢的肌腱和韌帶全都割斷,馬兒才總算分屍程工。只剩軀幹但仍在呼吸的達米安,被扔到了火堆上,斷掉的四肢也丟了進去。當他於四小時後化為灰燼時,群眾做鳥獸散,正義得以伸張。
作為OK繃的和解和修復式正義
假如審判遭到廢除,而是用查清楚誰執行了某項行動以及帶著何種心態的單純調查所取代。沒有監獄,沒有囚犯。沒有道德意義上的責任,沒有指責或應得的懲罰。
這種情境必定會引發的回應是,「所以你是說,暴力罪犯就該四處橫行,不為行動負責嗎?」不是。一台剎車不靈的車雖然本身沒有過錯,但不應該讓它上路。一個身上有著活性新冠病毒的人雖然本身沒有過錯,但應該要阻止他出席人擠人的音樂會。會把你撕成碎片的豹雖然本身沒有過錯,但應該阻止牠進入你家。
那麼,該對罪犯做什麼呢?有少數幾種方法,雖然立意甚好,卻還是有自由意志這個前提,但至少證明了真正聰明認真的人們正在思考以基進的替代作法,來取代我們目前對造成傷害者的回應。其中一種可能性是「真相和和解委員會」的模式,這種模式在後種族隔離時代的南非首度獲得委任,此後許多從內戰或暴力獨裁專政中恢復的國家都籌組了類似的委員會。
以南非的原型來說,種族隔離制度的設計者和黨羽可以出席委員會應答,而不是入獄。大約有10%的申請者獲得陳述機會,委員會則要求他們坦承自己出於政治動機所做的違反人權行為中的每個細節,包括他們殺了誰、刑求了誰、讓誰失蹤,甚至連沒人知道、不曾被咎罪的人都要說出來。他們會發誓不會再犯(好比說,再也不參加那種會威脅南非和平轉型自由國家過程的白人民兵組織);出席的受害者家屬也會發誓絕不採取報復行動。殺手接著會獲釋而不是入獄或遭到處決。提醒一下,沒人要求他們懊悔自責,沒有那種因悔罪而痛苦不堪的種族隔離凶手被受害者遺孀抱住原諒的擺拍畫面。這個方法反而(令許多親屬挫折地)非常務實,旨在幫助國家重建。最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種類似於警方追緝真凶的策略,像是抓到組織犯罪中某些笨菜鳥的犯罪證據,給他用供出上面的人來交換免罪的機會,然後往上又可以用同套做法擠出一些名字,這樣一路牽出背後的藏鏡人。這邊的情形是,豁免種族隔離政策的執行士兵之罪責,好讓他們牽出上面的犯罪首領,也就是種族隔離政府的首腦。有別於猶太人大屠殺或亞美尼亞種族滅絕,這麼做不會看到令人厭惡的種族隔離否認者堅稱暴力行徑是出於政治宣傳目的而遭到誇大,或是陳述說,那只是未經高層批准的個人行動而已。
雖然聽起來很動人,且在避免後續的暴行方面成果斐然,但這種委員會跟我們關心的重點其實沒太多關聯。在替一項罪行量刑的階段,有可能出現這樣的情況;加害者願意為犯行負責並對受害者表達懊悔之意,往往會導致刑期減少。但這整套做法充其量只是一種改革,罪犯不過就是被一個沒道理的體制處罰得少一點而已。基本上來說,人們主張他們的犯行是自由行使意志而為,而他們如今行使自由意志做出的負責悔悟行動,則是一個有所改變者行使自由意志做出的行動。那就不是我們這邊在處理的事情。
另一個有些神似但到頭來也跟我們主題不相干的模式,產生自「修復式正義」運動,關注的是罪犯和受害者之間的關係,而不是罪犯和國家的關係。這邊一如真相和和解委員會,也預期犯人要為所有行動的細節負責。接著,重點會放在相互理解。對加害者來說,是要認清自己造成的痛苦和折磨,透過去瞭解、去感受,去到會懊悔的地步。而對受害者來說,目標是在於瞭解讓違法者成為如今那個加害者的客觀環境,而那往往是個惡劣且徹底陌生的環境。而從那一刻開始,目標變成了要雙方(通常透過一個中間人)找一找自己可以做些什麼來消除彼此的痛苦,並找出一些方法來減少這種事再度發生的可能性。
修復式正義減低了累犯率,看似行得通。話雖如此,那當中卻有自我選擇偏誤的可能性――一個選擇這樣面對受害者的犯人,幾乎保證不是你所認為的一般囚犯,而是他本來就已經在改過向善了。
修復式正義似乎也以有益的方式影響著受害者。據報告顯示,走過這種流程的人對行凶者的恐懼和恨意都會降低,比較沒有安全方面的焦慮,整體運作機能也較佳,更能在日常活動感到愉快。這很好,但這之中同樣也可能有自我選擇偏誤。
不過,修復式正義也和我們關注的焦點無關。這是因為,它當真接受了應得懲罰的需求,使得如今瞭解到自己給人施加了什麼痛苦的囚犯,會更接受「被一個不合理體制懲罰」的正當性。
對我來說,實際上最有道理的方法就是「隔離」(quarantine)。知識上來說那一清二楚,而且完全能跟沒有自由意志一事相容。當然,它也會立刻讓許多人火冒三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