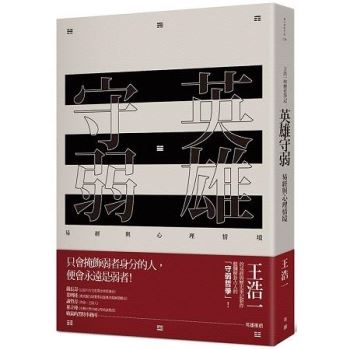花氣薰人欲破禪,心情其實過中年
回到四十五年前的中學,偶然聽到了黃庭堅前世的故事
今年春末,我重回已經畢業四十五年的國中校園,忝獲傑出校友獎項。十二歲青澀鄉下小孩,當年負笈嘉義市,就讀天主教輔仁中學,開啟了我的人生視野。重返學校,許多迷糊記憶掀開了,拿著麥克風說道:當年校外那攤陽春麵的薄薄兩片香腸肉,是我濃烈的美食初印象(幾位學長也頻頻點頭同意,露出笑容);至於住校三年,餐廳每天都是一樣的黃豆芽大骨湯,那是我的美食夢魘,略帶青菜腥的湯汁,永遠只飄著幾塊豆腐,幾輪玉米載浮載沉,湯色清澈湯味淡如水。我也說因為校園臨近八掌溪,沒有夜間設備的球場,晚上總是漫天的螢火蟲伴著我們打籃球……
輪到校友會理事長致詞,閒談中,他卻說了一個關於宋朝文學家黃庭堅的故事,第一次聽說,意涵悠遠,印象深刻。回家後,我急急查看了黃庭堅那則神祕的前世今生。
根據江西《修水縣志》的記載:二十六歲的黃庭堅出任黃州(蕪湖;湖北省東部)知府,一日午覺做夢,夢見自己走出衙門,前往一個村莊,看到一位白髮老婦倚門而立,口中還叫著女兒姓名,門口有一張香案,供著一碗芹菜麵。黃庭堅覺得餓,就端起來把麵吃了。不多時夢醒,嘴裡竟然真的有芹菜的香味。接連兩天都是同樣的夢境:吃了麵,醒來嘴裡有芹菜味香。
黃庭堅感到納悶,覺得此夢非比尋常,於是循著夢中的路徑走去,果然來到一處鄉村,一路的景致竟然和夢中的情景完全吻合,夢裡所見到的白髮老婦,也正站在門前,香案上供著芹菜麵,老婦口中喃喃著女兒的名字。
黃庭堅上前問了緣由,老婦說道,前天是她女兒的忌辰,女兒生前最愛吃她做的芹菜麵,所以每年這個時候,都會擺麵祭奠,喊她回來吃麵。黃庭堅自忖,事情也真巧,前天正是他的生日,遂又問,那女兒死去多久了?老婦說,二十六年了。黃庭堅一驚,自己正是二十六歲,她的忌日正是自己的生日。
「她的閨房在哪裡 我可以看看嗎?」進了屋內,房裡有座塵封多年的大櫃,因為不知道鑰匙放在那兒,所以一直沒打開過。黃庭堅想了一下,輕而易舉找到了鑰匙,櫃裡全是這個女兒生前讀的書,還有寫的文章。然而這些文章,居然和他自己歷次考試的試卷一字不差。
黃庭堅這時明白自己回到了前世的家,那老婦,自然是他前世的母親,老家只剩下她孤獨一人住著。黃庭堅跪拜在地上,說自己是她女兒轉世,認她為母。回到府衙的黃庭堅派人前來迎接老母,奉養終身。
蘇軾與佛印的深篤友誼,後世的小說家多了前世今生題材
前世今生傳說,總引人好奇也令人著迷。黃庭堅的前世,我們已經「見識」了,在《冷齋夜話》,蘇軾亦有雋永的前世故事流傳:話說元豐七年,一○八四年,四月,在筠州聖壽寺的雲庵禪師,夢到自己與蘇轍(當時被貶官在筠州高安)、聖壽寺的另一位聰和尚,三人一起出城迎接五戒和尚。他醒來後感到很奇怪,於是將此夢告訴了蘇轍,蘇轍還沒開口,聰和尚來了,蘇轍對他說:「剛才同雲庵談夢,你來也想一起談夢嗎?」聰和尚說:「昨晚夢見我們三人一起去迎接五戒和尚。」蘇轍撫掌大笑道:「世上果真有三人做同樣夢的事,真是奇怪啊!」
不久,蘇軾的書信到了,說他現在已經抵達距高安不遠的奉新,半天之內就可以見面。三人訝然,開心地趕赴城外二十里的建山寺,迎接蘇東坡。蘇軾到了後,大家對他談起了三人做相同夢的事,蘇軾若有所思:「我八九歲時,也曾經夢到我的前世是位僧人,往來陝右之間。還有,我的母親剛懷孕時,曾夢到一瘦高僧人來投宿,僧人風姿挺秀,一隻眼睛失明。」雲庵驚呼道:「五戒和尚就是陝右人,一隻眼睛失明,晚年時遊歷高安,在大愚過世。」此事算算已近五十年,而蘇軾現四十八歲。
至於五戒和尚的故事:五戒和尚本籍洛陽,自幼聰明,舉筆成文,琴棋書畫,無所不通。《宋元話本》有一則〈五戒禪師私紅蓮記〉,故事說的是五戒和尚與他的師弟明悟禪師,同在浙江寧海的淨慈孝光寺修行,五戒和尚則是住持。一日雪霽天晴,有僧人在山門外松樹下抱回一名女棄嬰,稟告住持。五戒和尚悲憫幼嬰,吩咐寺僧攜回寺中養育,取名紅蓮,「好生抱去房裡,養到五七歲,把與人家去,也是好事。」紅蓮長大後出落得清秀動人。一天,禪心清凈的五戒和尚萌生欲心色念,破了色欲大戒。師弟明悟禪師在禪椅入定回來,慧眼已知五戒和尚差了念頭,犯了色戒,淫了紅蓮,把多年清行,付之東流。
次日,正是六月盡,屋外翠池裡紅白蓮花正是盛開。明悟禪師採了一朵白蓮,攜回房中,取一花瓶插了,備妥清茶。派人邀請五戒和尚:「我與他賞蓮花,吟詩談話則個。」五戒和尚到了,明悟道:「師兄,我今日見蓮花盛開,對此美景,折一朵在瓶中,特請師兄吟詩清話。」五戒道:「多蒙清愛。」又問:「將何物為題?」明悟攤掌朝向桌案道:「便將蓮花為題。」五戒拈起筆來寫下:
一枝菡萏瓣初張,相伴葵榴花正芳。
似火石榴雖可愛,爭如翠蓋芰荷香?
明悟禪師接手落筆,便寫下四句詩,希望藉機作詩點醒師兄。
春來桃杏盡舒張,萬蕊千花鬥豔芳。
夏賞芰荷真可愛,紅蓮爭似白蓮香?
五戒和尚心中一時解悟,羞愧之下便轉身辭回臥房。沐浴後更新衣,取張禪椅到房中,跏趺而坐。將筆在手,拂開一張素紙,便寫八句《辭世頌》,之後坐化而去:
吾年四十七,萬法本歸一。
只為念頭差,今朝去得急。
傳與悟和尚,何勞苦相逼?
幻身如雷電,依舊蒼天碧。
前世是五戒和尚與明悟禪師,今生是蘇軾與佛印禪師
這個故事尚未結束……明悟禪師聽得五戒和尚坐化,大驚,入房也見了師兄的《辭世頌》,嘆說:「你好卻好了,只可惜差了這一著。你如今雖得個男子身,長成不信佛、法、僧三寶,必然滅佛謗僧,後世卻墮落苦海,不得皈依佛道,深可痛哉!真可惜哉!你道你走得快,我趕你不著不信!」當下也吩咐寺僧燒湯洗浴,換了衣服,上了禪椅跏趺而坐。明悟禪師向其他僧人細細說明:「我今去趕五戒和尚,汝等可將兩個龕子盛了,放三日一同焚化。」囑罷,圓寂而去。就這樣,兩個靈魂一路向西,來到四川。
兩位禪師同日坐化,當然驚動城內城外信眾,來燒香禮拜布施者,人山人海。傳聞四起,這且不表,回頭說說五戒和尚。此時他已經投胎四川眉州眉山縣城中一處詩禮之家,這個人家,姓蘇名洵,自號老泉居士。已經結婚十年的二十九歲蘇洵,其妻程氏,夜夢一瞽目和尚,走入房中,吃了一驚。次日早上分娩一子,取名蘇軾。
民間小說則記錄明悟禪師,內心一靈,也托生在本處人家,姓謝名原,字道清。謝原的妻子章氏「亦夢一羅漢,手持一印,來家抄化。因驚醒,遂生一子」。此幼兒,取名謝瑞卿,他即是後來的佛印禪師。自此蘇軾與謝瑞卿,今生兩人再續前緣。當然,這是小說之言,史書記錄蘇軾出生於四川眉山,當時是宋仁宗景祐三年,一○三七年,農曆十二月十九日。然而,佛印禪師本姓林,他是饒州浮梁(今江西)人,生於宋仁宗明道元年,一○三二年,早了蘇軾五年。史書記錄佛印:幼聰慧,三歲誦《論語》,五歲能誦詩三千首。
兩人出生日期與地點,史書所載與小說杜撰有出入,但卻不影響兩人彼此在佛法專研切磋的關係,野史中常有佛印與蘇軾鬥智的故事,大有禪機,總是引人入勝。佛印說法講究用詞,「人間寒食,洞裡花開。游蜂與蝴蝶爭飛,鷺子共黃鸝對語。」我以為,此話語也道盡佛印與蘇軾的「這輩子美麗的糾纏」,饒是人生幸福之事。
後人則把蘇軾與佛印交往的種種傳說,透過小說串連在一起,使其兼具文學性與趣味性,也為後世文學提供了豐富素材。而蘇軾「前世為僧」這個夢,雖未束縛蘇軾的人生,一輩子以僧為友,他卻不唸佛,依舊積極地仕進,愉悅地笙歌。
從富家子弟到進入佛門,佛印二十八歲時被譽為「英靈的衲子」
林語堂的《蘇東坡傳》提到佛印:「佛印從來不打算出家,而且是富家子弟。」宋神宗對佛教表示好感,願聽佛教徒進言,蘇軾就把他帶到朝中與皇帝對談。據推論此時應該是蘇軾三十三歲時,於熙寧二年,丁憂結束還朝之際,當時蘇軾在京任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當年,王安石的新政開始實施)。
「佛印盡量在皇帝面前表現他對佛教的信仰。皇帝看看他,發現他高大俊俏,容貌不凡,就慷慨答應給他一張度牒,讓他入寺當和尚。他進退兩難,只好接受皇帝的建議,於是被迫出家。」林語堂的文章繼續說佛印:「他住在杭州期間,傳說他一出門就帶了不少傭人和馱騾,根本不合乎禁欲的生活原則。」
需要交待的是「度牒」,古代政府頒發給合法出家者的身分證,僧尼憑此可免除地稅、徭役。過去,歷代政府對度牒數額一向從嚴控制。
佛印俗姓林,饒州浮梁人,自幼學習儒家經典,三歲能誦《論語》、諸家詩,五歲能誦詩三千首,長而精通五經,被稱為神童。少年即學習禪法,十九歲時曾到廬山學佛。被住持稱讚「骨格似雪竇,後來之俊也」。二十八歲,由於精究空宗,被稱為「英靈的衲子」。佛印自出家後,先後曾住過廬山開先寺、江州承天寺等,後來住持在潤州(今江蘇鎮江市)金山、焦山兩寺。期間,他也常常雲遊四處。
熙寧四年,一○七一年,三十五歲的蘇東坡因為得罪新黨,受到政治迫害。蘇軾自請外補以離開汴京的政治漩渦。他的官職從判官告院改為「權開封府推官」,到了冬天,離開汴京改任「杭州通判」。雖然是貶謫,蘇軾是開心的,因為杭州有西湖。在〈飲湖上初晴雨後〉一詩中,對西湖的讚美,成了經典名詩:
水光瀲灩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
蘇軾到了杭州,結識了佛印禪師,兩人過往甚密,甚至「沒大沒小」,成為至交。兩人常在佛學修養與詩詞聯對上切磋鬥智,甚至互相調侃彼此為樂,傳為美談。有一次,蘇軾跟佛印說:「和尚,古來的人,為什麼總是把出家人比做是雀鳥呢?」佛印說:「你說說看!」蘇軾說:「因為唐詩有一句說『鳥宿池邊樹,僧推月下門』,前一句說的『鳥』,後一句就對著這個『僧』啊!」蘇軾想藉這「鳥」對「僧」,轉個彎罵佛印是鳥……而鳥是笨的!沒想到佛印說:「那大人你現在對著僧人我,你豈不成了一隻鳥!」蘇軾一想……又輸了!一俗一僧,兩人的機鋒競賽成了蘇軾的「快樂泉源」。有時,彼此的聯對又成了「聰明人的遊戲」。一次,佛印出了上聯:「三年一閏,五年再閏,陰陽無差無錯。」蘇軾對上:「二月春分,八月秋分,冷熱不長不短。」
在易經有一卦〈比〉,比為親信、親密,親比之義,引申為輔佐。《彖傳》:「比,輔也,下順從也。」比卦為小方國順從於大國,小人(指力氣小的人)向大人表示服從,向大人親密、靠攏的意思。這一點,即使卜筮驗證,也是「元始」,是永遠堅貞的德行,說明「不會有災難,因為不使硬,剛毅中正」。如果心中不安,便是因為你在相親相愛的過程中,沒有堅持中正的原則,有趨炎附勢的嫌疑。
蘇軾之於佛教、佛禪的心靈階段,一直有諸多友人、名僧相親相輔,使得他的精神生活,得以靠參禪悟道來調節,幾次貶謫,依舊從容。
從《易經。比卦》看三十五歲後的蘇軾,好友佛印、道潛如何親密比輔
〈比〉卦上卦坎水,下卦坤地,卦象就是「地上布滿水」,水與地相親無間,喻示「親密比輔」,「水性潤下,今在地上,更相浸潤,比之義也。」其主要意旨涉及「人與人的親密、靠攏關係」普遍的意義,更有象徵「陷入孤獨」的另外意涵。如果說「當你孤獨的時候怎麼辦?」也是比卦的一種解釋。一般的情形下,人應該遠離孤獨。而遠離孤獨,就是要學會與人相親相輔。〈比卦〉六爻,僅有九五是陽爻,所以也是「卦主」,諸爻以親比九五為吉。卦主為眾所親輔,而上亦親下,這就是「比」的意涵。
第一爻。初六 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
「孚」就是中心誠信。滿也。缶,素器也。「有它吉」就是沒有期待於必得,「結
果得之」的吉祥。初六處與「比的開始」,必以誠信,乃得無咎。(「無」,古做
「无」。)初六居下居卑,離九五最遠,如果要親比九五,當誠信充實於內,
好像缶裝滿東西於其中,外表不需要修飾,誠信足矣。九五雖遠,終能來與初
六來親比,有它吉。
三十五歲的蘇軾在杭州多了達觀自在,與佛印相處則多了生活禪——
三十五歲的蘇軾任杭州通判,所謂「通判」是「通判州事」簡稱,此職由皇上直接委派,輔佐郡政,可視為知州副職。蘇軾的辦公地點在西湖南岸鳳凰山頂,可以北眺西湖,南望錢塘江。置身於此,在汴京所受的政治委屈早已雲散,他與友人盪舟西湖,沉醉湖光山色。
順便說說蘇軾的婚姻:當他十九歲,尚未赴京應考前,奉父母之命娶了四川青神縣進士王方的女兒王弗為妻,夫妻恩愛。當蘇軾二十三歲時長子蘇邁出生,之後蘇軾三年的「鳳翔府簽判﹂地方仕途三年,王弗也與蘇軾同行。蘇軾二十九歲時,宋英宗治平二年,正月,還朝回到汴京,任差「判登聞鼓院」,這是掌管接受文武官員及士民章奏表疏事宜的官職。五月,王弗病逝。
次年五月,父親蘇洵病逝,享年五十八歲。蘇軾偕弟扶柩還鄉,將父親與髮妻王弗安葬。於宋神宗熙寧元年,一○六八年七月,服完父喪後,蘇軾又娶了王弗的堂妹,二十歲的王閏之為妻,隨後兄弟二人離開眉州,還朝汴京。自此蘇氏兄弟再也沒有回過四川家鄉。
在杭州通判任上第四年,熙寧七年,一○七四年,在太守為他舉行的歡迎宴會上,年僅十二歲的王朝雲被招來獻藝,席中她第一眼看到蘇軾,就感覺到這是自己的親人來了。她逮個機會小心地湊到蘇軾身旁,大膽地說:「大人,您能帶我走嗎?」蘇軾細看這女孩歌妓,彎眉秀眼,貌美如花,纖細苗條,看她這麼小就淪落風月場所,不由動了惻隱之心,隨後為她脫籍,成了蘇太太王閏之的丫鬟,朝雲從此邁入蘇門。
照宋朝的說法,蘇軾收朝雲作妾。古人常把太太的丫鬟稱為「妾」,那是方便幫忙照顧丈夫的生活。可是朝雲還小,她是入了蘇家才開始學讀、學寫。後話,被貶謫到黃州的蘇軾,第三年才正式「收朝雲為妾」。元豐六年,一○八三年,蘇軾四十七歲,朝雲二十一歲時生了一個男孩,取名蘇遯(不過,未滿周歲而卒)。
話說在蘇軾當年從汴京往杭州赴任的路上,特地轉往陳州探望了弟弟蘇轍,當時蘇轍在陳州任「州學教授」。盤旋幾天之後,兄弟倆一起前往蔡州,拜訪任知州的恩師歐陽修。歐陽修建議蘇軾,抵達了杭州「到官三日,訪勤於孤山之下,抵掌而論人物」,這裡的「勤」,指的是西湖的惠勤和尚(還有師弟惠思禪師),他是一位有閱歷的高僧。蘇軾前往孤山廣化寺拜訪二僧,寫下:「天欲雪,雲滿湖,樓台明滅山有無……孤山孤絕誰肯廬?道人有道山不孤;紙窗竹屋深自暖,擁褐坐睡依團蒲……」詩句,此後孤山就成了蘇軾經常探訪之地。蘇軾在杭州的第二年,一○七二年晚秋,歐陽修病逝於潁州,享年六十六歲。蘇軾與惠勤和尚悼念他於孤山。
蘇軾很早接觸佛教,一生與禪師交遊頗廣。然而在杭州這四年,才是他真正意義上接觸「佛學」。他遍訪了西湖岸邊的靈隱寺、天竺寺等等,與出家人交遊辯談,也與惠勤、惠思二僧多有唱和。熙寧七年,一○七四年,他在杭州又認識了一位詩僧「道潛」,號「參寥子」,他倆成了一輩子的摯友,蘇軾稱他「道德高風,果在世外」。當然在杭州也有佛印、海月僧等好友,他們也常常與蘇軾遊廟談禪。
有一次佛印與蘇軾參觀一座廟宇,他們進了前殿,眼前有兩尊怒目兇猛神像,是鎮邪守護神。蘇軾問:「這兩尊菩薩,哪一個重要?」佛印說:「當然拳頭大的重要。」進了正殿,看到觀音菩薩手持念珠,蘇軾問:「觀音也是菩薩,祂數念珠幹什麼?」
佛印回答:「哦,祂也學別人拜佛呀。」「拜哪一尊菩薩呢?」佛印又回答:「祂也拜觀音菩薩呀。」「咦,這怎麼回事?祂是觀音菩薩,為何要拜自己?」
佛印說:「你知道嘛,求人不如求己!」
一天,蘇軾讓書僮戴上一頂草帽,穿一雙木屐,去佛印處取東西。書僮問:「老爺要取什麼東西?」蘇軾說:「佛印和尚一看你就知道了。」書僮到了佛印處說:「老爺讓我來取東西。」佛印問:「取何物?」書僮說:「老爺說你一看見我就知道了。」佛印看一看書僮,轉身包了一包東西讓書僮拿走。回家後,書僮把東西交給蘇軾,問道:「老爺,是不是這包東西?」蘇軾笑道:「正是!正是!」
答案是「茶」葉!草帽在上,木屐在下,中間是書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