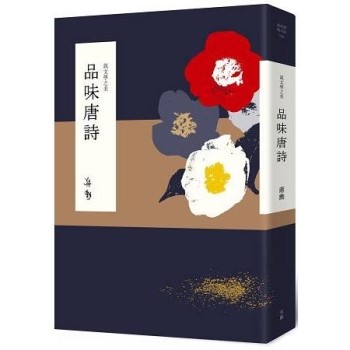(節錄自「第一講 大唐盛世」)
詩像一粒珍珠
有一天,語言和文字能夠成為一首華美的詩,是因為經過了這長期的琢磨
講到唐代美術史的時候,我有一種很不同的心情,發現完全沒有辦法解釋為什麼一到唐代,在色彩和線條上都出現了如此華麗的美學風格。我常常用「花季」來形容這個歷史時期。張萱、周昉、閻立本,這些初唐到盛唐的美術創作者,讓我們感覺到他們生命的精神完全像花一樣綻放開來。當然,歷史本身是延續的,在此之前自然會有一個慢慢積累的階段,有很多準備工作一直默默地進行,這個準備階段可能長達三百年之久,才會水到渠成。
在南北朝分裂時期,陶淵明的時代,有很多的實驗正在為一個大時代的到來做準備。在美術方面,要準備色彩,準備線條,準備造型能力;在文學方面,要準備文字,準備聲音,準備詩的韻律與結構,我稱其為「漫長的準備期」。
這個準備,特別是文學上的準備,不是很容易發現,因為文學上使用的語言和文字其實經過了長時間的琢磨。比如「五四運動」前後最早的那批白話文,「的」字用得很多,他們是在強調一種文字和語言的解放,希望在文學中能夠看到平常講話的白話形態。我們平常講話時,「嗎」或者「呢」這些字不見得會讀那麼重,可是當它們變成文字的時候,會特別觸目。「觸目」的意思是說,講話時,「你吃飯了嗎?」當中那個「嗎」,可能只是帶出來的一個音,一旦變成文字就跟「吃飯」這兩個字同等重要了。在聽覺上,這個「嗎」只是一語帶過;在視覺上,它卻有了很高的獨立性。可能就是這個反差,使得文字和語言之間,一直在互相琢磨。
詩很像一粒珍珠,它是要經過孕育以及琢磨的。我們的口腔、舌頭、牙齒、嘴唇在互動,像蚌殼一樣慢慢、慢慢地磨,磨出一粒很圓的珍珠。有一天,語言和文字能夠成為一首華美的詩,是因為經過了這長期的琢磨。魏晉南北朝的三百多年,就是琢磨唐詩這顆「珍珠」的過程。甚至在陶淵明這些詩人身上還可以看到琢磨的痕跡。陶淵明這麼好的詩人,我們給予他很高的文學評價,可是以文學的形式美來講,我其實沒有辦法完全欣賞他的詩。〈桃花源記〉是陶淵明一首詩的序,結果後來流傳較廣的反而是詩的序,不是詩本身。這種現象很有趣,可能也說明了這首詩在形式上的完美度還沒有被琢磨好。魏晉南北朝時,像唐詩那樣的文字、語言還處在「練習」的初期。
唐代是詩的盛世
唐代不僅在美術史上是一個花季,在文學史上也是一個花季
唐代是一個「水到渠成」的階段。整個中國文學史上,詩的高峰出現在唐代。當我們讀唐詩時,意思懂或不懂,都不是那麼重要,只覺得那個聲音是那樣好聽。唐代是詩的盛世,詩的形式已經完美到了極致。唐代不僅在美術史上是一個花季,在文學史上也是一個花季。我們常常說最好的詩人在唐代,這其中多少有些無奈,彷彿是一種歷史的宿命,那麼多詩人就像是彼此有約定一樣先後誕生。換一個角度來看,那個時代在語言和文字方面給詩人們提供的條件實在是太好了。如果反身看我們自己,就會發現白話文運動之後的漢語文學,不是處在像唐代那樣的黃金階段,而是比較像魏晉南北朝初期的狀態。
文學比美術對我們的影響要深。我們從來不會想到自己脫口而出的那個詞、那句話其實是唐朝的語言。臺灣早期民謠歌手陳達的《勸世歌》很像唐詩七言句的「二、二、三」結構,而且押韻,四個句子一韻,〈春江花月夜〉裡面的「春江潮水連海平」就是二、二、三的句式。
每個時代都對中國文學做出了自己的貢獻。「四」怎麼變成「五」?「五」怎麼變成「七」?幾百年間,不過在解決這些小問題而已。文化的工作非常艱苦,可是這些小問題一旦解決,就會一直影響我們。
當詩變成了成語、格言的時候,會對人產生更直接的影響。雖然宋代之後,文學有小小的變遷,但唐詩在民間已經變成一個根深柢固的美學形式。清代以後,幾乎每個人手上都有一本《唐詩三百首》。甚至在看戲時也會接觸到詩的形式,那些舊戲,無論是川劇、河南梆子,還是歌仔戲,人物一出場,就要念「定場詩」。所以,唐詩不僅影響讀書人,也透過戲劇在庶民的世界裡發生了影響。詩人的孤獨感
他寧可是孤獨的,因為在孤獨裡他還有自負
空間和時間的擴大,使原本定位在穩定的農業田園文化的漢文學忽然被放置到與遊牧民族關係較為密切的流浪文化當中。我們從李白身上看到很大的流浪感,不只是李白,許多唐代詩人最大的特徵幾乎就是流浪。在流浪的過程中,生命的狀態與農業家族的牽連被切斷了,孤獨感有一部分就來源於不再和親屬直接聯繫在一起的狀態。
安史之亂以前,李白與王維都有很大的孤獨感,都在面對絕對的自我。在整個漢語文學史上,面對自我的機會非常少,因為我們從小到大的環境,都要面對親族關係,生活在一個充滿人的情感聯繫的狀態裡。我們不要忘記人情越豐富,自我就越少。我們讀唐詩時,能感受到那種快樂,是因為這一次「自我」真正跑了出來。李白是徹頭徹尾地面對自我,在他的詩裡面很少讀到孩子、太太,甚至連朋友都很少。他描述自己和宇宙的對話:「五嶽尋仙不辭遠,一生好入名山遊」,李白的詩裡一直講他在找「仙」,我覺得這個「仙」是他心目中完美的自我。只有走到山裡去,他才比較接近那個完美的自我。到最後他也沒有找到,依舊茫然,可是他不要再回到人間。因為回到人間,他覺得離他想要尋找的完美自我更遙遠。他寧可是孤獨的,因為在孤獨裡他還有自負;如果他回來,他沒有了孤獨,他的自負也就會消失。李白一直在天上和人間游離。他是從人間出走的一個角色,先是感受到巨大的孤獨感,然後去尋找一種屬於「仙人」的完美性,可是他並沒有說他找到了,大部分時候,他有一種茫然。
初唐時期就是在為李白這種詩人的出現做準備。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邊塞詩的發展。
邊塞詩非常重要。中國文人很少有機會到塞外去,很少有機會把生命放到曠野上去冒險,去試探自己生命的極限。宋朝以後,文人寫詩泰半是在書房裡。我覺得唐詩當中有一個精神是出走和流浪,是以個人去面對自己的孤獨感。當時的詩人到塞外是非常特殊的經驗,詩人們在這之中激發出自己生命的巨大潛能。初唐詩的內在本質,很大一部分是詩人與邊塞之間的精神關係。唐朝開國的李家有鮮卑血統,他們透過婚姻促使漢族與遊牧民族不斷融合,產生了與農業社會不同的生命情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