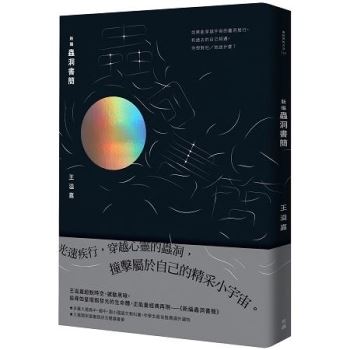鏡裡朱顏
M:
「這就是我嗎?」
你說你最近常在深夜攬鏡自照,如此自問,並感到迷惘。
希臘神話中的納西瑟斯(Narcissus),看到自己在水中的倒影,出神凝視,竟至愛上了自己。你說你是有點納西瑟斯,但又不那麼納西瑟斯,你沒那麼自戀,更不想成為水仙花。
你說你的眉毛雖然英挺,卻有點誇張;眼睛雖然清澈,卻有點空洞;嘴唇雖然紅潤,卻有點薄弱。在你那稚氣的優美中,你看到的是稚氣多於優美。
「這不是我想要的我。」你對鏡徬徨,你凝視鏡子,希望再造一個更令自己滿意的「我」。
攬鏡自照,是一種奇妙的體驗。面對鏡中那個影像,總是讓人想起「我是誰?」這個惱人的問題。
「我是誰?」當你對鏡猜疑時,我想你在意的並不是你叫M、是一個學生這類的身分,或是眉毛、眼睛、唇角所組成的形體,而是某些內在的特質、信念、期待、抱負、興趣等等,也就是你思想、意識、情感和記憶的主體,一種被稱為「靈魂」或「自我」的東西。
鏡子,不僅讓我們看清自己的形貌,而且想起形貌背後的靈魂或自我。
我們忍不住想對鏡裝扮。只是有些人想裝扮他的形貌,而有些人想裝扮他的靈魂。不管是裝扮自己的形貌或靈魂,我們都因鏡子而成為一名演員。
現在終於輪到你在塵世這個舞台登場演出的時刻。
如果你想裝扮自己的形貌,你可能需要更大的鏡子、更多的燈光;但如果你想裝扮自己的靈魂,我勸你最好將眼光從手中的鏡子挪開,到其他地方去尋找你需要的鏡子。
「以銅為鏡」不如「以人為鏡」。
在這齣即將由你擔綱演出的人生之戲裡,你要演出什麼角色,雖然由你自己決定;劇本也有賴你自己去編寫;但如果你想要有精采而漂亮的演出,那你也許應該先參考一下前人的戲碼。在古今中外的舞台上,有過多少可歌可泣可感的角色和劇本,它們都可以是你的鏡子。
其實,你也是一面鏡子。你彷彿「手中青銅鏡,照我少年時」,讓我想起年輕時候的自己,想起自己曾經有過的夢想、徬徨、執著與猜疑。「風雲入世多,日月擲人急;如何一少年,忽忽已四十?」聽到你對鏡猜疑的心聲,讓我興起無限的感慨。
在你即將登場演出的時候,我這個過來人也許可以提供你一些鏡子——一些我覺得不錯的角色和劇本,不是要你照單全收,依樣畫葫蘆,而是從中篩選適合裝扮你靈魂的顏料,擷取編寫你演出劇本的靈感。
W上小我與大我的追尋
M:
自我追尋有兩個層次:一是「小我的追尋」,具有私人性質的生命演出;一是「大我的追尋」,將個人融入更大的社會╱歷史╱文化劇場裡的追尋。
我在前面說過,印度聖雄甘地年輕時候到英國留學,學成後,到印度人嚮往的移民天堂─南非,當一名律師,過著相當西化的優渥生活。
他憑著個人的聰明才智,輕而易舉地就擺脫了他多數同胞的不幸命運,實現了他早年的人生目標。但他還是經常感到空虛與苦悶。
有一次在南非,他不顧朋友的忠言,買了頭等廂的車票搭乘火車旅行,結果因為白種乘客的抗議,而被查票員「請到」貨車廂去。甘地據理力爭,但這不是「錢」的問題,而是「膚色」的問題;最後,甘地連人帶行李被「推出」車外,孤獨地站在灰暗而陌生的驛站,看著「文明列車」發出亢奮的鳴聲,無情而決然地棄他而去。
這次的慘痛經驗及隨後的一些事,使他終於明白,不管他賺多少錢、英語說得多溜,他都只是「失根的蘭花」,都無法改變他是一個受歧視的印度人的事實,而這也是他在小有成就後,依然感到空虛與苦悶的真正原因,因為他到此為止的人生,雖然亮麗,但卻和他所屬的社會╱歷史╱文化布景不搭調。
在痛定思痛之餘,甘地放棄了獨善其身的「小我的追尋」,開始另一輪的「大我的追尋」——回到他所屬的社會中,重拾被他所淡忘的歷史和文化,並領導他的同胞,對抗英國的殖民統治。
這種「大我的追尋」,不僅使甘地的生命有了明確的歸屬和更踏實的意義,為印度和他自己創造新的歷史,同時也為日後的印度人提供了一個比較光采的社會╱歷史╱文化舞台。
同樣的道理,李遠哲在獲得諾貝爾化學獎後,毅然放棄在美國的優渥待遇和更上層樓的科學研究,回到故鄉台灣從事艱辛、吃力不討好的行政及教育改革工作,也是以「大我的追尋」來取代過去「小我的追尋」。因為他希望除了自己成長外,他所屬的社會和同胞也能跟著成長;他希望為後人提供一個更理想的社會╱歷史╱文化舞台。
你還年輕,才準備開始「小我的追尋」而已,現在跟你說這些也許言之過早,不過希望你了解,一個人應該在「大我的脈絡」裡從事「小我的追尋」,才會有比較踏實的感覺。自我的追尋是綿延不絕的,它並非從你開始,更並非到你就結束。前人的追尋不僅提供你人生的「劇本」,更搭建了供你演出的社會╱歷史╱文化舞台;而你和時下眾人的演出,也將為後人提供類似的劇本和舞台。對你所置身的這個舞台,不管你是滿意還是抱怨,它都是你必須認同與珍惜的舞台。但願你和所有的新新人類在接下來的日子裡能搭起更亮麗的舞台,而不是把前人辛苦建立起來的舞台弄糟了、弄垮了。
W上
M:
「這就是我嗎?」
你說你最近常在深夜攬鏡自照,如此自問,並感到迷惘。
希臘神話中的納西瑟斯(Narcissus),看到自己在水中的倒影,出神凝視,竟至愛上了自己。你說你是有點納西瑟斯,但又不那麼納西瑟斯,你沒那麼自戀,更不想成為水仙花。
你說你的眉毛雖然英挺,卻有點誇張;眼睛雖然清澈,卻有點空洞;嘴唇雖然紅潤,卻有點薄弱。在你那稚氣的優美中,你看到的是稚氣多於優美。
「這不是我想要的我。」你對鏡徬徨,你凝視鏡子,希望再造一個更令自己滿意的「我」。
攬鏡自照,是一種奇妙的體驗。面對鏡中那個影像,總是讓人想起「我是誰?」這個惱人的問題。
「我是誰?」當你對鏡猜疑時,我想你在意的並不是你叫M、是一個學生這類的身分,或是眉毛、眼睛、唇角所組成的形體,而是某些內在的特質、信念、期待、抱負、興趣等等,也就是你思想、意識、情感和記憶的主體,一種被稱為「靈魂」或「自我」的東西。
鏡子,不僅讓我們看清自己的形貌,而且想起形貌背後的靈魂或自我。
我們忍不住想對鏡裝扮。只是有些人想裝扮他的形貌,而有些人想裝扮他的靈魂。不管是裝扮自己的形貌或靈魂,我們都因鏡子而成為一名演員。
現在終於輪到你在塵世這個舞台登場演出的時刻。
如果你想裝扮自己的形貌,你可能需要更大的鏡子、更多的燈光;但如果你想裝扮自己的靈魂,我勸你最好將眼光從手中的鏡子挪開,到其他地方去尋找你需要的鏡子。
「以銅為鏡」不如「以人為鏡」。
在這齣即將由你擔綱演出的人生之戲裡,你要演出什麼角色,雖然由你自己決定;劇本也有賴你自己去編寫;但如果你想要有精采而漂亮的演出,那你也許應該先參考一下前人的戲碼。在古今中外的舞台上,有過多少可歌可泣可感的角色和劇本,它們都可以是你的鏡子。
其實,你也是一面鏡子。你彷彿「手中青銅鏡,照我少年時」,讓我想起年輕時候的自己,想起自己曾經有過的夢想、徬徨、執著與猜疑。「風雲入世多,日月擲人急;如何一少年,忽忽已四十?」聽到你對鏡猜疑的心聲,讓我興起無限的感慨。
在你即將登場演出的時候,我這個過來人也許可以提供你一些鏡子——一些我覺得不錯的角色和劇本,不是要你照單全收,依樣畫葫蘆,而是從中篩選適合裝扮你靈魂的顏料,擷取編寫你演出劇本的靈感。
W上小我與大我的追尋
M:
自我追尋有兩個層次:一是「小我的追尋」,具有私人性質的生命演出;一是「大我的追尋」,將個人融入更大的社會╱歷史╱文化劇場裡的追尋。
我在前面說過,印度聖雄甘地年輕時候到英國留學,學成後,到印度人嚮往的移民天堂─南非,當一名律師,過著相當西化的優渥生活。
他憑著個人的聰明才智,輕而易舉地就擺脫了他多數同胞的不幸命運,實現了他早年的人生目標。但他還是經常感到空虛與苦悶。
有一次在南非,他不顧朋友的忠言,買了頭等廂的車票搭乘火車旅行,結果因為白種乘客的抗議,而被查票員「請到」貨車廂去。甘地據理力爭,但這不是「錢」的問題,而是「膚色」的問題;最後,甘地連人帶行李被「推出」車外,孤獨地站在灰暗而陌生的驛站,看著「文明列車」發出亢奮的鳴聲,無情而決然地棄他而去。
這次的慘痛經驗及隨後的一些事,使他終於明白,不管他賺多少錢、英語說得多溜,他都只是「失根的蘭花」,都無法改變他是一個受歧視的印度人的事實,而這也是他在小有成就後,依然感到空虛與苦悶的真正原因,因為他到此為止的人生,雖然亮麗,但卻和他所屬的社會╱歷史╱文化布景不搭調。
在痛定思痛之餘,甘地放棄了獨善其身的「小我的追尋」,開始另一輪的「大我的追尋」——回到他所屬的社會中,重拾被他所淡忘的歷史和文化,並領導他的同胞,對抗英國的殖民統治。
這種「大我的追尋」,不僅使甘地的生命有了明確的歸屬和更踏實的意義,為印度和他自己創造新的歷史,同時也為日後的印度人提供了一個比較光采的社會╱歷史╱文化舞台。
同樣的道理,李遠哲在獲得諾貝爾化學獎後,毅然放棄在美國的優渥待遇和更上層樓的科學研究,回到故鄉台灣從事艱辛、吃力不討好的行政及教育改革工作,也是以「大我的追尋」來取代過去「小我的追尋」。因為他希望除了自己成長外,他所屬的社會和同胞也能跟著成長;他希望為後人提供一個更理想的社會╱歷史╱文化舞台。
你還年輕,才準備開始「小我的追尋」而已,現在跟你說這些也許言之過早,不過希望你了解,一個人應該在「大我的脈絡」裡從事「小我的追尋」,才會有比較踏實的感覺。自我的追尋是綿延不絕的,它並非從你開始,更並非到你就結束。前人的追尋不僅提供你人生的「劇本」,更搭建了供你演出的社會╱歷史╱文化舞台;而你和時下眾人的演出,也將為後人提供類似的劇本和舞台。對你所置身的這個舞台,不管你是滿意還是抱怨,它都是你必須認同與珍惜的舞台。但願你和所有的新新人類在接下來的日子裡能搭起更亮麗的舞台,而不是把前人辛苦建立起來的舞台弄糟了、弄垮了。
W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