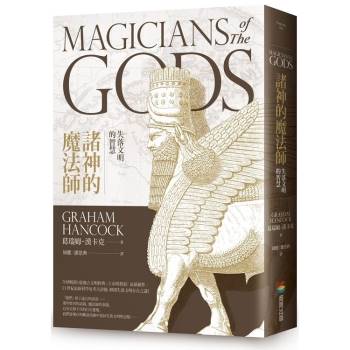第一章
神祕的哥貝克力石陣
哥貝克力石陣是目前為止全球任何地方所發現的雄偉建築之中,最古老的遺跡,或至少是考古學家所接受的最古老的遺跡。
它的體積非常龐大。
令人畏懼的、壯麗的、神祕的和難以抗拒的……很不幸地,這些形容詞都不足以評斷它。在最後的幾個小時,我和發掘者克勞斯‧許密特教授圍繞著遺址漫步。但坦白說,我感到很困惑。
我問他:「做為發現神廟並改寫歷史的人,感覺如何?」這位面色紅潤的德國考古學家,擁有寬大厚實的胸膛和灰色鬍鬚,他身穿褪色的牛仔褲、藍色斜紋粗棉布衫,袖子上有一些泥巴痕跡,光著腳穿著磨破的涼鞋。時值二○一三年九月,正是在他六十歲生日前的三個月,出乎我們意外的是,不到一年他即將離世。
他一邊思索我的問題,一邊擦拭前額閃閃發光的汗滴。雖然是上午中段,但土耳其東南方的安那托利亞(Anatolia)地區,太陽高掛,天空晴朗,我們所站立的托魯斯(Taurus)山脈的山脊上,熱得像烤箱。那裡沒有微風,甚至連一點氣息也沒有,任何可遮蔭之處均付之闕如。在二○一四年將建造頂蓋以覆蓋和保護遺址,但在二○一三年此刻,這裡只有建好的地基。我們站在木造的步道上,在我們的腳下,是一系列半地下的環狀物,圍牆環繞著數十根巨大T形石柱。從德國考古研究所來的許密特及其團隊,使這片遺址重見光明。在他們開始工作之前,這片遺址呈現圓形山丘的外貌。事實上,「哥貝克力石陣」亦即「肚臍之丘」(Hill of the Navel),有時亦譯為「大肚丘」(Potbelly Hill)。挖掘工作改變了許多原始的輪廓。
「嚴格來講,我們不能說哥貝克力石陣是一座神廟。」許密特終於回答,很明顯地用詞謹慎,「且讓我們稱呼它是一座山丘聖城。我不能說會改寫歷史,而是對現存的歷史增加一篇重要的章節。我們認為從獵食採集者到農夫的變遷過程很緩慢,是一步一步地進展。但現在出乎意料的是,在這樣的時期,這令人興奮的遺跡被建造了出來。」
「令人興奮的不只是遺跡。」我立刻回應,「起初當地的居民是獵食採集者,那裡並無農業發展的跡象。」
「沒有。」許密特承認。他在這片環形立柱上豪爽地比劃著。「但那些來到哥貝克力石陣,並且做了這些工程的人,『發明』了農業!所以,我們目睹這裡所發生的一切,和後來依賴農業而出現的新石器時代社會之間的關聯。」
我豎起耳朵聆聽「發明」這個詞彙。我希望我能正確地解讀。我強調,「所以,你的意思是建造哥貝克力石陣的人,『發明』了農業嗎?」
「對。是的。」
「你能詳細說明嗎?」
「因為在這個區域早已馴養動物和種植植物,都是在這裡完成的。所以他們是同一群人。」
「所以在你看來,這是世界上最初,也是最古老的農業嗎?」
「對。是全世界最早的。」
我感覺針對此一觀點的探討方式,許密特已有些不耐煩。但我有我的理由。從哥貝克力石陣地區的挖掘看來,已知年代有一萬兩千年之久(根據正統的編年表),比任何地方的任何巨石建築都還早六千年,例如馬爾他(Malta)的詹蒂亞(Ggantija)神廟和姆納德拉(Mnajdra)神廟、英格蘭的巨石陣(Stonehenge)和艾維柏瑞(Avebury)巨石圈,或埃及吉薩(Giza)的金字塔群。這些遺址皆是屬於被考古學家稱為「新石器時代」人類文明的演化階段,當時農業與社會組織逐漸形成,階級組織亦有良好的進步,技術熟練的專家出現,不需要去生產本身所需的糧食,因為他們會從農夫多餘的生產得到支援。相反的,哥貝克力石陣屬於「舊石器時代」的晚期,當時我們的祖先還是遊牧的獵食採集者,過著小型遷徙的族群生活,無法從事長期的耕作、複雜的勞力分工和高層次的管理技巧。
許密特和我站在可俯視C圍場及D圍場步道的要衝上,從我的研究背景中,我注意到列柱之中有一根上面有著引人深思的雕像。我企圖得到這位考古學家的允許爬上D圍場,以便近距離觀察這個雕像,好掌握關於農業起源和巨石建築之間關係的觀點。四個主要的挖掘坑中,最大的在C圍場,由兩根巨大的中央立柱主導,但已破損。原來應高達六公尺(二十呎),重達二十公噸。此外,還被十多根沒入土牆的立柱圍繞。這些立柱稍微矮小,但仍然非常巨大。D圍場亦是如此,同樣有較小的立柱圍繞著兩根高聳的中央立柱,均完整無缺。頂端呈T形,角度稍微向前傾斜,此外並無特別之處,但卻讓人連想到巨大的人頭,柱子上一些淡淡的輪廓加深了此一印象──側面有肘部彎曲的手臂,向下延伸至精心雕刻的人類手掌和細長手指。
我說:「所有這些巨石、人物肖像、遺址的總體概念和設計……老實說是個偉大的計畫,就像英格蘭的巨石陣,然而巨石陣非常年輕。你在哥貝克力石陣的發現,符合你對於獵食採集者社會的概念嗎?」
許密特同意道,「這裡的組織超乎我們的想像,我們在此所見的獵食採集者,很明顯地有勞力分配,因為巨石的工作乃專家所為,並非每個人都能做的事。他們還能搬運這些巨大的石頭,並將其豎立,這代表他們必須擁有某些工程方面的知識,我們不能期待這是獵食採集者能做到的。這真的是最早的建築,而且有不朽的規模。」
「所以,如果我的理解沒錯,許密特教授,你的意思是我們所站的地方,不只有偉大的建築,農業也已發明。」
「對,沒錯。」
「然而你在此地並未目睹任何真正的革命性變化?你看到的過程能置入現存的歷史架構中嗎?」
「是的,可以置入現存的歷史中。而且這段過程出乎意料地令人非常興奮。尤其是我們在哥貝克力石陣發現的東西,更多是屬於獵食採集者社會,而不是農業社會。這個時期是在獵食採集者的末期,但新石器時代尚未開始。」
「然而它是個變遷的時期,一個尖峰時刻。或許還不止於此?從我們的對話中,以及從你今天早上向我展示的遺址中,我得到一些想法,即哥貝克力石陣是一個先史時代的智囊團或創新中心,也許是居民當中的菁英分子在掌控。你同意此種看法嗎?」
「是的,是的。這是個聚會的場所。人們在此聚集,而且毫無疑問地,這是個傳佈知識和發明的舞台。」
「包括大規模石材加工的知識和農業的知識。你是否敢大膽揣測掌控這個場所和傳播這些思想的人是祭司?」
「不管他們是誰,他們不僅僅會施行簡單的薩滿教(Shamanism),更像是在遵循一種習俗。所以,是的,他們正朝著成為神職人員的方向發展。」
「一千多年以來,人們一直在使用哥貝克力石陣,這是否會變成一種帶有自身習俗的持續性文化呢?掌握此一場所的人,也在此時期持有相同思想和相同的『祭司制度』?」
「沒錯。但奇怪的是,隨著幾個世紀的逝去,過去的努力有很明顯的衰退。真正不朽的建築位在較古老的岩層;在年輕的岩層建築反而變得愈來愈小,品質上有很明顯地下滑。」
「所以,最古老的是最好的嗎?」
「是的,最古老的是最好的。」
「你不覺得這令人費解嗎?」
許密特看上去有些歉意。「我們希望最後能發現更古老的岩層,能看到期待卻尚未找到的微小起點。然後會看到不朽的階段,再來是再次衰敗的部分。」
我突然發覺,許密特教授剛才所說的話中,「希望」是最關鍵的詞句。我們習慣於從小而簡單的事物開始,然後進步,發展,成為更複雜和更考究的事物,所以這自然是在考古遺跡中所預期能找到的。但當我們面對像哥貝克力石陣的例子──一開始時便非常完美,然後傳承緩慢,直到成為早期自我衰弱的影子──這顛覆了我們精心建構的文明應該如何表現的概念,以及它們是如何成熟和發展的。我們並不反對文明退化的過程。文明會式微。看看羅馬帝國或大英帝國就知道了。
就像雅典娜從宙斯的額頭全副武裝且成熟地出生,哥貝克力石陣的問題在於,在遠古時突然出現,就已呈現出一種成熟的文明,在誕生之初,便「發明」了農業和紀念性的建築。
考古學無法進一步解釋,為何古埃及最早的紀念碑、藝術、雕塑、象形文字、數學、醫學、天文學和建築在早期就很完美,並無從簡單到複雜的痕跡。我們可對哥貝克力石陣發出疑問,如同我的朋友約翰‧安東尼‧韋斯特(John Anthony West)這樣問古埃及:
一種複雜的文明是如何發展成熟的?看看一九○五年的汽車,將它跟現代的汽車相比,「發展」的過程並沒有錯誤。但在埃及沒有相似之處,那裡的一切在一開始就很成熟。
此一奧祕的答案顯而易見。但是,因為當代主流思想排斥,所以不被考慮。即埃及文明並非是一種「發展」,而是遺產。
那麼在哥貝克力石陣,是否亦如此?
關於此一失落文明是所有後來已知文明起源的想法,許密特無暇思考。所以當我向他施壓時,他只是重複他的觀點,即哥貝克力石陣的許多遺址還未挖掘出來。「我說了,」他有些不耐煩地吼著,「等我們發掘出更早的遺址時,就能找到演化的證據了。」
他可能是正確的。哥貝克力石陣在很多方面讓人震驚,其中一點便是,當許密特在二○一三年帶我參觀遺址時,人們已經持續十八年的挖掘工作,而大部分仍然埋藏在地下。
但到底有多大?
「很難說。」許密特告訴我,「我們進行地質探勘,透過透地雷達,從這裡能看到至少還有十六處尚未挖掘的大型圍場。」
我問,「大型圍場?」我指向D圍場中高聳的巨石,「像這個嗎?」「是的,就像這個。至少有十六處。有些地區地質探勘無法提供完整的答案,我們也無法真正看清裡面,但預計會超過十六處。可能最後的實際數字會翻倍,甚至多達五十處。」
「五十處!」
「是的,五十處大型圍場,每個圍場有十四根或更多的石柱。但是,你知道,我們的目標並非挖出所有的東西,只要挖出一小部分就好。因為挖掘就是破壞。我們想讓大部分的遺址原封不動。」
思考古人建造哥貝克力石陣的規模,是需要豐富的想像力。這裡不僅挖掘出排成環狀的巨石柱,比其他世界上任何地區已知的巨石遺址還古老六千年,我現在也瞭解到,哥貝克力石陣非常巨大,它所占的地區可能最後將被證明,是一處比其他大型遺址,例如巨石陣,還要大三十倍的範圍。
換句話說,我們面對的是一個廣大和令人費解的古蹟,規模龐大和不為人知的目的,一切都是來源不明的未解之謎,沒有明顯的背景或鋪陳,完全籠罩在神祕之中。
巨人的圍場
我已經習慣當我出現在考古學家們的挖掘現場時,他們在背後鄙視我。但許密特的態度令人耳目一新,儘管他很清楚知道我的一切。他同意讓我和我的攝影師妻子桑莎‧法伊亞一起爬下D圍場,並研究它。哥貝克力石陣已被挖掘的所有四個主圍場,在有人看管之下,嚴格禁止人們進入,但我需要近距離觀察D圍場中一根石柱上的一幅圖像,只在步道上是無法觀察的。我在步道上怎麼也無法看到,所以許密特的慷慨令人感激。
我們沿著一塊木板進入圍場,木板通往一個兩公尺高,尚未挖掘的碎石堆,碎石堆將兩根中央的立柱分隔,一在東一在西。立柱是從這個地區非常堅硬的結晶狀石灰石場採集得來,經過完美的拋光處理,巨大的立柱在陽光下發出柔和的金光。我從許密特教授那裡得知,那些立柱高約五點五公尺(十八呎),重量超過十五公噸。爬下圍場的地面時,我注意到立柱均立在約二十公分(八吋)高的石質基石上,這些基石是直接從原有的岩床上雕刻而成。在東側立柱的基石前緣,有一列七隻看起來不會飛的鳥,尾巴下垂,翅膀並不明顯的高處浮雕。
兩根巨大的立柱有極具風格的人形外觀,又被傾斜的T形「頭部」所強化,彷彿是一對雙胞胎巨人隱約俯視著我。雖然它們不是我最初的目標,我還是把握機會仔細地檢驗它們。
立柱的前面邊緣,呈現的是它們的胸膛和腹部,非常纖細,只有大約二十公分寬,它們腰部的前後距離超過一公尺(大約四呎)。正如我從步道上觀察到的,兩座石柱的雕刻,側面都有手臂的浮雕,肘部彎曲,末端有著細長的手指。這些手指環繞到立柱的前方,幾乎在「肚子」處相會。
在手的上方,有開襟袍子的痕跡覆蓋著「胸膛」。而在手的下面,兩座人像穿戴著寬腰帶,也是浮雕,裝飾著獨特的扣環。似乎是某種動物的皮。許密特認為是狐狸從後腿到尾巴的毛皮,從扣環處懸掛下來以遮蔽生殖器官。
兩座人像均配戴項鍊。東邊的立柱上,項鍊裝飾著新月和盤形圖案,西邊的立柱上,則裝飾著一顆牛頭。
此外,兩根立柱以完全相同的獨特方式豎立在各自的底座上,但並非牢固地嵌在上面,而是不穩定地固定在僅僅十公分(四吋)深的溝槽裡。許密特及其團隊已使用木質的支柱使其穩固,我只能想像他們不得不像古人一樣,將石柱扶正。除非,在圍場的上方有一個框架,石像的頭部才能放進去予以固定。以前哥貝克力石陣的建造者,很明顯地是建造、移動和放置巨大石陣的專家,他們不選擇雕刻出更深的溝槽讓柱子牢牢地站穩,這必然有某些目的,但我無法洞察。
兩根中央立柱的相似處就是這些,但也有一些差異。例如,在東邊石柱的右側,有一隻與實物大小一樣的高凸浮雕的狐狸,看似要從手肘的彎曲處躍向前方。然而,西邊石柱的腰帶除扣環之外,並無其他裝飾;東邊石柱的腰帶上有一些引人好奇的裝飾,包括一連串像羅馬字母「C」的圖形文字,其他的則像羅馬字母「H」。當我研究它們時連想到,我們不可能知道這些符號對哥貝克力石陣的人有何意義,我們與他們相隔長達一萬一千多年的距離,難以想像他們擁有任何形式的書寫,更遑論我們現在所使用的字母!儘管這些符號的排列方式,奇特地具有現代性和目的性,對我們而言不僅僅是裝飾而已。在上古舊石器時代藝術的世界,沒有任何地方有跟其類似的存在,那些動物和鳥類的圖案亦如此。在這個早期的階段,巨石和複雜雕刻的結合是絕對獨特和前所未有。
神祕的哥貝克力石陣
哥貝克力石陣是目前為止全球任何地方所發現的雄偉建築之中,最古老的遺跡,或至少是考古學家所接受的最古老的遺跡。
它的體積非常龐大。
令人畏懼的、壯麗的、神祕的和難以抗拒的……很不幸地,這些形容詞都不足以評斷它。在最後的幾個小時,我和發掘者克勞斯‧許密特教授圍繞著遺址漫步。但坦白說,我感到很困惑。
我問他:「做為發現神廟並改寫歷史的人,感覺如何?」這位面色紅潤的德國考古學家,擁有寬大厚實的胸膛和灰色鬍鬚,他身穿褪色的牛仔褲、藍色斜紋粗棉布衫,袖子上有一些泥巴痕跡,光著腳穿著磨破的涼鞋。時值二○一三年九月,正是在他六十歲生日前的三個月,出乎我們意外的是,不到一年他即將離世。
他一邊思索我的問題,一邊擦拭前額閃閃發光的汗滴。雖然是上午中段,但土耳其東南方的安那托利亞(Anatolia)地區,太陽高掛,天空晴朗,我們所站立的托魯斯(Taurus)山脈的山脊上,熱得像烤箱。那裡沒有微風,甚至連一點氣息也沒有,任何可遮蔭之處均付之闕如。在二○一四年將建造頂蓋以覆蓋和保護遺址,但在二○一三年此刻,這裡只有建好的地基。我們站在木造的步道上,在我們的腳下,是一系列半地下的環狀物,圍牆環繞著數十根巨大T形石柱。從德國考古研究所來的許密特及其團隊,使這片遺址重見光明。在他們開始工作之前,這片遺址呈現圓形山丘的外貌。事實上,「哥貝克力石陣」亦即「肚臍之丘」(Hill of the Navel),有時亦譯為「大肚丘」(Potbelly Hill)。挖掘工作改變了許多原始的輪廓。
「嚴格來講,我們不能說哥貝克力石陣是一座神廟。」許密特終於回答,很明顯地用詞謹慎,「且讓我們稱呼它是一座山丘聖城。我不能說會改寫歷史,而是對現存的歷史增加一篇重要的章節。我們認為從獵食採集者到農夫的變遷過程很緩慢,是一步一步地進展。但現在出乎意料的是,在這樣的時期,這令人興奮的遺跡被建造了出來。」
「令人興奮的不只是遺跡。」我立刻回應,「起初當地的居民是獵食採集者,那裡並無農業發展的跡象。」
「沒有。」許密特承認。他在這片環形立柱上豪爽地比劃著。「但那些來到哥貝克力石陣,並且做了這些工程的人,『發明』了農業!所以,我們目睹這裡所發生的一切,和後來依賴農業而出現的新石器時代社會之間的關聯。」
我豎起耳朵聆聽「發明」這個詞彙。我希望我能正確地解讀。我強調,「所以,你的意思是建造哥貝克力石陣的人,『發明』了農業嗎?」
「對。是的。」
「你能詳細說明嗎?」
「因為在這個區域早已馴養動物和種植植物,都是在這裡完成的。所以他們是同一群人。」
「所以在你看來,這是世界上最初,也是最古老的農業嗎?」
「對。是全世界最早的。」
我感覺針對此一觀點的探討方式,許密特已有些不耐煩。但我有我的理由。從哥貝克力石陣地區的挖掘看來,已知年代有一萬兩千年之久(根據正統的編年表),比任何地方的任何巨石建築都還早六千年,例如馬爾他(Malta)的詹蒂亞(Ggantija)神廟和姆納德拉(Mnajdra)神廟、英格蘭的巨石陣(Stonehenge)和艾維柏瑞(Avebury)巨石圈,或埃及吉薩(Giza)的金字塔群。這些遺址皆是屬於被考古學家稱為「新石器時代」人類文明的演化階段,當時農業與社會組織逐漸形成,階級組織亦有良好的進步,技術熟練的專家出現,不需要去生產本身所需的糧食,因為他們會從農夫多餘的生產得到支援。相反的,哥貝克力石陣屬於「舊石器時代」的晚期,當時我們的祖先還是遊牧的獵食採集者,過著小型遷徙的族群生活,無法從事長期的耕作、複雜的勞力分工和高層次的管理技巧。
許密特和我站在可俯視C圍場及D圍場步道的要衝上,從我的研究背景中,我注意到列柱之中有一根上面有著引人深思的雕像。我企圖得到這位考古學家的允許爬上D圍場,以便近距離觀察這個雕像,好掌握關於農業起源和巨石建築之間關係的觀點。四個主要的挖掘坑中,最大的在C圍場,由兩根巨大的中央立柱主導,但已破損。原來應高達六公尺(二十呎),重達二十公噸。此外,還被十多根沒入土牆的立柱圍繞。這些立柱稍微矮小,但仍然非常巨大。D圍場亦是如此,同樣有較小的立柱圍繞著兩根高聳的中央立柱,均完整無缺。頂端呈T形,角度稍微向前傾斜,此外並無特別之處,但卻讓人連想到巨大的人頭,柱子上一些淡淡的輪廓加深了此一印象──側面有肘部彎曲的手臂,向下延伸至精心雕刻的人類手掌和細長手指。
我說:「所有這些巨石、人物肖像、遺址的總體概念和設計……老實說是個偉大的計畫,就像英格蘭的巨石陣,然而巨石陣非常年輕。你在哥貝克力石陣的發現,符合你對於獵食採集者社會的概念嗎?」
許密特同意道,「這裡的組織超乎我們的想像,我們在此所見的獵食採集者,很明顯地有勞力分配,因為巨石的工作乃專家所為,並非每個人都能做的事。他們還能搬運這些巨大的石頭,並將其豎立,這代表他們必須擁有某些工程方面的知識,我們不能期待這是獵食採集者能做到的。這真的是最早的建築,而且有不朽的規模。」
「所以,如果我的理解沒錯,許密特教授,你的意思是我們所站的地方,不只有偉大的建築,農業也已發明。」
「對,沒錯。」
「然而你在此地並未目睹任何真正的革命性變化?你看到的過程能置入現存的歷史架構中嗎?」
「是的,可以置入現存的歷史中。而且這段過程出乎意料地令人非常興奮。尤其是我們在哥貝克力石陣發現的東西,更多是屬於獵食採集者社會,而不是農業社會。這個時期是在獵食採集者的末期,但新石器時代尚未開始。」
「然而它是個變遷的時期,一個尖峰時刻。或許還不止於此?從我們的對話中,以及從你今天早上向我展示的遺址中,我得到一些想法,即哥貝克力石陣是一個先史時代的智囊團或創新中心,也許是居民當中的菁英分子在掌控。你同意此種看法嗎?」
「是的,是的。這是個聚會的場所。人們在此聚集,而且毫無疑問地,這是個傳佈知識和發明的舞台。」
「包括大規模石材加工的知識和農業的知識。你是否敢大膽揣測掌控這個場所和傳播這些思想的人是祭司?」
「不管他們是誰,他們不僅僅會施行簡單的薩滿教(Shamanism),更像是在遵循一種習俗。所以,是的,他們正朝著成為神職人員的方向發展。」
「一千多年以來,人們一直在使用哥貝克力石陣,這是否會變成一種帶有自身習俗的持續性文化呢?掌握此一場所的人,也在此時期持有相同思想和相同的『祭司制度』?」
「沒錯。但奇怪的是,隨著幾個世紀的逝去,過去的努力有很明顯的衰退。真正不朽的建築位在較古老的岩層;在年輕的岩層建築反而變得愈來愈小,品質上有很明顯地下滑。」
「所以,最古老的是最好的嗎?」
「是的,最古老的是最好的。」
「你不覺得這令人費解嗎?」
許密特看上去有些歉意。「我們希望最後能發現更古老的岩層,能看到期待卻尚未找到的微小起點。然後會看到不朽的階段,再來是再次衰敗的部分。」
我突然發覺,許密特教授剛才所說的話中,「希望」是最關鍵的詞句。我們習慣於從小而簡單的事物開始,然後進步,發展,成為更複雜和更考究的事物,所以這自然是在考古遺跡中所預期能找到的。但當我們面對像哥貝克力石陣的例子──一開始時便非常完美,然後傳承緩慢,直到成為早期自我衰弱的影子──這顛覆了我們精心建構的文明應該如何表現的概念,以及它們是如何成熟和發展的。我們並不反對文明退化的過程。文明會式微。看看羅馬帝國或大英帝國就知道了。
就像雅典娜從宙斯的額頭全副武裝且成熟地出生,哥貝克力石陣的問題在於,在遠古時突然出現,就已呈現出一種成熟的文明,在誕生之初,便「發明」了農業和紀念性的建築。
考古學無法進一步解釋,為何古埃及最早的紀念碑、藝術、雕塑、象形文字、數學、醫學、天文學和建築在早期就很完美,並無從簡單到複雜的痕跡。我們可對哥貝克力石陣發出疑問,如同我的朋友約翰‧安東尼‧韋斯特(John Anthony West)這樣問古埃及:
一種複雜的文明是如何發展成熟的?看看一九○五年的汽車,將它跟現代的汽車相比,「發展」的過程並沒有錯誤。但在埃及沒有相似之處,那裡的一切在一開始就很成熟。
此一奧祕的答案顯而易見。但是,因為當代主流思想排斥,所以不被考慮。即埃及文明並非是一種「發展」,而是遺產。
那麼在哥貝克力石陣,是否亦如此?
關於此一失落文明是所有後來已知文明起源的想法,許密特無暇思考。所以當我向他施壓時,他只是重複他的觀點,即哥貝克力石陣的許多遺址還未挖掘出來。「我說了,」他有些不耐煩地吼著,「等我們發掘出更早的遺址時,就能找到演化的證據了。」
他可能是正確的。哥貝克力石陣在很多方面讓人震驚,其中一點便是,當許密特在二○一三年帶我參觀遺址時,人們已經持續十八年的挖掘工作,而大部分仍然埋藏在地下。
但到底有多大?
「很難說。」許密特告訴我,「我們進行地質探勘,透過透地雷達,從這裡能看到至少還有十六處尚未挖掘的大型圍場。」
我問,「大型圍場?」我指向D圍場中高聳的巨石,「像這個嗎?」「是的,就像這個。至少有十六處。有些地區地質探勘無法提供完整的答案,我們也無法真正看清裡面,但預計會超過十六處。可能最後的實際數字會翻倍,甚至多達五十處。」
「五十處!」
「是的,五十處大型圍場,每個圍場有十四根或更多的石柱。但是,你知道,我們的目標並非挖出所有的東西,只要挖出一小部分就好。因為挖掘就是破壞。我們想讓大部分的遺址原封不動。」
思考古人建造哥貝克力石陣的規模,是需要豐富的想像力。這裡不僅挖掘出排成環狀的巨石柱,比其他世界上任何地區已知的巨石遺址還古老六千年,我現在也瞭解到,哥貝克力石陣非常巨大,它所占的地區可能最後將被證明,是一處比其他大型遺址,例如巨石陣,還要大三十倍的範圍。
換句話說,我們面對的是一個廣大和令人費解的古蹟,規模龐大和不為人知的目的,一切都是來源不明的未解之謎,沒有明顯的背景或鋪陳,完全籠罩在神祕之中。
巨人的圍場
我已經習慣當我出現在考古學家們的挖掘現場時,他們在背後鄙視我。但許密特的態度令人耳目一新,儘管他很清楚知道我的一切。他同意讓我和我的攝影師妻子桑莎‧法伊亞一起爬下D圍場,並研究它。哥貝克力石陣已被挖掘的所有四個主圍場,在有人看管之下,嚴格禁止人們進入,但我需要近距離觀察D圍場中一根石柱上的一幅圖像,只在步道上是無法觀察的。我在步道上怎麼也無法看到,所以許密特的慷慨令人感激。
我們沿著一塊木板進入圍場,木板通往一個兩公尺高,尚未挖掘的碎石堆,碎石堆將兩根中央的立柱分隔,一在東一在西。立柱是從這個地區非常堅硬的結晶狀石灰石場採集得來,經過完美的拋光處理,巨大的立柱在陽光下發出柔和的金光。我從許密特教授那裡得知,那些立柱高約五點五公尺(十八呎),重量超過十五公噸。爬下圍場的地面時,我注意到立柱均立在約二十公分(八吋)高的石質基石上,這些基石是直接從原有的岩床上雕刻而成。在東側立柱的基石前緣,有一列七隻看起來不會飛的鳥,尾巴下垂,翅膀並不明顯的高處浮雕。
兩根巨大的立柱有極具風格的人形外觀,又被傾斜的T形「頭部」所強化,彷彿是一對雙胞胎巨人隱約俯視著我。雖然它們不是我最初的目標,我還是把握機會仔細地檢驗它們。
立柱的前面邊緣,呈現的是它們的胸膛和腹部,非常纖細,只有大約二十公分寬,它們腰部的前後距離超過一公尺(大約四呎)。正如我從步道上觀察到的,兩座石柱的雕刻,側面都有手臂的浮雕,肘部彎曲,末端有著細長的手指。這些手指環繞到立柱的前方,幾乎在「肚子」處相會。
在手的上方,有開襟袍子的痕跡覆蓋著「胸膛」。而在手的下面,兩座人像穿戴著寬腰帶,也是浮雕,裝飾著獨特的扣環。似乎是某種動物的皮。許密特認為是狐狸從後腿到尾巴的毛皮,從扣環處懸掛下來以遮蔽生殖器官。
兩座人像均配戴項鍊。東邊的立柱上,項鍊裝飾著新月和盤形圖案,西邊的立柱上,則裝飾著一顆牛頭。
此外,兩根立柱以完全相同的獨特方式豎立在各自的底座上,但並非牢固地嵌在上面,而是不穩定地固定在僅僅十公分(四吋)深的溝槽裡。許密特及其團隊已使用木質的支柱使其穩固,我只能想像他們不得不像古人一樣,將石柱扶正。除非,在圍場的上方有一個框架,石像的頭部才能放進去予以固定。以前哥貝克力石陣的建造者,很明顯地是建造、移動和放置巨大石陣的專家,他們不選擇雕刻出更深的溝槽讓柱子牢牢地站穩,這必然有某些目的,但我無法洞察。
兩根中央立柱的相似處就是這些,但也有一些差異。例如,在東邊石柱的右側,有一隻與實物大小一樣的高凸浮雕的狐狸,看似要從手肘的彎曲處躍向前方。然而,西邊石柱的腰帶除扣環之外,並無其他裝飾;東邊石柱的腰帶上有一些引人好奇的裝飾,包括一連串像羅馬字母「C」的圖形文字,其他的則像羅馬字母「H」。當我研究它們時連想到,我們不可能知道這些符號對哥貝克力石陣的人有何意義,我們與他們相隔長達一萬一千多年的距離,難以想像他們擁有任何形式的書寫,更遑論我們現在所使用的字母!儘管這些符號的排列方式,奇特地具有現代性和目的性,對我們而言不僅僅是裝飾而已。在上古舊石器時代藝術的世界,沒有任何地方有跟其類似的存在,那些動物和鳥類的圖案亦如此。在這個早期的階段,巨石和複雜雕刻的結合是絕對獨特和前所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