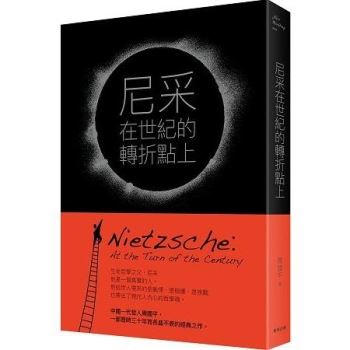看哪,在遠處迎候我們的
是死亡、榮譽和幸福!
──尼采
大自然的星空,群星燦爛。那最早閃現的,未必是最亮的星宿。有的星宿孤獨地燃燒著,熄滅了,很久很久以後,它的光才到達我們的眼睛。
文化和歷史的星空何嘗不是如此?
一顆敏感的心,太早太強烈地感受到了時代潛伏的病痛,發出了痛苦的呼喊。可是,在同時代人聽來,卻好似瘋子的譫語。直到世紀轉換,時代更替,潛伏的病痛露到面上,新一代人才從這瘋子的譫語中聽出了先知的啟示。
一百年以前,這位當時默默無聞的德國哲學家,攜帶一把綠色的小傘,一個筆記本,漂泊於南歐的山巔海濱。他的文字,鍾山水之靈秀,清新而雋永;他的思想,抒內心之焦渴,激烈而唐突。然而,世界幾乎把他遺忘了。直到他生命的最後歲月,他才小有名氣,但也不過是小有名氣而已。
尼采在一首詩中寫道:「誰終將聲震人間,必長久深自緘默;誰終將點燃閃電,必長久如雲漂泊。」
他對他身後的聲譽是充滿信心的:
「我的時代還沒有到來,有的人死後方生。」
「總有一天我會如願以償。這將是很遠的一天,我不能親眼看到了。那時候人們會打開我的書,我會有讀者。我應該為他們寫作。」
二十世紀的序幕剛剛揭開,尼采溘然長逝了。今天,當我們這個世紀也已經接近尾聲的時候,倘若要探溯本世紀西方思潮的源頭,我們發現確實不能撇開尼采。漂泊者早已倒下,他的影子卻籠罩了整整一個時代。有人說,在上個世紀的思想家中,若要舉出兩位對本世紀影響最大的人物,當推馬克思和尼采。的確,他們都不是學院式的哲學家,他們的影響都遠遠超出學術界的小圈子,而震撼了整個西方社會意識。
人們對馬克思已經談論得很多,儘管不乏驚人的誤解,現在,請允許我們稍稍結識一下尼采。
世紀末的漂泊者
人的命運真是不同。許多人終其一生,安居樂業,心安理得地接受環境和時運替他們安排的一切,悠然享其天年。可是,像尼采這樣的人,有著一顆不安的靈魂,總是在苦苦地尋求著什麼,精神上不斷地爆發危機,在動盪中度過了短促的一生。
赫拉克利特說:「一個人的性格就是他的命運。」真的,尼采的個性,注定了他的悲劇性的命運。一八四四年十月十五日,尼采生於德國東部呂采恩鎮附近的勒肯村。他的祖父是一個寫有神學著作的虔誠信徒,父親和外祖父都是牧師。未滿五歲時,父親病死,此後他便在母親和姑母的撫育下度過了童年和少年時代。一八六五年,二十一歲的尼采,在波恩大學攻讀了半年神學和古典語文學之後,斷然決定放棄神學,專修古典語文學。對於一個牧師世家的子弟來說,這不啻是一個反叛的信號,後來他果然成了基督教的死敵──「反基督徒」。與此同時,這個曾經與同學們一起酗酒、浪遊、毆鬥的青年人,突然變得少年老成起來。他退出了學生團體,離群索居,整日神情恍惚,冥思苦想。
這是尼采生涯中發生的第一次精神危機。眼前的一切,這喧鬧的大學生生活,刻板的課程,瑣碎的日常事務,未來的學者生涯,刹時顯得多麼陌生啊。難道人生是一番消遣,或是一場按部就班的課堂考試嗎?他心中醞釀著一種使命感,要為自己尋求更真實的人生。
一八六九年,尼采二十五歲,在李契爾的推薦下,到巴塞爾大學任古典語言學教授。李契爾是一位具有探索者性格和純真熱情的古典語文學學者,先後任教於波恩大學和萊比錫大學,對尼采極為欣賞,始終把他的這位高足帶在身邊。在推薦信裡,他不無誇耀之情地寫道:「三十九年來,我目睹了如此多的新秀,卻還不曾看到一個年輕人像尼采這樣,如此年紀輕輕就如此成熟……我預言,只要上天賜他長壽,他將在德國語言學界名列前茅。」他還把尼采稱作「萊比錫青年語言學界的偶像」,甚至說他是「奇跡」。尼采倒也不負所望,走馬上任,發表題為《荷馬和古典語文學》的就職演說,文質並茂,頓使新同事們嘆服。
也許,這位前程無量的青年學者要安心治他的學問了?
並不!僅僅兩年以後,尼采出版了他的處女作《悲劇的誕生》,這本以全新的眼光研究希臘悲劇起源的小冊子,同時宣告了尼采自己的悲劇生涯的開始。它引起了轟動,既受到熱烈的讚揚,也遭得激烈的攻擊。在正統語文學界看來,一個語文學家不好好地去琢磨柏拉圖古典語言的精妙,卻用什麼酒神精神批判蘇格拉底和柏拉圖,全然是荒誕不經。以青年學者維拉莫維茨為代表的正統語文學家們對尼采展開了激烈批評。尼采發現他的教室空了,不再有學生來聽他的課。尼采嘗到了孤獨的滋味。但是,他有他的「絕妙的慰藉」──叔本華的哲學和華格納的音樂。
還在學生時代,尼采在一家舊書店裡偶然地購得叔本華的《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一書,欣喜若狂,一口氣讀完了。後來他回憶說,當時他漫遊在一個願望的世界裡,夢想找到一位真正的哲學家,能夠把他從時代的缺陷中拯救出來,教他在思想和生活中重新變得單純和誠實,也就是「不合時宜」。正當他懷著如此渴望的時候,他發現了叔本華。他覺得,叔本華就像是特地為他寫了這部著作一樣。
到巴塞爾任教以後,尼采結識了當時卜居羅采恩湖畔的華格納。他經常去拜訪這位浪漫主義音樂大師,在華格納身邊度過了他一生中最愉快的時光。
正是在叔本華和華格納的影響下,尼采寫出了那本得罪德國正統語言學界、斷送自己學術前程的著作。
可是,尼采現在又要否定叔本華和華格納了。他的靈魂注定不得安寧,不斷地摒棄曾經推崇的一切,打碎一切偶像,終於面對空無所有的沙漠。他把自己逼到了沙漠裡。
在回顧自己的人生歷程時,尼采說,「通向智慧之路」有三個必經的階段。第一階段是「合群時期」,崇敬、順從、仿效隨便哪個比自己強的人。第二階段是「沙漠時期」,束縛最牢固的時候,崇敬之心破碎了,自由的精神茁壯生長,一無牽掛,重估一切價值。第三階段是「創造時期」,在否定的基礎上重新進行肯定,然而這肯定不是出於我之上的某個權威,而僅僅是出於我自己,我就是命運,我手中抓著人類的鬮。
一八七六年,尼采生命中的「沙漠時期」開始了。他的精神又一次爆發危機,這次的危機如此深刻,以致他不像前兩次那樣,僅僅同學生團體決裂,僅僅受到德國語文學界的譴責,而是要被整個時代放逐了。
這一年,華格納在德皇威廉一世支持下,在拜洛伊特舉辦聲勢浩大的第一屆音樂節。尼采原先把歐洲文化復興的希望寄託在華格納身上。可是,在拜洛伊特,目睹華格納的「演戲天才」、富裕市民觀眾的庸俗捧場,尼采失望了。他悄悄離開,躲進一片森林,醞釀了一部含蓄批評華格納的書。兩年後,華格納的最後一部歌劇《帕西法爾》的劇本寄到尼采手中,尼采的《人性的,太人性的》一書寄到華格納手中,兩人從此決裂。這一年,尼采與他大學時代最親密的朋友洛德之間也產生了隔閡,導致了後來的破裂。尼采與洛德,同為李契爾教授的高足,可是兩人志趣迥異。洛德脫不開世俗之路,當學生時也有一番雄心,畢業後,逐漸滿足於平穩的學者生涯和小家庭生活,終於不過是一個平庸之輩。尼采卻始終保持著青年時代產生的使命感。靈魂不同,自然就沒有了共同語言。
這一年,尼采向一位荷蘭女子求婚而遭拒絕。後來他儘管一再試圖為自己覓一配偶,均不成功,終於至死未婚。
也在這一年,尼采因健康惡化而停止了在大學授課,三年後辭掉巴塞爾大學教授職務,永遠退出了大學講壇。
決裂,失戀,辭職,這些遭遇似乎偶然地湊到了一起,卻顯示了某種必然的命運。一個精神貧乏、缺乏獨特個性的人,當然不會遭受精神上危機的折磨。可是,對於一個精神需求很高的人來說,危機,即供求關係的某種脫節,卻是不可避免的。他太挑剔了,世上不乏友誼、愛和事業,但不是他要的那一種,他的精神仍然感到饑餓。這樣的人,必須自己來為自己創造精神的食物。
尼采自己說:「當時我所做的抉擇不只是與華格納決裂──我覺得我的本性陷入了一種完全的迷亂,而其中的個別失誤,不管涉及華格納還是涉及巴塞爾的教職,僅是一個徵兆。一種焦躁籠罩了我;我知道是刻不容緩反省自己的時候了。我感到驚恐,一下子看清楚自己浪費了多少時間,──我以古典語文學家為我的全部生存,我的使命,這是多麼無益,多麼草率。我為這種錯誤的謙虛而羞愧……在過去十年裡,我的精神營養徹底停止,我沒有學到任何有用之事,我荒唐地為積滿灰塵的學術破爛而丟掉許多東西。睜著近視眼小心翼翼地爬行在古代詩韻學家腳下——這就是我所做的事情!」
一八七九年,尼采結束了十年教授生涯,從此開始了他的沒有職業、沒有家室、沒有友伴的孤獨的漂泊生涯。這時候的尼采,三十五歲,已過而立之年,精神上成熟了。許多人的所謂成熟,不過是被習俗磨去了棱角,變得世故而實際了。那不是成熟,而是精神的早衰和個性的夭亡。真正的成熟,應當是獨特個性的形成,真實自我的發現,精神上的結果和豐收。「現在我敢於自己來追求智慧,自己來做哲學家;而過去我只是崇敬哲學家們。」「現在我自己在各方面都努力尋求智慧,而過去我只是崇敬和愛慕智慧的人。」尼采不再是一個古典語文學學者,甚至也不再是一個哲學學者,他成長為一個真正的哲學家即一個獨創的哲學家了,因為,倘若沒有獨立的創造,算什麼哲學家呢?
雅斯貝爾斯說:「尼采一生的主要特色是他的脫出常規的生存。他沒有現實生計,沒有職業,沒有生活圈子。他不結婚,不招門徒和弟子,在人世間不營建自己的事務領域。他離鄉背井,到處流浪,似乎在尋找他一直未曾找到的什麼。然而,這種脫出常規的生存本身就是本質的東西,是尼采全部哲學活動的方式。」
事實上,尼采的主要著作,表達了他的基本思想的成熟作品,包括《朝霞》、《快樂的科學》、《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善惡的彼岸》、《道德的譜系》、《偶像的黃昏》以及未完成的《強力意志》,都是在脫出常規的漂泊生涯中寫出的。
問題在於,尼采的思想受孕於歐洲文明瀕臨深刻危機的時代,他的敏感使他對這種危機徵象有格外真切的感受,他的勇敢使他直言不諱,他的真誠又使他不肯言行不一,因而,這個反對一切傳統價值的哲學家,必不可免地要過一種脫出常規的生活。他的哲學思考方式必然要影響到他的實際生活方式。他向傳統的挑戰必然導致他與世俗生活領域的抵觸。他對這種情形是有清醒的認識的:「我必須永遠做一個殉道者,以度過徹底貸出了的一生。」「當一個人要靠作品來批准自己的一生,他在根基上就變得極為苛求了。」「我的境遇與我的生存方式之間的矛盾在於,作為一個哲學家,我必須擺脫職業、女人、孩子、祖國、信仰等等而獲得自由,然而,只要我還是一個幸運地活著的生物,而不是一架純粹的分析機器,我又感到缺乏這一切。」尼采並非一個生性孤僻的人,年復一年的孤獨的漂流也並非一件浪漫的樂事。在難以忍受的孤寂中,尼采一次次發出絕望的悲歎:「我期待一個人,我尋找一個人,我找到的始終是我自己,而我不再期待我自己了!」「現在再沒有人愛我了,我如何還能愛這生命!」「向我傳來的友好的聲音如此之少。如今我孤單極了,不可思議地孤單……成年累月沒有振奮人心的事,沒有一絲人間氣息,沒有一丁點兒愛。」在給妹妹的信中,他情不自禁地談到「那種突然瘋狂的時刻,寂寞的人想要擁抱隨便哪個人」!
友誼,尼采是多麼渴望友誼啊。「你神聖的,友誼!我的最高希望的第一縷晨曦……」
可是,這個害怕孤獨、悲歎孤獨的人,同時又嚮往孤獨,需要孤獨。因為「人與人之間的巨大差距迫使我孤獨」;他感到,在人群中比獨自一人更加孤獨。他不肯降格以求,寧願走到沙漠裡與猛獸一起忍受焦渴,不願與骯髒的趕駱駝人同坐在水槽邊。他把孤獨當作自己的家,並且說:「我需要孤獨,也就是說,需要康復,回到我自己,呼吸自由、輕快、活潑的空氣……我的整部《查拉圖斯特拉》是一曲孤獨之頌歌,或者,如果人們理解了我的意思的話,是一曲潔淨之頌歌……」
哪一個心靈正常的人,不需要來自同類的愛和理解呢?然而,哪一個真正獨立的思想家,不曾體會過孤獨的滋味呢?當尼采認清,孤獨乃是真正的思想家的命運,他就甘於孤獨,並且愛自己的命運了。在既自願又被迫的孤獨中,在無家可歸的漂泊中,靠著微薄的教員退休金,尼采度過了他生命中最豐產的十年。倘若不是因為精神失常,這種孤獨的漂泊生涯會延續到他生命的終結。可是,一八八九年以後,他的神智始終處於麻痹狀態,只是在母親和妹妹的護理下苟延無用的生命。他於一九○○年八月二十五日在魏瑪去世,而他的生命在一八八九年實際上已經結束了。
新世紀的早生兒
尼采的命運,有時令人想起屈原。這位「眾人皆醉、唯我獨醒」的楚國大夫,當年被腐敗的朝廷放逐,漂泊於瀟湘之際,在世人眼中是個狂人和瘋子。尼采,這位世紀末的漂泊者,又何嘗不被世人視為狂人和瘋子?尼采也的確狂,狂妄得令人吃驚。他的自傳,單是標題就夠咄咄逼人的了:「我為何如此智慧」,「我為何如此聰明」,「我為何寫出如此卓越的著作」,「我為何便是命運」……他如此自信:「在我之前沒有人知道正確的路,向上的路;只是從我開始,才有了給文化指路的希望和使命──我是這條路上的快樂的信使。」他甚至斷言,人類歷史將因他而分成兩個部分,他將取代耶穌成為紀元的依據。
尼采的病歷表明,他的精神病起於器質性腦病。不過,他的發病方式頗有自大狂的意味。當時,他的熟人和朋友們突然收到了他的一批奇怪的信,署名自稱「釘在十字架上的人」和「狄俄尼索斯」。當他的朋友奧維貝克趕到他的漂泊地去接他時,他又唱又舞,說自己是死去的上帝的繼承人。
也許,他的自大是一種心理上的過激反應,因為世人對他的遺忘和誤解,他就愈加要自我肯定?
瘋人的狂言似乎不必理會。然而,狂言裡有真知。尼采對於自己所扮演的歷史角色是有清醒的領悟的。他說:「我輩天生的猜謎者,我們好像在山上等待,置身於今日與明日之間,緊張於今日與明日之間的矛盾裡,我輩正在來臨的世紀的頭生子和早生兒,我們現在應該已經看見不久必將籠罩歐洲的陰影了……」「我輩新人,無名者,難於被理解者,一種尚未被證實的未來的早生兒……」一句話,他把自己視為新世紀的早生兒。孤獨,遺忘,誤解,責難,都從這種特殊的地位得到了解釋。
尼采所預見的「必將籠罩歐洲的陰影」,就是資本主義的精神危機。這一危機在十九世紀已露端倪,在二十世紀完全明朗化,特別是在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之後,為西方思想界廣泛地談論著。危機的實質是資產階級傳統價值觀念的崩潰。資本主義有力地促進了自然科學的發展,與之相伴隨,在哲學上便是經驗主義和理性主義半分天下,占據絕對優勢。無論是自然科學,還是經驗主義或理性主義哲學,都從根本上動搖了歐洲人基督教信仰的基礎。代之而起的是對於科學、理性和物質文明的迷信。接著,這種迷信也動搖了,人們發現,科學也有其局限性,單純的物質繁榮只能造成虛假的幸福。歐洲人失去了過去藉以生活的一切信仰,面對傳統價值的荒涼廢墟,苦悶彷徨,無所適從。在十九世紀,最早敏銳地感覺到這種危機並且試圖尋找一條出路的人,來自左邊的是馬克思,來自右邊的是齊克果、杜斯妥也夫斯基和尼采。
馬克思早在四十年代就揭示了資本主義物質繁榮背後的人的異化現象,並且確認,其根源在於資本主義制度本身,在於資本主義的勞動分工和私有制。他從中引出了社會革命的結論。
齊克果、杜斯妥也夫斯基和尼采試圖尋找另一條路。他們訴諸人的內心生活領域,想依靠某種「精神革命」來解決普遍的精神危機。這三個人,出生在不同國家(分別為丹麥、俄國和德國),活動於不同領域(分別為宗教、文學和哲學),基本上不相與聞,各自獨立地得出了某些共同的見解。他們的思想在精神實質上異常一致。尼采在一八八七年讀到陀氏的《地下室手記》法譯本,在此之前他還不知道有陀氏這個人,他描繪自己讀此書時的感覺道:「一種血統本能直接呼叫出來,我的欣喜超乎尋常。」他還讀過《地下室手記》,讚歎陀氏是「深刻的人」,並且說:「杜斯妥也夫斯基是我從之學到一點東西的唯一的心理學家,他屬於我生命中最美好的幸運情形」。一八八八年,尼采第一次聽到齊克果的名字,已經來不及有機會讀他的任何著作了。在這三個人中,若論思想的豐富性和徹底性,還是要推尼采。
如果我們檢視一下半個多世紀以來西方人文思想的文獻,尼采的影響是一目了然的。凡是現代西方思想界所熱衷談論的課題,尼采都以最明確的方式提出來了。他為現代西方思潮提供了一個清晰可辨的起點。
這裡,我們只是簡要地提示一下尼采對於現代思潮的一般影響。
這種影響集中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尼采首先從基督教信仰業已破產(「上帝死了」)的事實,引出了一切傳統價值必將隨之崩潰(「一切價值的重估」)的結論。他把歐洲人面臨的價值真空指給全體歐洲人看了。在他的時代,這種揭示或許被人看作危言聳聽;可是,到了二十世紀,人們愈來愈強烈地感覺到這種價值真空,愈來愈頻繁地談論起「現代人的無家可歸狀態」了。價值真空意味著人生失去了從前似乎明白而確定的意義,於是人的存在的荒謬性成了現代西方文學和哲學的一個主題。價值真空又意味著人生並無超驗的約束,於是人的自由、人性的開放性和無限可能性也成了現代西方文學和哲學的一個主題。第二,尼采由舊價值的崩潰進一步引出價值的相對性的結論,強調每個人必須獨立地為自己創造價值,提倡個人至上,自我實現。儘管他沒有使用「異化」的術語,但是他用自己的語言揭露了傳統文明導致個性喪失、自我失落的事實。現代西方思想界紛紛談論現代人的「無名無姓」,熱衷於探討「異化」問題,強調自我的重要性,部分地可以追溯到他。
第三,尼采是最早起來揭示科學理性的局限性的人之一,他也是第一個明確地揭示人的心理中無意識領域並加以細緻剖析的人。在這方面,在他之前儘管不乏先驅者,但都不及他論述得具體而透徹。遍及現代西方文化各領域的強大的非理性主義思潮,如現代派文學藝術,佛洛伊德精神分析學,現象學運動,存在主義哲學,等等,尼采實為始作俑者。
第四,尼采也是現代西方哲學人學主義的創始人之一。他明確主張,哲學以探求人生意義為鵠的。他對人性的看法,以人的超越性為基調,富有現代特點。在他之前,儘管有費爾巴哈首倡哲學人學,但費爾巴哈對人性的看法基本上落入傳統範圍,不足以代表現代的開端。
尼采的若干具體論點,包括強力意志、超人、永恆輪迴這樣的主要論點,對於現代西方思想界的影響不甚顯著,它們只有局部性的影響。尼采的真正意義在於,他首先揭示了現代西方人的基本境遇,提出並且嚴肅思考了激動著現代西方人心靈的重大問題。有人說:尼采所談的問題是人人都能領會的,特別是現代世界中那些迷失方向的人都能領會的。尼采哲學所表達的正是現代西方人在傳統價值崩潰時代的迷途的痛苦和尋求的渴望,也許這就是尼采哲學的生命力之所在。
誤解和發現
蓋棺論定也許適用於二、三流的思想家,可是對於天才並不適用。天才猶如自然,本身包含著巨大的豐富性和矛盾性,為世世代代的爭論留下了廣闊的餘地。有哪一個獨創性的思想家,不是在生前死後戲劇性地經歷著被誤解、被「發現」、又被誤解、又被重新「發現」的過程呢?
是死亡、榮譽和幸福!
──尼采
大自然的星空,群星燦爛。那最早閃現的,未必是最亮的星宿。有的星宿孤獨地燃燒著,熄滅了,很久很久以後,它的光才到達我們的眼睛。
文化和歷史的星空何嘗不是如此?
一顆敏感的心,太早太強烈地感受到了時代潛伏的病痛,發出了痛苦的呼喊。可是,在同時代人聽來,卻好似瘋子的譫語。直到世紀轉換,時代更替,潛伏的病痛露到面上,新一代人才從這瘋子的譫語中聽出了先知的啟示。
一百年以前,這位當時默默無聞的德國哲學家,攜帶一把綠色的小傘,一個筆記本,漂泊於南歐的山巔海濱。他的文字,鍾山水之靈秀,清新而雋永;他的思想,抒內心之焦渴,激烈而唐突。然而,世界幾乎把他遺忘了。直到他生命的最後歲月,他才小有名氣,但也不過是小有名氣而已。
尼采在一首詩中寫道:「誰終將聲震人間,必長久深自緘默;誰終將點燃閃電,必長久如雲漂泊。」
他對他身後的聲譽是充滿信心的:
「我的時代還沒有到來,有的人死後方生。」
「總有一天我會如願以償。這將是很遠的一天,我不能親眼看到了。那時候人們會打開我的書,我會有讀者。我應該為他們寫作。」
二十世紀的序幕剛剛揭開,尼采溘然長逝了。今天,當我們這個世紀也已經接近尾聲的時候,倘若要探溯本世紀西方思潮的源頭,我們發現確實不能撇開尼采。漂泊者早已倒下,他的影子卻籠罩了整整一個時代。有人說,在上個世紀的思想家中,若要舉出兩位對本世紀影響最大的人物,當推馬克思和尼采。的確,他們都不是學院式的哲學家,他們的影響都遠遠超出學術界的小圈子,而震撼了整個西方社會意識。
人們對馬克思已經談論得很多,儘管不乏驚人的誤解,現在,請允許我們稍稍結識一下尼采。
世紀末的漂泊者
人的命運真是不同。許多人終其一生,安居樂業,心安理得地接受環境和時運替他們安排的一切,悠然享其天年。可是,像尼采這樣的人,有著一顆不安的靈魂,總是在苦苦地尋求著什麼,精神上不斷地爆發危機,在動盪中度過了短促的一生。
赫拉克利特說:「一個人的性格就是他的命運。」真的,尼采的個性,注定了他的悲劇性的命運。一八四四年十月十五日,尼采生於德國東部呂采恩鎮附近的勒肯村。他的祖父是一個寫有神學著作的虔誠信徒,父親和外祖父都是牧師。未滿五歲時,父親病死,此後他便在母親和姑母的撫育下度過了童年和少年時代。一八六五年,二十一歲的尼采,在波恩大學攻讀了半年神學和古典語文學之後,斷然決定放棄神學,專修古典語文學。對於一個牧師世家的子弟來說,這不啻是一個反叛的信號,後來他果然成了基督教的死敵──「反基督徒」。與此同時,這個曾經與同學們一起酗酒、浪遊、毆鬥的青年人,突然變得少年老成起來。他退出了學生團體,離群索居,整日神情恍惚,冥思苦想。
這是尼采生涯中發生的第一次精神危機。眼前的一切,這喧鬧的大學生生活,刻板的課程,瑣碎的日常事務,未來的學者生涯,刹時顯得多麼陌生啊。難道人生是一番消遣,或是一場按部就班的課堂考試嗎?他心中醞釀著一種使命感,要為自己尋求更真實的人生。
一八六九年,尼采二十五歲,在李契爾的推薦下,到巴塞爾大學任古典語言學教授。李契爾是一位具有探索者性格和純真熱情的古典語文學學者,先後任教於波恩大學和萊比錫大學,對尼采極為欣賞,始終把他的這位高足帶在身邊。在推薦信裡,他不無誇耀之情地寫道:「三十九年來,我目睹了如此多的新秀,卻還不曾看到一個年輕人像尼采這樣,如此年紀輕輕就如此成熟……我預言,只要上天賜他長壽,他將在德國語言學界名列前茅。」他還把尼采稱作「萊比錫青年語言學界的偶像」,甚至說他是「奇跡」。尼采倒也不負所望,走馬上任,發表題為《荷馬和古典語文學》的就職演說,文質並茂,頓使新同事們嘆服。
也許,這位前程無量的青年學者要安心治他的學問了?
並不!僅僅兩年以後,尼采出版了他的處女作《悲劇的誕生》,這本以全新的眼光研究希臘悲劇起源的小冊子,同時宣告了尼采自己的悲劇生涯的開始。它引起了轟動,既受到熱烈的讚揚,也遭得激烈的攻擊。在正統語文學界看來,一個語文學家不好好地去琢磨柏拉圖古典語言的精妙,卻用什麼酒神精神批判蘇格拉底和柏拉圖,全然是荒誕不經。以青年學者維拉莫維茨為代表的正統語文學家們對尼采展開了激烈批評。尼采發現他的教室空了,不再有學生來聽他的課。尼采嘗到了孤獨的滋味。但是,他有他的「絕妙的慰藉」──叔本華的哲學和華格納的音樂。
還在學生時代,尼采在一家舊書店裡偶然地購得叔本華的《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一書,欣喜若狂,一口氣讀完了。後來他回憶說,當時他漫遊在一個願望的世界裡,夢想找到一位真正的哲學家,能夠把他從時代的缺陷中拯救出來,教他在思想和生活中重新變得單純和誠實,也就是「不合時宜」。正當他懷著如此渴望的時候,他發現了叔本華。他覺得,叔本華就像是特地為他寫了這部著作一樣。
到巴塞爾任教以後,尼采結識了當時卜居羅采恩湖畔的華格納。他經常去拜訪這位浪漫主義音樂大師,在華格納身邊度過了他一生中最愉快的時光。
正是在叔本華和華格納的影響下,尼采寫出了那本得罪德國正統語言學界、斷送自己學術前程的著作。
可是,尼采現在又要否定叔本華和華格納了。他的靈魂注定不得安寧,不斷地摒棄曾經推崇的一切,打碎一切偶像,終於面對空無所有的沙漠。他把自己逼到了沙漠裡。
在回顧自己的人生歷程時,尼采說,「通向智慧之路」有三個必經的階段。第一階段是「合群時期」,崇敬、順從、仿效隨便哪個比自己強的人。第二階段是「沙漠時期」,束縛最牢固的時候,崇敬之心破碎了,自由的精神茁壯生長,一無牽掛,重估一切價值。第三階段是「創造時期」,在否定的基礎上重新進行肯定,然而這肯定不是出於我之上的某個權威,而僅僅是出於我自己,我就是命運,我手中抓著人類的鬮。
一八七六年,尼采生命中的「沙漠時期」開始了。他的精神又一次爆發危機,這次的危機如此深刻,以致他不像前兩次那樣,僅僅同學生團體決裂,僅僅受到德國語文學界的譴責,而是要被整個時代放逐了。
這一年,華格納在德皇威廉一世支持下,在拜洛伊特舉辦聲勢浩大的第一屆音樂節。尼采原先把歐洲文化復興的希望寄託在華格納身上。可是,在拜洛伊特,目睹華格納的「演戲天才」、富裕市民觀眾的庸俗捧場,尼采失望了。他悄悄離開,躲進一片森林,醞釀了一部含蓄批評華格納的書。兩年後,華格納的最後一部歌劇《帕西法爾》的劇本寄到尼采手中,尼采的《人性的,太人性的》一書寄到華格納手中,兩人從此決裂。這一年,尼采與他大學時代最親密的朋友洛德之間也產生了隔閡,導致了後來的破裂。尼采與洛德,同為李契爾教授的高足,可是兩人志趣迥異。洛德脫不開世俗之路,當學生時也有一番雄心,畢業後,逐漸滿足於平穩的學者生涯和小家庭生活,終於不過是一個平庸之輩。尼采卻始終保持著青年時代產生的使命感。靈魂不同,自然就沒有了共同語言。
這一年,尼采向一位荷蘭女子求婚而遭拒絕。後來他儘管一再試圖為自己覓一配偶,均不成功,終於至死未婚。
也在這一年,尼采因健康惡化而停止了在大學授課,三年後辭掉巴塞爾大學教授職務,永遠退出了大學講壇。
決裂,失戀,辭職,這些遭遇似乎偶然地湊到了一起,卻顯示了某種必然的命運。一個精神貧乏、缺乏獨特個性的人,當然不會遭受精神上危機的折磨。可是,對於一個精神需求很高的人來說,危機,即供求關係的某種脫節,卻是不可避免的。他太挑剔了,世上不乏友誼、愛和事業,但不是他要的那一種,他的精神仍然感到饑餓。這樣的人,必須自己來為自己創造精神的食物。
尼采自己說:「當時我所做的抉擇不只是與華格納決裂──我覺得我的本性陷入了一種完全的迷亂,而其中的個別失誤,不管涉及華格納還是涉及巴塞爾的教職,僅是一個徵兆。一種焦躁籠罩了我;我知道是刻不容緩反省自己的時候了。我感到驚恐,一下子看清楚自己浪費了多少時間,──我以古典語文學家為我的全部生存,我的使命,這是多麼無益,多麼草率。我為這種錯誤的謙虛而羞愧……在過去十年裡,我的精神營養徹底停止,我沒有學到任何有用之事,我荒唐地為積滿灰塵的學術破爛而丟掉許多東西。睜著近視眼小心翼翼地爬行在古代詩韻學家腳下——這就是我所做的事情!」
一八七九年,尼采結束了十年教授生涯,從此開始了他的沒有職業、沒有家室、沒有友伴的孤獨的漂泊生涯。這時候的尼采,三十五歲,已過而立之年,精神上成熟了。許多人的所謂成熟,不過是被習俗磨去了棱角,變得世故而實際了。那不是成熟,而是精神的早衰和個性的夭亡。真正的成熟,應當是獨特個性的形成,真實自我的發現,精神上的結果和豐收。「現在我敢於自己來追求智慧,自己來做哲學家;而過去我只是崇敬哲學家們。」「現在我自己在各方面都努力尋求智慧,而過去我只是崇敬和愛慕智慧的人。」尼采不再是一個古典語文學學者,甚至也不再是一個哲學學者,他成長為一個真正的哲學家即一個獨創的哲學家了,因為,倘若沒有獨立的創造,算什麼哲學家呢?
雅斯貝爾斯說:「尼采一生的主要特色是他的脫出常規的生存。他沒有現實生計,沒有職業,沒有生活圈子。他不結婚,不招門徒和弟子,在人世間不營建自己的事務領域。他離鄉背井,到處流浪,似乎在尋找他一直未曾找到的什麼。然而,這種脫出常規的生存本身就是本質的東西,是尼采全部哲學活動的方式。」
事實上,尼采的主要著作,表達了他的基本思想的成熟作品,包括《朝霞》、《快樂的科學》、《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善惡的彼岸》、《道德的譜系》、《偶像的黃昏》以及未完成的《強力意志》,都是在脫出常規的漂泊生涯中寫出的。
問題在於,尼采的思想受孕於歐洲文明瀕臨深刻危機的時代,他的敏感使他對這種危機徵象有格外真切的感受,他的勇敢使他直言不諱,他的真誠又使他不肯言行不一,因而,這個反對一切傳統價值的哲學家,必不可免地要過一種脫出常規的生活。他的哲學思考方式必然要影響到他的實際生活方式。他向傳統的挑戰必然導致他與世俗生活領域的抵觸。他對這種情形是有清醒的認識的:「我必須永遠做一個殉道者,以度過徹底貸出了的一生。」「當一個人要靠作品來批准自己的一生,他在根基上就變得極為苛求了。」「我的境遇與我的生存方式之間的矛盾在於,作為一個哲學家,我必須擺脫職業、女人、孩子、祖國、信仰等等而獲得自由,然而,只要我還是一個幸運地活著的生物,而不是一架純粹的分析機器,我又感到缺乏這一切。」尼采並非一個生性孤僻的人,年復一年的孤獨的漂流也並非一件浪漫的樂事。在難以忍受的孤寂中,尼采一次次發出絕望的悲歎:「我期待一個人,我尋找一個人,我找到的始終是我自己,而我不再期待我自己了!」「現在再沒有人愛我了,我如何還能愛這生命!」「向我傳來的友好的聲音如此之少。如今我孤單極了,不可思議地孤單……成年累月沒有振奮人心的事,沒有一絲人間氣息,沒有一丁點兒愛。」在給妹妹的信中,他情不自禁地談到「那種突然瘋狂的時刻,寂寞的人想要擁抱隨便哪個人」!
友誼,尼采是多麼渴望友誼啊。「你神聖的,友誼!我的最高希望的第一縷晨曦……」
可是,這個害怕孤獨、悲歎孤獨的人,同時又嚮往孤獨,需要孤獨。因為「人與人之間的巨大差距迫使我孤獨」;他感到,在人群中比獨自一人更加孤獨。他不肯降格以求,寧願走到沙漠裡與猛獸一起忍受焦渴,不願與骯髒的趕駱駝人同坐在水槽邊。他把孤獨當作自己的家,並且說:「我需要孤獨,也就是說,需要康復,回到我自己,呼吸自由、輕快、活潑的空氣……我的整部《查拉圖斯特拉》是一曲孤獨之頌歌,或者,如果人們理解了我的意思的話,是一曲潔淨之頌歌……」
哪一個心靈正常的人,不需要來自同類的愛和理解呢?然而,哪一個真正獨立的思想家,不曾體會過孤獨的滋味呢?當尼采認清,孤獨乃是真正的思想家的命運,他就甘於孤獨,並且愛自己的命運了。在既自願又被迫的孤獨中,在無家可歸的漂泊中,靠著微薄的教員退休金,尼采度過了他生命中最豐產的十年。倘若不是因為精神失常,這種孤獨的漂泊生涯會延續到他生命的終結。可是,一八八九年以後,他的神智始終處於麻痹狀態,只是在母親和妹妹的護理下苟延無用的生命。他於一九○○年八月二十五日在魏瑪去世,而他的生命在一八八九年實際上已經結束了。
新世紀的早生兒
尼采的命運,有時令人想起屈原。這位「眾人皆醉、唯我獨醒」的楚國大夫,當年被腐敗的朝廷放逐,漂泊於瀟湘之際,在世人眼中是個狂人和瘋子。尼采,這位世紀末的漂泊者,又何嘗不被世人視為狂人和瘋子?尼采也的確狂,狂妄得令人吃驚。他的自傳,單是標題就夠咄咄逼人的了:「我為何如此智慧」,「我為何如此聰明」,「我為何寫出如此卓越的著作」,「我為何便是命運」……他如此自信:「在我之前沒有人知道正確的路,向上的路;只是從我開始,才有了給文化指路的希望和使命──我是這條路上的快樂的信使。」他甚至斷言,人類歷史將因他而分成兩個部分,他將取代耶穌成為紀元的依據。
尼采的病歷表明,他的精神病起於器質性腦病。不過,他的發病方式頗有自大狂的意味。當時,他的熟人和朋友們突然收到了他的一批奇怪的信,署名自稱「釘在十字架上的人」和「狄俄尼索斯」。當他的朋友奧維貝克趕到他的漂泊地去接他時,他又唱又舞,說自己是死去的上帝的繼承人。
也許,他的自大是一種心理上的過激反應,因為世人對他的遺忘和誤解,他就愈加要自我肯定?
瘋人的狂言似乎不必理會。然而,狂言裡有真知。尼采對於自己所扮演的歷史角色是有清醒的領悟的。他說:「我輩天生的猜謎者,我們好像在山上等待,置身於今日與明日之間,緊張於今日與明日之間的矛盾裡,我輩正在來臨的世紀的頭生子和早生兒,我們現在應該已經看見不久必將籠罩歐洲的陰影了……」「我輩新人,無名者,難於被理解者,一種尚未被證實的未來的早生兒……」一句話,他把自己視為新世紀的早生兒。孤獨,遺忘,誤解,責難,都從這種特殊的地位得到了解釋。
尼采所預見的「必將籠罩歐洲的陰影」,就是資本主義的精神危機。這一危機在十九世紀已露端倪,在二十世紀完全明朗化,特別是在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之後,為西方思想界廣泛地談論著。危機的實質是資產階級傳統價值觀念的崩潰。資本主義有力地促進了自然科學的發展,與之相伴隨,在哲學上便是經驗主義和理性主義半分天下,占據絕對優勢。無論是自然科學,還是經驗主義或理性主義哲學,都從根本上動搖了歐洲人基督教信仰的基礎。代之而起的是對於科學、理性和物質文明的迷信。接著,這種迷信也動搖了,人們發現,科學也有其局限性,單純的物質繁榮只能造成虛假的幸福。歐洲人失去了過去藉以生活的一切信仰,面對傳統價值的荒涼廢墟,苦悶彷徨,無所適從。在十九世紀,最早敏銳地感覺到這種危機並且試圖尋找一條出路的人,來自左邊的是馬克思,來自右邊的是齊克果、杜斯妥也夫斯基和尼采。
馬克思早在四十年代就揭示了資本主義物質繁榮背後的人的異化現象,並且確認,其根源在於資本主義制度本身,在於資本主義的勞動分工和私有制。他從中引出了社會革命的結論。
齊克果、杜斯妥也夫斯基和尼采試圖尋找另一條路。他們訴諸人的內心生活領域,想依靠某種「精神革命」來解決普遍的精神危機。這三個人,出生在不同國家(分別為丹麥、俄國和德國),活動於不同領域(分別為宗教、文學和哲學),基本上不相與聞,各自獨立地得出了某些共同的見解。他們的思想在精神實質上異常一致。尼采在一八八七年讀到陀氏的《地下室手記》法譯本,在此之前他還不知道有陀氏這個人,他描繪自己讀此書時的感覺道:「一種血統本能直接呼叫出來,我的欣喜超乎尋常。」他還讀過《地下室手記》,讚歎陀氏是「深刻的人」,並且說:「杜斯妥也夫斯基是我從之學到一點東西的唯一的心理學家,他屬於我生命中最美好的幸運情形」。一八八八年,尼采第一次聽到齊克果的名字,已經來不及有機會讀他的任何著作了。在這三個人中,若論思想的豐富性和徹底性,還是要推尼采。
如果我們檢視一下半個多世紀以來西方人文思想的文獻,尼采的影響是一目了然的。凡是現代西方思想界所熱衷談論的課題,尼采都以最明確的方式提出來了。他為現代西方思潮提供了一個清晰可辨的起點。
這裡,我們只是簡要地提示一下尼采對於現代思潮的一般影響。
這種影響集中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尼采首先從基督教信仰業已破產(「上帝死了」)的事實,引出了一切傳統價值必將隨之崩潰(「一切價值的重估」)的結論。他把歐洲人面臨的價值真空指給全體歐洲人看了。在他的時代,這種揭示或許被人看作危言聳聽;可是,到了二十世紀,人們愈來愈強烈地感覺到這種價值真空,愈來愈頻繁地談論起「現代人的無家可歸狀態」了。價值真空意味著人生失去了從前似乎明白而確定的意義,於是人的存在的荒謬性成了現代西方文學和哲學的一個主題。價值真空又意味著人生並無超驗的約束,於是人的自由、人性的開放性和無限可能性也成了現代西方文學和哲學的一個主題。第二,尼采由舊價值的崩潰進一步引出價值的相對性的結論,強調每個人必須獨立地為自己創造價值,提倡個人至上,自我實現。儘管他沒有使用「異化」的術語,但是他用自己的語言揭露了傳統文明導致個性喪失、自我失落的事實。現代西方思想界紛紛談論現代人的「無名無姓」,熱衷於探討「異化」問題,強調自我的重要性,部分地可以追溯到他。
第三,尼采是最早起來揭示科學理性的局限性的人之一,他也是第一個明確地揭示人的心理中無意識領域並加以細緻剖析的人。在這方面,在他之前儘管不乏先驅者,但都不及他論述得具體而透徹。遍及現代西方文化各領域的強大的非理性主義思潮,如現代派文學藝術,佛洛伊德精神分析學,現象學運動,存在主義哲學,等等,尼采實為始作俑者。
第四,尼采也是現代西方哲學人學主義的創始人之一。他明確主張,哲學以探求人生意義為鵠的。他對人性的看法,以人的超越性為基調,富有現代特點。在他之前,儘管有費爾巴哈首倡哲學人學,但費爾巴哈對人性的看法基本上落入傳統範圍,不足以代表現代的開端。
尼采的若干具體論點,包括強力意志、超人、永恆輪迴這樣的主要論點,對於現代西方思想界的影響不甚顯著,它們只有局部性的影響。尼采的真正意義在於,他首先揭示了現代西方人的基本境遇,提出並且嚴肅思考了激動著現代西方人心靈的重大問題。有人說:尼采所談的問題是人人都能領會的,特別是現代世界中那些迷失方向的人都能領會的。尼采哲學所表達的正是現代西方人在傳統價值崩潰時代的迷途的痛苦和尋求的渴望,也許這就是尼采哲學的生命力之所在。
誤解和發現
蓋棺論定也許適用於二、三流的思想家,可是對於天才並不適用。天才猶如自然,本身包含著巨大的豐富性和矛盾性,為世世代代的爭論留下了廣闊的餘地。有哪一個獨創性的思想家,不是在生前死後戲劇性地經歷著被誤解、被「發現」、又被誤解、又被重新「發現」的過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