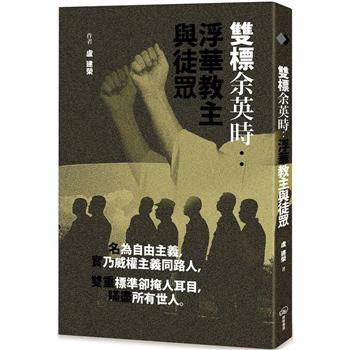第一章 昔日芳菲韋伯心 棲蘭風雨師生情
——余門師徒共打江山秘辛
一、台灣史學班底的本質
此處主要在討論新史學運動以來,史學班底的運作,如何仰賴對一個霸權機構的控制。該機構的內部運轉邏輯類似殖民主義性格,即有殖民主和被殖民者二重結構。殖民主出自反淘汰機制才是霸權機構的主人。代表人物個個都是夤緣悻進型的人物,真正有實力的學者中,多數不是被排擠淪為邊緣,就是早在求學過程中半途陣亡。本書此處討論的代表人物就是今天光環正盛、經營公共形像有術的王汎森先生。對於他如何發跡、如何做學問,以及如何附庸風雅而躋身兩岸名流圈,有詳細的介紹。
歷史上的亡國都是「朝中善類一空」的反淘汰結局,所以如何使人才出頭,必然是國家大戰略的一個重要環節,是可受社會公評之事。三國蜀漢人才盡而國亡,可為殷鑒。
當學術不再是志業,則淪為權勢集團搶佔位置的緣飾,以及合理化不當利益的藉口。
二、以學者專業倫理看余大師擇徒軌迹
余英時大師擇徒之奇,創古今所未有。康樂之特立異行,以其於二○○七年業已身亡,自不消說他。陳弱水博論一出版,就被美國漢學家在書評裡指出,第一頁第一句連錯三個史實,二○一○年他以國科會學門召集人,兼任主辦人、球員,以及裁判三合一,將極為稀少可貴的研究傑出獎頒發給自己。林富士的表現已經筆者專文討論,其於普林斯頓博士生期間之作為,且死於二○二一年前多在休養,無何大作為,按下不表可也。余大師關門弟子陸揚以雲中上師的花名,於離開師門後,透過互聯網向大陸同行指導學問,儼然以海外大師自居,十餘年後竟遭美國大學解聘,大師心疼其徒,令其麾下弟子合力演出,王汎森更囑咐務必將其以副研究員受聘於史語所,不料於二○一○年六月二十八日被史語所有識之士,以劉淑芬研究員為首,加以封殺。黃進興的指導教授不是余英時,而是哈佛的史華慈教授,但他情願做一個投余大師口味的博論,那就是清初一位三流理學家李紱的思想,結論甘充為印證余大師理學全盤看法的一個註腳。這樣赤裸裸不想青出於藍的姿態,被余大師認為是孺子可教。余大師如何拔擢王汎森之匪夷所思,只要聽我講解,自然會解除各位讀者心中疑惑。
史家從事的是一種專業化的工作,要求以理性思維,而非彈性道德、或和稀泥的人情,去處理自己的工作,以及處理社群的公共事務。專業化過程創造了工作文化的絕大部分,而工作文化是以法理權威為基礎,人情是不被考慮的,只有如此,專家才能勝任其職守。現代社會異於前近代社會的特徵之一,就是專業人員以理性治事,擺脫人情關說,即令有情感生活,那也是理性般的的情感生活。專家的職場會有同事,但對待同事的情感面是更像理性面的,碰到公事,則須公私分明。譬如你跟某同事昨晚雖一起飲酒作樂,但第二天上班面對該同事的審稿或升遷問題時,若覺得他尚不及格,你的理性應提醒你該如何不讓他的稿件或人事案通過。以上就是韋伯(Max Weber)為我們所揭示的理性乃是專家公務生活的唯一最高準則。關於這方面的詮釋,我建議讀者閱讀英國社會學家大衛.英格利斯(David Inglis)的Cultural and Everyday Life(中譯本二○一○年出版)一書,便知梗概。
三、史語所的前近代性格無力處理抄襲弊案
台灣近六十年來處理抄襲問題、或是人才徵募問題,頗多嚴重違反現代社會所該信守的理性原則,都替代以前近代社會的行事風尚:人情關說與和稀泥。此舉明顯對瞧不起抄襲的專業人士造成相對的不公平,同時因庸才出頭的反淘汰機制大行其道,更反饋回來傷害到專業。如此惡性循環不已,這使史界權勢集團吃定我們國家和搞不清狀況的納稅人。
我曾在拙編:《社會/文化史集刊》第五期揭發中研院史語所三位研究人員涉嫌抄襲李敖著作,詎料該期於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才上市,該研究所已在八月做成「沒抄襲」的處置。據查,該邱姓涉嫌人因獲任該所權力機構:「集刊編委員」的秘書一職,而該權力機構這屆頭頭就是王汎森先生,王另一身分是中研院副院長,但在史語所,他是邱姓涉嫌人的主官。主官要罩部屬是該所前近代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項文化行動。王嚴令該所全力護邱乃事理之必然。接著九月底,另二位涉嫌人身分曝光後,所長黃進興對外揚言沒有抄襲情事。迨十月一日,揭弊者,即筆者,召開記者會,席間劉錚雲副所長代表史語所與會(邱姓涉嫌人電話央求盧氏許其助理旁聽記者會,獲得進場),他表示身為所務負責人必須保護所員。看來該所正副所長在情事不明情形下選擇包庇一途定矣。接著十月八日黃所長以其機關首長名義,利用中研院官網發布「澄清啟事」,表示涉案三人「一向學術表現優異,學界自有公評」,基此理由,該所堅持這三人不會抄襲。
第一章 昔日芳菲韋伯心 棲蘭風雨師生情
——余門師徒共打江山秘辛
一、台灣史學班底的本質
此處主要在討論新史學運動以來,史學班底的運作,如何仰賴對一個霸權機構的控制。該機構的內部運轉邏輯類似殖民主義性格,即有殖民主和被殖民者二重結構。殖民主出自反淘汰機制才是霸權機構的主人。代表人物個個都是夤緣悻進型的人物,真正有實力的學者中,多數不是被排擠淪為邊緣,就是早在求學過程中半途陣亡。本書此處討論的代表人物就是今天光環正盛、經營公共形像有術的王汎森先生。對於他如何發跡、如何做學問,以及如何附庸風雅而躋身兩岸名流圈,有詳細的介紹。
歷史上的亡國都是「朝中善類一空」的反淘汰結局,所以如何使人才出頭,必然是國家大戰略的一個重要環節,是可受社會公評之事。三國蜀漢人才盡而國亡,可為殷鑒。
當學術不再是志業,則淪為權勢集團搶佔位置的緣飾,以及合理化不當利益的藉口。
二、以學者專業倫理看余大師擇徒軌迹
余英時大師擇徒之奇,創古今所未有。康樂之特立異行,以其於二○○七年業已身亡,自不消說他。陳弱水博論一出版,就被美國漢學家在書評裡指出,第一頁第一句連錯三個史實,二○一○年他以國科會學門召集人,兼任主辦人、球員,以及裁判三合一,將極為稀少可貴的研究傑出獎頒發給自己。林富士的表現已經筆者專文討論,其於普林斯頓博士生期間之作為,且死於二○二一年前多在休養,無何大作為,按下不表可也。余大師關門弟子陸揚以雲中上師的花名,於離開師門後,透過互聯網向大陸同行指導學問,儼然以海外大師自居,十餘年後竟遭美國大學解聘,大師心疼其徒,令其麾下弟子合力演出,王汎森更囑咐務必將其以副研究員受聘於史語所,不料於二○一○年六月二十八日被史語所有識之士,以劉淑芬研究員為首,加以封殺。黃進興的指導教授不是余英時,而是哈佛的史華慈教授,但他情願做一個投余大師口味的博論,那就是清初一位三流理學家李紱的思想,結論甘充為印證余大師理學全盤看法的一個註腳。這樣赤裸裸不想青出於藍的姿態,被余大師認為是孺子可教。余大師如何拔擢王汎森之匪夷所思,只要聽我講解,自然會解除各位讀者心中疑惑。
史家從事的是一種專業化的工作,要求以理性思維,而非彈性道德、或和稀泥的人情,去處理自己的工作,以及處理社群的公共事務。專業化過程創造了工作文化的絕大部分,而工作文化是以法理權威為基礎,人情是不被考慮的,只有如此,專家才能勝任其職守。現代社會異於前近代社會的特徵之一,就是專業人員以理性治事,擺脫人情關說,即令有情感生活,那也是理性般的的情感生活。專家的職場會有同事,但對待同事的情感面是更像理性面的,碰到公事,則須公私分明。譬如你跟某同事昨晚雖一起飲酒作樂,但第二天上班面對該同事的審稿或升遷問題時,若覺得他尚不及格,你的理性應提醒你該如何不讓他的稿件或人事案通過。以上就是韋伯(Max Weber)為我們所揭示的理性乃是專家公務生活的唯一最高準則。關於這方面的詮釋,我建議讀者閱讀英國社會學家大衛.英格利斯(David Inglis)的Cultural and Everyday Life(中譯本二○一○年出版)一書,便知梗概。
三、史語所的前近代性格無力處理抄襲弊案
台灣近六十年來處理抄襲問題、或是人才徵募問題,頗多嚴重違反現代社會所該信守的理性原則,都替代以前近代社會的行事風尚:人情關說與和稀泥。此舉明顯對瞧不起抄襲的專業人士造成相對的不公平,同時因庸才出頭的反淘汰機制大行其道,更反饋回來傷害到專業。如此惡性循環不已,這使史界權勢集團吃定我們國家和搞不清狀況的納稅人。
我曾在拙編:《社會/文化史集刊》第五期揭發中研院史語所三位研究人員涉嫌抄襲李敖著作,詎料該期於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才上市,該研究所已在八月做成「沒抄襲」的處置。據查,該邱姓涉嫌人因獲任該所權力機構:「集刊編委員」的秘書一職,而該權力機構這屆頭頭就是王汎森先生,王另一身分是中研院副院長,但在史語所,他是邱姓涉嫌人的主官。主官要罩部屬是該所前近代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項文化行動。王嚴令該所全力護邱乃事理之必然。接著九月底,另二位涉嫌人身分曝光後,所長黃進興對外揚言沒有抄襲情事。迨十月一日,揭弊者,即筆者,召開記者會,席間劉錚雲副所長代表史語所與會(邱姓涉嫌人電話央求盧氏許其助理旁聽記者會,獲得進場),他表示身為所務負責人必須保護所員。看來該所正副所長在情事不明情形下選擇包庇一途定矣。接著十月八日黃所長以其機關首長名義,利用中研院官網發布「澄清啟事」,表示涉案三人「一向學術表現優異,學界自有公評」,基此理由,該所堅持這三人不會抄襲。
四、黃所長:揭弊者即害群之馬!
倘依此邏輯,一九九四年該所資深研究員毛漢光同樣地也是「一向學術表現優異,學界自有公評」,而且成為院士候選人,正當院士選舉前夕爆發抄襲案件。何以當時該所並未做到保護所員呢?毛漢光與這三位所員所受權勢集團的「公評」是同一套標準、同一套行事邏輯下的產物。何以毛案和這三員案受到不同對待?這是值得我們今天省思的地方。是今天這三人的「背景」比當年毛氏的「背景」更加硬裡子嗎?還是有不可為外人道的原因?我們社會大眾亟欲知道。但無論如何,該所在處理涉嫌重大學術倫理違失案的事件上,既沒有法定程序(即韋伯所說的法理理性)、也沒有公開而透明的調查,更沒有調查報告公布等,應有程序正義之步驟,就憑行政裁量權片面宣布:「無罪開釋」、並「結案」。這真把前近代的人情文化(同事情、同夥愛)發揚到極致。讓懷抱理性的專家、讓信從法治的一般大眾看傻眼,以為活在偵騎四出的明朝社會呢?還有,黃所長明知盧建榮基於愛所、基於興利除弊之旨,於今年七月底即向他報告有抄襲情事,黃所長如今竟然在官網上痛批盧氏所為有害所譽。究竟是不除弊才害所譽,還是抄襲者所為才害所譽?黃所長及其一小撮權勢集團弄清楚了沒有?十一月十九日,盧氏向中研院政風處主任請教此事孰是孰非,蒙主任清楚告知,機關為嫌疑者背書為不妥,遑論利用官網公器私用云云。我們且拭目以待中研院內部監督機制有何作為,即知納稅人是否白養政風人員。
涉案三人皆是《新史學》社的常務社員,該社近二十年來乃稱霸台灣史壇、甚至人文/社會各學科所有學報總合的霸主。三人背景如此雄厚,反映的正是抄襲共犯結構的強大無比。這是九四年時毛漢光不具有的條件,難怪他會被打趴在地啊。
為此,筆者有必要為文揭露了《新史學》社內部的神秘面紗。同時有文繼續追踪報導、評論抄襲李敖著作的疑雲。
五、王汎森:當然用自家弟子 優於用師弟了
本書此處的主角是王汎森先生。筆者對於其圓融處事、面面俱到的行事風格,素所敬佩。這號人物的崛起江湖非常富戲劇性,他喜歡操弄權術,不免留下許多痕跡,讓筆者循線破案。他對待異議人士,兩岸兩套標準,出身號稱自由主義大師門下,卻著手干預新聞自由和出版自由,嘴巴講的和實際作的也是兩套標準。他為師門強迫史語所吃下被美國大學丟棄的師弟陸揚(結果不成功),但他賺得自己的碩士生,李仁淵,打敗十六位中外名校的博士,其中有哈佛和耶魯的博士。史語所寧要王汎森親自調教的碩士生。在此,十七位申請者中,有兩位在第一輪由所長黃進興所主持的學發會――人事提名的審議機構――就被刷掉,其中一位是哈佛博士宋家復,與會七位委員(包括黃進興在內)一致投七張否決票,相反地,王汎森碩士生李仁淵獲七張票。這樣令黃進興和王汎森龍心大悅的操盤手,不是別人,正是熱愛權勢、又是所長心靈導師的范毅軍(史丹佛大學博士,專攻清代市鎮研究)。李仁淵又在下一輪所務會議的投票活動中,打敗其餘十四位中外名校的博士,脫穎而出。我為李仁淵的超級優秀,大為贊歎。同時,我為史語所一股清流感到雀躍,各自義助我此一消息,特別是我的鄰友提供最翔實版。這裡還涉及當權二十年的集刊編委會頭頭邢義田與王汎森交換利益和交換權力的醜聞。反正他們是院士,高來高去,誰也管不得。
王汎森現象非孤立事件,是專業團體內摧毀專業的故事。這種故事讀起來令人怵目驚心。
六、活像武俠小說的老哏:江湖異人邂逅幸運少年
中研院史語所是個近親繁殖雙重結構體,一重是台大歷史系同學會,另一重是美國普林斯頓東亞所同學會。這雙重結構體的核心是余英時大師門下弟子群,而余門的核心人物是王汎森。余、王相識於一九八二年由《中國時報.人間副刊》所主辦於宜蘭棲蘭山莊的「近代中國的變遷與發展:人文及社會科學的探索」會議。開會期間適逢安迪颱風襲擊北台灣,宜蘭對台北鐵公路交通悉數中斷。然而獨裁者蔣經國總統為了試測余英時大師的政治忠誠度,乃故意選擇風雨交加的時刻,電召余大師見面。(按:騐之日後,一說余見蔣之約會,早在颱風前就訂好了。請讀者參考)身為自由主義大師的余英時果然不負獨裁者的期待,竟能及時趕到總統府赴約。余大師究竟如何插翅有術、排除交通險阻安抵台北的呢?原來《中國時報.副刊》辦公室有一位資淺雜役王汎森,時為台大歷史所碩士生,表示願意出任艱鉅,他有一部摩托車,甘冒北宜公路沿線落石、塌方之險阻,也要載余大師完成面見蔣總統的使命。風雨見真情,余英時遂識拔王汎森於危難之中,事成之後,王汎森在余大師內心中份量之重,從此無與倫比。這個棲蘭奇遇記促成了王汎森日後進史語所、入讀普林斯頓東亞所、以及每天晨昏定省(透過電話、電腦)於余大師座前。當年一九八五年余英時為推薦王入史語所,還在致丁所長信上,謊稱他從不識王汎森云云。這已見拙作〈原來大師愛說謊〉一文中,不贅。余大師在王博士到手後十年內,也幫王在劍橋出版社出版其博論,成為角逐二○○四年院士選舉的入門票。
一九八二年的棲蘭奇遇傳奇,不免使人懷疑台灣自由主義者與獨裁者之間有暗盤交易,以及象徵人才徵募傾向人情而非理性的前近代性格。
余大師的泰山大人陳雪屏,於抗戰期間從事學界特工工作,民主同盟大將聞一多,遭迫害是其傑作之一,一九四九年國民黨轉進來台,陳雪屏曾任台灣省教育廳廳長。陳余翁婿之間呈現極權、特務政治和自由主義結合的混搭風。一九八二年至一九八八年正是蔣經國鐵腕治台期間,蔣與余大師的相知相惜,王汎森於一九八七年後負笈美國親炙於余大師膝前,多少有所與聞。從此,王汎森得到余門獨裁主義為裡、自由主義為表混搭風的嫡傳。他表裡互歧特有的行事風格也就益發精進。
另一位余門弟子黃進興,就不如王汎森貼近余大師,他於一九八三年返國後提倡的是韋伯現代社會的理性處世準則。沒想到在前近代社會文化醬缸的史語所浸泡過久,黃進興情願棄韋伯而就余大師。
一九八二年棲蘭山莊奇遇傳奇和史語所的前近代治事風格交乘之下,就此決定了史語所權勢集團處理內部抄襲疑雲的基調。四、黃所長:揭弊者即害群之馬!
倘依此邏輯,一九九四年該所資深研究員毛漢光同樣地也是「一向學術表現優異,學界自有公評」,而且成為院士候選人,正當院士選舉前夕爆發抄襲案件。何以當時該所並未做到保護所員呢?毛漢光與這三位所員所受權勢集團的「公評」是同一套標準、同一套行事邏輯下的產物。何以毛案和這三員案受到不同對待?這是值得我們今天省思的地方。是今天這三人的「背景」比當年毛氏的「背景」更加硬裡子嗎?還是有不可為外人道的原因?我們社會大眾亟欲知道。但無論如何,該所在處理涉嫌重大學術倫理違失案的事件上,既沒有法定程序(即韋伯所說的法理理性)、也沒有公開而透明的調查,更沒有調查報告公布等,應有程序正義之步驟,就憑行政裁量權片面宣布:「無罪開釋」、並「結案」。這真把前近代的人情文化(同事情、同夥愛)發揚到極致。讓懷抱理性的專家、讓信從法治的一般大眾看傻眼,以為活在偵騎四出的明朝社會呢?還有,黃所長明知盧建榮基於愛所、基於興利除弊之旨,於今年七月底即向他報告有抄襲情事,黃所長如今竟然在官網上痛批盧氏所為有害所譽。究竟是不除弊才害所譽,還是抄襲者所為才害所譽?黃所長及其一小撮權勢集團弄清楚了沒有?十一月十九日,盧氏向中研院政風處主任請教此事孰是孰非,蒙主任清楚告知,機關為嫌疑者背書為不妥,遑論利用官網公器私用云云。我們且拭目以待中研院內部監督機制有何作為,即知納稅人是否白養政風人員。
涉案三人皆是《新史學》社的常務社員,該社近二十年來乃稱霸台灣史壇、甚至人文/社會各學科所有學報總合的霸主。三人背景如此雄厚,反映的正是抄襲共犯結構的強大無比。這是九四年時毛漢光不具有的條件,難怪他會被打趴在地啊。
為此,筆者有必要為文揭露了《新史學》社內部的神秘面紗。同時有文繼續追踪報導、評論抄襲李敖著作的疑雲。
五、王汎森:當然用自家弟子 優於用師弟了
本書此處的主角是王汎森先生。筆者對於其圓融處事、面面俱到的行事風格,素所敬佩。這號人物的崛起江湖非常富戲劇性,他喜歡操弄權術,不免留下許多痕跡,讓筆者循線破案。他對待異議人士,兩岸兩套標準,出身號稱自由主義大師門下,卻著手干預新聞自由和出版自由,嘴巴講的和實際作的也是兩套標準。他為師門強迫史語所吃下被美國大學丟棄的師弟陸揚(結果不成功),但他賺得自己的碩士生,李仁淵,打敗十六位中外名校的博士,其中有哈佛和耶魯的博士。史語所寧要王汎森親自調教的碩士生。在此,十七位申請者中,有兩位在第一輪由所長黃進興所主持的學發會――人事提名的審議機構――就被刷掉,其中一位是哈佛博士宋家復,與會七位委員(包括黃進興在內)一致投七張否決票,相反地,王汎森碩士生李仁淵獲七張票。這樣令黃進興和王汎森龍心大悅的操盤手,不是別人,正是熱愛權勢、又是所長心靈導師的范毅軍(史丹佛大學博士,專攻清代市鎮研究)。李仁淵又在下一輪所務會議的投票活動中,打敗其餘十四位中外名校的博士,脫穎而出。我為李仁淵的超級優秀,大為贊歎。同時,我為史語所一股清流感到雀躍,各自義助我此一消息,特別是我的鄰友提供最翔實版。這裡還涉及當權二十年的集刊編委會頭頭邢義田與王汎森交換利益和交換權力的醜聞。反正他們是院士,高來高去,誰也管不得。
王汎森現象非孤立事件,是專業團體內摧毀專業的故事。這種故事讀起來令人怵目驚心。
六、活像武俠小說的老哏:江湖異人邂逅幸運少年
中研院史語所是個近親繁殖雙重結構體,一重是台大歷史系同學會,另一重是美國普林斯頓東亞所同學會。這雙重結構體的核心是余英時大師門下弟子群,而余門的核心人物是王汎森。余、王相識於一九八二年由《中國時報.人間副刊》所主辦於宜蘭棲蘭山莊的「近代中國的變遷與發展:人文及社會科學的探索」會議。開會期間適逢安迪颱風襲擊北台灣,宜蘭對台北鐵公路交通悉數中斷。然而獨裁者蔣經國總統為了試測余英時大師的政治忠誠度,乃故意選擇風雨交加的時刻,電召余大師見面。(按:騐之日後,一說余見蔣之約會,早在颱風前就訂好了。請讀者參考)身為自由主義大師的余英時果然不負獨裁者的期待,竟能及時趕到總統府赴約。余大師究竟如何插翅有術、排除交通險阻安抵台北的呢?原來《中國時報.副刊》辦公室有一位資淺雜役王汎森,時為台大歷史所碩士生,表示願意出任艱鉅,他有一部摩托車,甘冒北宜公路沿線落石、塌方之險阻,也要載余大師完成面見蔣總統的使命。風雨見真情,余英時遂識拔王汎森於危難之中,事成之後,王汎森在余大師內心中份量之重,從此無與倫比。這個棲蘭奇遇記促成了王汎森日後進史語所、入讀普林斯頓東亞所、以及每天晨昏定省(透過電話、電腦)於余大師座前。當年一九八五年余英時為推薦王入史語所,還在致丁所長信上,謊稱他從不識王汎森云云。這已見拙作〈原來大師愛說謊〉一文中,不贅。余大師在王博士到手後十年內,也幫王在劍橋出版社出版其博論,成為角逐二○○四年院士選舉的入門票。
一九八二年的棲蘭奇遇傳奇,不免使人懷疑台灣自由主義者與獨裁者之間有暗盤交易,以及象徵人才徵募傾向人情而非理性的前近代性格。
余大師的泰山大人陳雪屏,於抗戰期間從事學界特工工作,民主同盟大將聞一多,遭迫害是其傑作之一,一九四九年國民黨轉進來台,陳雪屏曾任台灣省教育廳廳長。陳余翁婿之間呈現極權、特務政治和自由主義結合的混搭風。一九八二年至一九八八年正是蔣經國鐵腕治台期間,蔣與余大師的相知相惜,王汎森於一九八七年後負笈美國親炙於余大師膝前,多少有所與聞。從此,王汎森得到余門獨裁主義為裡、自由主義為表混搭風的嫡傳。他表裡互歧特有的行事風格也就益發精進。
另一位余門弟子黃進興,就不如王汎森貼近余大師,他於一九八三年返國後提倡的是韋伯現代社會的理性處世準則。沒想到在前近代社會文化醬缸的史語所浸泡過久,黃進興情願棄韋伯而就余大師。
一九八二年棲蘭山莊奇遇傳奇和史語所的前近代治事風格交乘之下,就此決定了史語所權勢集團處理內部抄襲疑雲的基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