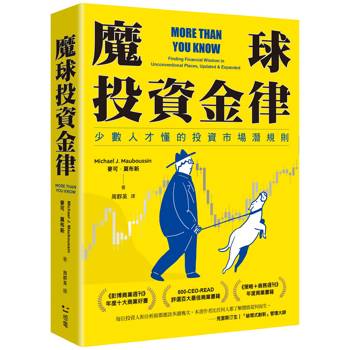貝比的打擊率
如果你去證券公司待一陣子,遲早會聽到人們說一些聽起來很有道理的話,例如:「嘿,如果我有51% 的時候是對的,我就會賺錢了。」如果你覺得這個說法有道理,那就繼續看下去吧,因為你即將看到投資最重要的一個概念。
首先我們要承認,人們心中深深烙印著「投資人賺錢的次數,應該多過賠錢的次數」的想法,而且這個想法從直覺上而言很有說服力。有一個資產經理人的故事,可以說明這種觀念的謬誤。
這位有名的投資人解釋,他們公司聘請了約20 位投資組合經理人,他是其中一位。該公司的財務主管,對旗下主動型基金經理人的整體績效很不滿意,決定評估每位經理的決策過程,然後淘汰表現不佳者。這位財務主管認為,就算是隨機選股,也會有一半左右的投資組合表現優於市場基準。所以,他決定根據每個組合裡打敗大盤的股票比例,來衡量經理人的績效。
這位投資組合經理人的狀況很奇特:在整個團隊裡,雖然他的總投資表現名列前茅,但他投資組合裡表現優異的股票比例,卻是最低的。財務主管馬上解僱所有表現「不佳」的經理,並和投資人召開一次會議,想弄清楚為什麼這位經理人有優異的績效,但打擊率(勝率)卻這麼糟糕。
投資組合經理的答案,解釋了所有涉及機率的活動,天生都有的重要課題:正確的次數不重要,正確的程度才重要。假設你有四支股票,其中三隻股票小跌,但第四支股票卻大漲。在這種情況下,即使你持有的大部分股票都下跌,你的投資組合仍然表現良好。
你必須以期望值分析(expected value analysis)來評估每一項投資,才能打造出可以帶來卓越績效的投資組合。讓人訝異的是,各個領域的頂尖思想家,包括賽馬投注、賭場賭博和投資,都強調過這一點,我們稱之為「貝比魯斯效應」(Babe Ruth effect):雖然魯斯常常被三振出局,他仍然是棒球史上最偉大的打擊手之一。
期望值這個課題之所以很普遍,是因為所有涉及機率的活動,都有相似的特徵。然而,要內化這個道理非常難,因為它在根本上有違人性。要指出上述財務主管邏輯裡的漏洞並不難,我也很容易理解他的想法。
做多、做空與賠率
塔雷伯(Nassim Taleb)在他那本引發爭議的著作《隨機騙局》(Fooled by Randomness)裡,分享過一個生動的故事,完美表達出期望值的概念。有一次塔雷伯在和其他交易員開會時,一位同事問他對市場的看法。他說,他認為市場在接下來一週內,微幅上漲的機率很高。人們進一步追問他,他認為上漲的機率有多少,他說70%。後來有人在會議中指出,塔雷伯大量做空標普500指數期貨,賭市場會下跌,似乎與他看漲的觀點自相矛盾。塔雷伯接著用期望值的觀點,解釋他的立場。下頁圖表3.1可以說明他的想法。
在這個例子裡,市場最有可能出現的結果是上漲,但期望值卻是負的,這是因為上漲和下跌會帶來不對稱的結果。現在,我們從股票市場來思考這件事。有時候,股價會完美訂價其價值。即使大多數時候(頻率),公司的股價會達到或些微超過其價值,股價也不會比價值高太多。但如果公司業績不如預期,股價就會重挫。高頻率出現讓人滿意的結果,但期望值卻是負的。
現在思考一下價值被低估的股票。這些公司大多數時候表現讓人失望,導致股價些微下跌,但如果出現正面的結果,股價就會劇烈上漲。在這種案例裡,機率偏向負面的結果,但期望值卻是正的。
投資人必須不看頻率,而是思考期望值。事實證明,這就是涉及機率領域裡,所有高績效人士的思考方式。然而,這樣的觀念在許多方面都很不自然,因為投資人希望他們的股票上漲,而非下跌。確實,展望理論最重要的實用結論,是投資人傾向太早賣掉賺錢的資產,這樣做可以滿足他們想要正確的欲望。同時,投資人也會太晚賣掉賠錢的資產,因為他們不想要承受損失。現在,我們來談三個不同機率領域裡優秀的實踐者。這三個領域是投資、賽馬下注和撲克牌的21點。
孔雀魚的模仿行為
從表面來看,生物學家李•杜加欽(Lee Dugatkin)似乎太閒了,因為他的研究重點看似想要解決一道深奧的問題:雌性孔雀魚如何選擇配偶。結果顯示,雌性孔雀魚先天偏好亮橘色的雄性孔雀魚。不過,當他讓一些母魚看到其他母魚選擇深色的雄魚後,其他母魚也開始選擇深色的雄魚。讓人驚訝的是,在許多情況下,看過同類選擇深色雄魚的母魚,會推翻自己的的本能,轉而模仿其他母魚。
為什麼會有人在意雌性孔雀魚如何選擇伴侶?這個答案點出一個熱門議題的核心,即動物行為是否只由基因決定,或是文化也發揮了一定的作用。杜加欽研究顯示,在動物界裡,模仿顯然以文化傳遞的形式存在,並且在物種發展裡扮演重要作用。
當然,模仿對人類來說是一種重要的力量,時尚、潮流和傳統都是模仿的結果。由於投資在本質上是一種社會性活動,因此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模仿在市場裡也扮演發揮重要作用。
大多數投資人和商人,都有基本的理念來規範他們的行為,就像基因會決定孔雀魚選擇配偶的方式一樣。然而,我們知道對於基金經理人和孔雀魚來說,模仿有時候會深刻影響他們的決策。那麼,模仿對投資人來說,是好是壞呢?
跟著你前面的螞蟻走
模仿是正向回饋的主要機制之一,例如動能投資(momentum investing)假設正在上漲的股票,將繼續上漲。如果有夠多的投資人遵循這個策略,那麼認為價格會持續走高的預言,就可能自我實現。
不過,大多數投資人對於單純的模仿會有疑慮,所以他們會掩飾自己的模仿行為。但其實模仿往往有其合理的根據,例如,思考以下幾種情況:
資訊不對稱:當其他投資人比你更了解某項投資時,模仿他們可能對你很有利。我們經常在日常生活的決策使用模仿策略,以利用他人的專業知識。
代理人成本:許多資產管理公司必須在最大化投資組合的績效(長期的絕對回報),以及最大化資產管理業務的價值(透過取得資產和收取手續費)之間取捨。選擇最大化資產管理公司業務的企業,有動機模仿其他人的做法。這種模仿行為,會讓投資組合相對於市場基準的追蹤誤差降到最小。
從眾偏好:就像凱因斯所說,「世俗智慧告訴我們,如果考慮到自己的名聲,那麼從眾失敗也比特立獨行而成功更好。」人類喜歡成為群體的一部分,因為群體常常讓我們覺得安全又安心。
在某些情況下,正向回饋確實可取,投資人的模仿行為也很合理,然而正向回饋也可能發展得過於極端。
財務經濟學家所說的羊群效應,是指一大群投資人根據別人的行為做相同選擇,而不仰賴自己的知識。實際上,當正向回饋主導狀況時,就會出現羊群效應。由於市場需要正向和負向回饋之間處在平衡狀態,因此這種不平衡會讓市場的效率低落。上述看法與傳統的觀點相左,傳統上認為投資人只會根據基本資訊進行交易。
我們也許永遠無法知道,到底多少的正向回饋屬於過量。許多科學研究顯示,在創新和概念傳播的過程中,通常會有一個臨界點,一旦傳播超過臨界點,正向回饋的效應便取得控制,於是正向的趨勢就能主導整個系統。市場泡沫和崩盤的相對頻率,強烈暗示價格和價值之間,總是有顯著差異。
市場不是唯一會出現次佳模仿行為的去中心化系統,比方說行軍蟻(army ant)就是另一個讓人著迷的案例。一群幾乎沒有視力的工蟻,有時候會和蟻群分開。由於沒有任何一隻螞蟻知道該如何讓整個蟻群重新定位,因此所有螞蟻都必須仰賴一個簡單的決策規則:跟著你前面那隻螞蟻走。如果有足夠多的螞蟻遵循這種策略(即達到臨界點),它們就會繞行成漩渦,一隻跟著一隻繞著圈子轉,直到死亡為止。曾有一個死亡漩渦繞行了兩天,圓週長達1,200 英尺(約366 公尺),轉一圈需要兩個半小時(見下頁圖表13.1)。最後,有一些工蟻脫離原有路徑,創造出必要的多樣性,才能打破漩渦。
當然,模仿是螞蟻天生的遺傳行為,而不是文化,而投資人則具備獨立的思考能力。然而,查爾斯•麥凱(Charles MacKay)曾在150 幾年前說過一句名言,提醒我們避免模仿的陷阱,這是一個古老問題。他說:「有句話說得好,人類的思考都是盲目從眾。他們會成群地瘋狂,然後一個接著一個慢慢恢復知覺。」
我願意—你呢?
並非所有資訊都一樣重要。穿著燕尾服在牧師和會眾面前說「我願意」的意義,比起老闆問你是否要在咖啡裡加牛奶時回答「我要」,來得更重要很多。妥善權衡生活裡各種資訊的重要程度非常重要,這一點對投資人來說尤為如此。
在投資的過程裡,我們需要收集和分析資訊。長久以來,投資人是透過收集資料或分析數據尋求競爭優勢。但是,隨著科技進步和法規的影響,近年來想要在取得資訊上具備優勢,變得愈來愈困難。
例如,網路化個人電腦的普及,讓資訊傳播變得非常迅速且幾乎沒有什麼成本。今天,網路當沖客可以隨時隨地取得的資訊,是25年前大型機構夢寐以求的內容。
此外,「公平資訊揭露規定」(Regulation FD)的目的是確保所有投資人,從最大的基金經理到最小的散戶投資人,都能同時接收到重要的資訊。
然而,分析師並未因此放棄取得專有資訊。近年來,我們看到調查和通路檢查(channel checks)的數量激增,以及企圖以其他不那麼正當的方式收集資訊。雖然追求更好的資訊並沒有錯,有一些公司也確實做得很好,但我質疑目前許多所謂的「專有」研究到底有多少投資價值。
我的懷疑來自三方面的考量。第一,投資人能否正確評估資訊。第二是抽樣問題,也就是分析師使用的抽樣技術,能夠真實反映人口基數到什麼程度。最後一個問題是,當今的專有研究,是否能夠為投資人帶來更好的投資績效。
篩選權重
1990 年代中期,比爾•蓋茲會隨身攜帶一份微軟的業務優先清單。網際網路才剛起步時,只排在他清單上的第五或第六名,但是,一旦蓋茲意識到網路對微軟未來的重要性時,他就把網路列為優先任務。蓋茲徹底重新權衡他已知的資訊,進而為微軟的股東帶來大量價值。同樣地,我們如何權衡資訊,將對我們看待世界和評估資產的方式有重大影響。
我們對特定假設有多少信心,通常取決於兩類證據:證據的強度,亦即極端程度;以及證據的重量, 亦即預測效度(predictive validity)。例如,你想檢驗一個假設:有一枚硬幣比較容易投出正面。在投擲的樣本裡,出現正面的次數比例反映出強度,而樣本數的大小則決定了重量。
機率論告訴我們該如何正確結合強度和重量的規則,然而大量實驗數據顯示,人類並不遵循這樣的理論。具體來說,證據的強度往往主導了人們的心。
這種偏誤會導致特定的過度自信和缺乏自信的模式。誠如許多華爾街贊助的研究結果顯示,當證據的強度高而重量較輕時,人們往往會過度自信;相反地,當證據的強度弱而重量較重時,人們往往會缺乏自信。
下方圖表17.1 顯示強度與重量的組合。當兩者都很高時,可能出現顯而易見的結論;當兩者皆低時,研究結果可能不太重要。然而,我們在剩下的兩個框框裡,可能出現誤判證據的狀況。
贏家詛咒(winner’s curse)是另一個具體例子,說明錯誤權衡資訊會帶來什麼風險。贏家詛咒是指在競爭激烈的拍賣會上,出價最高的人通常會為所購買的資產付出過高的溢價。因此,該投標者雖然「贏」得拍賣,卻得到「高溢價」的「詛咒」。投資人在評估資產價值時,經常把焦點放在其他出價者出的平均價格。但是,最後唯一重要的價值,是出價最高者願意支付的價格。
資訊權衡強調的是,並非所有資訊的價值和重要性都一樣。投資人必須時時謹慎,避免陷入因錯誤衡量資訊而產生的陷阱。
告訴我一些市場不知道的事
想要檢驗根據調查所做的研究有多少價值,最基本的標準是這研究是否能夠帶來更優秀的選股決策。在我們看來,這個答案就算不是否定的,頂多也只是模稜兩可。
第一個原因和市場吸收新資訊的速度有關。證據顯示,市場確實很快就會對新資訊有所反應,果真如此,想從這些數據獲得超額回報,似乎不太可能。想要取得資訊優勢確實不容易:賣方分析師的報告和通路檢查必須統一發布,而大規模的買方公司額外獲得的資訊,往往很快就會反映在股價上。與當前情況或未來可能發生的事情的相關資訊,最有可能已經有效反映在股票的價格上。相反地,有些證據顯示市場對於長期資訊的看法則十分短視。
第二個問題在於,理解一個產業或公司的基本面(或基本面的變化),與掌握當前股價的預期之間,有很大的差異。價格反映了市場集體的預期,而且包含的資訊往往遠超過任何一個人所能掌握的程度。所以關鍵問題在於,對你來說是新的資訊,對市場來說是否也是新的。
榮景不再
任何在電視上看過大自然節目的人,都很熟悉這樣的畫面:一隻年輕魯莽的獅子,挑戰獅群裡年邁的獅王,年邁的獅子以威嚇和適度的力量,成功壓制挑戰者一段時間。不過,獅王終究還是會屈服,被那頭年輕力壯的公獅取代。
當然,並非所有挑戰者都能成為獅群的新領袖,但獅群的新領袖都是挑戰者。2 商界和草原一樣,領導地位的爭奪戰永無止境。在自然界裡,成功表示可以把你的基因傳給下一代;在商界裡,成功指的是公司能夠創造出高經濟回報,股東的總回報率也會超過同業的平均水準。
思考領導者和挑戰者之間的較勁,對投資人有什麼幫助?這些較勁牽涉的不只是創新的思維模式,還反映了投資人對創新似乎有明顯的規律反應,因此了解這一點非常有用。投資人往往低估和高估成長的前景。
股票市場為創新的過程帶來一些曲折,因為股價反映的並非當下狀況,而是人們對未來的預期。投資人會用各種手段和方法,評估公司未來的現值—或者,更精確地說,是公司未來現金流的現值。股價反映的是投資人的集體期望。
因此,投資人不能只考慮到創新,還必須評估市場會如何看待創新。創新蘊藏著潛在的機會。
股市是終極的蜂巢嗎?
股票市場和社會性昆蟲與預測市場,有許多共同特徵。市場是由眾多個別投資人互動而成。我們已經看到,無論是昆蟲聚落還是預測市場,都能有效解決問題。為了更深入了解這些系統的運作方式,我們要同時檢視它們之間的相異與相似之處。
蜂巢和市場之間最大的差異,也許是激勵機制和價格的效果。在蜂巢裡,每隻蜜蜂的行為並不是為了最大化自己的福祉,而是為了整個蜂群(演化造成這種行為)。在市場裡,每個交易者都想要最大化自己的效益。這個差異可能讓昆蟲聚落比人類的市場更強韌,因為聚落比較不會像市場那樣,容易受到正向回饋的影響而變得脆弱。
此外,蜂巢沒有價格。價格在自由市場經濟體系裡扮演非常重要作用,因為價格可以協助人們決定如何分配資源。蜜蜂透過舞蹈傳遞資訊,但市場不只是單向告訴投資人價格為何,還會影響投資人的想法,進而引發不健康的模仿行為。
預測市場與股票市場很不一樣,因為前者有確切的時限,結果也很明確。這種特徵為結果劃定了邊界,有效限制投機的模仿行為。換句話說,趨勢動能策略在預測市場裡起不了作用。此外,在股市裡,股價的表現會影響公司的基本面前景。然而在預測市場裡,結果和市場本身相互獨立。
如果你去證券公司待一陣子,遲早會聽到人們說一些聽起來很有道理的話,例如:「嘿,如果我有51% 的時候是對的,我就會賺錢了。」如果你覺得這個說法有道理,那就繼續看下去吧,因為你即將看到投資最重要的一個概念。
首先我們要承認,人們心中深深烙印著「投資人賺錢的次數,應該多過賠錢的次數」的想法,而且這個想法從直覺上而言很有說服力。有一個資產經理人的故事,可以說明這種觀念的謬誤。
這位有名的投資人解釋,他們公司聘請了約20 位投資組合經理人,他是其中一位。該公司的財務主管,對旗下主動型基金經理人的整體績效很不滿意,決定評估每位經理的決策過程,然後淘汰表現不佳者。這位財務主管認為,就算是隨機選股,也會有一半左右的投資組合表現優於市場基準。所以,他決定根據每個組合裡打敗大盤的股票比例,來衡量經理人的績效。
這位投資組合經理人的狀況很奇特:在整個團隊裡,雖然他的總投資表現名列前茅,但他投資組合裡表現優異的股票比例,卻是最低的。財務主管馬上解僱所有表現「不佳」的經理,並和投資人召開一次會議,想弄清楚為什麼這位經理人有優異的績效,但打擊率(勝率)卻這麼糟糕。
投資組合經理的答案,解釋了所有涉及機率的活動,天生都有的重要課題:正確的次數不重要,正確的程度才重要。假設你有四支股票,其中三隻股票小跌,但第四支股票卻大漲。在這種情況下,即使你持有的大部分股票都下跌,你的投資組合仍然表現良好。
你必須以期望值分析(expected value analysis)來評估每一項投資,才能打造出可以帶來卓越績效的投資組合。讓人訝異的是,各個領域的頂尖思想家,包括賽馬投注、賭場賭博和投資,都強調過這一點,我們稱之為「貝比魯斯效應」(Babe Ruth effect):雖然魯斯常常被三振出局,他仍然是棒球史上最偉大的打擊手之一。
期望值這個課題之所以很普遍,是因為所有涉及機率的活動,都有相似的特徵。然而,要內化這個道理非常難,因為它在根本上有違人性。要指出上述財務主管邏輯裡的漏洞並不難,我也很容易理解他的想法。
做多、做空與賠率
塔雷伯(Nassim Taleb)在他那本引發爭議的著作《隨機騙局》(Fooled by Randomness)裡,分享過一個生動的故事,完美表達出期望值的概念。有一次塔雷伯在和其他交易員開會時,一位同事問他對市場的看法。他說,他認為市場在接下來一週內,微幅上漲的機率很高。人們進一步追問他,他認為上漲的機率有多少,他說70%。後來有人在會議中指出,塔雷伯大量做空標普500指數期貨,賭市場會下跌,似乎與他看漲的觀點自相矛盾。塔雷伯接著用期望值的觀點,解釋他的立場。下頁圖表3.1可以說明他的想法。
在這個例子裡,市場最有可能出現的結果是上漲,但期望值卻是負的,這是因為上漲和下跌會帶來不對稱的結果。現在,我們從股票市場來思考這件事。有時候,股價會完美訂價其價值。即使大多數時候(頻率),公司的股價會達到或些微超過其價值,股價也不會比價值高太多。但如果公司業績不如預期,股價就會重挫。高頻率出現讓人滿意的結果,但期望值卻是負的。
現在思考一下價值被低估的股票。這些公司大多數時候表現讓人失望,導致股價些微下跌,但如果出現正面的結果,股價就會劇烈上漲。在這種案例裡,機率偏向負面的結果,但期望值卻是正的。
投資人必須不看頻率,而是思考期望值。事實證明,這就是涉及機率領域裡,所有高績效人士的思考方式。然而,這樣的觀念在許多方面都很不自然,因為投資人希望他們的股票上漲,而非下跌。確實,展望理論最重要的實用結論,是投資人傾向太早賣掉賺錢的資產,這樣做可以滿足他們想要正確的欲望。同時,投資人也會太晚賣掉賠錢的資產,因為他們不想要承受損失。現在,我們來談三個不同機率領域裡優秀的實踐者。這三個領域是投資、賽馬下注和撲克牌的21點。
孔雀魚的模仿行為
從表面來看,生物學家李•杜加欽(Lee Dugatkin)似乎太閒了,因為他的研究重點看似想要解決一道深奧的問題:雌性孔雀魚如何選擇配偶。結果顯示,雌性孔雀魚先天偏好亮橘色的雄性孔雀魚。不過,當他讓一些母魚看到其他母魚選擇深色的雄魚後,其他母魚也開始選擇深色的雄魚。讓人驚訝的是,在許多情況下,看過同類選擇深色雄魚的母魚,會推翻自己的的本能,轉而模仿其他母魚。
為什麼會有人在意雌性孔雀魚如何選擇伴侶?這個答案點出一個熱門議題的核心,即動物行為是否只由基因決定,或是文化也發揮了一定的作用。杜加欽研究顯示,在動物界裡,模仿顯然以文化傳遞的形式存在,並且在物種發展裡扮演重要作用。
當然,模仿對人類來說是一種重要的力量,時尚、潮流和傳統都是模仿的結果。由於投資在本質上是一種社會性活動,因此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模仿在市場裡也扮演發揮重要作用。
大多數投資人和商人,都有基本的理念來規範他們的行為,就像基因會決定孔雀魚選擇配偶的方式一樣。然而,我們知道對於基金經理人和孔雀魚來說,模仿有時候會深刻影響他們的決策。那麼,模仿對投資人來說,是好是壞呢?
跟著你前面的螞蟻走
模仿是正向回饋的主要機制之一,例如動能投資(momentum investing)假設正在上漲的股票,將繼續上漲。如果有夠多的投資人遵循這個策略,那麼認為價格會持續走高的預言,就可能自我實現。
不過,大多數投資人對於單純的模仿會有疑慮,所以他們會掩飾自己的模仿行為。但其實模仿往往有其合理的根據,例如,思考以下幾種情況:
資訊不對稱:當其他投資人比你更了解某項投資時,模仿他們可能對你很有利。我們經常在日常生活的決策使用模仿策略,以利用他人的專業知識。
代理人成本:許多資產管理公司必須在最大化投資組合的績效(長期的絕對回報),以及最大化資產管理業務的價值(透過取得資產和收取手續費)之間取捨。選擇最大化資產管理公司業務的企業,有動機模仿其他人的做法。這種模仿行為,會讓投資組合相對於市場基準的追蹤誤差降到最小。
從眾偏好:就像凱因斯所說,「世俗智慧告訴我們,如果考慮到自己的名聲,那麼從眾失敗也比特立獨行而成功更好。」人類喜歡成為群體的一部分,因為群體常常讓我們覺得安全又安心。
在某些情況下,正向回饋確實可取,投資人的模仿行為也很合理,然而正向回饋也可能發展得過於極端。
財務經濟學家所說的羊群效應,是指一大群投資人根據別人的行為做相同選擇,而不仰賴自己的知識。實際上,當正向回饋主導狀況時,就會出現羊群效應。由於市場需要正向和負向回饋之間處在平衡狀態,因此這種不平衡會讓市場的效率低落。上述看法與傳統的觀點相左,傳統上認為投資人只會根據基本資訊進行交易。
我們也許永遠無法知道,到底多少的正向回饋屬於過量。許多科學研究顯示,在創新和概念傳播的過程中,通常會有一個臨界點,一旦傳播超過臨界點,正向回饋的效應便取得控制,於是正向的趨勢就能主導整個系統。市場泡沫和崩盤的相對頻率,強烈暗示價格和價值之間,總是有顯著差異。
市場不是唯一會出現次佳模仿行為的去中心化系統,比方說行軍蟻(army ant)就是另一個讓人著迷的案例。一群幾乎沒有視力的工蟻,有時候會和蟻群分開。由於沒有任何一隻螞蟻知道該如何讓整個蟻群重新定位,因此所有螞蟻都必須仰賴一個簡單的決策規則:跟著你前面那隻螞蟻走。如果有足夠多的螞蟻遵循這種策略(即達到臨界點),它們就會繞行成漩渦,一隻跟著一隻繞著圈子轉,直到死亡為止。曾有一個死亡漩渦繞行了兩天,圓週長達1,200 英尺(約366 公尺),轉一圈需要兩個半小時(見下頁圖表13.1)。最後,有一些工蟻脫離原有路徑,創造出必要的多樣性,才能打破漩渦。
當然,模仿是螞蟻天生的遺傳行為,而不是文化,而投資人則具備獨立的思考能力。然而,查爾斯•麥凱(Charles MacKay)曾在150 幾年前說過一句名言,提醒我們避免模仿的陷阱,這是一個古老問題。他說:「有句話說得好,人類的思考都是盲目從眾。他們會成群地瘋狂,然後一個接著一個慢慢恢復知覺。」
我願意—你呢?
並非所有資訊都一樣重要。穿著燕尾服在牧師和會眾面前說「我願意」的意義,比起老闆問你是否要在咖啡裡加牛奶時回答「我要」,來得更重要很多。妥善權衡生活裡各種資訊的重要程度非常重要,這一點對投資人來說尤為如此。
在投資的過程裡,我們需要收集和分析資訊。長久以來,投資人是透過收集資料或分析數據尋求競爭優勢。但是,隨著科技進步和法規的影響,近年來想要在取得資訊上具備優勢,變得愈來愈困難。
例如,網路化個人電腦的普及,讓資訊傳播變得非常迅速且幾乎沒有什麼成本。今天,網路當沖客可以隨時隨地取得的資訊,是25年前大型機構夢寐以求的內容。
此外,「公平資訊揭露規定」(Regulation FD)的目的是確保所有投資人,從最大的基金經理到最小的散戶投資人,都能同時接收到重要的資訊。
然而,分析師並未因此放棄取得專有資訊。近年來,我們看到調查和通路檢查(channel checks)的數量激增,以及企圖以其他不那麼正當的方式收集資訊。雖然追求更好的資訊並沒有錯,有一些公司也確實做得很好,但我質疑目前許多所謂的「專有」研究到底有多少投資價值。
我的懷疑來自三方面的考量。第一,投資人能否正確評估資訊。第二是抽樣問題,也就是分析師使用的抽樣技術,能夠真實反映人口基數到什麼程度。最後一個問題是,當今的專有研究,是否能夠為投資人帶來更好的投資績效。
篩選權重
1990 年代中期,比爾•蓋茲會隨身攜帶一份微軟的業務優先清單。網際網路才剛起步時,只排在他清單上的第五或第六名,但是,一旦蓋茲意識到網路對微軟未來的重要性時,他就把網路列為優先任務。蓋茲徹底重新權衡他已知的資訊,進而為微軟的股東帶來大量價值。同樣地,我們如何權衡資訊,將對我們看待世界和評估資產的方式有重大影響。
我們對特定假設有多少信心,通常取決於兩類證據:證據的強度,亦即極端程度;以及證據的重量, 亦即預測效度(predictive validity)。例如,你想檢驗一個假設:有一枚硬幣比較容易投出正面。在投擲的樣本裡,出現正面的次數比例反映出強度,而樣本數的大小則決定了重量。
機率論告訴我們該如何正確結合強度和重量的規則,然而大量實驗數據顯示,人類並不遵循這樣的理論。具體來說,證據的強度往往主導了人們的心。
這種偏誤會導致特定的過度自信和缺乏自信的模式。誠如許多華爾街贊助的研究結果顯示,當證據的強度高而重量較輕時,人們往往會過度自信;相反地,當證據的強度弱而重量較重時,人們往往會缺乏自信。
下方圖表17.1 顯示強度與重量的組合。當兩者都很高時,可能出現顯而易見的結論;當兩者皆低時,研究結果可能不太重要。然而,我們在剩下的兩個框框裡,可能出現誤判證據的狀況。
贏家詛咒(winner’s curse)是另一個具體例子,說明錯誤權衡資訊會帶來什麼風險。贏家詛咒是指在競爭激烈的拍賣會上,出價最高的人通常會為所購買的資產付出過高的溢價。因此,該投標者雖然「贏」得拍賣,卻得到「高溢價」的「詛咒」。投資人在評估資產價值時,經常把焦點放在其他出價者出的平均價格。但是,最後唯一重要的價值,是出價最高者願意支付的價格。
資訊權衡強調的是,並非所有資訊的價值和重要性都一樣。投資人必須時時謹慎,避免陷入因錯誤衡量資訊而產生的陷阱。
告訴我一些市場不知道的事
想要檢驗根據調查所做的研究有多少價值,最基本的標準是這研究是否能夠帶來更優秀的選股決策。在我們看來,這個答案就算不是否定的,頂多也只是模稜兩可。
第一個原因和市場吸收新資訊的速度有關。證據顯示,市場確實很快就會對新資訊有所反應,果真如此,想從這些數據獲得超額回報,似乎不太可能。想要取得資訊優勢確實不容易:賣方分析師的報告和通路檢查必須統一發布,而大規模的買方公司額外獲得的資訊,往往很快就會反映在股價上。與當前情況或未來可能發生的事情的相關資訊,最有可能已經有效反映在股票的價格上。相反地,有些證據顯示市場對於長期資訊的看法則十分短視。
第二個問題在於,理解一個產業或公司的基本面(或基本面的變化),與掌握當前股價的預期之間,有很大的差異。價格反映了市場集體的預期,而且包含的資訊往往遠超過任何一個人所能掌握的程度。所以關鍵問題在於,對你來說是新的資訊,對市場來說是否也是新的。
榮景不再
任何在電視上看過大自然節目的人,都很熟悉這樣的畫面:一隻年輕魯莽的獅子,挑戰獅群裡年邁的獅王,年邁的獅子以威嚇和適度的力量,成功壓制挑戰者一段時間。不過,獅王終究還是會屈服,被那頭年輕力壯的公獅取代。
當然,並非所有挑戰者都能成為獅群的新領袖,但獅群的新領袖都是挑戰者。2 商界和草原一樣,領導地位的爭奪戰永無止境。在自然界裡,成功表示可以把你的基因傳給下一代;在商界裡,成功指的是公司能夠創造出高經濟回報,股東的總回報率也會超過同業的平均水準。
思考領導者和挑戰者之間的較勁,對投資人有什麼幫助?這些較勁牽涉的不只是創新的思維模式,還反映了投資人對創新似乎有明顯的規律反應,因此了解這一點非常有用。投資人往往低估和高估成長的前景。
股票市場為創新的過程帶來一些曲折,因為股價反映的並非當下狀況,而是人們對未來的預期。投資人會用各種手段和方法,評估公司未來的現值—或者,更精確地說,是公司未來現金流的現值。股價反映的是投資人的集體期望。
因此,投資人不能只考慮到創新,還必須評估市場會如何看待創新。創新蘊藏著潛在的機會。
股市是終極的蜂巢嗎?
股票市場和社會性昆蟲與預測市場,有許多共同特徵。市場是由眾多個別投資人互動而成。我們已經看到,無論是昆蟲聚落還是預測市場,都能有效解決問題。為了更深入了解這些系統的運作方式,我們要同時檢視它們之間的相異與相似之處。
蜂巢和市場之間最大的差異,也許是激勵機制和價格的效果。在蜂巢裡,每隻蜜蜂的行為並不是為了最大化自己的福祉,而是為了整個蜂群(演化造成這種行為)。在市場裡,每個交易者都想要最大化自己的效益。這個差異可能讓昆蟲聚落比人類的市場更強韌,因為聚落比較不會像市場那樣,容易受到正向回饋的影響而變得脆弱。
此外,蜂巢沒有價格。價格在自由市場經濟體系裡扮演非常重要作用,因為價格可以協助人們決定如何分配資源。蜜蜂透過舞蹈傳遞資訊,但市場不只是單向告訴投資人價格為何,還會影響投資人的想法,進而引發不健康的模仿行為。
預測市場與股票市場很不一樣,因為前者有確切的時限,結果也很明確。這種特徵為結果劃定了邊界,有效限制投機的模仿行為。換句話說,趨勢動能策略在預測市場裡起不了作用。此外,在股市裡,股價的表現會影響公司的基本面前景。然而在預測市場裡,結果和市場本身相互獨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