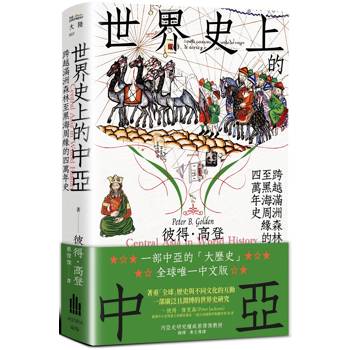導言 民族的層積(摘錄)
在歷史上,中亞人並沒有一個總括的詞語來稱呼該地區與諸民族。中亞人認同的主要構成要素是氏族、部族、地位、地域或宗教等紐帶,而且這些紐帶常常是多重疊加的。對其廣大遊牧人口而言,政治劃界並不重要。控制了人民就控制了領土。
中亞作為千年來東西方之間的橋樑,受到了中國、印度、伊朗、地中海諸島,以及新近的俄國所影響。它也是薩滿、佛教徒、祆教徒、猶太教徒、基督徒與穆斯林的彙聚之處。其變換的族群、語言、政治與文化邊界包含了兩種互相影響卻有基礎差異的生活方式,而這兩者各居於不同的生態宜居區當中:一為綠洲定居人群,另一則為草原遊牧民。上古與中世紀的觀察家認為中亞位於「文明」的邊際。由於中亞孕育了前現代時期最廣大的帝國,故現代史學家視其為歐亞歷史的「核心地區」或「樞紐」。
中亞占了地球陸地將近七分之一的面積,約八百萬平方英里。今天,中亞西部的人群主要是穆斯林,並且由新近獨立的前蘇聯國家所組成:土庫曼、烏茲別克、哈薩克、吉爾吉斯與塔吉克,即歷史上所謂的「西突厥斯坦」(Turkestan)。蘇聯的政策決定了這些現代國家的名稱與邊界,企圖將政治劃分的領土與特定的民族-語言群體聯結在一起,而這些群體則依據政治需求來加以定義。此舉亦為中亞史上首見。以穆斯林為主的中亞地區亦包括了中國新疆(亦稱為「東突厥斯坦」)以及其原住民維吾爾族和其他突厥-穆斯林人口。現今位於阿姆河與新疆之間的大半區域,在語言上通行突厥語,不過在過去主要以伊朗語為主。這個語言轉變已經進行了1500年,並且創造了一個「突厥-波斯」文化世界。往南,與其北方鄰居有著族群性和語言連結的阿富汗則是這個混合的縮影。中亞東部主要人口為佛教徒,由蒙古(今日被分隔為蒙古國與中國內蒙古自治區)與滿洲地區所組成。西藏儘管在語言上與中亞截然不同,不過在中亞事務上卻多次扮演重要角色。
位於伏爾加河與西伯利亞西部的森林-草原區則有大量穆斯林突厥人口,其歷史與文化根源則位於中亞。在政治與文化上,中亞作為民族的輸出者,其範圍也延伸到匈牙利、烏克蘭、俄國與中東。混合了匈牙利到阿爾泰山(Altay Mountains)的大草原(prairie)、沙漠與半沙漠的草原(steppe),再加上滿洲地區(Manchuria)的森林,就是中亞主要的生態區。儘管中亞一年當中有三分之一的時間被雪所覆蓋,其豐美的草場仍舊能養育廣大的畜群。在海一般浩瀚草場的沿邊,酷熱的沙漠(綠洲點綴其間)則是最常見的特徵,特別在南邊。這個區域的乾燥是如此之強烈,以至匈牙利裔英籍探險家奧萊爾.斯坦因爵士(Sir Aurel Stein)於二十世紀初從新疆東部的羅布泊(Lop or)一處保存良好之中世紀「廢物堆」發掘的材料中,仍舊能夠聞到其強烈的惡臭氣味。而從白雪覆蓋之山上融化的雪水所形成的河流,則會在夏季的暑熱下變成水窪或乾涸的河床。土壤侵蝕與乾燥的問題持續存在。
引人注目的是,植物在沙漠中仍舊存活著,在春季時開花,而在漫長的夏季與冬季休眠。農業之所以能在綠洲興盛起來,則是拜河流的滋養所賜,如澤拉夫尚河(Zeravshan)、阿姆河(Amu Darya)與錫爾河(Syr Darya)。後兩者流入鹹海(Aral Sea,實際上算是個大湖),但如今它遭到嚴重汙染一事則令人感到遺憾。中亞的河流一年中有超過二分之一的時間處於部分冰封狀態,而且這段時間常常會延長。不同於中國、印度、美索不達米亞與埃及等四大文明,中亞的河流沿岸相對人煙稀少,而且也不是商業與交通動脈。蒙古的鄂爾渾河(Orkhon)、色楞格河(Selenge)與克魯倫河(Kerulen)與偉大的草原帝國有所關聯,但是在其中並未扮演主要的經濟角色。除了捕魚以外,遊牧民從不利用河流。所謂的水上旅行通常指的就只是用動物皮所製成的皮筏渡過河流淺灘而已。
草原居民與其鄰近農業國家(agrarian states)之間的互動形塑了吾人關於中亞的知識。定居社會的記載通常存有對遊牧民的文化偏見,認為這些人住在「不適人居的蠻荒之地」。古代波斯傳統將阿姆河以北使用伊朗語(及後來的突厥語)之兇猛民族的遊牧世界「圖蘭」(Turan)與「伊朗」(Iran,歷史上又稱為「波斯」)對比為善惡之爭。許多用來稱呼這些民族的漢字習慣上英譯為「barbarian」,但其實這些詞語有著微小差異,其意義則可指稱從相對中性的「附庸」(vassal)與「域外」(foreign),到帶有貶義的「野蠻」(barbarous)。中國史家無意隱藏他們對遊牧民「原始」習俗、飲食,以及用動物毛皮與毛氈製成之衣著的嫌惡。
然而,考古的發現顯示有部分遊牧民過著富裕甚至奢侈的生活,而且這些情形也被前述抱持輕蔑態度的同時期觀察家所證實。……事實上,遊牧民與其「已開化」的鄰居相較之下並沒有比較嗜血或貪婪。生活在草原上是艱苦的,但是許多遊牧民感覺他們的生活比那些一輩子辛苦耕地的人來得優越許多。由於具有豐富與世界性的文化加上其農業和商業導向的經濟,中亞都市地區與其遊牧鄰居存在著共生關係,並且扮演連結草原與農業區的角色。
中亞歷史的關鍵主題之一就是民族和語言的移動以及新族群實體的創造。語言通常被歸類為許多「語系」(families),意指這些語言在語言學上(但不必然是生物學上)有著共同起源。在中亞歷史上有兩種語系占有主宰地位,分別是印歐語系和阿爾泰語系。印歐人於西元前4500年至西元前4000年間在黑海草原上形成了一個語言共同體。到了西元前3000年或西元前2500年,這個共同體開始分裂,部分人群移入中亞、南亞與西亞,以及地中海北岸。其語言學上的後裔從南亞的印度語使用者(印地-烏爾都語〔Hindi-Urdu languages〕、旁遮普語、以及許多在印度次大陸上的其他語言)與伊朗、阿富汗與中亞的伊朗語使用者(波斯語、塔吉克語、普什圖語和其他伊朗語),延伸到不列顛島並包括所有歐洲語言,但不包括巴斯克語、芬蘭語(Finnish)、愛沙尼亞語和相關的芬蘭語(Finnic),及其遠親匈牙利語。
阿爾泰語的使用者位於南西伯利亞、東蒙古與滿洲地區。阿爾泰語的成員包括了土耳其語和在中亞所使用的其他各種突厥語(如烏茲別克語、哈薩克語和維吾爾語),另外還有蒙古語。在蒙古國、內蒙以及中國和俄國接壤地區(包括伏爾加河地區的卡爾梅克人)境內發現了各類蒙古語形式。滿語(如今瀕臨滅絕)及在滿洲地區人口較少的通古斯民族則構成了阿爾泰語的東部分支。有些學者會將韓語及日語的祖先納入阿爾泰語的「家族」當中。而其他學者不僅拒斥這個連結,而且也爭論阿爾泰語(Altaic language)作為一個語系的想法。更確切地說,他們主張不同阿爾泰語言之間的相似之處僅僅是數個世紀以來互動及語彙採借的結果。
如同中亞歷史所充分證明的,中世紀與現代「民族」(peoples)常常是許多族群和語言層在時間中混合的產物,並且帶有不小程度的政治算計,特別是在現代。一種語言散播的方式並非總是那麼清楚無疑。征服、大規模遷徙,以及一個民族被另一個完全取代是一種模式。而另一種模式的特徵則是逐漸滲透、互動,與因而產生的雙語並用(bilingualism)。遷徙的人群本身常常就是廣泛的族群和語言互動的產物。隨著每次新的移動,族名以及隨其名稱相關的語言改變會以接力賽的形式傳遞給另一個人群。其結果是,擁有相同名稱且使用同一語言的人們可能實際上具有多重與相異的起源。民族的移動製造了一幅錯綜複雜的馬賽克圖案。今日我們所見到的族群-語言地圖僅僅是在某個時間點上對前述混合的點滴瞭解,而這個混合已經發生了超過千年以上。民族的創造仍然是個持續進行中的過程。
在歷史上,中亞人並沒有一個總括的詞語來稱呼該地區與諸民族。中亞人認同的主要構成要素是氏族、部族、地位、地域或宗教等紐帶,而且這些紐帶常常是多重疊加的。對其廣大遊牧人口而言,政治劃界並不重要。控制了人民就控制了領土。
中亞作為千年來東西方之間的橋樑,受到了中國、印度、伊朗、地中海諸島,以及新近的俄國所影響。它也是薩滿、佛教徒、祆教徒、猶太教徒、基督徒與穆斯林的彙聚之處。其變換的族群、語言、政治與文化邊界包含了兩種互相影響卻有基礎差異的生活方式,而這兩者各居於不同的生態宜居區當中:一為綠洲定居人群,另一則為草原遊牧民。上古與中世紀的觀察家認為中亞位於「文明」的邊際。由於中亞孕育了前現代時期最廣大的帝國,故現代史學家視其為歐亞歷史的「核心地區」或「樞紐」。
中亞占了地球陸地將近七分之一的面積,約八百萬平方英里。今天,中亞西部的人群主要是穆斯林,並且由新近獨立的前蘇聯國家所組成:土庫曼、烏茲別克、哈薩克、吉爾吉斯與塔吉克,即歷史上所謂的「西突厥斯坦」(Turkestan)。蘇聯的政策決定了這些現代國家的名稱與邊界,企圖將政治劃分的領土與特定的民族-語言群體聯結在一起,而這些群體則依據政治需求來加以定義。此舉亦為中亞史上首見。以穆斯林為主的中亞地區亦包括了中國新疆(亦稱為「東突厥斯坦」)以及其原住民維吾爾族和其他突厥-穆斯林人口。現今位於阿姆河與新疆之間的大半區域,在語言上通行突厥語,不過在過去主要以伊朗語為主。這個語言轉變已經進行了1500年,並且創造了一個「突厥-波斯」文化世界。往南,與其北方鄰居有著族群性和語言連結的阿富汗則是這個混合的縮影。中亞東部主要人口為佛教徒,由蒙古(今日被分隔為蒙古國與中國內蒙古自治區)與滿洲地區所組成。西藏儘管在語言上與中亞截然不同,不過在中亞事務上卻多次扮演重要角色。
位於伏爾加河與西伯利亞西部的森林-草原區則有大量穆斯林突厥人口,其歷史與文化根源則位於中亞。在政治與文化上,中亞作為民族的輸出者,其範圍也延伸到匈牙利、烏克蘭、俄國與中東。混合了匈牙利到阿爾泰山(Altay Mountains)的大草原(prairie)、沙漠與半沙漠的草原(steppe),再加上滿洲地區(Manchuria)的森林,就是中亞主要的生態區。儘管中亞一年當中有三分之一的時間被雪所覆蓋,其豐美的草場仍舊能養育廣大的畜群。在海一般浩瀚草場的沿邊,酷熱的沙漠(綠洲點綴其間)則是最常見的特徵,特別在南邊。這個區域的乾燥是如此之強烈,以至匈牙利裔英籍探險家奧萊爾.斯坦因爵士(Sir Aurel Stein)於二十世紀初從新疆東部的羅布泊(Lop or)一處保存良好之中世紀「廢物堆」發掘的材料中,仍舊能夠聞到其強烈的惡臭氣味。而從白雪覆蓋之山上融化的雪水所形成的河流,則會在夏季的暑熱下變成水窪或乾涸的河床。土壤侵蝕與乾燥的問題持續存在。
引人注目的是,植物在沙漠中仍舊存活著,在春季時開花,而在漫長的夏季與冬季休眠。農業之所以能在綠洲興盛起來,則是拜河流的滋養所賜,如澤拉夫尚河(Zeravshan)、阿姆河(Amu Darya)與錫爾河(Syr Darya)。後兩者流入鹹海(Aral Sea,實際上算是個大湖),但如今它遭到嚴重汙染一事則令人感到遺憾。中亞的河流一年中有超過二分之一的時間處於部分冰封狀態,而且這段時間常常會延長。不同於中國、印度、美索不達米亞與埃及等四大文明,中亞的河流沿岸相對人煙稀少,而且也不是商業與交通動脈。蒙古的鄂爾渾河(Orkhon)、色楞格河(Selenge)與克魯倫河(Kerulen)與偉大的草原帝國有所關聯,但是在其中並未扮演主要的經濟角色。除了捕魚以外,遊牧民從不利用河流。所謂的水上旅行通常指的就只是用動物皮所製成的皮筏渡過河流淺灘而已。
草原居民與其鄰近農業國家(agrarian states)之間的互動形塑了吾人關於中亞的知識。定居社會的記載通常存有對遊牧民的文化偏見,認為這些人住在「不適人居的蠻荒之地」。古代波斯傳統將阿姆河以北使用伊朗語(及後來的突厥語)之兇猛民族的遊牧世界「圖蘭」(Turan)與「伊朗」(Iran,歷史上又稱為「波斯」)對比為善惡之爭。許多用來稱呼這些民族的漢字習慣上英譯為「barbarian」,但其實這些詞語有著微小差異,其意義則可指稱從相對中性的「附庸」(vassal)與「域外」(foreign),到帶有貶義的「野蠻」(barbarous)。中國史家無意隱藏他們對遊牧民「原始」習俗、飲食,以及用動物毛皮與毛氈製成之衣著的嫌惡。
然而,考古的發現顯示有部分遊牧民過著富裕甚至奢侈的生活,而且這些情形也被前述抱持輕蔑態度的同時期觀察家所證實。……事實上,遊牧民與其「已開化」的鄰居相較之下並沒有比較嗜血或貪婪。生活在草原上是艱苦的,但是許多遊牧民感覺他們的生活比那些一輩子辛苦耕地的人來得優越許多。由於具有豐富與世界性的文化加上其農業和商業導向的經濟,中亞都市地區與其遊牧鄰居存在著共生關係,並且扮演連結草原與農業區的角色。
中亞歷史的關鍵主題之一就是民族和語言的移動以及新族群實體的創造。語言通常被歸類為許多「語系」(families),意指這些語言在語言學上(但不必然是生物學上)有著共同起源。在中亞歷史上有兩種語系占有主宰地位,分別是印歐語系和阿爾泰語系。印歐人於西元前4500年至西元前4000年間在黑海草原上形成了一個語言共同體。到了西元前3000年或西元前2500年,這個共同體開始分裂,部分人群移入中亞、南亞與西亞,以及地中海北岸。其語言學上的後裔從南亞的印度語使用者(印地-烏爾都語〔Hindi-Urdu languages〕、旁遮普語、以及許多在印度次大陸上的其他語言)與伊朗、阿富汗與中亞的伊朗語使用者(波斯語、塔吉克語、普什圖語和其他伊朗語),延伸到不列顛島並包括所有歐洲語言,但不包括巴斯克語、芬蘭語(Finnish)、愛沙尼亞語和相關的芬蘭語(Finnic),及其遠親匈牙利語。
阿爾泰語的使用者位於南西伯利亞、東蒙古與滿洲地區。阿爾泰語的成員包括了土耳其語和在中亞所使用的其他各種突厥語(如烏茲別克語、哈薩克語和維吾爾語),另外還有蒙古語。在蒙古國、內蒙以及中國和俄國接壤地區(包括伏爾加河地區的卡爾梅克人)境內發現了各類蒙古語形式。滿語(如今瀕臨滅絕)及在滿洲地區人口較少的通古斯民族則構成了阿爾泰語的東部分支。有些學者會將韓語及日語的祖先納入阿爾泰語的「家族」當中。而其他學者不僅拒斥這個連結,而且也爭論阿爾泰語(Altaic language)作為一個語系的想法。更確切地說,他們主張不同阿爾泰語言之間的相似之處僅僅是數個世紀以來互動及語彙採借的結果。
如同中亞歷史所充分證明的,中世紀與現代「民族」(peoples)常常是許多族群和語言層在時間中混合的產物,並且帶有不小程度的政治算計,特別是在現代。一種語言散播的方式並非總是那麼清楚無疑。征服、大規模遷徙,以及一個民族被另一個完全取代是一種模式。而另一種模式的特徵則是逐漸滲透、互動,與因而產生的雙語並用(bilingualism)。遷徙的人群本身常常就是廣泛的族群和語言互動的產物。隨著每次新的移動,族名以及隨其名稱相關的語言改變會以接力賽的形式傳遞給另一個人群。其結果是,擁有相同名稱且使用同一語言的人們可能實際上具有多重與相異的起源。民族的移動製造了一幅錯綜複雜的馬賽克圖案。今日我們所見到的族群-語言地圖僅僅是在某個時間點上對前述混合的點滴瞭解,而這個混合已經發生了超過千年以上。民族的創造仍然是個持續進行中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