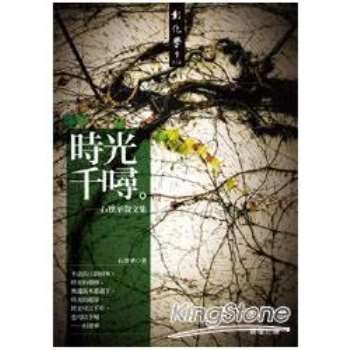凝注的餘光
PART1.第一人稱敍述觀點的逐漸淡入
置介聲光映象的影視空間,畫面中央,通常是視覺重心之所在,而在景格邊緣,亦即光的邊陲地帶,來來去去的角色,只給人們過眼即忘的瞬間印象。但是,懂得電影的人都會告訴你,一些最富戲劇變化的指涉符號,往往就存在畫面的邊緣地帶。
我熒熲眸光凝注不休的這個世界,以每秒二十四格,永不停止的流動狀態變換各種聲光畫面,於是,我常置身煙硝的腥嗆與過勞人體的酸味夾揉混雜的空氣裡,看到不同形式的崩塌與興立,看到等質謬忽的低調悲情與錯亂賁亢,看到被高吊掛醃漬風乾的公權與誠信,看到矮小亞洲的脫離自卑,看到政經主次易位的運會之趨……,當然,我更看到以快報姿態隨時插播畫面,碧藍海中一座心律不整的島,和它隨時都有可能出狀況,卻總在陡峭與平滑間不斷耍弄人們預期的心電圖。
在這樣一個你永遠不知道下一步會發生什麼事的蒙太奇世界,存在,已意味過去;猶豫,就已被擠落,你不得不承認,與這個世界相互凝注這件事,真是感官被餵得打飽嗝,縟麗無可名狀的特殊視覺經驗。可是,我是一個愛看電影的人,即便我凝注畫面中央的熱誠,一如拳著畸厚手套始終在場邊打轉,渴望加入棒球遊戲的涎羡小孩,但我仍能清醒記憶懂得閱讀電影的人的那句話,並且實在履踐了他們先知指示般的一句叮囑:
「當你凝注主畫面的同時,別忘了,善用眼睛的餘光。」
PART2. 畫面的左下角邊緣
梁祝電影插曲穿窗走戶的夏日黃昏,客廳裡半牆夕陽,油煎魚香濁濃了迷漫一室的燠悶暑氣,父親和一位陌生訪客坐在屋角的藤椅低聲交談。當夕陽走完一整面粉白的牆,訪客交給父親一個素色包袱,便帶著夕陽一起歛影消跡。
那布包袱裡藏神奇魔咒,它讓如山雄奇的靜毅的父親,剎那之間傾圮崩塌。
父親直直跪在攤開的素布前,縱聲嚎哭,素布上羅列一把小佩刀、一枚繪上青天白日的軍徽、和一張戴軍帽、斜披佩槍的軍人半身戎裝照片。父親的哭聲重且長,暮色掩襲,我稚犀的臉印貼陳舊紗門,從門外凝視父親許久,一直用靜默伴隨,從此不能忘卻跪地垂首的父親的身影,和龐巨垂臨,鏡頭仰攝而成的,那個詭橘滾染猛藍,情調稠穠誇艷的夏日晚天意象。
那是祖父昔日部屬輾轉由大陸帶來的祖父的遺物,撤守時,祖父負責掩護其他軍團的撤離,倉皇中不幸陷敵遇難。那天父親一直抬不起的臉朝西,望向大洋之外的自己的家鄉。
微渺個人的生命情事於那個壯闊年代,是拍不到岸的遙海波濤,無數次浪落之後的一次狂巨捲襲,也只是再一次的浪落,終其一生,我沒看過父親哭過第二次。
那年,我八歲,企圖用紗門外一顆幼細困惑的心,貼熨兜收父親哀長不絕哭聲而不能,後來我百出不窮的童年夢想中最持久的一樁;心中最初最深耕的犂痕,生命中一直存在的負擔,就是反攻大陸。
而我的反攻大陸,單純只意指父親的回家鄉。
蓬蓬大大的棉花糖,一口用力咬下,住往只有亂亂黏在唇上的絲縷糖絮,和滿口腔無味的虛空。過大的夢想就是一朵實實虛虛的棉花糖,「反攻大陸」終究不如我年少在燈下,獨自玩得幾近耽溺的一場筆尖和線條協力而成的秘密遊戲。
我讀本國地理那幾年,每當中國大陸地圖葉片一般攤展我眼前,我的眼光總能迅速柔焦其他省分,獨獨定位「湖南」這一省。燈下的「湖南」像花瓣大片疊複、軟枝墜垂的花的半羞合側影,湘、資、沅、澧四條向心水系的主流支脈由花托放射流成片片花瓣的鋸齒瓣沿,長沙在東北、衡陽在東南、父親的家在西南。鏡頭拉遠便看清楚台灣與這側影的花,恰恰形成擦肩走過的背背相對。
我的鉛筆尖由台灣略弓的背脊開始走動,朝左下斜斜滑下順利越過南海,登岸珠江三角洲,再一段短短溯筆便上至繁華廣州。當筆尖由廣州搭隨今已稱京廣鐵路粵漢鐵路,就是一段輕鬆之旅了。翻南嶺、入湖南、衡陽可以是終點,換轉公路再朝西;或者,乾脆筆尖不停,隨粗黑鐵路直上名城長沙,然經由水路,一路搖櫓,看帆影翩遷、涉楚辭浪漫,下湘江,回家鄉。而如果,從浙江上岸,那麼……。由某地到某地鐵路轉換方式,是那幾年地理科的熱門題型,也使我初初恣享心靈世界卓然獨特的自我而足。父親沒等到回鄉便病逝,只我在十七歲一年陪過他一次又一次,下湘江,回家鄉。
當你被電影畫面深深觸動的剎那總是靜靜默無言,用言語詮釋感受,那是感受轉醒之後才具有的意識及能力。我是在父親死後,才開始了解父親。
父親死後,我生命履帶不疾不徐轉運如昔,只是在很多個不同的時空,意識驟然斷電動作凝凍,心念畫面嘩然一片電波急雨,然後困愁不安六合八荒湧襲撲漫,我便不顧一切的,深切想見父親,也常會在不同場景的街道戞然乍見酷似父親的背影,便緊緊追隨且超前,再用孤注一擲後翻抓底牌的氣態扭身照見……。渴望是一種追尋的動力,但它最崇高深沉的狀態,可以超越一切物質非物質現象,成為宗教的神秘意識。我倉皇於茫茫人海想見父親瀕臨狂亂盲目,是否所有事物最深最盡處,皆會生成鋪染深深淺淺宿命色彩的非理性?我因此在非理性與宗教的無界面擺搖宛若深海之荇,終究讀出生命的最大虔誠在於深邃的渴望,而有些虔誠像拚盡生命全力的出拳甚且或縱身撲去,卻在虛無空氣中大力落空那般,你只能啞啞地無言。
那麼,隻身至異鄉不愛回顧不細說心情的父親,他的很特別禮遇白髮皤然的老者,他的不得不獻唱時老哼唱別人聽不懂的湖南小曲,他發病初期不斷夢見的迢遙故鄉親友,以及終其一生他很常有的獨坐沉思,就是父親最失重虔敬、最無力的全力了。生命原是悲傷基調荒謬基調荒謬本質的多形式物質,我因失去父親而了解父親。
歸鄉,過氣的世紀夢,曾是父親生命中一言不發的沉重,一開始我就說了,在高潮峰迭聲光倏幻充滿無限可能的大時代,微渺個人的塵夢與夢斷,運命梭織的乖謬與辛酸,都不過是,人們眼光不到的邊緣畫面。
PART3. 下一個畫面的右下角邊緣
時間是所有敍述最基本的次元,這個故事的發生早於上一個故事,但是我身處一個曾因身世複雜導致性格陰鶩百是禁忌的社會,因此我是長到適宜回首的年歲才知這故事的。就當他是電影中的平行式剪接吧,打破時間秩序讓不同情節發展並列而指向單一主題,在上段與這一段的承轉聯結中,清晰了主題意義。
一張泛黃的黑白照片,書寫五○年代市街景象:圓形噴水池居中,朝不同方向奔放三條筆直道路,各式商行沿街開設,來往行人及車輛錯落街道,雲和天幾乎辨不出顏色。然後,雲朵用人們察覺不到的速度緩緩挪變,水池的木柱竄高並濺落,行人與車開始流動了起來,流動在中台灣薄脆金亮的秋陽裡,流動在鬧市名街別見的活潑聲息裡,流動在寧靜小城從未設想到的驚奏變調裡……
「槍殺一個外省兵。」的流言耳語隨吉甫車、軍用卡車的相繼到來而凝湧滾沸,人群灑豆一般朝相同方位滾動且停止,蠕蠕堆圍砌厚,小孩在人牆外奔跑攢擠。人牆圈圍一個半徑數公尺大的空地,噴水池在人牆的最內層,隔著空地與一間鐘錶行相對。已開張的鐘錶店店門洞開,店內並無一人,幾個著草綠軍服的人在店門口排置擺弄,陸續走開後,留下一個面向鐘錶店大門,餒身跪在街邊的草綠身影。人群逐漸歛容噤聲,一股不安的靜默湮漫飽漲,空氣賁張欲裂,口令,準星在陽光下跳閃一朵星芒,槍聲驟響,人們別臉,閉目、低呼,槍聲再響,再響。
有人說這個外省兵一身餒餒垮垮的軍服,有人說還只是個少年兵,有人說一只錶抵一條命太過苛刻,有人說錶店老闆奔走求情但軍方執意不允以整軍紀。槍斃,扣下板機的單純動作,瞬間奪去一個人曾經以及來不及的擁有。一星期前,當這個外省兵走進鐘錶店,看見一只令他不能釋手的錶,不付錢強行拿走的時候,他一定在想,自己離鄉、戰敗、孤孓、卑微、失去的一生中,終於獲得一次珍貴細緻的擁有。無名無姓,無親無故,因一次短暫擁有從此滅絕今生所有,離亂世代血腥撲嗆,一個被槍斃在異鄉邊的外省兵,只配留下很多很多的有人說而已。
鐘錶店老闆是一個虔心禮佛,本分篤實的本地人,成家立業養兒育女就是他平凡飽實的生命理想,並非沒擔過生命風波,也並不畏懼意外忽來,只是這樣一樁聳動驚駭血流家門的事迅雷飆至,他感不感到命運翻撥的無情?他痛不痛苦生命結構的崩塌?發生過的重大事件,化成一襲襲透明的網,人,就透過這些網觀照世間,那麼,伴隨扭曲記憶同時存在的罪惡感,究竟要到什麼時候才算真正過去?槍響那一天,他始終沒出現,只有他的店一直閉不攏過度驚嚇而失聲的口,如果能夠,他一定願意將一天從自己生命剜剔剝離不辭代價,而遭刧報官,原也不過是一種本分。
是人類自己過度特寫了「影響一生最大因素在自己」這句話,其實人力微末無以違抗大環境的斑駁變異風雲翻覆。有時悲秋傷月起來,我婆娑的淚眼甚至會在不同事件的浮沉眾生身上,看到芻狗幻象的雙重疊影。當災難從潘朵拉來不及關上的黑盆跳落人間的時候,根本恣肆猖狂忘記了選擇。悲情,不會只是某些人的專利。生命原是悲傷基調荒謬本質的多形式物質,時代的軌道只要稍有脫逸,個人傾生命全力的虔敬或本分,輕易便被失速的輪轉離心飛甩而去,摔落在歷史廣垠的某一微點,支離破碎得徹底且無聲,影響一生最大因素在於──時代。
行刑畢,死者的袍澤青森著臉蹲在店口奠祭,五官扭曲連聲咒罵,不斷將焚燒的冥紙扔進店內,紙灰漫天飛揚,飛揚在五○年代中台灣薄脆金亮的秋陽裡,飛揚在鬧市名街別見的活潑聲息裡、飛揚在寧靜小城從未設想到驚奏變調裡,飛揚在一個沉重心靈揮之不去的夢魘裡……。
PART4. 無數畫面之後瀕臨劇終的幾個快速畫面
這些場面直接呈向觀眾毫無經營,敍述時間與故事時間大略相等,收歛所有表現手法,採取水平角度攝影,完全以寫實主義風格呈現。故事背景在綠樹與青草為鄰的校園,一個人們習慣稱作社會小縮影的地方。我喜歡「小」,因為一部好電影必定會在小處精緻;我挑年輕人為主要角色,因為年少是成年的最初,成年是年少的範本。
剛上完夜間輔導課的老師,疲憊地被月光拉長,在校牆驚見座車刮痕縱橫,引擎蓋噴漆了幾個大字:「外省豬滾回去!」老師連拍而過的記憶片段定格了,自己對島內大選有感而發的那節課,當時他企圖節制未遂,一不小心縫隙透光,流洩了自己的政治意態。
數名國中女生和老榮民的性交易事件,訇然蔚為各式媒體的熱銷賣點,年輕學生提著報紙,課堂上公然對老師大聲挑釁:「都是你們外省人幹的好事!」
在大學校園,「台灣」與「中華民國」、「西元」、「民國」是論文中最起碼的交鋒。升等錄用、評量核定、選擇口試委員指導教授,都見意識型態的回合交戰。
相對同質性的強烈訴求,排他性自然隨之增強,於是人群壁壘再分迫害相生。如果歷史教訓只能改變人類相殘的形式而非本質,你我終將是日日推悲情之石上山的西西弗斯,所以,當我的朋友告訴我:「同意識型態的人交朋友會比較自然。」我就知道我已失去這位朋友。就那一天,我找尋自己靈魂一般在街上遊盪,發現自己和父親、被槍斃的外省兵、錶店老闆,認識不認識的很多人迎面擦肩,然後看見一個身穿九○年代解嚴開放新潮時裝的五○年代不容異己病變的身軀,正款擺扭怩而來,綠燈亮,他吞吐欲過又趦趄不前,終於狼狽焦躁在四通八達十字路口……。
就在當天夜裡,書上的一句話無數次密集重複在我夢裡──弱者憤怒,抽刀向更弱的人。醒來後,我一直想問人一句話:「愛是我的意識型態,這樣會不會很可笑?」
PART5. 第一人稱敍述觀點的逐漸淡出並劇終
在電影裡,意義不直接告訴觀眾,永遠在設計形成中,我期使不同畫面的聯結,能產生畫面單獨存在時所沒有的一種新意義、新的品質,讓新的視覺帶來新的能量。
即使我將發生過的真實重建一個比較深廣的視野,我也仍只是個愛看電影的人而已。落在這個變動世代,終究不過小小一隅的邊緣景格,不知你習慣的視角可願微勢換轉?你凝注的餘光可願偏挪,向我,向我……。
PART1.第一人稱敍述觀點的逐漸淡入
置介聲光映象的影視空間,畫面中央,通常是視覺重心之所在,而在景格邊緣,亦即光的邊陲地帶,來來去去的角色,只給人們過眼即忘的瞬間印象。但是,懂得電影的人都會告訴你,一些最富戲劇變化的指涉符號,往往就存在畫面的邊緣地帶。
我熒熲眸光凝注不休的這個世界,以每秒二十四格,永不停止的流動狀態變換各種聲光畫面,於是,我常置身煙硝的腥嗆與過勞人體的酸味夾揉混雜的空氣裡,看到不同形式的崩塌與興立,看到等質謬忽的低調悲情與錯亂賁亢,看到被高吊掛醃漬風乾的公權與誠信,看到矮小亞洲的脫離自卑,看到政經主次易位的運會之趨……,當然,我更看到以快報姿態隨時插播畫面,碧藍海中一座心律不整的島,和它隨時都有可能出狀況,卻總在陡峭與平滑間不斷耍弄人們預期的心電圖。
在這樣一個你永遠不知道下一步會發生什麼事的蒙太奇世界,存在,已意味過去;猶豫,就已被擠落,你不得不承認,與這個世界相互凝注這件事,真是感官被餵得打飽嗝,縟麗無可名狀的特殊視覺經驗。可是,我是一個愛看電影的人,即便我凝注畫面中央的熱誠,一如拳著畸厚手套始終在場邊打轉,渴望加入棒球遊戲的涎羡小孩,但我仍能清醒記憶懂得閱讀電影的人的那句話,並且實在履踐了他們先知指示般的一句叮囑:
「當你凝注主畫面的同時,別忘了,善用眼睛的餘光。」
PART2. 畫面的左下角邊緣
梁祝電影插曲穿窗走戶的夏日黃昏,客廳裡半牆夕陽,油煎魚香濁濃了迷漫一室的燠悶暑氣,父親和一位陌生訪客坐在屋角的藤椅低聲交談。當夕陽走完一整面粉白的牆,訪客交給父親一個素色包袱,便帶著夕陽一起歛影消跡。
那布包袱裡藏神奇魔咒,它讓如山雄奇的靜毅的父親,剎那之間傾圮崩塌。
父親直直跪在攤開的素布前,縱聲嚎哭,素布上羅列一把小佩刀、一枚繪上青天白日的軍徽、和一張戴軍帽、斜披佩槍的軍人半身戎裝照片。父親的哭聲重且長,暮色掩襲,我稚犀的臉印貼陳舊紗門,從門外凝視父親許久,一直用靜默伴隨,從此不能忘卻跪地垂首的父親的身影,和龐巨垂臨,鏡頭仰攝而成的,那個詭橘滾染猛藍,情調稠穠誇艷的夏日晚天意象。
那是祖父昔日部屬輾轉由大陸帶來的祖父的遺物,撤守時,祖父負責掩護其他軍團的撤離,倉皇中不幸陷敵遇難。那天父親一直抬不起的臉朝西,望向大洋之外的自己的家鄉。
微渺個人的生命情事於那個壯闊年代,是拍不到岸的遙海波濤,無數次浪落之後的一次狂巨捲襲,也只是再一次的浪落,終其一生,我沒看過父親哭過第二次。
那年,我八歲,企圖用紗門外一顆幼細困惑的心,貼熨兜收父親哀長不絕哭聲而不能,後來我百出不窮的童年夢想中最持久的一樁;心中最初最深耕的犂痕,生命中一直存在的負擔,就是反攻大陸。
而我的反攻大陸,單純只意指父親的回家鄉。
蓬蓬大大的棉花糖,一口用力咬下,住往只有亂亂黏在唇上的絲縷糖絮,和滿口腔無味的虛空。過大的夢想就是一朵實實虛虛的棉花糖,「反攻大陸」終究不如我年少在燈下,獨自玩得幾近耽溺的一場筆尖和線條協力而成的秘密遊戲。
我讀本國地理那幾年,每當中國大陸地圖葉片一般攤展我眼前,我的眼光總能迅速柔焦其他省分,獨獨定位「湖南」這一省。燈下的「湖南」像花瓣大片疊複、軟枝墜垂的花的半羞合側影,湘、資、沅、澧四條向心水系的主流支脈由花托放射流成片片花瓣的鋸齒瓣沿,長沙在東北、衡陽在東南、父親的家在西南。鏡頭拉遠便看清楚台灣與這側影的花,恰恰形成擦肩走過的背背相對。
我的鉛筆尖由台灣略弓的背脊開始走動,朝左下斜斜滑下順利越過南海,登岸珠江三角洲,再一段短短溯筆便上至繁華廣州。當筆尖由廣州搭隨今已稱京廣鐵路粵漢鐵路,就是一段輕鬆之旅了。翻南嶺、入湖南、衡陽可以是終點,換轉公路再朝西;或者,乾脆筆尖不停,隨粗黑鐵路直上名城長沙,然經由水路,一路搖櫓,看帆影翩遷、涉楚辭浪漫,下湘江,回家鄉。而如果,從浙江上岸,那麼……。由某地到某地鐵路轉換方式,是那幾年地理科的熱門題型,也使我初初恣享心靈世界卓然獨特的自我而足。父親沒等到回鄉便病逝,只我在十七歲一年陪過他一次又一次,下湘江,回家鄉。
當你被電影畫面深深觸動的剎那總是靜靜默無言,用言語詮釋感受,那是感受轉醒之後才具有的意識及能力。我是在父親死後,才開始了解父親。
父親死後,我生命履帶不疾不徐轉運如昔,只是在很多個不同的時空,意識驟然斷電動作凝凍,心念畫面嘩然一片電波急雨,然後困愁不安六合八荒湧襲撲漫,我便不顧一切的,深切想見父親,也常會在不同場景的街道戞然乍見酷似父親的背影,便緊緊追隨且超前,再用孤注一擲後翻抓底牌的氣態扭身照見……。渴望是一種追尋的動力,但它最崇高深沉的狀態,可以超越一切物質非物質現象,成為宗教的神秘意識。我倉皇於茫茫人海想見父親瀕臨狂亂盲目,是否所有事物最深最盡處,皆會生成鋪染深深淺淺宿命色彩的非理性?我因此在非理性與宗教的無界面擺搖宛若深海之荇,終究讀出生命的最大虔誠在於深邃的渴望,而有些虔誠像拚盡生命全力的出拳甚且或縱身撲去,卻在虛無空氣中大力落空那般,你只能啞啞地無言。
那麼,隻身至異鄉不愛回顧不細說心情的父親,他的很特別禮遇白髮皤然的老者,他的不得不獻唱時老哼唱別人聽不懂的湖南小曲,他發病初期不斷夢見的迢遙故鄉親友,以及終其一生他很常有的獨坐沉思,就是父親最失重虔敬、最無力的全力了。生命原是悲傷基調荒謬基調荒謬本質的多形式物質,我因失去父親而了解父親。
歸鄉,過氣的世紀夢,曾是父親生命中一言不發的沉重,一開始我就說了,在高潮峰迭聲光倏幻充滿無限可能的大時代,微渺個人的塵夢與夢斷,運命梭織的乖謬與辛酸,都不過是,人們眼光不到的邊緣畫面。
PART3. 下一個畫面的右下角邊緣
時間是所有敍述最基本的次元,這個故事的發生早於上一個故事,但是我身處一個曾因身世複雜導致性格陰鶩百是禁忌的社會,因此我是長到適宜回首的年歲才知這故事的。就當他是電影中的平行式剪接吧,打破時間秩序讓不同情節發展並列而指向單一主題,在上段與這一段的承轉聯結中,清晰了主題意義。
一張泛黃的黑白照片,書寫五○年代市街景象:圓形噴水池居中,朝不同方向奔放三條筆直道路,各式商行沿街開設,來往行人及車輛錯落街道,雲和天幾乎辨不出顏色。然後,雲朵用人們察覺不到的速度緩緩挪變,水池的木柱竄高並濺落,行人與車開始流動了起來,流動在中台灣薄脆金亮的秋陽裡,流動在鬧市名街別見的活潑聲息裡,流動在寧靜小城從未設想到的驚奏變調裡……
「槍殺一個外省兵。」的流言耳語隨吉甫車、軍用卡車的相繼到來而凝湧滾沸,人群灑豆一般朝相同方位滾動且停止,蠕蠕堆圍砌厚,小孩在人牆外奔跑攢擠。人牆圈圍一個半徑數公尺大的空地,噴水池在人牆的最內層,隔著空地與一間鐘錶行相對。已開張的鐘錶店店門洞開,店內並無一人,幾個著草綠軍服的人在店門口排置擺弄,陸續走開後,留下一個面向鐘錶店大門,餒身跪在街邊的草綠身影。人群逐漸歛容噤聲,一股不安的靜默湮漫飽漲,空氣賁張欲裂,口令,準星在陽光下跳閃一朵星芒,槍聲驟響,人們別臉,閉目、低呼,槍聲再響,再響。
有人說這個外省兵一身餒餒垮垮的軍服,有人說還只是個少年兵,有人說一只錶抵一條命太過苛刻,有人說錶店老闆奔走求情但軍方執意不允以整軍紀。槍斃,扣下板機的單純動作,瞬間奪去一個人曾經以及來不及的擁有。一星期前,當這個外省兵走進鐘錶店,看見一只令他不能釋手的錶,不付錢強行拿走的時候,他一定在想,自己離鄉、戰敗、孤孓、卑微、失去的一生中,終於獲得一次珍貴細緻的擁有。無名無姓,無親無故,因一次短暫擁有從此滅絕今生所有,離亂世代血腥撲嗆,一個被槍斃在異鄉邊的外省兵,只配留下很多很多的有人說而已。
鐘錶店老闆是一個虔心禮佛,本分篤實的本地人,成家立業養兒育女就是他平凡飽實的生命理想,並非沒擔過生命風波,也並不畏懼意外忽來,只是這樣一樁聳動驚駭血流家門的事迅雷飆至,他感不感到命運翻撥的無情?他痛不痛苦生命結構的崩塌?發生過的重大事件,化成一襲襲透明的網,人,就透過這些網觀照世間,那麼,伴隨扭曲記憶同時存在的罪惡感,究竟要到什麼時候才算真正過去?槍響那一天,他始終沒出現,只有他的店一直閉不攏過度驚嚇而失聲的口,如果能夠,他一定願意將一天從自己生命剜剔剝離不辭代價,而遭刧報官,原也不過是一種本分。
是人類自己過度特寫了「影響一生最大因素在自己」這句話,其實人力微末無以違抗大環境的斑駁變異風雲翻覆。有時悲秋傷月起來,我婆娑的淚眼甚至會在不同事件的浮沉眾生身上,看到芻狗幻象的雙重疊影。當災難從潘朵拉來不及關上的黑盆跳落人間的時候,根本恣肆猖狂忘記了選擇。悲情,不會只是某些人的專利。生命原是悲傷基調荒謬本質的多形式物質,時代的軌道只要稍有脫逸,個人傾生命全力的虔敬或本分,輕易便被失速的輪轉離心飛甩而去,摔落在歷史廣垠的某一微點,支離破碎得徹底且無聲,影響一生最大因素在於──時代。
行刑畢,死者的袍澤青森著臉蹲在店口奠祭,五官扭曲連聲咒罵,不斷將焚燒的冥紙扔進店內,紙灰漫天飛揚,飛揚在五○年代中台灣薄脆金亮的秋陽裡,飛揚在鬧市名街別見的活潑聲息裡、飛揚在寧靜小城從未設想到驚奏變調裡,飛揚在一個沉重心靈揮之不去的夢魘裡……。
PART4. 無數畫面之後瀕臨劇終的幾個快速畫面
這些場面直接呈向觀眾毫無經營,敍述時間與故事時間大略相等,收歛所有表現手法,採取水平角度攝影,完全以寫實主義風格呈現。故事背景在綠樹與青草為鄰的校園,一個人們習慣稱作社會小縮影的地方。我喜歡「小」,因為一部好電影必定會在小處精緻;我挑年輕人為主要角色,因為年少是成年的最初,成年是年少的範本。
剛上完夜間輔導課的老師,疲憊地被月光拉長,在校牆驚見座車刮痕縱橫,引擎蓋噴漆了幾個大字:「外省豬滾回去!」老師連拍而過的記憶片段定格了,自己對島內大選有感而發的那節課,當時他企圖節制未遂,一不小心縫隙透光,流洩了自己的政治意態。
數名國中女生和老榮民的性交易事件,訇然蔚為各式媒體的熱銷賣點,年輕學生提著報紙,課堂上公然對老師大聲挑釁:「都是你們外省人幹的好事!」
在大學校園,「台灣」與「中華民國」、「西元」、「民國」是論文中最起碼的交鋒。升等錄用、評量核定、選擇口試委員指導教授,都見意識型態的回合交戰。
相對同質性的強烈訴求,排他性自然隨之增強,於是人群壁壘再分迫害相生。如果歷史教訓只能改變人類相殘的形式而非本質,你我終將是日日推悲情之石上山的西西弗斯,所以,當我的朋友告訴我:「同意識型態的人交朋友會比較自然。」我就知道我已失去這位朋友。就那一天,我找尋自己靈魂一般在街上遊盪,發現自己和父親、被槍斃的外省兵、錶店老闆,認識不認識的很多人迎面擦肩,然後看見一個身穿九○年代解嚴開放新潮時裝的五○年代不容異己病變的身軀,正款擺扭怩而來,綠燈亮,他吞吐欲過又趦趄不前,終於狼狽焦躁在四通八達十字路口……。
就在當天夜裡,書上的一句話無數次密集重複在我夢裡──弱者憤怒,抽刀向更弱的人。醒來後,我一直想問人一句話:「愛是我的意識型態,這樣會不會很可笑?」
PART5. 第一人稱敍述觀點的逐漸淡出並劇終
在電影裡,意義不直接告訴觀眾,永遠在設計形成中,我期使不同畫面的聯結,能產生畫面單獨存在時所沒有的一種新意義、新的品質,讓新的視覺帶來新的能量。
即使我將發生過的真實重建一個比較深廣的視野,我也仍只是個愛看電影的人而已。落在這個變動世代,終究不過小小一隅的邊緣景格,不知你習慣的視角可願微勢換轉?你凝注的餘光可願偏挪,向我,向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