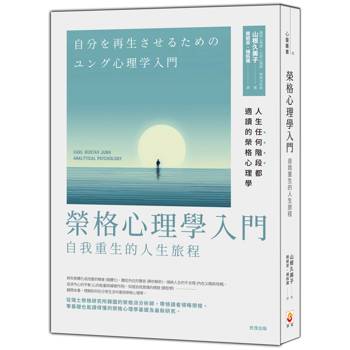無論眼鏡適不適合,都有各自的特性
世界上有許多試圖要理解「內心」構造的心理學,以及基於心理學的各式心理治療。這就表示,世界上有許多人對「內心」感興趣。榮格心理學也是其一。
心,不具備實體,也無法像體內臟器一樣能取出解剖、查看理解。既然沒有實體,就是想像之物,但現今卻有那麼多人相信它的存在。隨著腦科學的發展,曾針對「心=腦」有一番爭論,但過程中,人們逐漸發現,關於心,有許多無法用大腦理解與科學解釋的部分。心非常複雜,依每個人對心的理解而有各式樣貌,是個奇妙的存在。
心理學「相當於一副觀看心所需要的眼鏡」。即使這副眼鏡因為設計與用途有所不同,卻不分好壞。重要的是,適不適合配戴的人。
我們每個人都惴惴不安地生活著。人生有許多階段,該如何面對每個階段的不確定性,每個人在不同時刻都有應對的方法,我認為這是比較好的方式。
榮格曾說過,有些人在某些時候適合佛洛依德學派的精神分析,有某些人在某些時候適用阿德勒心理學,我的心理學並非萬能。
榮格心理學這副眼鏡,是現在帶領我觀看內心時最適合我的。我想要透過這本書告訴各位,這副榮格心理學的眼鏡戴起來究竟有多麼舒適。
試著戴戴看榮格心理學這副眼鏡,若你發現這副眼鏡非常適合你,那就表示你的個性已經反映在其中。
將邁入中年,不安悄悄靠近?
在現在這個時代,相信任何人都會感到不安,對於多數人來說,那種不安是幽微的。雖然三不五時浮上表面,但由於總是隱藏在內心深處,與我們相距甚遠,所以能遺忘它並過生活。然而,一旦那樣的不安變得非常明顯且具體可感知時,就會躍上人生舞臺上。
通常,人一感到不安就會用「我被不安感侵擾」「被不安感推動」等說法來表示,但仔細一看就會發現,這些表現都是被動的型態。
由於不安原本就是無法控制的,這種感覺不是我們自己發起,反倒是不安主動往我們身上靠。這是最常見的表現方式。
從榮格心理學的觀點來說,多數人在中年階段,不安感會明顯增強。
榮格認為,所謂的中年階段約是在三十六歲左右,這個階段也可以稱之為人生的正中午。將人的一生以一日來換算,中年階段大約就是一日的正中。
正中午既不是中午以前,也不是中午以後,而是介在兩者之間的時間。以一生來看,經歷了人生前半段,正要跨入人生後半段的時間就是中年階段。
一旦來到這個階段,體力會變得衰弱、身體不適也隨之出現,人會開始實際感受到年輕不再,老與死進入到現實範圍。另外,人們也經歷了事業與私生活中的轉捩點,在這之前,每個人是一起競爭,漸漸地轉換為個人戰了。
簡單來說,就是人生的前半部是屬於適應學校或公司等團體,然後把自己擺在某個位置上,屬「團體時期」;到了人生後半部,工作與家庭也都來到一個段落,就會專注於個人生活,屬「個人時期」。
遇人生轉折點時,內在的不安會更明顯
作家芥川龍之介由於對自己的未來有「幽微的不安」,於是在三十五歲時選擇自殺。榮格本身也是在中年階段選擇與佛洛依德決裂,之後經歷了許多年的精神危機。也可以說,中年階段就是被不安感攫獲,往死亡拖進的「逢魔之時」。
但是,榮格之所以認為中年階段是始於三十六歲應該是基於他自己本身的實際體驗。在我的心裡臨床經驗中,絕對是對不上的。因為在我的經驗中,有的人是二十歲後半到三十歲後半進入中年階段的心理,有的人則是到了六十多歲到七十多歲之後才感受到那股不安感而迎來危機。
然而,無論是幾歲,在這裡我想說的是,中年危機是因人而異的,人生中不安顯著化總有一天會出現。
多數情況下,不安感在人生的轉折期會變得明顯。因為,轉折時期會在原本進行順暢的事突然變得卡卡時出現,所以契機幾乎就是失敗或是落敗時。
要取得MBA的人不適合學習榮格心理學?
心理治療是當人們感到人生卡關、非得停下時才要做的,所以,人們正往成功邁進且顯得積極時是不會想去做的。在這一層意義上來說,當不走運與不幸來到眼前,經歷了失敗與落敗,才須要去做心理治療。
多數的心理學與奠基於各種心理學的心理治療,基本上就是以這次失敗了、輸了,但下次一定要贏回來為目標進行的。
另一方面,榮格心理學或是榮格學派的心理治療則不太在意成功或勝利。它是一門幫助人們從這次的失敗或是停滯中找出意義的心理學。
因此,對著眼於成功,並想要趁勝追擊的人來說,不太符合需求。
以前,我曾在瑞士的商科大學擔任針對目標是取得MBA學歷學生的心理治療課程講師,但是曾經有位在確定畢業後要進入世界知名企業上班、想要結束心理治療的學生對我說:「我不需要榮格學派的心理治療了。接下來,我想要專注在教練課程上。」
在商業世界裡,對成功並取得勝利有好評。在那樣的世界裡,沒有失敗者的容身之處。
倒是目標為取得MBA這件事本身,就是指成功並取得勝利。在競爭中脫穎而出,取得進入知名企業門票的人,要進一步投身於另一項競爭裡時,當然會認為,比起試圖停下腳步、細心領會失敗或敗北的榮格心理學,教練課程更有魅力。
在榮格學派的心理治療現場,編織的是那些失敗的悲痛與哀傷、憤怒與不安的諸多故事,那裡面不存在充滿光明與希望的故事,也不存在擊敗困難的勇敢故事。
正因如此,在人們被區分為「失敗組」與「勝利組」,且成功獲勝就能得到好評的現今格差社會中,榮格心理學被邊緣化或許也是自然。
失敗時與落敗時發揮本領的榮格心理學
榮格心理學之所以能在人經歷失敗時發揮出最大效用,是因為榮格本人在人生中曾經歷過諸多失敗。
據說,榮格雖然在世時就獲得了世界級的名聲,卻也飽受批判。他直到晚年都感嘆著,自己的工作不被多數人理解,時而也會因此感到憤慨。
回首自己的人生,他在自傳最末這麼寫道:
「我得罪過許多人,因為,當他們一旦認為無法理解我,就不再願意與我交談,而我也不去理會他們。我必須不斷地向前走。我對人沒有耐心,除了我的患者之外。」
據說,即使在心理治療臨床,榮格對於個案的狀態好時,不會顯示出太多的興趣,在個案狀態不好時則會突然表示在意。或許各位會覺得榮格性格惡劣,以榮格自身經驗來說,正是在失敗或是輸的時候才能站穩腳步,那個時間點才是變化的轉捩點。
當然,榮格並不是認為,成功或是勝利毫無意義。人生有許多階段,成功或勝利是非常重要的。
成功、勝利,或是以這兩者為目標是榮格所說的人生前半段,也就是人到中年遭逢危機前的那一段人生,會為了適應社會而得到往前進的原動力與推進力。雖然這與個別差異與所處狀況有關,尤其是年輕階段,以獲致成功,取得勝利為人生的主要課題時。
然而,人生可沒有美好到會持續成功或持續勝利,所有人終究都會面臨失敗。形式可能是挫折或跟不上團隊、離婚或分離、生病等。但也可能是遭到霸凌、職權騷擾、性騷擾等人禍或是天災等不合常理的事件。又或者,雖然事情成功也取得勝利了,但總覺得不踏實,因而覺到自己或許是失敗的。
由日本劇作家渡邊綾撰寫腳本的日劇《Elpis》中,年輕的岸木拓朗出生於富裕家庭,從小學到大學都就讀名校,長相帥氣,母親總稱他是人生勝利組,他自己本身也這麼認為,而且他還在知名大電視台擔任導播。但某日他內心開始出現疑問,他說:
「但是,我真的認為自己在任何地方都沒有贏⋯⋯我們為了要洗腦自己是人生勝利組而輸掉了更多,不是嗎?」
事實上,在拓朗中學時代,他與母親明知朋友遭到霸凌,卻因為主事者是該學年家長中最有力家長的兒子,而選擇不作為,沉默以對。結果,感覺被背叛且被冷眼以待的朋友自殺了,而拓朗則當作沒發生過這樣的事,繼續生活。
當他面對這樣的往事,他嚎啕大哭地說道:「我們輸了,澈底輸了,自那之後,一直輸到現在⋯⋯因為我當時一邊諂媚那個最該被厭棄且最不能原諒的人,一邊希望對方把我納入人生勝利組中⋯⋯」
在旁人眼中看來雖是人生勝利組,他卻為了能一直待在那樣的群組中,只好壓抑真正的自己、放棄思考、輸給權力與外力。
世界上有許多試圖要理解「內心」構造的心理學,以及基於心理學的各式心理治療。這就表示,世界上有許多人對「內心」感興趣。榮格心理學也是其一。
心,不具備實體,也無法像體內臟器一樣能取出解剖、查看理解。既然沒有實體,就是想像之物,但現今卻有那麼多人相信它的存在。隨著腦科學的發展,曾針對「心=腦」有一番爭論,但過程中,人們逐漸發現,關於心,有許多無法用大腦理解與科學解釋的部分。心非常複雜,依每個人對心的理解而有各式樣貌,是個奇妙的存在。
心理學「相當於一副觀看心所需要的眼鏡」。即使這副眼鏡因為設計與用途有所不同,卻不分好壞。重要的是,適不適合配戴的人。
我們每個人都惴惴不安地生活著。人生有許多階段,該如何面對每個階段的不確定性,每個人在不同時刻都有應對的方法,我認為這是比較好的方式。
榮格曾說過,有些人在某些時候適合佛洛依德學派的精神分析,有某些人在某些時候適用阿德勒心理學,我的心理學並非萬能。
榮格心理學這副眼鏡,是現在帶領我觀看內心時最適合我的。我想要透過這本書告訴各位,這副榮格心理學的眼鏡戴起來究竟有多麼舒適。
試著戴戴看榮格心理學這副眼鏡,若你發現這副眼鏡非常適合你,那就表示你的個性已經反映在其中。
將邁入中年,不安悄悄靠近?
在現在這個時代,相信任何人都會感到不安,對於多數人來說,那種不安是幽微的。雖然三不五時浮上表面,但由於總是隱藏在內心深處,與我們相距甚遠,所以能遺忘它並過生活。然而,一旦那樣的不安變得非常明顯且具體可感知時,就會躍上人生舞臺上。
通常,人一感到不安就會用「我被不安感侵擾」「被不安感推動」等說法來表示,但仔細一看就會發現,這些表現都是被動的型態。
由於不安原本就是無法控制的,這種感覺不是我們自己發起,反倒是不安主動往我們身上靠。這是最常見的表現方式。
從榮格心理學的觀點來說,多數人在中年階段,不安感會明顯增強。
榮格認為,所謂的中年階段約是在三十六歲左右,這個階段也可以稱之為人生的正中午。將人的一生以一日來換算,中年階段大約就是一日的正中。
正中午既不是中午以前,也不是中午以後,而是介在兩者之間的時間。以一生來看,經歷了人生前半段,正要跨入人生後半段的時間就是中年階段。
一旦來到這個階段,體力會變得衰弱、身體不適也隨之出現,人會開始實際感受到年輕不再,老與死進入到現實範圍。另外,人們也經歷了事業與私生活中的轉捩點,在這之前,每個人是一起競爭,漸漸地轉換為個人戰了。
簡單來說,就是人生的前半部是屬於適應學校或公司等團體,然後把自己擺在某個位置上,屬「團體時期」;到了人生後半部,工作與家庭也都來到一個段落,就會專注於個人生活,屬「個人時期」。
遇人生轉折點時,內在的不安會更明顯
作家芥川龍之介由於對自己的未來有「幽微的不安」,於是在三十五歲時選擇自殺。榮格本身也是在中年階段選擇與佛洛依德決裂,之後經歷了許多年的精神危機。也可以說,中年階段就是被不安感攫獲,往死亡拖進的「逢魔之時」。
但是,榮格之所以認為中年階段是始於三十六歲應該是基於他自己本身的實際體驗。在我的心裡臨床經驗中,絕對是對不上的。因為在我的經驗中,有的人是二十歲後半到三十歲後半進入中年階段的心理,有的人則是到了六十多歲到七十多歲之後才感受到那股不安感而迎來危機。
然而,無論是幾歲,在這裡我想說的是,中年危機是因人而異的,人生中不安顯著化總有一天會出現。
多數情況下,不安感在人生的轉折期會變得明顯。因為,轉折時期會在原本進行順暢的事突然變得卡卡時出現,所以契機幾乎就是失敗或是落敗時。
要取得MBA的人不適合學習榮格心理學?
心理治療是當人們感到人生卡關、非得停下時才要做的,所以,人們正往成功邁進且顯得積極時是不會想去做的。在這一層意義上來說,當不走運與不幸來到眼前,經歷了失敗與落敗,才須要去做心理治療。
多數的心理學與奠基於各種心理學的心理治療,基本上就是以這次失敗了、輸了,但下次一定要贏回來為目標進行的。
另一方面,榮格心理學或是榮格學派的心理治療則不太在意成功或勝利。它是一門幫助人們從這次的失敗或是停滯中找出意義的心理學。
因此,對著眼於成功,並想要趁勝追擊的人來說,不太符合需求。
以前,我曾在瑞士的商科大學擔任針對目標是取得MBA學歷學生的心理治療課程講師,但是曾經有位在確定畢業後要進入世界知名企業上班、想要結束心理治療的學生對我說:「我不需要榮格學派的心理治療了。接下來,我想要專注在教練課程上。」
在商業世界裡,對成功並取得勝利有好評。在那樣的世界裡,沒有失敗者的容身之處。
倒是目標為取得MBA這件事本身,就是指成功並取得勝利。在競爭中脫穎而出,取得進入知名企業門票的人,要進一步投身於另一項競爭裡時,當然會認為,比起試圖停下腳步、細心領會失敗或敗北的榮格心理學,教練課程更有魅力。
在榮格學派的心理治療現場,編織的是那些失敗的悲痛與哀傷、憤怒與不安的諸多故事,那裡面不存在充滿光明與希望的故事,也不存在擊敗困難的勇敢故事。
正因如此,在人們被區分為「失敗組」與「勝利組」,且成功獲勝就能得到好評的現今格差社會中,榮格心理學被邊緣化或許也是自然。
失敗時與落敗時發揮本領的榮格心理學
榮格心理學之所以能在人經歷失敗時發揮出最大效用,是因為榮格本人在人生中曾經歷過諸多失敗。
據說,榮格雖然在世時就獲得了世界級的名聲,卻也飽受批判。他直到晚年都感嘆著,自己的工作不被多數人理解,時而也會因此感到憤慨。
回首自己的人生,他在自傳最末這麼寫道:
「我得罪過許多人,因為,當他們一旦認為無法理解我,就不再願意與我交談,而我也不去理會他們。我必須不斷地向前走。我對人沒有耐心,除了我的患者之外。」
據說,即使在心理治療臨床,榮格對於個案的狀態好時,不會顯示出太多的興趣,在個案狀態不好時則會突然表示在意。或許各位會覺得榮格性格惡劣,以榮格自身經驗來說,正是在失敗或是輸的時候才能站穩腳步,那個時間點才是變化的轉捩點。
當然,榮格並不是認為,成功或是勝利毫無意義。人生有許多階段,成功或勝利是非常重要的。
成功、勝利,或是以這兩者為目標是榮格所說的人生前半段,也就是人到中年遭逢危機前的那一段人生,會為了適應社會而得到往前進的原動力與推進力。雖然這與個別差異與所處狀況有關,尤其是年輕階段,以獲致成功,取得勝利為人生的主要課題時。
然而,人生可沒有美好到會持續成功或持續勝利,所有人終究都會面臨失敗。形式可能是挫折或跟不上團隊、離婚或分離、生病等。但也可能是遭到霸凌、職權騷擾、性騷擾等人禍或是天災等不合常理的事件。又或者,雖然事情成功也取得勝利了,但總覺得不踏實,因而覺到自己或許是失敗的。
由日本劇作家渡邊綾撰寫腳本的日劇《Elpis》中,年輕的岸木拓朗出生於富裕家庭,從小學到大學都就讀名校,長相帥氣,母親總稱他是人生勝利組,他自己本身也這麼認為,而且他還在知名大電視台擔任導播。但某日他內心開始出現疑問,他說:
「但是,我真的認為自己在任何地方都沒有贏⋯⋯我們為了要洗腦自己是人生勝利組而輸掉了更多,不是嗎?」
事實上,在拓朗中學時代,他與母親明知朋友遭到霸凌,卻因為主事者是該學年家長中最有力家長的兒子,而選擇不作為,沉默以對。結果,感覺被背叛且被冷眼以待的朋友自殺了,而拓朗則當作沒發生過這樣的事,繼續生活。
當他面對這樣的往事,他嚎啕大哭地說道:「我們輸了,澈底輸了,自那之後,一直輸到現在⋯⋯因為我當時一邊諂媚那個最該被厭棄且最不能原諒的人,一邊希望對方把我納入人生勝利組中⋯⋯」
在旁人眼中看來雖是人生勝利組,他卻為了能一直待在那樣的群組中,只好壓抑真正的自己、放棄思考、輸給權力與外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