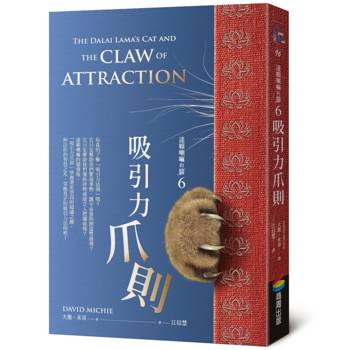第一章 花園裡的考古大發現
一說起吃的呀,有什麼會比「新奇」更叫我們貓族歡喜呢!從某人碗裡意外舀起來的一口食物所散發的誘人香氣;或是咀嚼風味絕佳的新菜色時,在齒間迸發的奇妙滋味。
某天早上,尊者外出參訪色拉寺,丹增便前來侍餐。他從背包裡拿出了一款我前所未見的貓糧品牌。罐頭的內容物才剛倒進碟子裡,一股強烈的魚蝦腥味就馬上弄得整個房間都是。
「尊者貓,準備好囉。」丹增呼喚我的時候,總是有點正式的感覺,他會用我在正式場合才使用,英文名號的第一個字母縮寫來稱呼我,尊者貓(HHC)是尊者的貓(His Holiness’s Cat)的簡稱。
他把碟子放在我面前的地板,但臉部卻閃現一個表情,那是在如此專業的外交官臉上極為少見的表情。他甚至想都沒想要掩飾他的噁心感。要是我能說話,我可能會轉告他達賴喇嘛經常提醒我們的一件事。那就是:就事物本身而言,事物的本質並不會讓人愉快或不愉快;而你會喜歡它或討厭它,那只是你的業力在驅使你那樣去看待罷了。
然而,要是我能說話──就算我這一輩子果真擁有這樣唯一一次的說話機會──那我還是不會去說的。因為啊,碟子才一下地,我臉就埋進去了,一邊狂吸那股有異於平常的芳醇,一邊開始嘖嘖有聲地大嚼著這塞得滿滿的第一大口。
「鱈魚、比目魚和蝦子雜燴,」丹增在我頭頂上方大聲唸著包裝紙上的文字,「並以層次豐富的鹹味醬汁來呈現。」
他到底為什麼會對這個感興趣,我不知道,也不關心。我一心一意全放在這口感絕佳、汁液潤澤的食物上。
自從我還是隻小小貓,第一次來到達蘭薩拉,我就一直對食物重度痴迷。有一個人比誰都能了解我這份渴望。那天早上,我在房裡打瞌睡,達賴喇嘛不在家,感覺空虛又淒涼,思緒便很自然地轉到她身上。也想到她曾經不停地送到我面前的點心和小吃。還有總是熱情洋溢地歡迎我。是時候了,該去拜訪尊者的貴賓主廚春喜夫人了,不是嗎?
直到最近,我才有機會去拜訪她──之前她住得太遠了。踏出尊勝寺大門時,我在想,正是那個有點意外、又討我歡心的新發現,這才把我的頭號粉絲給圈回了我的管轄範圍。春喜夫人的女兒瑟琳娜與她的丈夫席德就住在不遠處的塔拉弦月路二十一號。他們家就沿著尊勝寺前面這條路一直走下去,是一處占地寬廣、有高塔的平房,白色外牆,建物的四周有寬敞的環繞式陽台。它最顯著的特點是:有一座帶城垛的塔樓,約兩層樓高,上面還爬滿了常春藤。塔樓樓頂有一個四面都是大觀景窗的空間,我在那個觀景室裡度過好幾個夜晚。欣賞壯麗景色時,也與太陽、月亮和建物後方終年積雪的喜馬拉雅山群峰,融為一體。
席德和瑟琳娜住那裡的時候,已經對這個家多次進行翻修,然後他們的第一個孩子瑞希出生,這都快三年前的事了。這塊地這麼大,它的階梯式草坪一路延伸到很遠的松樹林,因此,他們一直都在開發這處房產的新面貌。
去年夏天某日下午,又有這樣一個出乎意料的發現。瑟琳娜先前就想帶瑞希去一個沒去過的地點野餐,於是,便來到大花園最遠的那邊。一大片一大片深紅和紫色的九重葛灌木叢是花園邊界的標誌;這裡是階梯式草坪的盡頭,也是松樹林的入口。不管怎麼說,看起來大概是這樣。
然後,席德從家裡走出來與他們會合。他才剛坐下,就接到了一通生意上的電話。起身接電話時,他繞到那一大片令人眼花撩亂的九重葛樹叢後方。就在這時,他注意到了某物。所以,一掛斷電話,就催促瑟琳娜快過去看看。不一會兒,她也走到這一大片野花蔓生的後方。眼前的一片平地是最近才翻土過的。盡頭處,二十公尺外,在森林地入口之前,有一棵雄偉而奇特的樹獨自矗立著。
「是義大利傘松!」瑟琳娜眼睛亮了起來,「就像拉維洛(Ravello)那樣的!」春喜夫人經常說她退休後要回拉維洛,就在她心愛的阿瑪菲海岸(Amalfi Coast)那裡的山上。這個夢想當然是異想天開,她和女兒在麥羅甘吉(McLeod Ganj)的生活早已扎根很深了,根本不會認真考慮這樣的改變。
然而,在懷舊思鄉時,尤其是當她喝著奇揚地(Chianti紅葡萄酒)或維蒙蒂諾(Vermentino白葡萄酒)的時候,她的黑色睫毛就會顫巍巍地闔上,然後開始描述她童年的美好時光:鈷藍色的地中海廣闊、平靜、逕向無邊無際滾滾而去。
夏日向晚的慵懶金光,空氣中薰衣草濃香瀰漫,蟬鳴輪唱。有如海岸線哨兵的義大利傘松,凌空升騰,樹頂的巨大華蓋供人躲避熱浪和風雨,而它們的枝條總在低聲訴說著遠古的祕密。
如果瑟琳娜提議「她在麥羅甘吉退休就好」的措辭上,稍稍有那麼一點強硬,她就會哀嚎:「可是,我好愛我的樹喔!」
「那我的樹怎麼辦?」若有人說她對故鄉的留戀只是感情用事,她就會用這句話堵住對方的嘴。
這裡所講的樹專指義大利傘松,學名pinus pinea,是她從小就有著濃厚興趣的樹種。而現在,竟有一棵那麼壯觀、高聳又獨特的傘松在麥羅甘吉這裡意外地現身了。
席德告訴瑟琳娜說,他最近要園丁將九重葛後方那片已經扎根的茂密植被處理掉。清理完後,除了有說不完的好處之外,最先看到的部分就是這棵樹了。瑟琳娜著了迷似地直直走過去,然後轉身看著席德。就在這時,她的臉上出現清新明亮的神采。
「你知道這是什麼嗎?」她有點興奮地問道。
「什麼?」
「過來這邊看看!」
席德走到她身旁,轉身面向九重葛。他和瑟琳娜一樣,都注意到了從另一邊看來並不明顯的對稱性。新翻過的土地兩側有高高的、連綿的杜鵑花叢。些許的砂岩顯示出這裡曾經是花壇的邊界。近處則是一塊鋪砌過的東西,上頭蓋滿了落葉。還有個長滿青苔的凹處。
「這裡以前是一座花園!」瑟琳娜猜想。
席德吃了一驚,向九重葛堆大步走去。他蹲下身子,撥開帶刺的枝條湊近過去,並往灌木叢裡窺探。「如果沒記錯的話,」他轉身對她說:「這個瓦礫堆以前是一座小屋。小小的,只有兩房。」
她和他一起把連串的花叢撥到一旁,以便看到更深處。沒多久,他們找到了一面殘存的牆壁。「這裡可以再蓋一個可愛的小屋喔!」席德沉思道:「我們這花園的規模已經有了。還有松樹,像在拉維洛一樣的松樹。」
「你和我是在想同樣的事嗎?」瑟琳娜目光炯炯有神。
「怎能不和妳想一樣的呢?」席德聳聳肩,曾經是土邦大君的他自帶一股謎樣神態。「一切都是冥冥中自有安排的。」
瑟琳娜和席德發現此處後,一天之內,春喜夫人便親自前來探訪這座重新發現的花園。她壯起膽兒走到九重葛叢後面,察看著成熟的杜鵑花剛剛劃出來的新邊界。其中最棒的是,這棵高貴的義大利傘松讓她讚歎不已。她一靠近樹身,淚水便奪眶而出,彷彿看到一位她深愛、思念的好友,在數十年後終於重逢。她用雙臂摟住樹身,就這樣抱著好久好久,好像跟一個老鄉心意相通一般;他們同樣都在這個喜馬拉雅山的村子裡落腳多年,也都離家鄉很遠。
那時,他們當場就做出了決定。不到幾週,春喜夫人的新屋計畫就得到了贊同和認可,也找好了工程承包商。因為這個計畫不大,也因為席德人脈廣,沒過多久,新家就蓋好了。小巧樸素,是根據女主人的要求設計的。開放式的起居空間和廚房通往客廳,然後是陽台,全部都面向剛鋪好的翠綠草坪。遠遠另一端的牆面中央有一個重要擺設,直立高聳,毫無疑問是地中海風格的,那是她新家的守護神。
至於我的部分,我一直在密切關注這裡的進度。通常在黃昏時分會來工地考察,因為那時候就沒有施工噪音了,還可以聞一聞各種建材怪異又刺鼻的氣味。必要時也有大量的沙堆可以利用。幾週以來,我看著工人挖地基,在平地上砌出了牆壁,接著又出現椽子和屋頂。
我好奇心最重的時候其實是春喜夫人搬進來之後。才一個週末,突然間就有一整個家的全新家具供我探索。而且,因為春喜夫人是繼達賴喇嘛本人之後,我的第二大恩人,她經常喚我為「有史以來最美生物」,所以,我在她家到處探索,那是絕對沒問題的。
那次特別的拜訪是在下午時分。我像往常一樣朝著房子側邊走去,然後從客廳通往陽台的滑動門走進去。春喜夫人會讓門開著,這樣子,空氣才能循環。
「噢,特索麗娜(tesorina,義大利文「小寶貝」的意思)!我的小寶貝兒!妳也來喝茶嗎?」春喜夫人穿著圍裙,正在光可鑑人的廚房長椅後方做著她最擅長的事情──準備做一份放縱味蕾的美味點心。
我喵喵叫了起來。茶會什麼的我是沒概念啦,但是從烤箱裡散發出來的烘烤香氣鐵定值得期待。每次春喜夫人招待她親朋好友時,一定也有我的份。
我走向離廚房最近的沙發,跳上座位,再跳上沙發扶手,最後回到我可以安坐的地方,看著她施展魔法。從她臉龐掠過的黑髮盤成髮髻,一有動作,右臂上的金手鐲便發出清脆的碰撞聲。她沉浸在自己正在做的事情當中。
我這一生經常觀察春喜夫人,而且大多是當她在尊勝寺的廚房,為達賴喇嘛的貴賓準備餐點的時候。早期的她常有很戲劇化的表現,在某些場合甚至會像火山爆發一樣恐怖。在我還是隻小奶貓時,她與達賴喇嘛的某次談話發揮了重大影響。尊者與幾位聯合國代表共進了最圓滿的午餐之後,邀請春喜夫人上樓,可是她好像有些不對勁,甚至不願意接受尊者的謝意。尊者提到她的工作時用了「慈愛」這個詞,她甚至表示反對。
「尊者,但願我真的有慈愛!」她打斷了他。
達賴喇嘛注視著她──有些驚訝,也有些慈悲。他舉起雙手,請她繼續說下去。
「我聽過您的教誨,也讀過一些佛法書籍。關於無限利他的心,說法有很多。但我不能說謊,我的心不是這樣的。如果是,那就好了!」她那塗著黑色睫毛膏的雙眼,睜得大大地盯著尊者,卻很悲傷。「我靠我自己活著。我沒有在助人。我想的主要都是我自己。一整天都是這樣的!」
「可是妳在這裡工作,」達賴喇嘛反駁道,「而且是自願的。」
她聳聳肩。
「妳帶給我的客人們很大的快樂。當然啦,」他揉揉肚子,調皮笑說:「我也很快樂!」
春喜夫人的心理很矛盾,她說:「有時候,或許只是您人好。只是出於禮貌。」
「但是,這位不一樣喔!」尊者用手勢示意我所在之處;那時我正趴在窗台上,旁邊有個小烤盤,正聽著他們這次談話。尊者笑著補充道:「她可不會假裝。」
春喜夫人的表情變得輕鬆起來。「這倒是真的。」她說。
尊者仔細地看了她一會兒,然後輕聲問道:「妳不認為妳所做的事是在修慈愛的心嗎?」
她搖搖頭。
「連在為我們做飯的時候也沒有嗎?」
「我太忙了,沒辦法集中注意力。」她回答。
停頓了許久之後,尊者才再次開口。「既然如此,我有一個正式的請求,」他說,目光突然變得十分嚴肅。「從現在開始,我希望妳做每頓飯時都添加一種特殊食材。」春喜夫人的表情也變得嚴肅起來。
「菩提心,」他說,「妳知道嗎?」
她引述了定義上的說法:「為了利益一切眾生而想獲得開悟的願望。」
尊者點了點頭。「透過做飯,」他模仿攪拌湯鍋的樣子,「願一切眾生都有美味的食物。願他們的日常需求得到滿足。願他們遠離痛苦。」他提議道。
「做主菜的時候?」她問。
「每一道都要,」尊者回答。「廚房裡的每一個動作;在廚房外也是,愈多愈好。每次思考的時候,就憶念菩提心。希望獲得開悟,也希望別人擺脫痛苦。」
春喜夫人臉上閃過一絲猶豫,似乎想說些什麼,卻又改變主意。
「怎麼了?」尊者看著她的眼睛。
「有菩提心是很好啦,」過了一會兒她坦承說:「但只是希望要怎樣,還是沒有實現啊!」
尊者的眼神稍微黯淡下來。「這會改變妳大腦裡面的東西。妳剛剛說,妳只想著自己?這可不是幸福的成因。然而,妳想著要用善意幫助別人的時候,那會怎樣?」
她不用回答,臉上恍然一笑已經說明。
「如果妳訓練自己持續這樣去想事情,那會怎樣?」
「我猜啊,那會成為你的一部分。」
「它會改變妳的為人,對嗎?首先是有幫助別人的想法,再來就是行動。」達賴喇嘛微笑著,伸手去握住她的手。「永遠別忘了這個特殊配料。」
自那時起,春喜夫人在廚房的時候大多都憶念著菩提心。她把這個特殊配料添加到她為尊者和貴賓所烹製的每一頓飯菜裡;添到她為寺裡人員所烘烤的每一袋司康裡;也添到她送到樓上行政助理辦公室的茶壺裡;或她工作或居家時,為瑟琳娜和她自己所調製的飲品裡。
幾年下來,她早已不是那個華格納歌劇版本的春喜夫人了。她以前那些強烈的負面情緒,好像都已經轉變為正面,有時候,慈悲心的能量會自然填滿她內心,就好像以前她總是會強烈表現出不滿那般地自然而然。
我在沙發高處暫歇,發出輕柔的咕嚕聲,看得出來她此刻正在添加特殊配料。她正把麵團從大碗移至烤盤,嘴脣微微嚅動著,臉上浮現出一種特殊神情。
正如尊者所說,菩提心不僅僅成了她的本能。她開始用這種慈悲心在關注、留意著她周圍的人,所以有好幾次,她的存在似乎在她周遭瀰漫出仁慈的光輝,與達賴喇嘛本人並無太大區別。她永遠都是春喜夫人沒錯──有好幾個手鐲叮叮噹噹、言行誇張卻又真情流露。但除此之外,她已經培養出一顆開放的心、熱情又慷慨,能把人們都吸引到她身邊來,就好像在她新發現的花園裡面那一整排怒放的杜鵑,蜜蜂群卻只停歇在其中一處特別茂盛的花叢那般。
⋯⋯
一說起吃的呀,有什麼會比「新奇」更叫我們貓族歡喜呢!從某人碗裡意外舀起來的一口食物所散發的誘人香氣;或是咀嚼風味絕佳的新菜色時,在齒間迸發的奇妙滋味。
某天早上,尊者外出參訪色拉寺,丹增便前來侍餐。他從背包裡拿出了一款我前所未見的貓糧品牌。罐頭的內容物才剛倒進碟子裡,一股強烈的魚蝦腥味就馬上弄得整個房間都是。
「尊者貓,準備好囉。」丹增呼喚我的時候,總是有點正式的感覺,他會用我在正式場合才使用,英文名號的第一個字母縮寫來稱呼我,尊者貓(HHC)是尊者的貓(His Holiness’s Cat)的簡稱。
他把碟子放在我面前的地板,但臉部卻閃現一個表情,那是在如此專業的外交官臉上極為少見的表情。他甚至想都沒想要掩飾他的噁心感。要是我能說話,我可能會轉告他達賴喇嘛經常提醒我們的一件事。那就是:就事物本身而言,事物的本質並不會讓人愉快或不愉快;而你會喜歡它或討厭它,那只是你的業力在驅使你那樣去看待罷了。
然而,要是我能說話──就算我這一輩子果真擁有這樣唯一一次的說話機會──那我還是不會去說的。因為啊,碟子才一下地,我臉就埋進去了,一邊狂吸那股有異於平常的芳醇,一邊開始嘖嘖有聲地大嚼著這塞得滿滿的第一大口。
「鱈魚、比目魚和蝦子雜燴,」丹增在我頭頂上方大聲唸著包裝紙上的文字,「並以層次豐富的鹹味醬汁來呈現。」
他到底為什麼會對這個感興趣,我不知道,也不關心。我一心一意全放在這口感絕佳、汁液潤澤的食物上。
自從我還是隻小小貓,第一次來到達蘭薩拉,我就一直對食物重度痴迷。有一個人比誰都能了解我這份渴望。那天早上,我在房裡打瞌睡,達賴喇嘛不在家,感覺空虛又淒涼,思緒便很自然地轉到她身上。也想到她曾經不停地送到我面前的點心和小吃。還有總是熱情洋溢地歡迎我。是時候了,該去拜訪尊者的貴賓主廚春喜夫人了,不是嗎?
直到最近,我才有機會去拜訪她──之前她住得太遠了。踏出尊勝寺大門時,我在想,正是那個有點意外、又討我歡心的新發現,這才把我的頭號粉絲給圈回了我的管轄範圍。春喜夫人的女兒瑟琳娜與她的丈夫席德就住在不遠處的塔拉弦月路二十一號。他們家就沿著尊勝寺前面這條路一直走下去,是一處占地寬廣、有高塔的平房,白色外牆,建物的四周有寬敞的環繞式陽台。它最顯著的特點是:有一座帶城垛的塔樓,約兩層樓高,上面還爬滿了常春藤。塔樓樓頂有一個四面都是大觀景窗的空間,我在那個觀景室裡度過好幾個夜晚。欣賞壯麗景色時,也與太陽、月亮和建物後方終年積雪的喜馬拉雅山群峰,融為一體。
席德和瑟琳娜住那裡的時候,已經對這個家多次進行翻修,然後他們的第一個孩子瑞希出生,這都快三年前的事了。這塊地這麼大,它的階梯式草坪一路延伸到很遠的松樹林,因此,他們一直都在開發這處房產的新面貌。
去年夏天某日下午,又有這樣一個出乎意料的發現。瑟琳娜先前就想帶瑞希去一個沒去過的地點野餐,於是,便來到大花園最遠的那邊。一大片一大片深紅和紫色的九重葛灌木叢是花園邊界的標誌;這裡是階梯式草坪的盡頭,也是松樹林的入口。不管怎麼說,看起來大概是這樣。
然後,席德從家裡走出來與他們會合。他才剛坐下,就接到了一通生意上的電話。起身接電話時,他繞到那一大片令人眼花撩亂的九重葛樹叢後方。就在這時,他注意到了某物。所以,一掛斷電話,就催促瑟琳娜快過去看看。不一會兒,她也走到這一大片野花蔓生的後方。眼前的一片平地是最近才翻土過的。盡頭處,二十公尺外,在森林地入口之前,有一棵雄偉而奇特的樹獨自矗立著。
「是義大利傘松!」瑟琳娜眼睛亮了起來,「就像拉維洛(Ravello)那樣的!」春喜夫人經常說她退休後要回拉維洛,就在她心愛的阿瑪菲海岸(Amalfi Coast)那裡的山上。這個夢想當然是異想天開,她和女兒在麥羅甘吉(McLeod Ganj)的生活早已扎根很深了,根本不會認真考慮這樣的改變。
然而,在懷舊思鄉時,尤其是當她喝著奇揚地(Chianti紅葡萄酒)或維蒙蒂諾(Vermentino白葡萄酒)的時候,她的黑色睫毛就會顫巍巍地闔上,然後開始描述她童年的美好時光:鈷藍色的地中海廣闊、平靜、逕向無邊無際滾滾而去。
夏日向晚的慵懶金光,空氣中薰衣草濃香瀰漫,蟬鳴輪唱。有如海岸線哨兵的義大利傘松,凌空升騰,樹頂的巨大華蓋供人躲避熱浪和風雨,而它們的枝條總在低聲訴說著遠古的祕密。
如果瑟琳娜提議「她在麥羅甘吉退休就好」的措辭上,稍稍有那麼一點強硬,她就會哀嚎:「可是,我好愛我的樹喔!」
「那我的樹怎麼辦?」若有人說她對故鄉的留戀只是感情用事,她就會用這句話堵住對方的嘴。
這裡所講的樹專指義大利傘松,學名pinus pinea,是她從小就有著濃厚興趣的樹種。而現在,竟有一棵那麼壯觀、高聳又獨特的傘松在麥羅甘吉這裡意外地現身了。
席德告訴瑟琳娜說,他最近要園丁將九重葛後方那片已經扎根的茂密植被處理掉。清理完後,除了有說不完的好處之外,最先看到的部分就是這棵樹了。瑟琳娜著了迷似地直直走過去,然後轉身看著席德。就在這時,她的臉上出現清新明亮的神采。
「你知道這是什麼嗎?」她有點興奮地問道。
「什麼?」
「過來這邊看看!」
席德走到她身旁,轉身面向九重葛。他和瑟琳娜一樣,都注意到了從另一邊看來並不明顯的對稱性。新翻過的土地兩側有高高的、連綿的杜鵑花叢。些許的砂岩顯示出這裡曾經是花壇的邊界。近處則是一塊鋪砌過的東西,上頭蓋滿了落葉。還有個長滿青苔的凹處。
「這裡以前是一座花園!」瑟琳娜猜想。
席德吃了一驚,向九重葛堆大步走去。他蹲下身子,撥開帶刺的枝條湊近過去,並往灌木叢裡窺探。「如果沒記錯的話,」他轉身對她說:「這個瓦礫堆以前是一座小屋。小小的,只有兩房。」
她和他一起把連串的花叢撥到一旁,以便看到更深處。沒多久,他們找到了一面殘存的牆壁。「這裡可以再蓋一個可愛的小屋喔!」席德沉思道:「我們這花園的規模已經有了。還有松樹,像在拉維洛一樣的松樹。」
「你和我是在想同樣的事嗎?」瑟琳娜目光炯炯有神。
「怎能不和妳想一樣的呢?」席德聳聳肩,曾經是土邦大君的他自帶一股謎樣神態。「一切都是冥冥中自有安排的。」
瑟琳娜和席德發現此處後,一天之內,春喜夫人便親自前來探訪這座重新發現的花園。她壯起膽兒走到九重葛叢後面,察看著成熟的杜鵑花剛剛劃出來的新邊界。其中最棒的是,這棵高貴的義大利傘松讓她讚歎不已。她一靠近樹身,淚水便奪眶而出,彷彿看到一位她深愛、思念的好友,在數十年後終於重逢。她用雙臂摟住樹身,就這樣抱著好久好久,好像跟一個老鄉心意相通一般;他們同樣都在這個喜馬拉雅山的村子裡落腳多年,也都離家鄉很遠。
那時,他們當場就做出了決定。不到幾週,春喜夫人的新屋計畫就得到了贊同和認可,也找好了工程承包商。因為這個計畫不大,也因為席德人脈廣,沒過多久,新家就蓋好了。小巧樸素,是根據女主人的要求設計的。開放式的起居空間和廚房通往客廳,然後是陽台,全部都面向剛鋪好的翠綠草坪。遠遠另一端的牆面中央有一個重要擺設,直立高聳,毫無疑問是地中海風格的,那是她新家的守護神。
至於我的部分,我一直在密切關注這裡的進度。通常在黃昏時分會來工地考察,因為那時候就沒有施工噪音了,還可以聞一聞各種建材怪異又刺鼻的氣味。必要時也有大量的沙堆可以利用。幾週以來,我看著工人挖地基,在平地上砌出了牆壁,接著又出現椽子和屋頂。
我好奇心最重的時候其實是春喜夫人搬進來之後。才一個週末,突然間就有一整個家的全新家具供我探索。而且,因為春喜夫人是繼達賴喇嘛本人之後,我的第二大恩人,她經常喚我為「有史以來最美生物」,所以,我在她家到處探索,那是絕對沒問題的。
那次特別的拜訪是在下午時分。我像往常一樣朝著房子側邊走去,然後從客廳通往陽台的滑動門走進去。春喜夫人會讓門開著,這樣子,空氣才能循環。
「噢,特索麗娜(tesorina,義大利文「小寶貝」的意思)!我的小寶貝兒!妳也來喝茶嗎?」春喜夫人穿著圍裙,正在光可鑑人的廚房長椅後方做著她最擅長的事情──準備做一份放縱味蕾的美味點心。
我喵喵叫了起來。茶會什麼的我是沒概念啦,但是從烤箱裡散發出來的烘烤香氣鐵定值得期待。每次春喜夫人招待她親朋好友時,一定也有我的份。
我走向離廚房最近的沙發,跳上座位,再跳上沙發扶手,最後回到我可以安坐的地方,看著她施展魔法。從她臉龐掠過的黑髮盤成髮髻,一有動作,右臂上的金手鐲便發出清脆的碰撞聲。她沉浸在自己正在做的事情當中。
我這一生經常觀察春喜夫人,而且大多是當她在尊勝寺的廚房,為達賴喇嘛的貴賓準備餐點的時候。早期的她常有很戲劇化的表現,在某些場合甚至會像火山爆發一樣恐怖。在我還是隻小奶貓時,她與達賴喇嘛的某次談話發揮了重大影響。尊者與幾位聯合國代表共進了最圓滿的午餐之後,邀請春喜夫人上樓,可是她好像有些不對勁,甚至不願意接受尊者的謝意。尊者提到她的工作時用了「慈愛」這個詞,她甚至表示反對。
「尊者,但願我真的有慈愛!」她打斷了他。
達賴喇嘛注視著她──有些驚訝,也有些慈悲。他舉起雙手,請她繼續說下去。
「我聽過您的教誨,也讀過一些佛法書籍。關於無限利他的心,說法有很多。但我不能說謊,我的心不是這樣的。如果是,那就好了!」她那塗著黑色睫毛膏的雙眼,睜得大大地盯著尊者,卻很悲傷。「我靠我自己活著。我沒有在助人。我想的主要都是我自己。一整天都是這樣的!」
「可是妳在這裡工作,」達賴喇嘛反駁道,「而且是自願的。」
她聳聳肩。
「妳帶給我的客人們很大的快樂。當然啦,」他揉揉肚子,調皮笑說:「我也很快樂!」
春喜夫人的心理很矛盾,她說:「有時候,或許只是您人好。只是出於禮貌。」
「但是,這位不一樣喔!」尊者用手勢示意我所在之處;那時我正趴在窗台上,旁邊有個小烤盤,正聽著他們這次談話。尊者笑著補充道:「她可不會假裝。」
春喜夫人的表情變得輕鬆起來。「這倒是真的。」她說。
尊者仔細地看了她一會兒,然後輕聲問道:「妳不認為妳所做的事是在修慈愛的心嗎?」
她搖搖頭。
「連在為我們做飯的時候也沒有嗎?」
「我太忙了,沒辦法集中注意力。」她回答。
停頓了許久之後,尊者才再次開口。「既然如此,我有一個正式的請求,」他說,目光突然變得十分嚴肅。「從現在開始,我希望妳做每頓飯時都添加一種特殊食材。」春喜夫人的表情也變得嚴肅起來。
「菩提心,」他說,「妳知道嗎?」
她引述了定義上的說法:「為了利益一切眾生而想獲得開悟的願望。」
尊者點了點頭。「透過做飯,」他模仿攪拌湯鍋的樣子,「願一切眾生都有美味的食物。願他們的日常需求得到滿足。願他們遠離痛苦。」他提議道。
「做主菜的時候?」她問。
「每一道都要,」尊者回答。「廚房裡的每一個動作;在廚房外也是,愈多愈好。每次思考的時候,就憶念菩提心。希望獲得開悟,也希望別人擺脫痛苦。」
春喜夫人臉上閃過一絲猶豫,似乎想說些什麼,卻又改變主意。
「怎麼了?」尊者看著她的眼睛。
「有菩提心是很好啦,」過了一會兒她坦承說:「但只是希望要怎樣,還是沒有實現啊!」
尊者的眼神稍微黯淡下來。「這會改變妳大腦裡面的東西。妳剛剛說,妳只想著自己?這可不是幸福的成因。然而,妳想著要用善意幫助別人的時候,那會怎樣?」
她不用回答,臉上恍然一笑已經說明。
「如果妳訓練自己持續這樣去想事情,那會怎樣?」
「我猜啊,那會成為你的一部分。」
「它會改變妳的為人,對嗎?首先是有幫助別人的想法,再來就是行動。」達賴喇嘛微笑著,伸手去握住她的手。「永遠別忘了這個特殊配料。」
自那時起,春喜夫人在廚房的時候大多都憶念著菩提心。她把這個特殊配料添加到她為尊者和貴賓所烹製的每一頓飯菜裡;添到她為寺裡人員所烘烤的每一袋司康裡;也添到她送到樓上行政助理辦公室的茶壺裡;或她工作或居家時,為瑟琳娜和她自己所調製的飲品裡。
幾年下來,她早已不是那個華格納歌劇版本的春喜夫人了。她以前那些強烈的負面情緒,好像都已經轉變為正面,有時候,慈悲心的能量會自然填滿她內心,就好像以前她總是會強烈表現出不滿那般地自然而然。
我在沙發高處暫歇,發出輕柔的咕嚕聲,看得出來她此刻正在添加特殊配料。她正把麵團從大碗移至烤盤,嘴脣微微嚅動著,臉上浮現出一種特殊神情。
正如尊者所說,菩提心不僅僅成了她的本能。她開始用這種慈悲心在關注、留意著她周圍的人,所以有好幾次,她的存在似乎在她周遭瀰漫出仁慈的光輝,與達賴喇嘛本人並無太大區別。她永遠都是春喜夫人沒錯──有好幾個手鐲叮叮噹噹、言行誇張卻又真情流露。但除此之外,她已經培養出一顆開放的心、熱情又慷慨,能把人們都吸引到她身邊來,就好像在她新發現的花園裡面那一整排怒放的杜鵑,蜜蜂群卻只停歇在其中一處特別茂盛的花叢那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