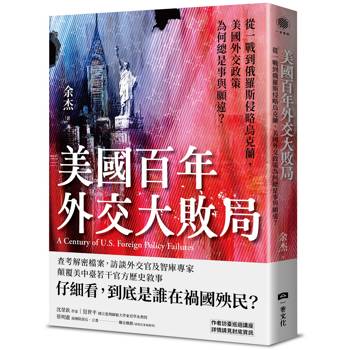「我也像馬歇爾一樣,曾受惑於史迪威(Joseph Warren Stilwell)的報告。但經驗使我對共產主義的威脅能有所警惕。」────魏德邁(Albert Coady Wedemeyer)
一九五一年四月十一日,韓戰緊要關頭,杜魯門將聯合國軍統帥麥克阿瑟免職。麥克阿瑟回到美國,受到民眾盛大歡迎。
反之,杜魯門及其國防部長馬歇爾遭到輿論猛烈抨擊。馬歇爾被傳喚至國會,受到嚴厲質詢,但他堅稱,罷黜麥克阿瑟是因為其策略「要使美國和中國、蘇俄掀起大戰」。麥克阿瑟卻在聽證會上提出截然相反的論點——美國為對華戰略的失策,引起一連串災難,是美國百年來政治的最大敗筆,「我們未來幾代人要為此付出代價:或許要一百年之久。」
馬歇爾與麥克阿瑟兩位五星上將之爭論,是幾年前「誰丟掉了中國」的餘音續唱。蘇聯的全球擴張和共產中國為虎作倀,使美國不斷遭受挫敗,激起美國民眾的危機感和對民主黨政府外交政策的不滿。
參議員麥卡錫(Joseph Raymond McCarthy)公開指控馬歇爾「賣國」:「馬歇爾放棄國民政府,使中國淪於中共;罷黜麥帥,使美國輸掉韓戰。」麥卡錫出版《美國從勝利中的潰退:馬歇爾將軍的故事》(America's Retreat from Victory: The Story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指控馬歇爾參與了「一個如此巨大的陰謀集團,犯下了如此黑暗的惡行,使得人類歷史上任何先前的冒險行為都相形見絀」。
麥卡錫對馬歇爾的指責駭人聽聞。馬歇爾當然不是賣國賊——對於指控,他只回應了一句話:「如果我必須在此刻解釋自己不是美國的叛徒,那麼我認為是不值得。」但馬歇爾確實對丟掉中國負有相當之責任。儘管「馬歇爾計畫」在歐洲大獲成功,馬歇爾榮獲諾貝爾和平獎,但這些光輝無法抹煞他在中國失敗的汙點。
馬歇爾自詡為中國通,卻從未真正了解中國,更對中共一無所知;反倒是沒有在中國任過職的麥克阿瑟,一眼看穿中國的本質:「在過去五十年中,中國人的觀念和理想變得日益軍事化,變成了一種全民一致的、愈來愈具有支配慾和好戰傾向的民族主義。」麥帥認為,馬歇爾鑄成一個根本性錯誤:「那就是天真地以為共產黨不過是群土地改革者,因此犧牲國民黨來同共產黨妥協。這個錯誤原本可以得到糾正,但可悲的是我們白白浪費了良機。放棄原則的做法鞏固了共黨對中國大陸的統治,幫助其發展壯大,使其在爭奪世界的鬥爭中很可能成為軍事天平另一端的砝碼。」
美國「丟掉中國」的命題只能算半個命題。不成立的一半是因為:美國從未真正「擁有」過中國,既然不曾「擁有」,何談「失去」?但它也成立一半:美國與中華民國政府儘管時有齟齬,但中華民國政府至少願意身處美國領導的自由陣營(雖然其威權體制下的自由「多乎哉,不多也」,但逃到臺灣後的國民政府仍然以「自由中國」自居);而通過內戰奪權的中共政權,毫不掩飾地將美國當作敵人,而且數十年後它確實將自己鍛造成美國建國以來最危險的敵人(超過了軍國主義的日本帝國、納粹德國、史達林主義的蘇聯以及伊斯蘭恐怖分子),此種局面的形成,跟美國對華戰略一錯再錯直接相關。
「丟掉中國」的第一責任人是腐敗無能、進退失據的蔣介石及其國民黨團隊,還有投向共產黨的大部分中國民眾——他們確實選擇了共產黨,共產黨軍隊進入北平和上海等大城市時,得到多數市民熱烈歡迎。
其次,負有重大責任的是被史達林操弄、簽署《雅爾達協定》導致滿洲乃至整個中國赤化的美國總統羅斯福。
再其次,就是羅斯福的接班人杜魯門及其派到中國的特使——在中國奔波一年之久、最後「揮一揮手,不帶走一片雲彩」的馬歇爾。
國民黨、共產黨及第三勢力都不是馬歇爾期待的「健康力量」
聽聞馬歇爾的任命,國民黨方面對馬歇爾的使命有相當之隱憂。陳立夫得知馬歇爾使華的消息以後,向蔣介石進言三點意見:「第一,國共間的問題,宜直接商諸蘇聯,反易解決;第二,美方對共黨問題,見解不深,易受其欺;第三,國共問題,調解成功之機會極小,馬歇爾將軍英雄人物,為世所稱,此番出任調人,只能成功,不能失敗,一旦失敗,如何收場?其咎若諉之於我方,我又將何以自處?」蔣深以為然,卻對美方做出的決定無能為力——此前,蔣已逼迫羅斯福換掉史迪威;如今,面對不太友好的杜魯門,他不可能逼其換掉馬歇爾(而馬歇爾是史迪威的老朋友,深受史迪威的影響,對國民政府頗有成見。)
十二月二十一日,馬歇爾抵達南京,與蔣介石夫婦討論國共停戰問題。他表示,美國的軍事援助及幫助戰後中國的重建,都取決於國民政府與共產黨達成和解。至於共產黨,如果他們不願配合,「他們將很快失去美國的所有同情」。
蔣略帶疑慮地回應說,共產黨擁有一支獨立的軍隊,而且得到蘇聯的幫助,在近期的幾次衝突中取得了勝利。馬歇爾對此提出異議,他並不認為蘇聯有意削弱國民黨政權。他說,二戰期間,他曾與史達林直接打過交道,以個人經驗來看,「這位領導人值得信賴」。他一度認為史達林是通情達理、信守承諾的人,西方有可能與蘇聯達成妥協,這個看法與羅斯福如出一轍。直到幾年後全球冷戰態勢形成,他才從對蘇聯的幻想中夢醒。
次年二月,蔣在日記中寫道:「唯馬歇爾與中共商談已有月餘,其對中共欺人之手法,或已漸瞭解乎?」數週後,他明確表示這位特使過於天真:「然其受共黨之麻醉日甚,美國民族之易受人欺誑,其老練如馬氏尚且如此,其他更可知矣。」
隨即,馬歇爾飛往中國戰時陪都重慶,在那裡建立總部。十二月二十三日,馬歇爾第一次會見中共代表周恩來、葉劍英和董必武三人。他對這三人、尤其是周恩來印象良好。
一九四六年一月,在馬歇爾倡議下,在重慶成立「三人小組」,成員包括馬歇爾、國民黨代表張群和共產黨代表周恩來,馬歇爾任小組主席。「三人小組」舉行了六次會議後,達成有關停戰的協議,然後再交由蔣介石和毛澤東批准。一月十日,在政治協商會議開幕當天,政府和中共雙方簽訂停戰協議,並將該命令下達到一切部隊。此為第一次停戰令。
為貫徹停戰協議,國共雙方決定在北平成立「軍事調處執行部」(即「軍調部」),該機構可派駐小組到一些衝突熱點地區去監督停戰狀況。
馬歇爾對該協定寄予厚望。他在三個月內便幫助中國敲定實現全面和解的框架,成功似乎唾手可得。魏德邁承認,馬歇爾「表現出色,贏得了所有與他接觸過的人們的尊重與讚賞」,但他又警告說,蔣介石和毛澤東只不過是利用停戰協定來重新結集各自的兵力以發動新的進攻,該協定相當脆弱。
一九四六年二月,「三人小組」經過五次商談,簽訂<關於軍隊整編及統編中共部隊為國軍之基本案>。二月二十八日,以馬歇爾為首的「和平觀察團」,自重慶出發,飛往北平、張家口、集寧、濟南、徐州、新鄉、太原、歸綏等地視察。
在此期間,馬歇爾的健康出現問題,經過無休止的奔波和談判,加上不計其數的會議與宴請,他看上去比過去更加憔悴,需要回國稍事修養。三月中旬,他返回華盛頓,受到英雄般的歡迎。然而,正如魏德邁所說,「(馬歇爾)所取得成就的時間長短,取決於他在當地停留時間的長短」,他的病假和離開極大地影響了其使命的達成。
參與「軍調部」工作的美國駐華武官吉勒姆將軍發現,中國人對已做出的承諾沒有責任感,美方除了弄到簽字外,別無他事可做,因為事先已知道協議和文件毫無實際意義。「軍調部」的共產黨委員葉劍英將軍告訴蘇聯駐華使館官員,共軍不會執行停戰令,「共產黨人對停止敵對行動不感興趣」。中共軍隊陽奉陰違,擅自移動部隊,攫取戰略要地,甚至繼續襲擊國軍。一九四六年初,中共控制之地區已擴至三百多個縣,比起一九四五年夏天日本投降時他們只占有八十一縣的情形,擴張了兩倍以上。
當馬歇爾於四月十七日返回中國之時,發現局勢已極度惡化。中共拒不執行所有協定,並派遣軍政人員潛入蘇聯控制之下的滿洲。四月十五日,周恩來公開宣稱,東北進入「全面敵對行動」狀態。馬歇爾奔波於重慶、南京、上海之間,與國共雙方代表接觸,尋求東北問題的解決方案。
在東北戰場上,情勢最初對國軍有利。國軍在四平街擊敗共軍,並一直追擊到哈爾濱。蔣介石視之為第五次圍剿之後最大一次決定性勝利。馬歇爾卻以斷絕美援為威脅,迫使蔣介石在六月六日頒發第二次停戰令。
七月,戰事在東北、華北各地蔓延。馬歇爾八上廬山,與蔣介石商談,並建議成立五人小組,商談政府改組和國民大會問題。十月五日,在馬歇爾施壓下,蔣介石決定停戰十天。馬歇爾和蔣介石都不知道,毛澤東在四天前的十月一日向黨內發出名為<三月總結>的祕密指示,將馬歇爾的調解視為「騙局」。十一月八日,蔣介石為了讓國民大會順利召開,頒布第三次停戰令,並再次邀請中共參與國民大會,但中共斷然拒絕。
一九四七年一月六日,杜魯門宣布馬歇爾業已結束其在華之調處任務,並召馬歇爾返美。七日,馬歇爾離華前,發表一篇冗長聲明,承認其使命失敗,但對中共之極權本質仍無認識。八日,馬歇爾回到華盛頓,就任國務卿——敗軍之將(馬歇爾在中國進行的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居然升職,這是杜魯門政府無能的又一表現。
一月二十九日,美國駐華大使館發表聲明,宣布美國退出三人小組及「軍調部」。次日,這兩個臨時機構正式解散。三月七日,中共駐南京和上海的兩機構人員,撤回延安,董必武稱,國共之聯繫從此斷絕。為時一年有餘的馬歇爾調處,至此完全終結。
馬歇爾不可能做到「不辱使命」,他面臨的困難超過他的解決能力及可運用的資源。
首先,馬歇爾無法解開《雅爾達協定》之魔咒——羅斯福與史達林聯手在協定中傷害中國之主權,規定「蘇聯應該恢復以前俄羅斯帝國之權利」,包括對大連、旅順、中東鐵路和南滿鐵路的控制等。而「得滿洲者得中國」,蘇聯一旦控制滿洲,必以滿洲的資源武裝中共,中共遂不再受制於任何協定。
其次,國共兩黨都相信成王敗寇、「槍桿子裡出政權」,這是由中國的政治傳統和政治現實,源遠流長的民情民風、觀念秩序,以及兩黨都是列寧式政黨的本質所決定的。中國人既沒有主權在民、政府民選的觀念,對三權分立的政治模式缺乏認識,更沒有現代民族國家「國防軍」只能對外作戰的憲制規定。馬歇爾不可能在一夜之間改變中國的民情和權力邏輯,更不能硬生生地將美國制度移植到中國。用親共的資深外交官戴維斯(John William Davis)的話來說,即使馬歇爾有「奧林匹斯山神的威望」,也不可能改變中國。
第三,在國共之外,馬歇爾找不到任何將中國帶往民主自由方向的健康力量。馬歇爾在中國與各種政治及意識形態傾向的政黨和團體的代表會見並交談,在此過程中發現了妨礙其實現任務的嚴重困難。他特別指出,中國對話人除了就中國的主要尖銳問題進行「有創見的討論」外,誰也想不出克服危機的出路,所有的中國人都持有需要民主的共同觀點,但誰也不曾提出過實現這一目標的具體方法,中國人對民主的真諦並無明確的概念。
馬歇爾為了提高「第三勢力」的地位,竭力遊說蔣介石吸收他們加入政府,同時又勸告蔣「不能照老一套的做法,以有誘惑力的任命收買他們以消除反對派」。然而,「第三勢力」並不爭氣,很多人早已待價而沽,青年黨的曾琦當面要求蔣:「行政院必須改組,吾輩無所謂,吾輩部下就希望分得幾部做官吃飯。」馬歇爾如若有知,當做何感想?
一九五一年四月十一日,韓戰緊要關頭,杜魯門將聯合國軍統帥麥克阿瑟免職。麥克阿瑟回到美國,受到民眾盛大歡迎。
反之,杜魯門及其國防部長馬歇爾遭到輿論猛烈抨擊。馬歇爾被傳喚至國會,受到嚴厲質詢,但他堅稱,罷黜麥克阿瑟是因為其策略「要使美國和中國、蘇俄掀起大戰」。麥克阿瑟卻在聽證會上提出截然相反的論點——美國為對華戰略的失策,引起一連串災難,是美國百年來政治的最大敗筆,「我們未來幾代人要為此付出代價:或許要一百年之久。」
馬歇爾與麥克阿瑟兩位五星上將之爭論,是幾年前「誰丟掉了中國」的餘音續唱。蘇聯的全球擴張和共產中國為虎作倀,使美國不斷遭受挫敗,激起美國民眾的危機感和對民主黨政府外交政策的不滿。
參議員麥卡錫(Joseph Raymond McCarthy)公開指控馬歇爾「賣國」:「馬歇爾放棄國民政府,使中國淪於中共;罷黜麥帥,使美國輸掉韓戰。」麥卡錫出版《美國從勝利中的潰退:馬歇爾將軍的故事》(America's Retreat from Victory: The Story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指控馬歇爾參與了「一個如此巨大的陰謀集團,犯下了如此黑暗的惡行,使得人類歷史上任何先前的冒險行為都相形見絀」。
麥卡錫對馬歇爾的指責駭人聽聞。馬歇爾當然不是賣國賊——對於指控,他只回應了一句話:「如果我必須在此刻解釋自己不是美國的叛徒,那麼我認為是不值得。」但馬歇爾確實對丟掉中國負有相當之責任。儘管「馬歇爾計畫」在歐洲大獲成功,馬歇爾榮獲諾貝爾和平獎,但這些光輝無法抹煞他在中國失敗的汙點。
馬歇爾自詡為中國通,卻從未真正了解中國,更對中共一無所知;反倒是沒有在中國任過職的麥克阿瑟,一眼看穿中國的本質:「在過去五十年中,中國人的觀念和理想變得日益軍事化,變成了一種全民一致的、愈來愈具有支配慾和好戰傾向的民族主義。」麥帥認為,馬歇爾鑄成一個根本性錯誤:「那就是天真地以為共產黨不過是群土地改革者,因此犧牲國民黨來同共產黨妥協。這個錯誤原本可以得到糾正,但可悲的是我們白白浪費了良機。放棄原則的做法鞏固了共黨對中國大陸的統治,幫助其發展壯大,使其在爭奪世界的鬥爭中很可能成為軍事天平另一端的砝碼。」
美國「丟掉中國」的命題只能算半個命題。不成立的一半是因為:美國從未真正「擁有」過中國,既然不曾「擁有」,何談「失去」?但它也成立一半:美國與中華民國政府儘管時有齟齬,但中華民國政府至少願意身處美國領導的自由陣營(雖然其威權體制下的自由「多乎哉,不多也」,但逃到臺灣後的國民政府仍然以「自由中國」自居);而通過內戰奪權的中共政權,毫不掩飾地將美國當作敵人,而且數十年後它確實將自己鍛造成美國建國以來最危險的敵人(超過了軍國主義的日本帝國、納粹德國、史達林主義的蘇聯以及伊斯蘭恐怖分子),此種局面的形成,跟美國對華戰略一錯再錯直接相關。
「丟掉中國」的第一責任人是腐敗無能、進退失據的蔣介石及其國民黨團隊,還有投向共產黨的大部分中國民眾——他們確實選擇了共產黨,共產黨軍隊進入北平和上海等大城市時,得到多數市民熱烈歡迎。
其次,負有重大責任的是被史達林操弄、簽署《雅爾達協定》導致滿洲乃至整個中國赤化的美國總統羅斯福。
再其次,就是羅斯福的接班人杜魯門及其派到中國的特使——在中國奔波一年之久、最後「揮一揮手,不帶走一片雲彩」的馬歇爾。
國民黨、共產黨及第三勢力都不是馬歇爾期待的「健康力量」
聽聞馬歇爾的任命,國民黨方面對馬歇爾的使命有相當之隱憂。陳立夫得知馬歇爾使華的消息以後,向蔣介石進言三點意見:「第一,國共間的問題,宜直接商諸蘇聯,反易解決;第二,美方對共黨問題,見解不深,易受其欺;第三,國共問題,調解成功之機會極小,馬歇爾將軍英雄人物,為世所稱,此番出任調人,只能成功,不能失敗,一旦失敗,如何收場?其咎若諉之於我方,我又將何以自處?」蔣深以為然,卻對美方做出的決定無能為力——此前,蔣已逼迫羅斯福換掉史迪威;如今,面對不太友好的杜魯門,他不可能逼其換掉馬歇爾(而馬歇爾是史迪威的老朋友,深受史迪威的影響,對國民政府頗有成見。)
十二月二十一日,馬歇爾抵達南京,與蔣介石夫婦討論國共停戰問題。他表示,美國的軍事援助及幫助戰後中國的重建,都取決於國民政府與共產黨達成和解。至於共產黨,如果他們不願配合,「他們將很快失去美國的所有同情」。
蔣略帶疑慮地回應說,共產黨擁有一支獨立的軍隊,而且得到蘇聯的幫助,在近期的幾次衝突中取得了勝利。馬歇爾對此提出異議,他並不認為蘇聯有意削弱國民黨政權。他說,二戰期間,他曾與史達林直接打過交道,以個人經驗來看,「這位領導人值得信賴」。他一度認為史達林是通情達理、信守承諾的人,西方有可能與蘇聯達成妥協,這個看法與羅斯福如出一轍。直到幾年後全球冷戰態勢形成,他才從對蘇聯的幻想中夢醒。
次年二月,蔣在日記中寫道:「唯馬歇爾與中共商談已有月餘,其對中共欺人之手法,或已漸瞭解乎?」數週後,他明確表示這位特使過於天真:「然其受共黨之麻醉日甚,美國民族之易受人欺誑,其老練如馬氏尚且如此,其他更可知矣。」
隨即,馬歇爾飛往中國戰時陪都重慶,在那裡建立總部。十二月二十三日,馬歇爾第一次會見中共代表周恩來、葉劍英和董必武三人。他對這三人、尤其是周恩來印象良好。
一九四六年一月,在馬歇爾倡議下,在重慶成立「三人小組」,成員包括馬歇爾、國民黨代表張群和共產黨代表周恩來,馬歇爾任小組主席。「三人小組」舉行了六次會議後,達成有關停戰的協議,然後再交由蔣介石和毛澤東批准。一月十日,在政治協商會議開幕當天,政府和中共雙方簽訂停戰協議,並將該命令下達到一切部隊。此為第一次停戰令。
為貫徹停戰協議,國共雙方決定在北平成立「軍事調處執行部」(即「軍調部」),該機構可派駐小組到一些衝突熱點地區去監督停戰狀況。
馬歇爾對該協定寄予厚望。他在三個月內便幫助中國敲定實現全面和解的框架,成功似乎唾手可得。魏德邁承認,馬歇爾「表現出色,贏得了所有與他接觸過的人們的尊重與讚賞」,但他又警告說,蔣介石和毛澤東只不過是利用停戰協定來重新結集各自的兵力以發動新的進攻,該協定相當脆弱。
一九四六年二月,「三人小組」經過五次商談,簽訂<關於軍隊整編及統編中共部隊為國軍之基本案>。二月二十八日,以馬歇爾為首的「和平觀察團」,自重慶出發,飛往北平、張家口、集寧、濟南、徐州、新鄉、太原、歸綏等地視察。
在此期間,馬歇爾的健康出現問題,經過無休止的奔波和談判,加上不計其數的會議與宴請,他看上去比過去更加憔悴,需要回國稍事修養。三月中旬,他返回華盛頓,受到英雄般的歡迎。然而,正如魏德邁所說,「(馬歇爾)所取得成就的時間長短,取決於他在當地停留時間的長短」,他的病假和離開極大地影響了其使命的達成。
參與「軍調部」工作的美國駐華武官吉勒姆將軍發現,中國人對已做出的承諾沒有責任感,美方除了弄到簽字外,別無他事可做,因為事先已知道協議和文件毫無實際意義。「軍調部」的共產黨委員葉劍英將軍告訴蘇聯駐華使館官員,共軍不會執行停戰令,「共產黨人對停止敵對行動不感興趣」。中共軍隊陽奉陰違,擅自移動部隊,攫取戰略要地,甚至繼續襲擊國軍。一九四六年初,中共控制之地區已擴至三百多個縣,比起一九四五年夏天日本投降時他們只占有八十一縣的情形,擴張了兩倍以上。
當馬歇爾於四月十七日返回中國之時,發現局勢已極度惡化。中共拒不執行所有協定,並派遣軍政人員潛入蘇聯控制之下的滿洲。四月十五日,周恩來公開宣稱,東北進入「全面敵對行動」狀態。馬歇爾奔波於重慶、南京、上海之間,與國共雙方代表接觸,尋求東北問題的解決方案。
在東北戰場上,情勢最初對國軍有利。國軍在四平街擊敗共軍,並一直追擊到哈爾濱。蔣介石視之為第五次圍剿之後最大一次決定性勝利。馬歇爾卻以斷絕美援為威脅,迫使蔣介石在六月六日頒發第二次停戰令。
七月,戰事在東北、華北各地蔓延。馬歇爾八上廬山,與蔣介石商談,並建議成立五人小組,商談政府改組和國民大會問題。十月五日,在馬歇爾施壓下,蔣介石決定停戰十天。馬歇爾和蔣介石都不知道,毛澤東在四天前的十月一日向黨內發出名為<三月總結>的祕密指示,將馬歇爾的調解視為「騙局」。十一月八日,蔣介石為了讓國民大會順利召開,頒布第三次停戰令,並再次邀請中共參與國民大會,但中共斷然拒絕。
一九四七年一月六日,杜魯門宣布馬歇爾業已結束其在華之調處任務,並召馬歇爾返美。七日,馬歇爾離華前,發表一篇冗長聲明,承認其使命失敗,但對中共之極權本質仍無認識。八日,馬歇爾回到華盛頓,就任國務卿——敗軍之將(馬歇爾在中國進行的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居然升職,這是杜魯門政府無能的又一表現。
一月二十九日,美國駐華大使館發表聲明,宣布美國退出三人小組及「軍調部」。次日,這兩個臨時機構正式解散。三月七日,中共駐南京和上海的兩機構人員,撤回延安,董必武稱,國共之聯繫從此斷絕。為時一年有餘的馬歇爾調處,至此完全終結。
馬歇爾不可能做到「不辱使命」,他面臨的困難超過他的解決能力及可運用的資源。
首先,馬歇爾無法解開《雅爾達協定》之魔咒——羅斯福與史達林聯手在協定中傷害中國之主權,規定「蘇聯應該恢復以前俄羅斯帝國之權利」,包括對大連、旅順、中東鐵路和南滿鐵路的控制等。而「得滿洲者得中國」,蘇聯一旦控制滿洲,必以滿洲的資源武裝中共,中共遂不再受制於任何協定。
其次,國共兩黨都相信成王敗寇、「槍桿子裡出政權」,這是由中國的政治傳統和政治現實,源遠流長的民情民風、觀念秩序,以及兩黨都是列寧式政黨的本質所決定的。中國人既沒有主權在民、政府民選的觀念,對三權分立的政治模式缺乏認識,更沒有現代民族國家「國防軍」只能對外作戰的憲制規定。馬歇爾不可能在一夜之間改變中國的民情和權力邏輯,更不能硬生生地將美國制度移植到中國。用親共的資深外交官戴維斯(John William Davis)的話來說,即使馬歇爾有「奧林匹斯山神的威望」,也不可能改變中國。
第三,在國共之外,馬歇爾找不到任何將中國帶往民主自由方向的健康力量。馬歇爾在中國與各種政治及意識形態傾向的政黨和團體的代表會見並交談,在此過程中發現了妨礙其實現任務的嚴重困難。他特別指出,中國對話人除了就中國的主要尖銳問題進行「有創見的討論」外,誰也想不出克服危機的出路,所有的中國人都持有需要民主的共同觀點,但誰也不曾提出過實現這一目標的具體方法,中國人對民主的真諦並無明確的概念。
馬歇爾為了提高「第三勢力」的地位,竭力遊說蔣介石吸收他們加入政府,同時又勸告蔣「不能照老一套的做法,以有誘惑力的任命收買他們以消除反對派」。然而,「第三勢力」並不爭氣,很多人早已待價而沽,青年黨的曾琦當面要求蔣:「行政院必須改組,吾輩無所謂,吾輩部下就希望分得幾部做官吃飯。」馬歇爾如若有知,當做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