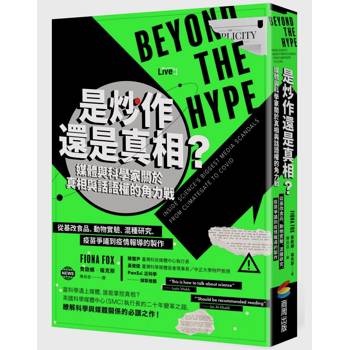序
二〇〇九年九月新聞頭條說「癌症疫苗導致少女死亡」,原因是十四歲女學生娜塔莉.莫頓(Natalie Morton)在校內接種人類乳突病毒(HPV)疫苗之後不幸喪命。以宗教界為首的某些社會群體本來就對學生接種子宮頸癌疫苗很感冒,他們認為既然病毒透過性行為傳染就不該給未滿十六歲的人注射疫苗。新聞一出,疫苗安全與否受到各方關注,頭條追蹤數日之久,然而事隔十年我在一場科普活動上詢問,請記得此事的聽眾舉手,結果一個也沒有。反觀麻疹、腮腺炎、德國麻疹混合疫苗(即MMR三合一疫苗)導致自閉症一說,最早於一九九八年就曾登上頭條,現場所有人都舉手表示有印象。
同樣是疫苗害命的驚悚新聞,為什麼一則深植人心、另一則卻遭到淡忘?我的答案,亦即本書的主題,就是科學家終於懂得如何發聲。這個轉變的部分原因在於我參與創立的組織──「科學媒體中心」(Science Media Centre, SMC)始於二〇〇二年,推廣科學界以嶄新主動的態度因應新聞頭條。我們的宗旨是「科學家懂媒體,媒體才能懂科學」,改善科學新聞最簡單有效的辦法就是科學家與記者攜手合作,一起努力將報導內容寫正確。
時至今日,科學媒體中心的人才庫已有三千多位頂尖科學家進駐,獲得全英國所有媒體渠道採用,每年舉辦約六十場記者會。我們也運用超過一百個組織團體的小額捐款擴大影響力,觸角遍及全世界,澳洲、加拿大、紐西蘭、德國各自成立了科學媒體中心,美國亦有性質類似的單位。最新生力軍包括臺灣以及面對全非洲大陸的機構,西班牙的新中心預計於二〇二二年初開始營運。
二〇〇九年,第一位記者致電我們想瞭解娜塔莉.莫頓的死因,我立刻聯繫人才庫內所有疫苗專家,請大家針對焦點新聞做出即時回應。從接下來幾小時延續到數日之內,許多專家接受新聞節目訪談,意見得到各大媒體轉述。他們協助製作問答集、事實查核表格與清晰圖片,於是媒體版面上不再只有少女意外暴斃這種嚇人的文字敘述。由於是突發個案,科學家們當然也無法徹底掌握來龍去脈,然而這並不代表不能回應,他們透過堆積如山的資料證明疫苗安全且有效,因此短短幾小時內頭條風向就變了,例如《每日郵報》報導「專家表示癌症疫苗安全無虞」。
過去科學家傾向迴避媒體,喜歡躲在實驗室而非暴露於鎂光燈下。這其實是人之常情。當時尚未強調科學傳播可及性(accessible science communication),也不將其視為公共財,學術界進入公眾討論的誘因少之又少,參與者多半只是推動科學普及,也就是介紹自己的研究領域或科學基本原則,而且人數並不多。不過情況逐漸轉變了,一九八五年皇家學會提出《公眾的科學理解》,又稱為「博瑪報告」(Bodmer Report),呼籲科學家將公眾參與視為自身的社會義務。一九九〇年代末,研究經費分配方式也有所調整,針對媒體工作提供更多誘因,譬如必須將成果與大眾分享才能獲得補助。種種措施發揮作用,科學家開始主動接觸媒體,將研究結果告知可信賴的科學記者。即便如此,科學爭議登上頭版頭條時問題仍在:一旦捲入媒體報導就得與各方運動人士或病友團體交鋒,不習慣大陣仗的研究人員通常無意涉入,許多不正確資訊在媒體狂潮中應運而生,對公眾的科學理解以及公眾政策制定造成莫大衝擊。
然而從HPV疫苗恐慌之中可以看見事情已經出現轉機,面對複雜、聳動、可能損及學術聲望的新聞,科學家不再選擇逃避而是正面迎擊。死亡個案本身固然是悲劇,但他們的參與將報導風向和資訊導回正途,最終促成公眾對疫苗證據更深入的瞭解。
是什麼改變了?雖然很想在此居功,不過若要理解科學界起了什麼變化,首先就要看看科學媒體中心為何存在。
*
千禧年前後登上頭版頭條的科學新聞並不只有MMR三合一疫苗,其他諸如動物研究設施與基因改造食品也招致負面觀感和資訊錯亂。儘管當下仍有少數勇敢科學家願意出面解釋,卻不足以扭轉輿論和政策遭到誤導的趨勢。
這些領域之中,多數科學家主動迴避媒體接觸。他們隱居在大學或研究所,心裡在乎的只有下一次實地實驗,抑或是在同儕審查期刊上發表成果。我訪問過世界一流研究機構內的植物科學家,他們對當年的情況著實不解,只能眼睜睜看著善於操作媒體的環境運動人士偕同各路小報以鋪天蓋地之姿妖魔化基因科技及其前景。結果如何呢?社會大眾、政治人物以至於超級市場在第一粒基改農作物問世之前就咬牙切齒全面抵制。
一九九九年,英國科學界無力回應媒體亂象的問題,得到上議院科學技術特別委員會重視。時任科技部長的森寶利勳爵(Lord Sainsbury)與已故的詹金勳爵(Lord Jenkin)共同推出《科學與社會調查報告》,對公眾的科學理解這個主題貢獻卓著,如今已是科技傳播課程的必讀經典。報告內容反映出上個千禧年末科學與媒體之間關係緊繃:知名科學家感慨媒體報導不受控制、指責記者破壞大眾對科學的信任,但科學記者反唇相譏,認為科學家自恃精英高高在上、每年露臉一次彷彿下詔,然後又會躲回學術舒適圈。英國廣播公司(BBC)科學記者帕拉卜.戈希(Pallab Ghosh)敦促科學家不要只會抱怨遊戲規則,捲起袖子跳進場內才是正解。
公元兩千年發表的《科學與社會調查報告》呼籲投入新資源,訓練並鼓勵科學家與媒體互動,其中一段提到:
英國科學文化需要一次重大革新,與媒體建立開放且正向的溝通管道。為達成此目標需要訓練與資源,更需要組織架構……尷尬與挫折在過程中在所難免,不過若能成功,重燃公眾信心便是最為豐碩的回報。
為了落實這些理念,科學媒體中心誕生了。
*
MMR三合一疫苗與基因改造食品掀起軒然大波的時期,我原本還在英國天主教海外發展處(Press for the Catholic Agency for Overseas Development, CAFOD)當媒體主任。千禧年前夕,我有幸在千禧債務減免運動(Jubilee 2000 Campaign)中擔任領頭羊,活動獲得一時成功,激發大眾與媒體對美好世界的固有追求,造就很多極具意義的重要改變。然而彷彿狂歡結束宿醉酒醒,媒體對開發中國家債務問題的興趣一下子煙消雲散,單純的發展議題越來越難勾起關注。
我的媒體策略也不得不走上偏鋒:讓約克郡水災難民與莫三比克水災難民會面、在唐寧街丟金條抗議國際貨幣基金拒絕出售黃金儲備資助減債計畫,並安排甫入教的國會議員安.維德坎姆(Ann Widdecombe)參觀天主教海外發展處的非洲專案,希望能扭轉她對減債的想法。結果適得其反:她原本就認為減債計畫會淪為非洲貪腐政府中飽私囊的機會,參訪過程反而深化了這種信念,行程結束回國後也在許多廣播或電視訪談表達立場。《每日電訊報》特稿編輯表示他們願意刊一篇來自我方的意見,前提是必須改以鮑勃.格爾多夫(Bob Geldof)或波諾(Bono)之類名人的名義。當下我明白離開的時候到了,我不想停留只有靠腥膻色或知名度才能爭取曝光的工作領域。再看看還有什麼主題能登上頭版,我發現答案是科學。
我表示自己想為科學界經營媒體關係的時候,不少朋友都笑了。以過去成績而言,我在威爾斯語、英語和歷史拿到了A,還有一個新聞學學位。但跟當時大部分人一樣,我很關心圍繞在基因改造食品和MMR三合一疫苗的辯論,而且我非常支持科學。此外,我也想為那些在報導上總是居於劣勢的陣營做點什麼努力。
大約同時,我讀到二〇〇一年一月蘇珊.格林菲爾德(Susan Greenfield)教授接受《金融時報》的專訪,她提到想在皇家研究院(Royal Institute)內成立全新獨立的媒體中心作為科學家與記者之間的橋梁。格林菲爾德教授除了在神經科學與科普方面厥功甚偉,也是皇家研究院首任女性院長。從她願意穿著招牌迷你裙為《Hello!》雜誌擺拍,解釋大腦機制也能講得許多聽眾津津有味,可以想見她對媒體工作有著獨樹一格的見解。森寶利勳爵在報告書中提到新形態媒體中心,詢問是否能以皇家研究院作為據點,格林菲爾德教授欣然接受。
六個月後,我的面試官陣容非常豪華,由八位科學界大人物組成,其中包括已由布萊爾首相授予爵位的格林菲爾德本人、《自然》期刊主編菲利普.坎貝爾(Philip Campbell)博士,以及前自然環境研究委員會主席約翰.克雷布斯(John Krebs)爵士教授。我的資歷其實並不合乎要求,但這也代表我無需對失敗畏首畏尾。而且雖然我不具備她們期待的科學背景,以二〇〇一年的情況而言我不認為有人真的能兼顧媒體處理與硬派科學,也因此我的訴求很明確:我認為科學媒體中心需要一個深度瞭解媒體需求,同時又能協助科學家將話講得簡白易懂的人,學術背景反而並不那麼重要。這場賭局最後是我贏了,不過她們也表明態度,基於這個決定有其風險所以給我的年薪比徵才啟事少了一萬英鎊,這筆錢會拿去多招募一個具博士學位的人。我無所謂,接下來好幾天宣佈新工作的時候,朋友們一臉不可置信。我在科學世界的冒險啟程了。
*
過去二十年間,科學界的文化經歷重大革新,科學家從象牙塔內遙不可及的存在搖身一變成為真正參與國民生活的專家學者,一般認為科學媒體中心既是這股變革的推手,也是其成果。透過本書內容,我記錄這場寧靜革命的進程,揭露過去二十年間最爭議的科學報導背後有何祕辛,並針對科學通訊面對的新威脅提出自身見解。由於阿拉斯泰爾.坎貝爾(Alastair Campbell)和多米尼克.卡明斯(Dominic Cummings)等幾位政治化妝師及特別顧問的爆料,社會大眾對於政壇內幕已經不再陌生;反觀科學雖然深深影響人類生活,尤其大眾仍在摸索新冠疫情後的新生態,我們對於科學新聞卻尚未建立同等意識。作為科學新聞負責人,在第一線見證過科學與媒體交鋒,我希望本書能激起讀者對於當代重要科學議題的興趣,或者幫助大家理解科學與政治、文化、社會整體之間有何複雜交集。
書中收錄的事件對某些年齡段的人或許耳熟能詳。想必還有人記得大衛.納特(David Nutt)教授曾經擔任英國政府的藥物首席顧問,卻在二〇〇九年十月被迫下臺(詳見第五章)。同年僅僅一個月之後,氣候變遷否定團體為證明暖化議題是造假,以駭客手法盜取了學術界的電子郵件並引發全球騷動(詳見第六章)。其他章節涉及的主題層面更廣,例如動物實驗如何從科學界的黑暗小祕密蛻變為大眾接受的醫藥研究環節(詳見第二章),或者原本對「科學怪人食品」之類聳動標題惶恐迴避的基因改造研究者如何轉型,不僅成為新形態媒體投入的主要推手,甚至不惜與查爾斯三世及環境運動人士槓上(詳見第一章)。再來也會提到政府試圖禁止科學家對人類和動物胚胎進行研究,結果引發科學界與病友代表團體史無前例的反撲(詳見第四章),為日後更複雜的倫理議題如人類基因編輯或所謂「三親嬰兒」奠定基調,深切影響了政壇與民間的思考方向。
有兩個篇章不講述特定事件,從更宏觀的角度探討科學傳播與新聞這個主題。第九章提到儘管我在科學媒體中心工作勢必常與媒體搏鬥,結果卻也常為英國的科技、健康和環境記者出頭,因為部分科學家批評媒體做出爛報導時其實根本良莠不分。第十章則談到我個人的擔憂:科學新聞發言人恐將瀕臨絕種,因為主攻研究的大學越來越走向商業化營運,研究通訊或許終將被巨大的行銷部門併吞。
少部分事件未能有個圓滿結局或落入較大主題分類中,甚至未必與科學媒體中心的職務緊密相連,但也不該因此忽略。二〇一五年某次科技新聞記者會上,諾貝爾生物學獎得主蒂姆.亨特(Tim Hunt)爵士的言論涉及性別歧視引起輿論嘩然,當時科學媒體中心沒有機會介入太多,但後來另一次全球重要科學報導上我則有機會提供建議(詳見第八章)。肌痛性腦脊髓炎(myalgic encephalomyelitis, ME)或稱慢性疲勞症候群(chronic fatigue syndrome)恐怕多數讀者並不熟悉,但事件經過呈現出科學家及研究證據持續遭到抨擊時,科學媒體中心能夠做什麼(詳見第三章)。
本書絕大多數內容圍繞一個主題:力爭得來的公開透明值得好好守護。部分事件描述中,讀者會看到我向政府據理力爭,避免獨立科學家承受高層壓力而無法公開發言。這種情況十分普遍,存在於政黨提出的反遊說條款中,也反映在政府通訊官員對獨立科學通訊的過度干預。
二〇〇九年九月新聞頭條說「癌症疫苗導致少女死亡」,原因是十四歲女學生娜塔莉.莫頓(Natalie Morton)在校內接種人類乳突病毒(HPV)疫苗之後不幸喪命。以宗教界為首的某些社會群體本來就對學生接種子宮頸癌疫苗很感冒,他們認為既然病毒透過性行為傳染就不該給未滿十六歲的人注射疫苗。新聞一出,疫苗安全與否受到各方關注,頭條追蹤數日之久,然而事隔十年我在一場科普活動上詢問,請記得此事的聽眾舉手,結果一個也沒有。反觀麻疹、腮腺炎、德國麻疹混合疫苗(即MMR三合一疫苗)導致自閉症一說,最早於一九九八年就曾登上頭條,現場所有人都舉手表示有印象。
同樣是疫苗害命的驚悚新聞,為什麼一則深植人心、另一則卻遭到淡忘?我的答案,亦即本書的主題,就是科學家終於懂得如何發聲。這個轉變的部分原因在於我參與創立的組織──「科學媒體中心」(Science Media Centre, SMC)始於二〇〇二年,推廣科學界以嶄新主動的態度因應新聞頭條。我們的宗旨是「科學家懂媒體,媒體才能懂科學」,改善科學新聞最簡單有效的辦法就是科學家與記者攜手合作,一起努力將報導內容寫正確。
時至今日,科學媒體中心的人才庫已有三千多位頂尖科學家進駐,獲得全英國所有媒體渠道採用,每年舉辦約六十場記者會。我們也運用超過一百個組織團體的小額捐款擴大影響力,觸角遍及全世界,澳洲、加拿大、紐西蘭、德國各自成立了科學媒體中心,美國亦有性質類似的單位。最新生力軍包括臺灣以及面對全非洲大陸的機構,西班牙的新中心預計於二〇二二年初開始營運。
二〇〇九年,第一位記者致電我們想瞭解娜塔莉.莫頓的死因,我立刻聯繫人才庫內所有疫苗專家,請大家針對焦點新聞做出即時回應。從接下來幾小時延續到數日之內,許多專家接受新聞節目訪談,意見得到各大媒體轉述。他們協助製作問答集、事實查核表格與清晰圖片,於是媒體版面上不再只有少女意外暴斃這種嚇人的文字敘述。由於是突發個案,科學家們當然也無法徹底掌握來龍去脈,然而這並不代表不能回應,他們透過堆積如山的資料證明疫苗安全且有效,因此短短幾小時內頭條風向就變了,例如《每日郵報》報導「專家表示癌症疫苗安全無虞」。
過去科學家傾向迴避媒體,喜歡躲在實驗室而非暴露於鎂光燈下。這其實是人之常情。當時尚未強調科學傳播可及性(accessible science communication),也不將其視為公共財,學術界進入公眾討論的誘因少之又少,參與者多半只是推動科學普及,也就是介紹自己的研究領域或科學基本原則,而且人數並不多。不過情況逐漸轉變了,一九八五年皇家學會提出《公眾的科學理解》,又稱為「博瑪報告」(Bodmer Report),呼籲科學家將公眾參與視為自身的社會義務。一九九〇年代末,研究經費分配方式也有所調整,針對媒體工作提供更多誘因,譬如必須將成果與大眾分享才能獲得補助。種種措施發揮作用,科學家開始主動接觸媒體,將研究結果告知可信賴的科學記者。即便如此,科學爭議登上頭版頭條時問題仍在:一旦捲入媒體報導就得與各方運動人士或病友團體交鋒,不習慣大陣仗的研究人員通常無意涉入,許多不正確資訊在媒體狂潮中應運而生,對公眾的科學理解以及公眾政策制定造成莫大衝擊。
然而從HPV疫苗恐慌之中可以看見事情已經出現轉機,面對複雜、聳動、可能損及學術聲望的新聞,科學家不再選擇逃避而是正面迎擊。死亡個案本身固然是悲劇,但他們的參與將報導風向和資訊導回正途,最終促成公眾對疫苗證據更深入的瞭解。
是什麼改變了?雖然很想在此居功,不過若要理解科學界起了什麼變化,首先就要看看科學媒體中心為何存在。
*
千禧年前後登上頭版頭條的科學新聞並不只有MMR三合一疫苗,其他諸如動物研究設施與基因改造食品也招致負面觀感和資訊錯亂。儘管當下仍有少數勇敢科學家願意出面解釋,卻不足以扭轉輿論和政策遭到誤導的趨勢。
這些領域之中,多數科學家主動迴避媒體接觸。他們隱居在大學或研究所,心裡在乎的只有下一次實地實驗,抑或是在同儕審查期刊上發表成果。我訪問過世界一流研究機構內的植物科學家,他們對當年的情況著實不解,只能眼睜睜看著善於操作媒體的環境運動人士偕同各路小報以鋪天蓋地之姿妖魔化基因科技及其前景。結果如何呢?社會大眾、政治人物以至於超級市場在第一粒基改農作物問世之前就咬牙切齒全面抵制。
一九九九年,英國科學界無力回應媒體亂象的問題,得到上議院科學技術特別委員會重視。時任科技部長的森寶利勳爵(Lord Sainsbury)與已故的詹金勳爵(Lord Jenkin)共同推出《科學與社會調查報告》,對公眾的科學理解這個主題貢獻卓著,如今已是科技傳播課程的必讀經典。報告內容反映出上個千禧年末科學與媒體之間關係緊繃:知名科學家感慨媒體報導不受控制、指責記者破壞大眾對科學的信任,但科學記者反唇相譏,認為科學家自恃精英高高在上、每年露臉一次彷彿下詔,然後又會躲回學術舒適圈。英國廣播公司(BBC)科學記者帕拉卜.戈希(Pallab Ghosh)敦促科學家不要只會抱怨遊戲規則,捲起袖子跳進場內才是正解。
公元兩千年發表的《科學與社會調查報告》呼籲投入新資源,訓練並鼓勵科學家與媒體互動,其中一段提到:
英國科學文化需要一次重大革新,與媒體建立開放且正向的溝通管道。為達成此目標需要訓練與資源,更需要組織架構……尷尬與挫折在過程中在所難免,不過若能成功,重燃公眾信心便是最為豐碩的回報。
為了落實這些理念,科學媒體中心誕生了。
*
MMR三合一疫苗與基因改造食品掀起軒然大波的時期,我原本還在英國天主教海外發展處(Press for the Catholic Agency for Overseas Development, CAFOD)當媒體主任。千禧年前夕,我有幸在千禧債務減免運動(Jubilee 2000 Campaign)中擔任領頭羊,活動獲得一時成功,激發大眾與媒體對美好世界的固有追求,造就很多極具意義的重要改變。然而彷彿狂歡結束宿醉酒醒,媒體對開發中國家債務問題的興趣一下子煙消雲散,單純的發展議題越來越難勾起關注。
我的媒體策略也不得不走上偏鋒:讓約克郡水災難民與莫三比克水災難民會面、在唐寧街丟金條抗議國際貨幣基金拒絕出售黃金儲備資助減債計畫,並安排甫入教的國會議員安.維德坎姆(Ann Widdecombe)參觀天主教海外發展處的非洲專案,希望能扭轉她對減債的想法。結果適得其反:她原本就認為減債計畫會淪為非洲貪腐政府中飽私囊的機會,參訪過程反而深化了這種信念,行程結束回國後也在許多廣播或電視訪談表達立場。《每日電訊報》特稿編輯表示他們願意刊一篇來自我方的意見,前提是必須改以鮑勃.格爾多夫(Bob Geldof)或波諾(Bono)之類名人的名義。當下我明白離開的時候到了,我不想停留只有靠腥膻色或知名度才能爭取曝光的工作領域。再看看還有什麼主題能登上頭版,我發現答案是科學。
我表示自己想為科學界經營媒體關係的時候,不少朋友都笑了。以過去成績而言,我在威爾斯語、英語和歷史拿到了A,還有一個新聞學學位。但跟當時大部分人一樣,我很關心圍繞在基因改造食品和MMR三合一疫苗的辯論,而且我非常支持科學。此外,我也想為那些在報導上總是居於劣勢的陣營做點什麼努力。
大約同時,我讀到二〇〇一年一月蘇珊.格林菲爾德(Susan Greenfield)教授接受《金融時報》的專訪,她提到想在皇家研究院(Royal Institute)內成立全新獨立的媒體中心作為科學家與記者之間的橋梁。格林菲爾德教授除了在神經科學與科普方面厥功甚偉,也是皇家研究院首任女性院長。從她願意穿著招牌迷你裙為《Hello!》雜誌擺拍,解釋大腦機制也能講得許多聽眾津津有味,可以想見她對媒體工作有著獨樹一格的見解。森寶利勳爵在報告書中提到新形態媒體中心,詢問是否能以皇家研究院作為據點,格林菲爾德教授欣然接受。
六個月後,我的面試官陣容非常豪華,由八位科學界大人物組成,其中包括已由布萊爾首相授予爵位的格林菲爾德本人、《自然》期刊主編菲利普.坎貝爾(Philip Campbell)博士,以及前自然環境研究委員會主席約翰.克雷布斯(John Krebs)爵士教授。我的資歷其實並不合乎要求,但這也代表我無需對失敗畏首畏尾。而且雖然我不具備她們期待的科學背景,以二〇〇一年的情況而言我不認為有人真的能兼顧媒體處理與硬派科學,也因此我的訴求很明確:我認為科學媒體中心需要一個深度瞭解媒體需求,同時又能協助科學家將話講得簡白易懂的人,學術背景反而並不那麼重要。這場賭局最後是我贏了,不過她們也表明態度,基於這個決定有其風險所以給我的年薪比徵才啟事少了一萬英鎊,這筆錢會拿去多招募一個具博士學位的人。我無所謂,接下來好幾天宣佈新工作的時候,朋友們一臉不可置信。我在科學世界的冒險啟程了。
*
過去二十年間,科學界的文化經歷重大革新,科學家從象牙塔內遙不可及的存在搖身一變成為真正參與國民生活的專家學者,一般認為科學媒體中心既是這股變革的推手,也是其成果。透過本書內容,我記錄這場寧靜革命的進程,揭露過去二十年間最爭議的科學報導背後有何祕辛,並針對科學通訊面對的新威脅提出自身見解。由於阿拉斯泰爾.坎貝爾(Alastair Campbell)和多米尼克.卡明斯(Dominic Cummings)等幾位政治化妝師及特別顧問的爆料,社會大眾對於政壇內幕已經不再陌生;反觀科學雖然深深影響人類生活,尤其大眾仍在摸索新冠疫情後的新生態,我們對於科學新聞卻尚未建立同等意識。作為科學新聞負責人,在第一線見證過科學與媒體交鋒,我希望本書能激起讀者對於當代重要科學議題的興趣,或者幫助大家理解科學與政治、文化、社會整體之間有何複雜交集。
書中收錄的事件對某些年齡段的人或許耳熟能詳。想必還有人記得大衛.納特(David Nutt)教授曾經擔任英國政府的藥物首席顧問,卻在二〇〇九年十月被迫下臺(詳見第五章)。同年僅僅一個月之後,氣候變遷否定團體為證明暖化議題是造假,以駭客手法盜取了學術界的電子郵件並引發全球騷動(詳見第六章)。其他章節涉及的主題層面更廣,例如動物實驗如何從科學界的黑暗小祕密蛻變為大眾接受的醫藥研究環節(詳見第二章),或者原本對「科學怪人食品」之類聳動標題惶恐迴避的基因改造研究者如何轉型,不僅成為新形態媒體投入的主要推手,甚至不惜與查爾斯三世及環境運動人士槓上(詳見第一章)。再來也會提到政府試圖禁止科學家對人類和動物胚胎進行研究,結果引發科學界與病友代表團體史無前例的反撲(詳見第四章),為日後更複雜的倫理議題如人類基因編輯或所謂「三親嬰兒」奠定基調,深切影響了政壇與民間的思考方向。
有兩個篇章不講述特定事件,從更宏觀的角度探討科學傳播與新聞這個主題。第九章提到儘管我在科學媒體中心工作勢必常與媒體搏鬥,結果卻也常為英國的科技、健康和環境記者出頭,因為部分科學家批評媒體做出爛報導時其實根本良莠不分。第十章則談到我個人的擔憂:科學新聞發言人恐將瀕臨絕種,因為主攻研究的大學越來越走向商業化營運,研究通訊或許終將被巨大的行銷部門併吞。
少部分事件未能有個圓滿結局或落入較大主題分類中,甚至未必與科學媒體中心的職務緊密相連,但也不該因此忽略。二〇一五年某次科技新聞記者會上,諾貝爾生物學獎得主蒂姆.亨特(Tim Hunt)爵士的言論涉及性別歧視引起輿論嘩然,當時科學媒體中心沒有機會介入太多,但後來另一次全球重要科學報導上我則有機會提供建議(詳見第八章)。肌痛性腦脊髓炎(myalgic encephalomyelitis, ME)或稱慢性疲勞症候群(chronic fatigue syndrome)恐怕多數讀者並不熟悉,但事件經過呈現出科學家及研究證據持續遭到抨擊時,科學媒體中心能夠做什麼(詳見第三章)。
本書絕大多數內容圍繞一個主題:力爭得來的公開透明值得好好守護。部分事件描述中,讀者會看到我向政府據理力爭,避免獨立科學家承受高層壓力而無法公開發言。這種情況十分普遍,存在於政黨提出的反遊說條款中,也反映在政府通訊官員對獨立科學通訊的過度干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