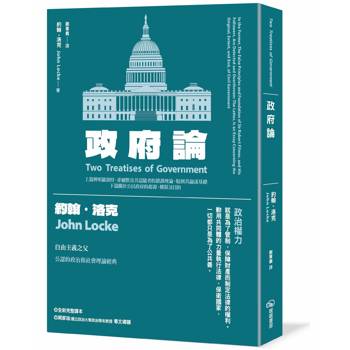導讀:
為不受支配的自由人所寫的宣言
周家瑜(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一、「審慎的洛克」
如果讀者們穿越回到十七世紀下半,閱讀到一本結論是「人民應當奮起反抗君主」的書籍,相信也能真切感受到此書帶來的莫大震撼與爭議性。在一個君主自認為上受上帝唯一真神賜予統治權利,下承祖先們據說六百年統治的漫長歷史形成的君主特權傳統的社會,洛克犀利地主張:君主統治權來自人民同意,人民應有反抗政府之權利。為什麼一個平民選擇投身於這樣充滿風險的政治志業?
一六三二年洛克出生於薩莫賽特郡的威靈頓,一七○四年底於好友馬薩姆的別墅中去世。在後來出版的洛克傳記中,他被稱為「一位多才多藝之士」,洛克不僅在神學與宗教方面有許多獨特見解,也以哲學家身分聞名於世,英國財政革命前後洛克也撰寫數篇經濟論文,甚至也出版過如何教養兒童的教育書籍,然而洛克最為人所知的身分可能是影響後世啟蒙運動與自由主義興起的政治思想家,此處所導讀的《政府論》便是奠定此一聲譽的經典作品。
洛克早年以學者身分在牛津大學基督教會學院(Christ Church)長達十五年,主要的作品環繞著宗教寬容的議題,此時的洛克明顯與後來人們熟知的政治哲學家洛克抱持相當不同的政治態度與原則,此時的作品《政府二論》(Two Tracts of Government)採取相當威權的保守立場,主張在許多事物上,行政長官的權威必須是絕對的,認為在進入政治社會之後,人們須放棄原先的自然自由,絕對地服從行政權力;然而,真正奠定洛克為「自由主義思想家」的成熟時期著作則是本書《政府論兩篇》(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即《政府論》),在其中洛克的政治立場一百八十度地轉變為對有限政府與自然權利的堅定支持,許多研究者相信這與洛克生涯中的贊助者、雇主與貴族庇護人艾希利(Anthony Ashley Cooper)──艾希利勛爵一世(First Lord Ashley),後來的沙夫茲伯里伯爵(First Earl of Shaftesbury)──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後者不僅曾在英國議會中獨握大權,極具政治眼光與才幹,在英國政局最是詭譎多變的時期中先是效忠國王,後來又成了議會派對抗國王的領袖,曾擔任審判了查理二世並將之送上斷頭台的克倫威爾政府的部長,後來又成了克倫威爾的敵人,促成了王室復辟大業。一六六六年洛克因緣際會憑藉醫術結識沙夫茲伯里伯爵之後,因志趣相投很快便投身艾希利家中,成為他的顧問與好友。
這個機緣也讓原本遠離政治的洛克一夕之間踩進了政局的深水區,在一六七九年以沙夫茲伯里伯爵為首的議會派反對查理二世與很可能成為其繼承人的天主教徒詹姆士(後來的詹姆士一世),這場撼動朝局的對立史稱「黜王危機」(The exclusion crisis),一六八四年據傳議會派甚至試圖在查理二世與詹姆士從賽馬會回程途中綁架他們,此一「黑麥房密謀」(Rye House Plt)失敗後,許多議會派成員被捕並處死,洛克流亡荷蘭。事情爆發後著名的輝格黨成員席德尼(Algernon Sidney, 1623-1683)被處絞刑,在他的審判罪名當中有一項就是撰寫具有煽動性的手稿,其中包含對當時著名的君權神授論理論家菲爾默(Robert Filmer)著作《先祖論》(Patriarcha)的批判,後來發表出來即《政府論集》(Discourses on Government)。這個事件為我們解釋了為什麼洛克終身沒有公開承認自己是這本舉足輕重、被認為是自由主義與天賦人權主張之源頭的《政府論》的作者──更精確的說是持續否認──一六八九年洛克仍對友人莫利紐克斯(William Molyneux)否認自己撰寫了《政府論》,即便後者是他畢生最親密的好友之一,因為洛克著名的《政府論》中正是以批判菲爾默為起點,最終推導出人民享有革命與反抗政府的權利。
另一件軼事也可看出《政府論》內容在當時政治氛圍下的敏感度,後世研究者發現在洛克藏書室中此一作品被偽稱為《論法國病》(De Morbo Gallico)──這個法國疾病當時通常指涉梅毒,但也可以理解為暗指法國路易十四統治下達到全盛的專制權力──當代讀者不難從這個謹慎措施中看出這本著作的高度政治危險性。那麼究竟「審慎的洛克」在《政府論》中提出了甚麼犀利論點呢?
二、專制政府的永恆對手
在一六八三年,洛克離開英國流亡荷蘭的前夕,牛津大學震撼於黑麥房密謀事件,召開宗教會議並提出了一份煽動這種陰謀的「天譴教義」(damnable doctrines),於同年七月二十一日發布,正式譴責其中所條列出來的原則,不出意料,洛克《政府論》的手稿中包含了這二十七條原則中的數條諸如「政治權威來自人民」、「君主與臣民之間存在某種契約關係」以及「暴君可以被剝奪統治權利」等,雖然沒有留下紀錄,但有論者相信當時洛克很可能人就在牛津,在各種包含這些原則的書籍被確認為「毒害人心的書籍」之後,被集中一起於牛津博德里安廣場(the Bodleian Quadrangle)上焚燒之際,洛克很可能便在自己基督教會學院的房間裡思考著如何逃離這個逐漸擴大的政治風暴。
儘管對於洛克撰寫《政府論》的時機有所爭論,──劍橋大學出版的《政府論》之編者便認為至少有一部分的《上篇》撰寫的時間點必然早於《下篇》──但是至少就理論內容上,讀者若要把《下篇》論有限政府當成是延續《上篇》反對絕對君主制的延續,也是沒有問題的。洛克在《上篇》與《下篇》所探討處理的都是當時最爭議且政治敏感度極高的主題:《上篇》處理的是統治者政治權力正當性基礎以及聖經文本中對於統治權力的論述,洛克主要目的在於駁斥當時廣泛受到保守派保皇人士與教會歡迎的羅伯特.菲爾默爵士提出的父權論述,菲爾默以聖經文本為主要證據,指出在世界的最初,神聖歷史的開端,上帝便給予世界第一個父親──亞當作為所有人類的先祖──對世界的統治權,可以說除了這個權力源自上帝授予以外,亞當的統治權的正當性基礎首要便是這個做為人類共同先祖、第一個父親的父親身分(Fatherhood);其次,菲爾默也從聖經文本中找出上帝也授予亞當在家庭中統治夏娃的絕對權力,最終推導出人民需絕對服從其當下統治者的絕對主義結論。
當代讀者可能認為這些論點荒誕無稽,根本無需與之爭辯,然而這些在我們的時代看似荒謬不可思議的論述,在洛克的時代則是一個連國王也肯認的看法,詹姆士一世著名地強調:人們應當將他們的君主認知為一個父親,而相對應地,君主作為所有人民的父親應當盡其父親的責任來「關照、撫育與教養臣民的美德」,在討論到臣民是否有可能可以被允許反抗君主?詹姆士一世回答道:「假設父親怒氣沖沖地持著武器追著他的兒子們,難道這就使得他們能夠正當地轉向並攻擊他嗎?或是做出任何反抗而非逃走嗎?」,由此可見此種家父長思維與絕對主義論點實為當時主流觀點。
《下篇》的論證則是從自然狀態與戰爭狀態的區分開始,作為社會契約論思想家的洛克從缺少一個共同的統治權威的前政治(自然)狀態開始,探討人們如何因為生活中的不方便之處,選擇放棄或交託部分自然權利,願意離開一個祥和自由的狀態接受某個權威的管理與統治,訴說這樣一個政治社會的形成過程是要讓人們了解到最初願意服從政府的理由──為了保障生命、自由與個人財產權──這個理由與目的因此便構成了政治權力的限制。確立了政府權力範圍與限制之後,洛克接下來分別討論當時英國立法權與行政權(也有人翻譯為執行權)的範圍與性質,最後特別強調三種權力──即父權、政治權力與專制權力──性質之不同。
整體而言,若要掌握《政府論》的核心關懷,可以說洛克主旨在於對任意權力的批判,任意權力可能以不同形式與面貌出現,有時甚至會以法律偽裝起來使人無法辨認。洛克提出的對不同權力的剖析便是要警示人民任意權力之存在,例如任意權力可以以父親權力的形態出現,甚至以聖經論述為依據──「根據父親的自然權利,亞當擁有絕對、無限的權力來支配所有後裔[…]他所有後裔就絕對都是他的臣民[…]都是他的奴隸」(《政府論上篇》六十九節)──有時也會以行政權力的面貌出現──「同樣的,當行政機構或立法機構掌握權力之後,要是他們企圖開始奴役人民或摧殘人民,人民和立法機構之間[…]因為統治者在這類的嘗試中所行使的,其實是人民從未交到他們手上的權力」(《政府論下篇》一六八節)。如果這些看似太抽象與遙遠,那麼借用當代政治理論家佩蒂特(Philip Petit)的描述,洛克所描述的任意權力之後果便是使人民「受他人支配之苦」,這種被支配的不幸就是「妻子發現丈夫可以隨心所欲地虐待自己,卻沒有辦法擺脫他;雇員受到程度不一的不公平待遇,卻不敢向雇主提出任何抗議;債務人不得不委曲求全地博得債權人或銀行要員的歡心,以免陷入絕對的貧困和破產狀態;領取福利救濟的人不得不忍受辦事人員的百般刁難,畢竟這些人掌握著決定是否為他們的孩子發放食品優惠券的權力」。在任意權力的支配下,人們只有屈從與受奴役的可能,洛克藉由《政府論》中各種權力的剖析,不僅要警示人民任意權力之危害,更呼籲人們起身捍衛自己「自由人」的身分!
三、洛克論財產權
《政府論》的當代重要性還不僅如此,書中對於財產權利的論證以及對於當時美洲殖民地的許多描述,都成了後續批判資本主義與殖民主義的重要資源。洛克在書中提出的關於財產權利的論述在一九七○年代成為馬克思主義學者們的關注焦點。洛克對於人們如何藉助自身能力進行勞動,開發與利用外在自然界並將之歸為己用的過程做了詳細的描述,洛克的論述解決了長期以來許多他同時代之人思考的問題:倘若聖經上告訴我們,「上帝把土地賜給世人,由天下所有人共用」,那麼如何去解釋世界上各種由私人獨占且排除他人使用資格的私有財產權利呢?這絕非某種理論上空中樓閣的抽象討論,洛克在《下篇》中提出關於土地佔有、貨幣的出現與財產權的建立等深入分析,實際上反映著洛克對於當時逐漸興起的商業社會的深刻思考,在必須高度依賴海外貿易的英國社會之中,人們如何看待海外貿易帶來的利潤與投機風氣?英國本身自然資源不足以自給自足,要如何倚賴國際貿易維繫經濟成長,同時又能避免奢侈浪費之習氣?洛克在《政府論下篇》中一一剖析人與自然資源的關係,貨幣的出現與人類勞動如何創造價值的過程,可以說先於德國哲學家馬克思一百五十年,洛克便已經提出某種勞動價值論。如果在當代社會中,資本主義自由市場下的貧富差距與社會不平等問題是你╱妳關切的政治經濟現實,那麼洛克提出的財產權理論與許多後續的討論與爭議便是很好的理論資源與線索。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洛克的經濟論述與分析也與其個人政治事業的起伏緊密相關,他曾出任貿易與國外墾殖事務委員會,在該委員會中擔任重要職務數年,個人也投資殖民地事業,據說收益相當不錯,換句話說洛克於公於私都直接涉入英國對外殖民事業,也因此對於國際政治、海外貿易與殖民地治理都有第一手的資料與觀察。這並不是要說洛克必然為殖民主義辯護,而是要指出:洛克並不是象牙塔裡的學者,《政府論》也絕非不切實際的理論空談,相反地,可以說《政府論》裡的每字每句都源自洛克所面對的時代困境與政治危機,《政府論》實際上是洛克採取的「政治行動」,藉此洛克積極地介入與掌握當時的政治現實。
四、結語
洛克的《政府論》處理了政治權力的性質、探討何謂正當的政治權威,論證政府的目的在於保障生命、自由與財產權。這些論述在今天可能是讀者耳熟能詳的口號,然而在洛克的同時代人眼中,這些論點則是面對冷酷政治現實與任意權力的危險理論武器。筆者撰寫此文的當下正逢現實政治中憲政體制改革爭議、行政權與立法權形成僵局,朝野爭執不休之際,相信此時閱讀《政府論》必然能為讀者們帶來更豐富的政治思考角度與視野。
原文版本與編輯體例說明:
本書實際首次出版時間是一六八九年十二月,但按當時印刷習慣標示為一六九○年。且因政治敏感問題,採用匿名的方式出版,僅管許多人都知曉洛克是作者,但他直至臨死前才在遺囑中正式承認。
初版內容有許多印刷上的錯誤,於是洛克分別在一六九四年的第二版、一六九八年的第三版都做了部分修正。但他仍不滿意,於是在第三版印刷的書頁上,直接以手寫方式在頁邊、行間、扉頁等空白處持續進行修改,但洛克並未看到第四版出版,就於一七○四年過世。修正稿交給了友人皮埃爾.科斯特(Pierre Coste),於一七一三年才出版第四版。一七二七年的第五版是重印第四版,有少許的編輯說明。但由於本書不斷重印,市面上的版本相當紊亂。直到一七六四年托馬斯.霍利斯(Thomas Hollis)取得科斯特的原始稿件,經過編輯校對後,交由劍橋大學基督學院出版的第六版,才有一個比較接近洛克希望看到後世流傳的版本。(詳盡的版本和細節說明,請參考Peter Laslett, "introduction",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1960)。
由於過去版本眾多之故,至今重新出版的內容細節也不盡相同,存在許多差異。故本譯稿的編輯校對,最終以一七六四年托馬斯.霍利斯的第六版為準,不同版本的重大文字變更之處,則盡量以編註加以說明。洛克原著中的重點字、引文,以及人名地名皆以斜體字標示,中文版則依本地慣例,重點字以粗體標示、引文前後以引號框起,人名地名則不另作標示。尤其是重點字的標示,第二講的前三版相當少,大多是第六版增添的,包括第一講也有添加,本譯本皆依第六版為準。至於譯文中的雙引號『』,則是為方便理解譯文所加,特此說明。
下篇 探討公民政府真正的起源、權限及目的
第一章 引論
1. 上篇已經表明:
第一,亞當並沒有如同某些人的宣稱,憑著父威的自然權利或上帝的確實授予而享有統治其子女的權威,或支配世界的權力。
第二,就算亞當擁有這種權力,他的繼承人也無權擁有。
第三,就算亞當的繼承人擁有這種權力,由於缺乏能夠在任何情況下都足以決定出合法繼承人的自然法,或上帝的實定法,因此無法確實決定繼承權及統治權的歸屬。
第四,即使有確定繼承人的辦法,然而亞當嫡系後裔的資訊早已無從查考,因此在人類的各家各族當中,任何人都不會比別人更有理由自稱為亞當嫡系,從而享有繼承的權利。
我認為,以上這些前提都已經交代清楚了,所以就算把亞當的私有支配權和父權當成是一切權力的根源,當今世上的任何統治者都無法藉由這種說法獲益,或是從中得出一絲一毫的權威。因此,任何人只要無法提出正當的理由接受以下這種想法――世上所有政府都不過是強權暴力的產物,共同生活的人類所依靠的法則沒有別的,正是那野獸般的弱肉強食,從而奠定了無窮無盡的混亂、災禍、騷擾、暴動、叛變(這全是那種假設的支持者大力聲討的現象)――那他就必須在羅勃特.菲爾默爵士的教誨之外另尋他路,找出另一種說法解釋政府的產生、政治權力的起源,並找出另一套能夠指定、指明掌權者人選的辦法。
2.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我就對『何謂政治權力?』提出自己的看法,我想這不至於有什麼不妥。我認為,行政官員統治臣民的權力有別於父親之於子女、主人之於奴僕、丈夫之於妻子、領主之於奴隸之類的權力。由於這些不同的權力有時是集於一人之手,如果我們從各種不同的人際關係進行探討的話,將有助於我們一一區別各種權力,說明一個國家的統治者、一個家庭的父親、一艘船的船長所具有的權力有何差別。
3. 因此,我認為政治權力就是為了管制、保障財產而制定法律的權利,用來判處死刑及其他比較輕微的處分;同時也是動用共同體的力量來執行法律,用來保衛國家、抵禦外侮,一切都只是為了公共善。
為不受支配的自由人所寫的宣言
周家瑜(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一、「審慎的洛克」
如果讀者們穿越回到十七世紀下半,閱讀到一本結論是「人民應當奮起反抗君主」的書籍,相信也能真切感受到此書帶來的莫大震撼與爭議性。在一個君主自認為上受上帝唯一真神賜予統治權利,下承祖先們據說六百年統治的漫長歷史形成的君主特權傳統的社會,洛克犀利地主張:君主統治權來自人民同意,人民應有反抗政府之權利。為什麼一個平民選擇投身於這樣充滿風險的政治志業?
一六三二年洛克出生於薩莫賽特郡的威靈頓,一七○四年底於好友馬薩姆的別墅中去世。在後來出版的洛克傳記中,他被稱為「一位多才多藝之士」,洛克不僅在神學與宗教方面有許多獨特見解,也以哲學家身分聞名於世,英國財政革命前後洛克也撰寫數篇經濟論文,甚至也出版過如何教養兒童的教育書籍,然而洛克最為人所知的身分可能是影響後世啟蒙運動與自由主義興起的政治思想家,此處所導讀的《政府論》便是奠定此一聲譽的經典作品。
洛克早年以學者身分在牛津大學基督教會學院(Christ Church)長達十五年,主要的作品環繞著宗教寬容的議題,此時的洛克明顯與後來人們熟知的政治哲學家洛克抱持相當不同的政治態度與原則,此時的作品《政府二論》(Two Tracts of Government)採取相當威權的保守立場,主張在許多事物上,行政長官的權威必須是絕對的,認為在進入政治社會之後,人們須放棄原先的自然自由,絕對地服從行政權力;然而,真正奠定洛克為「自由主義思想家」的成熟時期著作則是本書《政府論兩篇》(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即《政府論》),在其中洛克的政治立場一百八十度地轉變為對有限政府與自然權利的堅定支持,許多研究者相信這與洛克生涯中的贊助者、雇主與貴族庇護人艾希利(Anthony Ashley Cooper)──艾希利勛爵一世(First Lord Ashley),後來的沙夫茲伯里伯爵(First Earl of Shaftesbury)──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後者不僅曾在英國議會中獨握大權,極具政治眼光與才幹,在英國政局最是詭譎多變的時期中先是效忠國王,後來又成了議會派對抗國王的領袖,曾擔任審判了查理二世並將之送上斷頭台的克倫威爾政府的部長,後來又成了克倫威爾的敵人,促成了王室復辟大業。一六六六年洛克因緣際會憑藉醫術結識沙夫茲伯里伯爵之後,因志趣相投很快便投身艾希利家中,成為他的顧問與好友。
這個機緣也讓原本遠離政治的洛克一夕之間踩進了政局的深水區,在一六七九年以沙夫茲伯里伯爵為首的議會派反對查理二世與很可能成為其繼承人的天主教徒詹姆士(後來的詹姆士一世),這場撼動朝局的對立史稱「黜王危機」(The exclusion crisis),一六八四年據傳議會派甚至試圖在查理二世與詹姆士從賽馬會回程途中綁架他們,此一「黑麥房密謀」(Rye House Plt)失敗後,許多議會派成員被捕並處死,洛克流亡荷蘭。事情爆發後著名的輝格黨成員席德尼(Algernon Sidney, 1623-1683)被處絞刑,在他的審判罪名當中有一項就是撰寫具有煽動性的手稿,其中包含對當時著名的君權神授論理論家菲爾默(Robert Filmer)著作《先祖論》(Patriarcha)的批判,後來發表出來即《政府論集》(Discourses on Government)。這個事件為我們解釋了為什麼洛克終身沒有公開承認自己是這本舉足輕重、被認為是自由主義與天賦人權主張之源頭的《政府論》的作者──更精確的說是持續否認──一六八九年洛克仍對友人莫利紐克斯(William Molyneux)否認自己撰寫了《政府論》,即便後者是他畢生最親密的好友之一,因為洛克著名的《政府論》中正是以批判菲爾默為起點,最終推導出人民享有革命與反抗政府的權利。
另一件軼事也可看出《政府論》內容在當時政治氛圍下的敏感度,後世研究者發現在洛克藏書室中此一作品被偽稱為《論法國病》(De Morbo Gallico)──這個法國疾病當時通常指涉梅毒,但也可以理解為暗指法國路易十四統治下達到全盛的專制權力──當代讀者不難從這個謹慎措施中看出這本著作的高度政治危險性。那麼究竟「審慎的洛克」在《政府論》中提出了甚麼犀利論點呢?
二、專制政府的永恆對手
在一六八三年,洛克離開英國流亡荷蘭的前夕,牛津大學震撼於黑麥房密謀事件,召開宗教會議並提出了一份煽動這種陰謀的「天譴教義」(damnable doctrines),於同年七月二十一日發布,正式譴責其中所條列出來的原則,不出意料,洛克《政府論》的手稿中包含了這二十七條原則中的數條諸如「政治權威來自人民」、「君主與臣民之間存在某種契約關係」以及「暴君可以被剝奪統治權利」等,雖然沒有留下紀錄,但有論者相信當時洛克很可能人就在牛津,在各種包含這些原則的書籍被確認為「毒害人心的書籍」之後,被集中一起於牛津博德里安廣場(the Bodleian Quadrangle)上焚燒之際,洛克很可能便在自己基督教會學院的房間裡思考著如何逃離這個逐漸擴大的政治風暴。
儘管對於洛克撰寫《政府論》的時機有所爭論,──劍橋大學出版的《政府論》之編者便認為至少有一部分的《上篇》撰寫的時間點必然早於《下篇》──但是至少就理論內容上,讀者若要把《下篇》論有限政府當成是延續《上篇》反對絕對君主制的延續,也是沒有問題的。洛克在《上篇》與《下篇》所探討處理的都是當時最爭議且政治敏感度極高的主題:《上篇》處理的是統治者政治權力正當性基礎以及聖經文本中對於統治權力的論述,洛克主要目的在於駁斥當時廣泛受到保守派保皇人士與教會歡迎的羅伯特.菲爾默爵士提出的父權論述,菲爾默以聖經文本為主要證據,指出在世界的最初,神聖歷史的開端,上帝便給予世界第一個父親──亞當作為所有人類的先祖──對世界的統治權,可以說除了這個權力源自上帝授予以外,亞當的統治權的正當性基礎首要便是這個做為人類共同先祖、第一個父親的父親身分(Fatherhood);其次,菲爾默也從聖經文本中找出上帝也授予亞當在家庭中統治夏娃的絕對權力,最終推導出人民需絕對服從其當下統治者的絕對主義結論。
當代讀者可能認為這些論點荒誕無稽,根本無需與之爭辯,然而這些在我們的時代看似荒謬不可思議的論述,在洛克的時代則是一個連國王也肯認的看法,詹姆士一世著名地強調:人們應當將他們的君主認知為一個父親,而相對應地,君主作為所有人民的父親應當盡其父親的責任來「關照、撫育與教養臣民的美德」,在討論到臣民是否有可能可以被允許反抗君主?詹姆士一世回答道:「假設父親怒氣沖沖地持著武器追著他的兒子們,難道這就使得他們能夠正當地轉向並攻擊他嗎?或是做出任何反抗而非逃走嗎?」,由此可見此種家父長思維與絕對主義論點實為當時主流觀點。
《下篇》的論證則是從自然狀態與戰爭狀態的區分開始,作為社會契約論思想家的洛克從缺少一個共同的統治權威的前政治(自然)狀態開始,探討人們如何因為生活中的不方便之處,選擇放棄或交託部分自然權利,願意離開一個祥和自由的狀態接受某個權威的管理與統治,訴說這樣一個政治社會的形成過程是要讓人們了解到最初願意服從政府的理由──為了保障生命、自由與個人財產權──這個理由與目的因此便構成了政治權力的限制。確立了政府權力範圍與限制之後,洛克接下來分別討論當時英國立法權與行政權(也有人翻譯為執行權)的範圍與性質,最後特別強調三種權力──即父權、政治權力與專制權力──性質之不同。
整體而言,若要掌握《政府論》的核心關懷,可以說洛克主旨在於對任意權力的批判,任意權力可能以不同形式與面貌出現,有時甚至會以法律偽裝起來使人無法辨認。洛克提出的對不同權力的剖析便是要警示人民任意權力之存在,例如任意權力可以以父親權力的形態出現,甚至以聖經論述為依據──「根據父親的自然權利,亞當擁有絕對、無限的權力來支配所有後裔[…]他所有後裔就絕對都是他的臣民[…]都是他的奴隸」(《政府論上篇》六十九節)──有時也會以行政權力的面貌出現──「同樣的,當行政機構或立法機構掌握權力之後,要是他們企圖開始奴役人民或摧殘人民,人民和立法機構之間[…]因為統治者在這類的嘗試中所行使的,其實是人民從未交到他們手上的權力」(《政府論下篇》一六八節)。如果這些看似太抽象與遙遠,那麼借用當代政治理論家佩蒂特(Philip Petit)的描述,洛克所描述的任意權力之後果便是使人民「受他人支配之苦」,這種被支配的不幸就是「妻子發現丈夫可以隨心所欲地虐待自己,卻沒有辦法擺脫他;雇員受到程度不一的不公平待遇,卻不敢向雇主提出任何抗議;債務人不得不委曲求全地博得債權人或銀行要員的歡心,以免陷入絕對的貧困和破產狀態;領取福利救濟的人不得不忍受辦事人員的百般刁難,畢竟這些人掌握著決定是否為他們的孩子發放食品優惠券的權力」。在任意權力的支配下,人們只有屈從與受奴役的可能,洛克藉由《政府論》中各種權力的剖析,不僅要警示人民任意權力之危害,更呼籲人們起身捍衛自己「自由人」的身分!
三、洛克論財產權
《政府論》的當代重要性還不僅如此,書中對於財產權利的論證以及對於當時美洲殖民地的許多描述,都成了後續批判資本主義與殖民主義的重要資源。洛克在書中提出的關於財產權利的論述在一九七○年代成為馬克思主義學者們的關注焦點。洛克對於人們如何藉助自身能力進行勞動,開發與利用外在自然界並將之歸為己用的過程做了詳細的描述,洛克的論述解決了長期以來許多他同時代之人思考的問題:倘若聖經上告訴我們,「上帝把土地賜給世人,由天下所有人共用」,那麼如何去解釋世界上各種由私人獨占且排除他人使用資格的私有財產權利呢?這絕非某種理論上空中樓閣的抽象討論,洛克在《下篇》中提出關於土地佔有、貨幣的出現與財產權的建立等深入分析,實際上反映著洛克對於當時逐漸興起的商業社會的深刻思考,在必須高度依賴海外貿易的英國社會之中,人們如何看待海外貿易帶來的利潤與投機風氣?英國本身自然資源不足以自給自足,要如何倚賴國際貿易維繫經濟成長,同時又能避免奢侈浪費之習氣?洛克在《政府論下篇》中一一剖析人與自然資源的關係,貨幣的出現與人類勞動如何創造價值的過程,可以說先於德國哲學家馬克思一百五十年,洛克便已經提出某種勞動價值論。如果在當代社會中,資本主義自由市場下的貧富差距與社會不平等問題是你╱妳關切的政治經濟現實,那麼洛克提出的財產權理論與許多後續的討論與爭議便是很好的理論資源與線索。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洛克的經濟論述與分析也與其個人政治事業的起伏緊密相關,他曾出任貿易與國外墾殖事務委員會,在該委員會中擔任重要職務數年,個人也投資殖民地事業,據說收益相當不錯,換句話說洛克於公於私都直接涉入英國對外殖民事業,也因此對於國際政治、海外貿易與殖民地治理都有第一手的資料與觀察。這並不是要說洛克必然為殖民主義辯護,而是要指出:洛克並不是象牙塔裡的學者,《政府論》也絕非不切實際的理論空談,相反地,可以說《政府論》裡的每字每句都源自洛克所面對的時代困境與政治危機,《政府論》實際上是洛克採取的「政治行動」,藉此洛克積極地介入與掌握當時的政治現實。
四、結語
洛克的《政府論》處理了政治權力的性質、探討何謂正當的政治權威,論證政府的目的在於保障生命、自由與財產權。這些論述在今天可能是讀者耳熟能詳的口號,然而在洛克的同時代人眼中,這些論點則是面對冷酷政治現實與任意權力的危險理論武器。筆者撰寫此文的當下正逢現實政治中憲政體制改革爭議、行政權與立法權形成僵局,朝野爭執不休之際,相信此時閱讀《政府論》必然能為讀者們帶來更豐富的政治思考角度與視野。
原文版本與編輯體例說明:
本書實際首次出版時間是一六八九年十二月,但按當時印刷習慣標示為一六九○年。且因政治敏感問題,採用匿名的方式出版,僅管許多人都知曉洛克是作者,但他直至臨死前才在遺囑中正式承認。
初版內容有許多印刷上的錯誤,於是洛克分別在一六九四年的第二版、一六九八年的第三版都做了部分修正。但他仍不滿意,於是在第三版印刷的書頁上,直接以手寫方式在頁邊、行間、扉頁等空白處持續進行修改,但洛克並未看到第四版出版,就於一七○四年過世。修正稿交給了友人皮埃爾.科斯特(Pierre Coste),於一七一三年才出版第四版。一七二七年的第五版是重印第四版,有少許的編輯說明。但由於本書不斷重印,市面上的版本相當紊亂。直到一七六四年托馬斯.霍利斯(Thomas Hollis)取得科斯特的原始稿件,經過編輯校對後,交由劍橋大學基督學院出版的第六版,才有一個比較接近洛克希望看到後世流傳的版本。(詳盡的版本和細節說明,請參考Peter Laslett, "introduction",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1960)。
由於過去版本眾多之故,至今重新出版的內容細節也不盡相同,存在許多差異。故本譯稿的編輯校對,最終以一七六四年托馬斯.霍利斯的第六版為準,不同版本的重大文字變更之處,則盡量以編註加以說明。洛克原著中的重點字、引文,以及人名地名皆以斜體字標示,中文版則依本地慣例,重點字以粗體標示、引文前後以引號框起,人名地名則不另作標示。尤其是重點字的標示,第二講的前三版相當少,大多是第六版增添的,包括第一講也有添加,本譯本皆依第六版為準。至於譯文中的雙引號『』,則是為方便理解譯文所加,特此說明。
下篇 探討公民政府真正的起源、權限及目的
第一章 引論
1. 上篇已經表明:
第一,亞當並沒有如同某些人的宣稱,憑著父威的自然權利或上帝的確實授予而享有統治其子女的權威,或支配世界的權力。
第二,就算亞當擁有這種權力,他的繼承人也無權擁有。
第三,就算亞當的繼承人擁有這種權力,由於缺乏能夠在任何情況下都足以決定出合法繼承人的自然法,或上帝的實定法,因此無法確實決定繼承權及統治權的歸屬。
第四,即使有確定繼承人的辦法,然而亞當嫡系後裔的資訊早已無從查考,因此在人類的各家各族當中,任何人都不會比別人更有理由自稱為亞當嫡系,從而享有繼承的權利。
我認為,以上這些前提都已經交代清楚了,所以就算把亞當的私有支配權和父權當成是一切權力的根源,當今世上的任何統治者都無法藉由這種說法獲益,或是從中得出一絲一毫的權威。因此,任何人只要無法提出正當的理由接受以下這種想法――世上所有政府都不過是強權暴力的產物,共同生活的人類所依靠的法則沒有別的,正是那野獸般的弱肉強食,從而奠定了無窮無盡的混亂、災禍、騷擾、暴動、叛變(這全是那種假設的支持者大力聲討的現象)――那他就必須在羅勃特.菲爾默爵士的教誨之外另尋他路,找出另一種說法解釋政府的產生、政治權力的起源,並找出另一套能夠指定、指明掌權者人選的辦法。
2.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我就對『何謂政治權力?』提出自己的看法,我想這不至於有什麼不妥。我認為,行政官員統治臣民的權力有別於父親之於子女、主人之於奴僕、丈夫之於妻子、領主之於奴隸之類的權力。由於這些不同的權力有時是集於一人之手,如果我們從各種不同的人際關係進行探討的話,將有助於我們一一區別各種權力,說明一個國家的統治者、一個家庭的父親、一艘船的船長所具有的權力有何差別。
3. 因此,我認為政治權力就是為了管制、保障財產而制定法律的權利,用來判處死刑及其他比較輕微的處分;同時也是動用共同體的力量來執行法律,用來保衛國家、抵禦外侮,一切都只是為了公共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