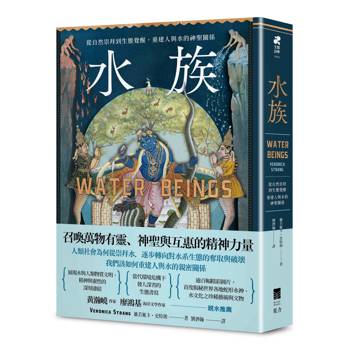第十二章 力挽狂瀾
43 體驗日常現象,就能喚起對水的神奇感
並非所有的「水崇拜」都刻意產生精神取向的內容;美學和感官接觸也會引起情緒反應並喚起神奇感。「神奇感」是一個有用的概念:在歷史上多半與宗教體驗聯繫在一起,因為宗教儀式的目標當然就是引起驚異與敬畏,不過這種經驗絕不局限於宗教脈絡。
透過藝術很容易體驗到一種神奇的感覺,其中景觀設計、繪畫、詩歌和其他媒介都讚頌了水的多重視覺和象徵屬性;在致力於探索「自然奇觀」的科學記錄片——或者電影——和文學中找到這種神奇感。這些媒介鼓吹要尊重所有生物、植物和物質世界的美麗和複雜,而不預設它們是神聖計劃的產物。正如在田野調查中訪問到的許多受訪者跟我說的,我們也可以透過體驗日常現象喚起對水的驚奇和喜悅的感受:在湖畔或河邊散步、在海裡游泳、有機會在本地公園的池塘邊靜靜地坐著。無論在哪裡遇到水,都會吸引感官,迷惑眼睛,釋放心靈。
這一點很重要,其中有幾個原因。世俗社會中的許多人對重新接納宗教信仰的想法猶豫不決,即使這些信仰更傾向於非人類力量,但是他們對將於將自然本身視為「神奇」的評價持開放態度。非人類世界引起神奇感與欣賞的能力,與人類對於保護其他生物的關注程度之間,也存在著有據可查的關係。
這個過程的關鍵有一部分涉及人類與地方及其非人類居民建立聯繫和共有認同的能力,以及表達「愛生命」的能力;「愛生命」(biophilia)一詞源自亞里斯多德關於「philia」(友誼)作為表達互惠關係的討論。博物學家艾德華‧威爾遜(Edward Wilson) 將其定義為一種與其他生命形式有聯繫的內在衝動;理查‧洛夫(Richard Louv)則認為,與其他物種疏遠會導致情感上的缺陷。愛生命自然就包括了「愛水」,因為水是生命的本質。黛博拉‧伯德‧羅斯(Deborah Bird Rose)觀察到澳洲原住民與水的關係提供了一個理想的哲學模型:
原住民的水哲學對水提供了一個廣泛支持生命的定義……第一步是將水置於愛生命的範圍內,因為熱愛生命的人顯然也必須熱愛水。也許非原住民的澳洲人也終於到了該發展水哲學的時候,這種哲學也將在互聯互通的模式中維持他們的生命。
44 承認「非人類」和生態系統具有人格
與非人類世界連結的渴望也反映了人類的認知過程,將思想向外延伸,並將人格特質編碼到其他生物與物質環境中。將意識置於自我之外的傾向意味著,雖然理性可能占主導地位,但是始終都有一片沃土,讓我們想像一個充滿活力且有感知力的非人類領域。當然,將他者擬人化對情感連結也有極大的助力,利用蛇形水族及其持久的能力來具體而微地展現水的屬性和力量。
對於「他者」的同理心需要一些共同認同,而關於非人類物種是否應該被視為人類,也有激烈的爭論。有關人與動物關係的人類學著作已經闡明,人們如何欣然地將家養動物(尤其是寵物)視為人和「親屬」。最近,多物種民族誌學者、哲學家和藝術家更進一步拒絕以人類為中心的觀點,在非人類生命世界的想像中向前躍進了一大步。洛夫也注意到連結與關懷之間的關係,認為「共同的跨物種凝視」既可以改變我們的生活,也可以拯救他們的生命。
這多半取決於人類和非人類之間的明確區別到什麼樣的程度。就像尤皮克人認為所有生物都是人一樣,在許多文化脈絡中都沒有這樣的區分。例如,人類學家喬安娜‧奧弗林(Joanna Overing)描述了南美洲的皮亞羅(Piaroa)部落如何將叢林動物視為自己的「同類」,並將食用動物視為同類相殘的一種食人形式,需要透過薩滿儀式來將它們的肉體轉化為植物性的物質。許多非西方文化在幾千年來就一直相信圖騰生物和有感知力的地景,完全可以接受將人格擴展到其他生物、地景和水景。
對某些社會來說,尤其是宗教發展軌跡在人類與他者之間建立了壁壘分明的界線並嚴格防守的社會,這是一個更棘手的問題。西元1990年代的「大猿計畫」(Great Ape Project)就引發了相當大的界線焦慮,哲學家彼得‧辛格(Peter Singer)和寶拉‧卡瓦列理(Paola Cavalieri)領導了反對靈長類動物科學實驗的抗議活動,認為「非人類的人科動物」應該享有生命權和免受酷刑的自由,並且應被視為有感知力的「人」。從那時起,動物權利運動及保護其他物種權利的努力就進一步挑戰人類例外論。關於人類與非人類關係的道德問題在邏輯上更進一步延伸到生命生態體系的管理,更有必要質疑社會是否有權剝削這些生態體系,損害它們的福祉。
此類爭論的核心始終都是水,也不斷湧現相關文獻,聚焦於人類與水之間的倫理關係。採礦業對國家經濟的巨大貢獻是否成為其污染生態體系的合理的藉口?為了支持工業化農業而過度抽取河流及含水層的地下水,是否一定凌駕非人類物種的需求及其棲地的健康?是否應該興建更多巨型水壩來滿足對廉價水力發電的渴望?無論目標多麼遠大,任何人——個人、政府或私人公司——有權利改變水流方向以滿足特定需求和利益,甚至不惜犧牲人類和非人類他者嗎?剝削行為往往是因為想要尋求短期解決方案來紓解社會和經濟壓力,然而,對此類措施的依賴卻導致了生態危機,很可能使這些措施徒勞無功。指定非人類物種為擁有正式合法權利的人則另闢蹊徑,可能將他們的需求和利益也納入決策過程的考量。
在紐西蘭就有一個現成的例子。當地的毛利蛇形水族塔尼瓦在關於將人格延伸到旺格努伊河的法律論辯中發揮了核心作用;除了將這條河定義為神聖的(taonga)河流之外,當地部落(iwi)還使用描術親屬關係的術語稱呼它為「祖先河」(Tupuna Awa),並將其定義為「重要的部落祖先」。泉源(puna wai)在「whānau」(大親屬群體)中也同樣有這種不可或缺的作用:「從whānau的puna wai湧出來的水,被視為在whānau中的taonga(神聖或特殊的東西),因為它承載著這個whānau的 Mauri(生命力)……每個whānau的精神本質都是河流的一部分……從這個意義上說,這條河不僅僅是一條 taonga,而是人。」
身為河流精神生命的後裔,毛利部落責任為後代子孫保護這位「活著的祖先」。西元2017年,這種祖先聯繫為法律訴訟案的勝訴奠定了基礎,確立了旺格努伊河作為「生命實體」的人格,並具有相應的權利。根據一個賦予圖霍伊(Ngäi Tuhoe)部落家園森林法律身份和權利的早期案例,這個判決定義「從山到海的河流、其支流及其所有物質與抽象元素為一個不可分割且有生命的整體……『靈魂河』(Te Awa Tupua) 是一個法人,擁有法人的所有的權利、權力、義務和責任」。官方和旺格努伊部落的指定代表有責任在法律體系內為河流的管理和使用「代言」。該法案創建了一個新角色「To Pou Tupua」,他們「是『靈魂河』的人形化形象,並以『靈魂河』 的名義行事」。
毛利族評論家表示,希望這項成功的行動能為其他地方的類似改革提供一個模式,而其他地方當然也曾經努力地確認河流作為人或有生命實體的權利。
西元2017年,印度的恆河和亞穆納河都獲得北阿坎德邦(Uttarakhand)高等法院認定為有生命的實體/法人,不過最高法院暫緩了這項裁決。西元2016年,哥倫比亞憲法法院承認阿特拉托河(Atrato River)為法律主體。
在澳大利亞,金伯利(Kimberley)地區的原住民群體呼籲現代河川管理必須尊重神聖水族所體現的「第一法則」。馬圖瓦拉—菲茨羅伊河議會(Martuwarra Fitzroy River Council)將古老的蛇形生物「Yoongoorrookoo」描述成有生命的祖先,並認定他是公共對話的參與者和共同作者。原住民長老喬‧南甘(Joe Nangan)描述了彩虹蛇如何維護法律並體現河流的人格:
在尼基納族(Nyikina)原住民的源始(Bookarrarra)故事中,Yoongorrookoo 是一條強大而神聖的彩虹蛇,能賜予人類雨水和生命……他可以非常仁慈,為尼基納人——他所選擇的人民——帶來溫和的雨水,填滿水坑。但是當他生氣時,他能引起旋風、洪水,甚至龍捲風。原住民在靠近水坑時總是非常謹慎,生怕冒犯神聖而強大的彩虹蛇 Yoongoorrookoo。
在厄瓜多和玻利維亞,原住民群體說服政府在憲法中賦予地球母親帕查媽媽更廣泛的權利,其立論基礎就是「buen vivir」(美好生活/活得美好)這個已經貫穿整個拉丁美洲論述的廣泛願景。「buen vivir」借鑒原住民世界觀,批判了永續發展的主流觀念,並提倡一個另類的未來,以人類和非人類之間集體且不可分割的福祉為基礎。
許多原住民和環保運動人士認為,承認非人類和生態體系為人類,將促進包容性思維,從而驅動實踐變革。然而,除了激怒保守的宗教團體外,對於「宗教」努力地重新魅惑非人類世界和重新引入與科學思維不一致的萬物有靈論,也引起了一些世俗的不安。
43 體驗日常現象,就能喚起對水的神奇感
並非所有的「水崇拜」都刻意產生精神取向的內容;美學和感官接觸也會引起情緒反應並喚起神奇感。「神奇感」是一個有用的概念:在歷史上多半與宗教體驗聯繫在一起,因為宗教儀式的目標當然就是引起驚異與敬畏,不過這種經驗絕不局限於宗教脈絡。
透過藝術很容易體驗到一種神奇的感覺,其中景觀設計、繪畫、詩歌和其他媒介都讚頌了水的多重視覺和象徵屬性;在致力於探索「自然奇觀」的科學記錄片——或者電影——和文學中找到這種神奇感。這些媒介鼓吹要尊重所有生物、植物和物質世界的美麗和複雜,而不預設它們是神聖計劃的產物。正如在田野調查中訪問到的許多受訪者跟我說的,我們也可以透過體驗日常現象喚起對水的驚奇和喜悅的感受:在湖畔或河邊散步、在海裡游泳、有機會在本地公園的池塘邊靜靜地坐著。無論在哪裡遇到水,都會吸引感官,迷惑眼睛,釋放心靈。
這一點很重要,其中有幾個原因。世俗社會中的許多人對重新接納宗教信仰的想法猶豫不決,即使這些信仰更傾向於非人類力量,但是他們對將於將自然本身視為「神奇」的評價持開放態度。非人類世界引起神奇感與欣賞的能力,與人類對於保護其他生物的關注程度之間,也存在著有據可查的關係。
這個過程的關鍵有一部分涉及人類與地方及其非人類居民建立聯繫和共有認同的能力,以及表達「愛生命」的能力;「愛生命」(biophilia)一詞源自亞里斯多德關於「philia」(友誼)作為表達互惠關係的討論。博物學家艾德華‧威爾遜(Edward Wilson) 將其定義為一種與其他生命形式有聯繫的內在衝動;理查‧洛夫(Richard Louv)則認為,與其他物種疏遠會導致情感上的缺陷。愛生命自然就包括了「愛水」,因為水是生命的本質。黛博拉‧伯德‧羅斯(Deborah Bird Rose)觀察到澳洲原住民與水的關係提供了一個理想的哲學模型:
原住民的水哲學對水提供了一個廣泛支持生命的定義……第一步是將水置於愛生命的範圍內,因為熱愛生命的人顯然也必須熱愛水。也許非原住民的澳洲人也終於到了該發展水哲學的時候,這種哲學也將在互聯互通的模式中維持他們的生命。
44 承認「非人類」和生態系統具有人格
與非人類世界連結的渴望也反映了人類的認知過程,將思想向外延伸,並將人格特質編碼到其他生物與物質環境中。將意識置於自我之外的傾向意味著,雖然理性可能占主導地位,但是始終都有一片沃土,讓我們想像一個充滿活力且有感知力的非人類領域。當然,將他者擬人化對情感連結也有極大的助力,利用蛇形水族及其持久的能力來具體而微地展現水的屬性和力量。
對於「他者」的同理心需要一些共同認同,而關於非人類物種是否應該被視為人類,也有激烈的爭論。有關人與動物關係的人類學著作已經闡明,人們如何欣然地將家養動物(尤其是寵物)視為人和「親屬」。最近,多物種民族誌學者、哲學家和藝術家更進一步拒絕以人類為中心的觀點,在非人類生命世界的想像中向前躍進了一大步。洛夫也注意到連結與關懷之間的關係,認為「共同的跨物種凝視」既可以改變我們的生活,也可以拯救他們的生命。
這多半取決於人類和非人類之間的明確區別到什麼樣的程度。就像尤皮克人認為所有生物都是人一樣,在許多文化脈絡中都沒有這樣的區分。例如,人類學家喬安娜‧奧弗林(Joanna Overing)描述了南美洲的皮亞羅(Piaroa)部落如何將叢林動物視為自己的「同類」,並將食用動物視為同類相殘的一種食人形式,需要透過薩滿儀式來將它們的肉體轉化為植物性的物質。許多非西方文化在幾千年來就一直相信圖騰生物和有感知力的地景,完全可以接受將人格擴展到其他生物、地景和水景。
對某些社會來說,尤其是宗教發展軌跡在人類與他者之間建立了壁壘分明的界線並嚴格防守的社會,這是一個更棘手的問題。西元1990年代的「大猿計畫」(Great Ape Project)就引發了相當大的界線焦慮,哲學家彼得‧辛格(Peter Singer)和寶拉‧卡瓦列理(Paola Cavalieri)領導了反對靈長類動物科學實驗的抗議活動,認為「非人類的人科動物」應該享有生命權和免受酷刑的自由,並且應被視為有感知力的「人」。從那時起,動物權利運動及保護其他物種權利的努力就進一步挑戰人類例外論。關於人類與非人類關係的道德問題在邏輯上更進一步延伸到生命生態體系的管理,更有必要質疑社會是否有權剝削這些生態體系,損害它們的福祉。
此類爭論的核心始終都是水,也不斷湧現相關文獻,聚焦於人類與水之間的倫理關係。採礦業對國家經濟的巨大貢獻是否成為其污染生態體系的合理的藉口?為了支持工業化農業而過度抽取河流及含水層的地下水,是否一定凌駕非人類物種的需求及其棲地的健康?是否應該興建更多巨型水壩來滿足對廉價水力發電的渴望?無論目標多麼遠大,任何人——個人、政府或私人公司——有權利改變水流方向以滿足特定需求和利益,甚至不惜犧牲人類和非人類他者嗎?剝削行為往往是因為想要尋求短期解決方案來紓解社會和經濟壓力,然而,對此類措施的依賴卻導致了生態危機,很可能使這些措施徒勞無功。指定非人類物種為擁有正式合法權利的人則另闢蹊徑,可能將他們的需求和利益也納入決策過程的考量。
在紐西蘭就有一個現成的例子。當地的毛利蛇形水族塔尼瓦在關於將人格延伸到旺格努伊河的法律論辯中發揮了核心作用;除了將這條河定義為神聖的(taonga)河流之外,當地部落(iwi)還使用描術親屬關係的術語稱呼它為「祖先河」(Tupuna Awa),並將其定義為「重要的部落祖先」。泉源(puna wai)在「whānau」(大親屬群體)中也同樣有這種不可或缺的作用:「從whānau的puna wai湧出來的水,被視為在whānau中的taonga(神聖或特殊的東西),因為它承載著這個whānau的 Mauri(生命力)……每個whānau的精神本質都是河流的一部分……從這個意義上說,這條河不僅僅是一條 taonga,而是人。」
身為河流精神生命的後裔,毛利部落責任為後代子孫保護這位「活著的祖先」。西元2017年,這種祖先聯繫為法律訴訟案的勝訴奠定了基礎,確立了旺格努伊河作為「生命實體」的人格,並具有相應的權利。根據一個賦予圖霍伊(Ngäi Tuhoe)部落家園森林法律身份和權利的早期案例,這個判決定義「從山到海的河流、其支流及其所有物質與抽象元素為一個不可分割且有生命的整體……『靈魂河』(Te Awa Tupua) 是一個法人,擁有法人的所有的權利、權力、義務和責任」。官方和旺格努伊部落的指定代表有責任在法律體系內為河流的管理和使用「代言」。該法案創建了一個新角色「To Pou Tupua」,他們「是『靈魂河』的人形化形象,並以『靈魂河』 的名義行事」。
毛利族評論家表示,希望這項成功的行動能為其他地方的類似改革提供一個模式,而其他地方當然也曾經努力地確認河流作為人或有生命實體的權利。
西元2017年,印度的恆河和亞穆納河都獲得北阿坎德邦(Uttarakhand)高等法院認定為有生命的實體/法人,不過最高法院暫緩了這項裁決。西元2016年,哥倫比亞憲法法院承認阿特拉托河(Atrato River)為法律主體。
在澳大利亞,金伯利(Kimberley)地區的原住民群體呼籲現代河川管理必須尊重神聖水族所體現的「第一法則」。馬圖瓦拉—菲茨羅伊河議會(Martuwarra Fitzroy River Council)將古老的蛇形生物「Yoongoorrookoo」描述成有生命的祖先,並認定他是公共對話的參與者和共同作者。原住民長老喬‧南甘(Joe Nangan)描述了彩虹蛇如何維護法律並體現河流的人格:
在尼基納族(Nyikina)原住民的源始(Bookarrarra)故事中,Yoongorrookoo 是一條強大而神聖的彩虹蛇,能賜予人類雨水和生命……他可以非常仁慈,為尼基納人——他所選擇的人民——帶來溫和的雨水,填滿水坑。但是當他生氣時,他能引起旋風、洪水,甚至龍捲風。原住民在靠近水坑時總是非常謹慎,生怕冒犯神聖而強大的彩虹蛇 Yoongoorrookoo。
在厄瓜多和玻利維亞,原住民群體說服政府在憲法中賦予地球母親帕查媽媽更廣泛的權利,其立論基礎就是「buen vivir」(美好生活/活得美好)這個已經貫穿整個拉丁美洲論述的廣泛願景。「buen vivir」借鑒原住民世界觀,批判了永續發展的主流觀念,並提倡一個另類的未來,以人類和非人類之間集體且不可分割的福祉為基礎。
許多原住民和環保運動人士認為,承認非人類和生態體系為人類,將促進包容性思維,從而驅動實踐變革。然而,除了激怒保守的宗教團體外,對於「宗教」努力地重新魅惑非人類世界和重新引入與科學思維不一致的萬物有靈論,也引起了一些世俗的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