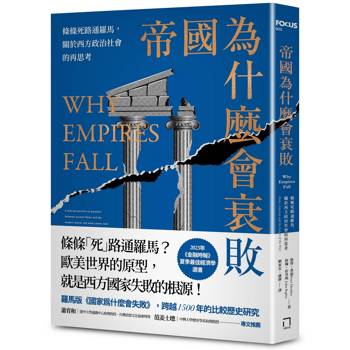內文試閱
第一章 盛世般的狂歡
西元一九九九年,華盛頓特區
現今的政治氛圍下,分歧愈演愈烈,輿論燒遍各項公共議題:社會不公持續加劇、生活水準停滯不前、債台高築,就連公共服務也日漸衰退。回頭來看,很難想像不過二十年前,西方世界有著看似光明燦爛的前景。當二十世紀邁入尾聲時,現代世界仍繞著美國轉。當時的美國是世上最大的經濟體,失業率創下新低,享受著有史以來最長的經濟成長潮,股市每年都以兩位數在成長。乘著網路經濟暴發的浪潮,數百萬一夕暴富的美國股民,大肆揮霍著他們的意外之財,進而帶來良性循環,經濟隨之起飛。不僅美國如此,整個「西方」都是如此,美國的盟友們,包含西歐、加拿大與亞洲(澳洲、紐西蘭以及後來居上的日本),以富裕、工業化的經濟體組成了足跡遍布全球的西方世界。西方的繁榮和富裕以及其對個人自由、民主和自由市場的價值觀,為全世界帶來莫大影響,這一切都成為無庸置疑的現實。
再往回推十年,似乎就是二十世紀最關鍵的歷史轉捩點,當時,東歐抗議者紛紛推翻他們的共產主義領袖。兩年後,蘇聯在公投後解體,而美國的經濟學家則開始環遊世界,四處遊說各國政府效法西方,重新打造他們的經濟與政治體制。甚至就連中國共產黨都伸手擁抱市場經濟。德國邁向統一、歐洲經濟復甦、英倫群島一片祥和,美國則乘風高飛。到了一九九九年,西方國家消費的全球產出份額達到驚人的歷史新高:全球產出的貨物及服務之中,百分之八十的全球產出被僅占全球人口六分之一的人消費掉。
美國總統柯林頓(Bill Clinton)在一九九九年的國情咨文演說當中,流露出好日子永不結束的樂觀看法,宣稱「我們的未來前景無限」。因為經濟學家告訴他,美國的「大穩定時期」將要到來,這將會是個經濟穩定、無限成長的年代,他的執政團隊認為政府盈餘很快就將達到數兆美元。柯林頓敦促國會將這筆龐大的資金投入養老金以及醫療保健,他的財政部長則宣稱,在政府赤字持續攀升數十年後,美國終於要開始償還過去兩世紀累積下來的所有債務,還會將更多錢放回美國人民的口袋。與此同時,大西洋彼端,英國首相布萊爾(Tony Blair)組織的新工黨政府(New Labour)順應時代精神,雄心勃勃地大幅擴張公共服務,歐盟則是冷靜且自信地準備迎接舊蘇聯集團解體後的大部分成員加入西方民主國家的菁英俱樂部。
僅僅幾年過去,這種樂觀之情就消失無蹤。二○○八年金融海嘯來襲,全球陷入經濟大衰退,然後就陷入大停滯。距離一九九九年達到高峰僅僅十年,西方國家在全球產出中的份額就已經縮減了四分之一,全球生產總額從百分之八十降到百分之六十。儘管各國政府與其央行大舉注入資金振興經濟,以免直接受到這場危機最嚴重的衝擊,但西方國家自此一蹶不振,至今仍未能恢復到過去的成長速度,而開發中國家的關鍵區域卻仍能持續維持快速成長。此消彼長之下,西方國家在全球生產總額中所占的比例持續下滑。西方國家頓失陣地的還不只是經濟層面。曾經閃亮的西方「招牌」變得黯淡無光,如今對外呈現出的往往是深刻分歧與搖擺不定的民主體制,似乎整個體制不過是為少數人牟利而存在。相反地,威權領導與單一政黨的模式,如今在經濟與政治上都逐漸拾回曾一度失去的公信力。
對部分西方評論家而言,吉朋以羅馬歷史為鑑做出的診斷,似乎就是對症下藥的良方。他們認為,西方在外來移民潮下失去了自己的身分認同,尤其是面對穆斯林移民時必須築起防禦,重新確立核心的文化價值觀,否則將注定走上帝國末路。然而,二十一世紀的歷史研究對於羅馬歷史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將能夠為現代西方帶來大不相同的教訓。
西元三九九年,羅馬
早在柯林頓過分樂觀地展望無限的可能性之前,距今十六個世紀前的羅馬,就曾有位帝國發言人在羅馬元老院面前,對羅馬世界的西半部發表當時的「國情咨文演說」。那時是三九九年一月一日,這天是新任執政官就職日,執政官是羅馬世界最具威望的官職,在這個日子,新任執政官將接下這項千年來不曾間斷的傳統,就職那年更會以其名紀年,讓他從此得到永生。而這一年將獲得永生殊榮的候選人是狄奧多魯斯(Flavius Mallius Theodorus),他是有豐富行政經驗的律師兼哲學家。迎接他到任的這場演說滿溢著勝利之情,預示著全新的黃金時代即將隨著他一起到來。負責演說的發言人是名為克勞狄安(Claudian)的詩人。他先是以浮誇的讚美向觀眾致意:「感謝這場盛會以宇宙般的度量,容我在此一睹全世界的輝煌共耀。」(就算現代最大膽的公關專家大概都說不出這種話)接著他就正式開始演說。
演說有兩大主題。首先,狄奧多魯斯願意出任執政官一職,正彰顯執政團隊傑出異稟之處。「吾皇千秋,誰人得拒?其功勳顯赫,何曾得及?綜觀古今,其智勇雙全無與倫比,即便是(凱撒的災星)布魯圖斯也會樂於為當今的皇帝效犬馬之力。」「再說,如今帝國輝煌盛世將臨。」「榮耀之路為智者而開,功勳必得彰顯,勤奮終將得償。」
乍聽之下,這整段演說講得天花亂墜,像是歷史上的那些失敗政權總是少不了的馬屁話。當時的西羅馬帝國皇帝是年僅十五歲的霍諾留斯(Honorius),真正的實權其實握在斯提里科(Stilicho)將軍手上。斯提里科將軍是個擁兵自重的軍頭,身上流著蠻族的血液,而他身邊的官員則個個都想找機會朝他背後刺上一刀。短短十年之後,名為阿拉里克(Alaric)的哥德國王就將率領著一群近年才移入羅馬世界的蠻族戰士,一路殺進羅馬城的大門。霍諾留斯的皇朝在接下來幾代邁向末路,西羅馬帝國分裂成一系列的蠻族王朝,阿拉里克率領的哥德後裔統治大部分西班牙及高盧南部的領地,高盧的東南地區由勃艮第(Burgundian)諸王控制,北部地區則是由法蘭克(Frankish)諸王控制,北非有汪達爾人(Vandals),盎格魯-撒克遜(Anglo-Saxon)的各部族瓜分英吉利海峽以北的地區。難道,當時的執政官、皇帝、發言人和元老院,典禮上的這些人全都是在自欺欺人嗎?吉朋顯然就是這麼認為。根據他的說法,自從二世紀的安東尼王朝(Antonine)的黃金時期過後,羅馬不論是經濟上、文化上還是政治上都持續衰退,到了三九九年時,羅馬的衰亡已經近在眼前。
後續歷史學家根據吉朋提出的模型持續深入研究,到了二十世紀中葉,他們彙整出一份衰亡狀況的條件清單,用來清楚表列當時的頹態。第一點,在四世紀的帝國法條當中,就有「荒廢農地」(agri deserti)一詞。羅馬世界幾乎完全是農業社會,羅馬帝國的農民在總人口中占有百分之八十五到九十的比例。荒廢農地的存在透露著經濟災難的氣息,其箇中原因是懲罰性稅制,而當時的文字記載也會不時抱怨這一點。第二點,由下而上的腐敗。在吉朋所寫的黃金時代(Golden Age),羅馬的中上階級通常會在刻有日期的石碑上,記錄其生平卓越之處。這些石碑記載著他們的功勳、職位和贈禮,這些贈禮通常會是為當地城市社群所蓋的一些建築和公共設施(在羅馬世界中,這能展現出受到高度重視的公民美德)。但是,在十九世紀進行的兩個龐大研究計畫中,收集並出版了所有已知的拉丁文及希臘文的石碑,縱觀下來就會清楚看到一個明顯的重點。從三世紀中葉開始,石碑製作頻率驟降,相較於先前的平均數量,每年製作的數量少了五分之四。羅馬世界富裕階級用以自捧的石碑戲劇性地減少,就和荒廢農地出現一樣強烈散發出經濟崩盤的氣息。第三點,當學者仔細檢視埃及留下的莎草紙,以及同一時期帝國發行的錢幣之後,更進一步地強化羅馬衰亡的觀點。第三世紀下半葉,帝國人民面對一波大幅通貨膨脹,程度不亞於一次大戰後的德國,這是第納里(denarius)銀幣逐漸貶值造成的。貨幣貶值、惡性通貨膨脹、上層階級失去信心、農地荒廢,種種跡象都指向一個顯而易見的結論:早在狄奧多魯斯就任的一個世紀以前,帝國經濟早已形同廢墟,基督教的興起則不過是讓事情更加混亂而已。
吉朋也開創了一種思維:新興宗教為帝國帶來深刻的負面影響。根據他的看法,基督教的教士與苦行者高達數千人,相當於數千名「閒散人口」依賴著帝國生活,消耗掉帝國的經濟活力。他同時也認為,基督教當中要以「連左臉也轉過來任由他打」來傳達愛的方式,削弱了過去造就羅馬的崇武美德,吉朋也非常厭惡基督教領袖之間的內鬥傾向,認為會因此阻撓帝國朝向和諧統一的古老目標邁進。結果,在二十世紀前半葉歷史學界達成普遍共識:三九九年時,整個羅馬的龐大體系是由臃腫的極權官僚體制勉強撐起的一棟大廈,而這棟大廈建立在一個由中央指揮的經濟體上,它所能做到的頂多就是不讓士兵挨餓而已。一次大戰後長大的這一代學者,不僅親眼目睹過威瑪共和國惡性通貨膨脹帶來的混亂局面,同時也面對著俄國布爾什維克時期,以及德國納粹時期的極權統治的例子。就這套對羅馬歷史的普遍觀點來看,羅馬帝國晚期百廢待興,只差蠻族入侵,就能一舉擊垮搖搖欲墜的帝國。而實際上也確實如此,就在狄奧多魯斯就任執政官,號稱將要開啟新的黃金時代的幾十年後,蠻族就敲破羅馬城的大門。
這套帝國中心在道德層面和經濟層面墮落的論點,將帝國瓦解的責任全然歸咎於羅馬領導人身上,為當代帶來難以言喻的影響。這套觀點不僅風靡於一些西方主流的保守評論家之間,同時也在社會學科占有一席之地,形塑出當代國際關係學界中一些具有影響力的思想,甚至還會不時滲進白宮。川普(Donald Trump)的前顧問班農(Steve Bannon)就經常引用吉朋的觀點,認為美國就是因為放棄宗教傳承而走向衰敗。川普總統的就職演說當中,就明確地提到這種世界觀,並將當時的美國現狀形容成「美國浩劫」。對柯林頓的外交政策有深刻影響的作家兼思想家卡普蘭(Robert Kaplan),也曾大力讚揚從吉朋書中得到的見解,其中特別提到吉朋的書影響他自己對於全球邊陲地帶「將要陷入無政府狀態」的預測看法。吉朋在經濟理論上也有深刻影響,在《國家為什麼會失敗》(Why Nations Fail)一書當中,兩位作者艾塞默魯(Daron Acemoglu)與羅賓森(James Robinson)就認為,自由制度為現代西方的成功奠定基礎,而威權體制則會無可避免地邁向衰敗。為了證明他們的論點,艾塞默魯和羅賓森引用吉朋的看法,認為羅馬在放棄共和體制那一刻起,就推動了漫長但是停不下來的歷史巨輪,步上帝國瓦解之路。
吉朋的《羅馬帝國衰亡史》在美國格外受到注目並不讓人意外。自從美國採用共和制以來,其知識分子就常自詡為羅馬的傳人,常以羅馬帝國史為借鏡。從吉朋提出的帝國內衰的模型當中各種元素,他們會依據各自想要表述的目的採用吉朋的觀點,並衍生出了一整個產業。有些評論家會將重點放在經濟失敗上,其他人則重視道德敗壞的問題,但是不論如何,他們都會一致強調:從根本來說,內在因素是導致帝國瓦解的主因。吉朋所述的羅馬歷史是段偉大的故事,文筆也很優美,光是為了吉朋的散文之美,就仍然會有許多人閱讀。此外,這套書歷史悠久,任何教過書的人都知道,對大多數學生而言,先入為主的印象往往根深柢固難以改變。但是,它必須要改變。在過去五十年裡,人們開始留意一套對於羅馬歷史的新詮釋。
第一章 盛世般的狂歡
西元一九九九年,華盛頓特區
現今的政治氛圍下,分歧愈演愈烈,輿論燒遍各項公共議題:社會不公持續加劇、生活水準停滯不前、債台高築,就連公共服務也日漸衰退。回頭來看,很難想像不過二十年前,西方世界有著看似光明燦爛的前景。當二十世紀邁入尾聲時,現代世界仍繞著美國轉。當時的美國是世上最大的經濟體,失業率創下新低,享受著有史以來最長的經濟成長潮,股市每年都以兩位數在成長。乘著網路經濟暴發的浪潮,數百萬一夕暴富的美國股民,大肆揮霍著他們的意外之財,進而帶來良性循環,經濟隨之起飛。不僅美國如此,整個「西方」都是如此,美國的盟友們,包含西歐、加拿大與亞洲(澳洲、紐西蘭以及後來居上的日本),以富裕、工業化的經濟體組成了足跡遍布全球的西方世界。西方的繁榮和富裕以及其對個人自由、民主和自由市場的價值觀,為全世界帶來莫大影響,這一切都成為無庸置疑的現實。
再往回推十年,似乎就是二十世紀最關鍵的歷史轉捩點,當時,東歐抗議者紛紛推翻他們的共產主義領袖。兩年後,蘇聯在公投後解體,而美國的經濟學家則開始環遊世界,四處遊說各國政府效法西方,重新打造他們的經濟與政治體制。甚至就連中國共產黨都伸手擁抱市場經濟。德國邁向統一、歐洲經濟復甦、英倫群島一片祥和,美國則乘風高飛。到了一九九九年,西方國家消費的全球產出份額達到驚人的歷史新高:全球產出的貨物及服務之中,百分之八十的全球產出被僅占全球人口六分之一的人消費掉。
美國總統柯林頓(Bill Clinton)在一九九九年的國情咨文演說當中,流露出好日子永不結束的樂觀看法,宣稱「我們的未來前景無限」。因為經濟學家告訴他,美國的「大穩定時期」將要到來,這將會是個經濟穩定、無限成長的年代,他的執政團隊認為政府盈餘很快就將達到數兆美元。柯林頓敦促國會將這筆龐大的資金投入養老金以及醫療保健,他的財政部長則宣稱,在政府赤字持續攀升數十年後,美國終於要開始償還過去兩世紀累積下來的所有債務,還會將更多錢放回美國人民的口袋。與此同時,大西洋彼端,英國首相布萊爾(Tony Blair)組織的新工黨政府(New Labour)順應時代精神,雄心勃勃地大幅擴張公共服務,歐盟則是冷靜且自信地準備迎接舊蘇聯集團解體後的大部分成員加入西方民主國家的菁英俱樂部。
僅僅幾年過去,這種樂觀之情就消失無蹤。二○○八年金融海嘯來襲,全球陷入經濟大衰退,然後就陷入大停滯。距離一九九九年達到高峰僅僅十年,西方國家在全球產出中的份額就已經縮減了四分之一,全球生產總額從百分之八十降到百分之六十。儘管各國政府與其央行大舉注入資金振興經濟,以免直接受到這場危機最嚴重的衝擊,但西方國家自此一蹶不振,至今仍未能恢復到過去的成長速度,而開發中國家的關鍵區域卻仍能持續維持快速成長。此消彼長之下,西方國家在全球生產總額中所占的比例持續下滑。西方國家頓失陣地的還不只是經濟層面。曾經閃亮的西方「招牌」變得黯淡無光,如今對外呈現出的往往是深刻分歧與搖擺不定的民主體制,似乎整個體制不過是為少數人牟利而存在。相反地,威權領導與單一政黨的模式,如今在經濟與政治上都逐漸拾回曾一度失去的公信力。
對部分西方評論家而言,吉朋以羅馬歷史為鑑做出的診斷,似乎就是對症下藥的良方。他們認為,西方在外來移民潮下失去了自己的身分認同,尤其是面對穆斯林移民時必須築起防禦,重新確立核心的文化價值觀,否則將注定走上帝國末路。然而,二十一世紀的歷史研究對於羅馬歷史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將能夠為現代西方帶來大不相同的教訓。
西元三九九年,羅馬
早在柯林頓過分樂觀地展望無限的可能性之前,距今十六個世紀前的羅馬,就曾有位帝國發言人在羅馬元老院面前,對羅馬世界的西半部發表當時的「國情咨文演說」。那時是三九九年一月一日,這天是新任執政官就職日,執政官是羅馬世界最具威望的官職,在這個日子,新任執政官將接下這項千年來不曾間斷的傳統,就職那年更會以其名紀年,讓他從此得到永生。而這一年將獲得永生殊榮的候選人是狄奧多魯斯(Flavius Mallius Theodorus),他是有豐富行政經驗的律師兼哲學家。迎接他到任的這場演說滿溢著勝利之情,預示著全新的黃金時代即將隨著他一起到來。負責演說的發言人是名為克勞狄安(Claudian)的詩人。他先是以浮誇的讚美向觀眾致意:「感謝這場盛會以宇宙般的度量,容我在此一睹全世界的輝煌共耀。」(就算現代最大膽的公關專家大概都說不出這種話)接著他就正式開始演說。
演說有兩大主題。首先,狄奧多魯斯願意出任執政官一職,正彰顯執政團隊傑出異稟之處。「吾皇千秋,誰人得拒?其功勳顯赫,何曾得及?綜觀古今,其智勇雙全無與倫比,即便是(凱撒的災星)布魯圖斯也會樂於為當今的皇帝效犬馬之力。」「再說,如今帝國輝煌盛世將臨。」「榮耀之路為智者而開,功勳必得彰顯,勤奮終將得償。」
乍聽之下,這整段演說講得天花亂墜,像是歷史上的那些失敗政權總是少不了的馬屁話。當時的西羅馬帝國皇帝是年僅十五歲的霍諾留斯(Honorius),真正的實權其實握在斯提里科(Stilicho)將軍手上。斯提里科將軍是個擁兵自重的軍頭,身上流著蠻族的血液,而他身邊的官員則個個都想找機會朝他背後刺上一刀。短短十年之後,名為阿拉里克(Alaric)的哥德國王就將率領著一群近年才移入羅馬世界的蠻族戰士,一路殺進羅馬城的大門。霍諾留斯的皇朝在接下來幾代邁向末路,西羅馬帝國分裂成一系列的蠻族王朝,阿拉里克率領的哥德後裔統治大部分西班牙及高盧南部的領地,高盧的東南地區由勃艮第(Burgundian)諸王控制,北部地區則是由法蘭克(Frankish)諸王控制,北非有汪達爾人(Vandals),盎格魯-撒克遜(Anglo-Saxon)的各部族瓜分英吉利海峽以北的地區。難道,當時的執政官、皇帝、發言人和元老院,典禮上的這些人全都是在自欺欺人嗎?吉朋顯然就是這麼認為。根據他的說法,自從二世紀的安東尼王朝(Antonine)的黃金時期過後,羅馬不論是經濟上、文化上還是政治上都持續衰退,到了三九九年時,羅馬的衰亡已經近在眼前。
後續歷史學家根據吉朋提出的模型持續深入研究,到了二十世紀中葉,他們彙整出一份衰亡狀況的條件清單,用來清楚表列當時的頹態。第一點,在四世紀的帝國法條當中,就有「荒廢農地」(agri deserti)一詞。羅馬世界幾乎完全是農業社會,羅馬帝國的農民在總人口中占有百分之八十五到九十的比例。荒廢農地的存在透露著經濟災難的氣息,其箇中原因是懲罰性稅制,而當時的文字記載也會不時抱怨這一點。第二點,由下而上的腐敗。在吉朋所寫的黃金時代(Golden Age),羅馬的中上階級通常會在刻有日期的石碑上,記錄其生平卓越之處。這些石碑記載著他們的功勳、職位和贈禮,這些贈禮通常會是為當地城市社群所蓋的一些建築和公共設施(在羅馬世界中,這能展現出受到高度重視的公民美德)。但是,在十九世紀進行的兩個龐大研究計畫中,收集並出版了所有已知的拉丁文及希臘文的石碑,縱觀下來就會清楚看到一個明顯的重點。從三世紀中葉開始,石碑製作頻率驟降,相較於先前的平均數量,每年製作的數量少了五分之四。羅馬世界富裕階級用以自捧的石碑戲劇性地減少,就和荒廢農地出現一樣強烈散發出經濟崩盤的氣息。第三點,當學者仔細檢視埃及留下的莎草紙,以及同一時期帝國發行的錢幣之後,更進一步地強化羅馬衰亡的觀點。第三世紀下半葉,帝國人民面對一波大幅通貨膨脹,程度不亞於一次大戰後的德國,這是第納里(denarius)銀幣逐漸貶值造成的。貨幣貶值、惡性通貨膨脹、上層階級失去信心、農地荒廢,種種跡象都指向一個顯而易見的結論:早在狄奧多魯斯就任的一個世紀以前,帝國經濟早已形同廢墟,基督教的興起則不過是讓事情更加混亂而已。
吉朋也開創了一種思維:新興宗教為帝國帶來深刻的負面影響。根據他的看法,基督教的教士與苦行者高達數千人,相當於數千名「閒散人口」依賴著帝國生活,消耗掉帝國的經濟活力。他同時也認為,基督教當中要以「連左臉也轉過來任由他打」來傳達愛的方式,削弱了過去造就羅馬的崇武美德,吉朋也非常厭惡基督教領袖之間的內鬥傾向,認為會因此阻撓帝國朝向和諧統一的古老目標邁進。結果,在二十世紀前半葉歷史學界達成普遍共識:三九九年時,整個羅馬的龐大體系是由臃腫的極權官僚體制勉強撐起的一棟大廈,而這棟大廈建立在一個由中央指揮的經濟體上,它所能做到的頂多就是不讓士兵挨餓而已。一次大戰後長大的這一代學者,不僅親眼目睹過威瑪共和國惡性通貨膨脹帶來的混亂局面,同時也面對著俄國布爾什維克時期,以及德國納粹時期的極權統治的例子。就這套對羅馬歷史的普遍觀點來看,羅馬帝國晚期百廢待興,只差蠻族入侵,就能一舉擊垮搖搖欲墜的帝國。而實際上也確實如此,就在狄奧多魯斯就任執政官,號稱將要開啟新的黃金時代的幾十年後,蠻族就敲破羅馬城的大門。
這套帝國中心在道德層面和經濟層面墮落的論點,將帝國瓦解的責任全然歸咎於羅馬領導人身上,為當代帶來難以言喻的影響。這套觀點不僅風靡於一些西方主流的保守評論家之間,同時也在社會學科占有一席之地,形塑出當代國際關係學界中一些具有影響力的思想,甚至還會不時滲進白宮。川普(Donald Trump)的前顧問班農(Steve Bannon)就經常引用吉朋的觀點,認為美國就是因為放棄宗教傳承而走向衰敗。川普總統的就職演說當中,就明確地提到這種世界觀,並將當時的美國現狀形容成「美國浩劫」。對柯林頓的外交政策有深刻影響的作家兼思想家卡普蘭(Robert Kaplan),也曾大力讚揚從吉朋書中得到的見解,其中特別提到吉朋的書影響他自己對於全球邊陲地帶「將要陷入無政府狀態」的預測看法。吉朋在經濟理論上也有深刻影響,在《國家為什麼會失敗》(Why Nations Fail)一書當中,兩位作者艾塞默魯(Daron Acemoglu)與羅賓森(James Robinson)就認為,自由制度為現代西方的成功奠定基礎,而威權體制則會無可避免地邁向衰敗。為了證明他們的論點,艾塞默魯和羅賓森引用吉朋的看法,認為羅馬在放棄共和體制那一刻起,就推動了漫長但是停不下來的歷史巨輪,步上帝國瓦解之路。
吉朋的《羅馬帝國衰亡史》在美國格外受到注目並不讓人意外。自從美國採用共和制以來,其知識分子就常自詡為羅馬的傳人,常以羅馬帝國史為借鏡。從吉朋提出的帝國內衰的模型當中各種元素,他們會依據各自想要表述的目的採用吉朋的觀點,並衍生出了一整個產業。有些評論家會將重點放在經濟失敗上,其他人則重視道德敗壞的問題,但是不論如何,他們都會一致強調:從根本來說,內在因素是導致帝國瓦解的主因。吉朋所述的羅馬歷史是段偉大的故事,文筆也很優美,光是為了吉朋的散文之美,就仍然會有許多人閱讀。此外,這套書歷史悠久,任何教過書的人都知道,對大多數學生而言,先入為主的印象往往根深柢固難以改變。但是,它必須要改變。在過去五十年裡,人們開始留意一套對於羅馬歷史的新詮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