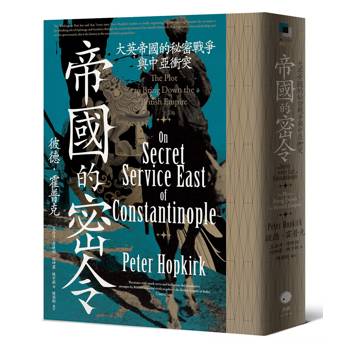前言
一九一四年夏季,德皇威廉二世發現自己嚴重誤判形勢,無可避免要與英國決一死戰。他發誓將對英國展開一場聖戰,永久消滅英國在亞洲的勢力。威廉二世下達諭令:「面對英國這個令人作嘔、說謊成性且厚顏無恥的國家,我們的間諜和特務必須讓穆斯林世界的怒火燃燒得更加旺盛。」如果戰爭無法避免,那麽這就是他扳倒整個大英帝國的機會。他會聯合鄂圖曼帝國的人民、高加索人、波斯人和阿富汗人,共同摧毀英國遍佈世界的帝國利益。他們會引燃導火線,將緊張情勢推往這些地區中最重要、卻也最脆弱的印度。如果能從英國手上奪走印度,那麼由虛張聲勢的大英帝國所掌控的其他地區也會跟著分崩離析。威廉二世的顧問向他保證,印度早已累積許多不滿情緒,就像一桶火藥,只需要一把革命火炬就可以點燃。事態發展若真如此順利,威廉二世或許就能從他厭惡無比的表弟喬治五世手裡搶來印度和整個英國的廣袤財富。
自登基以來,威廉二世的願望一直都是要把德意志帝國打造成世界霸權,以武力取代英國全球守護者的地位。他打算透過經濟優勢和外交滲透等手段,以及陸軍和海軍的堅強實力來實現他遠大的抱負,而非直接向英國王室和敵人發起戰爭。有了德意志銀行(Deutsche Bank)作為堅實的後盾,威廉二世的外交官和工業家籌劃著,要將自己國家在政治和商業上的利益和影響力擴張至全世界。
不過,德國人將大部分心力都投注於東方。他們在衰亡的鄂圖曼帝國身上看到大好機會,而為了確保德意志帝國能奪得先機,他們不惜一切:當時鄂圖曼帝國的蘇丹因為凌虐轄內少數基督徒族群而激怒全歐洲,德國卻選擇與他交好。威廉二世決定,要讓衰弱的土耳其在柏林的控制下,成為德意志東進擴張權力和影響力的經濟與政治基地。然而,實際上他的計畫出了嚴重差錯,不只使歐洲陷入戰爭的深淵,更將世界上幾乎所有國家牽扯進來。
在這場戰爭中,德意志帝國如何在盟友土耳其的幫助下操縱伊斯蘭武裝分子?這就是我想透過本書首度揭露的精彩故事。威廉二世和他的鷹派顧問們試圖透過煽動聖戰,將英國勢力驅離印度,並將俄國人趕出高加索地區和中亞。這個策略既大膽又冒險,因為在現代戰爭中,尚未有發動伊斯蘭聖戰的先例。然而,誠如德國歷史學家費里茨・費雪(Fritz Fischer)所言,這不過是威廉二世自一八九○年代以來東進侵略政策的延續而已。普魯士曾經是個渺小的內陸國家,國土極為破碎,其他國家的國土穿插其中,因此領土各區相距甚遠。從那時開始,德意志便因首相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的政治手腕得以不斷擴張。而威廉二世相信,現在就是德意志在東方建立新帝國的絕佳機會。
這場於柏林策劃、在君士坦丁堡發動的聖戰是過去所謂「大競逐」(Great Game)更加邪惡的新版本。此一戰爭的參與者包括英國、威廉二世、鄂圖曼帝國蘇丹和沙皇情報機關,戰場從君士坦丁堡一路向西延伸至喀布爾、向東至喀什噶爾(Kashgar),甚至波及波斯、高加索地區和俄國控制的中亞。英屬印度和緬甸也未能倖免於難,柏林當局希望能藉由走私的武器和資金煽動當地的穆斯林、錫克人或印度教徒,掀起暴力革命。這場陰謀的魔爪甚至伸向亞洲以外的地區。柏林的遠大計畫中還包括美國的軍火商、作為軍事會合點的一座太平洋偏遠小島(在墨西哥外海),以及位於倫敦鬧區托特納姆宮路(Tottenham Court Road),讓刺客用來制定計畫、完善演練的左輪手槍射擊場。計畫中還包含滿載武器的帆船,數量足以掀起第二次印度兵變(Indian Mutiny),還有一箱箱以英國經典文學作品封面掩護,走私進入印度的革命文學書籍。
然而,聖戰的主要攻勢會從君士坦丁堡向東展開,穿越中立的波斯和阿富汗,通過山口,進入印度。也就是說,柏林首先必須取得波斯沙阿(Shah)和阿富汗埃米爾(Emir)的支持。如果能夠獲得他們的支持,就能由德國和土耳其軍官率領兩國的軍隊,以豐厚獎賞提升士氣,往印度攻去。如此一來,除了少數精挑細選的軍官和士官,德國幾乎不用為聖戰付出任何代價,所需要的只有承諾和黃金。承諾在戰爭結束後才須兌現,而大部分的黃金只要從英國人開設在波斯的多家銀行搬走就好。若能說服印度眾多的異議分子同時起義,那麼英國將面臨內憂和外患。此外,土耳其會試圖與高加索和中亞地區的穆斯林結盟,邀請他們加入土耳其和德國的聖戰行列。情報機構傳回來的消息相當樂觀,柏林和君士坦丁堡的戰略家們已能預見整個亞洲陷入火海,而他們在英俄兩國的敵人被大火所吞噬。
威廉二世並未信奉伊斯蘭教,身為異教徒他自然沒有權力號召穆斯林參與聖戰。要發動這場戰爭,需要的遠遠不只黃金、武器和戰後兌現的承諾。確實也只有鄂圖曼蘇丹本人,也就是伊斯蘭教的哈里發(Caliph),才有權下達如此重大的諭令。因此,無論對於土耳其人民的利益而言是好是壞,土耳其都必須與德國結盟。雖然有些諷刺,但威廉二世在戰前培植土耳其及其不受各國歡迎的君主,可說是相當有遠見的做法,也一如預期獲得了回報。戰爭爆發後的三個月內,土耳其與德意志帝國、奧匈帝國締下盟約,一週後蘇丹便開始呼籲各處的穆斯林群起反抗,「無論身在何方,」都要除掉所有壓迫他們的基督徒。
就如德國所計畫的一樣,首當其衝的便是在印度的英國人,因為英國人所統治的印度是全球穆斯林人口最多的穆斯林帝國。英王喬治五世統治的穆斯林人口甚至超越了鄂圖曼蘇丹,更是俄國和法國的數倍。再者,威廉二世並沒有穆斯林殖民地或人民,因此多年來他一直宣稱自己是全球穆斯林的保護者。此說法總是讓英國、俄國和法國非常惱怒。蘇丹的宣言無疑使得在印度的英國人和協約國各國人民都非常緊張,因為他們四周都是穆斯林,而現代從來沒有人發起過對抗歐洲勢力的聖戰,也沒有人知道事態會如何發展。
但即使對於德國而言,聖戰也會導致一個尷尬的處境,必須妥善解決,否則整個計畫都會泡湯。一定有許多穆斯林都會問,為什麼一個信奉基督宗教的政權會想要煽動、資助這場殺害基督徒同胞的聖戰?(譯按:德國人信奉天主教與新教[即臺灣所謂的基督教],兩者人口皆很多。)不過,威廉二世的顧問團中有許多傑出的東方專家和學者,他們已經準備好回應這個問題。東方的清真寺和市集開始出現傳言,聲稱德意志皇帝已經秘密皈依了伊斯蘭教。他現在自稱「哈吉」・威廉・穆罕默德(“Haji” Wilhelm Mohammed),甚至便衣微行前往麥加朝聖。(譯按:哈吉[Haji],原意為「朝覲者」,是伊斯蘭教中用以尊稱曾前往麥加朝靚,並完成「五功」之穆斯林,而所謂「五功」即:念[唸誦證詞]、禮[跪拜祈禱]、齋[齋戒]、課[捐獻施捨]、朝[至麥加朝聖]。)親德的穆斯林學者甚至聲稱,《古蘭經》的段落可以證明,是阿拉授命威廉二世去解放異教徒統治底下的穆斯林。後來更有消息傳出,德意志帝國的人民效仿他們的皇帝,全部皈依了伊斯蘭教。最後,再由情報人員釋出土耳其和德意志帝國已經取得勝利的虛假捷報,並歸功於土耳其和德國之間高尚正義的同盟。這一切都是為了讓德意志帝國在穆斯林心中擁有正當地位。
與此同時,柏林當局會挑選一些德國軍官前往東方執行任務,散播聖戰的消息,最終目標是讓戰爭之火延燒至英屬印度。他們會帶著無數的黃金、武器及煽動人心的文宣,從新一代「大競逐」的基地君士坦丁堡出發,悄悄潛入中立的波斯。當他們行經沙漠、穿越山脈前往阿富汗時,會向沿途部落和村莊散佈聖戰的消息,試著爭取當地人的支持。但在抵達阿富汗首都後,這群軍官的最重要任務才要開始:想辦法說服位高權重的埃米爾加入德意志同盟,並同意命令他麾下各部落的大軍一起攻打戒備鬆散的印阿邊境。同一時間,德意志帝國還會向德黑蘭的年輕沙阿施壓,試圖將沙阿與他的穆斯林臣民捲入聖戰。在印度方面,德國也會脅迫一些地位最高的王侯加入同盟,其中某些是獲得英國允許擁有私人軍隊的。執行任務的軍官們會帶著威廉二世親筆寫的信,以皮革精心包裝,準備送到目標人物手中。信中承諾,若這些人改變立場,德國就能提供他們想要的一切。
這就是我要說的故事。本書參考了那段歷史的參與者們所寫的回憶錄,以及秘密情報機關的報告。有鑑於「大競逐」在動盪不斷的地區從未真正終結,書中所講述的事件其實與時下局勢息息相關,尤其某些族群可能會害怕俄國和德國再次崛起,因此我的論述對他們來講別具意義。然而,最重要的其實是當年那些足智多謀的勇士們所經歷的事件。無論來自哪一陣營,他們身不由己,捲入各種陰謀中。我會儘可能透過他們的經歷與不幸進行敘事。
約翰・布肯(John Buchan)膾炙人口的諜報驚悚小說《綠斗篷》(Greenmantle)即是以德國這個巨大陰謀為主軸所撰寫,銷售量甚至更勝於他的《三十九步》(The Thirty-Nine Steps)。我在上一本書《帝國的野心:十九世紀英俄帝國中亞大競逐》中,揭露了吉卜林(Rudyard Kipling)經典間諜小說《基姆》(Kim)背後的真實故事,本書則與啟發布肯戰時暢銷作品《綠斗篷》的一連串奇特事件有關。事實上,讀者將會發現,《綠斗篷》裡面許多角色都有本書那些人物的影子。或許這一切沒什麼好令人訝異的,因為布肯自己當年就是情報工作的參與者,也有獲取機密報告的管道,可以知道當時德意志帝國對東方有何野心。布肯的朋友T・E・勞倫斯(T. E. Lawrence)在戰後如此評論:「《綠斗篷》裡面有不少情節都是真實事件。」(譯按:T・E・勞倫斯就是鼎鼎大名的「阿拉伯的勞倫斯」,也是具有軍方背景的情報人員。)
正因為有了這些人,「大競逐」鮮為人知的新篇章才能向前推進、充滿刺激。不過,要了解他們在波斯、阿富汗、高加索地區等戰場的經歷,必須先從故事的真正開頭說起。雖然威廉二世幾乎以救世主自居,狂熱推行著東進政策(Drang nach Osten,把德意志帝國往東方擴張),但他並不是第一個想出這個計畫的人。東進的概念要回溯到十九世紀中葉,當時威廉二世甚至尚未出生,俾斯麥也還沒帶領普魯士與同樣屬於德意志文化圈的諸國整併,成立我們如今所知的德國。當時,一些目光遠大的志士紛紛出頭,他們大多是軍人、政治經濟學專家、工業家,從鄂圖曼蘇丹麾下衰頹帝國裡人煙稀少的地區,看見了自己的願景或能成真,自己的問題也許可以獲得解答。從那時開始,向東擴張的魔咒就降臨德意志民族,帶來災難般的後果,如同我們將在本書中所見。(譯按:某種程度上,後來第三帝國的希特勒也是執行東進政策,只不過他選擇的東進目標是波蘭,以及後來的蘇聯。當然,這一樣也為德國帶來大災難——但他自己其實是奧地利人。)
內文選讀
第四章:德皇威廉二世的聖戰
德國國內有許多人相當熱衷於威廉二世的偉大計劃,非常支持德皇煽動東方各部落及民族,共同對抗德國的敵人。在這些鷹派人士之中,最積極的當屬著名的東方學者馬克斯・馮・歐本海默,且當初就是他先提出了這個構想。數年以前,戰爭尚未開打之時,歐本海默在開羅透過外交工作掩護,替外交部的長官準備了一份秘密備忘錄,裡頭寫著德國軍隊或許能在戰時操控伊斯蘭武裝分子,並會帶來「莫大的效果」。有證據顯示這的確激發了威廉二世的靈感。毫無疑問的是,戰爭爆發時,柏林當局也找來了歐本海默,要他準備一個周全的計畫,說明如何對協約國發動恐怖行動,尤其是針對英國。
另一位支持德國將聖戰納入核心策略之中的倡議者則是赫爾穆特・馮・毛奇將軍,他是當時德國的參謀總長。他的伯父是曾擔任普魯士陸軍參謀長達三十年之久的老毛奇,名聲顯赫的老毛奇早在七十年還只是個上尉時就已經注意到,德國能在東方找到無限的機會。(譯按:老毛奇[Moltke the Younger]與小毛奇[Moltke the Younger]的名字很像,但全名不同,前者是Helmuth Karl Bernhard Graf von Moltke,後者則為Helmuth Johann Ludwig von Moltke,兩者相差四十八歲。)現在,毛奇將軍聲稱,德國可以利用「伊斯蘭狂熱主義」,在印度和高加索地區煽動暴力起義,以此打擊英國和俄國。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也替毛奇的主張背書,這位著名的探險家非常討厭英國和俄國,因此將自己對於東方的了解和在當地的經驗全部傳授給德國,任憑威廉二世自由運用。
德國另一位全心支持威廉二世野心的重要人物則是普魯士鋼鐵大亨奥古斯特・蒂森(August Thyssen),他非常渴望能看見印度和其出產的珍貴原物料脫離英國掌控。在戰爭剛開打時,蒂森發表了一份內容相當挑釁的備忘錄,說明由於德國的工業對自然資源有極大需求,因此德國必須永久併吞自然資源豐富的區域,包括盛產礦產和石油的高加索地區,且他主張德國可以穿越溫順的波斯,對印度發出「致命的一擊」。柏林大學土耳其歷史教授恩斯特・耶克(Ernst Jäckh)也是德國聖戰的擁護者之一。他是狂熱的擴張主義者,非常享受威廉二世對他的信任,不停鼓吹皇帝進行偉大的冒險,並保證東方的民族已經準備好要響應。
雖然有些軍隊高層對於耶克所言抱持懷疑的態度,但身為威廉二世親信的外交部卻是全力支持聖戰的策劃。先前提及的歐本海默和耶克為聖戰計畫的顧問,而主要負責人則是年輕時曾被派往東方擔任外交官的外交副大臣阿圖爾・齊默爾曼(Arthur Zimmermann),因此聖戰計畫也被稱為「齊默爾曼計畫」。(開戰兩年半之後,他升任為外交大臣。)德國駐君士坦丁堡大使康拉德・馮・旺根海姆也是聖戰計畫的要員,他的大使館建築相當宏偉,可以從高處眺望博斯普魯斯海峽的天際線,往東望去則是波斯、阿富汗和印度,因此這使館往後也成為德國發動聖戰的基地。
美國大使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多年之後回憶道,旺根海姆大使當初曾向他透露,「德國的最大目標就是煽動穆斯林世界。」摩根索表示,「當時,旺根海姆大使坐在辦公室,抽著一根巨大的黑色德國雪茄,向我坦承德國的策略就是煽動整個穆斯林世界起身對抗基督徒。」但是,旺根海姆也告訴摩根索,德國必須先設法讓當時還保持中立的土耳其加入德方,因為只有身為伊斯蘭哈里發的蘇丹有權發動聖戰。摩根索繼續寫道,因此,「威廉二世是否能成功統治世界,完全取決於旺根海姆的任務表現,」而任務內容就是確保土耳其會加入戰局,成為德國的盟友。此外,摩根索也表示,「旺根海姆相信,如果他成功達成此一任務,他多年來希望能成為德意志財政大臣的心願也就能夠實現。」
對於德國而言,發動聖戰的主要誘因之一是所費人力和金錢成本皆不高。只需要幾位積極的特務,再加上一些友好的親德部族,就能完成通常需要數個步兵兵團才能解決的任務。不過,要取得勝利,必須考慮周全,而德國人恰好非常擅長於制定計畫。在拉攏土耳其之後,德國當局必須找到適合的領導者,並針對特定任務進行訓練。由於齊默爾曼認為旺根海姆一定能成功將土耳其拉入戰局,這項工作也立即展開。雖然當時並沒有很多人知道,但齊默爾曼明白,在一九一四年八月二日,也就是德英雙方開戰的兩天前,旺根海姆與恩維爾帕夏率領的土耳其內閣親德派簽訂了秘密軍事同盟。雖然德國未能讓土耳其承諾加入德方並參戰,但也已經取得相當的進展。(譯按:帕夏[Pasha]是土耳其高官的頭銜,當時另外有兩位帕夏。)
事實上,德國當時並沒有想要催促土耳其加入戰局,因為歐洲的計畫才剛起步,且威廉二世的部下相信自己能迅速取得勝利,除非有任何意外,否則他們不需要土耳其的幫助。土耳其可以等到他們征服歐洲,準備好前進到東方之後再加入。另一方面,恩維爾同樣不希望土耳其必須立刻參戰。他需要三、四個月的時間來動員軍隊,讓人民先做好心理準備,因為土耳其人絕不會對這場戰爭抱有任何好感,他們長期以來都非常害怕俄國人覬覦自己的土地,尤其是君士坦丁堡和博斯普魯斯海峽等地方。況且,在克里米亞戰爭期間,許多英國人和法國人為了土耳其而犧牲,因此土耳其人大多都不討厭英、法兩國。再加上許多與德國人打過交道的土耳其人認為德國人太過專橫跋扈,如果一夕之間風雲變色,肯定會讓他們難以接受。
當時,英國造船廠正在為土耳其海軍製造兩艘軍艦,落成之後將會成為土耳其艦隊之中最為巨大且現代的艦艇,而費用是藉由公開呼籲後集結公眾募資而來。為了土耳其海軍的榮譽,以及為了對抗俄國的黑海艦隊,鄂圖曼帝國各層級的政府官員都接受了減薪。土耳其海軍已經啟程前往英國,準備接回軍艦,而在他們沿著博斯普魯斯海峽航行時,君士坦丁堡也特別將那些日子訂為「海軍週」,以歡迎新艦艇的到來。然而就在此時,英國海軍大臣溫斯頓・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突然宣布,要將兩艘土耳其新艦艇徵收為英國皇家海軍之用。諷刺的是,邱吉爾宣布的當天,德國和土耳其正好簽訂了秘密軍事同盟,雖然倫敦當局尚未發現兩國之間的協定,但這足以證明邱吉爾的決定非常正確。
新聞報導土耳其無法獲得新軍艦時,國內輿論既失望又憤怒。數千名將零用錢捐獻給船艦購買的中小學生上街遊行,抗議英國政府的行徑。雖然土耳其拿回了全部的款項,但隨後英國政府就發現了德國與土耳其的軍事同盟,因此英土兩國之間的關係來到史上最糟糕的狀況。對於恩維爾和親德派內閣而言,土耳其的輿論導向可說是老天給的大好機會,因為此刻土耳其民眾一定會欣然接受與德國之間的秘密條約。隨著國內輿情沸騰,恩維爾與他的親德同夥準備好要打出手上的王牌。
邱吉爾宣布徵用土耳其軍艦的一週後,德國巡洋艦格本號(Goeben)及布雷斯勞號(Breslau)受到英國海軍強力追擊,因此駛進博斯普魯斯海峽尋求庇護。而在後頭追捕的英軍艦隊則停留在土耳其水域之外,向當時仍是中立國的土耳其政府進行抗議。英國海軍要求土耳其依國際法拘留德國的船隻和船員,或是命令他們離開中立水域,自行面對英國皇家海軍。然而,土耳其的回應令英國震驚不已。土耳其宣布政府已經將這兩艘德國巡洋艦買下來,用以替代邱吉爾徵用的兩艘英製軍艦,且這兩艘德國巡洋艦立刻就冠上新的土耳其名字,德國船員也披上土耳其海軍制服、戴上氈帽。
這件事僅僅是個開頭,往後的一連串事件更是讓土耳其無可奈何地被拖進戰爭的泥淖。由於歐洲的計畫不如威廉二世手下原先預測的那麼順利,柏林當局認為是時候祭出東方的計策,但在土耳其內閣之中,還是有位高權重的成員認為土耳其應該要維持中立。旺根海姆和恩維爾已經等不及要將土耳其拉入德方,且當時溫和派的支持度正緩慢上升,因此兩人決定要採取激進的措施,讓溫和派不得不出手。
十月二十七日,戰爭開打後的兩個半月, 格本號和布雷斯勞號已重新命名為賽利姆蘇丹號(Sultan Selim)以及邁德里(Medilli)號,這兩艘巡洋艦帶著密封的命令,與蘇丹麾下其他海軍軍艦一起駛入黑海,他們徑直前往俄國奧德薩港(Odessa),在沒有宣戰的狀況下,開始發動砲擊,包括一艘俄國巡洋艦在內,土耳其的攻擊造成港口許多船隻沉沒、儲油槽起火。砲擊鄰近的俄國港口之後,蘇丹雇用的德國海軍將領就指揮軍艦回到位於博斯普魯斯海峽的土耳其基地。土耳其內閣溫和派非常震驚,海軍竟以他們的名義進行攻擊,其中四名立刻辭去了職務,而一手策劃整起行動的恩維爾則聲稱是俄國先行開火,但沒有任何人相信。雖然各方都要求恩維爾向俄國道歉,但一切都已經太遲了。俄國旋即向土耳其宣戰,並驅逐駐俄大使。此外,由於溫和派辭去內閣職務,親德派系從此完全掌控了土耳其的命運,恩維爾也毫無疑問成了國家的獨裁統治者。
十月三十日,英國和法國大使請求先行回國,並建議國民儘速離開土耳其,因為與土耳其交戰只是時間早晚問題。兩天後,英法駐土耳其大使將無法帶走的機密資料銷毀,搭上沿線只會經過中立國的火車離開君士坦丁堡,返回各自的母國。東方快車的終點站錫爾凱吉(Sirkeci)火車站陷入混亂,外國僑民都想儘快離開土耳其,因為據傳異教徒將會遭到大屠殺。當時,美國的摩根索大使協助英法兩國的撤僑工作,他還到車站送別兩國大使。後來,他寫道,「車站人滿為患,瀰漫既激動又恐懼的情緒。全副武裝的警察在那裡推著人潮向後,車站擠滿士兵、憲兵、外交官和土耳其官員,以及他們的行李,場面非常混亂。」人們心情暴躁,到處都有被打飛的帽子、撕破的衣服。摩根索大使還看到英國大使路易斯・馬勒爵士(Louis Mallet)「與一位多管閒事的土耳其人吵了起來,不過很快就吵贏了」,也看見法國大使「用力地搖晃一名土耳其警察」。
不是所有土耳其人都樂見於外國大使離去。許多人並不像恩維爾一樣盲目地崇尚德國,反而對未來感到不安,當中包括土耳其的大維齊爾,他一直以來都強烈反對土耳其參戰,更是不願加入德方。路易斯・馬勒爵士在前往車站、離開土耳其之前,還前往大維齊爾俯瞰金角灣(Golden Horn)的辦公室辭行。雖然大維齊爾名義上是整個國家權力最大、只需服從於蘇丹的宰相,但他和蘇丹如今都只是傀儡,恩維爾留下他們只是為了讓政權能夠體面一些。在最後,大維齊爾毫無保留地流著淚,懇求馬勒不要拋棄他和反對恩維爾的人們。絕望之中,他啜泣著用法語說:「不要走!」但局面已經無可挽回,四天之後,英國就對鄂圖曼帝國宣戰了。(未完)
一九一四年夏季,德皇威廉二世發現自己嚴重誤判形勢,無可避免要與英國決一死戰。他發誓將對英國展開一場聖戰,永久消滅英國在亞洲的勢力。威廉二世下達諭令:「面對英國這個令人作嘔、說謊成性且厚顏無恥的國家,我們的間諜和特務必須讓穆斯林世界的怒火燃燒得更加旺盛。」如果戰爭無法避免,那麽這就是他扳倒整個大英帝國的機會。他會聯合鄂圖曼帝國的人民、高加索人、波斯人和阿富汗人,共同摧毀英國遍佈世界的帝國利益。他們會引燃導火線,將緊張情勢推往這些地區中最重要、卻也最脆弱的印度。如果能從英國手上奪走印度,那麼由虛張聲勢的大英帝國所掌控的其他地區也會跟著分崩離析。威廉二世的顧問向他保證,印度早已累積許多不滿情緒,就像一桶火藥,只需要一把革命火炬就可以點燃。事態發展若真如此順利,威廉二世或許就能從他厭惡無比的表弟喬治五世手裡搶來印度和整個英國的廣袤財富。
自登基以來,威廉二世的願望一直都是要把德意志帝國打造成世界霸權,以武力取代英國全球守護者的地位。他打算透過經濟優勢和外交滲透等手段,以及陸軍和海軍的堅強實力來實現他遠大的抱負,而非直接向英國王室和敵人發起戰爭。有了德意志銀行(Deutsche Bank)作為堅實的後盾,威廉二世的外交官和工業家籌劃著,要將自己國家在政治和商業上的利益和影響力擴張至全世界。
不過,德國人將大部分心力都投注於東方。他們在衰亡的鄂圖曼帝國身上看到大好機會,而為了確保德意志帝國能奪得先機,他們不惜一切:當時鄂圖曼帝國的蘇丹因為凌虐轄內少數基督徒族群而激怒全歐洲,德國卻選擇與他交好。威廉二世決定,要讓衰弱的土耳其在柏林的控制下,成為德意志東進擴張權力和影響力的經濟與政治基地。然而,實際上他的計畫出了嚴重差錯,不只使歐洲陷入戰爭的深淵,更將世界上幾乎所有國家牽扯進來。
在這場戰爭中,德意志帝國如何在盟友土耳其的幫助下操縱伊斯蘭武裝分子?這就是我想透過本書首度揭露的精彩故事。威廉二世和他的鷹派顧問們試圖透過煽動聖戰,將英國勢力驅離印度,並將俄國人趕出高加索地區和中亞。這個策略既大膽又冒險,因為在現代戰爭中,尚未有發動伊斯蘭聖戰的先例。然而,誠如德國歷史學家費里茨・費雪(Fritz Fischer)所言,這不過是威廉二世自一八九○年代以來東進侵略政策的延續而已。普魯士曾經是個渺小的內陸國家,國土極為破碎,其他國家的國土穿插其中,因此領土各區相距甚遠。從那時開始,德意志便因首相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的政治手腕得以不斷擴張。而威廉二世相信,現在就是德意志在東方建立新帝國的絕佳機會。
這場於柏林策劃、在君士坦丁堡發動的聖戰是過去所謂「大競逐」(Great Game)更加邪惡的新版本。此一戰爭的參與者包括英國、威廉二世、鄂圖曼帝國蘇丹和沙皇情報機關,戰場從君士坦丁堡一路向西延伸至喀布爾、向東至喀什噶爾(Kashgar),甚至波及波斯、高加索地區和俄國控制的中亞。英屬印度和緬甸也未能倖免於難,柏林當局希望能藉由走私的武器和資金煽動當地的穆斯林、錫克人或印度教徒,掀起暴力革命。這場陰謀的魔爪甚至伸向亞洲以外的地區。柏林的遠大計畫中還包括美國的軍火商、作為軍事會合點的一座太平洋偏遠小島(在墨西哥外海),以及位於倫敦鬧區托特納姆宮路(Tottenham Court Road),讓刺客用來制定計畫、完善演練的左輪手槍射擊場。計畫中還包含滿載武器的帆船,數量足以掀起第二次印度兵變(Indian Mutiny),還有一箱箱以英國經典文學作品封面掩護,走私進入印度的革命文學書籍。
然而,聖戰的主要攻勢會從君士坦丁堡向東展開,穿越中立的波斯和阿富汗,通過山口,進入印度。也就是說,柏林首先必須取得波斯沙阿(Shah)和阿富汗埃米爾(Emir)的支持。如果能夠獲得他們的支持,就能由德國和土耳其軍官率領兩國的軍隊,以豐厚獎賞提升士氣,往印度攻去。如此一來,除了少數精挑細選的軍官和士官,德國幾乎不用為聖戰付出任何代價,所需要的只有承諾和黃金。承諾在戰爭結束後才須兌現,而大部分的黃金只要從英國人開設在波斯的多家銀行搬走就好。若能說服印度眾多的異議分子同時起義,那麼英國將面臨內憂和外患。此外,土耳其會試圖與高加索和中亞地區的穆斯林結盟,邀請他們加入土耳其和德國的聖戰行列。情報機構傳回來的消息相當樂觀,柏林和君士坦丁堡的戰略家們已能預見整個亞洲陷入火海,而他們在英俄兩國的敵人被大火所吞噬。
威廉二世並未信奉伊斯蘭教,身為異教徒他自然沒有權力號召穆斯林參與聖戰。要發動這場戰爭,需要的遠遠不只黃金、武器和戰後兌現的承諾。確實也只有鄂圖曼蘇丹本人,也就是伊斯蘭教的哈里發(Caliph),才有權下達如此重大的諭令。因此,無論對於土耳其人民的利益而言是好是壞,土耳其都必須與德國結盟。雖然有些諷刺,但威廉二世在戰前培植土耳其及其不受各國歡迎的君主,可說是相當有遠見的做法,也一如預期獲得了回報。戰爭爆發後的三個月內,土耳其與德意志帝國、奧匈帝國締下盟約,一週後蘇丹便開始呼籲各處的穆斯林群起反抗,「無論身在何方,」都要除掉所有壓迫他們的基督徒。
就如德國所計畫的一樣,首當其衝的便是在印度的英國人,因為英國人所統治的印度是全球穆斯林人口最多的穆斯林帝國。英王喬治五世統治的穆斯林人口甚至超越了鄂圖曼蘇丹,更是俄國和法國的數倍。再者,威廉二世並沒有穆斯林殖民地或人民,因此多年來他一直宣稱自己是全球穆斯林的保護者。此說法總是讓英國、俄國和法國非常惱怒。蘇丹的宣言無疑使得在印度的英國人和協約國各國人民都非常緊張,因為他們四周都是穆斯林,而現代從來沒有人發起過對抗歐洲勢力的聖戰,也沒有人知道事態會如何發展。
但即使對於德國而言,聖戰也會導致一個尷尬的處境,必須妥善解決,否則整個計畫都會泡湯。一定有許多穆斯林都會問,為什麼一個信奉基督宗教的政權會想要煽動、資助這場殺害基督徒同胞的聖戰?(譯按:德國人信奉天主教與新教[即臺灣所謂的基督教],兩者人口皆很多。)不過,威廉二世的顧問團中有許多傑出的東方專家和學者,他們已經準備好回應這個問題。東方的清真寺和市集開始出現傳言,聲稱德意志皇帝已經秘密皈依了伊斯蘭教。他現在自稱「哈吉」・威廉・穆罕默德(“Haji” Wilhelm Mohammed),甚至便衣微行前往麥加朝聖。(譯按:哈吉[Haji],原意為「朝覲者」,是伊斯蘭教中用以尊稱曾前往麥加朝靚,並完成「五功」之穆斯林,而所謂「五功」即:念[唸誦證詞]、禮[跪拜祈禱]、齋[齋戒]、課[捐獻施捨]、朝[至麥加朝聖]。)親德的穆斯林學者甚至聲稱,《古蘭經》的段落可以證明,是阿拉授命威廉二世去解放異教徒統治底下的穆斯林。後來更有消息傳出,德意志帝國的人民效仿他們的皇帝,全部皈依了伊斯蘭教。最後,再由情報人員釋出土耳其和德意志帝國已經取得勝利的虛假捷報,並歸功於土耳其和德國之間高尚正義的同盟。這一切都是為了讓德意志帝國在穆斯林心中擁有正當地位。
與此同時,柏林當局會挑選一些德國軍官前往東方執行任務,散播聖戰的消息,最終目標是讓戰爭之火延燒至英屬印度。他們會帶著無數的黃金、武器及煽動人心的文宣,從新一代「大競逐」的基地君士坦丁堡出發,悄悄潛入中立的波斯。當他們行經沙漠、穿越山脈前往阿富汗時,會向沿途部落和村莊散佈聖戰的消息,試著爭取當地人的支持。但在抵達阿富汗首都後,這群軍官的最重要任務才要開始:想辦法說服位高權重的埃米爾加入德意志同盟,並同意命令他麾下各部落的大軍一起攻打戒備鬆散的印阿邊境。同一時間,德意志帝國還會向德黑蘭的年輕沙阿施壓,試圖將沙阿與他的穆斯林臣民捲入聖戰。在印度方面,德國也會脅迫一些地位最高的王侯加入同盟,其中某些是獲得英國允許擁有私人軍隊的。執行任務的軍官們會帶著威廉二世親筆寫的信,以皮革精心包裝,準備送到目標人物手中。信中承諾,若這些人改變立場,德國就能提供他們想要的一切。
這就是我要說的故事。本書參考了那段歷史的參與者們所寫的回憶錄,以及秘密情報機關的報告。有鑑於「大競逐」在動盪不斷的地區從未真正終結,書中所講述的事件其實與時下局勢息息相關,尤其某些族群可能會害怕俄國和德國再次崛起,因此我的論述對他們來講別具意義。然而,最重要的其實是當年那些足智多謀的勇士們所經歷的事件。無論來自哪一陣營,他們身不由己,捲入各種陰謀中。我會儘可能透過他們的經歷與不幸進行敘事。
約翰・布肯(John Buchan)膾炙人口的諜報驚悚小說《綠斗篷》(Greenmantle)即是以德國這個巨大陰謀為主軸所撰寫,銷售量甚至更勝於他的《三十九步》(The Thirty-Nine Steps)。我在上一本書《帝國的野心:十九世紀英俄帝國中亞大競逐》中,揭露了吉卜林(Rudyard Kipling)經典間諜小說《基姆》(Kim)背後的真實故事,本書則與啟發布肯戰時暢銷作品《綠斗篷》的一連串奇特事件有關。事實上,讀者將會發現,《綠斗篷》裡面許多角色都有本書那些人物的影子。或許這一切沒什麼好令人訝異的,因為布肯自己當年就是情報工作的參與者,也有獲取機密報告的管道,可以知道當時德意志帝國對東方有何野心。布肯的朋友T・E・勞倫斯(T. E. Lawrence)在戰後如此評論:「《綠斗篷》裡面有不少情節都是真實事件。」(譯按:T・E・勞倫斯就是鼎鼎大名的「阿拉伯的勞倫斯」,也是具有軍方背景的情報人員。)
正因為有了這些人,「大競逐」鮮為人知的新篇章才能向前推進、充滿刺激。不過,要了解他們在波斯、阿富汗、高加索地區等戰場的經歷,必須先從故事的真正開頭說起。雖然威廉二世幾乎以救世主自居,狂熱推行著東進政策(Drang nach Osten,把德意志帝國往東方擴張),但他並不是第一個想出這個計畫的人。東進的概念要回溯到十九世紀中葉,當時威廉二世甚至尚未出生,俾斯麥也還沒帶領普魯士與同樣屬於德意志文化圈的諸國整併,成立我們如今所知的德國。當時,一些目光遠大的志士紛紛出頭,他們大多是軍人、政治經濟學專家、工業家,從鄂圖曼蘇丹麾下衰頹帝國裡人煙稀少的地區,看見了自己的願景或能成真,自己的問題也許可以獲得解答。從那時開始,向東擴張的魔咒就降臨德意志民族,帶來災難般的後果,如同我們將在本書中所見。(譯按:某種程度上,後來第三帝國的希特勒也是執行東進政策,只不過他選擇的東進目標是波蘭,以及後來的蘇聯。當然,這一樣也為德國帶來大災難——但他自己其實是奧地利人。)
內文選讀
第四章:德皇威廉二世的聖戰
德國國內有許多人相當熱衷於威廉二世的偉大計劃,非常支持德皇煽動東方各部落及民族,共同對抗德國的敵人。在這些鷹派人士之中,最積極的當屬著名的東方學者馬克斯・馮・歐本海默,且當初就是他先提出了這個構想。數年以前,戰爭尚未開打之時,歐本海默在開羅透過外交工作掩護,替外交部的長官準備了一份秘密備忘錄,裡頭寫著德國軍隊或許能在戰時操控伊斯蘭武裝分子,並會帶來「莫大的效果」。有證據顯示這的確激發了威廉二世的靈感。毫無疑問的是,戰爭爆發時,柏林當局也找來了歐本海默,要他準備一個周全的計畫,說明如何對協約國發動恐怖行動,尤其是針對英國。
另一位支持德國將聖戰納入核心策略之中的倡議者則是赫爾穆特・馮・毛奇將軍,他是當時德國的參謀總長。他的伯父是曾擔任普魯士陸軍參謀長達三十年之久的老毛奇,名聲顯赫的老毛奇早在七十年還只是個上尉時就已經注意到,德國能在東方找到無限的機會。(譯按:老毛奇[Moltke the Younger]與小毛奇[Moltke the Younger]的名字很像,但全名不同,前者是Helmuth Karl Bernhard Graf von Moltke,後者則為Helmuth Johann Ludwig von Moltke,兩者相差四十八歲。)現在,毛奇將軍聲稱,德國可以利用「伊斯蘭狂熱主義」,在印度和高加索地區煽動暴力起義,以此打擊英國和俄國。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也替毛奇的主張背書,這位著名的探險家非常討厭英國和俄國,因此將自己對於東方的了解和在當地的經驗全部傳授給德國,任憑威廉二世自由運用。
德國另一位全心支持威廉二世野心的重要人物則是普魯士鋼鐵大亨奥古斯特・蒂森(August Thyssen),他非常渴望能看見印度和其出產的珍貴原物料脫離英國掌控。在戰爭剛開打時,蒂森發表了一份內容相當挑釁的備忘錄,說明由於德國的工業對自然資源有極大需求,因此德國必須永久併吞自然資源豐富的區域,包括盛產礦產和石油的高加索地區,且他主張德國可以穿越溫順的波斯,對印度發出「致命的一擊」。柏林大學土耳其歷史教授恩斯特・耶克(Ernst Jäckh)也是德國聖戰的擁護者之一。他是狂熱的擴張主義者,非常享受威廉二世對他的信任,不停鼓吹皇帝進行偉大的冒險,並保證東方的民族已經準備好要響應。
雖然有些軍隊高層對於耶克所言抱持懷疑的態度,但身為威廉二世親信的外交部卻是全力支持聖戰的策劃。先前提及的歐本海默和耶克為聖戰計畫的顧問,而主要負責人則是年輕時曾被派往東方擔任外交官的外交副大臣阿圖爾・齊默爾曼(Arthur Zimmermann),因此聖戰計畫也被稱為「齊默爾曼計畫」。(開戰兩年半之後,他升任為外交大臣。)德國駐君士坦丁堡大使康拉德・馮・旺根海姆也是聖戰計畫的要員,他的大使館建築相當宏偉,可以從高處眺望博斯普魯斯海峽的天際線,往東望去則是波斯、阿富汗和印度,因此這使館往後也成為德國發動聖戰的基地。
美國大使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多年之後回憶道,旺根海姆大使當初曾向他透露,「德國的最大目標就是煽動穆斯林世界。」摩根索表示,「當時,旺根海姆大使坐在辦公室,抽著一根巨大的黑色德國雪茄,向我坦承德國的策略就是煽動整個穆斯林世界起身對抗基督徒。」但是,旺根海姆也告訴摩根索,德國必須先設法讓當時還保持中立的土耳其加入德方,因為只有身為伊斯蘭哈里發的蘇丹有權發動聖戰。摩根索繼續寫道,因此,「威廉二世是否能成功統治世界,完全取決於旺根海姆的任務表現,」而任務內容就是確保土耳其會加入戰局,成為德國的盟友。此外,摩根索也表示,「旺根海姆相信,如果他成功達成此一任務,他多年來希望能成為德意志財政大臣的心願也就能夠實現。」
對於德國而言,發動聖戰的主要誘因之一是所費人力和金錢成本皆不高。只需要幾位積極的特務,再加上一些友好的親德部族,就能完成通常需要數個步兵兵團才能解決的任務。不過,要取得勝利,必須考慮周全,而德國人恰好非常擅長於制定計畫。在拉攏土耳其之後,德國當局必須找到適合的領導者,並針對特定任務進行訓練。由於齊默爾曼認為旺根海姆一定能成功將土耳其拉入戰局,這項工作也立即展開。雖然當時並沒有很多人知道,但齊默爾曼明白,在一九一四年八月二日,也就是德英雙方開戰的兩天前,旺根海姆與恩維爾帕夏率領的土耳其內閣親德派簽訂了秘密軍事同盟。雖然德國未能讓土耳其承諾加入德方並參戰,但也已經取得相當的進展。(譯按:帕夏[Pasha]是土耳其高官的頭銜,當時另外有兩位帕夏。)
事實上,德國當時並沒有想要催促土耳其加入戰局,因為歐洲的計畫才剛起步,且威廉二世的部下相信自己能迅速取得勝利,除非有任何意外,否則他們不需要土耳其的幫助。土耳其可以等到他們征服歐洲,準備好前進到東方之後再加入。另一方面,恩維爾同樣不希望土耳其必須立刻參戰。他需要三、四個月的時間來動員軍隊,讓人民先做好心理準備,因為土耳其人絕不會對這場戰爭抱有任何好感,他們長期以來都非常害怕俄國人覬覦自己的土地,尤其是君士坦丁堡和博斯普魯斯海峽等地方。況且,在克里米亞戰爭期間,許多英國人和法國人為了土耳其而犧牲,因此土耳其人大多都不討厭英、法兩國。再加上許多與德國人打過交道的土耳其人認為德國人太過專橫跋扈,如果一夕之間風雲變色,肯定會讓他們難以接受。
當時,英國造船廠正在為土耳其海軍製造兩艘軍艦,落成之後將會成為土耳其艦隊之中最為巨大且現代的艦艇,而費用是藉由公開呼籲後集結公眾募資而來。為了土耳其海軍的榮譽,以及為了對抗俄國的黑海艦隊,鄂圖曼帝國各層級的政府官員都接受了減薪。土耳其海軍已經啟程前往英國,準備接回軍艦,而在他們沿著博斯普魯斯海峽航行時,君士坦丁堡也特別將那些日子訂為「海軍週」,以歡迎新艦艇的到來。然而就在此時,英國海軍大臣溫斯頓・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突然宣布,要將兩艘土耳其新艦艇徵收為英國皇家海軍之用。諷刺的是,邱吉爾宣布的當天,德國和土耳其正好簽訂了秘密軍事同盟,雖然倫敦當局尚未發現兩國之間的協定,但這足以證明邱吉爾的決定非常正確。
新聞報導土耳其無法獲得新軍艦時,國內輿論既失望又憤怒。數千名將零用錢捐獻給船艦購買的中小學生上街遊行,抗議英國政府的行徑。雖然土耳其拿回了全部的款項,但隨後英國政府就發現了德國與土耳其的軍事同盟,因此英土兩國之間的關係來到史上最糟糕的狀況。對於恩維爾和親德派內閣而言,土耳其的輿論導向可說是老天給的大好機會,因為此刻土耳其民眾一定會欣然接受與德國之間的秘密條約。隨著國內輿情沸騰,恩維爾與他的親德同夥準備好要打出手上的王牌。
邱吉爾宣布徵用土耳其軍艦的一週後,德國巡洋艦格本號(Goeben)及布雷斯勞號(Breslau)受到英國海軍強力追擊,因此駛進博斯普魯斯海峽尋求庇護。而在後頭追捕的英軍艦隊則停留在土耳其水域之外,向當時仍是中立國的土耳其政府進行抗議。英國海軍要求土耳其依國際法拘留德國的船隻和船員,或是命令他們離開中立水域,自行面對英國皇家海軍。然而,土耳其的回應令英國震驚不已。土耳其宣布政府已經將這兩艘德國巡洋艦買下來,用以替代邱吉爾徵用的兩艘英製軍艦,且這兩艘德國巡洋艦立刻就冠上新的土耳其名字,德國船員也披上土耳其海軍制服、戴上氈帽。
這件事僅僅是個開頭,往後的一連串事件更是讓土耳其無可奈何地被拖進戰爭的泥淖。由於歐洲的計畫不如威廉二世手下原先預測的那麼順利,柏林當局認為是時候祭出東方的計策,但在土耳其內閣之中,還是有位高權重的成員認為土耳其應該要維持中立。旺根海姆和恩維爾已經等不及要將土耳其拉入德方,且當時溫和派的支持度正緩慢上升,因此兩人決定要採取激進的措施,讓溫和派不得不出手。
十月二十七日,戰爭開打後的兩個半月, 格本號和布雷斯勞號已重新命名為賽利姆蘇丹號(Sultan Selim)以及邁德里(Medilli)號,這兩艘巡洋艦帶著密封的命令,與蘇丹麾下其他海軍軍艦一起駛入黑海,他們徑直前往俄國奧德薩港(Odessa),在沒有宣戰的狀況下,開始發動砲擊,包括一艘俄國巡洋艦在內,土耳其的攻擊造成港口許多船隻沉沒、儲油槽起火。砲擊鄰近的俄國港口之後,蘇丹雇用的德國海軍將領就指揮軍艦回到位於博斯普魯斯海峽的土耳其基地。土耳其內閣溫和派非常震驚,海軍竟以他們的名義進行攻擊,其中四名立刻辭去了職務,而一手策劃整起行動的恩維爾則聲稱是俄國先行開火,但沒有任何人相信。雖然各方都要求恩維爾向俄國道歉,但一切都已經太遲了。俄國旋即向土耳其宣戰,並驅逐駐俄大使。此外,由於溫和派辭去內閣職務,親德派系從此完全掌控了土耳其的命運,恩維爾也毫無疑問成了國家的獨裁統治者。
十月三十日,英國和法國大使請求先行回國,並建議國民儘速離開土耳其,因為與土耳其交戰只是時間早晚問題。兩天後,英法駐土耳其大使將無法帶走的機密資料銷毀,搭上沿線只會經過中立國的火車離開君士坦丁堡,返回各自的母國。東方快車的終點站錫爾凱吉(Sirkeci)火車站陷入混亂,外國僑民都想儘快離開土耳其,因為據傳異教徒將會遭到大屠殺。當時,美國的摩根索大使協助英法兩國的撤僑工作,他還到車站送別兩國大使。後來,他寫道,「車站人滿為患,瀰漫既激動又恐懼的情緒。全副武裝的警察在那裡推著人潮向後,車站擠滿士兵、憲兵、外交官和土耳其官員,以及他們的行李,場面非常混亂。」人們心情暴躁,到處都有被打飛的帽子、撕破的衣服。摩根索大使還看到英國大使路易斯・馬勒爵士(Louis Mallet)「與一位多管閒事的土耳其人吵了起來,不過很快就吵贏了」,也看見法國大使「用力地搖晃一名土耳其警察」。
不是所有土耳其人都樂見於外國大使離去。許多人並不像恩維爾一樣盲目地崇尚德國,反而對未來感到不安,當中包括土耳其的大維齊爾,他一直以來都強烈反對土耳其參戰,更是不願加入德方。路易斯・馬勒爵士在前往車站、離開土耳其之前,還前往大維齊爾俯瞰金角灣(Golden Horn)的辦公室辭行。雖然大維齊爾名義上是整個國家權力最大、只需服從於蘇丹的宰相,但他和蘇丹如今都只是傀儡,恩維爾留下他們只是為了讓政權能夠體面一些。在最後,大維齊爾毫無保留地流著淚,懇求馬勒不要拋棄他和反對恩維爾的人們。絕望之中,他啜泣著用法語說:「不要走!」但局面已經無可挽回,四天之後,英國就對鄂圖曼帝國宣戰了。(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