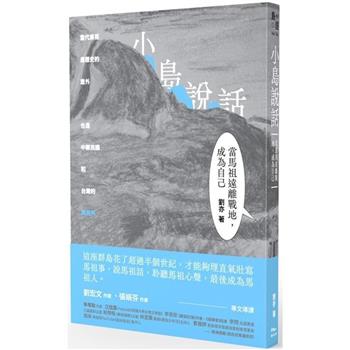〈台灣,是群島的國度〉
一九九二年,金門、馬祖解嚴,揮別戰地政務時代,台灣文學界大佬葉石濤在金門作家黃克全的小說座談會上說:「金門不屬於臺灣的一部分。將來當臺灣人走向自決之路時,金門應該不包括在內。縱然,金門全體人民願意與臺灣站在一起,但是其地理位置太靠近大陸了,其未來命運將是如何?」葉石濤一語道破金門和金門文學的尷尬處境:就算金門人願意和台灣站在一起,但因它靠近大陸/中國,仍然難逃其地緣位置帶來的強大引力。「金門應該不包括在內」一定程度上也代表台灣人對金馬的態度:不爭取亦不承認金門(與馬祖)是當下的共同體,以及未來以「台灣為主體的新國家」的一部分。
然而果真如此嗎?或者還能有其它想像?三十年後,台灣文學界終於回過頭來探問「離島問題」,二〇二一年台灣文學學會年度研討會以「台灣大文學史的建構與想像」為題,直言在討論台灣文學時多半集中台灣本島,我們是否能夠更宏觀的想像一部擴及金門、澎湖、馬祖乃至其他離島的「台灣大文學史」?學界開始出現「更新文學史」的呼聲 。
我將在這本書裡展示:隔著海峽,從過去素未謀面、到現在也因了解不深而難免猜忌的台灣和馬祖,其實在文學上的交織早已絡繹於途。馬祖的書寫過去不曾被系統性的指認出來,如今我們發現它早就坐落在台灣文學的星系之中。雖然它體積不大,引力卻不小,讓台灣文學裡的幾個重要概念:「軍中文學」、「懷鄉文學」與「地方文學」,都被牽引著稍稍偏離了本來的航道,發生了一點點斗轉星移。「一九四九」後大遷徙的寫作者們在東亞這一片小小的海域畫下複雜的軌跡,有的雄心壯志,有的萬般無奈。但連綴起來,就幾乎可以伸手去指:那是過去半世紀,台灣、馬祖、甚至中國的交相作用下,作家以生命歷程繪製出的群島圖。
如果不是一九四九,馬祖不會跟著中華民國的統治,匯入「中華民國台灣」,和中華民國政權、和台灣「本島」綁定。如果不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軍事對峙,邊疆小島不會成為戰地前線,得到黨國銳意經營、大力挹注。所以對馬祖而言,它的現代化和國家化是同時開始的。雖然馬祖常和金門並稱,有近乎難兄難弟的命運,但它們真的天南地北,毫不相同。
金門說的是閩南語,和台灣腔調有別,但大致能通;馬祖說的是閩東語,台灣朋友說乍聽像客家話,但完全不互通。金門的開發史遠早於台灣,當然更早於馬祖,所以有悠久的宗族組織,金門人注重功名、科舉,出了一堆儒家知識份子;馬祖不是,馬祖相較沒有長期、穩固的歷史,和儒家核心的士大夫相較,馬祖更以海盜的歷史自豪。雖然經過黨國的恐海教育,現在馬祖血液析出的體脂肪可能比海水鹽分更高了。
前現代的馬祖被哈佛學者宋怡明(Michael Szonyi)稱為「沒有社會的社會」,因為它在歷史上一直是座隨季風遷徙的臨時漁場和貿易小島,少有定居住民。直到國軍登陸,開始封鎖海洋。因此宋怡明稱:「馬祖本身是脫胎自軍事化時期的產物。」或謂「軍事現代性」。討論日治時期台灣史時,「殖民現代性」是一個關鍵詞,它表達一種難以評斷的曖昧:雖然日本統治帶入了醫療衛生、現代教育、標準時間制等「現代」產物,應該給予正評,但實際上這些「現代」事物並不是為了台灣人生活舒適,而是方便殖民統治。因此「現代」的好和「殖民」的惡,是糾結在一起的。
馬祖也是如此。軍方的統治固然帶給馬祖教育、醫療、經濟等發展,但其初衷並非帶給馬祖福祉,而是便於實施軍事統治。然而中華民國統治馬祖並不算殖民,因此「軍事現代性」不只言簡意賅說明了馬祖有別於台灣的獨特性,也表達了馬祖對戰地時代統治者的難以評價。
鳥瞰台灣周邊島嶼,雖然各擁脈絡,但仍有共相可尋。例如不只綠島,蘭嶼也在戒嚴時期被當成重刑犯、政治犯的監獄,台灣的海洋「兩岸」——台灣海峽與太平洋,因各自的地緣位置,受到戰後中華民國分派了不同的國家任務。金門、馬祖靠近「匪區」而被指派為「前線」;太平洋側的綠島、蘭嶼則成為國家的「垃圾桶」,丟棄衍生物、副產品——從社會的副產品罪犯,到能源的副產品核廢料。邏輯一以貫之,形成一個環繞著中華民國/台灣本島的「犧牲的體系」,為了本島的安全和繁榮服務。巧合的是,日本學者高橋哲哉曾在《犧牲的體系》中指出,服務於戰後東京之繁榮的福島、沖繩,正好是被轉嫁了能源與國家安全責任之處,可見現代國家的責任轉嫁是有共相的:「地方」為中央服務,服務項目是能源與軍事的負擔。無獨有偶,身為島嶼,馬祖、金門也曾經是核廢料的貯存候選地。
金馬的複雜還不只如此。一般談到「戰後」,盤桓在「中華民國台灣」上空的戰爭時間有兩股。其一是台灣史觀的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台灣改受中華民國統治;其二是中華民國史觀的一九四九年,國共戰敗,政府遷台。然而金馬其實存有第三股「戰後」時間,即解除戰地政務的一九九二年。至此之前,法律上金馬是戰地,受各種禁制。實際上的砲戰也直到一九七八年底才歇。論及台灣四大、乃至五大族群(原住民、閩南人、客家人、外省人,近年加上新住民),金馬人卡在各分類的中間,無處落座——金馬確實是「外省」(福建省),但和一九四九前後渡海來台那波外省人的脈絡大相逕庭。明明稱「台澎金馬」彷彿占了國土的二分之一,但其實是通天入地的「被缺席」。
對於馬祖而言,台灣和中華民國雖然未必全等,但兩者幾乎同步被馬祖認識——馬祖認識的「台灣」,已經是中華民國中央政府所在地的台灣。對馬祖人而言,無論中華民國和台灣都是外來或外在於馬祖的,兩者不一定有台灣人認知的這麼大不同。可能直到一九九〇年代,台灣本島才被以新興的政治力量——「台獨」之名,被馬祖重新認識,使馬祖意識到台馬有別。更令人五味雜陳的是,這個「新台灣」往往是來「切割」馬祖的。正如馬祖尷尬的地緣位置,它既陷落在中國與台灣「兩岸」,又同時受到中華民國和台灣兩股史觀的沖激,置身多重的夾縫中。
我曾經有一個版本的論文計畫,是將琉球(沖繩)和馬祖並置。二戰時死傷慘重的沖繩戰,可以比擬台澎金馬唯一發生過登陸戰的金門古寧頭;而二戰後迅速進入冷戰,沖繩為日本本土扛起基地化的任務,也如同金馬為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所承受的命運。不過礙於語言的次元之壁與沖繩學的汗牛充棟,我自認不足而放棄。不過沖繩經驗與省思仍值得對話,我甚至認為不具軍事化、基地化經驗,反而身為金馬軍事化之受益者的台灣,相較之下,是很難理解沖繩的。
進入現代以來,島嶼不可免俗被納編進以大陸國家為延長的政權之中,有學者語重心長:「現代國家權力粗暴地基於進步主義,將所有地方性的東西加以扼殺。」十九世紀的廢藩置縣、琉球處分之於沖繩如此,二十世紀的「一九四九」、戰地政務之於馬祖也莫不如此。
出身琉球西表島的作家崎山多美在一次來台演講就提到,對她而言沖繩(本島)和巴黎都像是異國。島嶼的成長經驗,讓她對「國家」的認知相當不同——「國界線」、「國籍」是有如殖民地的概念;對於日語則有「違和的身體感」。她認為也許正是在西表島生活、長大的身體,自然地抗拒「我是哪國人」,所以形成了傾軋、扞格的感受。在本書中,我們也能見到馬祖列島作為地方,面對現代國家強行刺入的張皇失措。
大江健三郎(一九三五-二〇二三)遊歷沖繩後,認為「日本屬於沖繩」(日本は沖縄に属する)。學者吳叡人在《受困的思想:臺灣重返世界》中對此的詮釋是:日本的自立建立在沖繩的犧牲之上。也就是說,沖繩為日本承擔苦難、付出代價,日本在道德上對沖繩有所虧欠(morally indebted)。從沖繩和日本的案例,除了能認識到「加害/被害」關係的重層性——以廣島核爆為代表,日本擁有「受害」經驗,但面對沖繩時,日本則是無庸置疑的加害者。延續著這樣的說法,台灣同樣可能屬於馬祖——不只在文化的互為涵融,更是政治道德的層次上。在大江健三郎的意義上。
日本小說家島尾敏雄(一九一七-一九八六)用拉丁語自創語彙「日本尼西亞」,也就是「日本-群島」。同一個構詞原則的「台灣群島」則是來自吳音寧在臉書粉絲專頁的說法:「我說的台灣島嶼,包括了澎湖、金門、馬祖、小琉球、綠島、蘭嶼等地。我們的台灣,是群島的國度。」「日本尼西亞」朝海洋與島群開放,「台灣群島」也擴張台灣,解除「本土」的狹隘性。所謂「本土」其實是多元,主體並立,秩序繽紛,就如同法律史學家王泰升所言:「台灣共同體內部是複雜的,只有看到複雜性,才能夠相互尊重。」
(本文摘自:第一章「開往家鄉的慢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