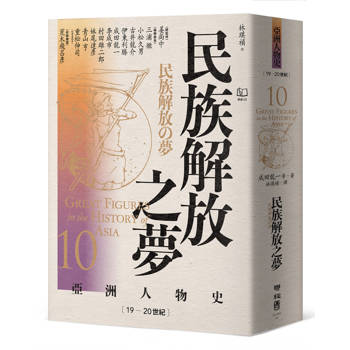內文選摘
第十五章 「國民作家」與現代的悲劇
姜尚中
序言
還在世時,夏目漱石似乎曾針對某事說過:「大概不會那麼順利吧。」這種帶著懷疑的,對什麼事都以冷淡眼光看待的發言,充滿夏目漱石的風格。之所以「因果」與「因緣」這類詞語會點綴在漱石的作品中,肯定也與這種態度有關。可說這種類似《草枕》般的「低徊趣味」構成了部分漱石的精神世界。關於這點,政治學家丸山真男認為這種「非國家的」、「非政治的」、「東洋式自由」的韜晦之道,與與國木田獨步的「山林存自由」屬於同一相位。
然而,若把漱石視為一個球體,那麼丸山的指摘僅提及這個球體的半球。因為,即便漱石追求陶淵明式的漢詩世界,也就是將其視為逃離現實世界的唯一「避難所」,但同時他也通過作品世界一直關注「現代」(contemporary)。
留下關於大逆事件(一九一〇~一一)的〈彷彿〉(かのように),以及〈打嗝〉(吃逆)、〈田樂豆腐〉、〈鎚一下〉等作品,經常被事件觸發並訴諸言論自由的森鷗外,在事件後雖然寫出堪稱日本文學最高峰的《澀江抽齋》與《伊澤蘭軒》,但他也不得不在這類史傳式文學中韜光養晦,明顯呈現出與同一時代持續相同堅持的漱石特徵。
確實不能否認,這種現代性具備受到因知識水準平準化而造成文藝消費者抬頭的新聞小說廣大讀者群歡迎的一面。然而不僅止於此,夏目漱石還一貫堅持「此時」與「此地」,通過書寫生活於同時代的登場人物的行動與心理糾葛,成功刻劃出二十世紀日本社會的原型。
漱石在大逆事件發生的翌年見到通過官方文藝委員會選出森鷗外、上田萬年、幸田露伴等擔任文藝委員一事,便嗅出國家將進行言論統制與檢閱的預兆,這也是因為漱石一直把文藝的競技場定位在「現代」之故。聚焦於這種現實的面向,本章還將關注三位與漱石同樣,較其他思想家更具先見,及早看出近代危機的人物:二葉亭四迷、幸德秋水與石川啄木。
那麼,對漱石而言貫穿「現代性」的命運紅繩是什麼?關於這點,一言以蔽之就是「悲劇性」。在最初的新聞小說《虞美人草》(一九〇七)中不怕犯過度單純化之大不韙,刻意道學家式地斷言「悲劇比喜劇更偉大」,這大概也是因為漱石自身也將該存在視為一種「悲劇」吧。
夏目漱石(一八六七~一九一六)
缺失「父性」的權威
夏目金之助,亦即日後的漱石,一八六七年(慶應三年)生於江戶牛込馬場下橫町(今日的新宿區喜久井町),是「名主」 的么子。他出生時父親已經五十歲,母親超過四十歲,而且在他之前還有兩個異母姐姐與三個同母哥哥,因此金之助的出生並不被雙親所喜。加上時代也發生劇變,隔年的一九六八年日本年號由慶應改為明治,名主制度廢除,夏目家也受到時代巨浪的衝擊。
之後金之助被送去當寄養的孩子,但旋即又被帶回,之後又成了養子,但因養父母不和,八年多之後結束了他的養子生涯回歸夏目家。這位多愁善感的少年被當作「麻煩人物」來處置,這種感受也成為漱石終身的內心陰影。這段經歷被詳細寫在可稱為自傳小說的《道草》(一九一五)中,此外在書寫晚年心境的《玻璃門內》(硝子戸の中,一九一五)也有赤裸裸的描寫。遭受親生父親「嚴苛對待」的記憶、出生的秘密,以及當他懂事後被雙親告知的事情等,可說是在描述如何靠一己之力一直背負悲慘「命運」帶來的精神創傷。
但如格蒙德・佛洛伊德所言,兒子通過納入父親這種「權威」來控制自身形成「超自我」,如果這是道德的起源,那麼對漱石而言也是憎恨的對象,因而難以簡單歸納為理想的「權威」。在某種意義上,對少年金之助來說自己心中並不存在應當納入的「父性」權威,反過來說,因為這種不存在導致的不安,也總是纏繞在金之助的內心。
此點與漱石如何看待成為近代國家的明治日本這個根本性問題,有著必然的連結。因為漱石無法把家父長的父親權威與可說是國家家長的天皇絕對權威無縫連接,也就是他很難把自己與明治日本及該時代的深刻糾葛同一化。對他而言這毋寧是有距離感的,且終身對此抱持著愛恨交織的二律背反心結。這在漱石小說世界中塑造那些惱於與日本近代化及對該時代有距離感的主人公們性格時造成決定性的影響。為何漱石主要都以都市中間階層或更上層的知識分子為主角,聚焦於他們的挫折、蹉跌、失敗的悲劇性模樣?因為其中投射的就是對明治這個近代國家的「末流」(epigone,有亞流、模仿者之意)意識趕到煩惱,既無法背過身去,也無法加以屈從,就如此吊在半空中的知識分子悲劇身影。
如果,缺乏作為內在規範原型的「父性」權威,而青少年時期的金之助最切實的課題便是填補這個空白,那麼之後漱石達到之「自我本位」境地,應該就是成人後的金之助面對此番糾葛的回答。漱石強烈的獨立心與反權威主義的心理狀態,應當被視為從自己出生與該時代悲劇性的糾葛發展而來。
如「逃亡者」般的生存
將金之助從這種不幸的生涯中拯救出來,之後獲得東京帝國大學與第一高等學校這種最高級品牌職位給予他的「僥倖」,便是學歷與橫跨公私官僚體制帶來的豐富人際網絡。
因複雜的家庭背景而換過三所小學的少年金之助,之後於一八七九年進入東京府第一中學正則科,之後雖短暫進入二松學舍但依舊不斷轉學,到一八九三年從帝國大學文學科大學英文科畢業準備進入研究所為止,多與擔任明治國家樞要職位的多元人士加深交流,這也為日後漱石能擔任最高學府教師備妥機會。這種條件意味著漱石與那些不隸屬任何公私官僚體制,在某種意義上算是自由人士但又帶著某種可疑形象的「文人」具備不同的生涯職歷。
亦即,伴隨漱石擔任明治國家教育行政的末端工作,就任最高學府的教職,之後更變身成為出版資本主義的代表並持續成長的《朝日新聞》「專屬作家」,至此為止他都以「組織中菁英」的「組織人」生活。在這層意義上,雖說在「組織人」身分上不及以軍醫站上最高地位的鷗外,但漱石也絕非明治國家及其社會的「局外人」知識分子,毋寧該說更接近內部者。大學預備門時代的朋友,如佐藤文熊日後成為警察官僚,擔任關東都督府警視總長等職位,其生涯摯友中村是公則是南滿洲鐵道(滿鐵)總裁,之後更是成為東京市長的一號人物。此外,進入帝國大學文科大學之後交往加深的狩野亨吉還是一高校長,日後更成為新成立的京都帝國大學文科大學校長。
在貫徹旺盛的獨立心與反權威主義下,歸屬公私官僚體制的「組織人」。置身此種相對立場中的漱石,加上自己的出生、家族關係以及與時代的糾葛,可說他是具備多層次與多面向矛盾心理(ambivalence)的作家。漱石之所以罹患神經症,大概也是起於此種矛盾心理。
漱石看穿這種神經症的矛盾心理與近代日本的「個人主義的世道」(パーソナリチーの世の中)相互共通。這是指在平等原則下各自自我覺醒,彼此主張相互對等立場並激烈競爭的世界。這種自主、獨立的原則一旦潰堤氾濫於社會時,則自我與他者、個人與共同體便將相互乖離,並維持此種狀態,無法填埋彼此間的鴻溝。漱石即稱抱持這種矛盾的社會為「個人主義的世道」。這是「一個盡量擴張自己,在不斷膨脹爆裂中過活的世道」,「妻子是妻子,丈夫是丈夫,截然不同,有如水與油」,意即彼此相背而生。
從《三四郎》至未完成的遺作《明暗》,漱石描繪的親子、兄弟、親戚、男女、夫婦、朋友關係等,沒有任何一人逃出「個人主義的世道」中的矛盾。即便擁有高學歷卻不見容於社會的「高等遊民」式知識分子們,他們內心生成的深刻陰影,可說宛如與漱石自身的神經症內心糾葛形成雙重曝光的描寫。
實際上大學畢業(一八九三)後的漱石,一直惱於神經衰弱症,他一直希望能從中「悟脫」,故從一八九四年底至隔年初為止進入圓覺寺參禪,下山之後突然在一八九五年四月隻身前往四國松山愛媛縣尋常中學校擔任英語教師。隔年的一八九六年四月在帝大以來的摯友菅虎雄的建議下轉任熊本的第五高等學校。為何漱石會前往松山,甚至是離帝都更遠的熊本赴任,其真正理由尚無定論,不過在熊本逗留長達四年三個月,這段期間與妻子鏡子結婚,長女筆子出生,必定讓壯年期的漱石形成了一家之主的意識。這對成長時背負「與家人之間的不幸」的漱石而言,他的家庭不僅是闔家團圓的場所,同時也是籌措生計與夫妻出現矛盾的場所。
如此看來,漱石這位作家可說是在轉型期的近代日本中懷抱矛盾的「境界人」(marginal man)。他雖身處多個文化或規範的多重錯位與糾葛中,但並不具被完全歸屬哪一個領域的意識,這意味著他過著宛如是「流亡者」般的生活。漱石之所以成為「搬家狂」,與此有絕對的關係。他在熊本至少搬家達六次,在倫敦遊學時大概也反覆搬家相同次數,恐怕近代日本中再也找不出如此頻繁搬家的作家。而這種「移動」,正是跨空間的越境,且不僅於此,同時還意味著時間上的越境。這也刻畫出在一刻也無法維持穩定,不斷反覆變化的近代時空中,不得不自行從中尋找棲留點的時代宿命。
何況,在日本的狀況是,連問題本身都是多重的。因為日本不得不外發式地「模仿」近代,在這個意義上大概也就不得不成為「理想中的西洋」的「奴隸」,隨之而來的就是最終「拼了命地努力成為奴隸」,最終還把此事當作「進步」。如果把英語學當作終生事業的一介教師夏目金之助也「拚了命地努力成為奴隸」,那麼那位甚至能看穿近代發展並佐以文明批評,名為夏目漱石的日本國民作家應該就不會出現。因為,漱石清楚自覺到明治的思想帶著「把西洋三百年的歷史活動用四十年的時間重新執行一次」的意義。
第十五章 「國民作家」與現代的悲劇
姜尚中
序言
還在世時,夏目漱石似乎曾針對某事說過:「大概不會那麼順利吧。」這種帶著懷疑的,對什麼事都以冷淡眼光看待的發言,充滿夏目漱石的風格。之所以「因果」與「因緣」這類詞語會點綴在漱石的作品中,肯定也與這種態度有關。可說這種類似《草枕》般的「低徊趣味」構成了部分漱石的精神世界。關於這點,政治學家丸山真男認為這種「非國家的」、「非政治的」、「東洋式自由」的韜晦之道,與與國木田獨步的「山林存自由」屬於同一相位。
然而,若把漱石視為一個球體,那麼丸山的指摘僅提及這個球體的半球。因為,即便漱石追求陶淵明式的漢詩世界,也就是將其視為逃離現實世界的唯一「避難所」,但同時他也通過作品世界一直關注「現代」(contemporary)。
留下關於大逆事件(一九一〇~一一)的〈彷彿〉(かのように),以及〈打嗝〉(吃逆)、〈田樂豆腐〉、〈鎚一下〉等作品,經常被事件觸發並訴諸言論自由的森鷗外,在事件後雖然寫出堪稱日本文學最高峰的《澀江抽齋》與《伊澤蘭軒》,但他也不得不在這類史傳式文學中韜光養晦,明顯呈現出與同一時代持續相同堅持的漱石特徵。
確實不能否認,這種現代性具備受到因知識水準平準化而造成文藝消費者抬頭的新聞小說廣大讀者群歡迎的一面。然而不僅止於此,夏目漱石還一貫堅持「此時」與「此地」,通過書寫生活於同時代的登場人物的行動與心理糾葛,成功刻劃出二十世紀日本社會的原型。
漱石在大逆事件發生的翌年見到通過官方文藝委員會選出森鷗外、上田萬年、幸田露伴等擔任文藝委員一事,便嗅出國家將進行言論統制與檢閱的預兆,這也是因為漱石一直把文藝的競技場定位在「現代」之故。聚焦於這種現實的面向,本章還將關注三位與漱石同樣,較其他思想家更具先見,及早看出近代危機的人物:二葉亭四迷、幸德秋水與石川啄木。
那麼,對漱石而言貫穿「現代性」的命運紅繩是什麼?關於這點,一言以蔽之就是「悲劇性」。在最初的新聞小說《虞美人草》(一九〇七)中不怕犯過度單純化之大不韙,刻意道學家式地斷言「悲劇比喜劇更偉大」,這大概也是因為漱石自身也將該存在視為一種「悲劇」吧。
夏目漱石(一八六七~一九一六)
缺失「父性」的權威
夏目金之助,亦即日後的漱石,一八六七年(慶應三年)生於江戶牛込馬場下橫町(今日的新宿區喜久井町),是「名主」 的么子。他出生時父親已經五十歲,母親超過四十歲,而且在他之前還有兩個異母姐姐與三個同母哥哥,因此金之助的出生並不被雙親所喜。加上時代也發生劇變,隔年的一九六八年日本年號由慶應改為明治,名主制度廢除,夏目家也受到時代巨浪的衝擊。
之後金之助被送去當寄養的孩子,但旋即又被帶回,之後又成了養子,但因養父母不和,八年多之後結束了他的養子生涯回歸夏目家。這位多愁善感的少年被當作「麻煩人物」來處置,這種感受也成為漱石終身的內心陰影。這段經歷被詳細寫在可稱為自傳小說的《道草》(一九一五)中,此外在書寫晚年心境的《玻璃門內》(硝子戸の中,一九一五)也有赤裸裸的描寫。遭受親生父親「嚴苛對待」的記憶、出生的秘密,以及當他懂事後被雙親告知的事情等,可說是在描述如何靠一己之力一直背負悲慘「命運」帶來的精神創傷。
但如格蒙德・佛洛伊德所言,兒子通過納入父親這種「權威」來控制自身形成「超自我」,如果這是道德的起源,那麼對漱石而言也是憎恨的對象,因而難以簡單歸納為理想的「權威」。在某種意義上,對少年金之助來說自己心中並不存在應當納入的「父性」權威,反過來說,因為這種不存在導致的不安,也總是纏繞在金之助的內心。
此點與漱石如何看待成為近代國家的明治日本這個根本性問題,有著必然的連結。因為漱石無法把家父長的父親權威與可說是國家家長的天皇絕對權威無縫連接,也就是他很難把自己與明治日本及該時代的深刻糾葛同一化。對他而言這毋寧是有距離感的,且終身對此抱持著愛恨交織的二律背反心結。這在漱石小說世界中塑造那些惱於與日本近代化及對該時代有距離感的主人公們性格時造成決定性的影響。為何漱石主要都以都市中間階層或更上層的知識分子為主角,聚焦於他們的挫折、蹉跌、失敗的悲劇性模樣?因為其中投射的就是對明治這個近代國家的「末流」(epigone,有亞流、模仿者之意)意識趕到煩惱,既無法背過身去,也無法加以屈從,就如此吊在半空中的知識分子悲劇身影。
如果,缺乏作為內在規範原型的「父性」權威,而青少年時期的金之助最切實的課題便是填補這個空白,那麼之後漱石達到之「自我本位」境地,應該就是成人後的金之助面對此番糾葛的回答。漱石強烈的獨立心與反權威主義的心理狀態,應當被視為從自己出生與該時代悲劇性的糾葛發展而來。
如「逃亡者」般的生存
將金之助從這種不幸的生涯中拯救出來,之後獲得東京帝國大學與第一高等學校這種最高級品牌職位給予他的「僥倖」,便是學歷與橫跨公私官僚體制帶來的豐富人際網絡。
因複雜的家庭背景而換過三所小學的少年金之助,之後於一八七九年進入東京府第一中學正則科,之後雖短暫進入二松學舍但依舊不斷轉學,到一八九三年從帝國大學文學科大學英文科畢業準備進入研究所為止,多與擔任明治國家樞要職位的多元人士加深交流,這也為日後漱石能擔任最高學府教師備妥機會。這種條件意味著漱石與那些不隸屬任何公私官僚體制,在某種意義上算是自由人士但又帶著某種可疑形象的「文人」具備不同的生涯職歷。
亦即,伴隨漱石擔任明治國家教育行政的末端工作,就任最高學府的教職,之後更變身成為出版資本主義的代表並持續成長的《朝日新聞》「專屬作家」,至此為止他都以「組織中菁英」的「組織人」生活。在這層意義上,雖說在「組織人」身分上不及以軍醫站上最高地位的鷗外,但漱石也絕非明治國家及其社會的「局外人」知識分子,毋寧該說更接近內部者。大學預備門時代的朋友,如佐藤文熊日後成為警察官僚,擔任關東都督府警視總長等職位,其生涯摯友中村是公則是南滿洲鐵道(滿鐵)總裁,之後更是成為東京市長的一號人物。此外,進入帝國大學文科大學之後交往加深的狩野亨吉還是一高校長,日後更成為新成立的京都帝國大學文科大學校長。
在貫徹旺盛的獨立心與反權威主義下,歸屬公私官僚體制的「組織人」。置身此種相對立場中的漱石,加上自己的出生、家族關係以及與時代的糾葛,可說他是具備多層次與多面向矛盾心理(ambivalence)的作家。漱石之所以罹患神經症,大概也是起於此種矛盾心理。
漱石看穿這種神經症的矛盾心理與近代日本的「個人主義的世道」(パーソナリチーの世の中)相互共通。這是指在平等原則下各自自我覺醒,彼此主張相互對等立場並激烈競爭的世界。這種自主、獨立的原則一旦潰堤氾濫於社會時,則自我與他者、個人與共同體便將相互乖離,並維持此種狀態,無法填埋彼此間的鴻溝。漱石即稱抱持這種矛盾的社會為「個人主義的世道」。這是「一個盡量擴張自己,在不斷膨脹爆裂中過活的世道」,「妻子是妻子,丈夫是丈夫,截然不同,有如水與油」,意即彼此相背而生。
從《三四郎》至未完成的遺作《明暗》,漱石描繪的親子、兄弟、親戚、男女、夫婦、朋友關係等,沒有任何一人逃出「個人主義的世道」中的矛盾。即便擁有高學歷卻不見容於社會的「高等遊民」式知識分子們,他們內心生成的深刻陰影,可說宛如與漱石自身的神經症內心糾葛形成雙重曝光的描寫。
實際上大學畢業(一八九三)後的漱石,一直惱於神經衰弱症,他一直希望能從中「悟脫」,故從一八九四年底至隔年初為止進入圓覺寺參禪,下山之後突然在一八九五年四月隻身前往四國松山愛媛縣尋常中學校擔任英語教師。隔年的一八九六年四月在帝大以來的摯友菅虎雄的建議下轉任熊本的第五高等學校。為何漱石會前往松山,甚至是離帝都更遠的熊本赴任,其真正理由尚無定論,不過在熊本逗留長達四年三個月,這段期間與妻子鏡子結婚,長女筆子出生,必定讓壯年期的漱石形成了一家之主的意識。這對成長時背負「與家人之間的不幸」的漱石而言,他的家庭不僅是闔家團圓的場所,同時也是籌措生計與夫妻出現矛盾的場所。
如此看來,漱石這位作家可說是在轉型期的近代日本中懷抱矛盾的「境界人」(marginal man)。他雖身處多個文化或規範的多重錯位與糾葛中,但並不具被完全歸屬哪一個領域的意識,這意味著他過著宛如是「流亡者」般的生活。漱石之所以成為「搬家狂」,與此有絕對的關係。他在熊本至少搬家達六次,在倫敦遊學時大概也反覆搬家相同次數,恐怕近代日本中再也找不出如此頻繁搬家的作家。而這種「移動」,正是跨空間的越境,且不僅於此,同時還意味著時間上的越境。這也刻畫出在一刻也無法維持穩定,不斷反覆變化的近代時空中,不得不自行從中尋找棲留點的時代宿命。
何況,在日本的狀況是,連問題本身都是多重的。因為日本不得不外發式地「模仿」近代,在這個意義上大概也就不得不成為「理想中的西洋」的「奴隸」,隨之而來的就是最終「拼了命地努力成為奴隸」,最終還把此事當作「進步」。如果把英語學當作終生事業的一介教師夏目金之助也「拚了命地努力成為奴隸」,那麼那位甚至能看穿近代發展並佐以文明批評,名為夏目漱石的日本國民作家應該就不會出現。因為,漱石清楚自覺到明治的思想帶著「把西洋三百年的歷史活動用四十年的時間重新執行一次」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