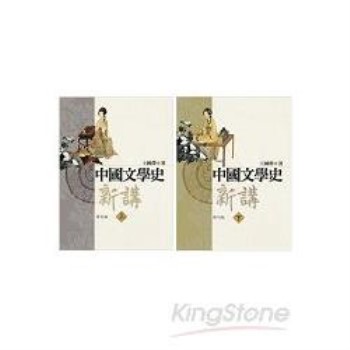第一章 緒說
先秦文學是中國文學的源頭,已是中國文學史論者之共識。所謂「先秦」,乃是指秦始皇統一天下(前211)之前漫長的歷史時期。雖然中國有文字可考的歷史將近四千年,不過在西周之前,作品遺留不多,現存先秦作品,少數產生於西周,大多則出現於春秋戰國時期。因而此處所稱「先秦文學」,主要是以周平王東遷之後,亦即出現在春秋戰國時期的作品為討論重點。
一、先秦文學的興起背景
自周平王東遷,王室衰微,宗法制度破壞,禮樂崩壞;且諸侯爭霸,列國兼併,爭戰頻繁。這時期無論是政治、經濟、社會、思想,各方面均發生劇烈的變化。惟其中兩項背景條件,與先秦文學的興起,關係最為密切:
(一)士階層的崛起
此處所謂「士」,乃指在商周時代原來屬於貴族的最低階層,包括可以遊仕四方的武士、文士、策士等。由於春秋戰國時期,正屬諸侯爭相用人之際,為了爭取霸權或鞏固政權,諸侯「禮賢下士」蔚然成風,於是「士」可以憑藉其才學見識,遊走活躍於諸侯列國之間,其社會地位自然日益重要。這些所謂的「士」,大抵受過「六藝」的教育,屬於一批有知識,有文化,有能力才幹的人物,其中最引人矚目的就是「文士」,亦即具有學識的「文學之士」。這些文士中,有不少是以從事講學授徒和學術著述,來宣揚自己的哲學理念或政治主張,不但是促進先秦思想蓬勃自由的生力軍,也是助長先秦文學興盛的主動力。
(二)思想蓬勃自由
自平王東遷,西周時代原先「學在官府」的局面已成過去,私人聚徒講學的風氣興起,教育或學識已非官方貴族階層的專利,乃至諸子百家的學說主張應運而生。包括儒、墨、道、法、縱橫諸家,各逞其說,放言爭辯,且互相影響,彼此滲透,遂形成中國歷史上罕見的思想蓬勃自由,百家爭鳴的局面。諸子論著與歷史著述的勃興,雖然在中國哲學史或思想史上,擁有不容忽略的地位,不過,從文學史的立場,二類著作以散行單句的行文說理敘事,亦可說是中國敘事文與說理文的源頭。此外,《詩三百》的收錄編輯整理,則為中國詩歌奠定了傳統;再者,思想蓬勃自由,畢竟提高了個體意識的伸張,戰國時期楚人屈原發憤以抒情,宋玉惆悵而自憐,可謂是形成自我抒情述懷文學的先驅。
二、先秦文學的普遍特徵
現存的先秦文學,作品之體制樣式多端,風格亦各異,不過仍然出現一些共同的普遍性的特徵,已經顯示出中國文學的一些傳統痕跡:
(一)尚實用,政治教化色彩濃郁
無論《詩經》、「楚辭」,或史家之著,諸子之說,乃至策士之辭,其撰述、采集,或編輯整理,多以「實用」為宗旨。或為了迎合在上位者之要求,以示君恩浩蕩;或藉其著述以圖自顯,博取聲名;或為批評當權者在政治品德方面的缺憾,以示勸戒;或為宣揚傳播自己的學說理論,以求任用、抒己懷;或為發洩個人在政壇受挫的激慨憂傷,以舒憤懣…。雖然作者或編撰者之目的各異,惟在作品內涵上,往往流露出對當前的政治社會、道德倫理之強烈關懷,乃至對後世中國文學的發展,造成既深且遠的影響。
(二)多非一人之作,作者難以確指
現存先秦時期的文學作品,無論詩或文,由於時代久遠,甚至原作者之姓名與確實時代均有難以考核者,加上官方之收集與編撰者之增潤修飾,乃至大多不是出於一人一時一地,故作者與寫作時代往往難以確指。試看《詩經》305篇,流傳既久,經手亦多,除少數幾篇僅自稱作者之名外,其餘均屬無名氏之作。此外,現存「楚辭」,其中有的作品,或許可以大致認定為屈原所作,惟除了〈離騷〉、〈九歌〉、〈天問〉〈九章〉之外,其他作者到底屬誰,則歷來始終爭議不斷。即使〈九歌〉組詩,一般也認為,或許是屈原根據荊楚一帶民間祀神祭歌改寫潤色而成。至於歷史著述中,諸如《尚書》、《左傳》、《國語》、《戰國策》等,顯然亦均非出自一人之手。另外諸子之文,包括《論語》、《墨子》、《莊子》等,則主要屬於某一學派師徒集體之筆,亦並非單純出於某一特定作者之手。即使《孟子》一書,其中也有弟子的參與紀錄,又經後人增潤者。
(三)文史哲不分,文學與非文學並存
前面論及中國文學的傳統特質,已經點出,文學的範圍雜而不純,乃是一特色。先秦文學作為中國文學的源頭,其範圍,除了《詩經》、「楚辭」以外,諸子論著,史家著述,往往亦涵蓋在內,乃至文史哲不分家,文學與非文學並存。這種現象,或可歸因於:首先,純文學的觀念尚未確立,此時期的作者,對於文學的本質尚無明確認識,亦無文學創作意識的自覺。其次,後世讀者在諸子論著與史家著述中,的確發現了一些影響後世文學作品內涵與風貌的元素。因此,當代每一部中國文學史的撰寫,似乎都用心良苦,特別為先秦的哲學論著和歷史著述,貼上一個「散文」的標籤,如「諸子散文」、「歷史散文」,表示注重的乃是其散體行文的文學色彩與文學價值而已。本書亦未敢例外。
先秦文學是中國文學的源頭,已是中國文學史論者之共識。所謂「先秦」,乃是指秦始皇統一天下(前211)之前漫長的歷史時期。雖然中國有文字可考的歷史將近四千年,不過在西周之前,作品遺留不多,現存先秦作品,少數產生於西周,大多則出現於春秋戰國時期。因而此處所稱「先秦文學」,主要是以周平王東遷之後,亦即出現在春秋戰國時期的作品為討論重點。
一、先秦文學的興起背景
自周平王東遷,王室衰微,宗法制度破壞,禮樂崩壞;且諸侯爭霸,列國兼併,爭戰頻繁。這時期無論是政治、經濟、社會、思想,各方面均發生劇烈的變化。惟其中兩項背景條件,與先秦文學的興起,關係最為密切:
(一)士階層的崛起
此處所謂「士」,乃指在商周時代原來屬於貴族的最低階層,包括可以遊仕四方的武士、文士、策士等。由於春秋戰國時期,正屬諸侯爭相用人之際,為了爭取霸權或鞏固政權,諸侯「禮賢下士」蔚然成風,於是「士」可以憑藉其才學見識,遊走活躍於諸侯列國之間,其社會地位自然日益重要。這些所謂的「士」,大抵受過「六藝」的教育,屬於一批有知識,有文化,有能力才幹的人物,其中最引人矚目的就是「文士」,亦即具有學識的「文學之士」。這些文士中,有不少是以從事講學授徒和學術著述,來宣揚自己的哲學理念或政治主張,不但是促進先秦思想蓬勃自由的生力軍,也是助長先秦文學興盛的主動力。
(二)思想蓬勃自由
自平王東遷,西周時代原先「學在官府」的局面已成過去,私人聚徒講學的風氣興起,教育或學識已非官方貴族階層的專利,乃至諸子百家的學說主張應運而生。包括儒、墨、道、法、縱橫諸家,各逞其說,放言爭辯,且互相影響,彼此滲透,遂形成中國歷史上罕見的思想蓬勃自由,百家爭鳴的局面。諸子論著與歷史著述的勃興,雖然在中國哲學史或思想史上,擁有不容忽略的地位,不過,從文學史的立場,二類著作以散行單句的行文說理敘事,亦可說是中國敘事文與說理文的源頭。此外,《詩三百》的收錄編輯整理,則為中國詩歌奠定了傳統;再者,思想蓬勃自由,畢竟提高了個體意識的伸張,戰國時期楚人屈原發憤以抒情,宋玉惆悵而自憐,可謂是形成自我抒情述懷文學的先驅。
二、先秦文學的普遍特徵
現存的先秦文學,作品之體制樣式多端,風格亦各異,不過仍然出現一些共同的普遍性的特徵,已經顯示出中國文學的一些傳統痕跡:
(一)尚實用,政治教化色彩濃郁
無論《詩經》、「楚辭」,或史家之著,諸子之說,乃至策士之辭,其撰述、采集,或編輯整理,多以「實用」為宗旨。或為了迎合在上位者之要求,以示君恩浩蕩;或藉其著述以圖自顯,博取聲名;或為批評當權者在政治品德方面的缺憾,以示勸戒;或為宣揚傳播自己的學說理論,以求任用、抒己懷;或為發洩個人在政壇受挫的激慨憂傷,以舒憤懣…。雖然作者或編撰者之目的各異,惟在作品內涵上,往往流露出對當前的政治社會、道德倫理之強烈關懷,乃至對後世中國文學的發展,造成既深且遠的影響。
(二)多非一人之作,作者難以確指
現存先秦時期的文學作品,無論詩或文,由於時代久遠,甚至原作者之姓名與確實時代均有難以考核者,加上官方之收集與編撰者之增潤修飾,乃至大多不是出於一人一時一地,故作者與寫作時代往往難以確指。試看《詩經》305篇,流傳既久,經手亦多,除少數幾篇僅自稱作者之名外,其餘均屬無名氏之作。此外,現存「楚辭」,其中有的作品,或許可以大致認定為屈原所作,惟除了〈離騷〉、〈九歌〉、〈天問〉〈九章〉之外,其他作者到底屬誰,則歷來始終爭議不斷。即使〈九歌〉組詩,一般也認為,或許是屈原根據荊楚一帶民間祀神祭歌改寫潤色而成。至於歷史著述中,諸如《尚書》、《左傳》、《國語》、《戰國策》等,顯然亦均非出自一人之手。另外諸子之文,包括《論語》、《墨子》、《莊子》等,則主要屬於某一學派師徒集體之筆,亦並非單純出於某一特定作者之手。即使《孟子》一書,其中也有弟子的參與紀錄,又經後人增潤者。
(三)文史哲不分,文學與非文學並存
前面論及中國文學的傳統特質,已經點出,文學的範圍雜而不純,乃是一特色。先秦文學作為中國文學的源頭,其範圍,除了《詩經》、「楚辭」以外,諸子論著,史家著述,往往亦涵蓋在內,乃至文史哲不分家,文學與非文學並存。這種現象,或可歸因於:首先,純文學的觀念尚未確立,此時期的作者,對於文學的本質尚無明確認識,亦無文學創作意識的自覺。其次,後世讀者在諸子論著與史家著述中,的確發現了一些影響後世文學作品內涵與風貌的元素。因此,當代每一部中國文學史的撰寫,似乎都用心良苦,特別為先秦的哲學論著和歷史著述,貼上一個「散文」的標籤,如「諸子散文」、「歷史散文」,表示注重的乃是其散體行文的文學色彩與文學價值而已。本書亦未敢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