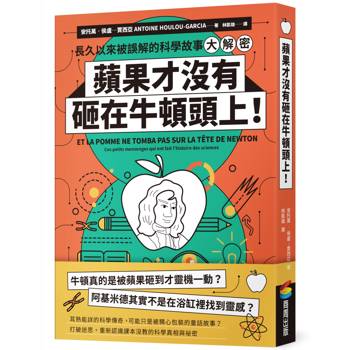█ 第3章:為女性打頭陣的女性 █
◤ 曾有個記者問瑪麗.居禮:「跟天才結婚是什麼感覺?」她回答:「這你得問我先生!」 ◢
本章開篇的這段對話相當有名,在許多書籍和網站都看得到,不論主題是科普、女性主義、個人成長,甚至是商管。然而這段對話雖然有趣(或是現在行銷書或名言時會說的「很勵志」),實則純屬虛構(比較專業的說法是「偽典」),此外這也不符合居禮夫人的個性,她更不是憑這股霸氣兩度獲得諾貝爾獎的。
所以說,在討論圍繞著居禮夫人創造的迷思之前,我們先來回顧她生涯的一些真實事蹟。一八六七年,瑪麗.居禮生於華沙,本名是瑪麗亞.斯郭多夫斯卡(Maria Skłodowska)。她在一八九一年前往巴黎,曾寄宿姊夫家一段時間,後來才租了自己的公寓,在大學攻讀物理(當時幾百名學生裡的女性只有寥寥幾位)。她在一八九三年首先取得物理學學士學位,隔年又取得數學學士學位。她在一間實驗室工作時認識了皮耶.居禮(Pierre Curie),兩人後來合作研究,並於一八九五年結為連理。一八九六年,她首次獲得數學講師資格。隔年,他們的長女伊雷娜出世(也就是伊雷娜.約里奧─居里[Irène Joliot-Curie],於一九三五年獲得諾貝爾化學獎)。
這段時期,科學家剛發現兩種放射線:威廉.倫琴(Wilhelm Röntgen)發現了X光,亨利.貝克勒(Henri Becquerel)發現了鈾射線。瑪麗以後者為博士論文主題,在一九〇三年論文答辯時發表驚人的成果:她發現了兩種新的化學元素,釙(polonium,以她的祖國波蘭命名)和鐳(radium),也發現了元素的「放射性」,並將放射性單位命名為「居禮」。在攻讀博士期間,她三度獲得法國科學院頒獎肯定。至於皮耶,在放射性被發現之後,他決定放下自己的研究主題,協助太太工作。
一九〇三年十二月十日,諾貝爾物理獎同時頒發給居禮夫婦,以及另一名得主貝克勒,以表揚他們傑出的放射性研究(之後會看到,內情沒有我們想像得那麼單純)。瑪麗也成為史上第一位獲得諾貝爾獎的女性。
一九〇四年,在次女艾芙(Ève)出生的兩個月前,巴黎大學新成立一個物理學講座,並聘請皮耶為正式教授,瑪麗則獲聘為講座附設實驗室的主研究員。
然而到了一九〇六年,悲劇發生了:皮耶不幸被馬車撞死,這對瑪麗造成長遠的影響。巴黎大學改將瑪麗亡夫的職位授予她,而她在一九〇六年十一月五日首度登台授課,成為巴黎索邦大學第一位女教授。一九〇八年,她成為該講座的正式教授。一九一一年她二度榮獲諾貝爾獎,這一回是化學獎,肯定她對釙和鐳的發現和研究(之後又會看到,內情同樣錯綜複雜。)
居禮夫人是史上第一個拿了兩次諾貝爾獎的人,此後只有四人達到相同成就:萊納斯.鮑林(Linus Pauling,一九五四年化學獎、一九六二年和平獎),約翰.巴丁(John Bardeen,一九五六年與一九七二年物理獎),弗雷德里克.桑格(Frederick Sanger,一九五八年與一九八〇年化學獎),以及卡爾.巴里.沙普利斯(K. Barry Sharpless,二〇〇一年與二〇二二年化學獎)。
後來居禮夫人創立並主持鐳研究所,在第一次大戰期間發起綽號「小居禮」的放射機救護車,更訓練許多年輕女性成為助理放射師。她本人也親赴前線,在女兒伊雷娜協助下為傷兵照放射影像。
一九二一年,一名美國女記者邀請居禮夫人到美國巡迴演講,為鐳研究所募款(後面會講到這趟美國行帶來的後果)。此時已無疑是名人的她,參與國際聯盟(聯合國前身)旗下的國際知識合作委員會(後來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與愛因斯坦等學者合作,負責協調國際科學研究與交流。一九二四年,因為長年接觸放射線導致的白血病,居里夫人與世長辭。
▎成為迷思的瑪麗.居禮
以上就是我們的主角、科學史上一大神人的生涯史實。舉凡物理、化學、醫學、原子彈……,她的研究發現對許多領域都造成關鍵影響。
今天說到瑪麗.居禮,我們會想到她是科學史上最偉大的女性,為其他女性在科學界打頭陣,激勵無數的女孩子投身研究工作。歐盟就在一九九四年開辦以她命名的科研獎助方案:瑪麗.居禮人才培育計畫(Actions Marie Skłodowska-Curie),且持續至今,是歐洲政壇在學界的重要工具。在歐盟執行委員會網站介紹這個計畫的頁面中,最後幾段話出自英國劍橋大學科學史家派翠西亞.法拉(Patricia Fara)。她的專長之一是女性科學家的歷史,而她就提到瑪麗對她的個人生涯來說有多重要:
她在身後留下深遠的影響,吸引後代無數女性投入科學研究。小時候在學校,她就是我崇拜不已的偶像。
要向女孩子證明科學不是男生的專利,瑪麗確實是最高典範。她也象徵了科學之門為女性敞開,並證明女性就能成為大科學家,不只是擔任大科學家的助理而已。居禮夫人因此成為女性主義象徵,不只因為她代表女性打入科學界,更廣泛而言,也代表女性進入職場。我們有時會說她是「行動派女性主義者」,這也幾乎成了一則迷思。若說愛因斯坦(第八章會提到)是男學者的代表,瑪麗就是女學者的代表了。二〇一一年是她拿到第二座諾貝爾獎的一百周年,聯合國大會就宣布那一年是「瑪麗.居禮年」。
▎差點落空的諾貝爾獎
然而,這篇文章並未反映當時最普遍的觀點。世人還是先看到她是個女人,所以充其量只是她先生的助理。
時間拉回一九〇三年,居禮夫人榮獲第一座諾貝爾獎那一年。一切始於一月二十七日,位於斯德哥爾摩的諾貝爾物理學委員會一如往常,收到法國官方來信推薦人選,而得主將於十一月公布。雖然連署人的姓名清楚可辨(全都是法國科學院院士),這封手寫信函由誰執筆卻難以確認。從筆跡看來,可能是亨利.龐加萊(Henri Poincaré)。不論作者是誰,他推薦的人選有兩位:貝克勒和皮耶.居禮。所以,法國官方單位並未舉薦瑪麗為諾獎候選人。很難說這是出於什麼理由。我們當然能認為這單純是厭女情結作祟(聯署人全為男性,而龐加萊要真是作者,那就不能不提,他的兒子跟他都是巴黎工科綜合學校的高材生,他的幾個女兒卻沒接受教育)。我們也能說,這是因為當時瑪麗還沒通過博士論文答辯(她在同年六月才進行答辯)。又或者,龐加萊跟貝克勒交情深厚,所以不願看到朋友被一對夫婦聯手「比下去」。
無論如何,皮耶馬上寫信給龐加萊(令人不禁認為推薦信就是龐加萊寫的),要求把瑪麗也列入推薦名單:
獲推薦一事令我深感榮幸,但在此仍要表達個人與居里夫人分享這份榮耀的強烈希望,請科學院將我們視為一體,正如我們的研究工作也是如此進行。居里夫人研究了鈾鹽、釷鹽及其他放射性礦物的放射性質。她是那個大膽著手研究新元素化學的人。她做了所有必要的分餾工作提取出鐳,確認該金屬的原子量,並投身研究放射線,發現了人工放射性。有鑑於此,我認為若不將我們視為一體,可謂宣告她只是助手,然而這並不符實情。
雖然如此,龐加萊置之不理。幾個月後,諾貝爾委員會的委員之一、數學家約斯塔.米塔—列夫勒(Magnus Gösta Mittag-Le er)與皮耶商談,因為皮耶接著寫信給他,內容與寄給龐加萊的很類似,籲請將瑪麗列為候選人。米塔—列夫勒勸龐加萊改變心意無果,於是決定暗中操作。在委員會投票決定得主的前一天晚上,他特意請好友克努特.埃斯特朗(Knut Ångström)在瑞典學院發表演講,主題就是鐳,並特別強調瑪麗的貢獻。隔天,諾貝爾獎頒給了居禮夫婦和貝克勒。值得注意的是,這次的獎金由居禮夫婦和貝克勒雙方平分,居禮夫婦只算作一人,然而獎金通常是照得獎人數平均分給每一位。不過這還是極具象徵意義,也總比沒有好:瑪麗成為史上第一位諾貝爾獎女性得主。
雖然如此,當時的輿論還是只把她當成學者的太太,不像我們今天視她為令人景仰的科學家。從節錄自《小巴黎人》(Le Petit Parisien)週報的這段文字就看得出來,寫於諾貝爾獎公布一個月後:
她是先生盡心盡力的友伴,她的名字連上了他們大部分的研究發現,日日都在他的實驗室與他並肩工作。
◤ 曾有個記者問瑪麗.居禮:「跟天才結婚是什麼感覺?」她回答:「這你得問我先生!」 ◢
本章開篇的這段對話相當有名,在許多書籍和網站都看得到,不論主題是科普、女性主義、個人成長,甚至是商管。然而這段對話雖然有趣(或是現在行銷書或名言時會說的「很勵志」),實則純屬虛構(比較專業的說法是「偽典」),此外這也不符合居禮夫人的個性,她更不是憑這股霸氣兩度獲得諾貝爾獎的。
所以說,在討論圍繞著居禮夫人創造的迷思之前,我們先來回顧她生涯的一些真實事蹟。一八六七年,瑪麗.居禮生於華沙,本名是瑪麗亞.斯郭多夫斯卡(Maria Skłodowska)。她在一八九一年前往巴黎,曾寄宿姊夫家一段時間,後來才租了自己的公寓,在大學攻讀物理(當時幾百名學生裡的女性只有寥寥幾位)。她在一八九三年首先取得物理學學士學位,隔年又取得數學學士學位。她在一間實驗室工作時認識了皮耶.居禮(Pierre Curie),兩人後來合作研究,並於一八九五年結為連理。一八九六年,她首次獲得數學講師資格。隔年,他們的長女伊雷娜出世(也就是伊雷娜.約里奧─居里[Irène Joliot-Curie],於一九三五年獲得諾貝爾化學獎)。
這段時期,科學家剛發現兩種放射線:威廉.倫琴(Wilhelm Röntgen)發現了X光,亨利.貝克勒(Henri Becquerel)發現了鈾射線。瑪麗以後者為博士論文主題,在一九〇三年論文答辯時發表驚人的成果:她發現了兩種新的化學元素,釙(polonium,以她的祖國波蘭命名)和鐳(radium),也發現了元素的「放射性」,並將放射性單位命名為「居禮」。在攻讀博士期間,她三度獲得法國科學院頒獎肯定。至於皮耶,在放射性被發現之後,他決定放下自己的研究主題,協助太太工作。
一九〇三年十二月十日,諾貝爾物理獎同時頒發給居禮夫婦,以及另一名得主貝克勒,以表揚他們傑出的放射性研究(之後會看到,內情沒有我們想像得那麼單純)。瑪麗也成為史上第一位獲得諾貝爾獎的女性。
一九〇四年,在次女艾芙(Ève)出生的兩個月前,巴黎大學新成立一個物理學講座,並聘請皮耶為正式教授,瑪麗則獲聘為講座附設實驗室的主研究員。
然而到了一九〇六年,悲劇發生了:皮耶不幸被馬車撞死,這對瑪麗造成長遠的影響。巴黎大學改將瑪麗亡夫的職位授予她,而她在一九〇六年十一月五日首度登台授課,成為巴黎索邦大學第一位女教授。一九〇八年,她成為該講座的正式教授。一九一一年她二度榮獲諾貝爾獎,這一回是化學獎,肯定她對釙和鐳的發現和研究(之後又會看到,內情同樣錯綜複雜。)
居禮夫人是史上第一個拿了兩次諾貝爾獎的人,此後只有四人達到相同成就:萊納斯.鮑林(Linus Pauling,一九五四年化學獎、一九六二年和平獎),約翰.巴丁(John Bardeen,一九五六年與一九七二年物理獎),弗雷德里克.桑格(Frederick Sanger,一九五八年與一九八〇年化學獎),以及卡爾.巴里.沙普利斯(K. Barry Sharpless,二〇〇一年與二〇二二年化學獎)。
後來居禮夫人創立並主持鐳研究所,在第一次大戰期間發起綽號「小居禮」的放射機救護車,更訓練許多年輕女性成為助理放射師。她本人也親赴前線,在女兒伊雷娜協助下為傷兵照放射影像。
一九二一年,一名美國女記者邀請居禮夫人到美國巡迴演講,為鐳研究所募款(後面會講到這趟美國行帶來的後果)。此時已無疑是名人的她,參與國際聯盟(聯合國前身)旗下的國際知識合作委員會(後來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與愛因斯坦等學者合作,負責協調國際科學研究與交流。一九二四年,因為長年接觸放射線導致的白血病,居里夫人與世長辭。
▎成為迷思的瑪麗.居禮
以上就是我們的主角、科學史上一大神人的生涯史實。舉凡物理、化學、醫學、原子彈……,她的研究發現對許多領域都造成關鍵影響。
今天說到瑪麗.居禮,我們會想到她是科學史上最偉大的女性,為其他女性在科學界打頭陣,激勵無數的女孩子投身研究工作。歐盟就在一九九四年開辦以她命名的科研獎助方案:瑪麗.居禮人才培育計畫(Actions Marie Skłodowska-Curie),且持續至今,是歐洲政壇在學界的重要工具。在歐盟執行委員會網站介紹這個計畫的頁面中,最後幾段話出自英國劍橋大學科學史家派翠西亞.法拉(Patricia Fara)。她的專長之一是女性科學家的歷史,而她就提到瑪麗對她的個人生涯來說有多重要:
她在身後留下深遠的影響,吸引後代無數女性投入科學研究。小時候在學校,她就是我崇拜不已的偶像。
要向女孩子證明科學不是男生的專利,瑪麗確實是最高典範。她也象徵了科學之門為女性敞開,並證明女性就能成為大科學家,不只是擔任大科學家的助理而已。居禮夫人因此成為女性主義象徵,不只因為她代表女性打入科學界,更廣泛而言,也代表女性進入職場。我們有時會說她是「行動派女性主義者」,這也幾乎成了一則迷思。若說愛因斯坦(第八章會提到)是男學者的代表,瑪麗就是女學者的代表了。二〇一一年是她拿到第二座諾貝爾獎的一百周年,聯合國大會就宣布那一年是「瑪麗.居禮年」。
▎差點落空的諾貝爾獎
然而,這篇文章並未反映當時最普遍的觀點。世人還是先看到她是個女人,所以充其量只是她先生的助理。
時間拉回一九〇三年,居禮夫人榮獲第一座諾貝爾獎那一年。一切始於一月二十七日,位於斯德哥爾摩的諾貝爾物理學委員會一如往常,收到法國官方來信推薦人選,而得主將於十一月公布。雖然連署人的姓名清楚可辨(全都是法國科學院院士),這封手寫信函由誰執筆卻難以確認。從筆跡看來,可能是亨利.龐加萊(Henri Poincaré)。不論作者是誰,他推薦的人選有兩位:貝克勒和皮耶.居禮。所以,法國官方單位並未舉薦瑪麗為諾獎候選人。很難說這是出於什麼理由。我們當然能認為這單純是厭女情結作祟(聯署人全為男性,而龐加萊要真是作者,那就不能不提,他的兒子跟他都是巴黎工科綜合學校的高材生,他的幾個女兒卻沒接受教育)。我們也能說,這是因為當時瑪麗還沒通過博士論文答辯(她在同年六月才進行答辯)。又或者,龐加萊跟貝克勒交情深厚,所以不願看到朋友被一對夫婦聯手「比下去」。
無論如何,皮耶馬上寫信給龐加萊(令人不禁認為推薦信就是龐加萊寫的),要求把瑪麗也列入推薦名單:
獲推薦一事令我深感榮幸,但在此仍要表達個人與居里夫人分享這份榮耀的強烈希望,請科學院將我們視為一體,正如我們的研究工作也是如此進行。居里夫人研究了鈾鹽、釷鹽及其他放射性礦物的放射性質。她是那個大膽著手研究新元素化學的人。她做了所有必要的分餾工作提取出鐳,確認該金屬的原子量,並投身研究放射線,發現了人工放射性。有鑑於此,我認為若不將我們視為一體,可謂宣告她只是助手,然而這並不符實情。
雖然如此,龐加萊置之不理。幾個月後,諾貝爾委員會的委員之一、數學家約斯塔.米塔—列夫勒(Magnus Gösta Mittag-Le er)與皮耶商談,因為皮耶接著寫信給他,內容與寄給龐加萊的很類似,籲請將瑪麗列為候選人。米塔—列夫勒勸龐加萊改變心意無果,於是決定暗中操作。在委員會投票決定得主的前一天晚上,他特意請好友克努特.埃斯特朗(Knut Ångström)在瑞典學院發表演講,主題就是鐳,並特別強調瑪麗的貢獻。隔天,諾貝爾獎頒給了居禮夫婦和貝克勒。值得注意的是,這次的獎金由居禮夫婦和貝克勒雙方平分,居禮夫婦只算作一人,然而獎金通常是照得獎人數平均分給每一位。不過這還是極具象徵意義,也總比沒有好:瑪麗成為史上第一位諾貝爾獎女性得主。
雖然如此,當時的輿論還是只把她當成學者的太太,不像我們今天視她為令人景仰的科學家。從節錄自《小巴黎人》(Le Petit Parisien)週報的這段文字就看得出來,寫於諾貝爾獎公布一個月後:
她是先生盡心盡力的友伴,她的名字連上了他們大部分的研究發現,日日都在他的實驗室與他並肩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