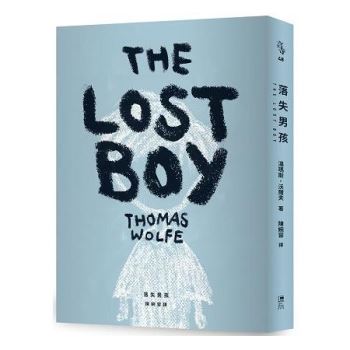Part II
……那天我們途經印第安納,一路前往──你當時還太小啦,孩子,應該記不得這事兒了──我老想著那個早晨,葛洛佛在我們坐車途經印第安納,一路前往博覽會時的模樣。這一路上,蘋果樹都開花了。那是個四月天,所有的樹都開花了。印第安納時逢初春,景物也開始有了綠意。我們家那頭當然沒有印第安納那種農場。那種農場是不可能出現在我們住的山上的。葛洛佛呢,不消說,也從未見過那樣的農場。我想他這孩子是打算用心欣賞,大飽眼福一番。
於是他坐在位子上,鼻子緊緊貼著窗戶向外望──我永遠忘不了他坐在那兒望著窗外的模樣──他動也不動地望著。他的樣子是多麼認真,多麼認真地望著窗外的景色──他從不曾見過那樣的農場,他要好好看個夠。那整個早晨,我們傍著沃巴什河而行──就是那條流經印第安納,還被寫成了歌的沃巴什河。是的,我們那個早晨就傍著這條河一路前進,你們這幾個孩子就在這趟行經印第安納的旅途上圍著我團團而坐。我們要去聖路易斯,去博覽會。
你們幾個一直在走道上跑來跑去──不,不對,欸,是呀,你當時還太小了;你那年才三歲大,我是不會讓你亂跑的。不過你的哥哥姊姊確實不停在走道上跑來跑去,將臉湊上一扇又一扇的車窗。他們一下跑到左邊、一下跑到右邊,發現了什麼新鮮事兒就會放聲吆喝,趕忙叫其他人也過來瞧瞧。他們一路上都試著眼觀六路,恨不得背後也長了眼睛似的。你瞧,孩子,這是他們頭一回到印第安納,所以我猜這幾個孩子都覺得眼前的一切是多麼陌生、多麼新奇呢。
他們好像怎樣都看不過癮似的,好像一刻都靜不下來。他們來來回回不停地跑來跑去,還不斷衝著對方大呼小叫。後來我終於開口:「我敢說!孩子們!我從沒見你們這麼激動過!」我說:「看看你們,一直跑來跑去,一刻也靜不下來──可真讓我大開眼界了。」我還說:「你們這些精力到底是打哪兒來的?」
你瞧,他們應該都因為這趟聖路易斯之行而興奮得不得了,也對這一路上的景物充滿了好奇。他們多麼青春,在他們眼裡,一切都好陌生、好新奇。他們克制不了自己,就是想看遍窗外的風景。但是──「我敢說!」我告訴他們。「你們這幾個孩子再不坐下歇一會兒,可沒那個力氣一遊聖路易斯和博覽會!」
葛洛佛卻不然!他──不,先生!唯有他例外。聽著,孩子,讓我告訴你──我一手將你們這群孩子拉拔長大──我看著你們漸漸長大,然後一個個離鄉背井、出外打拚──你們全都是腦袋靈光的聰明人,欸,不是我要說,我生的孩子沒有一個是傻瓜──可不是嘛!我總說你這孩子聰慧得很……那些人今兒個才來拜訪我,還大大誇讚你有多聰明。這讓我想到你是怎麼出人頭地,怎麼像俗話所說「一舉成名天下知」──但我不動聲色,你知道的。我只是靜靜坐在那兒,隨他們講。我不會把你誇得天花亂墜──他們要大肆吹捧你,那是他們的事兒。我這輩子從不在外人面前誇耀自己的孩子。當初爸拉拔大夥兒長大,就再三訓勉我們,有教養的人是不會拿親人來說嘴的。「要是外人想誇上幾句──」爸說。「就讓他們誇去。千萬別出言附和,也絕對不要顯露一絲絲了然於心的表情。就閉上嘴,讓他們說去。」
所以說,當他們來拜訪我,還在我面前提起你所有的成就,我完全不動聲色。我連一個字都沒回。欸,可不是嘛!──是,你瞧,就在這兒──哦,大約一個月前吧,這位小哥──是位穿著講究的人,你知道──那樣子頗有幾分書卷氣,看上去也算個有頭有臉的人物──他來拜訪過我。他說自己是打紐澤西來的,還是遠從那個地方的什麼地區來啊……他問了我林林總總的問題,比方你小時候是個什麼樣的孩子之類的問題。
我呢,就假裝仔仔細細前思後想了一番,然後說:「唔,是的。」──我擺出好不正經的樣子,你知道──「欸,是啊,我想我多少知道他的一些事情──他畢竟是我的孩子,正如其他幾個小孩也是──我是怎麼帶大其他那些孩子,就是怎麼將他教養長大的。他──」我說──哦,我當時的態度好不嚴肅呢,你知道──「他小時候並不是個壞孩子。當然呀──」我說。「他在十二歲之前,就跟我其他幾個孩子差不多──就只是那種普通而正常的好孩子。」
「喔。」他說。「但您都沒看出什麼跡象嗎?他難道沒有任何不太尋常的表現?」他說。「任何有別於您在其他孩子身上發現到的特出之處呢?」我沒透露一點口風,你知道──我只是靜靜聽著對方說,並擺出一副極其嚴肅的樣子──我就擺出一副極其嚴肅的樣子,假裝仔仔細細前思後想了一番。「啊,那當然是沒有的。」我說,一個字、一個字慢慢地說,就在我徹底思索過後。「他就跟我其他幾個孩子一樣有雙好眼睛、一個鼻子一張嘴,也有兩條胳臂兩條腿、一整頭的頭髮,手指和腳趾的數量也跟他們的一樣標準──現在想來,他小時候要是在這些方面有別於他的哥哥姊姊,我應該馬上就注意到了。不過,就我記憶所及,他就是那種乖巧、平凡、正常的男孩,就跟我其他幾個孩子沒有兩樣──」「是的……」他說──哦,他非常激動,你知道──「但他難道不聰明嗎──您難道不曾看出他有多聰明──他絕對比您其他幾個孩子都要聰明吧!」「嗯,這個嘛……」我說,也不忘裝出仔細思量的樣子。「讓我想想……有了──」我說。我就直視著他的眼睛,用正經八百的態度回答。「他在學校表現得相當不錯。從沒留過級。我從沒聽說他的老師會在課堂間罰他戴上『朽木不可雕也』的尖頂高帽。可話說回來……」我說。「我其他幾個孩子在學校也沒戴過那種帽子。說老實話,我沒有要誇讚他們的意思。我不認為誇讚自己的孩子是件好事。如果有人想誇我的孩子多好多聰明,那是他家的事兒;我們既平凡又普通,從不敢妄稱自己有多麼與眾不同。但這種話,我還是能替他們說說的──他們每個人生來都有一定的悟性與才智。他們或許誰也不是天才,可一個個都是頭腦清醒,能夠隨機應變的孩子。也從來沒有人建議我把哪個孩子送到弱智兒童之家照顧。好了──」我說,直視著他的眼睛說,你知道。「這話聽起來或許沒什麼大不了,卻已經超出我平時會為一些熟人說的好話了。嗯……」我說。「嗯,是啊……」我說。「我想他確實是個挺聰明的孩子。他這點一直讓我無可挑剔。他是夠聰明──」我說。「唯一的問題就是──這點我跟他提過上百遍了,所以我現在講的可不是他從沒聽過的事兒──他唯一的問題──」我說。「就是太懶惰。」
「懶惰!」他說──哦,你真該看看他當時的表情,你知道──他嚇了一大跳,好像讓人用針戳著似的。「懶惰!」他說。「哎呀,您該不是打算告訴我──」
「是的。」我說──哦,我從頭到尾都沒笑──「上回我見著他,也跟他說了同樣的話。我跟他說,他是何其幸運,有這能說善道的本事。當然,他上過大學,也念過不少書;我想那些人說他擁有所謂『流暢的語言』,應該就是這麼來的吧……不過,正如我上回見著他時對他說的:『聽我一句──』我說。『你能像現在這樣依靠輕鬆愉快,犯不著揮汗如雨的工作養活自己──』我說。『真的非常幸運。畢竟你的親戚裡沒有一個人──』我說。『能像你這般幸運。他們一個個為求溫飽,都得辛苦地勞作。』」
哦,你瞧,我告訴他了。我當場就挑明了告訴他,毫不掩飾地告訴他。而且,你知道嗎──我真巴不得你能看看他當時的表情。他那表情實在太有意思了。
「我說──」最後,他開口。「您不得不承認,對吧──他就是您所有孩子中最聰穎的一個,對不對?」
而我只是瞧了他一會兒。這下子,我必須講出真話了。我不能再這麼愚弄他了。「不。」我說。「他確實是個聰明的好孩子──他這點一直讓我無可挑剔──但要說我最聰明的孩子,那個在悟性、理解力和判斷能力都贏過我其他小孩的孩子──我最出色的孩子──我這輩子見過最聰明的孩子──則是你不曾認識的那位──你從沒見過的那位──我那已逝的孩子。」
他看了看我。片刻之後,他開口說:「是您的哪一位孩子呢?」
我試圖告訴他。可當我試圖說出「聖路易斯」,這幾個字就是脫不出口。孩子,孩子呀,我又憶起那可憎的地名──那地名還是那麼可憎,就跟以前一樣啊。我說不出口。我一聽到那個地名就痛得無法承受。事隔三十年──甚或更久?──每當有人對我說起那個地名,或只要我在什麼地方聽到那個地名,那段往事便會浮上我心頭。那種感覺就跟舊日的惡瘡再度裂開一樣──我沒辦法,事情永遠這個樣兒。孩子,孩子呀……當我又想起那個地方,當我正打算告訴這位先生實情,我也憶起了那段往事。我開不了口。我必須撇過頭去。我想我是在哭。
因為,每當我想到那個老地名,就會看見他在我們坐車途經印第安納,一路前往博覽會的那個早晨,是多麼認真地坐在那兒,還把鼻子緊緊貼在車窗上的模樣。路上的蘋果樹都開花了,桃樹也是,每一棵都開花了。那一路上的樹、一路上的景物,都在我們順著沃巴什河前往博覽會的那個四月天綻放著花朵。
而葛洛佛就坐在位子上,那模樣一動也不動,好不認真──你其他幾個哥哥姊姊則興奮非常,老在車廂裡跑來跑去,還大呼小叫,一下喚誰來、一下喚誰去──可葛洛佛卻坐在那兒看著窗外,一動也不動。他就這麼坐著,跟個大人似的。他當時才十一歲半啊。孩子,孩子呀──他真的好乖,而且就像他去世那會兒報上說的,他的判斷能力可比那些年紀大他一輪的人──他是我這輩子見過悟性最高,也最富判斷力和理解能力的孩子。
而且呢,我說啊!──他在這麼個早晨坐在這麼一位紳士旁邊看著窗外的景物──欸,是的,我現在要告訴你的事情,便可證明──即可證明他那不凡的悟性與判斷能力。我們就坐在順著沃巴什河前行的列車上,你知道。我們已經翻山越嶺,進入了印第安納的州境,然後──哦,當然,他們那兒是不來吉姆.克勞法 那一套的──然後車廂的門一開,他便走了進來,你知道,就提著手提袋大搖大擺地走至通道中間,彷彿這車廂就是歸他所有──欸,就辛普森.費瑟史東那人高馬大、膚色暗黃的黑麻子──屆時到了聖路易斯,我們就得靠你爸保護了──哦,他昂首闊步走了進來,接著多麼不知輕重、明目張膽地脫下身上的大衣,將手提袋放到行李架上,然後大大方方坐了下來,一點兒也不拘束。乖乖,好像整條鐵路都是他的一樣。當然啊,沒錯,我們當時是在印第安納,而當地並沒有禁止有色人種與白人乘坐同一車廂的法令。於是乎,就在我們進入印第安納州境之時,這恬不知恥的黑鬼也從後頭的黑鬼專用車廂進入了我們的車廂──哎呀,好個沒分寸的傢伙!「唔……」我暗自忖道。「要是他膽敢覺得可以這樣為所欲為下去,我可要好好修理他!立刻叫他明白這個國家都是誰在作主!」所以我出聲叫了叫他。我雖然曉得他在打什麼歪主意,但我沒有表現出來,只是像個法官嚴肅地對他說:「辛普森──」我說。「我想你搞錯了。」「不,夫人──」他說──哦,一副眉開眼笑的樣子呢──「咱啥也沒搞錯,艾莉莎小姐。」「哦,有的,你搞錯了。」我說。「你何不看看四周,瞧瞧自己身在何處?好了──」我直視著他的雙眼。「還不快起來,趕緊帶著你的行李從那條過道回到你們的車廂,回到你該坐的座位上。」「哦,不,夫人。」他說,還露出了牙咧嘴笑著。「咱不需要回那節車廂。」他說。「咱現在到了印第安納,咱愛坐哪兒就坐哪兒。」
接著,葛洛佛起身往回走,還直直瞧著他的雙眼。「不,你不能這麼做。」他說。「為什麼呢?是什麼原因讓咱不能這麼做?」辛普森.費瑟史東說。他看著葛洛佛說話,好像有點驚訝的樣子。「欸,葛洛佛先生,法律說咱可以這麼做。」他回道。葛洛佛便看著他說:「這兒的法律或許如此,我們的法律卻大不相同。我們不是這麼做事的,你也不是這麼做事的。沒錯,這點你心知肚明。」葛洛佛說。「因為你受的是全然不同的教養。現在請你站起來,照媽媽說的回到你該坐的車廂去。」
你真該瞧瞧那黑麻子臉上的表情。我後來想到這事兒,還會忍不住哈哈大笑呢。當然啦,他尊重葛洛佛的判斷,一如每個人都尊重葛洛佛的判斷──他知道葛洛佛說得對──所以他站了起來,先生,他隨即站了起來,先生,沒說第二句話。他拎起自己的手提袋和大衣,順著過道快步離開我們的車廂,回到他原本的車廂,他真正該坐的地方。這個時候,那位坐在葛洛佛旁邊的紳士轉過頭來,朝我點了點頭。「我說啊──」他告訴我。「好個了不起的孩子。」當然,他看出來了,你知道。他是個明眼人。他能看出葛洛佛比絕大多數的大人都要有品有格,而他沒看走眼。
所以他就坐在那兒,你知道,那個早晨,葛洛佛就坐在位子上看著窗外的沃巴什河,看著我們看到的一座座農場。因為,我想,他長這麼大還沒見過那樣的農場──我仍記得他坐在位子上看著窗外景物的模樣。我仍記得當時他那頭烏黑的頭髮、那雙瀝青似的黑眼睛,還有他脖子上的胎記──我生的孩子裡,就你跟葛洛佛是黑髮黑眼睛,其他人生來都是一頭輕盈的金髮、灰色的眼睛,就像他們的父親。但你和葛洛佛長得就像彭特蘭家族的人,就像他們的黑髮黑眼睛,就像黑髮黑眼睛的亞歷山大和彭特蘭家族的人。你跟你李舅舅簡直是一個模子刻出來的,但葛洛佛的髮色、眼睛的顏色,又比你們倆來得黑。
所以,葛洛佛就坐在這位紳士旁邊看著窗外的景物。然後他轉過頭來,開始問這位紳士各式各樣的問題──那是什麼樹啦、那頭種了什麼作物啦、那些農場有多大啦──各式各樣的問題,而這位紳士也能應答如流,直到我開口:「哎呀,我敢說,葛洛佛!你不該提這麼多問題的。你會擾了這位紳士的清靜。」我在擔心,你知道,我怕這名紳士會因為葛洛佛東問西問而感到煩不勝煩。
這位紳士立刻仰頭大笑,開懷地大笑。我不曉得他有何來頭,也不曾請教他的大名,不過他看上去一表人才,還非常喜歡葛洛佛的樣子。我說啊,他立刻仰頭大笑,並告訴我:「您別操心這個小傢伙。他不礙事兒。」他說。「小傢伙一點都沒打擾到我。我若曉得他問題的答案,便會回答他;不知道的話,也就如實告訴他便是。小傢伙不礙事兒。」他說,還伸出手臂摟住葛洛佛的雙肩。「您就別管他了。小傢伙完全沒有打擾到我。」
我依然記得他當時的模樣,他那雙黑眼睛、那頭黑髮,以及他脖子上的胎記──他那如此沉靜、嚴肅,又那麼認真的模樣。他就這樣看著窗外的蘋果樹、農場、穀倉、屋舍和果園,將看得見的一切盡收眼底、心裡,因為,我想,這一切對他來說是那麼陌生而新奇。
孩子,孩子呀,這都是好久以前的事了,但當我又聽見那個地名,這段往事便會浮上我心頭,彷彿昨天才發生過一樣歷歷在目。而今,那道舊日的惡瘡又裂開啦。我能看見他當時的模樣,就我們一路傍著沃巴什河,為了前往博覽會而行經印第安納的那個早晨,他映在我眼中的模樣。
……那天我們途經印第安納,一路前往──你當時還太小啦,孩子,應該記不得這事兒了──我老想著那個早晨,葛洛佛在我們坐車途經印第安納,一路前往博覽會時的模樣。這一路上,蘋果樹都開花了。那是個四月天,所有的樹都開花了。印第安納時逢初春,景物也開始有了綠意。我們家那頭當然沒有印第安納那種農場。那種農場是不可能出現在我們住的山上的。葛洛佛呢,不消說,也從未見過那樣的農場。我想他這孩子是打算用心欣賞,大飽眼福一番。
於是他坐在位子上,鼻子緊緊貼著窗戶向外望──我永遠忘不了他坐在那兒望著窗外的模樣──他動也不動地望著。他的樣子是多麼認真,多麼認真地望著窗外的景色──他從不曾見過那樣的農場,他要好好看個夠。那整個早晨,我們傍著沃巴什河而行──就是那條流經印第安納,還被寫成了歌的沃巴什河。是的,我們那個早晨就傍著這條河一路前進,你們這幾個孩子就在這趟行經印第安納的旅途上圍著我團團而坐。我們要去聖路易斯,去博覽會。
你們幾個一直在走道上跑來跑去──不,不對,欸,是呀,你當時還太小了;你那年才三歲大,我是不會讓你亂跑的。不過你的哥哥姊姊確實不停在走道上跑來跑去,將臉湊上一扇又一扇的車窗。他們一下跑到左邊、一下跑到右邊,發現了什麼新鮮事兒就會放聲吆喝,趕忙叫其他人也過來瞧瞧。他們一路上都試著眼觀六路,恨不得背後也長了眼睛似的。你瞧,孩子,這是他們頭一回到印第安納,所以我猜這幾個孩子都覺得眼前的一切是多麼陌生、多麼新奇呢。
他們好像怎樣都看不過癮似的,好像一刻都靜不下來。他們來來回回不停地跑來跑去,還不斷衝著對方大呼小叫。後來我終於開口:「我敢說!孩子們!我從沒見你們這麼激動過!」我說:「看看你們,一直跑來跑去,一刻也靜不下來──可真讓我大開眼界了。」我還說:「你們這些精力到底是打哪兒來的?」
你瞧,他們應該都因為這趟聖路易斯之行而興奮得不得了,也對這一路上的景物充滿了好奇。他們多麼青春,在他們眼裡,一切都好陌生、好新奇。他們克制不了自己,就是想看遍窗外的風景。但是──「我敢說!」我告訴他們。「你們這幾個孩子再不坐下歇一會兒,可沒那個力氣一遊聖路易斯和博覽會!」
葛洛佛卻不然!他──不,先生!唯有他例外。聽著,孩子,讓我告訴你──我一手將你們這群孩子拉拔長大──我看著你們漸漸長大,然後一個個離鄉背井、出外打拚──你們全都是腦袋靈光的聰明人,欸,不是我要說,我生的孩子沒有一個是傻瓜──可不是嘛!我總說你這孩子聰慧得很……那些人今兒個才來拜訪我,還大大誇讚你有多聰明。這讓我想到你是怎麼出人頭地,怎麼像俗話所說「一舉成名天下知」──但我不動聲色,你知道的。我只是靜靜坐在那兒,隨他們講。我不會把你誇得天花亂墜──他們要大肆吹捧你,那是他們的事兒。我這輩子從不在外人面前誇耀自己的孩子。當初爸拉拔大夥兒長大,就再三訓勉我們,有教養的人是不會拿親人來說嘴的。「要是外人想誇上幾句──」爸說。「就讓他們誇去。千萬別出言附和,也絕對不要顯露一絲絲了然於心的表情。就閉上嘴,讓他們說去。」
所以說,當他們來拜訪我,還在我面前提起你所有的成就,我完全不動聲色。我連一個字都沒回。欸,可不是嘛!──是,你瞧,就在這兒──哦,大約一個月前吧,這位小哥──是位穿著講究的人,你知道──那樣子頗有幾分書卷氣,看上去也算個有頭有臉的人物──他來拜訪過我。他說自己是打紐澤西來的,還是遠從那個地方的什麼地區來啊……他問了我林林總總的問題,比方你小時候是個什麼樣的孩子之類的問題。
我呢,就假裝仔仔細細前思後想了一番,然後說:「唔,是的。」──我擺出好不正經的樣子,你知道──「欸,是啊,我想我多少知道他的一些事情──他畢竟是我的孩子,正如其他幾個小孩也是──我是怎麼帶大其他那些孩子,就是怎麼將他教養長大的。他──」我說──哦,我當時的態度好不嚴肅呢,你知道──「他小時候並不是個壞孩子。當然呀──」我說。「他在十二歲之前,就跟我其他幾個孩子差不多──就只是那種普通而正常的好孩子。」
「喔。」他說。「但您都沒看出什麼跡象嗎?他難道沒有任何不太尋常的表現?」他說。「任何有別於您在其他孩子身上發現到的特出之處呢?」我沒透露一點口風,你知道──我只是靜靜聽著對方說,並擺出一副極其嚴肅的樣子──我就擺出一副極其嚴肅的樣子,假裝仔仔細細前思後想了一番。「啊,那當然是沒有的。」我說,一個字、一個字慢慢地說,就在我徹底思索過後。「他就跟我其他幾個孩子一樣有雙好眼睛、一個鼻子一張嘴,也有兩條胳臂兩條腿、一整頭的頭髮,手指和腳趾的數量也跟他們的一樣標準──現在想來,他小時候要是在這些方面有別於他的哥哥姊姊,我應該馬上就注意到了。不過,就我記憶所及,他就是那種乖巧、平凡、正常的男孩,就跟我其他幾個孩子沒有兩樣──」「是的……」他說──哦,他非常激動,你知道──「但他難道不聰明嗎──您難道不曾看出他有多聰明──他絕對比您其他幾個孩子都要聰明吧!」「嗯,這個嘛……」我說,也不忘裝出仔細思量的樣子。「讓我想想……有了──」我說。我就直視著他的眼睛,用正經八百的態度回答。「他在學校表現得相當不錯。從沒留過級。我從沒聽說他的老師會在課堂間罰他戴上『朽木不可雕也』的尖頂高帽。可話說回來……」我說。「我其他幾個孩子在學校也沒戴過那種帽子。說老實話,我沒有要誇讚他們的意思。我不認為誇讚自己的孩子是件好事。如果有人想誇我的孩子多好多聰明,那是他家的事兒;我們既平凡又普通,從不敢妄稱自己有多麼與眾不同。但這種話,我還是能替他們說說的──他們每個人生來都有一定的悟性與才智。他們或許誰也不是天才,可一個個都是頭腦清醒,能夠隨機應變的孩子。也從來沒有人建議我把哪個孩子送到弱智兒童之家照顧。好了──」我說,直視著他的眼睛說,你知道。「這話聽起來或許沒什麼大不了,卻已經超出我平時會為一些熟人說的好話了。嗯……」我說。「嗯,是啊……」我說。「我想他確實是個挺聰明的孩子。他這點一直讓我無可挑剔。他是夠聰明──」我說。「唯一的問題就是──這點我跟他提過上百遍了,所以我現在講的可不是他從沒聽過的事兒──他唯一的問題──」我說。「就是太懶惰。」
「懶惰!」他說──哦,你真該看看他當時的表情,你知道──他嚇了一大跳,好像讓人用針戳著似的。「懶惰!」他說。「哎呀,您該不是打算告訴我──」
「是的。」我說──哦,我從頭到尾都沒笑──「上回我見著他,也跟他說了同樣的話。我跟他說,他是何其幸運,有這能說善道的本事。當然,他上過大學,也念過不少書;我想那些人說他擁有所謂『流暢的語言』,應該就是這麼來的吧……不過,正如我上回見著他時對他說的:『聽我一句──』我說。『你能像現在這樣依靠輕鬆愉快,犯不著揮汗如雨的工作養活自己──』我說。『真的非常幸運。畢竟你的親戚裡沒有一個人──』我說。『能像你這般幸運。他們一個個為求溫飽,都得辛苦地勞作。』」
哦,你瞧,我告訴他了。我當場就挑明了告訴他,毫不掩飾地告訴他。而且,你知道嗎──我真巴不得你能看看他當時的表情。他那表情實在太有意思了。
「我說──」最後,他開口。「您不得不承認,對吧──他就是您所有孩子中最聰穎的一個,對不對?」
而我只是瞧了他一會兒。這下子,我必須講出真話了。我不能再這麼愚弄他了。「不。」我說。「他確實是個聰明的好孩子──他這點一直讓我無可挑剔──但要說我最聰明的孩子,那個在悟性、理解力和判斷能力都贏過我其他小孩的孩子──我最出色的孩子──我這輩子見過最聰明的孩子──則是你不曾認識的那位──你從沒見過的那位──我那已逝的孩子。」
他看了看我。片刻之後,他開口說:「是您的哪一位孩子呢?」
我試圖告訴他。可當我試圖說出「聖路易斯」,這幾個字就是脫不出口。孩子,孩子呀,我又憶起那可憎的地名──那地名還是那麼可憎,就跟以前一樣啊。我說不出口。我一聽到那個地名就痛得無法承受。事隔三十年──甚或更久?──每當有人對我說起那個地名,或只要我在什麼地方聽到那個地名,那段往事便會浮上我心頭。那種感覺就跟舊日的惡瘡再度裂開一樣──我沒辦法,事情永遠這個樣兒。孩子,孩子呀……當我又想起那個地方,當我正打算告訴這位先生實情,我也憶起了那段往事。我開不了口。我必須撇過頭去。我想我是在哭。
因為,每當我想到那個老地名,就會看見他在我們坐車途經印第安納,一路前往博覽會的那個早晨,是多麼認真地坐在那兒,還把鼻子緊緊貼在車窗上的模樣。路上的蘋果樹都開花了,桃樹也是,每一棵都開花了。那一路上的樹、一路上的景物,都在我們順著沃巴什河前往博覽會的那個四月天綻放著花朵。
而葛洛佛就坐在位子上,那模樣一動也不動,好不認真──你其他幾個哥哥姊姊則興奮非常,老在車廂裡跑來跑去,還大呼小叫,一下喚誰來、一下喚誰去──可葛洛佛卻坐在那兒看著窗外,一動也不動。他就這麼坐著,跟個大人似的。他當時才十一歲半啊。孩子,孩子呀──他真的好乖,而且就像他去世那會兒報上說的,他的判斷能力可比那些年紀大他一輪的人──他是我這輩子見過悟性最高,也最富判斷力和理解能力的孩子。
而且呢,我說啊!──他在這麼個早晨坐在這麼一位紳士旁邊看著窗外的景物──欸,是的,我現在要告訴你的事情,便可證明──即可證明他那不凡的悟性與判斷能力。我們就坐在順著沃巴什河前行的列車上,你知道。我們已經翻山越嶺,進入了印第安納的州境,然後──哦,當然,他們那兒是不來吉姆.克勞法 那一套的──然後車廂的門一開,他便走了進來,你知道,就提著手提袋大搖大擺地走至通道中間,彷彿這車廂就是歸他所有──欸,就辛普森.費瑟史東那人高馬大、膚色暗黃的黑麻子──屆時到了聖路易斯,我們就得靠你爸保護了──哦,他昂首闊步走了進來,接著多麼不知輕重、明目張膽地脫下身上的大衣,將手提袋放到行李架上,然後大大方方坐了下來,一點兒也不拘束。乖乖,好像整條鐵路都是他的一樣。當然啊,沒錯,我們當時是在印第安納,而當地並沒有禁止有色人種與白人乘坐同一車廂的法令。於是乎,就在我們進入印第安納州境之時,這恬不知恥的黑鬼也從後頭的黑鬼專用車廂進入了我們的車廂──哎呀,好個沒分寸的傢伙!「唔……」我暗自忖道。「要是他膽敢覺得可以這樣為所欲為下去,我可要好好修理他!立刻叫他明白這個國家都是誰在作主!」所以我出聲叫了叫他。我雖然曉得他在打什麼歪主意,但我沒有表現出來,只是像個法官嚴肅地對他說:「辛普森──」我說。「我想你搞錯了。」「不,夫人──」他說──哦,一副眉開眼笑的樣子呢──「咱啥也沒搞錯,艾莉莎小姐。」「哦,有的,你搞錯了。」我說。「你何不看看四周,瞧瞧自己身在何處?好了──」我直視著他的雙眼。「還不快起來,趕緊帶著你的行李從那條過道回到你們的車廂,回到你該坐的座位上。」「哦,不,夫人。」他說,還露出了牙咧嘴笑著。「咱不需要回那節車廂。」他說。「咱現在到了印第安納,咱愛坐哪兒就坐哪兒。」
接著,葛洛佛起身往回走,還直直瞧著他的雙眼。「不,你不能這麼做。」他說。「為什麼呢?是什麼原因讓咱不能這麼做?」辛普森.費瑟史東說。他看著葛洛佛說話,好像有點驚訝的樣子。「欸,葛洛佛先生,法律說咱可以這麼做。」他回道。葛洛佛便看著他說:「這兒的法律或許如此,我們的法律卻大不相同。我們不是這麼做事的,你也不是這麼做事的。沒錯,這點你心知肚明。」葛洛佛說。「因為你受的是全然不同的教養。現在請你站起來,照媽媽說的回到你該坐的車廂去。」
你真該瞧瞧那黑麻子臉上的表情。我後來想到這事兒,還會忍不住哈哈大笑呢。當然啦,他尊重葛洛佛的判斷,一如每個人都尊重葛洛佛的判斷──他知道葛洛佛說得對──所以他站了起來,先生,他隨即站了起來,先生,沒說第二句話。他拎起自己的手提袋和大衣,順著過道快步離開我們的車廂,回到他原本的車廂,他真正該坐的地方。這個時候,那位坐在葛洛佛旁邊的紳士轉過頭來,朝我點了點頭。「我說啊──」他告訴我。「好個了不起的孩子。」當然,他看出來了,你知道。他是個明眼人。他能看出葛洛佛比絕大多數的大人都要有品有格,而他沒看走眼。
所以他就坐在那兒,你知道,那個早晨,葛洛佛就坐在位子上看著窗外的沃巴什河,看著我們看到的一座座農場。因為,我想,他長這麼大還沒見過那樣的農場──我仍記得他坐在位子上看著窗外景物的模樣。我仍記得當時他那頭烏黑的頭髮、那雙瀝青似的黑眼睛,還有他脖子上的胎記──我生的孩子裡,就你跟葛洛佛是黑髮黑眼睛,其他人生來都是一頭輕盈的金髮、灰色的眼睛,就像他們的父親。但你和葛洛佛長得就像彭特蘭家族的人,就像他們的黑髮黑眼睛,就像黑髮黑眼睛的亞歷山大和彭特蘭家族的人。你跟你李舅舅簡直是一個模子刻出來的,但葛洛佛的髮色、眼睛的顏色,又比你們倆來得黑。
所以,葛洛佛就坐在這位紳士旁邊看著窗外的景物。然後他轉過頭來,開始問這位紳士各式各樣的問題──那是什麼樹啦、那頭種了什麼作物啦、那些農場有多大啦──各式各樣的問題,而這位紳士也能應答如流,直到我開口:「哎呀,我敢說,葛洛佛!你不該提這麼多問題的。你會擾了這位紳士的清靜。」我在擔心,你知道,我怕這名紳士會因為葛洛佛東問西問而感到煩不勝煩。
這位紳士立刻仰頭大笑,開懷地大笑。我不曉得他有何來頭,也不曾請教他的大名,不過他看上去一表人才,還非常喜歡葛洛佛的樣子。我說啊,他立刻仰頭大笑,並告訴我:「您別操心這個小傢伙。他不礙事兒。」他說。「小傢伙一點都沒打擾到我。我若曉得他問題的答案,便會回答他;不知道的話,也就如實告訴他便是。小傢伙不礙事兒。」他說,還伸出手臂摟住葛洛佛的雙肩。「您就別管他了。小傢伙完全沒有打擾到我。」
我依然記得他當時的模樣,他那雙黑眼睛、那頭黑髮,以及他脖子上的胎記──他那如此沉靜、嚴肅,又那麼認真的模樣。他就這樣看著窗外的蘋果樹、農場、穀倉、屋舍和果園,將看得見的一切盡收眼底、心裡,因為,我想,這一切對他來說是那麼陌生而新奇。
孩子,孩子呀,這都是好久以前的事了,但當我又聽見那個地名,這段往事便會浮上我心頭,彷彿昨天才發生過一樣歷歷在目。而今,那道舊日的惡瘡又裂開啦。我能看見他當時的模樣,就我們一路傍著沃巴什河,為了前往博覽會而行經印第安納的那個早晨,他映在我眼中的模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