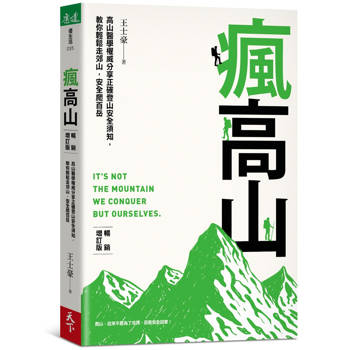19 高山喝酒,越喝越High?
有些朋友去爬高山時,都會在高山上喝酒,我年輕時也會在爬山時小酌一番。在高山上,美景當前,與夥伴們犒賞自己,幾杯黃湯下肚,感覺特別high,好像也特別容易醉。
在這之前,我們先簡單介紹一下「生理海拔」。生理海拔就是人體實際感受到的海拔高度,這會受到許多因素影響,像是特殊裝備、酒精或是激烈運動。例如,在海拔3,952 公尺的玉山,進行需要更多氧氣的跳繩激烈運動, 生理海拔就會比3,952 公尺再上升約500 公尺。或者,在海拔3,402 公尺的排雲山莊,躺在加壓完成的攜帶型加壓艙(PAC)裡面,生理海拔就會下降1,500 公尺,身體感受到的海拔高度大約是1,900 公尺。
到底,酒精作用和海拔高低有沒有相關呢? 這個問題要從4 個面向來討論:
問題1:酒精會不會讓生理海拔高度上升? 造成在平地「未爬山先登高」,或是在高山上「越喝酒,生理海拔越高」呢?
這答案是肯定的,酒精會讓生理海拔高度上升! 喝酒後,酒精會跟人體的組織細胞結合,並干擾人體組織細胞與氧氣的結合,讓組織細胞利用氧氣的效率下降,造成組織缺氧。根據醫學研究,每攝取1 盎司(28.35 ml)的純酒精, 會讓生理的海拔高度上升2,000 英尺( 約610 公尺),而且喝酒後會利尿缺水,導致生理海拔高度更進一步上升。
因此,喝一罐350ml 酒精濃度5% 的啤酒,就會讓生理海拔高度上升將近400 公尺。
所以,我們非常不建議爬高山時一開始就喝酒,這會讓你「未爬山先登高」,嚴重干擾高度適應,增加發生高山症的機率。
問題2:在高山喝酒會不會醉得比較快?
答案也是肯定的。在高山上,喝酒會醉得比較快! 酒精會讓生理海拔上升,是因為酒精和氧氣在與組織細胞結合時,會競爭相接近的位置。也就是說,有酒精時,組織細胞的氧氣結合會下降,而氧氣比較少的時候,組織細胞和酒精的結合會更容易。在高山缺氧的環境,人體吸入的氧氣比較少,血液中的氧氣也比較少。這時如果喝酒,那麼進入人體血液中的酒精,就會如入無人之境,盡情地快速與組織細胞結合。接下來,你就會發覺,喝酒後不久, 便有醉意,臉開始紅,整個人high 起來。
問題3:在高山上,酒精對人體的效應會不會比較持久?
這個答案也是肯定的,在高山上,酒精對人體的效應會比較持久。由於在高山缺氧的環境,酒精與人體組織細胞結合的效率會增加,結合的量也會增加,因此,人體需要更多的時間才能分解酒精,擺脫它的效應。而且,人體在高海拔的環境,比較容易缺水。而酒精的利尿效果,會讓人體進一步缺水。人體脫水時,血液裡的酒精濃度會上升,人體分解酒精的效率也會下降,也會造成酒精影響人體的時間延長。因此,在高山上喝酒,酒精影響人體的時間會延長,您會醉得比較久。
問題4:在高山上,酒精跟高山病的相關性?
由於酒精會造成人體脫水,而且酒精會造成組織缺氧,讓生理海拔高度上升。因此,在高山上喝酒,的確會更容易發生高山病。而且,酒醉後會造成走路不穩、人事時地物不清楚、神智不清,甚至昏迷,這些都與高海拔腦水腫的症狀相類似,容易造成混淆及誤判,錯失對於嚴重高山症病患的處置時機。
因此,在高山上喝酒,只可小酌,不可大醉。特別是,不要在一早行程開始時就喝酒,也不要在即將面臨困難路線、冰雪岩混合地形或是攀岩地形的前一天晚上或當天早上喝酒。最後,如果您過去時常發生高山症,或是您在高山上已經出現高山病的症狀,那您也千萬不要在高山上喝酒了。
至於在飛機上喝酒,會不會跟爬山一樣的身體反應呢? 民航客機,艙壓大致維持在海拔6,000 英尺至8,000 英尺,也就是大約是1,800 公尺至2,400 公尺之間。這個高度,可以兼顧飛機結構安全與旅客的舒適,並且低於高山病會發生的海拔2,500 公尺界線。然而,這還是屬於比較高的海拔,因此,喝酒後生理高度上升、比較快酒醉以及酒精影響人體的拉長等3 個效應,一樣會在搭乘客機喝酒的旅客山上發生,甚至有可能因此產生輕微頭痛及頭暈等高山病的症狀。
值得一提的是,客機機艙內濕度非常的低,人體更容易會脫水,酒精影響人體得時間會更加長,因此,在搭乘飛機時,如果要飲酒,一定要記得把水份喝夠。
那開飛機的人呢? 民航客機機師及空服員、戰鬥機或直升機飛官,是絕對不能「酒駕」的。因為,酒精造成的缺氧,會直接影響到飛行員操控飛機的能力,而酒精本身,對於腦細胞會產生麻醉、興奮及影響大腦判斷力,更會讓嚴重影響飛安。因此,機師、空服員及飛官,執行飛行任務前,可是要100% 酒測,以確保飛行安全。
24 聖母峰基地營驚險救人
2017 年3 月底,我前往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參加極限聖母峰醫學研究團隊慶祝10 週年而與尼泊爾山岳醫學會合辦的學術研討會。當中,一位尼泊爾醫師,分享了一名在海拔4,300 公尺的高海拔肺水腫病患的治療經驗。在現場,其實是由一位很有經驗的尼泊爾醫師來協助處理,可是他卻沒有處置得很理想,沒有依照高海拔肺水腫的方式處理,甚至還讓病患在海拔四千多公尺的地方觀察了2、3 天,結果症狀一天比一天惡化,最後病患陷入昏迷,醫師才趕緊叫直昇機,將病患下撤到海拔約1,350 公尺的加德滿都。所幸,病患在醫院治療幾天後,平安出院。
在聽這場演講時,我的身旁是一位英國南安普頓大學醫學院的教授,他也是國際知名的高山醫學專家。我們兩位,一邊聽,一邊搖頭。最後,我也跟他分享交流了幾年前的秋天,我去聖母峰基地營健行時,實際處理的幾個病人的經驗。
幾年前的10月, 我在距離尼泊爾聖母峰基地營(Everest Base Camp, EBC)前三個小時步程的地方,下撤。
那一次,我想要了解長天數超高海拔大眾化健行活動的健行者,一系列的生理與病理變化,走訪了一次聖母峰基地營,實際以一個高海拔健行者、醫學研究者及高山醫學醫師的身份,用自己的身體,與同行夥伴,一起感受尼泊爾最負盛名的國際級健行路線。
從家裡出發,到桃園機場,到加德滿都,就如同一般出國行程、行禮如儀的搭機與轉機。唯一的不同,是打包行李時,托運行李重量的拿捏。因為,隔天從加德滿都到盧卡拉,需搭乘雙引擎小飛機,這一趟約一小時的飛行, 降落在全世界最危險的盧卡拉機場,有嚴格的限重限制,每個人的托運行李只能15 公斤。可是,我除了有個人行李,還有為了做醫學探索所需的器材及問卷。在打包行李時,著實的花了好大的工夫。
從第二天開始,就是標準的EBC 健行。第二天,4 點起床,拂曉便趕往機場。小飛機約莫9 點於海拔1,350 公尺的加德滿都國際機場起飛。10 點, 安全抵達海拔2,850 公尺的盧卡拉。中午過後,開始健行,傍晚很順利的到達住宿地點,海拔2,640 公尺的法客定。之後,預計的住宿點分別是第三天住海拔3,440 公尺的南崎巴札、第四天住海拔3,860 公尺的湯波崎、第五天住海拔4,410 公尺的丁波崎,第六天原地停留做高度適應,接著第七天住海拔4,910 公尺的羅布崎,第八天抵達海拔5,400 公尺的EBC 後住海拔5,170 公尺的高樂雪,第九天下山住海拔4,280 公尺的斐麗崎,第十天住海拔3,440 公尺的南崎巴札,第十一天住海拔2,850 公尺的盧卡拉,第十二天回到海拔1,350 公尺的加德滿都。
這一趟行程,我每天早餐、中餐與晚餐的時段,都對隊友們,進行生理指標的測量,以及完成身體評估。一路下來, 十幾天, 我每一餐都要花費將近30 分鐘來做研究,一天花一個半小時,總共做了快四十次的測量。而我每頓飯的吃飯時間從40 分鐘變成10 分鐘內解決。所有隊友都很樂意接受研究。因為,研究本身可以提供隊友們更大的保護,讓我們有機會提早察覺不正常的生理指標以及身體不適,可以直接提升這趟EBC 健行隊伍的安全。
可是,我自己也是第一次走訪EBC 的登山健行者, 也同時擔任醫學研究者,蠟燭兩頭燒,這真的是用生命在執行的高海拔醫學研究啊! 殊不知,,冥冥之中註定,這次行程,我還肩負更重要的任務。
從盧卡拉起,開始健行的前幾天,所有隊友狀況都非常良好。在第五天,海拔接近4,000 公尺處,有一位隊友出狀況了! 他血氧飽和度接近60%,心跳些微偏快,嘴唇蒼白無血色,而且他行進時比較吃力,但是卻沒有很喘。我心中的警鈴大響,這是某些心血管疾病的症狀。後來,細問之下,原來他小時候就發現有先天性心臟病,由於在平地生活甚至輕度運動都沒有異狀,所以沒有特別治療。然而,這次在超高海拔地區健行時,症狀出現了。此時,我建議這位隊員需要立即下撤,減少活動,至少撤到海拔3,440 公尺的南崎巴札。於是,他立即搭乘馬匹下撤,我則貼身護送他。這位隊友下撤到3,860 公尺的湯波崎時,症狀明顯緩解。因為隨同病人下撤,我多待了一個晚上湯波崎,我高度適應地點也從原本規劃的海拔4,410 公尺的丁波崎,變成海拔3,860 公尺的湯波崎。
第六天上午,那位隊友症狀緩解,繼續騎馬下撤到海拔3,440 公尺的南崎巴札。我則是騎馬往上走,準備返隊。可能是平常有在登山,體能還算良好,我第六天要返回丁波崎與大隊會合時,從海拔3,900 公尺處,下馬開始步行到海拔4,410 公尺的丁波崎,五公里,背了快八公斤的小背包,我居然只花1 小時15 分鐘就完成,隨行的尼泊爾協作,頻頻對我說:「王醫師,我知道您很強壯,但是,走慢一點。」終於,在第六天下午,到達丁波崎,跟大隊會合。
第六天下午2 點,我回到大隊,在當晚住宿地跟夥伴們談天說笑時。我突然瞥見同住宿處另一支要去島峰(Island Peak, 海拔6,189 公尺)的隊伍,有一個人臉色有異。我趕緊主動做評估,發現他的症狀已經接近高海拔肺水腫的診斷標準,且當時他的血氧只有接近60%。我立即對他投與完整的藥物治療。事實上,他當時應該要下撤了,然而,他是那支要去島峰隊伍的重要人物,我當時對他說:「照理說,您現在吃完藥之後,就必須要下撤。但是,如果6 小時內,我針對您做評估,若您的症狀完全消失,說不定可以繼續前進。然而,如果症狀沒有改善、甚至持續惡化、或在接下來的行程症狀復發,則需要立即下撤。
他是我此行處置的第二個病人。我在第一時間察覺異常症狀並正確診斷,緊接著當機立斷的投藥,以及在山神的眷顧下。在當天傍晚5 點,他的血氧回升到百分之七十幾,症狀明顯減輕。在當天晚上九點,血氧改善且穩定維持於百分之八十幾,且症狀幾乎完全消失。隔天早上,他血氧回到接近九十,身體恢復到像一尾活龍,症狀完全消失。幾天後,他平安順利的帶著隊伍完成攀登島峰的任務。
這也許是剛好有遇到高山專業醫師的福利吧,還可以針對病情精準觀察幾個小時到隔天。如果現場沒有醫師,我仍然建議要遵守高山症的處置原則,高海拔肺水腫的病人,必須要立即下撤,並同時做必要處置。
第七天下午,在經過許多在聖母峰攀登時罹難的登山家的衣冠塚後不久,抵達海拔4,910 公尺的羅布崎。在安頓好行李後,我很開心的量測自己的血氧,「哇,我平靜呼吸時血氧可以到97%!」現場尼泊爾嚮導驚訝的說: 王醫師,昨天看您走得飛快,現在高度適應又這麼好,您有沒有考慮去攀登聖母峰?
身為很「帶賽」的急診醫師,病人常常會找上我。快樂的時光,過得很快,自己得意時,往往病人就來了。在晚餐時,我對隊友們進行生理指標量測。這時候,有一位女隊友,心跳每分鐘超過120 下,血氧只有百分之五十幾,還有輕微發燒。她說她身體很不舒服,而且臉色真的很差。我一看,不妙,她發生了高海拔肺水腫。後來,我立即對她投藥、打針注射高劑量類固醇(救命針)及使用氧氣鋼瓶給氧。經過2 個小時的治療,這位女隊友說她很想睡,想睡一下,可是,她的血氧只有百分之四十幾,醒來時,使用高流量氧氣的狀態下,血氧只有六十幾,而且,症狀越來越加重。大家看了憂心忡忡,我則直接講: 「今晚咱們要加班了,她需要連夜下撤!」。
此時, 是晚上九點半, 當地領隊及嚮導說:「王醫師, 我們護送她下去就好, 您第一次來, 您明天去EBC。」我聽完,回答:「您們是領隊及嚮導,請繼續完成原本的任務,把隊友們安全帶到EBC。這位女隊友, 病情如此嚴重,她下撤期間,需要醫師照顧。因此,沒關係,雖然這裡離EBC 走路只剩下3 小時,但是,我護送她下撤,並隨行給予醫療照顧。」
接著,我跟那位女隊友說明:「妳發生了高海拔肺水腫,症狀越來越嚴重,血氧很低,目前,命在旦夕,我們怕妳一睡著,就會過世。因此,我們現在要連夜把妳帶下山。相信我,別擔心,我們會把妳安全帶下山的。」
於是乎,我在距EBC 前3 小時步程的地方,下撤。
協助病患下撤的編組,是2 位尼泊爾的嚮導輪流揹人及帶路,另一位領隊則打點相關行政及開銷,以及我擔任隨行醫師照顧病人。
大約晚上10 點出發,只花了3 個小時,半夜1 點, 就用人力背負的方式, 將病患撤到海拔4,620 公尺的THUKLA(杜格拉),那是一個很迷你的聚落,有幾間小旅館。當時,天寒地凍,溫度攝氏零下十幾度,人員疲憊,大伙也快凍成冰棒,我們趕緊敲門,叫醒其中一間旅館的老闆,暫住一宿,稍作休息。
當時,我告訴自己,要觀察病人的病情,千萬不能睡著,因為病人可能隨時會過世,但是,忙了一天一夜,實在是很疲憊、難耐睡意,約莫是半夜兩點時,我不知不覺地沉沉入睡。
「王醫師! 王醫師!」我迷迷糊糊中聽到叫喚聲後猛然驚醒,一看時間,已經是上午6 點。一醒來,我大叫一聲:「完蛋了! 我怎麼睡著了! 她還活著嗎?」
接著聽到聲音說:「王醫師,我還活著啦! 可是我頭好痛,可以給我一顆止痛藥嗎? 我知道您很累,希望您不要生氣!」原來是那位女隊友。
我嚇了一大跳,我居然睡著了! 此時,雖然我從睡夢中被挖起來,但是卻沒有任何生氣的情緒,反而我非常高興的對她說:「啊,抱歉,我居然睡著了! 沒問題,我立刻給妳止痛藥。」我還說:「妳可以把我叫起來,代表妳還活著! 我太開心了,我完全沒有生氣。」
我給她服用包含止痛藥在內的高海拔肺水腫用藥後, 再幫她注射一針救命針類固醇,並幫她量血氧,此時,她清醒狀態下的血氧58%,臉色依舊呈現嚴重缺氧病徵。她依然生命垂危!
我隨即開始與嚮導及領隊們討論接下來白天的下撤方式,由於,這位女隊友當天至少需要下撤到南崎巴札,這路程非常遙遠,二十幾公里,平常速度,要走16 個小時以上,我們直覺的認為馬匹可能一天走不到,我們也問到直升機的費用當時報價是2 萬美金,現金交易,正當我們覺得人命無價,這個價錢可以接受時。我們看見門外有2 匹馬在吃草。於是,抱著姑且一試的心態,向馬匹主人提出需求。
我們的需求是,一天下撤到海拔高度相差1,200 公尺,二十幾公里外的南崎巴札。沒想到,馬匹主人說: 「可以呀。」, 一匹馬600 美金, 兩匹1,200 美金。Bingo ! 我們大聲歡呼,立刻付現金馬上成交,深怕馬主人反悔。
第八天,原本應該是抵達EBC 的時刻。我陪著那位女隊友, 騎著馬, 早上7 點, 由海拔4,620 公尺的THUKLA 出發,下午5 點,抵達海拔3,440 公尺的南崎巴札。抵達南崎巴札後,那位女隊友的症狀明顯緩解,休息時幾乎已經沒有症狀,走路時還有一點呼吸急促,而沒有使用氧氣狀態下休息時的血氧,則已經回升到96%。而在這裡,我也遇到先前因為先天性心臟病而撤退的第一個隊友,他這時已經完全沒有任何症狀。
而我們雇用的這兩匹馬,其中一匹馬一度被我們操到腿軟跌倒,還好我們反應夠快,即時跳開沒有受傷。中午午休時,兩匹馬各吃了2 大臉盆的馬鈴薯當午餐。嘿,真是難為及大大感謝牠們這兩匹救命「神獸」啊!
太棒了,2 位隊友的警報,幾乎都解除了! 當晚,經過討論後,我們決定,如果女隊友的病情持續好轉,那我們下撤的一行人,就在南崎巴札住上3 個晚上,在第十天與大隊下山的隊伍會合,並於第十一天,跟著大隊一起下山。當然,如果症狀再度惡化,則必須繼續下撤到盧卡拉,甚至直接撤到加德滿都。必須再次強調的是,這是在有高山醫學專業醫師在場,並且病患的病情恢復良好,才能夠像這樣讓病人在南崎巴札中途停留。如果大家到聖母峰基地營健行,萬一發生高海拔肺水腫或高海拔腦水腫, 一旦沒有醫師在場,您還是必須要將病患直接撤退到海拔1,350 公尺的加德滿都,不可在中途停留。
她是我在這次的活動中,成功處置的第3 個病人。我們在沒有使用到直升機的情況下,使用人力背負及馬匹, 由海拔4,910 公尺的羅布崎輾轉下撤到海拔3,440 公尺的南崎巴札, 下降高度將近1,500 公尺, 路程超過20 公里,僅僅花了19 個小時,就成功的讓生命垂危的高海拔肺水腫病患,轉危為安。
當天晚上,我詢問那位女隊友,妳知道昨天晚上,妳的病情有多嚴重嗎? 她說:「不知道。」我當時找不到適當的文字來形容,不過,尼泊爾當地嚮導立刻幫我接話: 「上個星期,您們還沒到加德滿都的時候,有一位來自印度的健行者,在海拔3,860 公尺的湯波崎當晚,出現跟妳類似的症狀,那個印度人的血氧五十幾,還比妳的血氧高。當時,隊友趕緊幫他叫直升機,但是他的隊友們都不是醫師,沒有給他任何現場治療,而直升機要隔天才能到。於是他們讓病患原地停留等待到隔天。
隔天,病患還必須要被移到一座吊橋空曠處,直升機才能吊掛。他們在搬運病患到吊橋的途中,病患身體越來越虛弱,逐漸陷入昏迷。抵達吊橋,直升機吊掛時,病患已經一動也不動。吊掛上直昇機之後,病患已經心跳停止,機上救護人員開始對病患CPR(心肺復甦術),後來, 急救無效, 那位來自印度的健行者在直升機上死亡。」
尼泊爾嚮導講完這個上週才剛發生的案例後,那位女隊友表情驚恐,整個人呆掉,口中喃喃自語一直對我們說:「謝謝您們! 謝謝醫師!」
第九天,那位女隊友的症狀更加好轉,只剩下走路時比較費力。第十天,那位女隊友高海拔肺水腫的症狀完全消失,當天早上,她看到尼泊爾當地可愛的小朋友,由於她的職業是瑜伽老師,她就開始教那些兒童做瑜伽。
看到兩天前還生命垂危的隊友,現在在教孩子們做瑜伽,這真是此行中最美麗的風景,對一個醫師而言,這無疑地是最快樂的一刻! 這比到達EBC,還要令人開心。當時,我立刻拿起相機,記錄下這個畫面,按下快門時,我內心非常非常激動,熱淚盈眶,我堅定的對自己說:「這就是身為一個醫師應該要做的事!」
時間再回到2017 年3 月底。
「這就是身為一個醫師應該要做的事!」我分享完經驗後,以這句話當結尾。
「王醫師,幹得好! 您處理嚴重高山病病患的能力, 已經超越國際水準了。」那位英國南安普頓大學醫學院教授對我說。
有些朋友去爬高山時,都會在高山上喝酒,我年輕時也會在爬山時小酌一番。在高山上,美景當前,與夥伴們犒賞自己,幾杯黃湯下肚,感覺特別high,好像也特別容易醉。
在這之前,我們先簡單介紹一下「生理海拔」。生理海拔就是人體實際感受到的海拔高度,這會受到許多因素影響,像是特殊裝備、酒精或是激烈運動。例如,在海拔3,952 公尺的玉山,進行需要更多氧氣的跳繩激烈運動, 生理海拔就會比3,952 公尺再上升約500 公尺。或者,在海拔3,402 公尺的排雲山莊,躺在加壓完成的攜帶型加壓艙(PAC)裡面,生理海拔就會下降1,500 公尺,身體感受到的海拔高度大約是1,900 公尺。
到底,酒精作用和海拔高低有沒有相關呢? 這個問題要從4 個面向來討論:
問題1:酒精會不會讓生理海拔高度上升? 造成在平地「未爬山先登高」,或是在高山上「越喝酒,生理海拔越高」呢?
這答案是肯定的,酒精會讓生理海拔高度上升! 喝酒後,酒精會跟人體的組織細胞結合,並干擾人體組織細胞與氧氣的結合,讓組織細胞利用氧氣的效率下降,造成組織缺氧。根據醫學研究,每攝取1 盎司(28.35 ml)的純酒精, 會讓生理的海拔高度上升2,000 英尺( 約610 公尺),而且喝酒後會利尿缺水,導致生理海拔高度更進一步上升。
因此,喝一罐350ml 酒精濃度5% 的啤酒,就會讓生理海拔高度上升將近400 公尺。
所以,我們非常不建議爬高山時一開始就喝酒,這會讓你「未爬山先登高」,嚴重干擾高度適應,增加發生高山症的機率。
問題2:在高山喝酒會不會醉得比較快?
答案也是肯定的。在高山上,喝酒會醉得比較快! 酒精會讓生理海拔上升,是因為酒精和氧氣在與組織細胞結合時,會競爭相接近的位置。也就是說,有酒精時,組織細胞的氧氣結合會下降,而氧氣比較少的時候,組織細胞和酒精的結合會更容易。在高山缺氧的環境,人體吸入的氧氣比較少,血液中的氧氣也比較少。這時如果喝酒,那麼進入人體血液中的酒精,就會如入無人之境,盡情地快速與組織細胞結合。接下來,你就會發覺,喝酒後不久, 便有醉意,臉開始紅,整個人high 起來。
問題3:在高山上,酒精對人體的效應會不會比較持久?
這個答案也是肯定的,在高山上,酒精對人體的效應會比較持久。由於在高山缺氧的環境,酒精與人體組織細胞結合的效率會增加,結合的量也會增加,因此,人體需要更多的時間才能分解酒精,擺脫它的效應。而且,人體在高海拔的環境,比較容易缺水。而酒精的利尿效果,會讓人體進一步缺水。人體脫水時,血液裡的酒精濃度會上升,人體分解酒精的效率也會下降,也會造成酒精影響人體的時間延長。因此,在高山上喝酒,酒精影響人體的時間會延長,您會醉得比較久。
問題4:在高山上,酒精跟高山病的相關性?
由於酒精會造成人體脫水,而且酒精會造成組織缺氧,讓生理海拔高度上升。因此,在高山上喝酒,的確會更容易發生高山病。而且,酒醉後會造成走路不穩、人事時地物不清楚、神智不清,甚至昏迷,這些都與高海拔腦水腫的症狀相類似,容易造成混淆及誤判,錯失對於嚴重高山症病患的處置時機。
因此,在高山上喝酒,只可小酌,不可大醉。特別是,不要在一早行程開始時就喝酒,也不要在即將面臨困難路線、冰雪岩混合地形或是攀岩地形的前一天晚上或當天早上喝酒。最後,如果您過去時常發生高山症,或是您在高山上已經出現高山病的症狀,那您也千萬不要在高山上喝酒了。
至於在飛機上喝酒,會不會跟爬山一樣的身體反應呢? 民航客機,艙壓大致維持在海拔6,000 英尺至8,000 英尺,也就是大約是1,800 公尺至2,400 公尺之間。這個高度,可以兼顧飛機結構安全與旅客的舒適,並且低於高山病會發生的海拔2,500 公尺界線。然而,這還是屬於比較高的海拔,因此,喝酒後生理高度上升、比較快酒醉以及酒精影響人體的拉長等3 個效應,一樣會在搭乘客機喝酒的旅客山上發生,甚至有可能因此產生輕微頭痛及頭暈等高山病的症狀。
值得一提的是,客機機艙內濕度非常的低,人體更容易會脫水,酒精影響人體得時間會更加長,因此,在搭乘飛機時,如果要飲酒,一定要記得把水份喝夠。
那開飛機的人呢? 民航客機機師及空服員、戰鬥機或直升機飛官,是絕對不能「酒駕」的。因為,酒精造成的缺氧,會直接影響到飛行員操控飛機的能力,而酒精本身,對於腦細胞會產生麻醉、興奮及影響大腦判斷力,更會讓嚴重影響飛安。因此,機師、空服員及飛官,執行飛行任務前,可是要100% 酒測,以確保飛行安全。
24 聖母峰基地營驚險救人
2017 年3 月底,我前往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參加極限聖母峰醫學研究團隊慶祝10 週年而與尼泊爾山岳醫學會合辦的學術研討會。當中,一位尼泊爾醫師,分享了一名在海拔4,300 公尺的高海拔肺水腫病患的治療經驗。在現場,其實是由一位很有經驗的尼泊爾醫師來協助處理,可是他卻沒有處置得很理想,沒有依照高海拔肺水腫的方式處理,甚至還讓病患在海拔四千多公尺的地方觀察了2、3 天,結果症狀一天比一天惡化,最後病患陷入昏迷,醫師才趕緊叫直昇機,將病患下撤到海拔約1,350 公尺的加德滿都。所幸,病患在醫院治療幾天後,平安出院。
在聽這場演講時,我的身旁是一位英國南安普頓大學醫學院的教授,他也是國際知名的高山醫學專家。我們兩位,一邊聽,一邊搖頭。最後,我也跟他分享交流了幾年前的秋天,我去聖母峰基地營健行時,實際處理的幾個病人的經驗。
幾年前的10月, 我在距離尼泊爾聖母峰基地營(Everest Base Camp, EBC)前三個小時步程的地方,下撤。
那一次,我想要了解長天數超高海拔大眾化健行活動的健行者,一系列的生理與病理變化,走訪了一次聖母峰基地營,實際以一個高海拔健行者、醫學研究者及高山醫學醫師的身份,用自己的身體,與同行夥伴,一起感受尼泊爾最負盛名的國際級健行路線。
從家裡出發,到桃園機場,到加德滿都,就如同一般出國行程、行禮如儀的搭機與轉機。唯一的不同,是打包行李時,托運行李重量的拿捏。因為,隔天從加德滿都到盧卡拉,需搭乘雙引擎小飛機,這一趟約一小時的飛行, 降落在全世界最危險的盧卡拉機場,有嚴格的限重限制,每個人的托運行李只能15 公斤。可是,我除了有個人行李,還有為了做醫學探索所需的器材及問卷。在打包行李時,著實的花了好大的工夫。
從第二天開始,就是標準的EBC 健行。第二天,4 點起床,拂曉便趕往機場。小飛機約莫9 點於海拔1,350 公尺的加德滿都國際機場起飛。10 點, 安全抵達海拔2,850 公尺的盧卡拉。中午過後,開始健行,傍晚很順利的到達住宿地點,海拔2,640 公尺的法客定。之後,預計的住宿點分別是第三天住海拔3,440 公尺的南崎巴札、第四天住海拔3,860 公尺的湯波崎、第五天住海拔4,410 公尺的丁波崎,第六天原地停留做高度適應,接著第七天住海拔4,910 公尺的羅布崎,第八天抵達海拔5,400 公尺的EBC 後住海拔5,170 公尺的高樂雪,第九天下山住海拔4,280 公尺的斐麗崎,第十天住海拔3,440 公尺的南崎巴札,第十一天住海拔2,850 公尺的盧卡拉,第十二天回到海拔1,350 公尺的加德滿都。
這一趟行程,我每天早餐、中餐與晚餐的時段,都對隊友們,進行生理指標的測量,以及完成身體評估。一路下來, 十幾天, 我每一餐都要花費將近30 分鐘來做研究,一天花一個半小時,總共做了快四十次的測量。而我每頓飯的吃飯時間從40 分鐘變成10 分鐘內解決。所有隊友都很樂意接受研究。因為,研究本身可以提供隊友們更大的保護,讓我們有機會提早察覺不正常的生理指標以及身體不適,可以直接提升這趟EBC 健行隊伍的安全。
可是,我自己也是第一次走訪EBC 的登山健行者, 也同時擔任醫學研究者,蠟燭兩頭燒,這真的是用生命在執行的高海拔醫學研究啊! 殊不知,,冥冥之中註定,這次行程,我還肩負更重要的任務。
從盧卡拉起,開始健行的前幾天,所有隊友狀況都非常良好。在第五天,海拔接近4,000 公尺處,有一位隊友出狀況了! 他血氧飽和度接近60%,心跳些微偏快,嘴唇蒼白無血色,而且他行進時比較吃力,但是卻沒有很喘。我心中的警鈴大響,這是某些心血管疾病的症狀。後來,細問之下,原來他小時候就發現有先天性心臟病,由於在平地生活甚至輕度運動都沒有異狀,所以沒有特別治療。然而,這次在超高海拔地區健行時,症狀出現了。此時,我建議這位隊員需要立即下撤,減少活動,至少撤到海拔3,440 公尺的南崎巴札。於是,他立即搭乘馬匹下撤,我則貼身護送他。這位隊友下撤到3,860 公尺的湯波崎時,症狀明顯緩解。因為隨同病人下撤,我多待了一個晚上湯波崎,我高度適應地點也從原本規劃的海拔4,410 公尺的丁波崎,變成海拔3,860 公尺的湯波崎。
第六天上午,那位隊友症狀緩解,繼續騎馬下撤到海拔3,440 公尺的南崎巴札。我則是騎馬往上走,準備返隊。可能是平常有在登山,體能還算良好,我第六天要返回丁波崎與大隊會合時,從海拔3,900 公尺處,下馬開始步行到海拔4,410 公尺的丁波崎,五公里,背了快八公斤的小背包,我居然只花1 小時15 分鐘就完成,隨行的尼泊爾協作,頻頻對我說:「王醫師,我知道您很強壯,但是,走慢一點。」終於,在第六天下午,到達丁波崎,跟大隊會合。
第六天下午2 點,我回到大隊,在當晚住宿地跟夥伴們談天說笑時。我突然瞥見同住宿處另一支要去島峰(Island Peak, 海拔6,189 公尺)的隊伍,有一個人臉色有異。我趕緊主動做評估,發現他的症狀已經接近高海拔肺水腫的診斷標準,且當時他的血氧只有接近60%。我立即對他投與完整的藥物治療。事實上,他當時應該要下撤了,然而,他是那支要去島峰隊伍的重要人物,我當時對他說:「照理說,您現在吃完藥之後,就必須要下撤。但是,如果6 小時內,我針對您做評估,若您的症狀完全消失,說不定可以繼續前進。然而,如果症狀沒有改善、甚至持續惡化、或在接下來的行程症狀復發,則需要立即下撤。
他是我此行處置的第二個病人。我在第一時間察覺異常症狀並正確診斷,緊接著當機立斷的投藥,以及在山神的眷顧下。在當天傍晚5 點,他的血氧回升到百分之七十幾,症狀明顯減輕。在當天晚上九點,血氧改善且穩定維持於百分之八十幾,且症狀幾乎完全消失。隔天早上,他血氧回到接近九十,身體恢復到像一尾活龍,症狀完全消失。幾天後,他平安順利的帶著隊伍完成攀登島峰的任務。
這也許是剛好有遇到高山專業醫師的福利吧,還可以針對病情精準觀察幾個小時到隔天。如果現場沒有醫師,我仍然建議要遵守高山症的處置原則,高海拔肺水腫的病人,必須要立即下撤,並同時做必要處置。
第七天下午,在經過許多在聖母峰攀登時罹難的登山家的衣冠塚後不久,抵達海拔4,910 公尺的羅布崎。在安頓好行李後,我很開心的量測自己的血氧,「哇,我平靜呼吸時血氧可以到97%!」現場尼泊爾嚮導驚訝的說: 王醫師,昨天看您走得飛快,現在高度適應又這麼好,您有沒有考慮去攀登聖母峰?
身為很「帶賽」的急診醫師,病人常常會找上我。快樂的時光,過得很快,自己得意時,往往病人就來了。在晚餐時,我對隊友們進行生理指標量測。這時候,有一位女隊友,心跳每分鐘超過120 下,血氧只有百分之五十幾,還有輕微發燒。她說她身體很不舒服,而且臉色真的很差。我一看,不妙,她發生了高海拔肺水腫。後來,我立即對她投藥、打針注射高劑量類固醇(救命針)及使用氧氣鋼瓶給氧。經過2 個小時的治療,這位女隊友說她很想睡,想睡一下,可是,她的血氧只有百分之四十幾,醒來時,使用高流量氧氣的狀態下,血氧只有六十幾,而且,症狀越來越加重。大家看了憂心忡忡,我則直接講: 「今晚咱們要加班了,她需要連夜下撤!」。
此時, 是晚上九點半, 當地領隊及嚮導說:「王醫師, 我們護送她下去就好, 您第一次來, 您明天去EBC。」我聽完,回答:「您們是領隊及嚮導,請繼續完成原本的任務,把隊友們安全帶到EBC。這位女隊友, 病情如此嚴重,她下撤期間,需要醫師照顧。因此,沒關係,雖然這裡離EBC 走路只剩下3 小時,但是,我護送她下撤,並隨行給予醫療照顧。」
接著,我跟那位女隊友說明:「妳發生了高海拔肺水腫,症狀越來越嚴重,血氧很低,目前,命在旦夕,我們怕妳一睡著,就會過世。因此,我們現在要連夜把妳帶下山。相信我,別擔心,我們會把妳安全帶下山的。」
於是乎,我在距EBC 前3 小時步程的地方,下撤。
協助病患下撤的編組,是2 位尼泊爾的嚮導輪流揹人及帶路,另一位領隊則打點相關行政及開銷,以及我擔任隨行醫師照顧病人。
大約晚上10 點出發,只花了3 個小時,半夜1 點, 就用人力背負的方式, 將病患撤到海拔4,620 公尺的THUKLA(杜格拉),那是一個很迷你的聚落,有幾間小旅館。當時,天寒地凍,溫度攝氏零下十幾度,人員疲憊,大伙也快凍成冰棒,我們趕緊敲門,叫醒其中一間旅館的老闆,暫住一宿,稍作休息。
當時,我告訴自己,要觀察病人的病情,千萬不能睡著,因為病人可能隨時會過世,但是,忙了一天一夜,實在是很疲憊、難耐睡意,約莫是半夜兩點時,我不知不覺地沉沉入睡。
「王醫師! 王醫師!」我迷迷糊糊中聽到叫喚聲後猛然驚醒,一看時間,已經是上午6 點。一醒來,我大叫一聲:「完蛋了! 我怎麼睡著了! 她還活著嗎?」
接著聽到聲音說:「王醫師,我還活著啦! 可是我頭好痛,可以給我一顆止痛藥嗎? 我知道您很累,希望您不要生氣!」原來是那位女隊友。
我嚇了一大跳,我居然睡著了! 此時,雖然我從睡夢中被挖起來,但是卻沒有任何生氣的情緒,反而我非常高興的對她說:「啊,抱歉,我居然睡著了! 沒問題,我立刻給妳止痛藥。」我還說:「妳可以把我叫起來,代表妳還活著! 我太開心了,我完全沒有生氣。」
我給她服用包含止痛藥在內的高海拔肺水腫用藥後, 再幫她注射一針救命針類固醇,並幫她量血氧,此時,她清醒狀態下的血氧58%,臉色依舊呈現嚴重缺氧病徵。她依然生命垂危!
我隨即開始與嚮導及領隊們討論接下來白天的下撤方式,由於,這位女隊友當天至少需要下撤到南崎巴札,這路程非常遙遠,二十幾公里,平常速度,要走16 個小時以上,我們直覺的認為馬匹可能一天走不到,我們也問到直升機的費用當時報價是2 萬美金,現金交易,正當我們覺得人命無價,這個價錢可以接受時。我們看見門外有2 匹馬在吃草。於是,抱著姑且一試的心態,向馬匹主人提出需求。
我們的需求是,一天下撤到海拔高度相差1,200 公尺,二十幾公里外的南崎巴札。沒想到,馬匹主人說: 「可以呀。」, 一匹馬600 美金, 兩匹1,200 美金。Bingo ! 我們大聲歡呼,立刻付現金馬上成交,深怕馬主人反悔。
第八天,原本應該是抵達EBC 的時刻。我陪著那位女隊友, 騎著馬, 早上7 點, 由海拔4,620 公尺的THUKLA 出發,下午5 點,抵達海拔3,440 公尺的南崎巴札。抵達南崎巴札後,那位女隊友的症狀明顯緩解,休息時幾乎已經沒有症狀,走路時還有一點呼吸急促,而沒有使用氧氣狀態下休息時的血氧,則已經回升到96%。而在這裡,我也遇到先前因為先天性心臟病而撤退的第一個隊友,他這時已經完全沒有任何症狀。
而我們雇用的這兩匹馬,其中一匹馬一度被我們操到腿軟跌倒,還好我們反應夠快,即時跳開沒有受傷。中午午休時,兩匹馬各吃了2 大臉盆的馬鈴薯當午餐。嘿,真是難為及大大感謝牠們這兩匹救命「神獸」啊!
太棒了,2 位隊友的警報,幾乎都解除了! 當晚,經過討論後,我們決定,如果女隊友的病情持續好轉,那我們下撤的一行人,就在南崎巴札住上3 個晚上,在第十天與大隊下山的隊伍會合,並於第十一天,跟著大隊一起下山。當然,如果症狀再度惡化,則必須繼續下撤到盧卡拉,甚至直接撤到加德滿都。必須再次強調的是,這是在有高山醫學專業醫師在場,並且病患的病情恢復良好,才能夠像這樣讓病人在南崎巴札中途停留。如果大家到聖母峰基地營健行,萬一發生高海拔肺水腫或高海拔腦水腫, 一旦沒有醫師在場,您還是必須要將病患直接撤退到海拔1,350 公尺的加德滿都,不可在中途停留。
她是我在這次的活動中,成功處置的第3 個病人。我們在沒有使用到直升機的情況下,使用人力背負及馬匹, 由海拔4,910 公尺的羅布崎輾轉下撤到海拔3,440 公尺的南崎巴札, 下降高度將近1,500 公尺, 路程超過20 公里,僅僅花了19 個小時,就成功的讓生命垂危的高海拔肺水腫病患,轉危為安。
當天晚上,我詢問那位女隊友,妳知道昨天晚上,妳的病情有多嚴重嗎? 她說:「不知道。」我當時找不到適當的文字來形容,不過,尼泊爾當地嚮導立刻幫我接話: 「上個星期,您們還沒到加德滿都的時候,有一位來自印度的健行者,在海拔3,860 公尺的湯波崎當晚,出現跟妳類似的症狀,那個印度人的血氧五十幾,還比妳的血氧高。當時,隊友趕緊幫他叫直升機,但是他的隊友們都不是醫師,沒有給他任何現場治療,而直升機要隔天才能到。於是他們讓病患原地停留等待到隔天。
隔天,病患還必須要被移到一座吊橋空曠處,直升機才能吊掛。他們在搬運病患到吊橋的途中,病患身體越來越虛弱,逐漸陷入昏迷。抵達吊橋,直升機吊掛時,病患已經一動也不動。吊掛上直昇機之後,病患已經心跳停止,機上救護人員開始對病患CPR(心肺復甦術),後來, 急救無效, 那位來自印度的健行者在直升機上死亡。」
尼泊爾嚮導講完這個上週才剛發生的案例後,那位女隊友表情驚恐,整個人呆掉,口中喃喃自語一直對我們說:「謝謝您們! 謝謝醫師!」
第九天,那位女隊友的症狀更加好轉,只剩下走路時比較費力。第十天,那位女隊友高海拔肺水腫的症狀完全消失,當天早上,她看到尼泊爾當地可愛的小朋友,由於她的職業是瑜伽老師,她就開始教那些兒童做瑜伽。
看到兩天前還生命垂危的隊友,現在在教孩子們做瑜伽,這真是此行中最美麗的風景,對一個醫師而言,這無疑地是最快樂的一刻! 這比到達EBC,還要令人開心。當時,我立刻拿起相機,記錄下這個畫面,按下快門時,我內心非常非常激動,熱淚盈眶,我堅定的對自己說:「這就是身為一個醫師應該要做的事!」
時間再回到2017 年3 月底。
「這就是身為一個醫師應該要做的事!」我分享完經驗後,以這句話當結尾。
「王醫師,幹得好! 您處理嚴重高山病病患的能力, 已經超越國際水準了。」那位英國南安普頓大學醫學院教授對我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