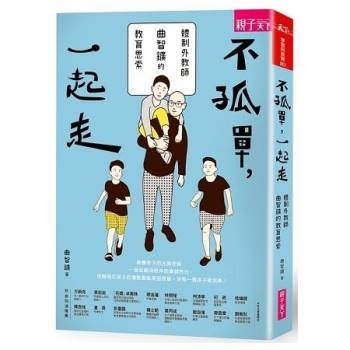【後記】生命的鬆綁與療癒
用智鑛的話說,我會認識他,也是「生命中有意義的巧合」。
原本沒有交集的兩個人,應該是因為「教育」這條線連上的;而我並不是專業老師,只是為了實踐公益旅行+深度旅行的夢想,曾經赴大陸山區小學擔任志工老師(大陸稱為「支教」)三年多。那段給山裡孩子當老師的經歷和記憶,是生命中獨特而難忘的「老師」生涯。
因為這段經歷,大學同學佩芬找到我,為智鑛的第一本書擔任文字整理工作。因緣際會,接下了原本不會接下的工作,因為這位特教老師很「特別」,他用自己獨樹一幟的方式在從事教育這件事,讓我很好奇,尤其是他強調「在實際的情境中學習」,常常帶孩子到外面活動,甚至去旅行……讓我十分認同且佩服。
在此之前,我對「特殊教育」可說是一無所知,接下這份工作後才開始慢慢了解︰原來過動的孩子是這樣的!想起從小到大很討厭的那種男生︰總是很白目,總是喜歡作弄別人,總是開些很不好笑的玩笑,總是很不文靜很不文明很無禮……原來他們不是故意的!
這個遲來的「看見」和「發現」,讓我有醍醐灌頂之感。原來,我誤會了「他們」那麼多年!心裡有種深深的歉疚。因為不了解,我像其他人一樣,嫌棄、討厭他們,而如果是與生俱來的特質,誰有權利去嫌棄、討厭誰?那不過是自以為高人一等的傲慢。
我也十分認同智鑛所說的「光譜」概念。與其用疾病的分類把人標籤化,不如以光譜的漸層來看待、理解每一個人,就如沒有一個人是絕對的內向或外向、悲觀或樂觀,每一個人,或多或少都有注意力不集中、活在自己的世界裡等特質,只是比重不同(而這個「比重」,和情境還有很大的關係)。平心而論,我的弟弟就有些自閉症的特質,只是那個年代「特教」還不發達;而我自己也有點亞斯伯格(智鑛說,現在沒有亞斯伯格了,都叫自閉症),只是沒有被「判定」。
漸漸發現︰特殊教育,其實能幫助人更理解他人、理解世界,能夠讓心更柔軟、更開放、更有愛。我感覺到︰成長的機會來了。
見面之前,我透過臉書先了解智鑛。那時他正在大陸沿海岸線滑行之旅中(這趟長達四個月的旅程,讓我好生羨慕……從來沒想到,我竟然會羨慕一位特教老師),看著他們行旅中的點點滴滴,印象最深的是他和學生同擠在一張旅社單人床上的照片,這讓我吃了一驚——以前在大陸山區支教時我也住在學校裡,學生們也常來我的房間,但我不會和他們親暱到同睡一張床。當然,智鑛和學生同擠一張床也不是表示親暱(其實兩人都一臉衰衰的面無表情),而是旅程中不得不然的安排,令我吃驚的是他的工作和個人生活是完全融在一起的!他可以一天二十四小時都和孩子、家長或老師相處在一起而不覺得累,這真的是天賦異稟。*因為,最美的是過程!
認識智鑛之後,很難想像現在這個體貼、敏感、有禮、大方的特教老師,小時候竟是午休時永遠被罰站、會莫名其妙拿石頭丟同學的孩子。他自己活脫就是一個有力實證︰再怎麼不被看好的孩子,都有「翻轉」的可能,甚至可能比你我想像得還要好,還要精采。
為了想多實際觀察他和孩子的互動,我跟著參加了愛奇兒單車環島行的後半段。智鑛此行帶了一個學生同行,這個高二輟學的孩子不久前才和智鑛從大陸遼寧丹東一路滑行到海南島,這次單車環島又同行,「其實他是來照顧我的,因為他已經單車環島過了。」第一次單車環島的智鑛說。
孩子常把臉包得密不透風,加上騎車時戴的帽子、墨鏡,讓人看不到他的表情和眼睛。和這樣裝扮的他說話時感覺很怪,不知道要看哪裡?看著墨鏡會讓人很想逃避。他總是跟在曲老師身邊,幾乎不會主動和別人說話、互動,但卻會問老師許多許多問題,有說不完的話,還喜歡把老師抱起來。他有一套「無聊」邏輯,什麼都是無聊,做的所有事情、去的所有地方都是無聊。「給我一把刀,我想殺人。」「老師我想吃你,你看起來很好吃。」是他的口頭禪。
第一天剛見面時邀孩子一起去吃晚飯他婉拒了,智鑛不以為意。「你自己決定。」第二天他答應和我們一起吃晚飯了,那晚他心情很好,臉上一切裝備都脫下了,不時在笑,不時說話……而半年前智鑛剛認識孩子時是不會笑的。那晚他還和我們分享了他的願望︰「我希望以後能去幫助需要幫助的人,但不是給錢,因為給錢的話會被其他人污走。我要自己去看對方需要什麼,然後親手把東西送到。」——其實是個善良的孩子啊!他懂得多,知識豐富。常會不自覺地打斷別人的話,但有一兩次我也不小心打斷了他的話,我向他道歉,他卻挺不好意思的,而且會很大方地說「沒關係」。雖然有時候的反應出乎人意料,但我也感覺到他是一個敏感、有禮貌的孩子,還有紳士的一面——我猜想,這一定和半年多來智鑛的貼身輔導有關吧?
孩子有時會說出「白目」的話,智鑛會用他的方式去﹁點﹂孩子。而且不只是當下點,之後有相呼應的情境時還會持續點、接著點。這些「點」,都是在亦師亦友的相處、說話、互動中進行,那樣的敏感度和平等自然的相處模式令人印象深刻。
在花蓮豐濱海邊的一個休息點,我說給他倆拍照,他倆說好,走到定點要拍,這時孩子卻拿著平板在拍別的東西。我們在等他,智鑛叫了他兩次,他仍在忙自己的事,我問智鑛︰「他是不是不想拍?」「不是。他不懂得顧慮別人的感受。」智鑛對我使個眼色,「我們先不拍了。」過了會兒孩子來找我們了,「不是要拍照嗎?」智鑛說︰「不拍了。」「你生氣囉?」「沒有啊。」「你就是生氣了!」
沒有明說什麼,但我感覺到,孩子知道自己剛剛做得不對了。
騎行的第三天,智鑛在臉書上分享了這麼一段話︰「今天跟我叨叨了一整天的孩子,在距離終點十五公里左右,突然很淡定地跟我說︰『老師,有你真好!我從來沒跟任何人說過!』夠了,這樣就夠了!」
環島的那幾天,只能趁休息的空檔和他們聊聊天,大部分時間他們都在踩踏前行。我有點想不通,一個工作忙碌的知名特教老師,為什麼會義無反顧來參加環島騎行,而且是全程九天八夜?在一個休息點我問他這個問題,他說︰「我覺得,當輔導老師,生命經驗要豐富。要不然怎麼可能在一個小小的空間、短短的時間裡就能影響孩子?」
這話說得太好了。
對每一個人,他都是那麼真誠、體貼,和他相處就是如沐春風的感覺。為什麼對每一個人際接觸都這麼用心?這樣不累嗎?他思索了一會兒說︰「我覺得我是個很重視關係的人。」
從智鑛身上,我「看見」很多。我感到我和他的個性有很相像的部分,但他的障礙比我少,能夠更柔軟自如地表達自己的情感、愛與能量,這是我要學習的。
騎行的第六天,智鑛在臉書上分享了這幾句話︰「明明知道結果的事你還願意努力嗎?已經知道結局的電影你還會想看嗎?……會啊!因為最美的是過程!」
我以為是孩子和他之間的對話呢,第二天聊起這事,他說不是,是他自己的感想。怎麼說呢?他進一步解釋︰「嗯,譬如說,如果我明知道這個孩子是個特殊的孩子,我還會選擇生下他嗎?……我的答案是『會』。」
*原來「教育」無處不在
環島行結束後不久,我又跟著他到南京幾天,大學裡的講座、到校入班觀察孩子的狀況、與家長晤談,晚上和廣西的特教老師們視訊課程..他住在孩子家裡,和孩子、家長一起吃飯,一起生活,就像親友一般。
南京那個孩子語言表達能力很好,可以叨叨叨說個不停,他從不會感到煩,也不會回應孩子的每句話,很多時候他在做自己的事,但時不時就會在關鍵時候做出回應——他不會緊黏著孩子,但也絕不掉隊。他還是個出色的演員,有時親和,有時嚴肅,有時幽默,有時難過。
跟著入班觀察,他大多時候盯著手機或筆電(有許多聯絡工作),但孩子的一舉一動、班級和老師的動態竟然全在他眼底——這時真覺得他有點像大內高手,武功深藏不露;旁聽他和家長、老師談話,簡簡單單的幾件事,他可以翻來覆去、揉來捻去、迴旋纏繞一兩個小時,我看到自己的缺乏耐心,也歎服他的化骨綿掌。「其實我是很重視效率的人。」事後他回答我的提問,「但人與人的溝通,要效果好,就不能只顧效率。」
真的,我又上了一課。
回台北後,又跟著他和孩子們爬了一次山。八個孩子,最小的五歲,最大的二十八歲,他兩兩分組,大的帶小的。只是爬郊山步道的小旅行,孩子們之間也有許多戲碼上演︰遲到的,愛現的,心情不好的,彼此看不順眼的,怕水的..他的節奏流暢而明快,不管任何戲碼現前,於他似乎都是司空見慣,明快處理,然後繼續前行。他是這個團體的帶領者,不管孩子們是什麼個性、什麼狀態或什麼速度,總是跟著他的步伐。他非常尊重孩子,平等相處,從不命令或要求孩子什麼,但孩子們都很聽他的話。
坦白說,從一開始接觸智鑛起,我心裡始終有個﹁坎﹂,我覺得他帶的孩子都是家裡條件比較好的,只有有資源、有能力的父母,才能為孩子投注這麼多關懷和支持,這是我所認識的那些山區孩子所欠缺、不可能擁有的。就像從小沒被愛夠的孩子,看到別的孩子擁有滿滿的愛,心裡有一種酸楚,一種不以為然。
這陣子以來,我心裡的這個﹁結﹂解開了。我了解到,確實很多請智鑛協助的父母都是比較有資源的,但並不表示他只協助這樣的父母和孩子。有些他陪伴了很多年的孩子,後來家庭經濟情況變得不好了,他仍然不計報酬陪伴。他這第一本書的版稅也是捐出去的。像這樣一位好老師,我相信,如果我所認識的那些山區孩子遇到了,他也一定會對他們好,會給他們滿滿的支持與愛。更重要的是,不管山裡或城裡,擁有其他人眼中很多資源或否,其實每個人的成長之路都是滿布坎坷;當需要幫助的人能夠得到幫助,就是好的,就是對的。
就這樣,認識智鑛,除了認識一位獨特的特教老師,認識了一個好朋友,也讓自己內心的一些「結」得到鬆綁,一些生命中的欠缺、傷口得到療癒。我知道智鑛也走在這樣的路上。多麼奇妙,「教育」並不只發生於父母子女或師生之間,它原來無處不在!
這「有意義的巧合」,無形中似乎也呼應了我們都非常喜歡的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的一段話:
教育,是人與人之間,
也是自己與自己之間發生的事,
它永不停止,
就像一棵樹搖動另一棵樹,
一朵雲觸碰另一朵雲,
一個靈魂喚醒另一個靈魂。
認識智鑛之後,我常說他是有願力的人,像是乘願再來的菩薩,這一生就是要為特殊需求的孩子和父母們做一些事。對這樣奇怪的「稱讚」他似乎難以回應,但數年前他曾寫下過這樣一句話︰「透過服務,讓我重新思考生命的價值,並感受人與人之間最純潔的愛與關懷」——看似平淡無奇的一句話,卻在我認識他之後,深深感覺到是那樣貼切、真誠。
世間總有這樣的人,讓人感到內心溫暖,充滿希望。
用智鑛的話說,我會認識他,也是「生命中有意義的巧合」。
原本沒有交集的兩個人,應該是因為「教育」這條線連上的;而我並不是專業老師,只是為了實踐公益旅行+深度旅行的夢想,曾經赴大陸山區小學擔任志工老師(大陸稱為「支教」)三年多。那段給山裡孩子當老師的經歷和記憶,是生命中獨特而難忘的「老師」生涯。
因為這段經歷,大學同學佩芬找到我,為智鑛的第一本書擔任文字整理工作。因緣際會,接下了原本不會接下的工作,因為這位特教老師很「特別」,他用自己獨樹一幟的方式在從事教育這件事,讓我很好奇,尤其是他強調「在實際的情境中學習」,常常帶孩子到外面活動,甚至去旅行……讓我十分認同且佩服。
在此之前,我對「特殊教育」可說是一無所知,接下這份工作後才開始慢慢了解︰原來過動的孩子是這樣的!想起從小到大很討厭的那種男生︰總是很白目,總是喜歡作弄別人,總是開些很不好笑的玩笑,總是很不文靜很不文明很無禮……原來他們不是故意的!
這個遲來的「看見」和「發現」,讓我有醍醐灌頂之感。原來,我誤會了「他們」那麼多年!心裡有種深深的歉疚。因為不了解,我像其他人一樣,嫌棄、討厭他們,而如果是與生俱來的特質,誰有權利去嫌棄、討厭誰?那不過是自以為高人一等的傲慢。
我也十分認同智鑛所說的「光譜」概念。與其用疾病的分類把人標籤化,不如以光譜的漸層來看待、理解每一個人,就如沒有一個人是絕對的內向或外向、悲觀或樂觀,每一個人,或多或少都有注意力不集中、活在自己的世界裡等特質,只是比重不同(而這個「比重」,和情境還有很大的關係)。平心而論,我的弟弟就有些自閉症的特質,只是那個年代「特教」還不發達;而我自己也有點亞斯伯格(智鑛說,現在沒有亞斯伯格了,都叫自閉症),只是沒有被「判定」。
漸漸發現︰特殊教育,其實能幫助人更理解他人、理解世界,能夠讓心更柔軟、更開放、更有愛。我感覺到︰成長的機會來了。
見面之前,我透過臉書先了解智鑛。那時他正在大陸沿海岸線滑行之旅中(這趟長達四個月的旅程,讓我好生羨慕……從來沒想到,我竟然會羨慕一位特教老師),看著他們行旅中的點點滴滴,印象最深的是他和學生同擠在一張旅社單人床上的照片,這讓我吃了一驚——以前在大陸山區支教時我也住在學校裡,學生們也常來我的房間,但我不會和他們親暱到同睡一張床。當然,智鑛和學生同擠一張床也不是表示親暱(其實兩人都一臉衰衰的面無表情),而是旅程中不得不然的安排,令我吃驚的是他的工作和個人生活是完全融在一起的!他可以一天二十四小時都和孩子、家長或老師相處在一起而不覺得累,這真的是天賦異稟。*因為,最美的是過程!
認識智鑛之後,很難想像現在這個體貼、敏感、有禮、大方的特教老師,小時候竟是午休時永遠被罰站、會莫名其妙拿石頭丟同學的孩子。他自己活脫就是一個有力實證︰再怎麼不被看好的孩子,都有「翻轉」的可能,甚至可能比你我想像得還要好,還要精采。
為了想多實際觀察他和孩子的互動,我跟著參加了愛奇兒單車環島行的後半段。智鑛此行帶了一個學生同行,這個高二輟學的孩子不久前才和智鑛從大陸遼寧丹東一路滑行到海南島,這次單車環島又同行,「其實他是來照顧我的,因為他已經單車環島過了。」第一次單車環島的智鑛說。
孩子常把臉包得密不透風,加上騎車時戴的帽子、墨鏡,讓人看不到他的表情和眼睛。和這樣裝扮的他說話時感覺很怪,不知道要看哪裡?看著墨鏡會讓人很想逃避。他總是跟在曲老師身邊,幾乎不會主動和別人說話、互動,但卻會問老師許多許多問題,有說不完的話,還喜歡把老師抱起來。他有一套「無聊」邏輯,什麼都是無聊,做的所有事情、去的所有地方都是無聊。「給我一把刀,我想殺人。」「老師我想吃你,你看起來很好吃。」是他的口頭禪。
第一天剛見面時邀孩子一起去吃晚飯他婉拒了,智鑛不以為意。「你自己決定。」第二天他答應和我們一起吃晚飯了,那晚他心情很好,臉上一切裝備都脫下了,不時在笑,不時說話……而半年前智鑛剛認識孩子時是不會笑的。那晚他還和我們分享了他的願望︰「我希望以後能去幫助需要幫助的人,但不是給錢,因為給錢的話會被其他人污走。我要自己去看對方需要什麼,然後親手把東西送到。」——其實是個善良的孩子啊!他懂得多,知識豐富。常會不自覺地打斷別人的話,但有一兩次我也不小心打斷了他的話,我向他道歉,他卻挺不好意思的,而且會很大方地說「沒關係」。雖然有時候的反應出乎人意料,但我也感覺到他是一個敏感、有禮貌的孩子,還有紳士的一面——我猜想,這一定和半年多來智鑛的貼身輔導有關吧?
孩子有時會說出「白目」的話,智鑛會用他的方式去﹁點﹂孩子。而且不只是當下點,之後有相呼應的情境時還會持續點、接著點。這些「點」,都是在亦師亦友的相處、說話、互動中進行,那樣的敏感度和平等自然的相處模式令人印象深刻。
在花蓮豐濱海邊的一個休息點,我說給他倆拍照,他倆說好,走到定點要拍,這時孩子卻拿著平板在拍別的東西。我們在等他,智鑛叫了他兩次,他仍在忙自己的事,我問智鑛︰「他是不是不想拍?」「不是。他不懂得顧慮別人的感受。」智鑛對我使個眼色,「我們先不拍了。」過了會兒孩子來找我們了,「不是要拍照嗎?」智鑛說︰「不拍了。」「你生氣囉?」「沒有啊。」「你就是生氣了!」
沒有明說什麼,但我感覺到,孩子知道自己剛剛做得不對了。
騎行的第三天,智鑛在臉書上分享了這麼一段話︰「今天跟我叨叨了一整天的孩子,在距離終點十五公里左右,突然很淡定地跟我說︰『老師,有你真好!我從來沒跟任何人說過!』夠了,這樣就夠了!」
環島的那幾天,只能趁休息的空檔和他們聊聊天,大部分時間他們都在踩踏前行。我有點想不通,一個工作忙碌的知名特教老師,為什麼會義無反顧來參加環島騎行,而且是全程九天八夜?在一個休息點我問他這個問題,他說︰「我覺得,當輔導老師,生命經驗要豐富。要不然怎麼可能在一個小小的空間、短短的時間裡就能影響孩子?」
這話說得太好了。
對每一個人,他都是那麼真誠、體貼,和他相處就是如沐春風的感覺。為什麼對每一個人際接觸都這麼用心?這樣不累嗎?他思索了一會兒說︰「我覺得我是個很重視關係的人。」
從智鑛身上,我「看見」很多。我感到我和他的個性有很相像的部分,但他的障礙比我少,能夠更柔軟自如地表達自己的情感、愛與能量,這是我要學習的。
騎行的第六天,智鑛在臉書上分享了這幾句話︰「明明知道結果的事你還願意努力嗎?已經知道結局的電影你還會想看嗎?……會啊!因為最美的是過程!」
我以為是孩子和他之間的對話呢,第二天聊起這事,他說不是,是他自己的感想。怎麼說呢?他進一步解釋︰「嗯,譬如說,如果我明知道這個孩子是個特殊的孩子,我還會選擇生下他嗎?……我的答案是『會』。」
*原來「教育」無處不在
環島行結束後不久,我又跟著他到南京幾天,大學裡的講座、到校入班觀察孩子的狀況、與家長晤談,晚上和廣西的特教老師們視訊課程..他住在孩子家裡,和孩子、家長一起吃飯,一起生活,就像親友一般。
南京那個孩子語言表達能力很好,可以叨叨叨說個不停,他從不會感到煩,也不會回應孩子的每句話,很多時候他在做自己的事,但時不時就會在關鍵時候做出回應——他不會緊黏著孩子,但也絕不掉隊。他還是個出色的演員,有時親和,有時嚴肅,有時幽默,有時難過。
跟著入班觀察,他大多時候盯著手機或筆電(有許多聯絡工作),但孩子的一舉一動、班級和老師的動態竟然全在他眼底——這時真覺得他有點像大內高手,武功深藏不露;旁聽他和家長、老師談話,簡簡單單的幾件事,他可以翻來覆去、揉來捻去、迴旋纏繞一兩個小時,我看到自己的缺乏耐心,也歎服他的化骨綿掌。「其實我是很重視效率的人。」事後他回答我的提問,「但人與人的溝通,要效果好,就不能只顧效率。」
真的,我又上了一課。
回台北後,又跟著他和孩子們爬了一次山。八個孩子,最小的五歲,最大的二十八歲,他兩兩分組,大的帶小的。只是爬郊山步道的小旅行,孩子們之間也有許多戲碼上演︰遲到的,愛現的,心情不好的,彼此看不順眼的,怕水的..他的節奏流暢而明快,不管任何戲碼現前,於他似乎都是司空見慣,明快處理,然後繼續前行。他是這個團體的帶領者,不管孩子們是什麼個性、什麼狀態或什麼速度,總是跟著他的步伐。他非常尊重孩子,平等相處,從不命令或要求孩子什麼,但孩子們都很聽他的話。
坦白說,從一開始接觸智鑛起,我心裡始終有個﹁坎﹂,我覺得他帶的孩子都是家裡條件比較好的,只有有資源、有能力的父母,才能為孩子投注這麼多關懷和支持,這是我所認識的那些山區孩子所欠缺、不可能擁有的。就像從小沒被愛夠的孩子,看到別的孩子擁有滿滿的愛,心裡有一種酸楚,一種不以為然。
這陣子以來,我心裡的這個﹁結﹂解開了。我了解到,確實很多請智鑛協助的父母都是比較有資源的,但並不表示他只協助這樣的父母和孩子。有些他陪伴了很多年的孩子,後來家庭經濟情況變得不好了,他仍然不計報酬陪伴。他這第一本書的版稅也是捐出去的。像這樣一位好老師,我相信,如果我所認識的那些山區孩子遇到了,他也一定會對他們好,會給他們滿滿的支持與愛。更重要的是,不管山裡或城裡,擁有其他人眼中很多資源或否,其實每個人的成長之路都是滿布坎坷;當需要幫助的人能夠得到幫助,就是好的,就是對的。
就這樣,認識智鑛,除了認識一位獨特的特教老師,認識了一個好朋友,也讓自己內心的一些「結」得到鬆綁,一些生命中的欠缺、傷口得到療癒。我知道智鑛也走在這樣的路上。多麼奇妙,「教育」並不只發生於父母子女或師生之間,它原來無處不在!
這「有意義的巧合」,無形中似乎也呼應了我們都非常喜歡的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的一段話:
教育,是人與人之間,
也是自己與自己之間發生的事,
它永不停止,
就像一棵樹搖動另一棵樹,
一朵雲觸碰另一朵雲,
一個靈魂喚醒另一個靈魂。
認識智鑛之後,我常說他是有願力的人,像是乘願再來的菩薩,這一生就是要為特殊需求的孩子和父母們做一些事。對這樣奇怪的「稱讚」他似乎難以回應,但數年前他曾寫下過這樣一句話︰「透過服務,讓我重新思考生命的價值,並感受人與人之間最純潔的愛與關懷」——看似平淡無奇的一句話,卻在我認識他之後,深深感覺到是那樣貼切、真誠。
世間總有這樣的人,讓人感到內心溫暖,充滿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