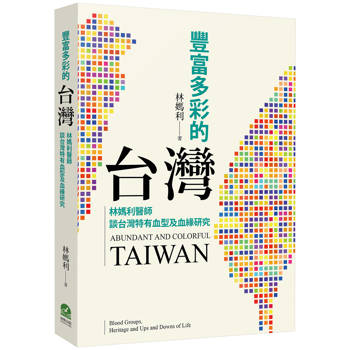寫在前面
1981年,我在美國德州大學做完四年美國病理專科醫師訓練,並考取美國病理專科醫師執照,同年10月1日,帶著台大醫學院病理研究所副教授及美國病理專科醫師的光環,到馬偕醫院的檢驗科(臨床病理)報到,我很快發現並不能在馬偕醫院同時也做熟悉的(之前在台大病理研究所做了16年)的組織病理(解剖病理),而在檢驗科只能做血庫。因為當時血庫(immunohematology, 免疫血液學)是一個新的學門,許多人並不是很了解,而我在美國四年的訓練主要在血庫,於是我勉強接受這個工作。和大部分的醫院一樣,當時血庫只有兩三坪大,有一台冰箱、一個離心機、一張桌子和一位醫檢師,害得我台大的同事看到這個情形就說:「妳在這裡做什麼血庫?」
投身血液政策與血型研究
我每天上班,只是看到醫檢師忙著抽血牛(有價供血者)的血,當時捐血量非常少,所以只能提供給醫院一小部分的病人使用。我試著教醫檢師最基本的交叉實驗,從教她如何搖試管,如何看結果開始。我同時也發現,台灣有關血型的資料,除了ABO、Rh 以外,好像只有一點點MN 血型的資料而已,一切需要從頭開始!
當時全台為盛行的高B 型肝炎帶原率所不安,我一有空就往衛生署跑,因為我受到高醫時代的老師許子秋衛生署長邀請,參與制定國家的血液政策 [ 國家的血液政策,見附件1 ]。台灣的捐血輸血在1980 年代初期都很混亂,於是我偕同台灣輸血學會會員孫建峰、李正華和美國的高源祥等醫師,衛生署的長官葉金川、蔡素玲及助理石美春等,做了全台捐血機構及醫院輸血單位(血庫)的評鑑及督導,再根據評鑑的結果,擬定制度及規範。所以從1984到1992年,在八年之中,把台灣的捐輸血制度建立起來。
在1992 年,台灣的捐血量足夠提供全台醫院所需要的用血,有價供血(血牛)從此消失。1992年台灣變成一個沒有血液買賣的國家,在短短八年,把買賣血液的國家變成捐血的國家,應該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
另一方面,在1983年,英國血庫專家、宣教師鮑博瑞先生(Richard E. Broadberry, FIMLS)應上帝的呼召,來到台北的馬偕醫院血庫工作,他變成我最好的工作夥伴,從此展開了1-20年燦爛非凡的台灣血型的拓荒研究工作。後來加入年輕的生力軍余榮熾博士,繼續做後續的血型基因的研究,使得許多亞洲,尤其是東南亞特有的血型及新的血型,不斷地被發現。同時大家驚訝的發現,不只是白種人和黃種人的血型分布不同,連東北亞的日本(中國很晚才做血型的研究,所以1980年代沒有資料可以做比較)和屬於東南亞的台灣,兩者的血型也有所不同。
台灣血型的發現,使歐美輸血醫學先進國家的專家、科學家,張大眼睛觀看台灣,特別是我們團隊一連串的發現,於是台灣的血型在1980、1990年代,在國際上喧騰一時。我們跟國際專家的討論信件,也就好幾年每年約有100封,包括和國際專家討論的往返信件,和國際友人做稀有血型血液的交換,常常使我們的信件滿天飛。同時我們的年輕人也在國際輸血學界佔有一席之地。
我們著名的發現之一,是分泌型亞孟買血型,這血型讓親子間ABO血型不配合。如1985年馬偕醫院的嬰兒室,發生一對O型的父母親生出一個B型的男嬰而引起家庭糾紛,我們很快地證明,嬰兒的父親是帶B 基因的亞孟買血型者,而他給男嬰的B基因,經過嬰兒母親所帶正常的H 基因傳給嬰兒而表現出來,而生出B型的小孩。原來ABO血型的表現,必須有兩個基因,一個是ABO 血型的基因,另外一個是為要表現ABO基因,須要有的另一個H 基因。亞孟買血型的人並沒有正常的H基因,所以沒有辦法表現他的A 或者是B 的基因,因此表現成O血型。在台灣,每8,000個人有一個是屬於亞孟買血型,所以全台應該至少有3,000個亞孟買血型的人。
另外,台灣的亞孟買血型和白種人的亞孟買血型不同,可輸一般ABO 血型的血,可能因亞洲的亞孟買血型全部是分泌型,所以血漿中出現ABO 血型物質,而阻止了ABO血型抗體的產生,因此可輸一般ABO 血型的血,我們也經人體試驗證實了這個結果。白種人的亞孟買血型或孟買血型,是一定要輸相同的孟買血型的血,我還記得小時候讀了一本小說,說一個孟買血型的車手要出去賽車,就必須帶同一血型的妹妹一起去,以防失事受傷沒血輸,現在想來,這個故事應該是白種人的故事。
此外,我們也發現台灣的路易士血型中,出現只在亞洲出現的血型Le(a+b+) 血型。因為歐美血型專家沒看過這血型,所以開始時以為我們做錯,經過不斷的交換測試血液檢體以及試藥,最後說服國際學者接受亞洲有這個Le(a+b+) 血型。而且我們比著名的瑞典頒發諾貝爾獎的Karolinska Institute,早一年找到Le(a+b+)血型的相對基因Sew 基因,震撼國際。
我們也發現稀有血型i 血型與先天性白內障的關連,進而發現I血型的基因,而促成I血型變成國際上第27 個血型系統(這是台灣的努力促成的),Blood期刊將這報告當成當期的傑出論文,說:「i to I and the eye」[109],翻成中文是「從小我到大我,再到靈魂之窗眼睛」。這血型的發現,最大的協助,來自日本大阪府紅十字會血液中心的大久保康人教授的幫助及提供稀有的抗體及細胞。
我們在2003年SARS流行期間發現,組織抗原HLA-B*4601(越族的主要血緣)使帶這血緣的病人容易轉成重症。我們從SARS在台灣流行時,開始研究收集血液檢體,因為我的工作人員的家人,也怕他們把病毒從醫院帶回家,許多人變成有家歸不得,所以不少人就因此辭職。我希望可以找出一個和SARS相關的檢查方法,來篩檢工作人員,讓工作人員較安全的照顧SARS的病人。所以我把收集到的血液做組織抗原的研究,因為抗原系統是和人體的感染和免疫反應有關的。我一共收集到166位和SARS 感染相關的血液檢體(有些是曾暴露在SARS 病毒),因為SARS 的感染力很強,所以我全副武裝在負壓的工作台上,完成血液檢體前半部白血球分離的危險工作。從5月中開始收集血液檢體,在短短的一個半月,完成SARS 相關人員HLA 的檢測,分析結果,寫成報告,馬上投稿,很快的在三個月後(9月中),出現在國際期刊上,結果各大媒體爭相報導,變成國際上重要的醫藥新聞。最讓人不解的是,我們的發現在《華爾街日報》(¬e Wall Street Journal)有半版的介紹,路透社、日本的《朝日新聞》也有報導,我的朋友從馬來西亞剪了一塊有關我們發現的報紙寄來給我,甚至我和先夫在加德滿都的候機室,還遇到一個德國的復健師對我們說:「你們台灣發現了SARS相關的病毒。」但是我們國內的新聞只有半天講一講,就全部消音,我不太知道背後是什麼因素,只是我知道,當時的衛生署長到立法院報告的時候,說我的SARS研究的個案數不夠,但是《華爾街日報》上說,他們的記者去訪問歐洲的一位教授,該名教授說有37 個病人已經足夠來分析了。2003 年的SARS流行,顯然和2019年爆發的全球COVID-19的流行有很大的差異,因為後者看不到前者的族群傾向。
另外讓國際友人絕倒的是,1983年(不是1986年)在馬偕醫院病人身上找到米田堡血型(Miltenberger blood group)的抗體,這個重要血型的發現,是1983-1986年的三年間,經馬偕醫院血庫、北倫敦血液中心、英國醫學研究委員會(MRC)、日本紅十字會東京血液中心及大阪府紅十字會血液中心、泰國Siriraj 醫院的Chandanayingyong 的共同努力定出的血型。這種血型,在歐美白種人的國家是沒有看過的稀有血型,在台灣人有4.5%是這個血型,更令人驚訝的是,台灣原住民的頻率是從零到95%。後來證明,這個血型在台灣是繼ABO血型之後,最重要的血型,因為米田堡血型抗體危險,可引起溶血性輸血反應及新生兒溶血症,而我們的病人有2%帶這個抗體,所幸全台血庫在1990年就開始做輸血前米田堡血型抗體的篩檢。很快的,東南亞國家也發現這是最重要的抗體,所以紛紛學習台灣的作業。
我也發現了在華人的第一個ABO亞血型的B3血型,這血型在白種人是稀有血型,各國專家紛紛向我要B3 的血球。至於其他重要的發現,詳見內文(〈一、談台灣的輸血與血型〉)。
最讓我覺得遺憾的是,我畢生主張「廢除常規的Rh血型的篩檢,來解決在台灣屬於稀有血型Rh陰性(RhD–)者輸血的問題」,並沒得到適當的結果。我看到過去RhD–的人死亡的主要原因,是緊急需要輸血的時候沒有血輸,因為許多醫護人員並不太懂血型,不知道台灣絕大部分RhD–的病人因沒帶抗體,可以安全的輸入陽性的血,詳見內文(〈一、談台灣的輸血與血型〉)。
許多人一定會覺得奇怪,為什麼在亞洲,會是台灣獨領風騷?因為在亞洲,除了北亞洲的日本有好的血型研究及健全的捐血輸血系統外,東南亞的國家,當時大部分處於開發中國家,輸血醫學須在更開發的社會才可能發生,輸血醫學也叫做免疫血液學,所以須要加上有免疫血液學的專家才能做成,因為血型必須先從血清學的發現做起,再做基因的研究,剛好馬偕有血清學及基因研究最強的陣容。我們血型基因的研究,開始於1993年,台大生化研究所博士班剛畢業的余榮熾博士參加我們的團隊,當時我們剛好用免疫血清學的方法發現了許多新的血型,在接下來的近九年中,余榮熾努力做新血型基因的研究,因此重要的論文紛紛刊登在國際刊物上面。他在2001年被台大生化研究所以副教授聘回,讓我們很高興,記得我在推薦函中寫說「我們為這件事覺得很光榮」。之後的近20年,余榮熾繼續和我們合作研究,後來才會有重要的Sew及I基因的相繼發現。
至於中國,因為之前經過紅衛兵之亂,所以1990年代當我被中國輸血協會邀請去中國講學(在國際輸血學會安排下),發現中國情況和1983 年之前的台灣差不多。東南亞除了泰國,當時其他的國家都還沒發展輸血醫學,所以東南亞的血型大部分沒有被研究過,因此給馬偕的團隊一大片未開發的大地,以致著名的紐約血液中心從事輸血醫學研究的學者Dr. Laurence Marsh,看到我就羨慕的說:「林醫師是坐在金礦上的人,有挖不完的寶!」
在大家的努力下,台灣在短短的十年當中,趕上歐美的輸血醫學。除了天時、地利、人和,還加上馬偕團隊的努力,這可以從每一年馬偕醫院血庫約有100封的往返國際信件看到。我們的發現及研究的結果,很快的也變成東南亞國家輸血醫學重要的參考資料。
1981年,我在美國德州大學做完四年美國病理專科醫師訓練,並考取美國病理專科醫師執照,同年10月1日,帶著台大醫學院病理研究所副教授及美國病理專科醫師的光環,到馬偕醫院的檢驗科(臨床病理)報到,我很快發現並不能在馬偕醫院同時也做熟悉的(之前在台大病理研究所做了16年)的組織病理(解剖病理),而在檢驗科只能做血庫。因為當時血庫(immunohematology, 免疫血液學)是一個新的學門,許多人並不是很了解,而我在美國四年的訓練主要在血庫,於是我勉強接受這個工作。和大部分的醫院一樣,當時血庫只有兩三坪大,有一台冰箱、一個離心機、一張桌子和一位醫檢師,害得我台大的同事看到這個情形就說:「妳在這裡做什麼血庫?」
投身血液政策與血型研究
我每天上班,只是看到醫檢師忙著抽血牛(有價供血者)的血,當時捐血量非常少,所以只能提供給醫院一小部分的病人使用。我試著教醫檢師最基本的交叉實驗,從教她如何搖試管,如何看結果開始。我同時也發現,台灣有關血型的資料,除了ABO、Rh 以外,好像只有一點點MN 血型的資料而已,一切需要從頭開始!
當時全台為盛行的高B 型肝炎帶原率所不安,我一有空就往衛生署跑,因為我受到高醫時代的老師許子秋衛生署長邀請,參與制定國家的血液政策 [ 國家的血液政策,見附件1 ]。台灣的捐血輸血在1980 年代初期都很混亂,於是我偕同台灣輸血學會會員孫建峰、李正華和美國的高源祥等醫師,衛生署的長官葉金川、蔡素玲及助理石美春等,做了全台捐血機構及醫院輸血單位(血庫)的評鑑及督導,再根據評鑑的結果,擬定制度及規範。所以從1984到1992年,在八年之中,把台灣的捐輸血制度建立起來。
在1992 年,台灣的捐血量足夠提供全台醫院所需要的用血,有價供血(血牛)從此消失。1992年台灣變成一個沒有血液買賣的國家,在短短八年,把買賣血液的國家變成捐血的國家,應該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
另一方面,在1983年,英國血庫專家、宣教師鮑博瑞先生(Richard E. Broadberry, FIMLS)應上帝的呼召,來到台北的馬偕醫院血庫工作,他變成我最好的工作夥伴,從此展開了1-20年燦爛非凡的台灣血型的拓荒研究工作。後來加入年輕的生力軍余榮熾博士,繼續做後續的血型基因的研究,使得許多亞洲,尤其是東南亞特有的血型及新的血型,不斷地被發現。同時大家驚訝的發現,不只是白種人和黃種人的血型分布不同,連東北亞的日本(中國很晚才做血型的研究,所以1980年代沒有資料可以做比較)和屬於東南亞的台灣,兩者的血型也有所不同。
台灣血型的發現,使歐美輸血醫學先進國家的專家、科學家,張大眼睛觀看台灣,特別是我們團隊一連串的發現,於是台灣的血型在1980、1990年代,在國際上喧騰一時。我們跟國際專家的討論信件,也就好幾年每年約有100封,包括和國際專家討論的往返信件,和國際友人做稀有血型血液的交換,常常使我們的信件滿天飛。同時我們的年輕人也在國際輸血學界佔有一席之地。
我們著名的發現之一,是分泌型亞孟買血型,這血型讓親子間ABO血型不配合。如1985年馬偕醫院的嬰兒室,發生一對O型的父母親生出一個B型的男嬰而引起家庭糾紛,我們很快地證明,嬰兒的父親是帶B 基因的亞孟買血型者,而他給男嬰的B基因,經過嬰兒母親所帶正常的H 基因傳給嬰兒而表現出來,而生出B型的小孩。原來ABO血型的表現,必須有兩個基因,一個是ABO 血型的基因,另外一個是為要表現ABO基因,須要有的另一個H 基因。亞孟買血型的人並沒有正常的H基因,所以沒有辦法表現他的A 或者是B 的基因,因此表現成O血型。在台灣,每8,000個人有一個是屬於亞孟買血型,所以全台應該至少有3,000個亞孟買血型的人。
另外,台灣的亞孟買血型和白種人的亞孟買血型不同,可輸一般ABO 血型的血,可能因亞洲的亞孟買血型全部是分泌型,所以血漿中出現ABO 血型物質,而阻止了ABO血型抗體的產生,因此可輸一般ABO 血型的血,我們也經人體試驗證實了這個結果。白種人的亞孟買血型或孟買血型,是一定要輸相同的孟買血型的血,我還記得小時候讀了一本小說,說一個孟買血型的車手要出去賽車,就必須帶同一血型的妹妹一起去,以防失事受傷沒血輸,現在想來,這個故事應該是白種人的故事。
此外,我們也發現台灣的路易士血型中,出現只在亞洲出現的血型Le(a+b+) 血型。因為歐美血型專家沒看過這血型,所以開始時以為我們做錯,經過不斷的交換測試血液檢體以及試藥,最後說服國際學者接受亞洲有這個Le(a+b+) 血型。而且我們比著名的瑞典頒發諾貝爾獎的Karolinska Institute,早一年找到Le(a+b+)血型的相對基因Sew 基因,震撼國際。
我們也發現稀有血型i 血型與先天性白內障的關連,進而發現I血型的基因,而促成I血型變成國際上第27 個血型系統(這是台灣的努力促成的),Blood期刊將這報告當成當期的傑出論文,說:「i to I and the eye」[109],翻成中文是「從小我到大我,再到靈魂之窗眼睛」。這血型的發現,最大的協助,來自日本大阪府紅十字會血液中心的大久保康人教授的幫助及提供稀有的抗體及細胞。
我們在2003年SARS流行期間發現,組織抗原HLA-B*4601(越族的主要血緣)使帶這血緣的病人容易轉成重症。我們從SARS在台灣流行時,開始研究收集血液檢體,因為我的工作人員的家人,也怕他們把病毒從醫院帶回家,許多人變成有家歸不得,所以不少人就因此辭職。我希望可以找出一個和SARS相關的檢查方法,來篩檢工作人員,讓工作人員較安全的照顧SARS的病人。所以我把收集到的血液做組織抗原的研究,因為抗原系統是和人體的感染和免疫反應有關的。我一共收集到166位和SARS 感染相關的血液檢體(有些是曾暴露在SARS 病毒),因為SARS 的感染力很強,所以我全副武裝在負壓的工作台上,完成血液檢體前半部白血球分離的危險工作。從5月中開始收集血液檢體,在短短的一個半月,完成SARS 相關人員HLA 的檢測,分析結果,寫成報告,馬上投稿,很快的在三個月後(9月中),出現在國際期刊上,結果各大媒體爭相報導,變成國際上重要的醫藥新聞。最讓人不解的是,我們的發現在《華爾街日報》(¬e Wall Street Journal)有半版的介紹,路透社、日本的《朝日新聞》也有報導,我的朋友從馬來西亞剪了一塊有關我們發現的報紙寄來給我,甚至我和先夫在加德滿都的候機室,還遇到一個德國的復健師對我們說:「你們台灣發現了SARS相關的病毒。」但是我們國內的新聞只有半天講一講,就全部消音,我不太知道背後是什麼因素,只是我知道,當時的衛生署長到立法院報告的時候,說我的SARS研究的個案數不夠,但是《華爾街日報》上說,他們的記者去訪問歐洲的一位教授,該名教授說有37 個病人已經足夠來分析了。2003 年的SARS流行,顯然和2019年爆發的全球COVID-19的流行有很大的差異,因為後者看不到前者的族群傾向。
另外讓國際友人絕倒的是,1983年(不是1986年)在馬偕醫院病人身上找到米田堡血型(Miltenberger blood group)的抗體,這個重要血型的發現,是1983-1986年的三年間,經馬偕醫院血庫、北倫敦血液中心、英國醫學研究委員會(MRC)、日本紅十字會東京血液中心及大阪府紅十字會血液中心、泰國Siriraj 醫院的Chandanayingyong 的共同努力定出的血型。這種血型,在歐美白種人的國家是沒有看過的稀有血型,在台灣人有4.5%是這個血型,更令人驚訝的是,台灣原住民的頻率是從零到95%。後來證明,這個血型在台灣是繼ABO血型之後,最重要的血型,因為米田堡血型抗體危險,可引起溶血性輸血反應及新生兒溶血症,而我們的病人有2%帶這個抗體,所幸全台血庫在1990年就開始做輸血前米田堡血型抗體的篩檢。很快的,東南亞國家也發現這是最重要的抗體,所以紛紛學習台灣的作業。
我也發現了在華人的第一個ABO亞血型的B3血型,這血型在白種人是稀有血型,各國專家紛紛向我要B3 的血球。至於其他重要的發現,詳見內文(〈一、談台灣的輸血與血型〉)。
最讓我覺得遺憾的是,我畢生主張「廢除常規的Rh血型的篩檢,來解決在台灣屬於稀有血型Rh陰性(RhD–)者輸血的問題」,並沒得到適當的結果。我看到過去RhD–的人死亡的主要原因,是緊急需要輸血的時候沒有血輸,因為許多醫護人員並不太懂血型,不知道台灣絕大部分RhD–的病人因沒帶抗體,可以安全的輸入陽性的血,詳見內文(〈一、談台灣的輸血與血型〉)。
許多人一定會覺得奇怪,為什麼在亞洲,會是台灣獨領風騷?因為在亞洲,除了北亞洲的日本有好的血型研究及健全的捐血輸血系統外,東南亞的國家,當時大部分處於開發中國家,輸血醫學須在更開發的社會才可能發生,輸血醫學也叫做免疫血液學,所以須要加上有免疫血液學的專家才能做成,因為血型必須先從血清學的發現做起,再做基因的研究,剛好馬偕有血清學及基因研究最強的陣容。我們血型基因的研究,開始於1993年,台大生化研究所博士班剛畢業的余榮熾博士參加我們的團隊,當時我們剛好用免疫血清學的方法發現了許多新的血型,在接下來的近九年中,余榮熾努力做新血型基因的研究,因此重要的論文紛紛刊登在國際刊物上面。他在2001年被台大生化研究所以副教授聘回,讓我們很高興,記得我在推薦函中寫說「我們為這件事覺得很光榮」。之後的近20年,余榮熾繼續和我們合作研究,後來才會有重要的Sew及I基因的相繼發現。
至於中國,因為之前經過紅衛兵之亂,所以1990年代當我被中國輸血協會邀請去中國講學(在國際輸血學會安排下),發現中國情況和1983 年之前的台灣差不多。東南亞除了泰國,當時其他的國家都還沒發展輸血醫學,所以東南亞的血型大部分沒有被研究過,因此給馬偕的團隊一大片未開發的大地,以致著名的紐約血液中心從事輸血醫學研究的學者Dr. Laurence Marsh,看到我就羨慕的說:「林醫師是坐在金礦上的人,有挖不完的寶!」
在大家的努力下,台灣在短短的十年當中,趕上歐美的輸血醫學。除了天時、地利、人和,還加上馬偕團隊的努力,這可以從每一年馬偕醫院血庫約有100封的往返國際信件看到。我們的發現及研究的結果,很快的也變成東南亞國家輸血醫學重要的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