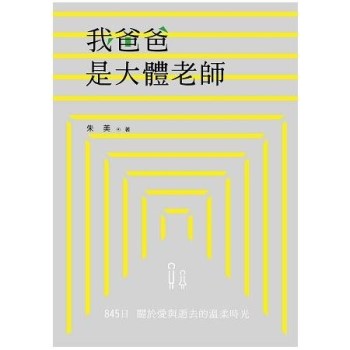命運的安排
一切都是無法解釋的巧合。
百分之百的指名,毫不猶豫的派任,
製作公共電視《誰來晚餐》大體老師家人的影片,
及寫作這本《我爸爸是大體老師》的工作,
同時巧妙地轟然而下砸在我的頭頂上。
二○一七年五月五日,第一次進實驗室拍攝。拍攝順利,學生很認真學,表達很流暢,對陳俊明老師很感恩,收錄的畫面和訪問都很美好,符合節目所需。
我看到什麼?講難聽點,市場的豬肉攤。雖然老師們的頭和身體還有四肢都還是連在一起的,可是那個顏色真的很難讓人不聯想到餐桌上的肉,還是煮熟的。醫學系老師告訴你,第一次上解剖課,會長達三天不想吃肉,我想,何止三天,都拍完兩個月了,我今天吃雞肉還是想到大體解剖。
朋友紛紛稱讚:「哇!你好勇敢!好了不起!」不,我沒有向上天祈求要做這件事,我也不覺得這有什麼勇敢。我和所有家屬一樣:默默等待學期結束,火化,送爸爸的骨灰上五指山,讓他安息。如此而已。就是這麼平凡而普通的,一位小小的、微不足道的家屬的願望。
然而命運之神卻不這麼想,更令人驚懼的事在後頭。
接下公共電視案不久,因事和以前雜誌社同事碰面。她看到我的臉書留言,想邀請我寫關於我爸是大體老師的一本書。第一個步驟,就是交試寫稿去公司會議提案。
一般非學醫的人聽到解剖大體雖然會好奇,然而要出一本書卻是超過二十萬元的投資。更何況,那還是她的新老闆。
我很放鬆、很隨緣地寫了四千字試稿。
結果提案過了。
「因緣俱足」,佛家說的話。好事多磨,都是因為因緣不俱足。這件大體老師的專案影片、書籍,就好像躺在那裡等著我到來。我彷彿在自己的生死簿上看到了這幾行字──
「朱美,二○一七年夏,大體老師紀錄片、專書,獨立企畫,限期完成。完畢。」
那是無法辯駁、無法反應甚至反抗的使命,就落在我人生地圖上。像一片悄然而來的落葉。
你知道,如果偶然間看到一個恐怖畫面,只要離開現場便可以慢慢淡忘。不同的是,你看了這個恐怖畫面之後,還要鉅細靡遺地描述它,一再地回憶它,還要和很多的人討論,這個恐怖畫面所代表的意義與知識。
這就是我寫書時所做的事。
而恐怖畫面,就是我爸爸赤裸的、經防腐液浸泡後變色的,皮膚硬化得像塑膠般,被切割了好幾十刀的身體。
我開始懷疑是爸爸搞的鬼。因為他過世的時候我沒有盡情地哭,常常逃避不去想念他,現在課快上完了,他用神祕的力量把我弄到課堂上,強迫我看他最後一眼……我想:爸,你也太殘忍了吧!知道你女兒膽子大,也不能這樣啊!誰會想看到自己的親人被切得面目全非啊!
他身體上的每條縫線,如今我閉上眼都還記得。每一個內臟的狀況,我也都看到了。
這些事情都是被迫發生的。孫悟空被壓在五指山下動彈不得的感覺,剎那間我全明白了。
年輕時常聽老人家說:一切冥冥中自有安排。我當下完全了解。其他煩人的事怎麼不替我安排好?這件事怎麼安排得這麼好?
我再發十頁的牢騷,也無法表達我被命運「鎖定」的心情於萬一。它真的是一件很痛苦的差事,必須忍耐內心巨大的驚嚇與痛苦,才能完成的一件困難事。如果要我指派這件事給任何一個人,我會因為同情他的痛苦,而無法執行。
然而我對這項任務,卻從來沒有拒絕的念頭。
原因是什麼,我也不明白,大概相信這就是「命運的安排」吧!
於是,我開始進行本書的寫作。在寫作過程中,我重回到爸爸還年輕的時代,重回我的童年時代,兩年多了,當初糾葛錯綜複雜的情緒,到了成書終於可以一一釐清。最初也是最後的一站:家屬心之路
身為一個承辦捐贈事務的人員,
家屬們似乎願意跟我吐露很多心事。
理論上,我們應該保持超然,
不去涉入也不對他們的故事動感情,
可有時難免情不自禁,對他們的傷痛感同身受。
不知該怎麼形容,這種因為親人生命走到盡頭,
跟我們之間開啟的緣分。
──國防醫學院生物及解剖學科暨研究所秘書 羅世圓
爸爸在一○四年三月七日早晨於臥室跌倒。救護車送至榮總之後,我們抵達急診室,親眼見到出血已漫過三分之一腦的斷層掃瞄影像,醫生宣布病危。依他生前的叮嚀,全家人當天決定不進行侵入性急救,不進行開腦手術。結果爸爸住院九天後離世。
心電圖完全靜止前約六小時,哥哥致電北區遺體聯絡捐贈中心,國防醫學院接到通知之後,成功在四十八小時內接走了遺體,進行防腐處理。終於圓滿爸爸多年來捐贈大體的宏大遺願。
冬天,爸爸坐在桌前,吃力地填寫一份表格,忍不住埋怨:「你看你看,我現在連寫字都會抖了,一個字都寫不好……」我注視著那份表格,原來是「大體捐贈同意書」。當時還安撫他:「沒關係啊,你多久才寫一次字?已經寫完啦!」「不行啦……現在連寫字都不行啦……」爸嘆著氣。
爸爸一向以他工整漂亮的字而自豪。即使是草寫,也都規規矩矩同樣大小,細密整齊落在書頁的邊緣。他的筆記真是模範,任誰看到都會汗顏。
爸爸跌倒宣布病危後,媽媽趕快把捐贈志願書用限時掛號寄出。國防醫學院的回覆很快,兩天後我們就接到了回函。至於遺囑,爸爸很早就手寫好,塗改過,又改寫,在一次家庭聚餐的傍晚,把四個孩子叫到跟前一一簽了名。
爸爸過世後,媽媽開始翻找辦理繼承及除戶的種種證件資料,竟然一打開抽屜就找到。沒想到他在跌倒前,早就一一備妥了。
在榮總懷遠堂冰櫃放置了一個晚上,三月十七日一早九點半,國防醫學院的大體專車抵達。我和媽媽、姊姊,陪伴著爸爸上車。媽雖孱弱但仍堅持要坐在屍袋旁。天氣很暖和,我們三人都只穿春季的服裝,行進中,媽媽不時隔著冒著寒氣的屍袋,輕輕摸著爸的臉。
也是國防醫學院校友的嫂嫂,早在大體車停妥前就在解剖學科入口等待。羅世圓小姐迎接我們進去,到「大體處理室」前止步。
「從這裡進去以後,你們就永遠見不到朱先生了,在這裡看他最後一面吧!」羅小姐幫我們拉開了屍袋的拉鏈,露出透著冰霜的爸爸的臉。
姊姊拍下爸的遺容。我突然發現,他沒有戴假牙,啊,我們忘了幫爸爸在臨終前戴上假牙!難怪下顎是凹陷的!這樣不好看!
「處理大體的時候,假牙也是要拿掉的。」羅小姐說。那是媽媽和姊姊見爸爸的最後一面,再怎麼也沒想到,我,兩年後竟還會再見經化學處理,已經是「永垂不朽」的爸爸。
在解剖學科辦公室,羅小姐體貼送上了仍溫的午餐便當和茶水,招待我們休息片刻。她說了些什麼安慰感謝的話,我全沒聽進去。當時的生物及解剖學科主任馬國興,從外匆匆趕進來致意。一坐下,便情不自禁地握拳慨嘆:「朱信老師在我們這裡也服務很久!大家都這麼熟!怎麼會想到是他的爸爸……」
看到外人的悲傷,我們一臉木然。相遇在慰靈公祭
死亡,在尚未割捨之際是沈重的,是悲痛的。
然而,若死者告訴我們,不要哭泣,
他並未長眠於泥土中,
而是化作微風日日吹拂……
小哥,穿著整齊筆挺的軍服,頭髮梳得油亮整齊,以沈穩的語氣開始說話。小哥曾說他是全家最愛哭的人,此刻,他為了更重要的事,把悲傷和眼淚都隱藏在心裡。
爸爸,您好嗎?你離開我們一年了。今天,媽媽、大姊、小妹、大哥、媳婦、姊夫,大家到齊了。我們已經完成了你捐贈的志願。我很驕傲,所以我著軍服來參加這個儀式。
您十五歲離家從軍,一生都是大時代的見證。您雖然只有小學畢業,卻在軍中自學自修,考取公費出國。我也在您的鼓勵之下,放棄台大牙醫,決定進入國防醫學院。一九九○年、醫科八十三期畢業後,成為一個中尉的醫官。
身為職業軍人,您從來不是一個刻板印象中的好父親、好先生。因為您要值班留守、戰備、演習……我們小時候可能一個月或兩個月才看到您一次。
您沒辦法陪媽媽照顧小孩,沒辦法陪媽媽去買菜、處理家務,媽媽一個人把我們四個小孩拉拔長大。但我從小看著您,無怨無悔奉獻一切給國家。所以我也毫無畏懼地走向職業軍人的生涯。
我更驕傲的是,我們都同為國防醫學院的老師,我在航空醫學、航空生理、臨床神經的領域教學生,是言教。暑假之後,您馬上就要開始教育我的學弟學妹進入醫學領域最重要一門課:人體解剖學。您才是真正的身教。
您的選擇,身為醫學系學生的我最清楚:那是千刀萬剮,但是您很坦然。
小時候,您告訴我們:「十幾歲起就參加諸多戰役,身上哪裡有子彈碎片,哪裡有傷痕……」戰爭的時候沒有糧食,你們會吃中彈死亡的馬肉。在臨終前幾年您說要捐贈大體,而且要捐給國防醫學院。我知道,一部分原因,因為我是國防醫學院畢業的,另一方面,您一生奉獻國家,軍校在你腦海中,代表國家。
今年暑假以後,爸爸,您會成為醫科一一四期學弟學妹們的老師。他們在解剖過程會了解到您做過食道氣室的手術,白內障開過刀,還有肺氣腫,以及左腳臏骨因為車禍碎裂被移除,腹股溝疝氣動過兩次手術,裡面用網膜來修補。七年前您曾發生心肌梗塞,所以有一部分心臟肌肉已經壞死,他們還會發現臀部有作戰留下的砲彈碎片。
我相信,他們從您身上,除了學到生理解剖知識之外,更希望我的學弟學妹們要記得,今天其他所有大體老師,所有躺在不銹鋼解剖枱上的老師。也會記得我爸爸是奉獻一輩子的軍人,他的太太身為軍眷,要一個人帶領所有小孩長大,他有四位子女,是個淡泊名利的人。
爸爸,我很高興我和您都是軍人,我是救人的軍醫,您是保國衛民的將軍。
我們也同樣是國防醫學院的老師。我教學生活著時候的疾病,您教學生最重要的人生的課程:死亡。
您已經離開一年了,我知道您會眷顧著我們。小時候您最常訓勉我的一句話「取法乎上,盡得乎中。」您說,學習的目標訂得很高,還不見得能達到,更何況是沒有最高的目標?這句話,我希望所有醫科一一四期,還有其他參與解剖的同學都要謹記,所有奉獻他的身體的這些大體老師。
爸爸,謝謝您。我以一個身為兒子的身分,以一個醫學系學生、國防醫學院的校友的身份,還有一個身為國防醫學院老師的身分。
謝謝!
雖然本屆大體老師有七位,然而致詞的卻只有兩位。聽著小哥的致詞,情感綿長動人,一些觀眾不禁低頭啜泣。
小哥二度哽咽,卻依然完成這個艱難的任務。快轉人生:大體老師家訪
升上大三的國防醫學院醫學系學生即將上大體解剖課,
親訪大體老師的家庭,是老師規定的作業,
了解大體老師的生平與家庭成員背景……
也是讓這些孩子們對「老師」貢獻大體的尊重。
因為幫公共電視企畫拍攝《誰來晚餐》節目,認識了與爸同期的大體老師陳俊明的家人,開啟了拍攝他們家庭紀錄片的緣分。
這位朋友口中愛冒險、活力充沛、喜歡教人開車的陳老師,生前與爸爸素不相識,卻在死後成了鄰枱同事。在二○一七這個暴雨淹台的失常夏季,由我幫他們兩人,分別製作了影像和書籍的不朽回憶。
一個是住台中清水道地本省人,一個是終生住台北的外省老芋仔;一個是不苟言笑,另一個口若懸河、花招奇多;爸沒有跳舞細胞,陳俊明老師卻是天生舞棍;爸不喜旅行,陳老師卻在高中時環就環島遊台灣;爸高大健壯,陳老師纖瘦修長;爸是路痴,連路邊停車都很有障礙;陳老師卻是能馴服大遊覽車的「交通工具狂」,擁有「腦內導航」的超能力;我爸一放假就宅在家,陳老師卻是休假就載全家大小出去玩……爸爸出生入死,不管是手術或任何治療一聲都不會吭,而陳老師卻毫不隱藏他的「幼秀」,連打針都會唉唷唉唷地大聲喊疼……
唯一的共通點,是他們都很喜歡學英文。一個喜歡聽英文老歌,一個生前是英文老師。還有他們都非常愛乾淨愛漂亮。爸生前最難忍受的是小腹突出,肌肉變小,頭髮被風吹亂了沒人告訴他,一有汗臭馬上去沖澡……陳老師則是出門一定要穿襯衫,或乾淨的T恤配牛仔褲,一定繫皮帶,連鞋子全身搭配好才出門……
年齡相差三十歲,去世日子差四天,同期成為大體老師。鄰枱的同事,一起被切割。好欸。
就在我們接待家訪的同一個月,陳俊明老師的第二組學生李佳怡等同學們,一行人也浩浩盪盪來到陳老師家,和陳老師的太太,我尊稱她「溫姐」的溫玉蕊,還有陳老師生前的死黨好友進行訪問。
客廳的吊燈泛著淡黃色。十位同學來到陳老師家的客廳,圍著咖啡桌,把客廳擠滿了。同學問的問題大概也是圍繞著陳老師的個性,為什麼要捐大體,以及他和師母及好友之間的共同回憶等等。
※ ※ ※
聊完歡樂的回憶,免不了談到捐贈,略為傷感的主題。三位老朋友,哽咽過了又開始開玩笑:「你們在解剖的時候看看他的腦神經有沒有錯綜複雜?」老師的朋友黃先生說著,「他的想法很奇怪嘛!是不是腦筋跟人家有什麼不一樣?幫我們檢查看看!」學生笑了。
溫姐知不知道解剖之後,他的先生會變成什麼樣子?學生沒問,可能還沒經歷到,不清楚,也不忍問。但她對這件事是豁達的,看開的,因為她也追隨先生簽妥大體捐贈志願書了。
「你們在幫他做『那個』的時候,可以放音樂嗎?」溫姐輕輕地請求著。帶著一種大家閨秀的禮貌。
「應該可以。」學生答。「我們跟老師說說看。」
「他喜歡聽英文老歌,他喜歡聽的,對……」
「阿姨歌單可以給我們。」學生們笑著說,「我們自己去找歌。」
「他有英文名字叫馬克,Mark,或麥克。」
後來教解剖學的馬國興老師回憶,當初聽到放音樂這個要求很奇怪,但沒有理由不答應。於是第二組就成了馬老師教授解剖學二十多年來,第一批為大體老師播放音樂的學生。
一切都是無法解釋的巧合。
百分之百的指名,毫不猶豫的派任,
製作公共電視《誰來晚餐》大體老師家人的影片,
及寫作這本《我爸爸是大體老師》的工作,
同時巧妙地轟然而下砸在我的頭頂上。
二○一七年五月五日,第一次進實驗室拍攝。拍攝順利,學生很認真學,表達很流暢,對陳俊明老師很感恩,收錄的畫面和訪問都很美好,符合節目所需。
我看到什麼?講難聽點,市場的豬肉攤。雖然老師們的頭和身體還有四肢都還是連在一起的,可是那個顏色真的很難讓人不聯想到餐桌上的肉,還是煮熟的。醫學系老師告訴你,第一次上解剖課,會長達三天不想吃肉,我想,何止三天,都拍完兩個月了,我今天吃雞肉還是想到大體解剖。
朋友紛紛稱讚:「哇!你好勇敢!好了不起!」不,我沒有向上天祈求要做這件事,我也不覺得這有什麼勇敢。我和所有家屬一樣:默默等待學期結束,火化,送爸爸的骨灰上五指山,讓他安息。如此而已。就是這麼平凡而普通的,一位小小的、微不足道的家屬的願望。
然而命運之神卻不這麼想,更令人驚懼的事在後頭。
接下公共電視案不久,因事和以前雜誌社同事碰面。她看到我的臉書留言,想邀請我寫關於我爸是大體老師的一本書。第一個步驟,就是交試寫稿去公司會議提案。
一般非學醫的人聽到解剖大體雖然會好奇,然而要出一本書卻是超過二十萬元的投資。更何況,那還是她的新老闆。
我很放鬆、很隨緣地寫了四千字試稿。
結果提案過了。
「因緣俱足」,佛家說的話。好事多磨,都是因為因緣不俱足。這件大體老師的專案影片、書籍,就好像躺在那裡等著我到來。我彷彿在自己的生死簿上看到了這幾行字──
「朱美,二○一七年夏,大體老師紀錄片、專書,獨立企畫,限期完成。完畢。」
那是無法辯駁、無法反應甚至反抗的使命,就落在我人生地圖上。像一片悄然而來的落葉。
你知道,如果偶然間看到一個恐怖畫面,只要離開現場便可以慢慢淡忘。不同的是,你看了這個恐怖畫面之後,還要鉅細靡遺地描述它,一再地回憶它,還要和很多的人討論,這個恐怖畫面所代表的意義與知識。
這就是我寫書時所做的事。
而恐怖畫面,就是我爸爸赤裸的、經防腐液浸泡後變色的,皮膚硬化得像塑膠般,被切割了好幾十刀的身體。
我開始懷疑是爸爸搞的鬼。因為他過世的時候我沒有盡情地哭,常常逃避不去想念他,現在課快上完了,他用神祕的力量把我弄到課堂上,強迫我看他最後一眼……我想:爸,你也太殘忍了吧!知道你女兒膽子大,也不能這樣啊!誰會想看到自己的親人被切得面目全非啊!
他身體上的每條縫線,如今我閉上眼都還記得。每一個內臟的狀況,我也都看到了。
這些事情都是被迫發生的。孫悟空被壓在五指山下動彈不得的感覺,剎那間我全明白了。
年輕時常聽老人家說:一切冥冥中自有安排。我當下完全了解。其他煩人的事怎麼不替我安排好?這件事怎麼安排得這麼好?
我再發十頁的牢騷,也無法表達我被命運「鎖定」的心情於萬一。它真的是一件很痛苦的差事,必須忍耐內心巨大的驚嚇與痛苦,才能完成的一件困難事。如果要我指派這件事給任何一個人,我會因為同情他的痛苦,而無法執行。
然而我對這項任務,卻從來沒有拒絕的念頭。
原因是什麼,我也不明白,大概相信這就是「命運的安排」吧!
於是,我開始進行本書的寫作。在寫作過程中,我重回到爸爸還年輕的時代,重回我的童年時代,兩年多了,當初糾葛錯綜複雜的情緒,到了成書終於可以一一釐清。最初也是最後的一站:家屬心之路
身為一個承辦捐贈事務的人員,
家屬們似乎願意跟我吐露很多心事。
理論上,我們應該保持超然,
不去涉入也不對他們的故事動感情,
可有時難免情不自禁,對他們的傷痛感同身受。
不知該怎麼形容,這種因為親人生命走到盡頭,
跟我們之間開啟的緣分。
──國防醫學院生物及解剖學科暨研究所秘書 羅世圓
爸爸在一○四年三月七日早晨於臥室跌倒。救護車送至榮總之後,我們抵達急診室,親眼見到出血已漫過三分之一腦的斷層掃瞄影像,醫生宣布病危。依他生前的叮嚀,全家人當天決定不進行侵入性急救,不進行開腦手術。結果爸爸住院九天後離世。
心電圖完全靜止前約六小時,哥哥致電北區遺體聯絡捐贈中心,國防醫學院接到通知之後,成功在四十八小時內接走了遺體,進行防腐處理。終於圓滿爸爸多年來捐贈大體的宏大遺願。
冬天,爸爸坐在桌前,吃力地填寫一份表格,忍不住埋怨:「你看你看,我現在連寫字都會抖了,一個字都寫不好……」我注視著那份表格,原來是「大體捐贈同意書」。當時還安撫他:「沒關係啊,你多久才寫一次字?已經寫完啦!」「不行啦……現在連寫字都不行啦……」爸嘆著氣。
爸爸一向以他工整漂亮的字而自豪。即使是草寫,也都規規矩矩同樣大小,細密整齊落在書頁的邊緣。他的筆記真是模範,任誰看到都會汗顏。
爸爸跌倒宣布病危後,媽媽趕快把捐贈志願書用限時掛號寄出。國防醫學院的回覆很快,兩天後我們就接到了回函。至於遺囑,爸爸很早就手寫好,塗改過,又改寫,在一次家庭聚餐的傍晚,把四個孩子叫到跟前一一簽了名。
爸爸過世後,媽媽開始翻找辦理繼承及除戶的種種證件資料,竟然一打開抽屜就找到。沒想到他在跌倒前,早就一一備妥了。
在榮總懷遠堂冰櫃放置了一個晚上,三月十七日一早九點半,國防醫學院的大體專車抵達。我和媽媽、姊姊,陪伴著爸爸上車。媽雖孱弱但仍堅持要坐在屍袋旁。天氣很暖和,我們三人都只穿春季的服裝,行進中,媽媽不時隔著冒著寒氣的屍袋,輕輕摸著爸的臉。
也是國防醫學院校友的嫂嫂,早在大體車停妥前就在解剖學科入口等待。羅世圓小姐迎接我們進去,到「大體處理室」前止步。
「從這裡進去以後,你們就永遠見不到朱先生了,在這裡看他最後一面吧!」羅小姐幫我們拉開了屍袋的拉鏈,露出透著冰霜的爸爸的臉。
姊姊拍下爸的遺容。我突然發現,他沒有戴假牙,啊,我們忘了幫爸爸在臨終前戴上假牙!難怪下顎是凹陷的!這樣不好看!
「處理大體的時候,假牙也是要拿掉的。」羅小姐說。那是媽媽和姊姊見爸爸的最後一面,再怎麼也沒想到,我,兩年後竟還會再見經化學處理,已經是「永垂不朽」的爸爸。
在解剖學科辦公室,羅小姐體貼送上了仍溫的午餐便當和茶水,招待我們休息片刻。她說了些什麼安慰感謝的話,我全沒聽進去。當時的生物及解剖學科主任馬國興,從外匆匆趕進來致意。一坐下,便情不自禁地握拳慨嘆:「朱信老師在我們這裡也服務很久!大家都這麼熟!怎麼會想到是他的爸爸……」
看到外人的悲傷,我們一臉木然。相遇在慰靈公祭
死亡,在尚未割捨之際是沈重的,是悲痛的。
然而,若死者告訴我們,不要哭泣,
他並未長眠於泥土中,
而是化作微風日日吹拂……
小哥,穿著整齊筆挺的軍服,頭髮梳得油亮整齊,以沈穩的語氣開始說話。小哥曾說他是全家最愛哭的人,此刻,他為了更重要的事,把悲傷和眼淚都隱藏在心裡。
爸爸,您好嗎?你離開我們一年了。今天,媽媽、大姊、小妹、大哥、媳婦、姊夫,大家到齊了。我們已經完成了你捐贈的志願。我很驕傲,所以我著軍服來參加這個儀式。
您十五歲離家從軍,一生都是大時代的見證。您雖然只有小學畢業,卻在軍中自學自修,考取公費出國。我也在您的鼓勵之下,放棄台大牙醫,決定進入國防醫學院。一九九○年、醫科八十三期畢業後,成為一個中尉的醫官。
身為職業軍人,您從來不是一個刻板印象中的好父親、好先生。因為您要值班留守、戰備、演習……我們小時候可能一個月或兩個月才看到您一次。
您沒辦法陪媽媽照顧小孩,沒辦法陪媽媽去買菜、處理家務,媽媽一個人把我們四個小孩拉拔長大。但我從小看著您,無怨無悔奉獻一切給國家。所以我也毫無畏懼地走向職業軍人的生涯。
我更驕傲的是,我們都同為國防醫學院的老師,我在航空醫學、航空生理、臨床神經的領域教學生,是言教。暑假之後,您馬上就要開始教育我的學弟學妹進入醫學領域最重要一門課:人體解剖學。您才是真正的身教。
您的選擇,身為醫學系學生的我最清楚:那是千刀萬剮,但是您很坦然。
小時候,您告訴我們:「十幾歲起就參加諸多戰役,身上哪裡有子彈碎片,哪裡有傷痕……」戰爭的時候沒有糧食,你們會吃中彈死亡的馬肉。在臨終前幾年您說要捐贈大體,而且要捐給國防醫學院。我知道,一部分原因,因為我是國防醫學院畢業的,另一方面,您一生奉獻國家,軍校在你腦海中,代表國家。
今年暑假以後,爸爸,您會成為醫科一一四期學弟學妹們的老師。他們在解剖過程會了解到您做過食道氣室的手術,白內障開過刀,還有肺氣腫,以及左腳臏骨因為車禍碎裂被移除,腹股溝疝氣動過兩次手術,裡面用網膜來修補。七年前您曾發生心肌梗塞,所以有一部分心臟肌肉已經壞死,他們還會發現臀部有作戰留下的砲彈碎片。
我相信,他們從您身上,除了學到生理解剖知識之外,更希望我的學弟學妹們要記得,今天其他所有大體老師,所有躺在不銹鋼解剖枱上的老師。也會記得我爸爸是奉獻一輩子的軍人,他的太太身為軍眷,要一個人帶領所有小孩長大,他有四位子女,是個淡泊名利的人。
爸爸,我很高興我和您都是軍人,我是救人的軍醫,您是保國衛民的將軍。
我們也同樣是國防醫學院的老師。我教學生活著時候的疾病,您教學生最重要的人生的課程:死亡。
您已經離開一年了,我知道您會眷顧著我們。小時候您最常訓勉我的一句話「取法乎上,盡得乎中。」您說,學習的目標訂得很高,還不見得能達到,更何況是沒有最高的目標?這句話,我希望所有醫科一一四期,還有其他參與解剖的同學都要謹記,所有奉獻他的身體的這些大體老師。
爸爸,謝謝您。我以一個身為兒子的身分,以一個醫學系學生、國防醫學院的校友的身份,還有一個身為國防醫學院老師的身分。
謝謝!
雖然本屆大體老師有七位,然而致詞的卻只有兩位。聽著小哥的致詞,情感綿長動人,一些觀眾不禁低頭啜泣。
小哥二度哽咽,卻依然完成這個艱難的任務。快轉人生:大體老師家訪
升上大三的國防醫學院醫學系學生即將上大體解剖課,
親訪大體老師的家庭,是老師規定的作業,
了解大體老師的生平與家庭成員背景……
也是讓這些孩子們對「老師」貢獻大體的尊重。
因為幫公共電視企畫拍攝《誰來晚餐》節目,認識了與爸同期的大體老師陳俊明的家人,開啟了拍攝他們家庭紀錄片的緣分。
這位朋友口中愛冒險、活力充沛、喜歡教人開車的陳老師,生前與爸爸素不相識,卻在死後成了鄰枱同事。在二○一七這個暴雨淹台的失常夏季,由我幫他們兩人,分別製作了影像和書籍的不朽回憶。
一個是住台中清水道地本省人,一個是終生住台北的外省老芋仔;一個是不苟言笑,另一個口若懸河、花招奇多;爸沒有跳舞細胞,陳俊明老師卻是天生舞棍;爸不喜旅行,陳老師卻在高中時環就環島遊台灣;爸高大健壯,陳老師纖瘦修長;爸是路痴,連路邊停車都很有障礙;陳老師卻是能馴服大遊覽車的「交通工具狂」,擁有「腦內導航」的超能力;我爸一放假就宅在家,陳老師卻是休假就載全家大小出去玩……爸爸出生入死,不管是手術或任何治療一聲都不會吭,而陳老師卻毫不隱藏他的「幼秀」,連打針都會唉唷唉唷地大聲喊疼……
唯一的共通點,是他們都很喜歡學英文。一個喜歡聽英文老歌,一個生前是英文老師。還有他們都非常愛乾淨愛漂亮。爸生前最難忍受的是小腹突出,肌肉變小,頭髮被風吹亂了沒人告訴他,一有汗臭馬上去沖澡……陳老師則是出門一定要穿襯衫,或乾淨的T恤配牛仔褲,一定繫皮帶,連鞋子全身搭配好才出門……
年齡相差三十歲,去世日子差四天,同期成為大體老師。鄰枱的同事,一起被切割。好欸。
就在我們接待家訪的同一個月,陳俊明老師的第二組學生李佳怡等同學們,一行人也浩浩盪盪來到陳老師家,和陳老師的太太,我尊稱她「溫姐」的溫玉蕊,還有陳老師生前的死黨好友進行訪問。
客廳的吊燈泛著淡黃色。十位同學來到陳老師家的客廳,圍著咖啡桌,把客廳擠滿了。同學問的問題大概也是圍繞著陳老師的個性,為什麼要捐大體,以及他和師母及好友之間的共同回憶等等。
※ ※ ※
聊完歡樂的回憶,免不了談到捐贈,略為傷感的主題。三位老朋友,哽咽過了又開始開玩笑:「你們在解剖的時候看看他的腦神經有沒有錯綜複雜?」老師的朋友黃先生說著,「他的想法很奇怪嘛!是不是腦筋跟人家有什麼不一樣?幫我們檢查看看!」學生笑了。
溫姐知不知道解剖之後,他的先生會變成什麼樣子?學生沒問,可能還沒經歷到,不清楚,也不忍問。但她對這件事是豁達的,看開的,因為她也追隨先生簽妥大體捐贈志願書了。
「你們在幫他做『那個』的時候,可以放音樂嗎?」溫姐輕輕地請求著。帶著一種大家閨秀的禮貌。
「應該可以。」學生答。「我們跟老師說說看。」
「他喜歡聽英文老歌,他喜歡聽的,對……」
「阿姨歌單可以給我們。」學生們笑著說,「我們自己去找歌。」
「他有英文名字叫馬克,Mark,或麥克。」
後來教解剖學的馬國興老師回憶,當初聽到放音樂這個要求很奇怪,但沒有理由不答應。於是第二組就成了馬老師教授解剖學二十多年來,第一批為大體老師播放音樂的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