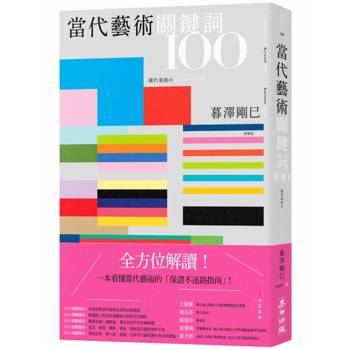003.
立體主義 cubisme 〔法〕
キュビスム
二十世紀初興起的抽象繪畫風潮,原本是馬諦斯對喬治‧布拉克作品的蔑稱。不過,畫面中引進多個焦點,形成立體架構,徹底顛覆一點透視法(以一個消失點為中心的畫面架構技法)的構圖方式,或是以明暗法為本的近代繪畫的寫實描繪方式,可謂二十世紀藝術最具革命創新性的風潮和手法之一。
運用多視點的畫面架構,可追溯到皮耶羅‧弗朗西斯卡。不過,真正明確刻意運用的是塞尚等後期印象派畫家,而立體主義承繼這項改革,主要兩名大將是布拉克和畢卡索。當時,布拉克的作品近似野獸主義(*頁6)風格,畢卡索正在摸索「藍色時期」之後的風格。
立體主義的發展是從兩人相遇的一九○七年開始,直到一九一八年,前後約十年。其間的發展可分為初期立體主義、分析立體主義、綜合立體主義等三個階段。一九○七~八年,透過馬諦斯等人,畢卡索大量接觸非洲的黑人雕刻,對於其迥異於西洋明暗法、大量運用凹面的造形,深受衝擊。這種衝擊的影響,反映在《阿維儂的少女們》(*頁xxii,圖3)等作品中。另一方面,在一九○七年舉辦的塞尚展中,布拉克深受刺激,開始不斷思考自己「以圓筒、球、三角錐處理自然」的主張應該如何發展。透過兩人的結合,立體質感轉換到平面的立體主義正式展開。
之後的分析立體主義時代,兩人的合作正式邁上軌道。立體主義一開始發展時還存留的事物具象性逐漸消失,拋棄一點透視法、引進多視點也是在這個時期。一九一一年,和畢卡索簽有專屬契約的巴黎康懷勒畫廊舉辦兩人的聯展,促使立體主義廣為人知,並帶來費爾南‧雷捷、羅伯‧德洛內等追隨者。
一九一二年,兩人開發運用報紙等將紙片黏貼在畫布上的拼貼技法,並幾乎在同一時期開始創作三度空間作品的集合藝術(經由拼裝組合黏貼而成的立體作品),開啟綜合立體主義時代,邁向更多視點的造形。此時,畢卡索經常描繪吉他、小提琴、曼陀琴等樂器。這些樂器充滿人工匠意,且是具抽象性的構造物,恰巧適合用來表現立體主義意識追求的主題。這個時期還加入新追隨者梵‧格里斯,將「從圓筒型製作瓶子」技法更推上層樓。
一九一八年,布拉克從軍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人康懷勒的援助因此斷絕,布拉克和畢卡索的合作也告終。畢卡索開始轉移興趣,醉心新古典主義。當時熱潮已過的立體主義,正如曾是畫家的建築家勒‧柯比意所批判的:「立體主義已經走進了死胡同。」
作為一個藝術潮流,立體主義雖然短命,可是對於抽象藝術、奧菲主義(進一步推動立體主義的抽象繪畫運動)、純粹主義(柯比意等人推動的繪畫運動)、未來派(*頁10)或是巴黎畫派(一九二○年代在巴黎蒙帕納斯或蒙馬特活動的各種不同國籍和作風的畫家總稱)等同時代的藝術,都帶來莫大的影響。
021.
普普藝術 pop art
ポップ・アート
大眾藝術(Popular Art)的略稱,專指將誕生於現代大眾文化的圖像、記號、成品等,大膽引進繪畫和雕刻領域的現代藝術潮流。一九五○年代後半,起始於倫敦,一九六○年代初期傳到美國,形成反映該時代社會百態的一大潮流。
一九五○年代中期,倫敦藝評勞倫斯‧艾洛威等藝術界人士開始使用普普藝術這個詞。一九五六年,在理查‧漢彌頓的繪畫作品中,已經出現「POP」的字樣。漢彌頓、愛德瓦多‧巴洛奇、彼得‧布萊克、艾倫‧瓊斯等年輕藝術家,不約而同運用大眾文化的形象,製作能夠產生強烈共鳴的作品。不過,一九六○年代以後,隨著艾洛威轉移陣地到美國,普普藝術的重心也移至美國。
在倫敦出現普普藝術作品不久後,運用大眾文化形象的作品,也在美國登場。最初創作這類作品的是賈斯培‧瓊斯、羅伯特‧羅森伯格等新達達(*頁40)藝術家。然後是一九六二年在紐約辛得尼‧簡尼斯畫廊舉辦的《新寫實主義者》展中,展出以好萊塢電影明星或是米老鼠等美國卡通為主題的作品,轟動一時。商業設計師出身的安迪‧沃荷運用絹印技法,製作貓王、瑪麗蓮夢露的肖像。和安迪‧沃荷齊名的畫家羅伊‧李奇登斯坦則在一九六五年,放大單格漫畫,製作《紮髮巾的女孩》(*頁xxviii,圖10),引進完全不同於以往的手法。這些作品比強烈諷刺工業社會的新達達更為深入,且更顯著地操弄消費社會的大眾文化記號,因而稱為普普藝術,獲得大眾狂熱的支持。尤其是安迪‧沃荷,無論是他的作品或現實生活,都一改以往藝術家的形象。他將自己的畫室稱為工廠,量產以流行巨星為圖像的作品,也參與電影製作;在私生活方面,也不時傳出不亞於好萊塢明星的花邊新聞,甚至還發生暗殺未遂等醜聞事件。普普藝術的其他藝術家還有詹姆士‧羅森奎斯特、湯姆‧威塞爾曼、克雷斯‧歐登伯格、喬治‧西格爾、愛德華‧金霍茲、吉姆‧代恩等人。
普普藝術在藝術史上的最大意義,在於促使人們重新思考以往區分高級文化和大眾文化的觀念。對於從抽象表現主義(*頁36)到低限藝術(*頁48)一路發展而來的美國現代藝術,普普藝術可謂提出了重要的另一種選擇,促成嶄新價值觀的產生。
其他國家類似普普藝術的潮流,有法國的新寫實主義、德國的資本寫實主義、前蘇聯的蘇聯普普藝術(Sots Art)等。這些潮流的共通點都在於運用大眾文化形象,以及對資本主義展現嘲諷的態度。
日本的普普先驅則有橫尾忠則、立石大河亞等人。後來,由於越戰陷入苦戰,以及學生運動爆發等社會變化,進入七○年代後,觀念藝術(*頁56)抬頭,於是一九六○年代和時代性緊密相扣的普普藝術熱潮衰退。不過,運用大眾文化形象的手法,日後的藝術潮流仍舊以各種形式持續嘗試。
057.
意識形態 ideology
イデオロギー
表示思想、世界觀的傾向或體系的用語,尤其常用於表示政治信念,例如保守主義者、民族主義者稱為右翼;共產主義者、社會民主主義者稱為左翼。ideology一詞則源自於希臘文的「觀念」(ideo)。
最初直接提起這個概念的,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德意志意識形態》,因此,意識形態的定義和理論,長期以來和馬克思主義有著難分難解的關係。馬克思和恩格斯在黑格爾歷史哲學的延長線上,將意識形態定位為各個階級固有的價值觀。也就是說,在階級社會中,各有對應的意識形態支配著特定階級的價值觀。馬克思「中產階級意識形態」、「無產階級藝術意識形態」的概念,後來被列寧將其正當化為階級鬥爭的理念。
後來,共產主義革命的烏托邦社會建設大夢瓦解,由馬克思提出的、具批判性功能的意識形態也剩下空殼。在一九六○年代的法國,透過結構主義和符號學,意識形態獲得嶄新的解釋,重新組合成思考人類主體的新概念。這一點,令人立刻想起哲學家路易‧阿圖塞。以科學觀點徹底重新解讀馬克思的阿圖塞,認為意識形態是以人類為主體,能夠為既有社會關係賦予保證的事物。這項結論完全不同於以往的解釋,過去是將意識形態視為結合各種制度、為了肯定現況的裝置,而阿圖塞則認為它是人類在社會中為了生存,必須重新審視的各種不同框架。這種解釋在當時的影響力,甚至重挫蘇聯型社會主義的信賴度。
意識形態的重新解釋,當然對藝術的研究和評論也影響重大。這個影響廣及各個層面,以藝術史研究(*頁184)來說,以往的藝術史,都極為重視原創性(*頁134)和藝術家。無須贅言,現代主義的藝術觀為兩者賦予獨一無二的地位。可是,在後現代主義(*頁196)下,原創或複製已無分別的作品流通市面,甚至高唱「藝術家之死」。如果依照阿圖塞的說法,無論是原創性或作者,都只是一個能夠置換為其他價值觀的意識形態罷了。
在藝術家中,當然有不少人自覺地注意到意識形態的問題。尤其是以宣傳特定政治訊息為主的政治藝術(*頁68)、以女性為主的女性主義藝術(*頁192),就是其中典型。即使社會性訊息稀薄,也有藝術家將藝術視為是根據展覽或教育制度而構成的一種制度,來探究其中相關的意識形態性質。
另一方面,完全不同於阿圖塞對意識形態的解釋,卻能有效解釋藝術作品的是皮耶‧布赫迪厄的「慣習」(habitus)。「慣習」是指品味和階級之間有著強烈關係。布赫迪厄根據詳細調查,發現兩者的確具有密切關聯,他在《德意志意識形態》、《資本論》上,再以康德的《判斷力批判》為基準,發展出「慣習」理論。「慣習」理論其實具有「品味的意識形態」特點。布赫迪厄和以政治作風著稱的藝術家漢斯‧海克對談,整理兩人對談而成的《自由─交換》內容充實,其中提出的想法已證實能夠有效解釋當代藝術。
096.
白立方空間 white cube
ホワイトキューブ
天花板、牆壁都是純白色,除了出入口以外,沒有任何開口,也沒有樑柱等遮蔽物和裝飾物的室內空間。這樣的空間被認為是展示藝術作品的最標準空間,廣泛使用於全球的美術館(*頁182)和畫廊(*頁140)。
這種白立方空間的空間性質,受到繪畫、雕刻或是只具鑑賞目的的純粹藝術的喜好,因為它沒有任何妨礙鑑賞的遮蔽物或裝飾物,以及能在安定的光源下欣賞;此外,許多當代藝術作品是不規則形狀,在展示時,偏好毫無任何主張、不具個性特徵的空間。白立方空間就是以現代主義藝術的這些約定為前提的展示空間。
此外,因為世界各地都是性質相同的空間,同樣的作品即使轉換展示場所,都能以相同的條件提供鑑賞,促使收藏品的外借、展覽會的各地巡展成為常態。即使是將空間作品化的裝置藝術(*頁122),也能以毫無個性、卻又充滿運用彈性的白立方空間為基礎進行創作。
白立方空間的普及,使得繪畫裝框與否也和以往的展示大為不同。直到二十世紀前半,無論是油彩或水彩的畫作,幾乎都是加裝畫框,抽象表現主義(*頁30)以後,作品不加裝畫框、直接擺設在牆上的實例愈來愈多。除了因為許多作品的尺寸無法尋得適合的畫框外,也因為畫框的裝飾性會妨礙作品鑑賞,所以將純白色的牆壁視為一種畫框,作為誘使觀眾投入畫作世界的觸媒。在大型畫布上塗滿色彩、擁有獨特視覺錯覺(繪畫的錯覺效果),正是抽象表現主義繪畫的精采之處;這種特質,唯有在不進行裝框、直接架設在純白牆面的白立方空間中,才能最為凸顯。
白立方空間的普及和建築風格的流行也大有關聯。一九二○年代的歐洲,稱為「國際風格」的功能主義建築正值全盛時期。這項設計思潮,不同於以往重視各地區傳統創意和建材的建築,而是期望讓簡潔明快且理性設計的功能主義建築普及全世界,於是,在鋼筋、玻璃、混凝土等便宜且容易得手的高耐久性建材出現後,在正方體建築物中設置幾個立方體狀空間的單純設計迅速擴展。最具代表性的建築家之一是密斯‧凡德羅,他將這個想法更為延伸發展,構想出「通用空間」這種形狀單純的同質空間,純素色的白立方空間,就是實踐了通用空間的理念。在注重功能主義的美術館建設日漸普及後,白立方空間也更為普及。
白立方空間確立成為美術館或畫廊的標準空間後(倫敦有間名為白立方空間的畫廊,就是為了凸顯這種存在感),有些藝術家卻厭惡在這種無機空間中展示作品,因此,故意製作破壞空間調和感的作品,或是像地景藝術(*頁50)般設法向戶外尋求展示場所。有些經手美術館建築的建築家,也厭倦白立方空間,而為空間設計出不同的性格變化。例如在美術館建築當中,積極引進建地所在地區的固有特質,打造出適合設置特定場域(*頁150)性作品的空間,磯崎新的「第三世代美術館」就是其中典型。
立體主義 cubisme 〔法〕
キュビスム
二十世紀初興起的抽象繪畫風潮,原本是馬諦斯對喬治‧布拉克作品的蔑稱。不過,畫面中引進多個焦點,形成立體架構,徹底顛覆一點透視法(以一個消失點為中心的畫面架構技法)的構圖方式,或是以明暗法為本的近代繪畫的寫實描繪方式,可謂二十世紀藝術最具革命創新性的風潮和手法之一。
運用多視點的畫面架構,可追溯到皮耶羅‧弗朗西斯卡。不過,真正明確刻意運用的是塞尚等後期印象派畫家,而立體主義承繼這項改革,主要兩名大將是布拉克和畢卡索。當時,布拉克的作品近似野獸主義(*頁6)風格,畢卡索正在摸索「藍色時期」之後的風格。
立體主義的發展是從兩人相遇的一九○七年開始,直到一九一八年,前後約十年。其間的發展可分為初期立體主義、分析立體主義、綜合立體主義等三個階段。一九○七~八年,透過馬諦斯等人,畢卡索大量接觸非洲的黑人雕刻,對於其迥異於西洋明暗法、大量運用凹面的造形,深受衝擊。這種衝擊的影響,反映在《阿維儂的少女們》(*頁xxii,圖3)等作品中。另一方面,在一九○七年舉辦的塞尚展中,布拉克深受刺激,開始不斷思考自己「以圓筒、球、三角錐處理自然」的主張應該如何發展。透過兩人的結合,立體質感轉換到平面的立體主義正式展開。
之後的分析立體主義時代,兩人的合作正式邁上軌道。立體主義一開始發展時還存留的事物具象性逐漸消失,拋棄一點透視法、引進多視點也是在這個時期。一九一一年,和畢卡索簽有專屬契約的巴黎康懷勒畫廊舉辦兩人的聯展,促使立體主義廣為人知,並帶來費爾南‧雷捷、羅伯‧德洛內等追隨者。
一九一二年,兩人開發運用報紙等將紙片黏貼在畫布上的拼貼技法,並幾乎在同一時期開始創作三度空間作品的集合藝術(經由拼裝組合黏貼而成的立體作品),開啟綜合立體主義時代,邁向更多視點的造形。此時,畢卡索經常描繪吉他、小提琴、曼陀琴等樂器。這些樂器充滿人工匠意,且是具抽象性的構造物,恰巧適合用來表現立體主義意識追求的主題。這個時期還加入新追隨者梵‧格里斯,將「從圓筒型製作瓶子」技法更推上層樓。
一九一八年,布拉克從軍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人康懷勒的援助因此斷絕,布拉克和畢卡索的合作也告終。畢卡索開始轉移興趣,醉心新古典主義。當時熱潮已過的立體主義,正如曾是畫家的建築家勒‧柯比意所批判的:「立體主義已經走進了死胡同。」
作為一個藝術潮流,立體主義雖然短命,可是對於抽象藝術、奧菲主義(進一步推動立體主義的抽象繪畫運動)、純粹主義(柯比意等人推動的繪畫運動)、未來派(*頁10)或是巴黎畫派(一九二○年代在巴黎蒙帕納斯或蒙馬特活動的各種不同國籍和作風的畫家總稱)等同時代的藝術,都帶來莫大的影響。
021.
普普藝術 pop art
ポップ・アート
大眾藝術(Popular Art)的略稱,專指將誕生於現代大眾文化的圖像、記號、成品等,大膽引進繪畫和雕刻領域的現代藝術潮流。一九五○年代後半,起始於倫敦,一九六○年代初期傳到美國,形成反映該時代社會百態的一大潮流。
一九五○年代中期,倫敦藝評勞倫斯‧艾洛威等藝術界人士開始使用普普藝術這個詞。一九五六年,在理查‧漢彌頓的繪畫作品中,已經出現「POP」的字樣。漢彌頓、愛德瓦多‧巴洛奇、彼得‧布萊克、艾倫‧瓊斯等年輕藝術家,不約而同運用大眾文化的形象,製作能夠產生強烈共鳴的作品。不過,一九六○年代以後,隨著艾洛威轉移陣地到美國,普普藝術的重心也移至美國。
在倫敦出現普普藝術作品不久後,運用大眾文化形象的作品,也在美國登場。最初創作這類作品的是賈斯培‧瓊斯、羅伯特‧羅森伯格等新達達(*頁40)藝術家。然後是一九六二年在紐約辛得尼‧簡尼斯畫廊舉辦的《新寫實主義者》展中,展出以好萊塢電影明星或是米老鼠等美國卡通為主題的作品,轟動一時。商業設計師出身的安迪‧沃荷運用絹印技法,製作貓王、瑪麗蓮夢露的肖像。和安迪‧沃荷齊名的畫家羅伊‧李奇登斯坦則在一九六五年,放大單格漫畫,製作《紮髮巾的女孩》(*頁xxviii,圖10),引進完全不同於以往的手法。這些作品比強烈諷刺工業社會的新達達更為深入,且更顯著地操弄消費社會的大眾文化記號,因而稱為普普藝術,獲得大眾狂熱的支持。尤其是安迪‧沃荷,無論是他的作品或現實生活,都一改以往藝術家的形象。他將自己的畫室稱為工廠,量產以流行巨星為圖像的作品,也參與電影製作;在私生活方面,也不時傳出不亞於好萊塢明星的花邊新聞,甚至還發生暗殺未遂等醜聞事件。普普藝術的其他藝術家還有詹姆士‧羅森奎斯特、湯姆‧威塞爾曼、克雷斯‧歐登伯格、喬治‧西格爾、愛德華‧金霍茲、吉姆‧代恩等人。
普普藝術在藝術史上的最大意義,在於促使人們重新思考以往區分高級文化和大眾文化的觀念。對於從抽象表現主義(*頁36)到低限藝術(*頁48)一路發展而來的美國現代藝術,普普藝術可謂提出了重要的另一種選擇,促成嶄新價值觀的產生。
其他國家類似普普藝術的潮流,有法國的新寫實主義、德國的資本寫實主義、前蘇聯的蘇聯普普藝術(Sots Art)等。這些潮流的共通點都在於運用大眾文化形象,以及對資本主義展現嘲諷的態度。
日本的普普先驅則有橫尾忠則、立石大河亞等人。後來,由於越戰陷入苦戰,以及學生運動爆發等社會變化,進入七○年代後,觀念藝術(*頁56)抬頭,於是一九六○年代和時代性緊密相扣的普普藝術熱潮衰退。不過,運用大眾文化形象的手法,日後的藝術潮流仍舊以各種形式持續嘗試。
057.
意識形態 ideology
イデオロギー
表示思想、世界觀的傾向或體系的用語,尤其常用於表示政治信念,例如保守主義者、民族主義者稱為右翼;共產主義者、社會民主主義者稱為左翼。ideology一詞則源自於希臘文的「觀念」(ideo)。
最初直接提起這個概念的,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德意志意識形態》,因此,意識形態的定義和理論,長期以來和馬克思主義有著難分難解的關係。馬克思和恩格斯在黑格爾歷史哲學的延長線上,將意識形態定位為各個階級固有的價值觀。也就是說,在階級社會中,各有對應的意識形態支配著特定階級的價值觀。馬克思「中產階級意識形態」、「無產階級藝術意識形態」的概念,後來被列寧將其正當化為階級鬥爭的理念。
後來,共產主義革命的烏托邦社會建設大夢瓦解,由馬克思提出的、具批判性功能的意識形態也剩下空殼。在一九六○年代的法國,透過結構主義和符號學,意識形態獲得嶄新的解釋,重新組合成思考人類主體的新概念。這一點,令人立刻想起哲學家路易‧阿圖塞。以科學觀點徹底重新解讀馬克思的阿圖塞,認為意識形態是以人類為主體,能夠為既有社會關係賦予保證的事物。這項結論完全不同於以往的解釋,過去是將意識形態視為結合各種制度、為了肯定現況的裝置,而阿圖塞則認為它是人類在社會中為了生存,必須重新審視的各種不同框架。這種解釋在當時的影響力,甚至重挫蘇聯型社會主義的信賴度。
意識形態的重新解釋,當然對藝術的研究和評論也影響重大。這個影響廣及各個層面,以藝術史研究(*頁184)來說,以往的藝術史,都極為重視原創性(*頁134)和藝術家。無須贅言,現代主義的藝術觀為兩者賦予獨一無二的地位。可是,在後現代主義(*頁196)下,原創或複製已無分別的作品流通市面,甚至高唱「藝術家之死」。如果依照阿圖塞的說法,無論是原創性或作者,都只是一個能夠置換為其他價值觀的意識形態罷了。
在藝術家中,當然有不少人自覺地注意到意識形態的問題。尤其是以宣傳特定政治訊息為主的政治藝術(*頁68)、以女性為主的女性主義藝術(*頁192),就是其中典型。即使社會性訊息稀薄,也有藝術家將藝術視為是根據展覽或教育制度而構成的一種制度,來探究其中相關的意識形態性質。
另一方面,完全不同於阿圖塞對意識形態的解釋,卻能有效解釋藝術作品的是皮耶‧布赫迪厄的「慣習」(habitus)。「慣習」是指品味和階級之間有著強烈關係。布赫迪厄根據詳細調查,發現兩者的確具有密切關聯,他在《德意志意識形態》、《資本論》上,再以康德的《判斷力批判》為基準,發展出「慣習」理論。「慣習」理論其實具有「品味的意識形態」特點。布赫迪厄和以政治作風著稱的藝術家漢斯‧海克對談,整理兩人對談而成的《自由─交換》內容充實,其中提出的想法已證實能夠有效解釋當代藝術。
096.
白立方空間 white cube
ホワイトキューブ
天花板、牆壁都是純白色,除了出入口以外,沒有任何開口,也沒有樑柱等遮蔽物和裝飾物的室內空間。這樣的空間被認為是展示藝術作品的最標準空間,廣泛使用於全球的美術館(*頁182)和畫廊(*頁140)。
這種白立方空間的空間性質,受到繪畫、雕刻或是只具鑑賞目的的純粹藝術的喜好,因為它沒有任何妨礙鑑賞的遮蔽物或裝飾物,以及能在安定的光源下欣賞;此外,許多當代藝術作品是不規則形狀,在展示時,偏好毫無任何主張、不具個性特徵的空間。白立方空間就是以現代主義藝術的這些約定為前提的展示空間。
此外,因為世界各地都是性質相同的空間,同樣的作品即使轉換展示場所,都能以相同的條件提供鑑賞,促使收藏品的外借、展覽會的各地巡展成為常態。即使是將空間作品化的裝置藝術(*頁122),也能以毫無個性、卻又充滿運用彈性的白立方空間為基礎進行創作。
白立方空間的普及,使得繪畫裝框與否也和以往的展示大為不同。直到二十世紀前半,無論是油彩或水彩的畫作,幾乎都是加裝畫框,抽象表現主義(*頁30)以後,作品不加裝畫框、直接擺設在牆上的實例愈來愈多。除了因為許多作品的尺寸無法尋得適合的畫框外,也因為畫框的裝飾性會妨礙作品鑑賞,所以將純白色的牆壁視為一種畫框,作為誘使觀眾投入畫作世界的觸媒。在大型畫布上塗滿色彩、擁有獨特視覺錯覺(繪畫的錯覺效果),正是抽象表現主義繪畫的精采之處;這種特質,唯有在不進行裝框、直接架設在純白牆面的白立方空間中,才能最為凸顯。
白立方空間的普及和建築風格的流行也大有關聯。一九二○年代的歐洲,稱為「國際風格」的功能主義建築正值全盛時期。這項設計思潮,不同於以往重視各地區傳統創意和建材的建築,而是期望讓簡潔明快且理性設計的功能主義建築普及全世界,於是,在鋼筋、玻璃、混凝土等便宜且容易得手的高耐久性建材出現後,在正方體建築物中設置幾個立方體狀空間的單純設計迅速擴展。最具代表性的建築家之一是密斯‧凡德羅,他將這個想法更為延伸發展,構想出「通用空間」這種形狀單純的同質空間,純素色的白立方空間,就是實踐了通用空間的理念。在注重功能主義的美術館建設日漸普及後,白立方空間也更為普及。
白立方空間確立成為美術館或畫廊的標準空間後(倫敦有間名為白立方空間的畫廊,就是為了凸顯這種存在感),有些藝術家卻厭惡在這種無機空間中展示作品,因此,故意製作破壞空間調和感的作品,或是像地景藝術(*頁50)般設法向戶外尋求展示場所。有些經手美術館建築的建築家,也厭倦白立方空間,而為空間設計出不同的性格變化。例如在美術館建築當中,積極引進建地所在地區的固有特質,打造出適合設置特定場域(*頁150)性作品的空間,磯崎新的「第三世代美術館」就是其中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