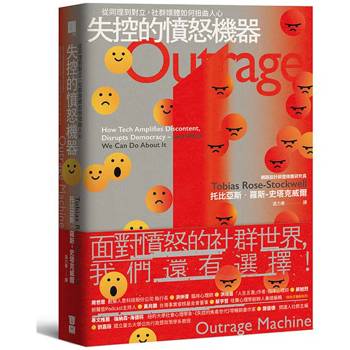Chapter 11 直覺和網路
我對比特犬沒有意見。我這輩子到現在養過幾條狗,牠們全都是雜種狗,大多很難看出血統。偶爾我會在廣播或社群媒體上聽到有人公開辯論比特犬的事情,他們的論點包括指控比特犬是暴力品種,被用來當鬥犬,還有眾所周知比特犬會咬小孩。辯論的方向在 於是否該嚴格控管這個犬種。
可是我在這個議題上沒有確切想法(可以說我跟這件事沒有一丁點關係),所以避免對此有意見。我個人跟比特犬有關的趣聞就 只有一個,那段關係挺討人喜歡;有位老朋友養了耳聾的救援比特犬,牠叫愛西絲,每次我見到愛西絲只覺得有牠相伴真好。
這個蠻不在乎的態度在我某一天滑社群媒體時有了轉變,因為我看到動態消息裡有個看似無害的短影片播放了起來,那甚至不是 我認識的人分享的推薦影片。
這支短影片播放的是某郊區街上住家前,監視器所拍到的畫面。畫面裡可以看到一隻貓慵懶地坐在車道上,過了一會兒,有個女人牽著兩隻比特犬從左邊人行道進入鏡頭範圍。
接下來發生的事情讓我有些不忍。兩隻比特犬一看到那隻貓便朝牠衝去,把主人面朝下拖倒在地,又拖著她越過人行道衝到貓那裡,然後兩隻狗開始凶猛地咬貓。兩隻比特犬的力氣很大,主人沒辦法控制牠們,她站起身試著把狗踢開救那隻貓,但是兩隻狗沒有 停下來,影片結束時我只能假設貓應該被咬死了。
這支影片太嚇人了,看完後我覺得既憤怒又厭惡,而且立刻就讓我在比特犬議題上產生非常極端的想法,對任何捍衛比特犬的證 據也出現更多質疑。
但是這支影片是否可以代表整個比特犬品種呢?於是我上網查 詢,結果快速查了Google之後,搜尋結果顯示:沒錯,比特犬很危險。二○○五至二○一七年間,在致命傷人的犬隻攻擊事件中,此 品種占其中的六六%。這個統計數據和以下圖表,應該就足以斷 定那支駭人的短影片不是騙人的。比特犬攻擊貓的事件與統計數據 十分吻合。
那支短影片再加上這些統計數據,等於強力支持針對特定犬種立法,即基於公眾安全立法禁養特定犬種。事實上,一九八○和一 九九○年代就通過許多地方條文和州法規,以減少比特犬的盛行。
我的情緒反應源自於一起事件。這起事件非常強烈,又有畫面為證,再加上Google的搜尋結果也為它背書。我如常過著生活,但對網路提供給我的比特犬資訊抱持強烈的道德立場─這個犬種問題很大。
過了一陣子,一位我信任的朋友提到比特犬是深受誤解的犬種之一。我強迫自己停下來重新思考。「不對,」我說道:「有不錯的研究結果指出,這種狗到目前為止是國內犬隻攻擊事件中傷人致死率最高的犬種。」他親切地建議我回去多做一點功課。「數據另有說法。」他告訴我。
我深表懷疑,但不敢多辯解什麼,所以我回去多讀了一些資料,重新檢驗我在這個議題上的資訊來源。我也去耙梳了其他若干帳號的內容,挖得更深入,結果找到的發現令我吃驚。
朋友的質疑讓我開始漸漸有了自己的想法。更深入的人口數據 發現,人們多半會選擇自己想養什麼品種的狗。很多犬種對某些類 型的人來講具有獨特魅力,有如潮流的象徵或某種生活態度那般。從這些數據的分析結果可以找到確鑿的證據,顯示飼養具攻擊性犬 種的主人犯下暴力罪行的機率較高。這一類主人偏好飼養比特犬的占比,基本上也解釋了這個犬種為何在傷人致死率上特別高。簡而言之,暴力傾向的主人偏愛比特犬,並且也將寵物狗訓練成有攻擊性。
二○一四年由美國獸醫學會提出的文獻探討指出,針對特定犬種所制訂的法規多半沒有效果,因為「對照研究並未認定此犬種 別特別危險」,而且「也未展現出針對特定犬種所制訂的禁養令,能降低社區發生狗咬人的機率或嚴重程度。」這些研究結果意味 的是,在正常環境中飼養的比特犬就跟其他犬種一樣可愛,而且不 太可能去攻擊人類。文獻並沒有忽視犬種天生有攻擊性傾向的可能性,但也不認為比特犬這「整個品種」的性情本來就不安全。
我在網路上看到的不同資訊,讓我對比特犬的觀點轉變了兩次。首先我因為一支情緒性影片而對比特犬的議題有了極端看法,後來被一位信任的朋友質疑,我不得不審視自己的情緒反應,並試 著為自己的意見建構合乎邏輯的基礎。這兩次經驗都迫使我重新對事實理出不同的輪廓。第一次找到的資訊為我的直覺背書,但並不完全正確。
直覺優先,解釋其次
這番過程,描繪的正是情緒會用奇特的方式改變和影響人們理性的決定,這也充分解釋了為什麼人處於強烈情緒狀態下時,用網 路來釐清事情是十分不利的做法。
我最後得出定見的路徑,可以溯及到心理學界一個很關鍵的爭論。一九七○年代末,認知心理學家羅伯特.扎榮茲(Robert Zajonc)提出有力證據,直接挑戰了當時對人做決定時如何處理情緒的既有認知。那個年代的盛行觀點是「認知」歷程(即「決定」) 先發生,繼之而來的是「感觸」(即人附加於此決定的情緒)。他在自己的純理論論文〈感覺與思考〉(Feeling and Thinking)中翻轉了 此觀點,不但主張認知與情感是分開的,且影響的方向是反過來,即人的感觸先到,然後再根據那些感觸做決定。
與我合作的紐約大學教授強納森.海德特(Jonathan Haidt)把這個理論多加了一個「評斷」步驟,將該理論擴充為他所謂的「社會直覺模型」(social intuitionist model)。這套模型充分解釋了為什麼 我的第一個反應是感覺,再來是評斷,然後是驗證自己的直覺。
輕而易舉就驗證了直覺,這讓我更難去質疑自己的情緒衝動。我更有可能試著去確認自己最初的情緒性想法,而且這種事只要上 Google搜尋一下就能馬上做到。
我對比特犬這個品種既厭惡又憤怒,也評斷這種狗就是危險犬種。我有了這樣的解釋,然後再用確認過的網路搜尋結果來支持這 個解釋。
但既然人如此擅長驗證自己的信念,那麼碰到被誤導的狀況時又該如何糾正?假如滿腦子都是衝動的評斷,又怎麼有辦法還是做 對很多事呢?這就是「他人」派上用場的地方。就像我信任的那位 朋友提到他不同的見解,反倒迫使我重新檢驗自己最初的評斷並加以修正。
他的意見就是一個觸發點,強迫我重新思考自己的想法,然後 感覺到新的情緒(對自己先前可能想錯了覺得有點丟臉),再回過 頭去重新檢視其他觀點(讀到不少比特犬飼主有暴力傾向),最後形成一個更準確的意見(比特犬是一種被誤解的犬種)。那次被質疑的結果,就是得到了修正過的洞見,並且在最終獲得更正確的知 識。
這便是人的意見經由社會互動而得以改善的過程。海德特的社會直覺模型解釋了人可以既憑直覺,證明自己大部分的直覺都是正確的,又能利用他人測試自己的想法。別人拿我們的情緒性想法來對照他們的情緒性想法,進而使我們的想法得到檢驗。我們透過別人檢驗自己的直覺,便得以更準確的釐清世事。
那麼,直覺若是碰上社群媒體機器時會發生什麼狀況呢?
如果我沒有把比特犬的事情說給朋友聽,而是將短影片分享到我的動態消息,再補充一點道德譴責的言論,就會透過按讚、留言 和分享的形式,集結成不斷增強又吵雜的回饋來驗證我的直覺。有可能其中一些留言是反對者所寫,他們希望我可以重新審視自己的觀點。不過更有可能的情況是,我對比特犬品種的道德譴責貼文收穫了廣大的人氣。我的情緒因為那支觸發力驚人的影片得到許多的讚和分享而得到驗證。假使貼文沒有收到任何互動,它大概會就此 石沉網路大海。
社群媒體的動態會在網路上替人們的直覺營造出持續增強的回饋迴路。用戶的情緒有很大的機會,在網路上以明確指標的形式得 到肯定。獲得讚、分享和追蹤,都會讓用戶覺得自己的事後推理合理正當,即使實際上錯得離譜。
上圖為數位空間動態的簡化模型,有利於瞭解社群媒體為什麼會逐漸成為劍拔弩張的直覺衝突戰場。
究竟什麼是情緒?
如果人的情緒那麼容易出錯,為什麼一開始會有這些情緒?認清人的道德情緒運作方式以及身分認同如何體現,是參透網路如何 扭曲人們彼此觀點的關鍵。
從演化角度來看,情緒非常古老,它們演化了數百萬年,而且包含了在語言尚未出現時,人類祖先用來溝通的表情特徵。我們之 所以知道情緒很古老,是因為觀察相近的其他物種祖先就可以看到 類似的情緒溝通模式。
一九六○年代開始進行的一項大型研究,有助於對情緒這門領域有更清晰的瞭解。雖然科學界對情緒處理機制尚未有統一的說法,但有明確的證據指出,情緒可作為一種捷思法,或稱為捷徑,能在人類祖先面對經常重複碰到的情況或經驗模式時,優化他們的 行為與認知反應。
情緒這種工具有利於人將自己導向特定行動,並幫忙把注意力集中在需要解決問題類型上。情緒堪稱是生物性的操作指南,人 可以據此快速行動,提高生存機會,譬如看到蛇的時候就跳開(恐懼)、不可以喝有臭味的水(厭惡)、別讓別人欺騙或剝削你(怒氣),或者是改變你的社會地位(哀傷)。
但所謂的「道德情緒」又不同了。道德情緒跟人類的基本情緒有很多共同特徵,感覺也十分類似,不過道德情緒因為涉及到「他人」,因此有其獨特性。道德情緒是指有助於群體——而非個人——蓬勃發展和繁榮興旺的情緒,也是以整個大我族群的連結和凝 聚為導向的情緒。有鑑於此,道德情緒是非常特殊的情緒種類,是 一種對別人「應該」或「不應該」做什麼事所產生的感覺。
海德特認為道德情緒可分成四類。
「譴責他人」類:蔑視、憤怒與厭惡,再加上諸如憤慨、憤怒、義氣和憎惡等的各種變化體。
「自我意識」類:羞愧、尷尬和罪惡感。
「感受他人苦難」類:愛心與同理心。
第四個則是「讚許他人」類:感激、敬畏和上進。
沉迷於社交的動物有這些情緒也是合情合理。這些情緒起初都是個人在受到壓力的情況下形塑而成,在部落文化時代來臨前就 已經生根。憤怒、厭惡、羞愧、同情⋯⋯這些原先都是為了幫助人在一個緊密又充滿社會評價、具備共同道德世界觀的群體裡生存下 去。人類和祖先在相互合作的社會群體中生活了七百多萬年,這段期間人類發展出一套深層連動的行為與常規,讓人與人之間合作得更順利,活得更長久。這些以群體為導向的情緒本能,很有可能是為了賦予人類適應的優勢,而特別揀選出來的。
這些根深蒂固的行為及其產生的感覺每一個人都很熟悉,它們 以強烈的道德情緒出現在我們身上,實在難以忽略。
道德基礎
試圖搞懂自己人生中的道德情緒,會有點像對自己動腦部手術一樣。過程的一開始就會觸發你對於是非的感知,因此在踏入之前 請將以下幾個重點銘記在心:
首先,世界各地的社會文化對於是非的概念並沒有普世通行的認知。(這是一個備受挑戰的思維,不過稍後會對此有更多探討。) 其次,每一個人都有獨特的道德感,其中有一部分是由自身的基 因、文化和獨特的經驗塑造而成。
海德特與同僚開發了「道德基礎理論」模型,用來解釋人類道德推理的源頭與變換,透過這個觀察性工具可以分析人類各種判斷對 與錯的多元經驗。
道德情緒是人類這種社會性動物十分深層的信號。由於這種情緒界定了群體常規的界限,所以沒辦法隨心所欲加以更新。假如輕而易舉就能修改它們,恐怕會導致個人被放逐到群體之外,在遠古 時代這往往是攸關生死的事情。揭開道德情緒的面貌之所以如此困 難,原因就在於此。即便證據就擺在眼前,人通常只會找理由不去相信證據,所以往往還是不會改變自己的道德直覺。
海德特用「味蕾」來打比方,說明人有各種不同的道德基礎。譬如我對甜食或鹹食的偏好就有點不同。你大概討厭辣的食物,我卻很喜歡。道德情緒也是類似的原理。也許你天生就對朋友背叛這種 事特別反感,或生來看到有人不尊重長輩就會感到厭惡。我的天性 是見到有人遭受不公平待遇就會火大,你的同事碰到同樣狀況說不 定沒有這麼強烈的情緒。這便是各位的道德「味覺」。
海德特和同僚傑西.葛拉罕(Jesse Graham)設計了一份問卷調查,評估人們形形色色的道德基礎。各位可以造訪https://yourmorals. org,即可取得該問卷,查看自己的道德基礎為何。
道德基礎可分為六大類。關愛、公平、忠誠、權威、聖潔和自由。保守派與自由派人士的道德基礎往往南轅北轍,大不相同。
有時候和朋友聚餐時,為了向他們說明這個理論,我通常會請大家閉上眼睛,然後把改編自海德特的著作《好人總是自以為是》(The Righteous Mind)裡的一組問題拿來問他們。我告訴朋友們如 果覺得哪個問題是「道德錯誤」就舉起手。
「有個女人正在打掃浴室,但抹布沒了,她找到一面國旗——正是你國家的國旗——便決定用這面國旗來打掃馬桶裡裡外外需要 清潔的地方。你覺得這件事是錯的嗎?」
先停一下,讓大家表示意見。有人舉手了,也有人沒舉手。
「兄妹倆一起去露營,他們年紀相仿,都是年輕又單身的成人,彼此間也十分親近。露營期間的某一天晚上,他們決定做愛。這完全是雙方合意,也用了兩種不同的避孕方式。隔天醒來後,他 們說好這是兩人之間共有的特別經驗,但不會把這件事告訴別人, 以後也不會再發生。兩人回去各過各的生活,把這件事當作他們之間的小祕密。你覺得這件事是錯的嗎?」
對不少朋友來說,他們覺得這些問題「明顯」是錯的,但令人意外的是,大家的反應竟如此不同,即便是同坐在餐桌旁的家人、愛人或親近的朋友之間。很多人認為自己的道德觀一定和同伴差不多,所以當他們發現彼此的認知不同時都感到十分驚訝。
我請大家閉上眼睛的理由,正是因為同處一個空間時會有「強大的社會勢力」,這股力量會透過群體參照讓人們對道德議題形成一致的口徑。假如睜開眼睛回答問題的話,多數人一定會快速瞄一下同伴,試圖找出周遭空間裡的「對錯」方向來代替自己的道德直 覺。這種情況彷彿大家在餐桌旁共同創造一個道德母體,尋求與他人同步。我們在社群媒體上碰到道德議題時,也會去看看朋友和追 蹤者的意向來判斷對錯,那股發揮作用的正是這裡所說的社會勢 力。
除此之外,我詢問朋友們給出答案的緣由,也就是為什麼會覺得這個問題是錯的時,他們竭盡所能地說明,但往往很難解釋清楚。我請他們特別留意,在面對答案之對錯所產生的強烈深層感受時,那股想要「附加理由」的奇怪拉力與衝動,雖然理由的背後根 本沒有道理可言。一般來講,他們最後大概都會給我一個可以歸納為「因為那感覺就是不對」的說法。海德特把這種覺得不對又說不出 理由的現象稱為「道德錯愕」(moral dumbfounding)。
情緒不需要「理由」才能出現;情緒獨立於理由之外。
現在先回頭看看前文提過的「系統一」和「系統二」快思慢想處理模型。人用系統一快速做出道德評斷,事後再用系統二為這個評斷找出理由。海德特用另一個巧妙的比喻,來形容這兩種系統力 量發揮作用的過程:快速反應的系統一是「大象」,理性的系統二則是「騎象人」。大象就是人類所擁有的情緒本能,它是一頭龐大 威猛的野獸,任憑感覺拉著牠往某個方向跑。騎象人就是人的理性 邏輯腦,即系統二程序,它試圖為情緒性的系統一大象之所以朝某 個方向移動「找出正當理由」。騎象人看上去是個聰明的律師,他 坐在這頭情緒野獸的背上,向周遭世界大喊我們有這種信念的「理由」。不過大象通常都能受控,會用情緒慣性拉著我們做出評斷,過後我們的邏輯大腦會設法解釋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