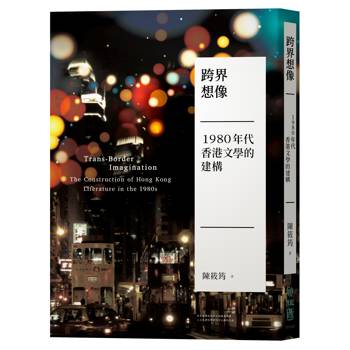第一章 一九八○年代香港文學場域
一、香港文學浮現的脈絡
自一九七九年以來,由於政治、經濟等等因素,香港變得十分矚目,香港人忽然回頭來看看這個身處而又一直沒加注意的環境,中國人也驚覺要好好研究一下這個行將我屬的城市,於是,「香港熱」遂成為潮流。文學,自然也同時排在受注視的行列中。(盧瑋鑾,一九八八:九)
「香港文學」過去大概有點像南中國的一個無名島,島民或漁或耕,帝力於我何有哉?自從上世紀八○年代開始,「香港文學」才漸漸成為文化人和學界的議題。這當然和中英就香港前途問題進行談判,以至一九八四年簽訂中英聯合聲明,讓香港進入一個漫長的過渡期有關。(陳國球,二○一四:一七)
一九八○年代隨著香港主權即將移交中國,有關於香港的歷史、身分與認同等議題也藉由許多文化形式而被再現。當時在文學的表現上,有西西、也斯、劉以鬯、辛其氏、吳煦斌和顏純鈎等人書寫偏向純文學的小說;鍾曉陽、李碧華、亦舒、陳韻文、林燕妮和倪匡等人遊走在雅俗之間或偏向通俗大眾的創作;在報章上考慮到市場需求,以實用和消費性質為主的專欄雜文;在一九八○年代創辦或由一九七○年代延續至一九八○年代繼續發行的文藝刊物,包括《大拇指》、《八方》、《香港文學》、《素葉文學》、《九分壹》、《破土》、《新穗》、《詩風》、《文藝季刊》、《香港文藝》和《博益月刊》等等。
在文化藝術的呈現上,有偏向流行文化或電影藝術評論的《號外》、《年青人周報》、《突破》、《文化焦點》、《助聽器》、《外邊》和《電影雙週刊》等(陳智德,二○○九:二一三─二一四);由徐克、方育平、許鞍華、譚家明和嚴浩等人引領的香港電影新浪潮,也有《傾城之戀》或《胭脂扣》這些因回歸而引起充滿懷舊風潮的電影;羅卡、陸離、石琪、吳昊和李焯桃等人對香港文化或電影的評論;邵國華、林木、莊百川、章嘉雯(呂大樂)、游真和張月愛等人在《信報》開闢的《文化失言》專欄,探討文化潮流,評析香港文化現象的文化雜文(黃子程,二○○○:二八八─二九○);以及達明一派在流行樂曲中對香港政治處境的嘲諷。這些文學與文化現象各自座落在香港純文學、通俗文學或大眾流行文化所構成的光譜上,他們皆在不同的層面上折射出對於香港一九八○年代這個時代的回應。
值得留意的是,在香港主流文化占據著重要位置的,並非是嚴肅或高雅的文學與藝術傳統,而是通俗、商業和大眾的文化潮流(洛楓,一九九五:一二六),但在當時香港文學場域所進行的香港文學建構過程中,則主要是先以嚴肅文學作為討論範疇。這或許與香港在一九七○年代末期到一九八○年代中期,香港學院文化的轉變,包括大批在英美受訓練的文學教授來港任教、比較文學的興起、現代文學的學科位置確立、香港文學進入學界視野,以及學術和文學活動的相互刺激有關(陳國球,二○○○:一六)。
以「香港文學」作為一個具體的言說概念,為它定義、描畫,以至追源溯流,還是晚近發生的事。從流傳下來的資料中,我們偶然也會見到「香港文學」一詞在一九六○年代以前的文學活動中出現。例如在香港大學中文系任教的羅香林,就曾在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以「近百年來之香港文學」為題進行演講,但這主要是以香港所見的中國文學活動為談論對象(陳國球,二○一六:三七─三八)。到了一九七○年代,隨著人們對於香港歸屬感的發展,才開啟了較多偏向以香港作為主體,進而討論香港文學的活動。一九七二年《中國學生周報》曾發起過香港文學問題討論,當時一位名叫偉男的讀者來信表示對於香港文藝的消逝感到憂心,之後報刊陸續刊載了多篇回應偉男的提問。在當時的討論裡,問題主要圍繞在文學的普遍性問題、文學貴族化、文學的功效,以及世代的銜接等層面。一九七○年代中後期,香港開始試圖對文學進行較有系統的整理,一九七五年香港大學文社主辦「香港四十年文學史學習班」,並編印了《香港四十年文學史學習班資料彙編》,可惜這一份資料裡頭有許多不完整且錯誤的資訊,但我們可以看到,香港文學開始慢慢的受到關注。比方自一九七九年到整個一九八○年代以來,香港大學文社和香港中文大學文社,陸續主辦有關香港文學的講座、報紙與文藝雜誌召開的筆談會或座談會、香港市政局圖書館主辦的中文文學週以香港文學為主題,或是為了向大眾推廣香港文學的認知,由中西區文化藝術協會和香港大學校外課程部合辦的香港文學講座等等。
一九七九年三月香港總督麥理浩至北京與鄧小平商討香港在一九九七年,即新界租借條約期限屆滿後的前途問題。麥理浩是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以來首位到訪的港督,此行在政治意義上可謂是揭開中英談判香港問題的序幕,同年九月收錄於《八方》的「香港有沒有文學」的筆談會,即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所產生。香港九七回歸中國雖然要到一九八四年中英聯合聲明條約的簽訂之後才真正確立,但一九七九年麥理浩的訪北京行程實際上已讓回歸的問題浮現,這場筆談會雖然是在討論香港有沒有文學,但這個問題的拋出卻也透露了,香港在意識到自身即將可能走向另一個重大轉變的歷史階段下,對於自身定位的重新找尋與確認。一九七九年香港前途問題的浮現刺激香港文學對於自身文學與定位的反省,到了一九八○年代,一九八二年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與鄧小平的會談,以及一九八四年的回歸確立,皆再度加速香港論述的形成與建構。香港文學的被提出,這個意義並非只是在討論「何謂香港文學」?或是尋找「香港文學的存在與否」,從一九七九年以來到整個一九八○年代,香港文學的被提出與被討論,更為重要的意義還在於,將香港文學以一種更具學術視角的方式建構,摸索香港在此時期的特殊位置。
在這樣的脈絡底下我們可以看到,一九七九年刊載於《八方》創刊號中「香港有沒有文學」的筆談會,以及一九八五年《香港文學》創刊號中對於香港文學未來走向的討論文章,其思索的主軸是沿著思考香港文學的定位與方向逐步開展,並且強調香港文學在未來面臨轉型的過程中,如何更有系統地建立香港文學。一九七九年《八方》的筆談會已觸及了「香港文學的被提出」、「香港文學的建構」以及「香港文學的跨界想像」等重要議題。《八方》和《香港文學》在創刊號的討論開啟了香港文學的建構,在後續的發行中積極加強香港的文學評論、整理香港文學史料,以及開闢香港作家專輯等方式,在各個層面持續建構香港文學。
一、香港文學浮現的脈絡
自一九七九年以來,由於政治、經濟等等因素,香港變得十分矚目,香港人忽然回頭來看看這個身處而又一直沒加注意的環境,中國人也驚覺要好好研究一下這個行將我屬的城市,於是,「香港熱」遂成為潮流。文學,自然也同時排在受注視的行列中。(盧瑋鑾,一九八八:九)
「香港文學」過去大概有點像南中國的一個無名島,島民或漁或耕,帝力於我何有哉?自從上世紀八○年代開始,「香港文學」才漸漸成為文化人和學界的議題。這當然和中英就香港前途問題進行談判,以至一九八四年簽訂中英聯合聲明,讓香港進入一個漫長的過渡期有關。(陳國球,二○一四:一七)
一九八○年代隨著香港主權即將移交中國,有關於香港的歷史、身分與認同等議題也藉由許多文化形式而被再現。當時在文學的表現上,有西西、也斯、劉以鬯、辛其氏、吳煦斌和顏純鈎等人書寫偏向純文學的小說;鍾曉陽、李碧華、亦舒、陳韻文、林燕妮和倪匡等人遊走在雅俗之間或偏向通俗大眾的創作;在報章上考慮到市場需求,以實用和消費性質為主的專欄雜文;在一九八○年代創辦或由一九七○年代延續至一九八○年代繼續發行的文藝刊物,包括《大拇指》、《八方》、《香港文學》、《素葉文學》、《九分壹》、《破土》、《新穗》、《詩風》、《文藝季刊》、《香港文藝》和《博益月刊》等等。
在文化藝術的呈現上,有偏向流行文化或電影藝術評論的《號外》、《年青人周報》、《突破》、《文化焦點》、《助聽器》、《外邊》和《電影雙週刊》等(陳智德,二○○九:二一三─二一四);由徐克、方育平、許鞍華、譚家明和嚴浩等人引領的香港電影新浪潮,也有《傾城之戀》或《胭脂扣》這些因回歸而引起充滿懷舊風潮的電影;羅卡、陸離、石琪、吳昊和李焯桃等人對香港文化或電影的評論;邵國華、林木、莊百川、章嘉雯(呂大樂)、游真和張月愛等人在《信報》開闢的《文化失言》專欄,探討文化潮流,評析香港文化現象的文化雜文(黃子程,二○○○:二八八─二九○);以及達明一派在流行樂曲中對香港政治處境的嘲諷。這些文學與文化現象各自座落在香港純文學、通俗文學或大眾流行文化所構成的光譜上,他們皆在不同的層面上折射出對於香港一九八○年代這個時代的回應。
值得留意的是,在香港主流文化占據著重要位置的,並非是嚴肅或高雅的文學與藝術傳統,而是通俗、商業和大眾的文化潮流(洛楓,一九九五:一二六),但在當時香港文學場域所進行的香港文學建構過程中,則主要是先以嚴肅文學作為討論範疇。這或許與香港在一九七○年代末期到一九八○年代中期,香港學院文化的轉變,包括大批在英美受訓練的文學教授來港任教、比較文學的興起、現代文學的學科位置確立、香港文學進入學界視野,以及學術和文學活動的相互刺激有關(陳國球,二○○○:一六)。
以「香港文學」作為一個具體的言說概念,為它定義、描畫,以至追源溯流,還是晚近發生的事。從流傳下來的資料中,我們偶然也會見到「香港文學」一詞在一九六○年代以前的文學活動中出現。例如在香港大學中文系任教的羅香林,就曾在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以「近百年來之香港文學」為題進行演講,但這主要是以香港所見的中國文學活動為談論對象(陳國球,二○一六:三七─三八)。到了一九七○年代,隨著人們對於香港歸屬感的發展,才開啟了較多偏向以香港作為主體,進而討論香港文學的活動。一九七二年《中國學生周報》曾發起過香港文學問題討論,當時一位名叫偉男的讀者來信表示對於香港文藝的消逝感到憂心,之後報刊陸續刊載了多篇回應偉男的提問。在當時的討論裡,問題主要圍繞在文學的普遍性問題、文學貴族化、文學的功效,以及世代的銜接等層面。一九七○年代中後期,香港開始試圖對文學進行較有系統的整理,一九七五年香港大學文社主辦「香港四十年文學史學習班」,並編印了《香港四十年文學史學習班資料彙編》,可惜這一份資料裡頭有許多不完整且錯誤的資訊,但我們可以看到,香港文學開始慢慢的受到關注。比方自一九七九年到整個一九八○年代以來,香港大學文社和香港中文大學文社,陸續主辦有關香港文學的講座、報紙與文藝雜誌召開的筆談會或座談會、香港市政局圖書館主辦的中文文學週以香港文學為主題,或是為了向大眾推廣香港文學的認知,由中西區文化藝術協會和香港大學校外課程部合辦的香港文學講座等等。
一九七九年三月香港總督麥理浩至北京與鄧小平商討香港在一九九七年,即新界租借條約期限屆滿後的前途問題。麥理浩是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以來首位到訪的港督,此行在政治意義上可謂是揭開中英談判香港問題的序幕,同年九月收錄於《八方》的「香港有沒有文學」的筆談會,即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所產生。香港九七回歸中國雖然要到一九八四年中英聯合聲明條約的簽訂之後才真正確立,但一九七九年麥理浩的訪北京行程實際上已讓回歸的問題浮現,這場筆談會雖然是在討論香港有沒有文學,但這個問題的拋出卻也透露了,香港在意識到自身即將可能走向另一個重大轉變的歷史階段下,對於自身定位的重新找尋與確認。一九七九年香港前途問題的浮現刺激香港文學對於自身文學與定位的反省,到了一九八○年代,一九八二年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與鄧小平的會談,以及一九八四年的回歸確立,皆再度加速香港論述的形成與建構。香港文學的被提出,這個意義並非只是在討論「何謂香港文學」?或是尋找「香港文學的存在與否」,從一九七九年以來到整個一九八○年代,香港文學的被提出與被討論,更為重要的意義還在於,將香港文學以一種更具學術視角的方式建構,摸索香港在此時期的特殊位置。
在這樣的脈絡底下我們可以看到,一九七九年刊載於《八方》創刊號中「香港有沒有文學」的筆談會,以及一九八五年《香港文學》創刊號中對於香港文學未來走向的討論文章,其思索的主軸是沿著思考香港文學的定位與方向逐步開展,並且強調香港文學在未來面臨轉型的過程中,如何更有系統地建立香港文學。一九七九年《八方》的筆談會已觸及了「香港文學的被提出」、「香港文學的建構」以及「香港文學的跨界想像」等重要議題。《八方》和《香港文學》在創刊號的討論開啟了香港文學的建構,在後續的發行中積極加強香港的文學評論、整理香港文學史料,以及開闢香港作家專輯等方式,在各個層面持續建構香港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