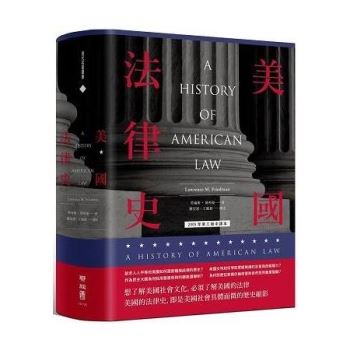前言
現代的通訊與技術已經使世界的距離變小,也使世界文化中的許多差異變小。然而,人們仍然說不同的語言,穿不同的衣服,信仰不同的宗教,持有不同的價值觀。人們也遵守不同的法律。到底各國法律彼此有多麼不同,難以一言敝之,但顯然法律體系間的差異不如語言的差異來得大。我們現在居住的新世界是城市的、工業的與科技的,它產生了某一類型的社會。而這樣的社會依賴、並且歡迎某類型的法律。舉例而言,所得稅制度是已開發國家的共有特色。但某個稅法究竟採取哪種確切形式,則取決於該國的一般法律文化。美國人自然是習慣於美國法。法律是美國文化內在的一部分。要美國人去適應非常異國的法律與程序,可能就像要他們去適應吃烤螞蟻或穿羅馬長袍一樣難。法官與陪審團、遺囑與契據、熟悉的刑事審判戲碼、民選的制定法律的議會、結婚許可、養狗、獵鹿,這些都是美國特有的共同經驗的一部份。沒有其他的法律文化與它完全相同。我們亦可假設,沒有其他文化能如此恰當地適合美國的體系。
很多人認為歷史與傳統對美國法的影響非常大。這個看法是有某些依據。某些部分的美國法,例如陪審團制度、抵押制度、信託法、土地法的某些部分,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但是,其他許多部分的法律卻是相當新的。我們每天使用、真正對我們每天產生影響的活的法或運作中的法(living law),像是稅法、交通法規、社會福利法等,整體說來,是相當晚近的法律。有些律師建議他的客戶如何因應華府當日做成的最新判決;有些律師則告訴他的客戶,他的訴訟因為亨利八世時代傳下來的法律的限制、或因為某些古代法官的判決的限制,所以無法提起,即使這些古代法官的名字、使用的語言與習慣對今日的律師及客戶皆已成為深不可測的謎。但是前者的情形比後者的情形更可能發生。法律的某些部份就像是地質結構中一層層的地層。新的地層壓覆在舊的上面,造成了取代和改變,但不必然會完全抹除從前發生過的一切。大致上,法律是逐漸演化的,它的改變是一點一點地。根本結構性的革命相當罕見,而且彼此間隔甚久。至少,這是英美法的經驗。法律系統中的大部分是新的,但是某些舊的法律仍然被保留下來而存在於新的法律之中。
但哪些舊法獲得保留是高度選擇性的。社會的改變或許快速、或許緩慢,但都是無情的。不論演化或革命都是不帶情感的。舊的法律與舊的制度,只有當它們還能符合某些目的的時候,才有辦法存留下來。它們必須有存留的價值。信託、抵押、陪審團都是可以追溯到數百年前的法律制度。但它們至今仍有年輕的活力。它們是從中世紀流傳下來,但現在它們因應的是21世紀的需求。它們之所以能夠存留,是因為它們在活力旺盛、咄咄逼人的現代社會中找到了立足點—這個社會會毫不猶豫地以新瓶裝舊酒,或以舊瓶裝新酒,或乾脆把瓶子和酒一起拋棄。不論如何,本書的理論是:法律隨時代而演進,而且永遠是新的。有時這個理論無法切合事實。但是,如果我們去問「為什麼這個法律可以存留下來」,而不是認為「法律只是一堆事件和木乃伊般的過去的陳列館」的話,我們可以從法律史上得到更多的啟示。
在某個重要的意義上,法律總是最新的(up-to-date)。法律系統總是在「運作」。每個社會都在自我管理並解決紛爭。每個社會都有一個運作中的法律系統。例如,假設法院是迂腐而無效率的,那表示有其他機關行使了原本是法院應該行使的職權。這個系統就像一個盲目的、沒感覺的機器,它依據具有控制地位的人的指示行事。中國、美國、沙烏地阿拉伯、法國、北韓和南韓的法律,都反映那些能夠決定社會的基調的人的目標與政策。通常,當我們說法律是「陳腐」的,意思是說這個社會的權力體系在道德上已經走調。但是只要權力體系被改變,法律便會跟著改變。本書的基本假設是:僅管有過去的歷史與習性的強烈影響,美國法在任何時候的最有力的成份是「當下」—當下的情緒、現實的經濟利益、具體的政治團體。在一本關於歷史的著作的一開頭就貶低歷史的重要性,或許是有些奇怪的,但這並不是真的有什麼矛盾。只有當我們假設法律不可或缺的部分是新的、改變中的,是形式追隨功能、而非功能追隨形式的,法律史才有意義。法律史不是(而且也不應該是)對於古代化石的搜尋,而是對於隨著時間而開展的社會發展的研究。
美國的法律與社會都有長久而複雜的歷史。與某些國家相比,美國是一個新的國家,但波士頓與紐約都已有三百年之久,而美國憲法應該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仍在運作中的組織法。簡言之,已經有夠長的時間使美國法成為真正是美國的,屬於美國經驗的產物。
但美國法並不是與世隔絕的。它現在和過去都與其他的法律文化有密切關係。美國法最重要的淵源是很容易辨認出來的。美國法的基礎,就像美國使用的語言一樣,是來自英國。在歐洲人到來之前,這個國家屬於美洲原住民。後來,歐洲人大量移入。最初他們在沿海定居。西班牙人在佛羅里達殖民,法國人建造了紐奧良。瑞典人曾經短暫地移民至德拉瓦,但後來被荷蘭人趕走。接著英國人又戰勝了荷蘭人。哈德遜與德拉瓦殖民地被加入一連串的小型殖民地的行列,所有的這些殖民地都說英語且位於大西洋沿岸。它們的人口不斷增加。更多的英國人來到。作為英國人或美國人的英語系人口後來將原住民趕走,佔(xiii)去了他們的土地,也佔去了法國人和西班牙人的土地、佔去了墨西哥的一大塊。他們建立了一個延亙兩大洋之間的帝國。之後,他們還向外推展到夏威夷、波多黎各以及菲律賓。
每個文化族群依據他們自己的法律規範生活。持平而論,很多他們自己原始的法律如今已經沒有留下任何痕跡,但其他一些法律則至今仍然保有其生命力。有些美國原住民的社群今日仍然有著他們自己的法院系統,而且他們原有傳統中的某些片段至今仍然繼續被適用。某些學者曾經宣稱:他們發現有少許荷蘭法律的傳統至今還留存著,例如地方檢察官辦公室的制度可能源自於荷蘭。法國法律至今在路易斯安那多多少少有其持續的影響力,在當地它(經翻譯後)繼續留存。西班牙法律的影響雖然沒有較深,但其散布的範圍較廣。沒有任何一州的法律我們會稱它為西班牙法的,但是西班牙法或墨西哥法的某些部份,例如夫妻共同財產制(community-property system),至今仍然存在於加州及西部的其他幾個地區。美國法當中其他的部份,如果不是純粹美國本土發展出來的,就是英國的,它們來自於英國、或是建立於英國法的基礎上。
但是英國法是相當複雜而令人困惑的。要確切說出究竟是哪些英國法成為美國法的淵源,是相當不容易的。畢竟,直到美國獨立為止的所謂「殖民地法」是一個抽象概念,並沒有一個在所有殖民地共通的一部殖民地法,就好像在今日的美國五十州沒有真正的一部「美國法」一樣。有多少個殖民地,當時就有多少個殖民地系統。最初的組合是由十三個州組成的,但「十三」這個數字只是在某個任意擷取的時點做出的計算。某些殖民地,像是普利茅斯(Plymouth)與紐海文(New Haven),後來被較大的殖民地所併吞。而紐澤西是兩個殖民地區域合併之後的產物,每個區域原本都有它自己的法律體系。
而且,每個殖民地都建立於不同的時期。麻薩諸塞的建立與喬治亞的建立,彼此至少相隔一世紀之久。在這段時間中,英國法並不是靜止的,所以每個殖民地都是在法律發展過程中的不同的時點開始自己的發展。在整個殖民時期,母國的法律在理論上具有較高地位。但殖民地當時的情況並不是個單純的從屬關係,並不像是區與市、或郡與州的那種從屬關係。即使就理論上而言,亦不確定英國國會的哪部法律或法院的哪個判決拘束殖民地。各個殖民地在它們希望、或是被迫的範圍內,儘可能借用了英國法。它們對英國法的喜好取決於當時的需要、取決於它們對海外發生的事務的理解或無知、或者只是一種單純的固執的行為。想要找出殖民地法與英國法一致的程度幾乎是不可能的。每個殖民地都有各自不同的法律文化。新英格蘭地區偏離英國法的程度更甚於南方的殖民地。大西洋兩岸之間雖然總是有著強而有力的連結,但卻從來都不是彼此一致的。它們中間隔了一個巨大的海洋,事實上距離相當遙遠。對於母國而言,它很難控制那任性的孩子。殖民地與母國之間,不僅在政治與稅的問題上爭執,也在法律上爭執。即使在獨立革命之後,兩地之間在法律上的連結也沒有被完全切斷。在1776年之後,一個複雜的法律上連結關係仍然存在。英國法仍然在有需要的時候,於需要的範圍內被引進。即使到了19世紀末,這樣的連結的細流仍然持續。
正如我們說過的,英國法是相當複雜而困難的。但什麼是英國法?在美國獨立革命之前的二十年左右,威廉‧布萊克史東爵士(Sir William Blackstone)把他所認為的普通法(common law)的精髓形諸文字。他分為四個部份寫成的「英國法評論」(Commentaries on the Law of England)是一本非常厚,但令人有辦法掌握的書。這本風格沈悶但典雅的書,當時在英國與美國兩地都成為暢銷書。大致而言,布萊克史東成功地把雜亂無章的英國法做了些有秩序的整理。但他所做的描繪仍然是片面的、有瑕疵的,就像一本忽略了所有的俚語、方言、口語用法與技術詞彙的字典。但在1750年代以前,殖民地裡卻連如此不完美的法律指南都沒有。他們欠缺能夠快速通曉英國法的工具,可是這樣的工具卻是極為必需的。英國普通法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法律體系之一,但是它難以熟練與理解的程度,令人難以置信。
過去與現在的英國法都跟歐洲其他大部分地區的法律體系不同。自從中世紀以來,一種被修正的、現代化的形式的羅馬法橫掃歐洲大陸的多數地區,而英國法當初拒絕「接受」大陸法。現代大陸法的最高表現形式便是法典。在法國與德國,所謂「法律」尤其指的是成文法。但另一方面,如同布萊克史東所用的詞彙,普通法是不成文法(unwritten law)。此處的「不成文」不能從它的字面意義來理解;英國法與美國法其實都有太多的書寫文件。布萊克史東所謂的「不成文」是指:法律的最終最高的來源不是立法、不是國會制定的法律,而是「具有普遍適用性的習慣」(general custom),而其反映於普通法法官的判決之中。法官是「法律的受託人—他們是活生生的神諭傳達者,他們必須決定所有有疑問的案件,而且他們必須遵守其『依據國家的法律做判決』的誓言」(布萊克史東評論第一卷第六十九節)。普通法是法官造的法(judge-made law),於真正的案件中被塑造、精練、檢驗與改變,而且以案件報導的形式代代相傳。理論上而言,法官是基於既存的法律原則做成判決;這些原則最終是在反映英國人民現有的價值、態度、與倫理概念。但實際上,法官倚賴他們自己過去的判決,並基於時代與訴訟型態改變的壓力去修正這些過去的判決。
普通法的基本原則就是遵循判決先例(precedent)。判決先例通常被視為普通法最重要的基本概念之一。不過,它其實並不像有些門外漢(與法律人)所以為的,有那麼強的約束力。只要他們認為某個判決有嚴重錯誤,美國的法官向來擁有推翻既往案例的權力。這項權力過去並不常被行使。不過,它始終在那裡,與另一項更為重要的「區辨先例」的權力同時存在~去設法使一個令人為難的先例可以被跳過、或設法將其意涵做些扭轉。無論如何,普通法在過去跟現在,都是一個由法官主宰的制度。不管是遵循先例還是區辨先例,他們創造並闡釋法律原則。過去所做的判決乃是建構法律的重要基石。長久以來,法官們始終以相當懷疑的態度看待成文法。成文法被視為是法律領域內不受歡迎的入侵者,而且也被當作如此來加以對待。在大陸法系中,(理論上)所有的法都被包含在成文法裡。但在普通法系統下,許多基本的法律規則,只有在法官的判決意見書裡才找得到。
國會在一個月的密集工作下可以做到的事,法院卻需要花上經年累月的時間來做,而且從來不會是有系統地做,因為普通法只處理現實發生的紛爭、真實的案件。普通法不能去處理假設性或未來性的案件。如果沒有人提出案件,它就根本不會進入法院。說「所有重要的問題最終都會形成紛爭」並沒有太大意義,因為「紛爭」並不等於「訴訟」,在普通法中僅有「訴訟」(而且事實上只有上訴的訴訟)才會創造出新的法律。對於法官來說,要去制定量化的規則,或是制定需要大量公共支援(藉由稅收)來執行的規則,或是制定必須由新的一批公務人員才有辦法執行的法律,對他們來說都是相當困難的事情。法官被認為應該依據法律的原則來做判決。他們判決具體個案,但是只有有限的權力能夠做管制。他們沒有辦法決定行車速限應該幾公里、哪些食品添加物是致癌物質、或是哪些動物應列入瀕臨絕種的名單。一個英國(或美國)的法院不可能有辦法「演化」出一部社會福利法。因此,普通法的進化不但有時緩慢,而且常常沒有能力發展出某些重要的法律變遷。
較古老的英國法,其改變的迂迴與緩慢都是相當常見的。普通法的文化常常不願意直接去正式、明白地廢止一些過時的傳統與制度,英國法比較喜歡只是跳過或忽略它們而已。決鬥斷訟(trial by battle)這個制度,是中世紀羅曼史和古裝電影的最愛之一,但是它在英國一直存續到1819年才被廢止。數百年以來它卻一直都在石棺中沈睡著;但法院在1818年不經意犯下的一個錯誤,提醒了法律專業界:決鬥仍然是一個法律上允許的斷訟方式。感到難堪的國會,很快地就在1819年埋葬了這個古時遺骸。有時候法律的演進是因為法律的虛擬(legal fictions)這個捷徑的使用而開展。「逐出租地之訴」(ejectment)的興起就是一個著名的例子。現在假設有兩個人,一個叫布萊克、另一個叫布朗,他們正因為對某個土地的所有權而相執不下。布朗目前占有土地,但布萊克主張對之有權利。兩個人都認為自己才是真正的所有權人。中世紀的普通法有一種審理的方式可以用來解決這種紛爭,但是,這種方式是相當折磨人且笨拙的。因此「逐出租地之訴」就被發展出來繞過它。在「逐出租地之訴」中,訴狀裡會說一個有點古怪的故事:有個人叫張三,他似乎曾經向布萊克承租了這塊土地。而另一個人叫李四,他則是向布朗承租了這塊土地。而據說呢,李四把張三給「逐出」這塊土地了。事實上,張三、李四和這兩份租賃契約,都是法律虛構故事中臆造的事物。在本案中,只有布萊克和布朗是真實的人物。這種做作可笑的儀式(包含法官在內每個人都知道它是虛構的)可以把土地所有權歸屬的爭點帶到法院面前來。現在這案件是個有關「租約」(雖然是個虛擬的租約)的案件了,因此古老的那種土地訴訟的作法就可以被迴避掉,因為其不適用於有租約的情形,藉此虛擬租約和虛擬逐出租地的故事,訴訟可以採取更為有效率的方式來進行。後來隨著時間的經過,「逐出租地之訴」這種作法本身也被認為是太過複雜的一種麻煩。但一直到19世紀中葉以後,這種作法才在英國進行改革。
這個「逐出租地之訴」的古怪歷史,就高度形式技術性與虛擬化的作法而言,並不是一個特例。是什麼樣的不太法律的腦袋,會去創造出將公司當做是「人」的社會制度?會去將奴隸歸類為不動產?會去允許原告陳述「巴黎市乃位於英國」或「倫敦位於公海上」,卻不允許被告反駁這種荒謬的主張?以上這些作法中,公司當做「人」的擬制迄今依然存在(且有用),但其他的作法則在滿足其當初的目的之後消逝了。
由於有許多太過高度形式技術性的部份存在,英美法因此成為一個無論是律師、還是一般民眾都感到困難的系統。但是普通法之所以相當紛亂、過度形式化、而且充斥著虛擬,這並不是因為它缺乏變化,反而正是因為它持續處於改變中所導致。部份問題出在傳統理論認為普通法是個緊緊包裹好的系統。傳統理論認為:普通法並不是一般語意所謂的「人造」的產物;法官們揭示(或發現)既存的法律,而沒有創造法律,也沒有在發現法律時將之予以竄改。現在我們將法律當成是人造的、且基本上是種工具或手段,這種觀念對於古典的普通法來說,是相當陌生的。因此,在過去,法律上的改變必須被隱藏或偽裝起來。(法官所做的)明顯而公然的改革是不可能的。而且,對於既有運作中的法律原則,不管它們看起來多麼古怪,都還是必須讓它們繼續運作,以維護某些既有的經濟或社會利益。處於一個有著許多粗暴又愛爭執、經常彼此戰爭的權力控制者的社會中,法院只能緩慢而微妙地設法影響權力關係,否則,原本脆弱的權力平衡狀態就會被打亂。
而且,愚蠢的傳統只要是無害的,就還是可以被繼續忍受。決鬥斷訟的廢止可以說明這一點。如果決鬥斷訟不是實質上早已名存實亡,它是不可能存留到19世紀的。造成改變的有力引擎雖然可以、而且也確實存在於法律體系中,但它們常常可能是在法院外的。法律的某些主要變化,是藉由制度上的安全閥的開啟與關閉而發生的。某些事項從一個法律機構移到另一個法律機構處理。法院獲得一些工作,然後失去了一些,後來又再取得一些新的工作。國會的角色變得益發重要,國王的權力則逐漸消長。在這些變化的過程中,某些古老的、專門的、性質上屬於比較邊緣性的事務,繼續保持由法院主管。由於他們相當多彩且歷史久遠,所以這些像化石的古老事務吸引到過多的注意。它們給人一種相當古老而陳腐的印象,但這個印象大部分是錯誤的。
此外,有許多法律並沒有直接傳達到公眾。法律人位於一般民眾與立法者之間,法律人的工作是要容忍並熟練法律中的機靈巧詐。畢竟,法律技術的困難是法律人存在的理由:他們的權力、收入、壟斷地位來自於此,他們對於法院的工作、文件起草和提供客戶法律諮詢的掌控,也是來自於此。英國的律師業從一開始就是形塑英國法的一股重要的力量。律師業的演進是一個長久且複雜的過程,不過到了1600年時,英國的律師顯然已經成為一種專業,是一群接受法律的訓練與教育的人。然而,他們並不是在牛津、劍橋這些大學中接受訓練的,而是從倫敦的律師會(Inns of Court)訓練出來的。律師會跟大學並沒有關係,它們跟羅馬法或一般的歐陸法律文化也沒有關連性。律師會中的年輕人,他們學的就是英國法、英國的訴訟程序與英國的法律經驗。法律訓練基本上是實務性的,而不是學理性的。這種特殊的英國法律教育方式,使普通法在歐陸的法律都沈迷於「接受」復興的羅馬法的同時,得以抗拒羅馬法的誘惑。在英國,法官也是從律師裡選取的。律師與法官共同建立同一個法律社群,他們有著許多共通的背景與經驗,迄今亦然。他們形成了一個有凝聚力的團體或行會。
現代的通訊與技術已經使世界的距離變小,也使世界文化中的許多差異變小。然而,人們仍然說不同的語言,穿不同的衣服,信仰不同的宗教,持有不同的價值觀。人們也遵守不同的法律。到底各國法律彼此有多麼不同,難以一言敝之,但顯然法律體系間的差異不如語言的差異來得大。我們現在居住的新世界是城市的、工業的與科技的,它產生了某一類型的社會。而這樣的社會依賴、並且歡迎某類型的法律。舉例而言,所得稅制度是已開發國家的共有特色。但某個稅法究竟採取哪種確切形式,則取決於該國的一般法律文化。美國人自然是習慣於美國法。法律是美國文化內在的一部分。要美國人去適應非常異國的法律與程序,可能就像要他們去適應吃烤螞蟻或穿羅馬長袍一樣難。法官與陪審團、遺囑與契據、熟悉的刑事審判戲碼、民選的制定法律的議會、結婚許可、養狗、獵鹿,這些都是美國特有的共同經驗的一部份。沒有其他的法律文化與它完全相同。我們亦可假設,沒有其他文化能如此恰當地適合美國的體系。
很多人認為歷史與傳統對美國法的影響非常大。這個看法是有某些依據。某些部分的美國法,例如陪審團制度、抵押制度、信託法、土地法的某些部分,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但是,其他許多部分的法律卻是相當新的。我們每天使用、真正對我們每天產生影響的活的法或運作中的法(living law),像是稅法、交通法規、社會福利法等,整體說來,是相當晚近的法律。有些律師建議他的客戶如何因應華府當日做成的最新判決;有些律師則告訴他的客戶,他的訴訟因為亨利八世時代傳下來的法律的限制、或因為某些古代法官的判決的限制,所以無法提起,即使這些古代法官的名字、使用的語言與習慣對今日的律師及客戶皆已成為深不可測的謎。但是前者的情形比後者的情形更可能發生。法律的某些部份就像是地質結構中一層層的地層。新的地層壓覆在舊的上面,造成了取代和改變,但不必然會完全抹除從前發生過的一切。大致上,法律是逐漸演化的,它的改變是一點一點地。根本結構性的革命相當罕見,而且彼此間隔甚久。至少,這是英美法的經驗。法律系統中的大部分是新的,但是某些舊的法律仍然被保留下來而存在於新的法律之中。
但哪些舊法獲得保留是高度選擇性的。社會的改變或許快速、或許緩慢,但都是無情的。不論演化或革命都是不帶情感的。舊的法律與舊的制度,只有當它們還能符合某些目的的時候,才有辦法存留下來。它們必須有存留的價值。信託、抵押、陪審團都是可以追溯到數百年前的法律制度。但它們至今仍有年輕的活力。它們是從中世紀流傳下來,但現在它們因應的是21世紀的需求。它們之所以能夠存留,是因為它們在活力旺盛、咄咄逼人的現代社會中找到了立足點—這個社會會毫不猶豫地以新瓶裝舊酒,或以舊瓶裝新酒,或乾脆把瓶子和酒一起拋棄。不論如何,本書的理論是:法律隨時代而演進,而且永遠是新的。有時這個理論無法切合事實。但是,如果我們去問「為什麼這個法律可以存留下來」,而不是認為「法律只是一堆事件和木乃伊般的過去的陳列館」的話,我們可以從法律史上得到更多的啟示。
在某個重要的意義上,法律總是最新的(up-to-date)。法律系統總是在「運作」。每個社會都在自我管理並解決紛爭。每個社會都有一個運作中的法律系統。例如,假設法院是迂腐而無效率的,那表示有其他機關行使了原本是法院應該行使的職權。這個系統就像一個盲目的、沒感覺的機器,它依據具有控制地位的人的指示行事。中國、美國、沙烏地阿拉伯、法國、北韓和南韓的法律,都反映那些能夠決定社會的基調的人的目標與政策。通常,當我們說法律是「陳腐」的,意思是說這個社會的權力體系在道德上已經走調。但是只要權力體系被改變,法律便會跟著改變。本書的基本假設是:僅管有過去的歷史與習性的強烈影響,美國法在任何時候的最有力的成份是「當下」—當下的情緒、現實的經濟利益、具體的政治團體。在一本關於歷史的著作的一開頭就貶低歷史的重要性,或許是有些奇怪的,但這並不是真的有什麼矛盾。只有當我們假設法律不可或缺的部分是新的、改變中的,是形式追隨功能、而非功能追隨形式的,法律史才有意義。法律史不是(而且也不應該是)對於古代化石的搜尋,而是對於隨著時間而開展的社會發展的研究。
美國的法律與社會都有長久而複雜的歷史。與某些國家相比,美國是一個新的國家,但波士頓與紐約都已有三百年之久,而美國憲法應該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仍在運作中的組織法。簡言之,已經有夠長的時間使美國法成為真正是美國的,屬於美國經驗的產物。
但美國法並不是與世隔絕的。它現在和過去都與其他的法律文化有密切關係。美國法最重要的淵源是很容易辨認出來的。美國法的基礎,就像美國使用的語言一樣,是來自英國。在歐洲人到來之前,這個國家屬於美洲原住民。後來,歐洲人大量移入。最初他們在沿海定居。西班牙人在佛羅里達殖民,法國人建造了紐奧良。瑞典人曾經短暫地移民至德拉瓦,但後來被荷蘭人趕走。接著英國人又戰勝了荷蘭人。哈德遜與德拉瓦殖民地被加入一連串的小型殖民地的行列,所有的這些殖民地都說英語且位於大西洋沿岸。它們的人口不斷增加。更多的英國人來到。作為英國人或美國人的英語系人口後來將原住民趕走,佔(xiii)去了他們的土地,也佔去了法國人和西班牙人的土地、佔去了墨西哥的一大塊。他們建立了一個延亙兩大洋之間的帝國。之後,他們還向外推展到夏威夷、波多黎各以及菲律賓。
每個文化族群依據他們自己的法律規範生活。持平而論,很多他們自己原始的法律如今已經沒有留下任何痕跡,但其他一些法律則至今仍然保有其生命力。有些美國原住民的社群今日仍然有著他們自己的法院系統,而且他們原有傳統中的某些片段至今仍然繼續被適用。某些學者曾經宣稱:他們發現有少許荷蘭法律的傳統至今還留存著,例如地方檢察官辦公室的制度可能源自於荷蘭。法國法律至今在路易斯安那多多少少有其持續的影響力,在當地它(經翻譯後)繼續留存。西班牙法律的影響雖然沒有較深,但其散布的範圍較廣。沒有任何一州的法律我們會稱它為西班牙法的,但是西班牙法或墨西哥法的某些部份,例如夫妻共同財產制(community-property system),至今仍然存在於加州及西部的其他幾個地區。美國法當中其他的部份,如果不是純粹美國本土發展出來的,就是英國的,它們來自於英國、或是建立於英國法的基礎上。
但是英國法是相當複雜而令人困惑的。要確切說出究竟是哪些英國法成為美國法的淵源,是相當不容易的。畢竟,直到美國獨立為止的所謂「殖民地法」是一個抽象概念,並沒有一個在所有殖民地共通的一部殖民地法,就好像在今日的美國五十州沒有真正的一部「美國法」一樣。有多少個殖民地,當時就有多少個殖民地系統。最初的組合是由十三個州組成的,但「十三」這個數字只是在某個任意擷取的時點做出的計算。某些殖民地,像是普利茅斯(Plymouth)與紐海文(New Haven),後來被較大的殖民地所併吞。而紐澤西是兩個殖民地區域合併之後的產物,每個區域原本都有它自己的法律體系。
而且,每個殖民地都建立於不同的時期。麻薩諸塞的建立與喬治亞的建立,彼此至少相隔一世紀之久。在這段時間中,英國法並不是靜止的,所以每個殖民地都是在法律發展過程中的不同的時點開始自己的發展。在整個殖民時期,母國的法律在理論上具有較高地位。但殖民地當時的情況並不是個單純的從屬關係,並不像是區與市、或郡與州的那種從屬關係。即使就理論上而言,亦不確定英國國會的哪部法律或法院的哪個判決拘束殖民地。各個殖民地在它們希望、或是被迫的範圍內,儘可能借用了英國法。它們對英國法的喜好取決於當時的需要、取決於它們對海外發生的事務的理解或無知、或者只是一種單純的固執的行為。想要找出殖民地法與英國法一致的程度幾乎是不可能的。每個殖民地都有各自不同的法律文化。新英格蘭地區偏離英國法的程度更甚於南方的殖民地。大西洋兩岸之間雖然總是有著強而有力的連結,但卻從來都不是彼此一致的。它們中間隔了一個巨大的海洋,事實上距離相當遙遠。對於母國而言,它很難控制那任性的孩子。殖民地與母國之間,不僅在政治與稅的問題上爭執,也在法律上爭執。即使在獨立革命之後,兩地之間在法律上的連結也沒有被完全切斷。在1776年之後,一個複雜的法律上連結關係仍然存在。英國法仍然在有需要的時候,於需要的範圍內被引進。即使到了19世紀末,這樣的連結的細流仍然持續。
正如我們說過的,英國法是相當複雜而困難的。但什麼是英國法?在美國獨立革命之前的二十年左右,威廉‧布萊克史東爵士(Sir William Blackstone)把他所認為的普通法(common law)的精髓形諸文字。他分為四個部份寫成的「英國法評論」(Commentaries on the Law of England)是一本非常厚,但令人有辦法掌握的書。這本風格沈悶但典雅的書,當時在英國與美國兩地都成為暢銷書。大致而言,布萊克史東成功地把雜亂無章的英國法做了些有秩序的整理。但他所做的描繪仍然是片面的、有瑕疵的,就像一本忽略了所有的俚語、方言、口語用法與技術詞彙的字典。但在1750年代以前,殖民地裡卻連如此不完美的法律指南都沒有。他們欠缺能夠快速通曉英國法的工具,可是這樣的工具卻是極為必需的。英國普通法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法律體系之一,但是它難以熟練與理解的程度,令人難以置信。
過去與現在的英國法都跟歐洲其他大部分地區的法律體系不同。自從中世紀以來,一種被修正的、現代化的形式的羅馬法橫掃歐洲大陸的多數地區,而英國法當初拒絕「接受」大陸法。現代大陸法的最高表現形式便是法典。在法國與德國,所謂「法律」尤其指的是成文法。但另一方面,如同布萊克史東所用的詞彙,普通法是不成文法(unwritten law)。此處的「不成文」不能從它的字面意義來理解;英國法與美國法其實都有太多的書寫文件。布萊克史東所謂的「不成文」是指:法律的最終最高的來源不是立法、不是國會制定的法律,而是「具有普遍適用性的習慣」(general custom),而其反映於普通法法官的判決之中。法官是「法律的受託人—他們是活生生的神諭傳達者,他們必須決定所有有疑問的案件,而且他們必須遵守其『依據國家的法律做判決』的誓言」(布萊克史東評論第一卷第六十九節)。普通法是法官造的法(judge-made law),於真正的案件中被塑造、精練、檢驗與改變,而且以案件報導的形式代代相傳。理論上而言,法官是基於既存的法律原則做成判決;這些原則最終是在反映英國人民現有的價值、態度、與倫理概念。但實際上,法官倚賴他們自己過去的判決,並基於時代與訴訟型態改變的壓力去修正這些過去的判決。
普通法的基本原則就是遵循判決先例(precedent)。判決先例通常被視為普通法最重要的基本概念之一。不過,它其實並不像有些門外漢(與法律人)所以為的,有那麼強的約束力。只要他們認為某個判決有嚴重錯誤,美國的法官向來擁有推翻既往案例的權力。這項權力過去並不常被行使。不過,它始終在那裡,與另一項更為重要的「區辨先例」的權力同時存在~去設法使一個令人為難的先例可以被跳過、或設法將其意涵做些扭轉。無論如何,普通法在過去跟現在,都是一個由法官主宰的制度。不管是遵循先例還是區辨先例,他們創造並闡釋法律原則。過去所做的判決乃是建構法律的重要基石。長久以來,法官們始終以相當懷疑的態度看待成文法。成文法被視為是法律領域內不受歡迎的入侵者,而且也被當作如此來加以對待。在大陸法系中,(理論上)所有的法都被包含在成文法裡。但在普通法系統下,許多基本的法律規則,只有在法官的判決意見書裡才找得到。
國會在一個月的密集工作下可以做到的事,法院卻需要花上經年累月的時間來做,而且從來不會是有系統地做,因為普通法只處理現實發生的紛爭、真實的案件。普通法不能去處理假設性或未來性的案件。如果沒有人提出案件,它就根本不會進入法院。說「所有重要的問題最終都會形成紛爭」並沒有太大意義,因為「紛爭」並不等於「訴訟」,在普通法中僅有「訴訟」(而且事實上只有上訴的訴訟)才會創造出新的法律。對於法官來說,要去制定量化的規則,或是制定需要大量公共支援(藉由稅收)來執行的規則,或是制定必須由新的一批公務人員才有辦法執行的法律,對他們來說都是相當困難的事情。法官被認為應該依據法律的原則來做判決。他們判決具體個案,但是只有有限的權力能夠做管制。他們沒有辦法決定行車速限應該幾公里、哪些食品添加物是致癌物質、或是哪些動物應列入瀕臨絕種的名單。一個英國(或美國)的法院不可能有辦法「演化」出一部社會福利法。因此,普通法的進化不但有時緩慢,而且常常沒有能力發展出某些重要的法律變遷。
較古老的英國法,其改變的迂迴與緩慢都是相當常見的。普通法的文化常常不願意直接去正式、明白地廢止一些過時的傳統與制度,英國法比較喜歡只是跳過或忽略它們而已。決鬥斷訟(trial by battle)這個制度,是中世紀羅曼史和古裝電影的最愛之一,但是它在英國一直存續到1819年才被廢止。數百年以來它卻一直都在石棺中沈睡著;但法院在1818年不經意犯下的一個錯誤,提醒了法律專業界:決鬥仍然是一個法律上允許的斷訟方式。感到難堪的國會,很快地就在1819年埋葬了這個古時遺骸。有時候法律的演進是因為法律的虛擬(legal fictions)這個捷徑的使用而開展。「逐出租地之訴」(ejectment)的興起就是一個著名的例子。現在假設有兩個人,一個叫布萊克、另一個叫布朗,他們正因為對某個土地的所有權而相執不下。布朗目前占有土地,但布萊克主張對之有權利。兩個人都認為自己才是真正的所有權人。中世紀的普通法有一種審理的方式可以用來解決這種紛爭,但是,這種方式是相當折磨人且笨拙的。因此「逐出租地之訴」就被發展出來繞過它。在「逐出租地之訴」中,訴狀裡會說一個有點古怪的故事:有個人叫張三,他似乎曾經向布萊克承租了這塊土地。而另一個人叫李四,他則是向布朗承租了這塊土地。而據說呢,李四把張三給「逐出」這塊土地了。事實上,張三、李四和這兩份租賃契約,都是法律虛構故事中臆造的事物。在本案中,只有布萊克和布朗是真實的人物。這種做作可笑的儀式(包含法官在內每個人都知道它是虛構的)可以把土地所有權歸屬的爭點帶到法院面前來。現在這案件是個有關「租約」(雖然是個虛擬的租約)的案件了,因此古老的那種土地訴訟的作法就可以被迴避掉,因為其不適用於有租約的情形,藉此虛擬租約和虛擬逐出租地的故事,訴訟可以採取更為有效率的方式來進行。後來隨著時間的經過,「逐出租地之訴」這種作法本身也被認為是太過複雜的一種麻煩。但一直到19世紀中葉以後,這種作法才在英國進行改革。
這個「逐出租地之訴」的古怪歷史,就高度形式技術性與虛擬化的作法而言,並不是一個特例。是什麼樣的不太法律的腦袋,會去創造出將公司當做是「人」的社會制度?會去將奴隸歸類為不動產?會去允許原告陳述「巴黎市乃位於英國」或「倫敦位於公海上」,卻不允許被告反駁這種荒謬的主張?以上這些作法中,公司當做「人」的擬制迄今依然存在(且有用),但其他的作法則在滿足其當初的目的之後消逝了。
由於有許多太過高度形式技術性的部份存在,英美法因此成為一個無論是律師、還是一般民眾都感到困難的系統。但是普通法之所以相當紛亂、過度形式化、而且充斥著虛擬,這並不是因為它缺乏變化,反而正是因為它持續處於改變中所導致。部份問題出在傳統理論認為普通法是個緊緊包裹好的系統。傳統理論認為:普通法並不是一般語意所謂的「人造」的產物;法官們揭示(或發現)既存的法律,而沒有創造法律,也沒有在發現法律時將之予以竄改。現在我們將法律當成是人造的、且基本上是種工具或手段,這種觀念對於古典的普通法來說,是相當陌生的。因此,在過去,法律上的改變必須被隱藏或偽裝起來。(法官所做的)明顯而公然的改革是不可能的。而且,對於既有運作中的法律原則,不管它們看起來多麼古怪,都還是必須讓它們繼續運作,以維護某些既有的經濟或社會利益。處於一個有著許多粗暴又愛爭執、經常彼此戰爭的權力控制者的社會中,法院只能緩慢而微妙地設法影響權力關係,否則,原本脆弱的權力平衡狀態就會被打亂。
而且,愚蠢的傳統只要是無害的,就還是可以被繼續忍受。決鬥斷訟的廢止可以說明這一點。如果決鬥斷訟不是實質上早已名存實亡,它是不可能存留到19世紀的。造成改變的有力引擎雖然可以、而且也確實存在於法律體系中,但它們常常可能是在法院外的。法律的某些主要變化,是藉由制度上的安全閥的開啟與關閉而發生的。某些事項從一個法律機構移到另一個法律機構處理。法院獲得一些工作,然後失去了一些,後來又再取得一些新的工作。國會的角色變得益發重要,國王的權力則逐漸消長。在這些變化的過程中,某些古老的、專門的、性質上屬於比較邊緣性的事務,繼續保持由法院主管。由於他們相當多彩且歷史久遠,所以這些像化石的古老事務吸引到過多的注意。它們給人一種相當古老而陳腐的印象,但這個印象大部分是錯誤的。
此外,有許多法律並沒有直接傳達到公眾。法律人位於一般民眾與立法者之間,法律人的工作是要容忍並熟練法律中的機靈巧詐。畢竟,法律技術的困難是法律人存在的理由:他們的權力、收入、壟斷地位來自於此,他們對於法院的工作、文件起草和提供客戶法律諮詢的掌控,也是來自於此。英國的律師業從一開始就是形塑英國法的一股重要的力量。律師業的演進是一個長久且複雜的過程,不過到了1600年時,英國的律師顯然已經成為一種專業,是一群接受法律的訓練與教育的人。然而,他們並不是在牛津、劍橋這些大學中接受訓練的,而是從倫敦的律師會(Inns of Court)訓練出來的。律師會跟大學並沒有關係,它們跟羅馬法或一般的歐陸法律文化也沒有關連性。律師會中的年輕人,他們學的就是英國法、英國的訴訟程序與英國的法律經驗。法律訓練基本上是實務性的,而不是學理性的。這種特殊的英國法律教育方式,使普通法在歐陸的法律都沈迷於「接受」復興的羅馬法的同時,得以抗拒羅馬法的誘惑。在英國,法官也是從律師裡選取的。律師與法官共同建立同一個法律社群,他們有著許多共通的背景與經驗,迄今亦然。他們形成了一個有凝聚力的團體或行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