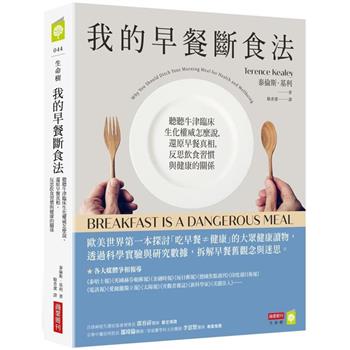前言
人類每天早上都會收到一份上帝的恩賜:斷食。我們花一整個晚上消化前一天吃進肚子裡的食物,到了早上,代謝作用已從進食模式轉換為斷食模式。
斷食是一種非常健康的狀態。斷食期間,胰島素濃度降低,血糖、三酸甘油酯與膽固醇的濃度也會下滑。最大的好處是,斷食可以減重。多數人早上醒來的時候會做什麼事?我們破壞美好的斷食恩賜。我們真的「停止」(break)「斷食」(fast,譯注:英語的早餐是breakfast),把食物吃進肚子裡,增加罹患疾病的風險:第二型糖尿病、肥胖症、心臟病、中風、高血壓、癡呆症,以及肝癌、乳癌、胰臟癌與子宮癌。
早餐至少會造成四種健康危害。第一,吃早餐會增加(而不是減少)我們攝取的總熱量。第二,吃早餐會引發強烈的飢餓感。第三,吃早餐會加劇代謝症候群(metabolic syndrome),這是現代人的頭號殺手。第四,早餐通常富含碳水化合物,而這對健康的危害更是雪上加霜。
早餐是一天之中最重要的一餐,因為你不該吃它。
早餐常見迷思:早餐有助減肥?
專家們前仆後繼地說早餐能製造飽足感。據稱早餐可把胃填滿、增加血糖值,接下來幾餐就會吃得比較少。真的是這樣嗎?
做出上述結論且經過同儕審查的研究論文當然不少,德州的心理學家約翰.德.卡斯楚博士(John de Castro)就曾寫過多篇相關論文。他曾於2004年寫道:「我們發現如果受試者的早餐份量高於一日進食總量的平均值,接下來一整天的進食量會顯著減少。」這句話顯然是在說早餐吃得越多,接下來一天內就會吃得越少。德.卡斯楚把這個現象歸因於飽足感。這是他建立的模型:
吃早餐 飽足感 午餐減量 體重減輕
這個模型影響強大,且乍看之下似乎非常合理。但是大多數的科學家認為恰恰相反。紐約康乃爾大學的大衛.勒維斯基(David Levitsky)與卡莉.派卡諾斯基(Carly Pacanowski)最近做了一項研究,發現就算讓受試者吃輕食早餐(約350大卡),他們午餐攝取的熱量也完全沒有改變。換句話說,早餐攝取的350大卡並未減少午餐攝取的熱量,因此吃早餐會讓一日攝取的熱量多出350大卡。此外,如果讓受試者吃624大卡左右的正式早餐,午餐攝取的熱量只會減少約144大卡,也就是一日熱量淨增480大卡。難怪勒維斯基與派卡諾斯基得出以下結論:「或許不吃早餐才是有效降低熱量攝取的方法。」他們建立的模型是:
不吃早餐 吃得更少 降低熱量攝取
或是反過來
吃早餐 吃得更多 增加熱量攝取
勒維斯基與派卡諾斯基的研究之所以意義重大,是因為他們證明了「這些數據與已發表的文獻一致」。也就是說,德.卡斯楚的飽足感假設錯誤,吃早餐會增加熱量的攝取。
從1952到2003年最具權威性的47份早餐研究結果看來,不吃早餐的兒童與成年人約占20%,而且「吃早餐的人每天攝取的總熱量通常更高」。因此與這則迷思正好相反,吃早餐其實會增加熱量。那麼,我們如何解釋德.卡斯楚的發現:「如果受試者的早餐份量高於一日進食總量的平均值,接下來一整天的進食量會顯著減少」?
德國慕尼黑工業大學(Technical University of Munich)減重診所的沃克.舒斯茲艾拉醫師(Volker Schusdziarra)與他的同事都不認同德.卡斯楚的早餐研究,他們說那是一種統計上的錯覺。舒斯茲艾拉用一組受試者做實驗,發現如果讓受試者自行決定,他們早上的進食量通常相當穩定(意即出於習慣,早餐的份量相當固定),但是接下來的進食量就很不穩定了。有時午餐和晚餐會大吃大喝(沒有固定原因,例如參加阿姨的生日會,或是上餐廳吃大餐慶祝),有時反而會吃得比較少(沒有固定原因,例如身體不舒服,或是急著處理工作)。
由於早餐的進食量相當固定,因此碰到午餐和晚餐大吃大喝的時候,早餐的進食量比例上比較低;碰到午餐和晚餐吃得比較少的時候,早餐的進食量比例上比較高。所以表面上看起來是:
早餐吃得少 全日進食量高
以及
早餐吃得多 全日進食量低
其實這是因為午餐和晚餐變化較大造成的假象,真正的模型應該是:
午餐和晚餐吃得多 早餐相對上吃得少
以及
午餐和晚餐吃得少 早餐相對上吃得多
舒斯茲艾拉立場公正,他尊重德.卡斯楚的實驗數據,挑戰的是德.卡斯楚對數據的詮釋。這正是本書的重點,稍後將會討論:由數百位科學家累積起來的早餐研究數據幾乎都沒問題(早餐研究的數量多得驚人),只是有系統地遭到錯誤詮釋。
晝夜/一日節律
為什麼吃早餐很危險?人類的生活遵循晝夜(circadian)或一日(diurnal)節律(「circadian」源自拉丁文的「circa」,意指「大約於」;「diem」或「dies」,意指「日」;「diurnalis」意指「一日」)。因此,並非所有的用餐時間都該一視同仁。
驅動晝夜節律的是明/暗週期。連接到雙眼的特化腦細胞辨識日升與日落,這些細胞會刺激位在大腦底部的腺體,依照晝夜循環分泌荷爾蒙。這些荷爾蒙調節身體的晝夜節律:體內10%以上的活性基因是在白天震盪,控制震盪的荷爾蒙本身受到大腦的感光細胞控制。
「經典」的白晝荷爾蒙是褪黑激素(melatonin)。分泌褪黑激素的是松果腺(pineal gland),這個微小的腺體位在大腦底部。法國哲學家笛卡兒相信松果腺是靈魂的居所,但現在我們知道松果腺是明/暗管弦樂團的指揮家。松果腺分泌的褪黑激素主導身體大部分的晝夜節律。
白天時,血液裡的褪黑激素幾乎微不可查,但是在凌晨兩點到四點之間會達到高峰。從褪黑激素被用來治療時差,可看出它的重要性。當晝夜節律與新環境不同調,就會出現時差。全球最具權威性的臨床審查組織考科藍(Cochrane)表示:「(口服)褪黑激素預防與減輕時差效果絕佳……飛行跨越至少五個時區的成年人都建議服用。」
看起來褪黑激素跟糖尿病患的早餐沒有直接關係,但是另一種白晝荷爾蒙皮質醇卻跟早餐有關。皮質醇是「警覺心」荷爾蒙。清晨時,血液裡的皮質醇濃度上升(幫助我們甦醒),到了晚上就會下降(幫助我們入睡)。皮質醇可以強化已升高的意識。
如果皮質醇的功能只是強化警覺心,早餐可能會變得比較安全。但是皮質醇還有一個功能,那就是所謂的「戰鬥或逃跑反應」(fight or flight reaction):若我們即將迎戰或逃離劍齒虎或是敵對部落,我們必須保持警覺,因此在受到驚嚇的時候,我們會分泌皮質醇到血液裡。皮質醇不只讓我們保持警覺,也會增加血糖值。原因何在?
無論選擇戰鬥或逃跑,肌肉都必須快速燃燒葡萄糖,為了動用葡萄糖,皮質醇會阻礙胰島素的效果(胰島素可降低血糖值)。因此,皮質醇會引發胰島素阻抗,使血糖值升高,透過非胰島素的機制為肌肉供應緊急能源。但因為早晨也會分泌皮質醇,所以我們身上會出現皮質醇引發的胰島素阻抗。
史提芬.傑伊.古爾德(Stephen Jay Gould)跟理查.列溫廷(Richard Lewontin)在1979年發表了一篇知名的論文,標題很華麗,叫〈聖馬可教堂的層間牆與過度樂觀的思維:對於適應主義的評論〉(The spandrels of San Marco and the Panglossian paradigm: a critique of the adaptationist programme)。古爾德與列溫廷借用建築學的「層間牆」(spandrel)來描述一種生物學現象,這種現象並非演化而來,它是一種副產品。在建築學中,層間牆是用來填滿拱門與圓頂之間的空隙:以拱門支撐的圓頂建築,在拱門與圓頂之間本來就會出現空隙,這些空隙需要填補,層間牆的功能就是填補空隙。古爾德與列溫廷說,沒有一個建築師會把層間牆當成設計的主體,層間牆上的設計只是拱門/圓頂裝飾圖案的副產品。
同樣地,皮質醇在早晨使葡萄糖濃度上升,這個現象是否帶有演化目的尚未可知,它也可能只是皮質醇做為戰鬥或逃跑荷爾蒙的副產品。但無論如何,早晨確實會出現胰島素阻抗。黎明現象
早晨是分泌皮質醇的時間,難怪第二型糖尿病患會出現高血糖的「黎明現象」。健康的血糖值會在夜間下降,而且維持在低濃度的狀態;但第二型糖尿病患的血糖值會隨著時間接近黎明而慢慢上升。我在第1章提過克利斯提安森教授的實驗,健康的人早上醒來時,血糖值約為4到5 mmol/l;克利斯提安森教授的第二型糖尿病患早上醒來時,血糖值約為7.0 mmol/l。
值得注意的是,黎明現象的程度與第二型糖尿病的病況有關。英國佩納斯(Penarth)的糖尿病研究單位做了一項研究,發現輕微糖尿病患(糖化血色素低於7.3%或56 mmol/mol)早上醒來時,血糖值約為7.0 mmol/l(吃完早餐後約為11.5 mmol/l);嚴重糖尿病患(糖化血色素高於8%或64 mmol/mol)早上醒來時,血糖值約為10.0 mmol/l(吃完早餐後約為15.0 mmol/l)。
這些數據使我深感疑惑:吃早餐會使血糖值上升到危險的地步,為什麼這些病患還要吃早餐?我把這個問題留到後面再討論。在此我想討論的問題是:為什麼第二型糖尿病患的早晨血糖值跟病況有關?其中一個答案是,還有一種因素會使糖尿病患的早晨血糖升高,那就是「自由脂肪酸」。
自由脂肪酸
自由脂肪酸可以解決一種生理問題。如我們所知,葡萄糖是身體的主要燃料。葡萄糖來自碳水化合物,會在血液裡自由流動,很容易就能被身體組織氧化,成為主要燃料理所當然。只不過,葡萄糖的儲存是個問題。
葡萄糖無法以自由化學物質的形態儲存,因為它是水溶性的;而溶解後的葡萄糖只能為一顆細胞提供短短數秒能量。燃料必須是固態才能堆疊成高密度的能量庫。因此葡萄糖是以肝醣(glycogen)的形態儲存(字源跟葡萄糖一樣有「glykys」,意指「甜」;還有跟「創世紀Genesis」一樣的「genes」,意指「誕生」)。過去肝醣被稱為「動物澱粉」,因為與來自植物的澱粉一樣,都是由長鏈葡萄糖聚合組成。肝醣不是理想的燃料儲存方式,原因有二。
首先,肝醣是一種部分氧化的碳水化合物(化學式是CH2O,有「碳」跟「水合物」,因為C已跟H2O水合在一起),因此肝醣氧化時提供的能量,來自C氧化成CO2,也就是二氧化碳。H不會再氧化成H2O產生能量,因為它早已氧化。
第二個原因是肝醣有很高的親水性。肝醣本身的分子太大,無法溶於水,因此是以顆粒的形態儲存。但肝醣是由高溶水性的葡萄糖單元構成,所以肝醣顆粒飽含水分,水分子會自動進入肝醣分子裡。水不是燃料卻占據了很多空間,重量也很重,因此身體儲存的肝醣顆粒(主要位在肝臟)只能滿足幾小時的能量需求。
脂肪是比較理想的燃料儲存方式,原因同樣有兩個。第一,脂肪的化學式是CH2,脂肪氧化不只釋放碳的能量C CO2,也會釋放氫的能量H HO2。第二,脂肪既不溶於水也不親水,儲存時不會裝滿無用的水。基於這兩個原因,身體優先選擇儲存脂肪非常合理,也因此我們儲存的肝醣大約只有900大卡,但是以三酸甘油酯儲存的脂肪卻高達12萬大卡。
問題來了。人體儲存的脂肪不會以葡萄糖的形態釋放到血液裡,而是以脂肪的形態(當然),尤其是一種叫做自由脂肪酸的脂肪。人體組織必須有能力氧化兩種不同的能源:
․飯後氧化來自腸道的葡萄糖
․空腹時氧化來自備用脂肪的自由脂肪酸
這是一個分為四階段的過程:
․消化食物時,葡萄糖從腸道進入血液,胰島偵測到葡萄糖。胰島分泌胰島素,細胞吸收並氧化葡萄糖。
․食物完全消化之後(大約需要四到六小時),不會再有葡萄糖從腸道進入血液,血糖值下降。胰島偵測到血糖值下降,減少分泌胰島素。
․胰島素減少本身就是一種信號,提示肝臟分解肝醣,釋放葡萄糖到血液裡。
․肝醣的儲量只能維持數小時(只要斷食一夜,隔天早上肝醣就已耗盡)。因此禁食幾個小時把肝醣用完之後,血液裡的胰島素濃度變得更低,這是第二種信號:提示備用脂肪釋放自由脂肪酸進入血液。
照理說,斷食的身體會先消耗肝醣分解而成的葡萄糖,肝醣用盡之後,改成氧化自由脂肪酸。但身體沒有這麼理性,因為大腦不會立刻氧化自由脂肪酸。就算身體的其他地方都已開始氧化自由脂肪酸,大腦仍須氧化葡萄糖。為什麼?沒有人知道答案。這是一個謎。
但是這個謎帶來不好的後果。身體在斷食的時候,血液裡會有兩種燃料:葡萄糖(大腦用)與自由脂肪酸(其他組織用)。這個情況令人擔憂,因為「一般的」細胞也可能消耗只有大腦才能用的葡萄糖。為了確保其他細胞不會搶走珍貴的葡萄糖,有一種信號會告訴身體各部位組織,如果葡萄糖與自由脂肪酸同時出現,它們應該消耗自由脂肪酸,這樣就能把葡萄糖留給大腦。
是誰發出這種信號呢?答案是自由脂肪酸;這會引發大規模、近乎全面性的葡萄糖抗性(glucose resistance)與胰島素阻抗。也帶我們回到早餐與黎明現象。
自由脂肪酸會在斷食的時候釋放出來,所以血液裡的自由脂肪酸濃度自然會在早餐前達到高峰。而自由脂肪酸引發的胰島素阻抗,會在早餐時達到高峰。自由脂肪酸引發胰島素阻抗,強化了皮質醇使血糖上升的效應。黎明時分的高皮質醇加上高自由脂肪酸會使血糖值上升,連健康人士也不例外(不過健康人士會分泌更多胰島素來調節早晨的胰島素阻抗);至於在第二型糖尿病患身上,胰島素濃度雖然上升了,卻不足以降低血糖。
此外,第二型糖尿病患的胰島素阻抗會削弱脂肪細胞對胰島素的反應,於是脂肪細胞釋放出更多自由脂肪酸,導致胰島素阻抗升高,血糖值也隨之上升。這是一個惡性循環,罪魁禍首正是早餐。
有沒有解決辦法?方法很簡單。第二型糖尿病患不應該吃早餐。到了午餐時間,黎明時增加的皮質醇已經變少,雖然自由脂肪酸濃度依然很高,但是對胰島素來說現在只剩下一道障礙,而不是兩道。實驗已經證明:對第二型糖尿病患來說,跨越午餐的單一障礙要比早餐的雙重障礙容易得多。
人類每天早上都會收到一份上帝的恩賜:斷食。我們花一整個晚上消化前一天吃進肚子裡的食物,到了早上,代謝作用已從進食模式轉換為斷食模式。
斷食是一種非常健康的狀態。斷食期間,胰島素濃度降低,血糖、三酸甘油酯與膽固醇的濃度也會下滑。最大的好處是,斷食可以減重。多數人早上醒來的時候會做什麼事?我們破壞美好的斷食恩賜。我們真的「停止」(break)「斷食」(fast,譯注:英語的早餐是breakfast),把食物吃進肚子裡,增加罹患疾病的風險:第二型糖尿病、肥胖症、心臟病、中風、高血壓、癡呆症,以及肝癌、乳癌、胰臟癌與子宮癌。
早餐至少會造成四種健康危害。第一,吃早餐會增加(而不是減少)我們攝取的總熱量。第二,吃早餐會引發強烈的飢餓感。第三,吃早餐會加劇代謝症候群(metabolic syndrome),這是現代人的頭號殺手。第四,早餐通常富含碳水化合物,而這對健康的危害更是雪上加霜。
早餐是一天之中最重要的一餐,因為你不該吃它。
早餐常見迷思:早餐有助減肥?
專家們前仆後繼地說早餐能製造飽足感。據稱早餐可把胃填滿、增加血糖值,接下來幾餐就會吃得比較少。真的是這樣嗎?
做出上述結論且經過同儕審查的研究論文當然不少,德州的心理學家約翰.德.卡斯楚博士(John de Castro)就曾寫過多篇相關論文。他曾於2004年寫道:「我們發現如果受試者的早餐份量高於一日進食總量的平均值,接下來一整天的進食量會顯著減少。」這句話顯然是在說早餐吃得越多,接下來一天內就會吃得越少。德.卡斯楚把這個現象歸因於飽足感。這是他建立的模型:
吃早餐 飽足感 午餐減量 體重減輕
這個模型影響強大,且乍看之下似乎非常合理。但是大多數的科學家認為恰恰相反。紐約康乃爾大學的大衛.勒維斯基(David Levitsky)與卡莉.派卡諾斯基(Carly Pacanowski)最近做了一項研究,發現就算讓受試者吃輕食早餐(約350大卡),他們午餐攝取的熱量也完全沒有改變。換句話說,早餐攝取的350大卡並未減少午餐攝取的熱量,因此吃早餐會讓一日攝取的熱量多出350大卡。此外,如果讓受試者吃624大卡左右的正式早餐,午餐攝取的熱量只會減少約144大卡,也就是一日熱量淨增480大卡。難怪勒維斯基與派卡諾斯基得出以下結論:「或許不吃早餐才是有效降低熱量攝取的方法。」他們建立的模型是:
不吃早餐 吃得更少 降低熱量攝取
或是反過來
吃早餐 吃得更多 增加熱量攝取
勒維斯基與派卡諾斯基的研究之所以意義重大,是因為他們證明了「這些數據與已發表的文獻一致」。也就是說,德.卡斯楚的飽足感假設錯誤,吃早餐會增加熱量的攝取。
從1952到2003年最具權威性的47份早餐研究結果看來,不吃早餐的兒童與成年人約占20%,而且「吃早餐的人每天攝取的總熱量通常更高」。因此與這則迷思正好相反,吃早餐其實會增加熱量。那麼,我們如何解釋德.卡斯楚的發現:「如果受試者的早餐份量高於一日進食總量的平均值,接下來一整天的進食量會顯著減少」?
德國慕尼黑工業大學(Technical University of Munich)減重診所的沃克.舒斯茲艾拉醫師(Volker Schusdziarra)與他的同事都不認同德.卡斯楚的早餐研究,他們說那是一種統計上的錯覺。舒斯茲艾拉用一組受試者做實驗,發現如果讓受試者自行決定,他們早上的進食量通常相當穩定(意即出於習慣,早餐的份量相當固定),但是接下來的進食量就很不穩定了。有時午餐和晚餐會大吃大喝(沒有固定原因,例如參加阿姨的生日會,或是上餐廳吃大餐慶祝),有時反而會吃得比較少(沒有固定原因,例如身體不舒服,或是急著處理工作)。
由於早餐的進食量相當固定,因此碰到午餐和晚餐大吃大喝的時候,早餐的進食量比例上比較低;碰到午餐和晚餐吃得比較少的時候,早餐的進食量比例上比較高。所以表面上看起來是:
早餐吃得少 全日進食量高
以及
早餐吃得多 全日進食量低
其實這是因為午餐和晚餐變化較大造成的假象,真正的模型應該是:
午餐和晚餐吃得多 早餐相對上吃得少
以及
午餐和晚餐吃得少 早餐相對上吃得多
舒斯茲艾拉立場公正,他尊重德.卡斯楚的實驗數據,挑戰的是德.卡斯楚對數據的詮釋。這正是本書的重點,稍後將會討論:由數百位科學家累積起來的早餐研究數據幾乎都沒問題(早餐研究的數量多得驚人),只是有系統地遭到錯誤詮釋。
晝夜/一日節律
為什麼吃早餐很危險?人類的生活遵循晝夜(circadian)或一日(diurnal)節律(「circadian」源自拉丁文的「circa」,意指「大約於」;「diem」或「dies」,意指「日」;「diurnalis」意指「一日」)。因此,並非所有的用餐時間都該一視同仁。
驅動晝夜節律的是明/暗週期。連接到雙眼的特化腦細胞辨識日升與日落,這些細胞會刺激位在大腦底部的腺體,依照晝夜循環分泌荷爾蒙。這些荷爾蒙調節身體的晝夜節律:體內10%以上的活性基因是在白天震盪,控制震盪的荷爾蒙本身受到大腦的感光細胞控制。
「經典」的白晝荷爾蒙是褪黑激素(melatonin)。分泌褪黑激素的是松果腺(pineal gland),這個微小的腺體位在大腦底部。法國哲學家笛卡兒相信松果腺是靈魂的居所,但現在我們知道松果腺是明/暗管弦樂團的指揮家。松果腺分泌的褪黑激素主導身體大部分的晝夜節律。
白天時,血液裡的褪黑激素幾乎微不可查,但是在凌晨兩點到四點之間會達到高峰。從褪黑激素被用來治療時差,可看出它的重要性。當晝夜節律與新環境不同調,就會出現時差。全球最具權威性的臨床審查組織考科藍(Cochrane)表示:「(口服)褪黑激素預防與減輕時差效果絕佳……飛行跨越至少五個時區的成年人都建議服用。」
看起來褪黑激素跟糖尿病患的早餐沒有直接關係,但是另一種白晝荷爾蒙皮質醇卻跟早餐有關。皮質醇是「警覺心」荷爾蒙。清晨時,血液裡的皮質醇濃度上升(幫助我們甦醒),到了晚上就會下降(幫助我們入睡)。皮質醇可以強化已升高的意識。
如果皮質醇的功能只是強化警覺心,早餐可能會變得比較安全。但是皮質醇還有一個功能,那就是所謂的「戰鬥或逃跑反應」(fight or flight reaction):若我們即將迎戰或逃離劍齒虎或是敵對部落,我們必須保持警覺,因此在受到驚嚇的時候,我們會分泌皮質醇到血液裡。皮質醇不只讓我們保持警覺,也會增加血糖值。原因何在?
無論選擇戰鬥或逃跑,肌肉都必須快速燃燒葡萄糖,為了動用葡萄糖,皮質醇會阻礙胰島素的效果(胰島素可降低血糖值)。因此,皮質醇會引發胰島素阻抗,使血糖值升高,透過非胰島素的機制為肌肉供應緊急能源。但因為早晨也會分泌皮質醇,所以我們身上會出現皮質醇引發的胰島素阻抗。
史提芬.傑伊.古爾德(Stephen Jay Gould)跟理查.列溫廷(Richard Lewontin)在1979年發表了一篇知名的論文,標題很華麗,叫〈聖馬可教堂的層間牆與過度樂觀的思維:對於適應主義的評論〉(The spandrels of San Marco and the Panglossian paradigm: a critique of the adaptationist programme)。古爾德與列溫廷借用建築學的「層間牆」(spandrel)來描述一種生物學現象,這種現象並非演化而來,它是一種副產品。在建築學中,層間牆是用來填滿拱門與圓頂之間的空隙:以拱門支撐的圓頂建築,在拱門與圓頂之間本來就會出現空隙,這些空隙需要填補,層間牆的功能就是填補空隙。古爾德與列溫廷說,沒有一個建築師會把層間牆當成設計的主體,層間牆上的設計只是拱門/圓頂裝飾圖案的副產品。
同樣地,皮質醇在早晨使葡萄糖濃度上升,這個現象是否帶有演化目的尚未可知,它也可能只是皮質醇做為戰鬥或逃跑荷爾蒙的副產品。但無論如何,早晨確實會出現胰島素阻抗。黎明現象
早晨是分泌皮質醇的時間,難怪第二型糖尿病患會出現高血糖的「黎明現象」。健康的血糖值會在夜間下降,而且維持在低濃度的狀態;但第二型糖尿病患的血糖值會隨著時間接近黎明而慢慢上升。我在第1章提過克利斯提安森教授的實驗,健康的人早上醒來時,血糖值約為4到5 mmol/l;克利斯提安森教授的第二型糖尿病患早上醒來時,血糖值約為7.0 mmol/l。
值得注意的是,黎明現象的程度與第二型糖尿病的病況有關。英國佩納斯(Penarth)的糖尿病研究單位做了一項研究,發現輕微糖尿病患(糖化血色素低於7.3%或56 mmol/mol)早上醒來時,血糖值約為7.0 mmol/l(吃完早餐後約為11.5 mmol/l);嚴重糖尿病患(糖化血色素高於8%或64 mmol/mol)早上醒來時,血糖值約為10.0 mmol/l(吃完早餐後約為15.0 mmol/l)。
這些數據使我深感疑惑:吃早餐會使血糖值上升到危險的地步,為什麼這些病患還要吃早餐?我把這個問題留到後面再討論。在此我想討論的問題是:為什麼第二型糖尿病患的早晨血糖值跟病況有關?其中一個答案是,還有一種因素會使糖尿病患的早晨血糖升高,那就是「自由脂肪酸」。
自由脂肪酸
自由脂肪酸可以解決一種生理問題。如我們所知,葡萄糖是身體的主要燃料。葡萄糖來自碳水化合物,會在血液裡自由流動,很容易就能被身體組織氧化,成為主要燃料理所當然。只不過,葡萄糖的儲存是個問題。
葡萄糖無法以自由化學物質的形態儲存,因為它是水溶性的;而溶解後的葡萄糖只能為一顆細胞提供短短數秒能量。燃料必須是固態才能堆疊成高密度的能量庫。因此葡萄糖是以肝醣(glycogen)的形態儲存(字源跟葡萄糖一樣有「glykys」,意指「甜」;還有跟「創世紀Genesis」一樣的「genes」,意指「誕生」)。過去肝醣被稱為「動物澱粉」,因為與來自植物的澱粉一樣,都是由長鏈葡萄糖聚合組成。肝醣不是理想的燃料儲存方式,原因有二。
首先,肝醣是一種部分氧化的碳水化合物(化學式是CH2O,有「碳」跟「水合物」,因為C已跟H2O水合在一起),因此肝醣氧化時提供的能量,來自C氧化成CO2,也就是二氧化碳。H不會再氧化成H2O產生能量,因為它早已氧化。
第二個原因是肝醣有很高的親水性。肝醣本身的分子太大,無法溶於水,因此是以顆粒的形態儲存。但肝醣是由高溶水性的葡萄糖單元構成,所以肝醣顆粒飽含水分,水分子會自動進入肝醣分子裡。水不是燃料卻占據了很多空間,重量也很重,因此身體儲存的肝醣顆粒(主要位在肝臟)只能滿足幾小時的能量需求。
脂肪是比較理想的燃料儲存方式,原因同樣有兩個。第一,脂肪的化學式是CH2,脂肪氧化不只釋放碳的能量C CO2,也會釋放氫的能量H HO2。第二,脂肪既不溶於水也不親水,儲存時不會裝滿無用的水。基於這兩個原因,身體優先選擇儲存脂肪非常合理,也因此我們儲存的肝醣大約只有900大卡,但是以三酸甘油酯儲存的脂肪卻高達12萬大卡。
問題來了。人體儲存的脂肪不會以葡萄糖的形態釋放到血液裡,而是以脂肪的形態(當然),尤其是一種叫做自由脂肪酸的脂肪。人體組織必須有能力氧化兩種不同的能源:
․飯後氧化來自腸道的葡萄糖
․空腹時氧化來自備用脂肪的自由脂肪酸
這是一個分為四階段的過程:
․消化食物時,葡萄糖從腸道進入血液,胰島偵測到葡萄糖。胰島分泌胰島素,細胞吸收並氧化葡萄糖。
․食物完全消化之後(大約需要四到六小時),不會再有葡萄糖從腸道進入血液,血糖值下降。胰島偵測到血糖值下降,減少分泌胰島素。
․胰島素減少本身就是一種信號,提示肝臟分解肝醣,釋放葡萄糖到血液裡。
․肝醣的儲量只能維持數小時(只要斷食一夜,隔天早上肝醣就已耗盡)。因此禁食幾個小時把肝醣用完之後,血液裡的胰島素濃度變得更低,這是第二種信號:提示備用脂肪釋放自由脂肪酸進入血液。
照理說,斷食的身體會先消耗肝醣分解而成的葡萄糖,肝醣用盡之後,改成氧化自由脂肪酸。但身體沒有這麼理性,因為大腦不會立刻氧化自由脂肪酸。就算身體的其他地方都已開始氧化自由脂肪酸,大腦仍須氧化葡萄糖。為什麼?沒有人知道答案。這是一個謎。
但是這個謎帶來不好的後果。身體在斷食的時候,血液裡會有兩種燃料:葡萄糖(大腦用)與自由脂肪酸(其他組織用)。這個情況令人擔憂,因為「一般的」細胞也可能消耗只有大腦才能用的葡萄糖。為了確保其他細胞不會搶走珍貴的葡萄糖,有一種信號會告訴身體各部位組織,如果葡萄糖與自由脂肪酸同時出現,它們應該消耗自由脂肪酸,這樣就能把葡萄糖留給大腦。
是誰發出這種信號呢?答案是自由脂肪酸;這會引發大規模、近乎全面性的葡萄糖抗性(glucose resistance)與胰島素阻抗。也帶我們回到早餐與黎明現象。
自由脂肪酸會在斷食的時候釋放出來,所以血液裡的自由脂肪酸濃度自然會在早餐前達到高峰。而自由脂肪酸引發的胰島素阻抗,會在早餐時達到高峰。自由脂肪酸引發胰島素阻抗,強化了皮質醇使血糖上升的效應。黎明時分的高皮質醇加上高自由脂肪酸會使血糖值上升,連健康人士也不例外(不過健康人士會分泌更多胰島素來調節早晨的胰島素阻抗);至於在第二型糖尿病患身上,胰島素濃度雖然上升了,卻不足以降低血糖。
此外,第二型糖尿病患的胰島素阻抗會削弱脂肪細胞對胰島素的反應,於是脂肪細胞釋放出更多自由脂肪酸,導致胰島素阻抗升高,血糖值也隨之上升。這是一個惡性循環,罪魁禍首正是早餐。
有沒有解決辦法?方法很簡單。第二型糖尿病患不應該吃早餐。到了午餐時間,黎明時增加的皮質醇已經變少,雖然自由脂肪酸濃度依然很高,但是對胰島素來說現在只剩下一道障礙,而不是兩道。實驗已經證明:對第二型糖尿病患來說,跨越午餐的單一障礙要比早餐的雙重障礙容易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