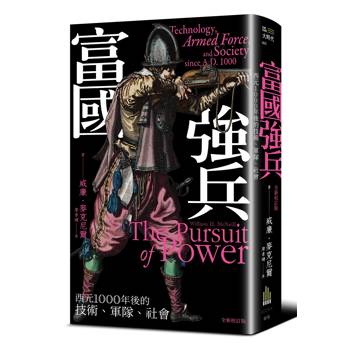作者序(摘錄)
本書是我較早一部著作《瘟疫與人》(Plagues and People)的姊妹作。《瘟疫與人》一書在於探討人類與微寄生物(microparasite)的互動下的主要事件,特別是對於微生物而言,相對較小的環境突發變化。每當新的地理環境出現某些新的突變或突發現象時,微生物便能不時短暫突破原先的生態限制,從而發生上述變化。本書則是以類似方式探討巨寄生模式(macroparasitism)的變化。病菌是人類需要對付的首要微寄生物。而我們唯一最主要的巨寄生物(macroparasite)則是一些專精於暴力的人士,他們無須自行生產糧食和消費商品即可生存無虞。因此,對人類社群中的巨寄生物的研究在此書中便轉化成對武裝力量的組織,特別是對戰士裝備種類變化的探究。就某種意義上而言,軍備武器的變化與微生物的基因突變類似,它經常能開創新探索領域,或從寄生社會本身內打破老舊軍事常規的限制。
然而,我在描述人類武裝力量的組織變化時,力求避免使用流行病學和生態學的語言。我會如此做的部分原因是,一來,此舉會牽涉到「巨寄生模式」的嚴格定義之比喻性擴展,再來則是因為有效武裝力量和支持它們的社會之間的共生關係,通常會將維持它們生存所需的地方資源消耗殆盡。微寄生物的共生現象在疾病生態學中也很重要。實際上,我在《瘟疫與人》書中曾主張,每當從未經歷過某些陌生傳染病的社會初次接觸到這些傳染病時,曾有患病經驗的文明就比隔絕於世的社群在生存上更具優勢。當一支裝備精良、組織強大的軍隊和缺乏同等戰力組織的社會接觸時,它所起的作用就和曾有患病經驗的社會中的細菌雷同。在這樣的遭遇戰中,較弱的社會可能會在戰事中承受嚴重傷亡。它所承受的主要損失往往出自於毫無防備地暴露在經濟和流行病的侵襲中,而這類侵略則是由較強大民族的軍事優勢所造成。但無論究竟是哪些因素引發,一個沒有能力保護自己免於外力侵擾的社群在這種情況下,除了喪失自治權外,也許還會喪失其整體地位。
戰爭和人類的有組織的暴力中,含有深刻的矛盾。一方面,英雄行徑、自我犧牲和尚武精神是社會性的最高體現。戰士間的團結和結盟關係堅韌強固。的確,人類在擁有痛恨、恐懼和需要毀滅的對象上,以及擁有能分享暴力行徑的危險和勝利的戰友兩方面,最能充分展現天性。因此,我們以狩獵為生的遠祖團結起來過這種生活,儘管他們的敵人多半是野獸,而不是人類。但在我們意識的表面之下仍舊殘存這類古老心理傾向,並深遠地影響著人類的戰爭行為。
另一方面,當代人的意識極端痛恨具有組織且刻意毀滅生命和財產的行徑,特別是自一九四五年以後,人類不必親自下手的遠距離殺戮能力得到大幅增長。事實上,過去近身肉搏所需的剽悍驍勇在現代戰爭技術下幾乎消失無蹤。發展不到百年的戰爭工業化已經抹消了往昔的作戰現實,但是自古流傳下來的集體使用武力之心理傾向卻未曾改變,而這便導致了危險的不穩定狀態。武裝力量、軍事技術和全體人類如何繼續共存,的確是我們這個時代的重大課題。
檢視過往的強權歷史,分析技術、武裝力量和社會之間原有平衡的改變,將無法解決當代難題。話雖如此,它卻可以提供一種角度,而在擁有以歷史綜觀事物的習慣後,將不再必然陷入簡單的解決方法和極端的沮喪。在大難臨頭下笨拙地摸索應付,是所有過去世代的命運。或許我們及我們的後代也將如此。然而,既然我們仍舊必須每天做出決定,更瞭解我們究竟是如何陷入當今的可怕困境,或許會有幫助。
本書明白彰顯作者對使用這類知識的謹慎信念,可以想見,它能為更明智的行動提供依據。即使最終證明那是錯的,我們在了解過去的事物如何與今日不同,又怎樣迅速演變成現在這個狀態的過程中,仍能保有根本的理智,並得到真正的樂趣。
本書寫作過程歷經二十年,最初寫此書的動力是來自一位批評家對《西方的興起》(The Rise of the West)一書的評論。那位批評家指出,我對於軍事技術和政治模式之間互動關係的論述,在往昔歷史的部分強調較多,但在談及現代時,則著墨較少。因此,本書可說是《西方的興起》這本書遲來的註腳。……
本書是我較早一部著作《瘟疫與人》(Plagues and People)的姊妹作。《瘟疫與人》一書在於探討人類與微寄生物(microparasite)的互動下的主要事件,特別是對於微生物而言,相對較小的環境突發變化。每當新的地理環境出現某些新的突變或突發現象時,微生物便能不時短暫突破原先的生態限制,從而發生上述變化。本書則是以類似方式探討巨寄生模式(macroparasitism)的變化。病菌是人類需要對付的首要微寄生物。而我們唯一最主要的巨寄生物(macroparasite)則是一些專精於暴力的人士,他們無須自行生產糧食和消費商品即可生存無虞。因此,對人類社群中的巨寄生物的研究在此書中便轉化成對武裝力量的組織,特別是對戰士裝備種類變化的探究。就某種意義上而言,軍備武器的變化與微生物的基因突變類似,它經常能開創新探索領域,或從寄生社會本身內打破老舊軍事常規的限制。
然而,我在描述人類武裝力量的組織變化時,力求避免使用流行病學和生態學的語言。我會如此做的部分原因是,一來,此舉會牽涉到「巨寄生模式」的嚴格定義之比喻性擴展,再來則是因為有效武裝力量和支持它們的社會之間的共生關係,通常會將維持它們生存所需的地方資源消耗殆盡。微寄生物的共生現象在疾病生態學中也很重要。實際上,我在《瘟疫與人》書中曾主張,每當從未經歷過某些陌生傳染病的社會初次接觸到這些傳染病時,曾有患病經驗的文明就比隔絕於世的社群在生存上更具優勢。當一支裝備精良、組織強大的軍隊和缺乏同等戰力組織的社會接觸時,它所起的作用就和曾有患病經驗的社會中的細菌雷同。在這樣的遭遇戰中,較弱的社會可能會在戰事中承受嚴重傷亡。它所承受的主要損失往往出自於毫無防備地暴露在經濟和流行病的侵襲中,而這類侵略則是由較強大民族的軍事優勢所造成。但無論究竟是哪些因素引發,一個沒有能力保護自己免於外力侵擾的社群在這種情況下,除了喪失自治權外,也許還會喪失其整體地位。
戰爭和人類的有組織的暴力中,含有深刻的矛盾。一方面,英雄行徑、自我犧牲和尚武精神是社會性的最高體現。戰士間的團結和結盟關係堅韌強固。的確,人類在擁有痛恨、恐懼和需要毀滅的對象上,以及擁有能分享暴力行徑的危險和勝利的戰友兩方面,最能充分展現天性。因此,我們以狩獵為生的遠祖團結起來過這種生活,儘管他們的敵人多半是野獸,而不是人類。但在我們意識的表面之下仍舊殘存這類古老心理傾向,並深遠地影響著人類的戰爭行為。
另一方面,當代人的意識極端痛恨具有組織且刻意毀滅生命和財產的行徑,特別是自一九四五年以後,人類不必親自下手的遠距離殺戮能力得到大幅增長。事實上,過去近身肉搏所需的剽悍驍勇在現代戰爭技術下幾乎消失無蹤。發展不到百年的戰爭工業化已經抹消了往昔的作戰現實,但是自古流傳下來的集體使用武力之心理傾向卻未曾改變,而這便導致了危險的不穩定狀態。武裝力量、軍事技術和全體人類如何繼續共存,的確是我們這個時代的重大課題。
檢視過往的強權歷史,分析技術、武裝力量和社會之間原有平衡的改變,將無法解決當代難題。話雖如此,它卻可以提供一種角度,而在擁有以歷史綜觀事物的習慣後,將不再必然陷入簡單的解決方法和極端的沮喪。在大難臨頭下笨拙地摸索應付,是所有過去世代的命運。或許我們及我們的後代也將如此。然而,既然我們仍舊必須每天做出決定,更瞭解我們究竟是如何陷入當今的可怕困境,或許會有幫助。
本書明白彰顯作者對使用這類知識的謹慎信念,可以想見,它能為更明智的行動提供依據。即使最終證明那是錯的,我們在了解過去的事物如何與今日不同,又怎樣迅速演變成現在這個狀態的過程中,仍能保有根本的理智,並得到真正的樂趣。
本書寫作過程歷經二十年,最初寫此書的動力是來自一位批評家對《西方的興起》(The Rise of the West)一書的評論。那位批評家指出,我對於軍事技術和政治模式之間互動關係的論述,在往昔歷史的部分強調較多,但在談及現代時,則著墨較少。因此,本書可說是《西方的興起》這本書遲來的註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