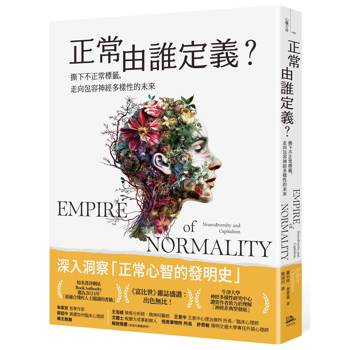【摘文一】
發現神經多樣性
一九九○年代,神經多樣性運動開始出現在自閉症的社運團體中,那時我還是個孩子,正在努力適應學校。當時社會普遍認為自閉症是一種個人的悲劇疾病,病人沒有能力過上健全的生活。人們認為,自閉症者和病患家人的唯一希望,是在未來透過行為制約或生物醫學的介入治療來治癒這個病症。
然而,到了一九九三年左右,越來越多人接觸到個人電腦和網路,這是自閉症者第一次有辦法透過網路建立連結。自閉症者彼此認識後,對於相關症狀的認知在短時間內大幅提高,他們開始質疑社會大眾對於自閉症的主流理解。這些自閉症社會運動的先驅者聚在一起,很快便意識到他們遇到的問題全都很類似,其中也包括我當時才剛開始留意到的各種生活問題。他們逐漸開始討論,或許他們會經歷這些相似的問題,主要並不是因為他們的大腦損壞了,而是因為這個社會無法順應他們在神經方面的不同之處。他們因而開始探討《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在一九九七年一篇報導中描述的「神經多元論」(neurological pluralism)。這種論述強調了「非典型人士」的行為和處事方式,需要這個社會接受並提供支持,而不是被建構成一種需要被控制、診療和治癒的醫學疾病。
神經多樣性(neurodiversity)正是出自於此,當時首位把這個概念記錄下來的是社會學系的學生茱蒂.辛格(Judy Singer)。神經多樣性的基本概念是:我們不應該把「正常」大腦和「神經典型」視為理想狀態,而應該以看待生物多樣性的觀點看待心智運作。以這種觀點來說,一個社會需要各種類型的心智才能順利運作,因此我們不應該預先認為「常態」勝過「歧異」。取而代之的是,我們應該認為社會中有各式各樣的心智,不同環境會使得各種心智變得具有行為能力或失去行為能力,沒有任何一種心智狀態天生就比其他的更優越。以我親身經歷過的各種感官問題為例,我們可以認為這一類問題的成因在於,學校、工作場所與公共空間在設計時,都是以神經典型人士為主要考量。更廣泛地來說,從這個觀點來看,我們可以用社會邊緣化與社會歧視的脈絡,理解自閉症者的許多痛苦經歷――例如我在學校受到霸凌。
為了解決這種問題,辛格與其他社運人士呼籲社會應進行新的「神經多樣性政治」(politics of neurological diversity)。對他們來說,神經多樣性政治是新社會運動的一部分,他們會在推動此運動時以早期的民權運動為模板,而那些民權運動的訴求是終結國內外在種族、性別與性這三方面的隔離與壓迫。他們希望這個嶄新的神經多樣性運動,能替神經異常人士和神經障礙人士爭取應有的權利,藉此幫助這些人減輕生命中的困難。他們希望能以推動神經多樣性發展的方式重新設計這個世界,結束全球各地對神經多樣性價值的壓迫。
他們呼籲社會大眾注意神經多樣性政治,此舉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聚集了許多支持這個目標的新倡議者。雖然這項運動早期大多聚焦在自閉症上,不過其他領域的人很快就開始應用各種源於自閉研究領域的架構和詞彙。第一批使用的是同屬發展障礙的群體,例如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簡稱ADHD)和運動障礙症(Dyspraxia)。接下來,其他被診斷為病患的人(例如雙極性障礙者與邊緣人格障礙者)也開始應用神經多樣性的框架,更不用說那些沒有獲得正式醫學診斷的人了。
二○○○年代早期,卡西安.阿薩蘇馬蘇(Kassiane Asasumasu)創造了「神經多樣者」(neurodivergent)這個詞彙,我們可以藉此得知自閉症框架的延伸應用程度。對她來說,只要一個人的神經功能被視為「不同於典型」,就是神經多樣者,無論這個人的差異是因為社會無法順應多樣性,或癲癇症等醫療診斷而導致的障礙,都一樣是神經多樣者。阿薩蘇馬蘇寫道:我們尤其可以把這個概念「視為一種包容的工具」,所有神經非典型人士都能夠應用。儘管這種延伸應用使人們開始質疑神經多樣性框架的範圍和界線,但這種延伸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能幫助更多人進入神經多樣性的標籤之下。同時,正如史帝夫.格拉比(Steve Graby)觀察到的,反精神醫學的擁護者強調,他們和肢體障礙者不一樣,他們認為精神病患者並不是真正的障礙者;而神經多樣性的觀點則全然接受精神病患者的障礙者身分,並且強調心理障礙和生理障礙之間的相似性,允許社會發展出應用更廣泛、包容性更高的政治信念,神經多樣性的支持者也跨越了身體被醫療化的人與精神被醫療化的人之間的分立。
隨著這項運動的成長,神經多樣性理論也有了進一步的發展與適應。對我來說,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名為尼克.沃克的自閉症年輕學者在二○一一年指出,若要解放神經多樣性,不只是患者需要取得權利,這個社會也需要在科學與文化方面進行大規模的「典範轉移」。這種轉移會帶領我們遠離主流的「病理學典範」,沃克認為這種典範是依照精神正常者的極度受限標準定義出來的,這種定義本身就會把精神多樣性病理化與污名化。沃克呼籲眾人留意病理學典範,並指出這種典範鞏固了精神醫學和心理學的研究與醫療,也鞏固了普羅大眾對神經多樣的刻板反應。
她認為神經多樣性的支持者必須建立「神經多樣性典範」,包容並接納人們在認知與情緒方面更大幅度的差異。這種可能性不只為無數神經多樣者帶來希望,同時也提出了一種理想,讓人們可以一起努力。這個理想讓身為哲學家的我迅速投身其中,因為我知道這種典範轉移不但需要科學、臨床與文化方面的實踐,也需要更基礎的理論研究。
我在二○一二年初次接觸到這個觀點,那時沃克的關鍵著作已經出版一年了。我在閱讀了辛格、沃克和其他倡導者的著作後,看到了一條截然不同的道路,既不是病理學典範的框架,也不是反精神醫學的否認主義。這條道路允許我徹底認清我有身心障礙的現實,同時又幫助我逐漸意識到,這些建構了我人生的障礙具有一種政治本質。舉例來說,我開始透過神經多樣性的觀點去思考,我從小到大經歷的障礙是不是這個奉行神經基準性的社會加諸在我身上的。我逐漸意識到,自我出生開始,這個僵化且極為侷限的神經基準性社會就在阻礙我的學習、我的發展和我的成功機會。我也開始意識到,我的創傷和心理疾病不只源自於相對的貧困和父母的忽視,也源自於這個打從結構性歧視障礙人士的世界。對我和許許多多人來說,這些精確的理解帶來了自由,讓我能夠用嶄新的態度看待人生。
同樣重要的是,這個觀點也幫助我和其他障礙人士與慢性疾病人士變得團結一致,甚至發展出身為障礙人士的自豪感。總體來說,這些知識幫助我對抗孤立、政治慣性和羞愧,也幫助我和許多人逐漸找到出路。突然之間,神經多樣性者似乎只要同心協力,就能改變這個世界――讓這個世界更加包容神經異常人士和神經障礙人士。我們獲得了過去看似不可能實現的希望。因此,我在神經多樣性運動迅速發展的年代投身於這個運動,當時沒有任何人預料到,這個運動會以何種方式發展到多大的程度。
【摘文二】
常態帝國
本書開創先河,在闡述資本主義的歷史時把核心焦點放在神經多樣性,而非階級。雖然我採用交叉方法考慮了階級、種族、性別、性傾向和身體障礙,不過我因為把焦點放在神經多樣性,所以能清楚追蹤我稱作「常態帝國」的現象是如何出現的。常態帝國指的是從資本主義制度中出現的機制,包括物質關係、社會實踐、科學研究計畫、官僚體系、經濟強制性和行政程序,這些機制在資本主義制度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後就會出現。相較於過去出現的各個社會,這些機制使得人們對於身體、認知與情緒的正常範圍採取了更受限的觀點。同時,這種帝國式的框架也突顯了神經多樣性壓迫、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之間的關聯。我們因而能夠藉此研究神經多樣性的政治發展前景,這種前景也同樣能幫助我們達到集體的自由解放。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我提供的並不是全面的歷史,而是聚焦於謹慎選擇關鍵思想家,把他們放在更宏觀的物質背景中。我這麼做的目的,不是使他們重新成為「偉大的」(或不怎麼偉大的)人物,而是要描繪出物質因素如何對病理學典範思維的發展造成重大影響,而引導這些影響的是具體化的資本力量關係與階級制度,我會格外關注某些關鍵時刻的發展。我們因此得以理解,物質和意識形態一直以來都在互相影響並互相加強,這些相互作用甚至會因為是社會定位為「幫助科學進步的人」的研究而實現,可以說這些人發揮了特別大的影響力。
考慮到這一點,我會先介紹在古希臘被稱為「希波克拉底學派」(Hippocratic)的醫師們提出的研究,以及世界各地的古醫學。他們往往認為健康是一種和諧或平衡,無論在個人體內或是在個人與環境之間都是如此。我們將會讀到,隨著資本主義的崛起,這種健康的觀點也消失了,主要是因為資本主義強調競爭力與勞工生產力。這種新經濟體系使得人類被重新定義為機器,而我將透過哲學家笛卡兒(René Descartes)的思想來探討這種定義。接著,「正常基準」(normality)的概念出現了,人們利用此概念重新想像健康和能力的本質。我接著會指出,社會開始使用這種方式區分階級與控制人口,雖然這麼做確實帶來科學進步,但也帶來了越加嚴重的壓迫。隨著時間推移,正常基準的想法深植於我們的集體意識,它變得永恆又看似客觀,隱藏了它的物質性起源和歷史偶然性。
在這樣的背景下,我認為病理學典範有很大一部分可以追溯至一位怪異的先驅科學家法蘭西斯.高爾頓(Francis Galton)的研究――高爾頓是查爾斯.達爾文(Charles Darwin)的同輩遠親,達爾文正是在當代以優生學和各種科學創新而聞名的那位科學家。以我們的目標來說,高爾頓在十九世紀晚期引進的事物中,最重要的是比較認知和測量生物學的創新方法,這兩者以達爾文的階級系統為基礎,歸化了工業資本主義的認知階級,以及社會地位、種族與性別的階級。對高爾頓來說,這個新方法的重點在於規範與強化社會對人口的常態化和控制,這一點如今已變成了科學領域的合法目標。這個發展的其中一個影響,是人們把「常態基準、生產率和健康」的概念全都交錯合併在一起。
我在本書的其中一個關鍵論述指出,後來埃米爾.克雷佩林(Emil Kraepelin)等著名的精神科醫師,以及其他心理學、心理測量和生物醫學方面的研究,全都積極地接納並拓展這種典範。因此,我在追溯高爾頓的影響時,也介紹了更宏觀的優生學意識形態如何變成文化霸權,而高爾頓的研究模式,則同時引導科學知識產物的理論、研究方法和結果,藉此推動資本主義逐漸實現。因此,我認為在精神醫學與相關領域使用的當代主流科學典範是由高爾頓創造的,而不是許多精神科歷史中常認為的克雷佩林。
意識形態的偏誤,源自於資本主義和帝國制英國的物質關係,接下來我們會看到,直至今日,這些偏誤一直都在透過高爾頓的典範,引導有關神經多樣性的科學知識產出、社會大眾理解、政策與臨床醫療行為。即使舊帝國秩序的其他重要層面已瓦解,但神經多樣性的概念仍沒有改變。正是這種以科學、行政、文化和法律的強制性所組成的新機制,創造出了常態帝國。在大英帝國崩解後許久,帝國的許多階級與權力關係仍透過這些新機制持續維持、重現與擴張,這些新機制不但存活了下來,更隨著資本主義持續擴張,變成更加強大的霸權。因此,關鍵問題不單是病理學典範,還包括資本主義邏輯和病理學典範如何彼此強化,使得神經多樣性沒有機會解放。唯有改變深層體制,才能使神經多樣性獲得自由。
我的目標不是針對政策提出建議或制訂政治策略。我的目標是幫助讀者清楚瞭解根本的問題,我認為這個問題比病理學典範更深、更古老也更狡猾。釐清這個問題只是第一步,我們還需要花更多時間一起努力,才能繼續和常態帝國戰鬥,所謂的常態帝國,就是病理學典範背後的支撐力,也是維持病理學典範的必要機制。我們必須理解這種典範和這種宏觀機制的相互關係,以及這種典範和資本主義生產模式的基礎配置之間的相互關係,唯有如此,我們才能清楚瞭解我們得怎麼做,才能達到神經多樣性的自由解放。
值得強調的是,我也因為目前的政治狀態而寫下一些具有急迫性的內容。在過去幾年間,隨著神經多樣性的行動主義快速成長,我們不但看到神經多樣性倡議者使用的詞彙、概念與建議,開始出現在臨床醫師和政治家的口中(他們利用神經多樣性來維持現狀),也會看到新出現的各種多樣性包容顧問多不勝數,他們收取越來越多錢和企業協商合作,而後企業便開始把神經多樣者視為一種新資源,可以在開採後獲得生產率。我們可以在這時注意到,我所謂的「神經柴契爾主義」(neuro-Thatcherism)正在興起,資本主義甚至徹底反轉了那些想抵抗資本主義有害影響的行動,把那些行動轉變成新機會,將利潤與生產率最大化。在這種情況下,儘管新行動似乎正逐漸獲得越來越多的權力,但事實上,這種新行動的解放潛力正逐漸消失。
在我們逐漸邁向二十世紀末的同時,反精神醫學運動又再次流行了起來。反精神醫學運動的傳統思想和我的分析相反,這種思想認為核心問題在於精神醫學本身,與精神醫學相信的「心理疾病」概念。這個論點源自右派自由主義者湯瑪士.薩茲(Thomas Szasz),儘管並非所有反精神醫學的醫師都支持這個論點,但這或許是能替代主流精神醫學的各個論點中最有影響力的一種。
最重要的是,雖然我的分析可能在表面上看來和薩茲有許多重疊之處,但我徹底否定他們認為自閉症、ADHD等狀態並不是「真正」障礙的概念。我也強烈否定薩茲流派認為心理疾病是一種「迷思」(myth)的說法。儘管我對主流精神醫學典範的基礎和影響力確實有許多批評,不過我批評的重點在於:人們是如何把健康的概念與基準常態以及生產率混為一談,還有在資本主義的物質關係中,障礙與疾病如何出現具體的成長。這並不代表我拒絕承認心理疾病或障礙等狀態。正如我們將會在本書看到的,事實上,我認為反精神醫學是問題的一部分,而不是解決之道。這是因為,儘管反精神醫學和病理學典範在表面上看起來截然不同,但事實上,反精神醫學並沒有抵制病理學典範的邏輯與基準常態的大範圍機制,反而加強了它們。
相對地,我在探尋神經多樣性運動的崛起時,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綜合了重要的神經多樣性理論學家茱蒂.辛格和尼克.沃克的研究。這件事至關重要,我因而得以清楚說明人們尚未釐清的資本主義衝突,展現了神經柴契爾主義的徒勞無功。在這之中最重要的是,無論我們和神經典型的距離是遠是近,我們都越來越接近神經基準常態的雙重束縛,每個人都因此陷入更艱難的困境中。在人類這個物種中,許多目前無法應用的神經認知多樣性都受到無能力化、剝奪價值與歧視;而能夠被使用的那些多樣性則受到殘忍的剝削,導致健康狀態不佳。我認為,無論是哪種精神認知狀態的人,他的心靈和自我都會因為資本主義製造出來的精神階級而逐漸疏離。繼續這樣下去,我們將會陷入「所有人都生病」或「全都成為障礙人士」的狀況,又或者至少陷入「多數人都難以維持身心健康」的狀況。根據這個觀點,壓迫神經多樣者的並不是神經典型者,而是資本主義者的優勢地位,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種優勢地位會同時創造並傷害神經典型者和神經多樣者,只不過每個人被創造與傷害的方式,會因為自身距離基準常態的遠近而有些微不同。
我希望能指出的其中一個觀點是,儘管資本主義社會允許社會階級出現一定程度的流動性,但這並不代表優勢地位徹底消失了,優勢地位只是稍微偏向神經多樣性罷了。我認為,這打破了資本主義的最後一個承諾,也就是幫助我們實踐菁英領導制度(meritocracy),在這種制度下,自由個體的價值取決於美德與工作的努力程度,而非取決於繼承的地位。
菁英領導制度在國家層面與全球層面上都沒有實現,國家中的社會階級仍大幅限制了個人的經濟狀況,而北方國家的有錢人,依靠的正是南方國家中相對貧困的人。除此之外,我認為即使資本主義確實帶來了有限的進步,使社會階級的流動性增加,但相對於資本日益增加的認知需求,我們也只是把比較傳統形態的地位優勢,轉換成神經典型的地位優勢罷了。因此,在資本主義之下,自由解放的機會非常有限,而且這種自由解放只是依據我們的階級位置,給予不同形式的地位優勢與異化。我認為這個世界正是因此需要更基進的神經多樣性政治,直接反抗常態帝國。
【摘文三】
神經多樣性運動
一九九七年六月,一位正在就讀兼讀制社會學位的年輕女子在《紐約時報》上讀到一篇文章,作者是記者哈維.布盧姆(Harvey Blume),標題為〈自閉症者在網際空間中連結〉。這篇文章立刻引起茱蒂.辛格的注意。布盧姆寫道,有鑑於近年來網路的可用性越來越廣,「許多美國的自閉症者都開始進行這個症候群本應阻礙他們做的事:溝通」。他們會這麼做,其實並不只是因為在線上建立連結比面對面容易。布盧姆詳細指出,除此之外,有越來越多「自閉症者不願意、也無法放棄他們自己的習慣。取而代之的是,他們現在正在提出嶄新的社會協議,將神經多元論視為重點。」也就是說,他們不是因為壓力而表現得更貼近「常態」,而是反對這麼做,並在網路上建立連結的過程中反抗「自閉症需要被修正」這一點。
當時辛格在澳洲的雪梨科技大學修習社會學。辛格先是從醫學系休學,再轉而就讀社會學,進一步瞭解她關注的各種政治。她關注的其中一個主題是障礙政治(politics of disability),辛格在讀到布盧姆的文章之前,就已經覺得自己位於自閉症光譜中了――自閉症光譜是當時人們知之甚少的症候群,主要和社交問題、溝通問題、受限的興趣、受限的習慣有關。她發現在自己的生活中,有許多問題和自閉症者的問題相呼應,當時她已經加入了許多不同的線上自閉症團體,認識了其他自閉症者。此外,辛格也已經開始透過社會學研究障礙的視角來思考自閉症,將障礙視為一種社會問題,而非個體問題。
辛格之所以會受到布盧姆的文章所吸引,除了因為這些經驗之外,也因為她對於布盧姆所描述的「神經多元論」感同身受,也能理解在這個神經典型的世界中拒絕放棄自閉症習慣的心情。其中最重要的是,辛格對自閉症反抗性格的理解,是基於她身為流亡猶太人的經驗。也就是說,她屬於拒絕同化的外來者團體――而他們也因此付出了代價。畢竟,辛格自己就是大屠殺倖存者的女兒,她母親在二戰後搬到了澳洲。儘管辛格是在澳洲出生長大的,但她仍覺得自己在這裡就像是個外來者。身為流亡者的傳承與經驗,使辛格能深入體會神經多元論的新政治,以及在面對巨大的社會壓力時,拒絕放棄自閉症習慣的想法。
因此,辛格在讀了布盧姆的文章後,迅速聯絡上他,成為「自閉症光譜的獨立生活」這個新社群的成員之一。她不但在一年內融入這個社群,還提出「神經多樣性」這個更簡潔的概念,提供歷史上首次出現的持續性社會學分析,將這些想法定位於障礙研究領域中。這樣的經驗讓她得以在一九九九年的書籍章節中呼籲眾人理解「神經多樣性的政治」,再加上布盧姆的報導,推動了這個自閉症社運人士的先驅社群,點燃了神經多樣性運動的跨國火花。
辛格在這項重要的研究中指出,人們應該把神經多樣性視為「原本已熟悉的階級、性別、種族等政治分類的新增項目」。她將自閉症概念化成一種人們尚未認知到的集合(intersection),藉此設想出一種新的民權運動,能夠引導這個社會發展成她所謂的「生態」社會。對辛格來說,這個社會看待神經多樣性的方式,應該要像是生態環境保護者看待生物多樣性那樣,因此,這個社會應該要改變社交與物質的條件,滿足並保護自閉症者的生活方式。這些改變,包括在政策制訂與行動方面變得更包容,並建立合適的認知位置,藉此協助社會培養自閉症者的繁榮發展與包容能力。這和主流的社會組織方式截然不同,主流方式是隔離障礙者,並對自閉症者例行性地施加壓力,要他們更接近「常態」。這場運動的核心思想是由無數行動主義者和活動家共同發展出來的,而辛格的貢獻是將這些新興的想法,根植在障礙研究發展出來的理論體系中。在這之後,辛格所建立的理論基礎引導了往後的運動走向、戰術與展望。
障礙理論
若要瞭解這些想法源自何處,我們必須回到更久之前。事實上,我們要一路回到一九六八年,當時三十歲的維克.芬克爾斯坦以難民的身分來到英國。芬克爾斯坦是政治活動家,曾因為參與反種族隔離運動而遭到監禁。他也因為疑似是共產主義者,而被禁止出入南非五年。不過,監禁他的政府當局沒有意識到,他們對待他的方式,卻幫助他發展出了足以改變世界的想法。
對政府來說,芬克爾斯坦帶來的問題在於,他在十六歲的一次意外摔斷了頸部,從此之後就必須使用輪椅。這也就代表政府為了監禁他,就必須順應他的身體損傷而做出各種調整。由於政府在適合的狀況下能找到方法順應他的障礙,所以芬克爾斯坦開始思考,社會是否應該施加壓力讓政府可以――以及應該――在預設的狀況下做出這些調整。在這十八個月的拘留期間,他也注意到他因身體障礙而被隔離的經驗,以及他反抗的種族隔離之間,其實有更多相似之處。他因此開始探索歷史的過往力量,是如何導致了障礙隔離這樣的結果,以及改變這種結果的可能性。
一九七○年代,肢體障礙者反隔離協會(Union of Physically Impaired Against Segregation,簡稱UPIAS)正式化了這些想法。該協會是由一群支持馬克思主義的基進障礙社運人士所組成,過去曾在倫敦的一間酒吧見面。這個團體是芬克爾斯坦和另一位身心障礙社運人士保羅.亨特(Paul Hunt)在一九七二年共同創辦的,亨特從小就在英國各地被拘留過。他們兩人結合了彼此的過往經驗,意識到他們的障礙其實是物質社會因素的產物,而不只是身體的問題。他們在一九七五年出版的文件《身心障礙基礎原則》中闡明了這種想法,並在其中提出了一個概念,被往後的人稱為障礙的「社會模式」(social model)。
他們將這個新模式拿去和個人模式以及醫學模式做比較。醫學模式認為障礙源自損傷與功能異常。也就是說,如果一個人的身體出了問題,就會導致這個人沒有能力做到普通的事。依據這樣的思想――當時這種想法仍屬於霸權――障礙是一種會影響個體的生理悲劇。在許多案例中,人們都認為障礙的本質會使人沒有機會過上充實的理想人生。個體能指望的最好結果就是獲得醫學治療,減少障礙對日常生活的影響。
UPIAS幾乎拒絕了所有和這個傳統框架有關的想法。他們的核心理論運動是拒絕接受「身體損傷」與「障礙失能」之間的因果關聯。相反地,肢體障礙反隔離協會認為:
是這個社會使身體損傷者遇到障礙。是因為我們遭受了不必要的隔離,被排除在完整的社會參與之外,所以障礙才會被強制施加在我們的身體損傷上。
依據這個觀點,是物質環境和社會的結構與行動(例如沒有通往建築內的緩坡)將障礙「強制施加」在那些身體損傷者身上的。他們承認損傷真實存在,也是身體的一部分,但他們拒絕預設損傷代表了障礙就是個體的悲劇。從這個角度來看,障礙者遭遇的主要問題是邊緣化和壓迫,而不只是個人醫療。換句話說,障礙――或者至少就肢體障礙而言(UPIAS將認知障礙排除在他們的論述之外)――不再是個體醫療問題,而是與整個社會環境以及物質環境有關的問題。
雖然這種社會模式通常可以追溯到UPIAS,但值得注意的是,其他基進群體也在差不多的時間點發展出了類似的觀點。舉例來說,以薩米.沙爾克(Sami Schalk)所說的,美國的黑人權力與馬克思列寧主義組織――黑豹(Black Panthers)也開始認為,障礙者解放與集體解放有密切關聯。因此,到了一九七○年代晚期,黑豹開始支持基進障礙行動主義。他們「迅速採用了障礙者提出的社會模式,這是因為這種模式符合他們對於種族與階級壓迫的理解,這種壓迫源自更大規模的社會偏見與失敗」。
其他組織開發的社會模式和類似的分析法,也都成了障礙人士推行運動的理論基礎,該運動在剛開始數十年間主要聚焦在肢體障礙上。他們把焦點放在「態度、身體結構、社會期望與社會支持不足」是如何抑制了障礙者的運作能力與發展,這場運動因此而在法律和社會方面獲得意義重大的認可,也在去除障礙者的阻礙與隔離時取得顯著的成果。這場大規模運動正是為什麼如今在英國與其他國家中,建築物通常都會設置障礙者停車位、無障礙洗手間、坡道等。英國、美國與其他國家都因為這場運動,而在法律上為障礙者的權利帶來了重大益處。
發現神經多樣性
一九九○年代,神經多樣性運動開始出現在自閉症的社運團體中,那時我還是個孩子,正在努力適應學校。當時社會普遍認為自閉症是一種個人的悲劇疾病,病人沒有能力過上健全的生活。人們認為,自閉症者和病患家人的唯一希望,是在未來透過行為制約或生物醫學的介入治療來治癒這個病症。
然而,到了一九九三年左右,越來越多人接觸到個人電腦和網路,這是自閉症者第一次有辦法透過網路建立連結。自閉症者彼此認識後,對於相關症狀的認知在短時間內大幅提高,他們開始質疑社會大眾對於自閉症的主流理解。這些自閉症社會運動的先驅者聚在一起,很快便意識到他們遇到的問題全都很類似,其中也包括我當時才剛開始留意到的各種生活問題。他們逐漸開始討論,或許他們會經歷這些相似的問題,主要並不是因為他們的大腦損壞了,而是因為這個社會無法順應他們在神經方面的不同之處。他們因而開始探討《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在一九九七年一篇報導中描述的「神經多元論」(neurological pluralism)。這種論述強調了「非典型人士」的行為和處事方式,需要這個社會接受並提供支持,而不是被建構成一種需要被控制、診療和治癒的醫學疾病。
神經多樣性(neurodiversity)正是出自於此,當時首位把這個概念記錄下來的是社會學系的學生茱蒂.辛格(Judy Singer)。神經多樣性的基本概念是:我們不應該把「正常」大腦和「神經典型」視為理想狀態,而應該以看待生物多樣性的觀點看待心智運作。以這種觀點來說,一個社會需要各種類型的心智才能順利運作,因此我們不應該預先認為「常態」勝過「歧異」。取而代之的是,我們應該認為社會中有各式各樣的心智,不同環境會使得各種心智變得具有行為能力或失去行為能力,沒有任何一種心智狀態天生就比其他的更優越。以我親身經歷過的各種感官問題為例,我們可以認為這一類問題的成因在於,學校、工作場所與公共空間在設計時,都是以神經典型人士為主要考量。更廣泛地來說,從這個觀點來看,我們可以用社會邊緣化與社會歧視的脈絡,理解自閉症者的許多痛苦經歷――例如我在學校受到霸凌。
為了解決這種問題,辛格與其他社運人士呼籲社會應進行新的「神經多樣性政治」(politics of neurological diversity)。對他們來說,神經多樣性政治是新社會運動的一部分,他們會在推動此運動時以早期的民權運動為模板,而那些民權運動的訴求是終結國內外在種族、性別與性這三方面的隔離與壓迫。他們希望這個嶄新的神經多樣性運動,能替神經異常人士和神經障礙人士爭取應有的權利,藉此幫助這些人減輕生命中的困難。他們希望能以推動神經多樣性發展的方式重新設計這個世界,結束全球各地對神經多樣性價值的壓迫。
他們呼籲社會大眾注意神經多樣性政治,此舉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聚集了許多支持這個目標的新倡議者。雖然這項運動早期大多聚焦在自閉症上,不過其他領域的人很快就開始應用各種源於自閉研究領域的架構和詞彙。第一批使用的是同屬發展障礙的群體,例如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簡稱ADHD)和運動障礙症(Dyspraxia)。接下來,其他被診斷為病患的人(例如雙極性障礙者與邊緣人格障礙者)也開始應用神經多樣性的框架,更不用說那些沒有獲得正式醫學診斷的人了。
二○○○年代早期,卡西安.阿薩蘇馬蘇(Kassiane Asasumasu)創造了「神經多樣者」(neurodivergent)這個詞彙,我們可以藉此得知自閉症框架的延伸應用程度。對她來說,只要一個人的神經功能被視為「不同於典型」,就是神經多樣者,無論這個人的差異是因為社會無法順應多樣性,或癲癇症等醫療診斷而導致的障礙,都一樣是神經多樣者。阿薩蘇馬蘇寫道:我們尤其可以把這個概念「視為一種包容的工具」,所有神經非典型人士都能夠應用。儘管這種延伸應用使人們開始質疑神經多樣性框架的範圍和界線,但這種延伸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能幫助更多人進入神經多樣性的標籤之下。同時,正如史帝夫.格拉比(Steve Graby)觀察到的,反精神醫學的擁護者強調,他們和肢體障礙者不一樣,他們認為精神病患者並不是真正的障礙者;而神經多樣性的觀點則全然接受精神病患者的障礙者身分,並且強調心理障礙和生理障礙之間的相似性,允許社會發展出應用更廣泛、包容性更高的政治信念,神經多樣性的支持者也跨越了身體被醫療化的人與精神被醫療化的人之間的分立。
隨著這項運動的成長,神經多樣性理論也有了進一步的發展與適應。對我來說,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名為尼克.沃克的自閉症年輕學者在二○一一年指出,若要解放神經多樣性,不只是患者需要取得權利,這個社會也需要在科學與文化方面進行大規模的「典範轉移」。這種轉移會帶領我們遠離主流的「病理學典範」,沃克認為這種典範是依照精神正常者的極度受限標準定義出來的,這種定義本身就會把精神多樣性病理化與污名化。沃克呼籲眾人留意病理學典範,並指出這種典範鞏固了精神醫學和心理學的研究與醫療,也鞏固了普羅大眾對神經多樣的刻板反應。
她認為神經多樣性的支持者必須建立「神經多樣性典範」,包容並接納人們在認知與情緒方面更大幅度的差異。這種可能性不只為無數神經多樣者帶來希望,同時也提出了一種理想,讓人們可以一起努力。這個理想讓身為哲學家的我迅速投身其中,因為我知道這種典範轉移不但需要科學、臨床與文化方面的實踐,也需要更基礎的理論研究。
我在二○一二年初次接觸到這個觀點,那時沃克的關鍵著作已經出版一年了。我在閱讀了辛格、沃克和其他倡導者的著作後,看到了一條截然不同的道路,既不是病理學典範的框架,也不是反精神醫學的否認主義。這條道路允許我徹底認清我有身心障礙的現實,同時又幫助我逐漸意識到,這些建構了我人生的障礙具有一種政治本質。舉例來說,我開始透過神經多樣性的觀點去思考,我從小到大經歷的障礙是不是這個奉行神經基準性的社會加諸在我身上的。我逐漸意識到,自我出生開始,這個僵化且極為侷限的神經基準性社會就在阻礙我的學習、我的發展和我的成功機會。我也開始意識到,我的創傷和心理疾病不只源自於相對的貧困和父母的忽視,也源自於這個打從結構性歧視障礙人士的世界。對我和許許多多人來說,這些精確的理解帶來了自由,讓我能夠用嶄新的態度看待人生。
同樣重要的是,這個觀點也幫助我和其他障礙人士與慢性疾病人士變得團結一致,甚至發展出身為障礙人士的自豪感。總體來說,這些知識幫助我對抗孤立、政治慣性和羞愧,也幫助我和許多人逐漸找到出路。突然之間,神經多樣性者似乎只要同心協力,就能改變這個世界――讓這個世界更加包容神經異常人士和神經障礙人士。我們獲得了過去看似不可能實現的希望。因此,我在神經多樣性運動迅速發展的年代投身於這個運動,當時沒有任何人預料到,這個運動會以何種方式發展到多大的程度。
【摘文二】
常態帝國
本書開創先河,在闡述資本主義的歷史時把核心焦點放在神經多樣性,而非階級。雖然我採用交叉方法考慮了階級、種族、性別、性傾向和身體障礙,不過我因為把焦點放在神經多樣性,所以能清楚追蹤我稱作「常態帝國」的現象是如何出現的。常態帝國指的是從資本主義制度中出現的機制,包括物質關係、社會實踐、科學研究計畫、官僚體系、經濟強制性和行政程序,這些機制在資本主義制度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後就會出現。相較於過去出現的各個社會,這些機制使得人們對於身體、認知與情緒的正常範圍採取了更受限的觀點。同時,這種帝國式的框架也突顯了神經多樣性壓迫、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之間的關聯。我們因而能夠藉此研究神經多樣性的政治發展前景,這種前景也同樣能幫助我們達到集體的自由解放。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我提供的並不是全面的歷史,而是聚焦於謹慎選擇關鍵思想家,把他們放在更宏觀的物質背景中。我這麼做的目的,不是使他們重新成為「偉大的」(或不怎麼偉大的)人物,而是要描繪出物質因素如何對病理學典範思維的發展造成重大影響,而引導這些影響的是具體化的資本力量關係與階級制度,我會格外關注某些關鍵時刻的發展。我們因此得以理解,物質和意識形態一直以來都在互相影響並互相加強,這些相互作用甚至會因為是社會定位為「幫助科學進步的人」的研究而實現,可以說這些人發揮了特別大的影響力。
考慮到這一點,我會先介紹在古希臘被稱為「希波克拉底學派」(Hippocratic)的醫師們提出的研究,以及世界各地的古醫學。他們往往認為健康是一種和諧或平衡,無論在個人體內或是在個人與環境之間都是如此。我們將會讀到,隨著資本主義的崛起,這種健康的觀點也消失了,主要是因為資本主義強調競爭力與勞工生產力。這種新經濟體系使得人類被重新定義為機器,而我將透過哲學家笛卡兒(René Descartes)的思想來探討這種定義。接著,「正常基準」(normality)的概念出現了,人們利用此概念重新想像健康和能力的本質。我接著會指出,社會開始使用這種方式區分階級與控制人口,雖然這麼做確實帶來科學進步,但也帶來了越加嚴重的壓迫。隨著時間推移,正常基準的想法深植於我們的集體意識,它變得永恆又看似客觀,隱藏了它的物質性起源和歷史偶然性。
在這樣的背景下,我認為病理學典範有很大一部分可以追溯至一位怪異的先驅科學家法蘭西斯.高爾頓(Francis Galton)的研究――高爾頓是查爾斯.達爾文(Charles Darwin)的同輩遠親,達爾文正是在當代以優生學和各種科學創新而聞名的那位科學家。以我們的目標來說,高爾頓在十九世紀晚期引進的事物中,最重要的是比較認知和測量生物學的創新方法,這兩者以達爾文的階級系統為基礎,歸化了工業資本主義的認知階級,以及社會地位、種族與性別的階級。對高爾頓來說,這個新方法的重點在於規範與強化社會對人口的常態化和控制,這一點如今已變成了科學領域的合法目標。這個發展的其中一個影響,是人們把「常態基準、生產率和健康」的概念全都交錯合併在一起。
我在本書的其中一個關鍵論述指出,後來埃米爾.克雷佩林(Emil Kraepelin)等著名的精神科醫師,以及其他心理學、心理測量和生物醫學方面的研究,全都積極地接納並拓展這種典範。因此,我在追溯高爾頓的影響時,也介紹了更宏觀的優生學意識形態如何變成文化霸權,而高爾頓的研究模式,則同時引導科學知識產物的理論、研究方法和結果,藉此推動資本主義逐漸實現。因此,我認為在精神醫學與相關領域使用的當代主流科學典範是由高爾頓創造的,而不是許多精神科歷史中常認為的克雷佩林。
意識形態的偏誤,源自於資本主義和帝國制英國的物質關係,接下來我們會看到,直至今日,這些偏誤一直都在透過高爾頓的典範,引導有關神經多樣性的科學知識產出、社會大眾理解、政策與臨床醫療行為。即使舊帝國秩序的其他重要層面已瓦解,但神經多樣性的概念仍沒有改變。正是這種以科學、行政、文化和法律的強制性所組成的新機制,創造出了常態帝國。在大英帝國崩解後許久,帝國的許多階級與權力關係仍透過這些新機制持續維持、重現與擴張,這些新機制不但存活了下來,更隨著資本主義持續擴張,變成更加強大的霸權。因此,關鍵問題不單是病理學典範,還包括資本主義邏輯和病理學典範如何彼此強化,使得神經多樣性沒有機會解放。唯有改變深層體制,才能使神經多樣性獲得自由。
我的目標不是針對政策提出建議或制訂政治策略。我的目標是幫助讀者清楚瞭解根本的問題,我認為這個問題比病理學典範更深、更古老也更狡猾。釐清這個問題只是第一步,我們還需要花更多時間一起努力,才能繼續和常態帝國戰鬥,所謂的常態帝國,就是病理學典範背後的支撐力,也是維持病理學典範的必要機制。我們必須理解這種典範和這種宏觀機制的相互關係,以及這種典範和資本主義生產模式的基礎配置之間的相互關係,唯有如此,我們才能清楚瞭解我們得怎麼做,才能達到神經多樣性的自由解放。
值得強調的是,我也因為目前的政治狀態而寫下一些具有急迫性的內容。在過去幾年間,隨著神經多樣性的行動主義快速成長,我們不但看到神經多樣性倡議者使用的詞彙、概念與建議,開始出現在臨床醫師和政治家的口中(他們利用神經多樣性來維持現狀),也會看到新出現的各種多樣性包容顧問多不勝數,他們收取越來越多錢和企業協商合作,而後企業便開始把神經多樣者視為一種新資源,可以在開採後獲得生產率。我們可以在這時注意到,我所謂的「神經柴契爾主義」(neuro-Thatcherism)正在興起,資本主義甚至徹底反轉了那些想抵抗資本主義有害影響的行動,把那些行動轉變成新機會,將利潤與生產率最大化。在這種情況下,儘管新行動似乎正逐漸獲得越來越多的權力,但事實上,這種新行動的解放潛力正逐漸消失。
在我們逐漸邁向二十世紀末的同時,反精神醫學運動又再次流行了起來。反精神醫學運動的傳統思想和我的分析相反,這種思想認為核心問題在於精神醫學本身,與精神醫學相信的「心理疾病」概念。這個論點源自右派自由主義者湯瑪士.薩茲(Thomas Szasz),儘管並非所有反精神醫學的醫師都支持這個論點,但這或許是能替代主流精神醫學的各個論點中最有影響力的一種。
最重要的是,雖然我的分析可能在表面上看來和薩茲有許多重疊之處,但我徹底否定他們認為自閉症、ADHD等狀態並不是「真正」障礙的概念。我也強烈否定薩茲流派認為心理疾病是一種「迷思」(myth)的說法。儘管我對主流精神醫學典範的基礎和影響力確實有許多批評,不過我批評的重點在於:人們是如何把健康的概念與基準常態以及生產率混為一談,還有在資本主義的物質關係中,障礙與疾病如何出現具體的成長。這並不代表我拒絕承認心理疾病或障礙等狀態。正如我們將會在本書看到的,事實上,我認為反精神醫學是問題的一部分,而不是解決之道。這是因為,儘管反精神醫學和病理學典範在表面上看起來截然不同,但事實上,反精神醫學並沒有抵制病理學典範的邏輯與基準常態的大範圍機制,反而加強了它們。
相對地,我在探尋神經多樣性運動的崛起時,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綜合了重要的神經多樣性理論學家茱蒂.辛格和尼克.沃克的研究。這件事至關重要,我因而得以清楚說明人們尚未釐清的資本主義衝突,展現了神經柴契爾主義的徒勞無功。在這之中最重要的是,無論我們和神經典型的距離是遠是近,我們都越來越接近神經基準常態的雙重束縛,每個人都因此陷入更艱難的困境中。在人類這個物種中,許多目前無法應用的神經認知多樣性都受到無能力化、剝奪價值與歧視;而能夠被使用的那些多樣性則受到殘忍的剝削,導致健康狀態不佳。我認為,無論是哪種精神認知狀態的人,他的心靈和自我都會因為資本主義製造出來的精神階級而逐漸疏離。繼續這樣下去,我們將會陷入「所有人都生病」或「全都成為障礙人士」的狀況,又或者至少陷入「多數人都難以維持身心健康」的狀況。根據這個觀點,壓迫神經多樣者的並不是神經典型者,而是資本主義者的優勢地位,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種優勢地位會同時創造並傷害神經典型者和神經多樣者,只不過每個人被創造與傷害的方式,會因為自身距離基準常態的遠近而有些微不同。
我希望能指出的其中一個觀點是,儘管資本主義社會允許社會階級出現一定程度的流動性,但這並不代表優勢地位徹底消失了,優勢地位只是稍微偏向神經多樣性罷了。我認為,這打破了資本主義的最後一個承諾,也就是幫助我們實踐菁英領導制度(meritocracy),在這種制度下,自由個體的價值取決於美德與工作的努力程度,而非取決於繼承的地位。
菁英領導制度在國家層面與全球層面上都沒有實現,國家中的社會階級仍大幅限制了個人的經濟狀況,而北方國家的有錢人,依靠的正是南方國家中相對貧困的人。除此之外,我認為即使資本主義確實帶來了有限的進步,使社會階級的流動性增加,但相對於資本日益增加的認知需求,我們也只是把比較傳統形態的地位優勢,轉換成神經典型的地位優勢罷了。因此,在資本主義之下,自由解放的機會非常有限,而且這種自由解放只是依據我們的階級位置,給予不同形式的地位優勢與異化。我認為這個世界正是因此需要更基進的神經多樣性政治,直接反抗常態帝國。
【摘文三】
神經多樣性運動
一九九七年六月,一位正在就讀兼讀制社會學位的年輕女子在《紐約時報》上讀到一篇文章,作者是記者哈維.布盧姆(Harvey Blume),標題為〈自閉症者在網際空間中連結〉。這篇文章立刻引起茱蒂.辛格的注意。布盧姆寫道,有鑑於近年來網路的可用性越來越廣,「許多美國的自閉症者都開始進行這個症候群本應阻礙他們做的事:溝通」。他們會這麼做,其實並不只是因為在線上建立連結比面對面容易。布盧姆詳細指出,除此之外,有越來越多「自閉症者不願意、也無法放棄他們自己的習慣。取而代之的是,他們現在正在提出嶄新的社會協議,將神經多元論視為重點。」也就是說,他們不是因為壓力而表現得更貼近「常態」,而是反對這麼做,並在網路上建立連結的過程中反抗「自閉症需要被修正」這一點。
當時辛格在澳洲的雪梨科技大學修習社會學。辛格先是從醫學系休學,再轉而就讀社會學,進一步瞭解她關注的各種政治。她關注的其中一個主題是障礙政治(politics of disability),辛格在讀到布盧姆的文章之前,就已經覺得自己位於自閉症光譜中了――自閉症光譜是當時人們知之甚少的症候群,主要和社交問題、溝通問題、受限的興趣、受限的習慣有關。她發現在自己的生活中,有許多問題和自閉症者的問題相呼應,當時她已經加入了許多不同的線上自閉症團體,認識了其他自閉症者。此外,辛格也已經開始透過社會學研究障礙的視角來思考自閉症,將障礙視為一種社會問題,而非個體問題。
辛格之所以會受到布盧姆的文章所吸引,除了因為這些經驗之外,也因為她對於布盧姆所描述的「神經多元論」感同身受,也能理解在這個神經典型的世界中拒絕放棄自閉症習慣的心情。其中最重要的是,辛格對自閉症反抗性格的理解,是基於她身為流亡猶太人的經驗。也就是說,她屬於拒絕同化的外來者團體――而他們也因此付出了代價。畢竟,辛格自己就是大屠殺倖存者的女兒,她母親在二戰後搬到了澳洲。儘管辛格是在澳洲出生長大的,但她仍覺得自己在這裡就像是個外來者。身為流亡者的傳承與經驗,使辛格能深入體會神經多元論的新政治,以及在面對巨大的社會壓力時,拒絕放棄自閉症習慣的想法。
因此,辛格在讀了布盧姆的文章後,迅速聯絡上他,成為「自閉症光譜的獨立生活」這個新社群的成員之一。她不但在一年內融入這個社群,還提出「神經多樣性」這個更簡潔的概念,提供歷史上首次出現的持續性社會學分析,將這些想法定位於障礙研究領域中。這樣的經驗讓她得以在一九九九年的書籍章節中呼籲眾人理解「神經多樣性的政治」,再加上布盧姆的報導,推動了這個自閉症社運人士的先驅社群,點燃了神經多樣性運動的跨國火花。
辛格在這項重要的研究中指出,人們應該把神經多樣性視為「原本已熟悉的階級、性別、種族等政治分類的新增項目」。她將自閉症概念化成一種人們尚未認知到的集合(intersection),藉此設想出一種新的民權運動,能夠引導這個社會發展成她所謂的「生態」社會。對辛格來說,這個社會看待神經多樣性的方式,應該要像是生態環境保護者看待生物多樣性那樣,因此,這個社會應該要改變社交與物質的條件,滿足並保護自閉症者的生活方式。這些改變,包括在政策制訂與行動方面變得更包容,並建立合適的認知位置,藉此協助社會培養自閉症者的繁榮發展與包容能力。這和主流的社會組織方式截然不同,主流方式是隔離障礙者,並對自閉症者例行性地施加壓力,要他們更接近「常態」。這場運動的核心思想是由無數行動主義者和活動家共同發展出來的,而辛格的貢獻是將這些新興的想法,根植在障礙研究發展出來的理論體系中。在這之後,辛格所建立的理論基礎引導了往後的運動走向、戰術與展望。
障礙理論
若要瞭解這些想法源自何處,我們必須回到更久之前。事實上,我們要一路回到一九六八年,當時三十歲的維克.芬克爾斯坦以難民的身分來到英國。芬克爾斯坦是政治活動家,曾因為參與反種族隔離運動而遭到監禁。他也因為疑似是共產主義者,而被禁止出入南非五年。不過,監禁他的政府當局沒有意識到,他們對待他的方式,卻幫助他發展出了足以改變世界的想法。
對政府來說,芬克爾斯坦帶來的問題在於,他在十六歲的一次意外摔斷了頸部,從此之後就必須使用輪椅。這也就代表政府為了監禁他,就必須順應他的身體損傷而做出各種調整。由於政府在適合的狀況下能找到方法順應他的障礙,所以芬克爾斯坦開始思考,社會是否應該施加壓力讓政府可以――以及應該――在預設的狀況下做出這些調整。在這十八個月的拘留期間,他也注意到他因身體障礙而被隔離的經驗,以及他反抗的種族隔離之間,其實有更多相似之處。他因此開始探索歷史的過往力量,是如何導致了障礙隔離這樣的結果,以及改變這種結果的可能性。
一九七○年代,肢體障礙者反隔離協會(Union of Physically Impaired Against Segregation,簡稱UPIAS)正式化了這些想法。該協會是由一群支持馬克思主義的基進障礙社運人士所組成,過去曾在倫敦的一間酒吧見面。這個團體是芬克爾斯坦和另一位身心障礙社運人士保羅.亨特(Paul Hunt)在一九七二年共同創辦的,亨特從小就在英國各地被拘留過。他們兩人結合了彼此的過往經驗,意識到他們的障礙其實是物質社會因素的產物,而不只是身體的問題。他們在一九七五年出版的文件《身心障礙基礎原則》中闡明了這種想法,並在其中提出了一個概念,被往後的人稱為障礙的「社會模式」(social model)。
他們將這個新模式拿去和個人模式以及醫學模式做比較。醫學模式認為障礙源自損傷與功能異常。也就是說,如果一個人的身體出了問題,就會導致這個人沒有能力做到普通的事。依據這樣的思想――當時這種想法仍屬於霸權――障礙是一種會影響個體的生理悲劇。在許多案例中,人們都認為障礙的本質會使人沒有機會過上充實的理想人生。個體能指望的最好結果就是獲得醫學治療,減少障礙對日常生活的影響。
UPIAS幾乎拒絕了所有和這個傳統框架有關的想法。他們的核心理論運動是拒絕接受「身體損傷」與「障礙失能」之間的因果關聯。相反地,肢體障礙反隔離協會認為:
是這個社會使身體損傷者遇到障礙。是因為我們遭受了不必要的隔離,被排除在完整的社會參與之外,所以障礙才會被強制施加在我們的身體損傷上。
依據這個觀點,是物質環境和社會的結構與行動(例如沒有通往建築內的緩坡)將障礙「強制施加」在那些身體損傷者身上的。他們承認損傷真實存在,也是身體的一部分,但他們拒絕預設損傷代表了障礙就是個體的悲劇。從這個角度來看,障礙者遭遇的主要問題是邊緣化和壓迫,而不只是個人醫療。換句話說,障礙――或者至少就肢體障礙而言(UPIAS將認知障礙排除在他們的論述之外)――不再是個體醫療問題,而是與整個社會環境以及物質環境有關的問題。
雖然這種社會模式通常可以追溯到UPIAS,但值得注意的是,其他基進群體也在差不多的時間點發展出了類似的觀點。舉例來說,以薩米.沙爾克(Sami Schalk)所說的,美國的黑人權力與馬克思列寧主義組織――黑豹(Black Panthers)也開始認為,障礙者解放與集體解放有密切關聯。因此,到了一九七○年代晚期,黑豹開始支持基進障礙行動主義。他們「迅速採用了障礙者提出的社會模式,這是因為這種模式符合他們對於種族與階級壓迫的理解,這種壓迫源自更大規模的社會偏見與失敗」。
其他組織開發的社會模式和類似的分析法,也都成了障礙人士推行運動的理論基礎,該運動在剛開始數十年間主要聚焦在肢體障礙上。他們把焦點放在「態度、身體結構、社會期望與社會支持不足」是如何抑制了障礙者的運作能力與發展,這場運動因此而在法律和社會方面獲得意義重大的認可,也在去除障礙者的阻礙與隔離時取得顯著的成果。這場大規模運動正是為什麼如今在英國與其他國家中,建築物通常都會設置障礙者停車位、無障礙洗手間、坡道等。英國、美國與其他國家都因為這場運動,而在法律上為障礙者的權利帶來了重大益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