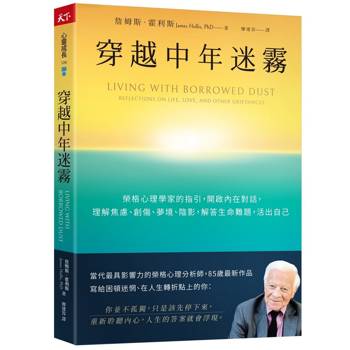◆序言 與靈魂展開深層對話
過去五年裡,我自願選擇進行人工膝關節與髖關節置換手術,也接受了非做不可的癌症治療,包括手術、放射治療與化療,深部靜脈栓塞手術(DVT),還有兩次重大脊椎手術(因為脊椎骨溶解並骨折,可能是癌症治療導致的後果)。此外,我的骨盆現在是靠螺栓固定在脊椎上。因此,委婉的說法是,我近日遭疼痛與各種治療纏身,尤其我在出院之後,依然繼續從事心理分析的工作。由於我的醫療預後充滿變數,最近我和太太搬到退休社區居住。我在這一切的過程中發現,比起不確定的身體狀況,我把更多心思放在心理分析的工作上。這個發現令我感到驚訝,但我只能歸結為,榮格的理論與心理動力學持續賦予靈魂生命力、引導與滋養,至少對我的靈魂而言是如此。若不是這樣,我現在可能每天以集郵或是編織杯墊度日,或者大概早已離世。
雖然分析心理學並非現代心理治療方法的主流,相對來說,從事這個領域的治療師人數非常稀少,我倒是從來不曾為此感到困擾。假如我們為自己和個案做的是正確的事,雖然我們的文化非常看重並聚焦於症狀的緩解,而忽略意義的問題(我認為這是精神病理學的根源),但我相信更深層的工作會給予我們應得的補償。當我們與自己的靈魂有隔閡,會產生一種可怕的苦難,必然會外溢到外在世界、人際關係、下一代,並且擴散至人類社會。
榮格指出,精神官能症是一種尚未找到其意義的痛苦。當然,他並沒有排除痛苦的存在,但他確實提醒我們,去體會受苦過程的意義,能幫助我們度過艱難時期。榮格的治療模式並不輕鬆,但回報也非常巨大。我不只一次對個案說,我們的合作不是為了治療你,因為你並非是一種疾病。我們的合作召喚我們進入一種更深層的對話,這種對話會使你的人生變得更有趣,並且很可能引領你前往你原本沒有預期造訪的靈性風景,但每處風景都會為你的生命旅程帶來更豐富、更深沉的色彩。
★醫治我們的心靈
當我回顧早年職涯,當時我還是人文學科的教授,在那段時間開始教授榮格的觀念,因為我認為他對象徵形成的理解非常有啟發性。當我在中年時因為憂鬱而接受了第一次心理分析時,我的內在某個部分意識到,自己對榮格概念的理解非常淺薄。如果那些概念沒有化為具體,使我們對自己的真實生活進行反思,那就只是英國哲學家懷海德(Alfred North Whitehead)所稱的「類別的蒼白之舞」。
我曾在州立精神病院從事兼職工作三年,以便完成訓練。由於我在隔離病房工作,院方要求我打領帶,好讓人辨識我是醫院員工,並在下班後可以離開醫院。我在那家醫院體驗到的人類苦難,其程度深重的滲入我生命的各個層面。我從小體弱多病,長大後對醫院既愛且怕。當我在醫院工作時,負責指導我的資深醫生曾帶我去看屍體解剖。接下來好幾天,我的腦海中都會浮現那具腫脹的屍體,我意識到,我的心靈不知怎地將我重新帶回了那個我年少時曾逃離的世界。我將這個體會分享給蘇黎士的心理分析師,他簡短回應:「當你面對了自己的恐懼之後,其他人的恐懼就不會那麼難以處理了。」
在那之後不久,我協助一位醫師縫合某位病人的臉,他因為遭人拿椅子砸中而受傷。我不禁對心靈的智慧與自主性感到佩服,它悄然將我拉回以前逃離的那個世界,因為我逃進了那具有吸引力的心智避難所之中。儘管聽起來難以置信,但我的心靈藉由把我帶回創傷之處,來尋求醫治。如今的我已經有足夠的力量承擔創傷,並找到它的意義,這是我童年時的自我無法做到的。我們知道,感到恐懼是一件很自然且正常的事,但受到恐懼宰制的人生則是另一回事。如今我將那段醫院的實習視為一次真正個人的體會,引領我個人進入心靈的醫治意圖。
就和其他接受分析的人一樣,我學會尊重夢境與積極想像的世界,並開始提出這樣的問題:「這個選擇是服務內在的哪一種需求?」這個問題不難,但它開啟了鑑識性的深層探究。無意識的問題在於,它存在無意識中。
近日我住院時,一位護士問我從事什麼工作。
「那跟一般心理學有什麼不同?」她問。
「嗯,首先,我們試圖與無意識展開對話。」
她思索了一會兒,然後回答,「哦,我懂了。你工作的對象是陷入昏迷的人。」我愈是反思她的話,愈覺得很有道理。因為我們每個人在大多數時候,其實是處於意識的變動狀態。也就是說,我們受到恐懼驅使,以慣性與反射性的行為,去回應人生的挑戰,而且對於潛藏在表層之下的龐大心理劇,幾乎毫無覺察。
在過去半個世紀中,我致力於透過教學、寫作與私人執業等形式,將分析心理學的洞察、態度與實踐,盡可能傳遞給最多的人。對我來說,與其說是一份工作,不如說是一種「召喚」(calling)。如果我認為某件事對我有益,為什麼不與他人分享呢?因此,我觀察到,許多人渴望探索心靈的生活,並願意面對試煉,也願意迎接改變。即使大眾文化本身就是一套規模龐大多樣的分心機制,使我們遠離心靈的生活,仍然有許多人知道,在光鮮亮麗的喧鬧中,似乎少了某種極其重要的東西。在喧囂與表象之下,我們每個人靈魂深處有某個東西正在吶喊,懷著期待的張力產生共鳴。儘管我們可能因為分心而忽略了這個召喚,或是無法理會它的懇求,靈魂仍然持續要求我們去注意它。這些召喚時刻,會透過我們身體和心理的症狀、夢境,甚至是在輾轉難眠的失眠之夜來到。
◆探索人生的重要課題
在接下來的章節中,我將檢視與評論,人們為何總是想要從外界尋找「應該做什麼」、「應該成為什麼樣的人」的答案,例如應該如何得到「幸福」。但即使如此,我們內在的某個部分卻更清楚明白,拒絕配合。我希望在接下來的篇章指出一些工具與方法,讓我們能夠與內在靈魂展開更深層的對話。藉由檢視集體文化的狀況如何影響我們(有時是支持我們的旅程,但更常見的是製造更多噪音,使我們聽不見內在的召喚),我們才能開始在各自獨立、偶有交會的生命旅程中成長。
過去五年裡,我自願選擇進行人工膝關節與髖關節置換手術,也接受了非做不可的癌症治療,包括手術、放射治療與化療,深部靜脈栓塞手術(DVT),還有兩次重大脊椎手術(因為脊椎骨溶解並骨折,可能是癌症治療導致的後果)。此外,我的骨盆現在是靠螺栓固定在脊椎上。因此,委婉的說法是,我近日遭疼痛與各種治療纏身,尤其我在出院之後,依然繼續從事心理分析的工作。由於我的醫療預後充滿變數,最近我和太太搬到退休社區居住。我在這一切的過程中發現,比起不確定的身體狀況,我把更多心思放在心理分析的工作上。這個發現令我感到驚訝,但我只能歸結為,榮格的理論與心理動力學持續賦予靈魂生命力、引導與滋養,至少對我的靈魂而言是如此。若不是這樣,我現在可能每天以集郵或是編織杯墊度日,或者大概早已離世。
雖然分析心理學並非現代心理治療方法的主流,相對來說,從事這個領域的治療師人數非常稀少,我倒是從來不曾為此感到困擾。假如我們為自己和個案做的是正確的事,雖然我們的文化非常看重並聚焦於症狀的緩解,而忽略意義的問題(我認為這是精神病理學的根源),但我相信更深層的工作會給予我們應得的補償。當我們與自己的靈魂有隔閡,會產生一種可怕的苦難,必然會外溢到外在世界、人際關係、下一代,並且擴散至人類社會。
榮格指出,精神官能症是一種尚未找到其意義的痛苦。當然,他並沒有排除痛苦的存在,但他確實提醒我們,去體會受苦過程的意義,能幫助我們度過艱難時期。榮格的治療模式並不輕鬆,但回報也非常巨大。我不只一次對個案說,我們的合作不是為了治療你,因為你並非是一種疾病。我們的合作召喚我們進入一種更深層的對話,這種對話會使你的人生變得更有趣,並且很可能引領你前往你原本沒有預期造訪的靈性風景,但每處風景都會為你的生命旅程帶來更豐富、更深沉的色彩。
★醫治我們的心靈
當我回顧早年職涯,當時我還是人文學科的教授,在那段時間開始教授榮格的觀念,因為我認為他對象徵形成的理解非常有啟發性。當我在中年時因為憂鬱而接受了第一次心理分析時,我的內在某個部分意識到,自己對榮格概念的理解非常淺薄。如果那些概念沒有化為具體,使我們對自己的真實生活進行反思,那就只是英國哲學家懷海德(Alfred North Whitehead)所稱的「類別的蒼白之舞」。
我曾在州立精神病院從事兼職工作三年,以便完成訓練。由於我在隔離病房工作,院方要求我打領帶,好讓人辨識我是醫院員工,並在下班後可以離開醫院。我在那家醫院體驗到的人類苦難,其程度深重的滲入我生命的各個層面。我從小體弱多病,長大後對醫院既愛且怕。當我在醫院工作時,負責指導我的資深醫生曾帶我去看屍體解剖。接下來好幾天,我的腦海中都會浮現那具腫脹的屍體,我意識到,我的心靈不知怎地將我重新帶回了那個我年少時曾逃離的世界。我將這個體會分享給蘇黎士的心理分析師,他簡短回應:「當你面對了自己的恐懼之後,其他人的恐懼就不會那麼難以處理了。」
在那之後不久,我協助一位醫師縫合某位病人的臉,他因為遭人拿椅子砸中而受傷。我不禁對心靈的智慧與自主性感到佩服,它悄然將我拉回以前逃離的那個世界,因為我逃進了那具有吸引力的心智避難所之中。儘管聽起來難以置信,但我的心靈藉由把我帶回創傷之處,來尋求醫治。如今的我已經有足夠的力量承擔創傷,並找到它的意義,這是我童年時的自我無法做到的。我們知道,感到恐懼是一件很自然且正常的事,但受到恐懼宰制的人生則是另一回事。如今我將那段醫院的實習視為一次真正個人的體會,引領我個人進入心靈的醫治意圖。
就和其他接受分析的人一樣,我學會尊重夢境與積極想像的世界,並開始提出這樣的問題:「這個選擇是服務內在的哪一種需求?」這個問題不難,但它開啟了鑑識性的深層探究。無意識的問題在於,它存在無意識中。
近日我住院時,一位護士問我從事什麼工作。
「那跟一般心理學有什麼不同?」她問。
「嗯,首先,我們試圖與無意識展開對話。」
她思索了一會兒,然後回答,「哦,我懂了。你工作的對象是陷入昏迷的人。」我愈是反思她的話,愈覺得很有道理。因為我們每個人在大多數時候,其實是處於意識的變動狀態。也就是說,我們受到恐懼驅使,以慣性與反射性的行為,去回應人生的挑戰,而且對於潛藏在表層之下的龐大心理劇,幾乎毫無覺察。
在過去半個世紀中,我致力於透過教學、寫作與私人執業等形式,將分析心理學的洞察、態度與實踐,盡可能傳遞給最多的人。對我來說,與其說是一份工作,不如說是一種「召喚」(calling)。如果我認為某件事對我有益,為什麼不與他人分享呢?因此,我觀察到,許多人渴望探索心靈的生活,並願意面對試煉,也願意迎接改變。即使大眾文化本身就是一套規模龐大多樣的分心機制,使我們遠離心靈的生活,仍然有許多人知道,在光鮮亮麗的喧鬧中,似乎少了某種極其重要的東西。在喧囂與表象之下,我們每個人靈魂深處有某個東西正在吶喊,懷著期待的張力產生共鳴。儘管我們可能因為分心而忽略了這個召喚,或是無法理會它的懇求,靈魂仍然持續要求我們去注意它。這些召喚時刻,會透過我們身體和心理的症狀、夢境,甚至是在輾轉難眠的失眠之夜來到。
◆探索人生的重要課題
在接下來的章節中,我將檢視與評論,人們為何總是想要從外界尋找「應該做什麼」、「應該成為什麼樣的人」的答案,例如應該如何得到「幸福」。但即使如此,我們內在的某個部分卻更清楚明白,拒絕配合。我希望在接下來的篇章指出一些工具與方法,讓我們能夠與內在靈魂展開更深層的對話。藉由檢視集體文化的狀況如何影響我們(有時是支持我們的旅程,但更常見的是製造更多噪音,使我們聽不見內在的召喚),我們才能開始在各自獨立、偶有交會的生命旅程中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