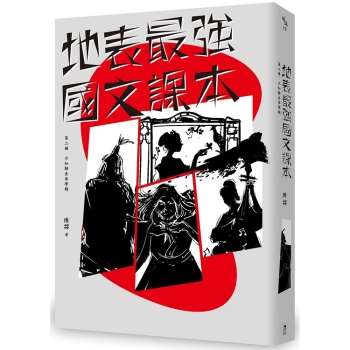第六課:兵車行/杜甫
【題解】
〈兵車行〉是杜甫在安史之亂前的作品。最初決定要將杜甫選進第二冊的時候,為了要選哪一首作品我猶豫了很久。要談杜甫這個人,有其易處亦有其難處。杜甫是大家耳熟能詳的詩人,代表的作品俯拾即是,這是其容易處;然而杜甫的作品開展的面向也很廣,有著不同的特色,這則是讓我遲遲難以下決定的原因。
我所思考的問題是:杜甫在過去的教材中一直以一個「社會寫實詩人」的形象出現,但課本裡面所選的詩,多半不是他最具代表性的社會寫實詩。另一方面,如前面所提的,杜甫絕對不只是一個社會寫實詩人,他在後代得到的評價之高,作詩而能稱聖,也早已遠遠超過社會詩人這個形象所包含的一切了。
這是我在選擇杜甫作品時面臨的難題,特別選〈兵車行〉這首詩,目的也是為了回應上述考量。
這首詩中有對社會現實的揭露,也有對時局的批判。這些內容在傳統上很受重視,被看作是杜甫代表特色之一,然而,多數被注意到的作品,都是安史之亂中後被創作出來的。也就是說,若試著點出〈兵車行〉的社會意義,至少可以回去檢視某些既有的認知:杜甫並不是在經歷了安史之亂後才開始寫作社會詩,在這之前,他便以詩歌批判社會了。
再者,〈兵車行〉屬於「歌行體」,「歌行體」在過去教材中很少被特別強調,介紹的篇章也不多。然而,這個體裁的詩歌在唐代的創作數量相當可觀,是盛唐詩的主流體裁之一。
「歌行體」源自樂府,「行」是樂府常見的題名,其他如某某歌、某某吟、某某曲,乃至樂、弄、操、引等,凡是詩歌的題目出現這些字眼,或多或少都與音樂有關,或是詩人刻意以樂府舊題來寫作。
盛唐擅長寫歌行體的詩人很多,這類詩歌,多半以七言為主,我們可以將其當作篇幅略長的七言詩來看。歌行體的流動性、韻律感比較強,很常被拿來處理一些格局、畫面較為寬闊的題材。與近體詩不同的,歌行體沒有那麼多的格律限制,對於創作風格較奔放自由的詩人來說,是很適合的體裁。比如著名的邊塞詩人岑參、詩仙李白,留下的歌行體質量都很可觀。
杜甫入長安時正值天寶年間,是唐王朝的盛世,長安作為首都,氣象繁華、民生富庶自不在話下。杜甫晚年回憶那時候的京城,也曾描述了「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等豐衣足食的場景。當時的長安不僅繁榮,更是文化、音樂的中心,歌行體流動的韻律感,適合搭配樂器演奏的質性,十分受宮廷歡迎。玄宗皇帝也好此道,除了原本流傳的舊曲外,更命人創作新曲,足見樂府歌行的流行。
創作歌詞的士人們,新作的詩歌若是能夠取代舊詞,更是十分榮耀的事。活躍於民間的詩人,也可能因為作品能見度高而受到官方重視,經過「采詩」(官方自民間搜羅作品)而入宮廷,披之管絃。
杜甫在長安旅居時,必然受到這樣的風氣影響,因而也跟著寫起了歌行體。而這段期間,正是杜甫創作歌行體數量直線上升的時期。只不過,歌行體在那個時代的流行,或多或少與當時的音樂、娛樂文化有關,多數歌行體創作展現的是盛世光鮮亮麗的一面,有獨特的生命力,甚至有作者狂放奔騰的氣息,難掩浪漫色彩。這樣的傾向與屬性,讓這類型的詩歌與深刻、沉重的文學有一段距離。由此可見,杜甫的〈兵車行〉在狂傲浪漫的歌行體中,其實是相當特殊的存在。
〈兵車行〉作於天寶十一年,杜甫四十一歲。這年十一月,權相李林甫過世,繼任的楊國忠掌權,朝廷弊病已多,卻又頻頻對外用兵。前一年朝廷派兵征南詔,南詔位於唐帝國西南邊,那時版圖已擴張至今天的雲貴一帶。唐帝國的軍隊在這場戰役中是戰敗的,但楊國忠當時掌握了權勢,隻手遮天,竟向中央報捷,一方面又向民間徵兵,直接在道上捉捕人民以補充兵額,搞得民不聊生。
根據考證,杜甫〈兵車行〉中前半所描述的,就是當時徵兵的場景,且應為親眼所見。
〈兵車行〉可說是杜甫生命中第一首社會詩,第一次為了民間疾苦發聲。在這之前,大部分的歌行體不會處理這類題材,或者說,盛唐詩很少見這樣的內容。無可否認的,這是杜甫開創的詩歌價值。
傳統用以區分唐詩的四期說(初唐、盛唐、中唐、晚唐),是後人分析唐詩的創作情形採用的一個粗略分類。唐詩的階段還有很多分類方式,只是四期說最多人使用,也成為我們現在看待唐代詩歌的主流。四期說中的盛唐與中唐分界,就是安史之亂,因此,杜甫可說是橫跨盛唐與中唐時代最重要的詩人。
安史之亂前杜甫品雖然也有佳作、名作(如著名的〈飲中八仙歌〉),但畢竟沒有那麼大的影響力。安史之亂後才是他創作能量真正爆發之時,被後人稱道的多數作品,都是這時期寫出來的。
故〈兵車行〉在杜甫的創作歷程中是有指標性意義的,它開啟了杜甫的社會寫實之路。自時代言,他是盛唐最末尾的聲音;自內容言,他是中唐新樂府的先驅。
看似強盛的帝國,內部早已千瘡百孔,這是杜甫用詩歌紀錄下來,血淋淋的事實。杜甫被稱為詩史,而中國歷代真正被肯定的「史」,必然有其諷喻,需要對時代發出批評、怒吼,或是沉痛的控訴。〈兵車行〉徹底反映了這一點,也讓我們看見杜甫的思索與關懷,因此這首詩與其後受到戰亂刺激的社會詩相比,未有絲毫遜色。
還有件事值得一提。〈兵車行〉直陳了當時徵兵的民間慘況,也稍稍抨擊了朝廷的政策,詩歌後半更不針對個別事件而發,進而點出了許多長久以來的問題。這看起來是杜甫詩人風骨的展現,但也可能是一種逃避。
詩裡面痛惜的,不只是一開始被強行徵召的人民,不只是一去不返的征夫,更包含了田園荒蕪,繳不起租稅的農民。清代的錢謙益就指出,杜甫這首詩不明寫征南詔,後面卻寫山東、關西,寫青海等處,是對當時權勢正盛的楊國忠有所顧忌,才不直接抨擊當時出兵西南之舉。
這樣的說法有其道理,但也不必自這一點批判杜甫的軟弱。因為這首詩反映的,是早已問題重重的社會,是一個即將走向衰敗的帝國。詩中景象讀來固然沉痛,但對於當時在各個角落不斷發生的諸多苦難來說,不過是冰山一角。
杜甫從來都不是一個會直接針砭時政的改革派,他的詩歌只著重於陳述現實黑暗,功能也只能是消極的。但這也許更符合一個詩人真實能及的一切,對於荒誕現實,他什麼也不能做,什麼也改變不了。
詩人在文學史上開創的一切成就,正暴露了一個國家社稷的腐敗與不堪,詩歌成就愈高,時代的悲劇往往也愈深。
清代詩人趙翼曾言「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正好用以說明這一切。當時局變異,社會動盪之際,詩人的作品往往更撼動人心,也更能探觸文學藝術之高度,但這一切終歸是人間悲劇,是每個愛著世界的人所不樂見的。
詩人的作品愈偉大,他在那個時代就愈無力,杜甫即是這樣的典型。
這一課,是這本書最後一首詩歌。在第一冊我沒有選過詩歌,這一冊特意選了一些。詩歌的文字往往能開啟比文章還要多的畫面,美學上的可能也更多,然而那些真正令人感到震撼的詩作,背後的掙扎與無奈,似乎又都過於沉重了。
【題解】
〈兵車行〉是杜甫在安史之亂前的作品。最初決定要將杜甫選進第二冊的時候,為了要選哪一首作品我猶豫了很久。要談杜甫這個人,有其易處亦有其難處。杜甫是大家耳熟能詳的詩人,代表的作品俯拾即是,這是其容易處;然而杜甫的作品開展的面向也很廣,有著不同的特色,這則是讓我遲遲難以下決定的原因。
我所思考的問題是:杜甫在過去的教材中一直以一個「社會寫實詩人」的形象出現,但課本裡面所選的詩,多半不是他最具代表性的社會寫實詩。另一方面,如前面所提的,杜甫絕對不只是一個社會寫實詩人,他在後代得到的評價之高,作詩而能稱聖,也早已遠遠超過社會詩人這個形象所包含的一切了。
這是我在選擇杜甫作品時面臨的難題,特別選〈兵車行〉這首詩,目的也是為了回應上述考量。
這首詩中有對社會現實的揭露,也有對時局的批判。這些內容在傳統上很受重視,被看作是杜甫代表特色之一,然而,多數被注意到的作品,都是安史之亂中後被創作出來的。也就是說,若試著點出〈兵車行〉的社會意義,至少可以回去檢視某些既有的認知:杜甫並不是在經歷了安史之亂後才開始寫作社會詩,在這之前,他便以詩歌批判社會了。
再者,〈兵車行〉屬於「歌行體」,「歌行體」在過去教材中很少被特別強調,介紹的篇章也不多。然而,這個體裁的詩歌在唐代的創作數量相當可觀,是盛唐詩的主流體裁之一。
「歌行體」源自樂府,「行」是樂府常見的題名,其他如某某歌、某某吟、某某曲,乃至樂、弄、操、引等,凡是詩歌的題目出現這些字眼,或多或少都與音樂有關,或是詩人刻意以樂府舊題來寫作。
盛唐擅長寫歌行體的詩人很多,這類詩歌,多半以七言為主,我們可以將其當作篇幅略長的七言詩來看。歌行體的流動性、韻律感比較強,很常被拿來處理一些格局、畫面較為寬闊的題材。與近體詩不同的,歌行體沒有那麼多的格律限制,對於創作風格較奔放自由的詩人來說,是很適合的體裁。比如著名的邊塞詩人岑參、詩仙李白,留下的歌行體質量都很可觀。
杜甫入長安時正值天寶年間,是唐王朝的盛世,長安作為首都,氣象繁華、民生富庶自不在話下。杜甫晚年回憶那時候的京城,也曾描述了「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等豐衣足食的場景。當時的長安不僅繁榮,更是文化、音樂的中心,歌行體流動的韻律感,適合搭配樂器演奏的質性,十分受宮廷歡迎。玄宗皇帝也好此道,除了原本流傳的舊曲外,更命人創作新曲,足見樂府歌行的流行。
創作歌詞的士人們,新作的詩歌若是能夠取代舊詞,更是十分榮耀的事。活躍於民間的詩人,也可能因為作品能見度高而受到官方重視,經過「采詩」(官方自民間搜羅作品)而入宮廷,披之管絃。
杜甫在長安旅居時,必然受到這樣的風氣影響,因而也跟著寫起了歌行體。而這段期間,正是杜甫創作歌行體數量直線上升的時期。只不過,歌行體在那個時代的流行,或多或少與當時的音樂、娛樂文化有關,多數歌行體創作展現的是盛世光鮮亮麗的一面,有獨特的生命力,甚至有作者狂放奔騰的氣息,難掩浪漫色彩。這樣的傾向與屬性,讓這類型的詩歌與深刻、沉重的文學有一段距離。由此可見,杜甫的〈兵車行〉在狂傲浪漫的歌行體中,其實是相當特殊的存在。
〈兵車行〉作於天寶十一年,杜甫四十一歲。這年十一月,權相李林甫過世,繼任的楊國忠掌權,朝廷弊病已多,卻又頻頻對外用兵。前一年朝廷派兵征南詔,南詔位於唐帝國西南邊,那時版圖已擴張至今天的雲貴一帶。唐帝國的軍隊在這場戰役中是戰敗的,但楊國忠當時掌握了權勢,隻手遮天,竟向中央報捷,一方面又向民間徵兵,直接在道上捉捕人民以補充兵額,搞得民不聊生。
根據考證,杜甫〈兵車行〉中前半所描述的,就是當時徵兵的場景,且應為親眼所見。
〈兵車行〉可說是杜甫生命中第一首社會詩,第一次為了民間疾苦發聲。在這之前,大部分的歌行體不會處理這類題材,或者說,盛唐詩很少見這樣的內容。無可否認的,這是杜甫開創的詩歌價值。
傳統用以區分唐詩的四期說(初唐、盛唐、中唐、晚唐),是後人分析唐詩的創作情形採用的一個粗略分類。唐詩的階段還有很多分類方式,只是四期說最多人使用,也成為我們現在看待唐代詩歌的主流。四期說中的盛唐與中唐分界,就是安史之亂,因此,杜甫可說是橫跨盛唐與中唐時代最重要的詩人。
安史之亂前杜甫品雖然也有佳作、名作(如著名的〈飲中八仙歌〉),但畢竟沒有那麼大的影響力。安史之亂後才是他創作能量真正爆發之時,被後人稱道的多數作品,都是這時期寫出來的。
故〈兵車行〉在杜甫的創作歷程中是有指標性意義的,它開啟了杜甫的社會寫實之路。自時代言,他是盛唐最末尾的聲音;自內容言,他是中唐新樂府的先驅。
看似強盛的帝國,內部早已千瘡百孔,這是杜甫用詩歌紀錄下來,血淋淋的事實。杜甫被稱為詩史,而中國歷代真正被肯定的「史」,必然有其諷喻,需要對時代發出批評、怒吼,或是沉痛的控訴。〈兵車行〉徹底反映了這一點,也讓我們看見杜甫的思索與關懷,因此這首詩與其後受到戰亂刺激的社會詩相比,未有絲毫遜色。
還有件事值得一提。〈兵車行〉直陳了當時徵兵的民間慘況,也稍稍抨擊了朝廷的政策,詩歌後半更不針對個別事件而發,進而點出了許多長久以來的問題。這看起來是杜甫詩人風骨的展現,但也可能是一種逃避。
詩裡面痛惜的,不只是一開始被強行徵召的人民,不只是一去不返的征夫,更包含了田園荒蕪,繳不起租稅的農民。清代的錢謙益就指出,杜甫這首詩不明寫征南詔,後面卻寫山東、關西,寫青海等處,是對當時權勢正盛的楊國忠有所顧忌,才不直接抨擊當時出兵西南之舉。
這樣的說法有其道理,但也不必自這一點批判杜甫的軟弱。因為這首詩反映的,是早已問題重重的社會,是一個即將走向衰敗的帝國。詩中景象讀來固然沉痛,但對於當時在各個角落不斷發生的諸多苦難來說,不過是冰山一角。
杜甫從來都不是一個會直接針砭時政的改革派,他的詩歌只著重於陳述現實黑暗,功能也只能是消極的。但這也許更符合一個詩人真實能及的一切,對於荒誕現實,他什麼也不能做,什麼也改變不了。
詩人在文學史上開創的一切成就,正暴露了一個國家社稷的腐敗與不堪,詩歌成就愈高,時代的悲劇往往也愈深。
清代詩人趙翼曾言「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正好用以說明這一切。當時局變異,社會動盪之際,詩人的作品往往更撼動人心,也更能探觸文學藝術之高度,但這一切終歸是人間悲劇,是每個愛著世界的人所不樂見的。
詩人的作品愈偉大,他在那個時代就愈無力,杜甫即是這樣的典型。
這一課,是這本書最後一首詩歌。在第一冊我沒有選過詩歌,這一冊特意選了一些。詩歌的文字往往能開啟比文章還要多的畫面,美學上的可能也更多,然而那些真正令人感到震撼的詩作,背後的掙扎與無奈,似乎又都過於沉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