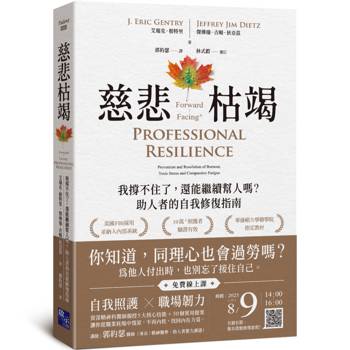當我們協助經歷倦怠的專業人士去理解,真正讓他們痛苦的並非外在環境,而是他們對環境的感知,在那一刻,希望便開始浮現。當引導他們認識到,他們並非被強制徵召的囚徒,而是擁有選擇如何回應自己工作的權利時,改變就會悄然發生。
當他們意識到:自己並非身處真正的危險之中,而只是「感知到」威脅時,便能開始調節自律神經系統,逐步中斷本能性的威脅反應。一旦這些調節技能得以培養並日漸熟練,專業人士將發現壓力逐漸減輕。隨著壓力降低,大腦新皮質功能(負責思考與理性判斷)將重新發揮作用,使他們得以發展出更成熟的職場感知,減少環境的「毒性」影響,並將控制感從外在環境(外控) 轉向內在賦能與韌力的培養(內控)。透過持續練習這些技能, 並融入專業韌力的原則,照護者終將為自己騰出空間,重新點燃對工作的使命感、熱情與喜悅。
核心概念在於:我們將控制感從外在環境(職場)轉移到內在(對職場的回應方式)。這種感知轉變的一個關鍵在於:我們如何重新看待職場中的各種責任。我們往往習慣把這些責任視為強加於我們的要求,但事實上,沒有任何事是被強迫的,我們始終擁有選擇是否執行某項任務的自由。並不存在「絕對的要求」, 也沒有人能真正強迫我們去做任何事。
此刻,許多人可能正搖著頭,心想:「這太荒謬了,當然有加諸於我的要求!如果我不遵從這些要求,可能會受到批評,甚至被解僱。」
讓我們更加批判性地審視這種反應,並透過兩位醫療照護者的故事來深入探討。
【案例分享】
◆案例一:倦怠的鮑比
喬是醫院繁忙急診室的醫療主任。下午四點,喬接到威廉的電話,他原訂在當晚十點值大夜班,但因生病而無法上班。喬查看排班表與輪班可用表,發現鮑比可能有空,於是拿起電話撥了過去。
「喂?」
「嘿,鮑比,我是喬。聽著,威廉生病了,今晚沒辦法來上大夜班。我想問問你是否能幫忙替班?」
鮑比的身體瞬間繃緊,他最不想做的,就是再多上一個大夜班。心想:「喬一定還在記恨上週交班時,我讓他處理過一位棘手的病人。這肯定是報復,他正在利用權力強壓我,而我根本別無選擇,只能接受。」
「呃⋯⋯好吧,我去。」鮑比語氣不善地回應。
「太好了,謝啦。」
鮑比掛上電話,繼續修整庭院,只是動作比平常更為粗暴。他心煩意亂,整個晚餐時間都沉浸在對這場額外值班的不滿中,無法和妻兒共享愉快時光。家人們早已學會,在他這種煩躁的情緒下,最好小心行事。
鮑比草草吞下晚餐,隨後上樓試圖小睡,為大夜班做準備。但內心的憤怒與受害感,加上交感神經系統的過度激化,他根本無法放鬆。他翻來覆去,腦中不斷反芻著「喬的不公平要求」。
最終,鮑比受不了,乾脆起床看電視,卻因煩躁而無法專心看任何自己喜歡的節目,不停地轉台,試圖分散注意力,卻無濟於事。過了一個小時,他終於放棄,沖了個澡, 然後出發去醫院。
到了醫院,護理師們立刻察覺到鮑比的暴躁情緒,這種負能量滲透進他和病人及同事的互動中。護理師們竭盡全力確保他所有的醫囑都被妥善執行,避免任何疏失,但這並未讓鮑比的煩躁稍減。下班後,他頭也不回地匆匆離開,連一句「再見」都沒對護理同仁說。回到家,迫不及待地爬上床,卻發現自己仍然無法放鬆入睡。
◆案例二:強韌的蘿希
喬是醫院繁忙急診室的醫療主任。下午四點,接到威廉的電話,他原訂在當晚十點值大夜班,但因生病而無法上班。喬查看排班表與輪班可用表,發現蘿希可能有空,於是拿起電話撥了過去。
「喂?」
「嘿,蘿希,我是喬。聽著,威廉生病了,今晚沒辦法來上大夜班。我想問問你是否能幫忙替班?」
蘿希冷靜地聆聽喬的請求後,才回應道:「嘿,喬!讓我先看看能不能找到保母,等一下回電給你。」
事實上,蘿希早就知道有保母能幫忙,因為和丈夫本來就計畫今晚的約會。她這樣回應,是給自己時間來評估喬的請求,並考慮幾個因素:這個班確實需要有人頂替,而她答應的話,未來若有需要,喬可能會更願意幫她一把;此外,這額外的收入還能幫她補貼那輛她一直想買的新登山腳踏車。
幾分鐘後,蘿希回撥電話給喬。
「嘿,喬,我聯絡到保母,一切都安排好了。我可以去替班。」
「太好了,謝謝。」
掛上電話,她愉快地繼續完成庭院整理工作,並欣賞著自己精心修剪的花圃,對成果感到滿意。她隨後進屋向丈夫說明情況,丈夫立刻表示可以改期約會,並幫她取消當晚的保母預約。晚餐時間,一家人輕鬆地聊著他們未來想去挑戰的登山車路線。飯後,蘿希上樓稍作休息,很快便安心入睡,為即將到來的夜班養精蓄銳。
當鬧鐘響起時,蘿希神清氣爽地起床,沖了個澡後開車前往醫院。路上,她還想到,夜班的好處之一就是可以避開交通壅塞。在醫院裡,蘿希一如往常地友善且專注,和護理團隊緊密合作,整個班次進行得順利且沒有重大問題。清晨時,大家互相道別,蘿希開車回家,一回到家就直接上床休息。躺下時,她心滿意足地計畫著何時去把那輛新登山車帶回家,然後沉沉睡去。
在上述兩種情境中,身為醫療主任的喬皆因人手短缺而致電尋求支援,最終大夜班都順利填補。然而,這兩次互動的結果截然不同。鮑比將喬的來電視為一種「要求」(demand),並本能地選擇順從。他在當班前和當班中都經歷了強烈的壓力與痛苦,這進一步加劇了他的職業倦怠症狀。
蘿希則將喬的來電視為一種「請求」(request),並且意識到自己擁有選擇的空間。這個請求沒有讓她感到壓力,決定本身也沒有對她造成任何困擾,反而為她帶來多重好處,例如和喬建立更好的關係、賺取額外收入來買她心儀的登山車等。
可以看出,鮑比的這次經歷可能加劇他的職業倦怠。而蘿希雖然在工作後可能會有點疲勞,但她並未經歷因「要求」而產生的憤怒、怨懟或敵意(即「戰或逃」的壓力反應)。再進一步思考,和鮑比一起工作的團隊經歷又是如何?和蘿希共事的團隊又如何?另外,這兩位醫師在這些情境下提供的醫療照護風格與水準,又有何不同?
分析兩個對比案例之後,就能凸顯出:當控制點(locus of control)從外在轉向內在所顯現的好處。也顯示出調整感知方式所帶來的優勢,只要記住「我們總是擁有選擇的權利」,就能降低職場環境對我們的毒性影響,並降低它對我們造成的負面作用。
我們真的隨時都有選擇嗎?如果選擇不順從,會發生什麼事?會受到批評嗎?這確實有可能,因為我們無法控制別人的評價。但我們可以選擇:我們是否願意承受這些批評,而不去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會因此被解雇嗎?也可能不會。即使真的會,那麼我們是否願意待在這樣一個僵化而苛刻的職場中?
當我們能進行自我調節,並且牢記「沒有任何事情是強加於我們的」,就能創造出依個人意願而選擇的空間,而不是單純被動地反應。
感知成熟的第一步:職場解毒
接下來,將介紹一些關鍵的感知轉變,這些轉變已幫助許多專業照護者減輕痛苦、改善生活品質。在閱讀本章過程中,請試著思考並記錄你自己的想法,將有助於在本章後續的習作部分填寫回應。
◆真實危險或感知威脅
到目前為止,你應該已經理解,由於創傷生成機制的影響,每天感知到的威脅遠遠多於實際遇到的危險。然而,身體無法區分兩者,當交感神經系統反覆因感知威脅而被激化時,便會導致慈悲枯竭與倦怠的症狀。要打破這種自動化的「戰或逃」反應的第一步,就是學會降低環境中那些看似具有威脅性的因素。
舉例來說,我們曾受邀在某大型、高競爭力的都市醫院,為一群急診醫師連續兩天舉辦兩場工作坊。這些醫師給我們的第一印象是:他們似乎已經「硬化」了,明顯展現出倦怠的特徵。我們不禁懷疑,這種非傳統的方法是否能引起他們的共鳴(是的, 當站在台上面對觀眾時,我們自己也會產生「威脅感知」!)。
到了第二天上午的休息時間,一位前天參加過工作坊的醫師特地來找我們。他才剛結束夜班輪值,甚至比預定時間多待了兩個小時,就是為了向我們分享他的親身經驗。他說:「我已擔任急診醫師二十年了,而剛剛結束的這個夜班,對我來說前所未有地不同!我開始能察覺到自己的身體何時變得緊繃,並運用昨天學到的『骨盆底放鬆技術』進行自我調節。最棒的是,我能一次又一次地提醒自己,雖然感覺自己『好像』處於危險之中,但實際上我『並未真正』陷入危險!這種感知的轉變,讓我對這個夜班的體驗產生了巨大的改變!今天特地來這裡,就是想和你們分享這件事。而且,我的妻子和女兒也要向你們表達感謝,因為昨天的課程對我的幫助實在太大了!」
僅僅是一個「微小」的感知轉變:從「我好像處於危險之中」到「其實我並未真正陷入危險」,就能幫助這位醫師放鬆了身體, 重塑對職場的感知。他的職場,不再是一個「戰區」,而是一個安全、並且能展現自己專業能力的地方。
◆要求或選擇
「沒有人真的對你有所要求。」讀到這句話時,你的第一反應是什麼?是否本能地感到排斥,甚至立即想要反駁?如果是這樣,這可能反映出你對工作環境的習慣性感知,一種源自生活經驗的內在感知模式,可能因而成為壓力的隱性來源。
許多人從小到大接受到各種影響,來自家庭、同事、大學、主管、病人或媒體,讓我們習慣性地將別人的「請求」視為對我們的「要求」。在職場中,當這種「被要求」的感受不斷累積,就越容易將其視為一種潛在威脅。當要求被誤解為威脅時,就可能觸發威脅反應,引發我們試圖避免的身心負擔及其伴隨症狀。因此, 我們必須轉變觀點,不再將所有和工作相關的任務視為無可避免的要求,而是重新解讀成我們可以選擇接受或拒絕的活動。
當主管分派給我們一項工作任務時,並不自動構成對我們的要求。可以自問三個問題:
● 每個選擇的後果是什麼?
● 執行它會帶來哪些正面成果?
● 我選擇怎麼做?
這些都是很好的起頭問題,同時應該記住:我們不必立即回應,也無須一味地迎合對方的期望。如果忽視自己擁有選擇的自由,反而將這些任務視為強加於我們的要求,這將成為助長職場環境毒化的關鍵因素之一。一旦將主管、病人或家屬的請求視為要求,那麼很可能會:一、將這個要求視為威脅;二、產生恐懼感,甚至出現逃避相關任務的行為;三、透過蠻力(即「壓力」) 來完成這些令人抗拒的任務。
我們會發現,即使面對那些不特別想做的工作,當我們主動選擇投入並完成時,職場壓力反而會顯著減輕。
在第四章中,曾討論過兩位醫師的對比經歷,分別是「倦怠的鮑比」和「強韌的蘿希」,以及他們如何因應來自醫療主管的意外電話,要求填補夜班。鮑比把醫療主管的電話視為要求,本能地接起電話並立即同意接班,過程中經歷了個人的痛苦(他的家人、同事,甚至可能是病人也受到影響)。另一方面,蘿希則把醫療主管的電話視為請求,在接起電話並聽完主管的問題後, 告訴對方她會稍後回覆。在決定之前,蘿希進行自我調節,激發最大的腦功能,並基於充分的理由選擇接受這個班次。
因為她是基於自由選擇而接受,她的家人和同事都能愉快地配合,讓夜班的安排順利進行。最重要的是,這個夜班都被填補了。參與者之間的差異可以歸因於個人的感知,一位認為是基於自由、舒適與接受的選擇;另一位則將其視為要求,因而未能帶來上述的正向結果。
當他們意識到:自己並非身處真正的危險之中,而只是「感知到」威脅時,便能開始調節自律神經系統,逐步中斷本能性的威脅反應。一旦這些調節技能得以培養並日漸熟練,專業人士將發現壓力逐漸減輕。隨著壓力降低,大腦新皮質功能(負責思考與理性判斷)將重新發揮作用,使他們得以發展出更成熟的職場感知,減少環境的「毒性」影響,並將控制感從外在環境(外控) 轉向內在賦能與韌力的培養(內控)。透過持續練習這些技能, 並融入專業韌力的原則,照護者終將為自己騰出空間,重新點燃對工作的使命感、熱情與喜悅。
核心概念在於:我們將控制感從外在環境(職場)轉移到內在(對職場的回應方式)。這種感知轉變的一個關鍵在於:我們如何重新看待職場中的各種責任。我們往往習慣把這些責任視為強加於我們的要求,但事實上,沒有任何事是被強迫的,我們始終擁有選擇是否執行某項任務的自由。並不存在「絕對的要求」, 也沒有人能真正強迫我們去做任何事。
此刻,許多人可能正搖著頭,心想:「這太荒謬了,當然有加諸於我的要求!如果我不遵從這些要求,可能會受到批評,甚至被解僱。」
讓我們更加批判性地審視這種反應,並透過兩位醫療照護者的故事來深入探討。
【案例分享】
◆案例一:倦怠的鮑比
喬是醫院繁忙急診室的醫療主任。下午四點,喬接到威廉的電話,他原訂在當晚十點值大夜班,但因生病而無法上班。喬查看排班表與輪班可用表,發現鮑比可能有空,於是拿起電話撥了過去。
「喂?」
「嘿,鮑比,我是喬。聽著,威廉生病了,今晚沒辦法來上大夜班。我想問問你是否能幫忙替班?」
鮑比的身體瞬間繃緊,他最不想做的,就是再多上一個大夜班。心想:「喬一定還在記恨上週交班時,我讓他處理過一位棘手的病人。這肯定是報復,他正在利用權力強壓我,而我根本別無選擇,只能接受。」
「呃⋯⋯好吧,我去。」鮑比語氣不善地回應。
「太好了,謝啦。」
鮑比掛上電話,繼續修整庭院,只是動作比平常更為粗暴。他心煩意亂,整個晚餐時間都沉浸在對這場額外值班的不滿中,無法和妻兒共享愉快時光。家人們早已學會,在他這種煩躁的情緒下,最好小心行事。
鮑比草草吞下晚餐,隨後上樓試圖小睡,為大夜班做準備。但內心的憤怒與受害感,加上交感神經系統的過度激化,他根本無法放鬆。他翻來覆去,腦中不斷反芻著「喬的不公平要求」。
最終,鮑比受不了,乾脆起床看電視,卻因煩躁而無法專心看任何自己喜歡的節目,不停地轉台,試圖分散注意力,卻無濟於事。過了一個小時,他終於放棄,沖了個澡, 然後出發去醫院。
到了醫院,護理師們立刻察覺到鮑比的暴躁情緒,這種負能量滲透進他和病人及同事的互動中。護理師們竭盡全力確保他所有的醫囑都被妥善執行,避免任何疏失,但這並未讓鮑比的煩躁稍減。下班後,他頭也不回地匆匆離開,連一句「再見」都沒對護理同仁說。回到家,迫不及待地爬上床,卻發現自己仍然無法放鬆入睡。
◆案例二:強韌的蘿希
喬是醫院繁忙急診室的醫療主任。下午四點,接到威廉的電話,他原訂在當晚十點值大夜班,但因生病而無法上班。喬查看排班表與輪班可用表,發現蘿希可能有空,於是拿起電話撥了過去。
「喂?」
「嘿,蘿希,我是喬。聽著,威廉生病了,今晚沒辦法來上大夜班。我想問問你是否能幫忙替班?」
蘿希冷靜地聆聽喬的請求後,才回應道:「嘿,喬!讓我先看看能不能找到保母,等一下回電給你。」
事實上,蘿希早就知道有保母能幫忙,因為和丈夫本來就計畫今晚的約會。她這樣回應,是給自己時間來評估喬的請求,並考慮幾個因素:這個班確實需要有人頂替,而她答應的話,未來若有需要,喬可能會更願意幫她一把;此外,這額外的收入還能幫她補貼那輛她一直想買的新登山腳踏車。
幾分鐘後,蘿希回撥電話給喬。
「嘿,喬,我聯絡到保母,一切都安排好了。我可以去替班。」
「太好了,謝謝。」
掛上電話,她愉快地繼續完成庭院整理工作,並欣賞著自己精心修剪的花圃,對成果感到滿意。她隨後進屋向丈夫說明情況,丈夫立刻表示可以改期約會,並幫她取消當晚的保母預約。晚餐時間,一家人輕鬆地聊著他們未來想去挑戰的登山車路線。飯後,蘿希上樓稍作休息,很快便安心入睡,為即將到來的夜班養精蓄銳。
當鬧鐘響起時,蘿希神清氣爽地起床,沖了個澡後開車前往醫院。路上,她還想到,夜班的好處之一就是可以避開交通壅塞。在醫院裡,蘿希一如往常地友善且專注,和護理團隊緊密合作,整個班次進行得順利且沒有重大問題。清晨時,大家互相道別,蘿希開車回家,一回到家就直接上床休息。躺下時,她心滿意足地計畫著何時去把那輛新登山車帶回家,然後沉沉睡去。
在上述兩種情境中,身為醫療主任的喬皆因人手短缺而致電尋求支援,最終大夜班都順利填補。然而,這兩次互動的結果截然不同。鮑比將喬的來電視為一種「要求」(demand),並本能地選擇順從。他在當班前和當班中都經歷了強烈的壓力與痛苦,這進一步加劇了他的職業倦怠症狀。
蘿希則將喬的來電視為一種「請求」(request),並且意識到自己擁有選擇的空間。這個請求沒有讓她感到壓力,決定本身也沒有對她造成任何困擾,反而為她帶來多重好處,例如和喬建立更好的關係、賺取額外收入來買她心儀的登山車等。
可以看出,鮑比的這次經歷可能加劇他的職業倦怠。而蘿希雖然在工作後可能會有點疲勞,但她並未經歷因「要求」而產生的憤怒、怨懟或敵意(即「戰或逃」的壓力反應)。再進一步思考,和鮑比一起工作的團隊經歷又是如何?和蘿希共事的團隊又如何?另外,這兩位醫師在這些情境下提供的醫療照護風格與水準,又有何不同?
分析兩個對比案例之後,就能凸顯出:當控制點(locus of control)從外在轉向內在所顯現的好處。也顯示出調整感知方式所帶來的優勢,只要記住「我們總是擁有選擇的權利」,就能降低職場環境對我們的毒性影響,並降低它對我們造成的負面作用。
我們真的隨時都有選擇嗎?如果選擇不順從,會發生什麼事?會受到批評嗎?這確實有可能,因為我們無法控制別人的評價。但我們可以選擇:我們是否願意承受這些批評,而不去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會因此被解雇嗎?也可能不會。即使真的會,那麼我們是否願意待在這樣一個僵化而苛刻的職場中?
當我們能進行自我調節,並且牢記「沒有任何事情是強加於我們的」,就能創造出依個人意願而選擇的空間,而不是單純被動地反應。
感知成熟的第一步:職場解毒
接下來,將介紹一些關鍵的感知轉變,這些轉變已幫助許多專業照護者減輕痛苦、改善生活品質。在閱讀本章過程中,請試著思考並記錄你自己的想法,將有助於在本章後續的習作部分填寫回應。
◆真實危險或感知威脅
到目前為止,你應該已經理解,由於創傷生成機制的影響,每天感知到的威脅遠遠多於實際遇到的危險。然而,身體無法區分兩者,當交感神經系統反覆因感知威脅而被激化時,便會導致慈悲枯竭與倦怠的症狀。要打破這種自動化的「戰或逃」反應的第一步,就是學會降低環境中那些看似具有威脅性的因素。
舉例來說,我們曾受邀在某大型、高競爭力的都市醫院,為一群急診醫師連續兩天舉辦兩場工作坊。這些醫師給我們的第一印象是:他們似乎已經「硬化」了,明顯展現出倦怠的特徵。我們不禁懷疑,這種非傳統的方法是否能引起他們的共鳴(是的, 當站在台上面對觀眾時,我們自己也會產生「威脅感知」!)。
到了第二天上午的休息時間,一位前天參加過工作坊的醫師特地來找我們。他才剛結束夜班輪值,甚至比預定時間多待了兩個小時,就是為了向我們分享他的親身經驗。他說:「我已擔任急診醫師二十年了,而剛剛結束的這個夜班,對我來說前所未有地不同!我開始能察覺到自己的身體何時變得緊繃,並運用昨天學到的『骨盆底放鬆技術』進行自我調節。最棒的是,我能一次又一次地提醒自己,雖然感覺自己『好像』處於危險之中,但實際上我『並未真正』陷入危險!這種感知的轉變,讓我對這個夜班的體驗產生了巨大的改變!今天特地來這裡,就是想和你們分享這件事。而且,我的妻子和女兒也要向你們表達感謝,因為昨天的課程對我的幫助實在太大了!」
僅僅是一個「微小」的感知轉變:從「我好像處於危險之中」到「其實我並未真正陷入危險」,就能幫助這位醫師放鬆了身體, 重塑對職場的感知。他的職場,不再是一個「戰區」,而是一個安全、並且能展現自己專業能力的地方。
◆要求或選擇
「沒有人真的對你有所要求。」讀到這句話時,你的第一反應是什麼?是否本能地感到排斥,甚至立即想要反駁?如果是這樣,這可能反映出你對工作環境的習慣性感知,一種源自生活經驗的內在感知模式,可能因而成為壓力的隱性來源。
許多人從小到大接受到各種影響,來自家庭、同事、大學、主管、病人或媒體,讓我們習慣性地將別人的「請求」視為對我們的「要求」。在職場中,當這種「被要求」的感受不斷累積,就越容易將其視為一種潛在威脅。當要求被誤解為威脅時,就可能觸發威脅反應,引發我們試圖避免的身心負擔及其伴隨症狀。因此, 我們必須轉變觀點,不再將所有和工作相關的任務視為無可避免的要求,而是重新解讀成我們可以選擇接受或拒絕的活動。
當主管分派給我們一項工作任務時,並不自動構成對我們的要求。可以自問三個問題:
● 每個選擇的後果是什麼?
● 執行它會帶來哪些正面成果?
● 我選擇怎麼做?
這些都是很好的起頭問題,同時應該記住:我們不必立即回應,也無須一味地迎合對方的期望。如果忽視自己擁有選擇的自由,反而將這些任務視為強加於我們的要求,這將成為助長職場環境毒化的關鍵因素之一。一旦將主管、病人或家屬的請求視為要求,那麼很可能會:一、將這個要求視為威脅;二、產生恐懼感,甚至出現逃避相關任務的行為;三、透過蠻力(即「壓力」) 來完成這些令人抗拒的任務。
我們會發現,即使面對那些不特別想做的工作,當我們主動選擇投入並完成時,職場壓力反而會顯著減輕。
在第四章中,曾討論過兩位醫師的對比經歷,分別是「倦怠的鮑比」和「強韌的蘿希」,以及他們如何因應來自醫療主管的意外電話,要求填補夜班。鮑比把醫療主管的電話視為要求,本能地接起電話並立即同意接班,過程中經歷了個人的痛苦(他的家人、同事,甚至可能是病人也受到影響)。另一方面,蘿希則把醫療主管的電話視為請求,在接起電話並聽完主管的問題後, 告訴對方她會稍後回覆。在決定之前,蘿希進行自我調節,激發最大的腦功能,並基於充分的理由選擇接受這個班次。
因為她是基於自由選擇而接受,她的家人和同事都能愉快地配合,讓夜班的安排順利進行。最重要的是,這個夜班都被填補了。參與者之間的差異可以歸因於個人的感知,一位認為是基於自由、舒適與接受的選擇;另一位則將其視為要求,因而未能帶來上述的正向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