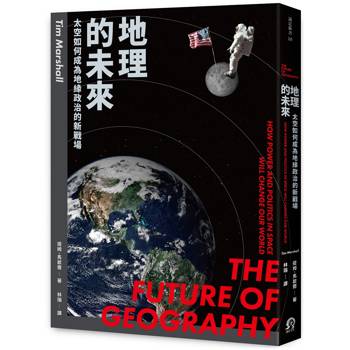第五章 中國:長征……進入太空
二○二二年初,北京發表航天計畫「觀點報告」,一開始就引用習近平的話說,「探索浩瀚宇宙,發展航天事業,建設航天強國,是我們不懈追求的航天夢。」整篇文件談的都是太空產業如何有助於中國成長,有助於「外太空探索與利用的全球共識與共同努力,有助於人類進步」。文件中一一列舉中國迄今為止的各項成就,還對中國新一代載人飛船、人類登月、在月球建立國際研究站、以及探討小行星與深入太空的計畫做了說明。報告中還談到「探索木星系統等等」,這話頗為耐人尋味,「等等」指的是什麼,只怕大有文章。
根據這項「觀點報告」,中國航天計畫的「任務願景」是「自由進出、有效使用與有效管理太空」。這「自由進出」與「有效管理」的表述,不啻是對美國、以及任何不讓中國進軍太空的意圖的警告。二○一九年,中國登月計畫負責人葉培建說,「如果我們現在儘管有能力卻不上去,有一天我們的後代子孫會罵我們。如果其他人上去了,控制了那裡,你就算想去也去不了。單單這個理由已經夠了。」
文件中明文呼籲聯合國「在外太空事務的管理」上扮演核心角色。它指出,自從二○一六年以來,中國已經與包括巴基斯坦、沙烏地阿拉伯、阿根廷、南非與泰國等十九個國家與地區,以及四個國際組織簽署航太協議或諒解備忘錄。它強調與歐洲太空總署、瑞典、德國與荷蘭的合作。它大吹大擂,說中國已經為許多國家提供衛星發射服務,還為寮國、緬甸等開發中國家開放其設施。
這一切表述的主旨,就在於打擊北京所謂「美國主控太空治理的意圖」。中國與美國在過去許多年也曾嘗試合作。一九八四年初,雷根總統同意讓一名中國航天員登上美國太空梭出行。一九八六年,為準備中國航天員參與的事,一群中國科學家原本計畫訪問休士頓載人太空船中心,但在那年一月,「挑戰者號」(Challenger)太空梭在升空後七十三秒爆炸,所有七名太空人全部罹難。這項訪問取消,所有「客座計畫」俱皆無限期暫緩。
在美國國會根據二○一一年「伍爾夫條款」(Wolf Amendment),為航太總署與中國的合作設限之後,中國被阿蒂米絲協定排斥在外。當時擔任共和黨國會議員的法蘭克.伍爾夫(Frank Wolf),所以提出這項條款的理由是,有鑒於太空探討、科技進步與中國軍事之間的關係,中國對美國構成的威脅越來越大,美國不能與這樣的競爭對手合作。特別是,美國人擔心中國可能對航太總署電腦與美中聯合研究項目進行智慧財產剽竊,將竊來的資料用於彈道飛彈等敏感軍事科技。
根據已知資料,中國駭客曾短暫侵入美國國防部、國防部長辦公室、美國海軍戰爭學院(US Naval War College)、一座核武實驗室、以及白宮的電腦系統。遭美國破獲的傳統間諜活動更多。以二○○八年為例,住在維吉尼亞州的華裔美籍科學家舒全勝,因為將美國火箭液態氫燃料槽的情報交給北京而被定罪。二○一○年,前波音(Boeing)工程師鍾東蕃,因為將三十幾萬頁敏感情報──包括有關美國太空梭的情資──提供中國而被定罪。
在遭到阿蒂米絲協定排擠之後,中國開始打造自己的空間站,與國際太空站放對,與許多國家建立戰略科學關係,並建立一個至少看起來與美國一樣先進的國內航天產業。在沒有來自美方奧援的情況下,中國做到了這一切。
這令人印象深刻。而且中國人動作很快:軍機飛行員楊利偉少將於二○○三年成為第一個進入太空的中國人。中國自行研發的「長征二F」火箭將載有楊利偉的太空艙送進軌道。楊利偉在二十一小時的飛行中,環繞地球十四圈,中國也因此成為第三個將人送進太空的國家。《中國日報》稱楊利偉此行是「飛向天空的大躍進」。
好成績不斷出爐。戰鬥機飛行員劉洋少校於二○一二年成為中國第一名女性航天員。二○一四年,中國完成專供大直徑「長征」火箭(這類型火箭需要在水邊發射)的文昌發射場。二○一六年,兩名航天員的飛船成功靠上「天宮二號」空間站,在空間站停留了一個月。
二○一九年,無人太空船「嫦娥四號」探測器在月球背面登陸。這次任務是中、美兩國合作潛能的又一個例子。美國航太總署奉准可以為中方提供有關登陸區資料,兩國之後同意,將這項協調作業的發現成果,透過聯合國,與國際科研學界共享。二○二○年,最後一顆北斗衛星進入軌道位置,挑戰美國「全球定位系統」(GPS)的北斗導航系統於焉完成,是另一值得一提的日子。翌年,王亞平成為中國第一名太空漫步的航天員。
對中國而言,或許在上一個十年,最重要的里程碑是火星漫遊車的環軌、登陸與之後的佈署。「天問一號」探測器於二○二一年二月抵達火星軌道,花了三個月搜尋適合登陸的地點。五月十四日,「天問一號」攜帶的祝融(火神)漫遊車脫離載具,在火星軟著陸,隨即展開火星地形觀測活動,搜尋水源,並且將聲音與畫面訊號送回地球。現在火星上有了三輛運作中的漫遊車:祝融號,以及航太總署在早先兩次任務送上火星的「毅力號」(Perseverance)與「好奇號」(Curiosity)。
所有這一切都讓中國引以為傲,也都與共產黨的神話交織、糾葛。中國的「長征」火箭以一九三四到三五年內戰期間,共產黨一場著名的撤軍行動命名。當時紅軍敗退九千公里,穿越崎嶇山區徹入安全地帶。毛澤東隨即掌權,最後擊敗反共的政府軍。「長征」因此成為中國共產黨創黨神話的一章,中共每在談到英勇犧牲、完成重大成就時,常以它做為例子。「長征」火箭將中國推上太空,完成偉大任務,極具象徵意義。
但有趣的是,近年來,中國在大肆宣揚共產主義優勢方面似乎有所軟化,開始擁抱民族主義元素,以及來自集體歷史記憶的神話。太空任務與裝備的命名反映了這種趨勢。舉例說,在二○○七年,無人環繞月軌探測器「嫦娥一號」就取名於中國民俗神話。根據這篇神話,美女嫦娥偷喝了丈夫的長生不老藥,飛上月亮,成為月宮女神。嫦娥養了一隻兔子,名叫「玉兔」,玉兔不斷在月宮忙著,在一個缽裡磨製長生不老藥,以保證嫦娥用藥無缺。當嫦娥三號於二○一三年登陸月球表面時,使用的登月車就叫「玉兔號」。
同時,搭「神舟」太空船登上「天宮」空間站的航天員,得為他們能來到這裡而慶幸。根據中國神話,主宰宇宙萬物、至高無上的大帝,就住在這座「天宮」。用來特指中國太空人的英文字「taikonaut」是中文與希臘文的組合,「taikong」是中文音譯,意即「太空」、「宇宙」,而「naut」是希臘文「海員」、「水手」之意。「taikonaut」的稱謂,因中國太空分析師陳藍,以及他的網站「Go Taikonauts!」發揚光大而流行。中國太空人的官方名稱是「宇航員」,也就是「宇宙旅者」(或者,更不好聽一點,就是「在宇宙流浪的工人」。)
這些名字很重要。它們向世人傳遞一種訊息:太空不是美國人與歐洲人專屬領域,每有一個月女神,就有一個嫦娥。(未完)
二○二二年初,北京發表航天計畫「觀點報告」,一開始就引用習近平的話說,「探索浩瀚宇宙,發展航天事業,建設航天強國,是我們不懈追求的航天夢。」整篇文件談的都是太空產業如何有助於中國成長,有助於「外太空探索與利用的全球共識與共同努力,有助於人類進步」。文件中一一列舉中國迄今為止的各項成就,還對中國新一代載人飛船、人類登月、在月球建立國際研究站、以及探討小行星與深入太空的計畫做了說明。報告中還談到「探索木星系統等等」,這話頗為耐人尋味,「等等」指的是什麼,只怕大有文章。
根據這項「觀點報告」,中國航天計畫的「任務願景」是「自由進出、有效使用與有效管理太空」。這「自由進出」與「有效管理」的表述,不啻是對美國、以及任何不讓中國進軍太空的意圖的警告。二○一九年,中國登月計畫負責人葉培建說,「如果我們現在儘管有能力卻不上去,有一天我們的後代子孫會罵我們。如果其他人上去了,控制了那裡,你就算想去也去不了。單單這個理由已經夠了。」
文件中明文呼籲聯合國「在外太空事務的管理」上扮演核心角色。它指出,自從二○一六年以來,中國已經與包括巴基斯坦、沙烏地阿拉伯、阿根廷、南非與泰國等十九個國家與地區,以及四個國際組織簽署航太協議或諒解備忘錄。它強調與歐洲太空總署、瑞典、德國與荷蘭的合作。它大吹大擂,說中國已經為許多國家提供衛星發射服務,還為寮國、緬甸等開發中國家開放其設施。
這一切表述的主旨,就在於打擊北京所謂「美國主控太空治理的意圖」。中國與美國在過去許多年也曾嘗試合作。一九八四年初,雷根總統同意讓一名中國航天員登上美國太空梭出行。一九八六年,為準備中國航天員參與的事,一群中國科學家原本計畫訪問休士頓載人太空船中心,但在那年一月,「挑戰者號」(Challenger)太空梭在升空後七十三秒爆炸,所有七名太空人全部罹難。這項訪問取消,所有「客座計畫」俱皆無限期暫緩。
在美國國會根據二○一一年「伍爾夫條款」(Wolf Amendment),為航太總署與中國的合作設限之後,中國被阿蒂米絲協定排斥在外。當時擔任共和黨國會議員的法蘭克.伍爾夫(Frank Wolf),所以提出這項條款的理由是,有鑒於太空探討、科技進步與中國軍事之間的關係,中國對美國構成的威脅越來越大,美國不能與這樣的競爭對手合作。特別是,美國人擔心中國可能對航太總署電腦與美中聯合研究項目進行智慧財產剽竊,將竊來的資料用於彈道飛彈等敏感軍事科技。
根據已知資料,中國駭客曾短暫侵入美國國防部、國防部長辦公室、美國海軍戰爭學院(US Naval War College)、一座核武實驗室、以及白宮的電腦系統。遭美國破獲的傳統間諜活動更多。以二○○八年為例,住在維吉尼亞州的華裔美籍科學家舒全勝,因為將美國火箭液態氫燃料槽的情報交給北京而被定罪。二○一○年,前波音(Boeing)工程師鍾東蕃,因為將三十幾萬頁敏感情報──包括有關美國太空梭的情資──提供中國而被定罪。
在遭到阿蒂米絲協定排擠之後,中國開始打造自己的空間站,與國際太空站放對,與許多國家建立戰略科學關係,並建立一個至少看起來與美國一樣先進的國內航天產業。在沒有來自美方奧援的情況下,中國做到了這一切。
這令人印象深刻。而且中國人動作很快:軍機飛行員楊利偉少將於二○○三年成為第一個進入太空的中國人。中國自行研發的「長征二F」火箭將載有楊利偉的太空艙送進軌道。楊利偉在二十一小時的飛行中,環繞地球十四圈,中國也因此成為第三個將人送進太空的國家。《中國日報》稱楊利偉此行是「飛向天空的大躍進」。
好成績不斷出爐。戰鬥機飛行員劉洋少校於二○一二年成為中國第一名女性航天員。二○一四年,中國完成專供大直徑「長征」火箭(這類型火箭需要在水邊發射)的文昌發射場。二○一六年,兩名航天員的飛船成功靠上「天宮二號」空間站,在空間站停留了一個月。
二○一九年,無人太空船「嫦娥四號」探測器在月球背面登陸。這次任務是中、美兩國合作潛能的又一個例子。美國航太總署奉准可以為中方提供有關登陸區資料,兩國之後同意,將這項協調作業的發現成果,透過聯合國,與國際科研學界共享。二○二○年,最後一顆北斗衛星進入軌道位置,挑戰美國「全球定位系統」(GPS)的北斗導航系統於焉完成,是另一值得一提的日子。翌年,王亞平成為中國第一名太空漫步的航天員。
對中國而言,或許在上一個十年,最重要的里程碑是火星漫遊車的環軌、登陸與之後的佈署。「天問一號」探測器於二○二一年二月抵達火星軌道,花了三個月搜尋適合登陸的地點。五月十四日,「天問一號」攜帶的祝融(火神)漫遊車脫離載具,在火星軟著陸,隨即展開火星地形觀測活動,搜尋水源,並且將聲音與畫面訊號送回地球。現在火星上有了三輛運作中的漫遊車:祝融號,以及航太總署在早先兩次任務送上火星的「毅力號」(Perseverance)與「好奇號」(Curiosity)。
所有這一切都讓中國引以為傲,也都與共產黨的神話交織、糾葛。中國的「長征」火箭以一九三四到三五年內戰期間,共產黨一場著名的撤軍行動命名。當時紅軍敗退九千公里,穿越崎嶇山區徹入安全地帶。毛澤東隨即掌權,最後擊敗反共的政府軍。「長征」因此成為中國共產黨創黨神話的一章,中共每在談到英勇犧牲、完成重大成就時,常以它做為例子。「長征」火箭將中國推上太空,完成偉大任務,極具象徵意義。
但有趣的是,近年來,中國在大肆宣揚共產主義優勢方面似乎有所軟化,開始擁抱民族主義元素,以及來自集體歷史記憶的神話。太空任務與裝備的命名反映了這種趨勢。舉例說,在二○○七年,無人環繞月軌探測器「嫦娥一號」就取名於中國民俗神話。根據這篇神話,美女嫦娥偷喝了丈夫的長生不老藥,飛上月亮,成為月宮女神。嫦娥養了一隻兔子,名叫「玉兔」,玉兔不斷在月宮忙著,在一個缽裡磨製長生不老藥,以保證嫦娥用藥無缺。當嫦娥三號於二○一三年登陸月球表面時,使用的登月車就叫「玉兔號」。
同時,搭「神舟」太空船登上「天宮」空間站的航天員,得為他們能來到這裡而慶幸。根據中國神話,主宰宇宙萬物、至高無上的大帝,就住在這座「天宮」。用來特指中國太空人的英文字「taikonaut」是中文與希臘文的組合,「taikong」是中文音譯,意即「太空」、「宇宙」,而「naut」是希臘文「海員」、「水手」之意。「taikonaut」的稱謂,因中國太空分析師陳藍,以及他的網站「Go Taikonauts!」發揚光大而流行。中國太空人的官方名稱是「宇航員」,也就是「宇宙旅者」(或者,更不好聽一點,就是「在宇宙流浪的工人」。)
這些名字很重要。它們向世人傳遞一種訊息:太空不是美國人與歐洲人專屬領域,每有一個月女神,就有一個嫦娥。(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