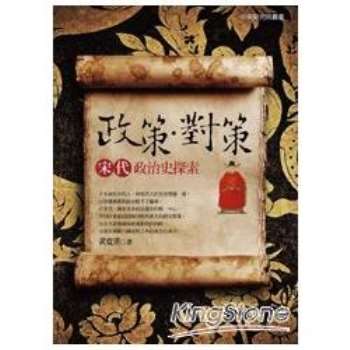第一章 沿唐變制──五代巡檢的轉型與特色
在唐宋社會變遷的研究中,制度的轉型與變遷尤為重要議題。然而,一項制度從初創到定制,過程往往極為細緻而複雜,尤其制度初始萌芽階段常因資料隱晦不足,難以爬梳明確清楚的脈絡。面對這種情況,不同專業的研究者或從問題出發,或由梳理史料著手,從不同的角度就有限的資料提出詮釋,企圖尋覓制度形成的緣由。最常見的討論方式,便是從一項制度發展成熟期向前追溯,只是這種方式常需跨越朝代與突破資料的限制,十分費力,最終也常因史料不足而眾說紛紜,雖每有新見,卻難有定論。本章所擬探究的巡檢就是一個例子。
自宋迄明,巡檢都是維持地方治安的重要職務,是皇朝統治基層社會的主要武職。巡檢制度的形成歷經複雜、曲折的過程,特別是自唐末到北宋前期之間,其職能與角色的變化較多,不但可用以觀察制度從初創到定型的轉變,也可藉此掌握政治、社會環境變化的重要線索,是探討唐宋社會變遷的重要課題。學界有關巡檢的專題研究不在少數,卻仍待開拓。其中,黃清連的〈圓仁與唐代巡檢〉、劉琴麗的〈五代巡檢研究〉和苗書梅的〈宋代巡檢初探〉三篇,分別討論唐、五代和宋代的巡檢制度。三篇論文研究取向和討論重點各異,?都指出了巡檢一職發展的重要方向:在唐代,巡檢尚非一項職稱,而是有巡?檢查、巡行視察之意;到了五代至北宋時期,其職能才有多方面的發展。北宋中期以後,尤其到南宋,巡檢已成為維護基層治安的要角之一。就歷史發展而言,這項觀察是正確的,不過從唐到五代的發展過程卻還有許多討論空間。
制度的萌芽:唐末的巡檢
黃清連以日本僧人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為例,藉由圓仁入唐所歷時期和記錄中使用的詞彙,說明「巡檢」一詞在唐末尚非命官職稱,而是動詞。此一說法就唐末一般情況而言,並無疑義。不過,倘若因此判定唐末尚未以巡檢為命官,待後梁、後唐才出現巡檢使、都巡檢使等官職,則或須斟酌。關於唐代巡檢是否已作為官職,清末民初收藏家端方最早提出討論。在其所編《匋齋藏石志》的〈歸義縣魏惟儼等題名〉中,端方考證「四縣巡檢副將」張君爽、韓定、王全慶、吳倉等人時,就明白指出一般以為巡檢始於宋代的說法有待商榷,進而提出題名所載「四縣巡檢副將」與《通考》所載「宋朝巡檢或一州縣而一置,或數州數縣而一置」的設置相符,因此巡檢「不獨不始於宋,其設官疏密,亦皆沿唐舊制」。端方的看法可以從下文所引資料得到進一步印證。
巡檢在唐代已具官職名稱之實,有四件唐末人物的墓誌銘可為佐證。最早的一件是張敬祐撰〈唐故雄武軍提生狀太中大夫試殿中監黃公墓誌銘并序〉,文中提到黃直是匯夏人,其父黃暉曾任巡檢馬步都將;這件資料的時間不詳,但可確定在咸通(860-873)以前。一件是溫景中撰〈故幽州節度衙前討擊副使太中大夫試殿中監?府君合?墓誌并序〉,墓主河東并州人溫令綬因識略果敢,被張公任為燕樂鎮巡檢將,任職時間約在咸通年間。一件是〈太原王公夫人清河張氏墓誌〉,墓主王宏泰曾任雄武軍平地柵巡檢烽浦大將游擊將,時間約在咸通四年(863)。一件是余渥撰〈故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右散騎常侍右內率府同正兼御史大夫上柱國郭府君墓誌銘〉,墓主郭彥瓊於昭宗光化二年(899)任度支巡檢官、銀清光錄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
前述四位曾任巡檢的唐人除了是武職軍將之外,職務尚與財政有關,這一點和李錦?的說法一致。李錦?在其《唐代財政史稿》中提出,唐末有武將掌理財務的趨勢。她在探討唐代後期直屬朝廷財政機關的巡院時,將巡檢列為巡院吏職,並以貞元十三年(797)同州郃陽縣尉楊叔興充兩池都巡檢官為例,指出唐廷為了防止鹽場地私鹽盜竊等事件,在安邑、解縣兩池鹽專置保衛鹽地的巡檢。她引《冊府元龜》卷494〈邦計部‧山澤門〉大中元年(847)閏三月兩池榷鹽司空輿奏略所稱:「又弓射所由等,晝夜只於池內巡檢。其壕籬外面,山林掩映,竹柵相次。」認為巡檢官即為統領弓射所由之官,兩池置有巡檢官員額。可知負責產鹽地安全防護的巡檢與販鹽流通的交通要路上的檢閱官,是唐代為取締私鹽所設雙重防範檢查的官員。咸通年間,嶺南東道的南道十州設有巡檢務,吳太楚即曾擔任此職,這是晚唐巡院分務化的體現。
除鹽場外,晚唐也設置維護河塘安全的河塘巡檢官。這些巡檢官似先由文職官員充任;到了唐代後期,朝廷為確保財政無虞,實施鹽法運輸、營田、茶酒專賣等法,需要以武力維護利益,或協助財務管理,促成了巡檢系統官吏的出現。他們的主要任務為出巡、緝私、巡查等等,協助財務行政管理。同時,由於晚唐政局混亂,藩鎮對立形勢日趨嚴峻,不但使巡檢官的設置更為普遍,而且出現武職軍將侵奪原由文職僚佐執掌事務的現象。這種現象在財務行政領域尤為明顯,形成武將掌理財務的情況。因此,李錦?認為巡檢官豐富了唐後期財務系統的官吏構成,也體現了唐宋官制的變革。
若將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以及唐末墓誌與石刻資料涉
在唐宋社會變遷的研究中,制度的轉型與變遷尤為重要議題。然而,一項制度從初創到定制,過程往往極為細緻而複雜,尤其制度初始萌芽階段常因資料隱晦不足,難以爬梳明確清楚的脈絡。面對這種情況,不同專業的研究者或從問題出發,或由梳理史料著手,從不同的角度就有限的資料提出詮釋,企圖尋覓制度形成的緣由。最常見的討論方式,便是從一項制度發展成熟期向前追溯,只是這種方式常需跨越朝代與突破資料的限制,十分費力,最終也常因史料不足而眾說紛紜,雖每有新見,卻難有定論。本章所擬探究的巡檢就是一個例子。
自宋迄明,巡檢都是維持地方治安的重要職務,是皇朝統治基層社會的主要武職。巡檢制度的形成歷經複雜、曲折的過程,特別是自唐末到北宋前期之間,其職能與角色的變化較多,不但可用以觀察制度從初創到定型的轉變,也可藉此掌握政治、社會環境變化的重要線索,是探討唐宋社會變遷的重要課題。學界有關巡檢的專題研究不在少數,卻仍待開拓。其中,黃清連的〈圓仁與唐代巡檢〉、劉琴麗的〈五代巡檢研究〉和苗書梅的〈宋代巡檢初探〉三篇,分別討論唐、五代和宋代的巡檢制度。三篇論文研究取向和討論重點各異,?都指出了巡檢一職發展的重要方向:在唐代,巡檢尚非一項職稱,而是有巡?檢查、巡行視察之意;到了五代至北宋時期,其職能才有多方面的發展。北宋中期以後,尤其到南宋,巡檢已成為維護基層治安的要角之一。就歷史發展而言,這項觀察是正確的,不過從唐到五代的發展過程卻還有許多討論空間。
制度的萌芽:唐末的巡檢
黃清連以日本僧人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為例,藉由圓仁入唐所歷時期和記錄中使用的詞彙,說明「巡檢」一詞在唐末尚非命官職稱,而是動詞。此一說法就唐末一般情況而言,並無疑義。不過,倘若因此判定唐末尚未以巡檢為命官,待後梁、後唐才出現巡檢使、都巡檢使等官職,則或須斟酌。關於唐代巡檢是否已作為官職,清末民初收藏家端方最早提出討論。在其所編《匋齋藏石志》的〈歸義縣魏惟儼等題名〉中,端方考證「四縣巡檢副將」張君爽、韓定、王全慶、吳倉等人時,就明白指出一般以為巡檢始於宋代的說法有待商榷,進而提出題名所載「四縣巡檢副將」與《通考》所載「宋朝巡檢或一州縣而一置,或數州數縣而一置」的設置相符,因此巡檢「不獨不始於宋,其設官疏密,亦皆沿唐舊制」。端方的看法可以從下文所引資料得到進一步印證。
巡檢在唐代已具官職名稱之實,有四件唐末人物的墓誌銘可為佐證。最早的一件是張敬祐撰〈唐故雄武軍提生狀太中大夫試殿中監黃公墓誌銘并序〉,文中提到黃直是匯夏人,其父黃暉曾任巡檢馬步都將;這件資料的時間不詳,但可確定在咸通(860-873)以前。一件是溫景中撰〈故幽州節度衙前討擊副使太中大夫試殿中監?府君合?墓誌并序〉,墓主河東并州人溫令綬因識略果敢,被張公任為燕樂鎮巡檢將,任職時間約在咸通年間。一件是〈太原王公夫人清河張氏墓誌〉,墓主王宏泰曾任雄武軍平地柵巡檢烽浦大將游擊將,時間約在咸通四年(863)。一件是余渥撰〈故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右散騎常侍右內率府同正兼御史大夫上柱國郭府君墓誌銘〉,墓主郭彥瓊於昭宗光化二年(899)任度支巡檢官、銀清光錄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
前述四位曾任巡檢的唐人除了是武職軍將之外,職務尚與財政有關,這一點和李錦?的說法一致。李錦?在其《唐代財政史稿》中提出,唐末有武將掌理財務的趨勢。她在探討唐代後期直屬朝廷財政機關的巡院時,將巡檢列為巡院吏職,並以貞元十三年(797)同州郃陽縣尉楊叔興充兩池都巡檢官為例,指出唐廷為了防止鹽場地私鹽盜竊等事件,在安邑、解縣兩池鹽專置保衛鹽地的巡檢。她引《冊府元龜》卷494〈邦計部‧山澤門〉大中元年(847)閏三月兩池榷鹽司空輿奏略所稱:「又弓射所由等,晝夜只於池內巡檢。其壕籬外面,山林掩映,竹柵相次。」認為巡檢官即為統領弓射所由之官,兩池置有巡檢官員額。可知負責產鹽地安全防護的巡檢與販鹽流通的交通要路上的檢閱官,是唐代為取締私鹽所設雙重防範檢查的官員。咸通年間,嶺南東道的南道十州設有巡檢務,吳太楚即曾擔任此職,這是晚唐巡院分務化的體現。
除鹽場外,晚唐也設置維護河塘安全的河塘巡檢官。這些巡檢官似先由文職官員充任;到了唐代後期,朝廷為確保財政無虞,實施鹽法運輸、營田、茶酒專賣等法,需要以武力維護利益,或協助財務管理,促成了巡檢系統官吏的出現。他們的主要任務為出巡、緝私、巡查等等,協助財務行政管理。同時,由於晚唐政局混亂,藩鎮對立形勢日趨嚴峻,不但使巡檢官的設置更為普遍,而且出現武職軍將侵奪原由文職僚佐執掌事務的現象。這種現象在財務行政領域尤為明顯,形成武將掌理財務的情況。因此,李錦?認為巡檢官豐富了唐後期財務系統的官吏構成,也體現了唐宋官制的變革。
若將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以及唐末墓誌與石刻資料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