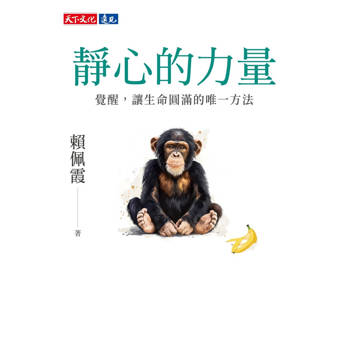靜心修練1 停止自責
早早起床。坐在臨窗,望向基隆河蜿蜒的水岸,波光粼粼,如仙人銀白水袖飄落凡間。今天吃得豐盛,兩顆雞蛋、綠色蔬菜、水果拼盤,還有一小碗燕麥粥、一小杯優格。時間充裕,悠悠哉哉就著天光美景,每一口細嚼慢嚥。最後泡了一大杯美式咖啡,裝進保溫瓶上課去。
今天要去師大上密集班的心理課程。我不喜歡上課遲到,習慣開車較能掌握時間,這天路況卻出乎意料,時間有點緊,把車開到慣常停車的龍泉街內,這裡平日白天都有許多路邊停車位。我急忙停好車,背起書包拿著保溫瓶,小快步奔向教室。話說起來,這已經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
幾堂課下來並不輕鬆。上午小組討論,下午輪到我帶領個案,分配到不熟悉的領域,雖然準備了滿滿的資料,但心裡還是有點小壓力。
上完一整天課,心靈充實也很愉悅,拖著疲倦沉重的身軀走出校門,拐進熟悉的小巷內。車子呢?不見了!地上留著保管場的電話。回過神來看清楚,早上竟然把車停在黃線上。
一時之間,萬分懊惱……
「為什麼這麼不小心?為什麼不多看一眼?為什麼不提早出門?為什麼……為什麼……」突然,「黑猩猩」醒了,開始焦躁不安了,冒出嚴厲譴責,腦海裡出現排山倒海般的自我衝撞。
縱有千般理由似乎都不足以原諒自己。
「都是我的錯,怎麼搞的,每次都這樣,我怎麼老是闖禍……」
「賴佩霞,你糟透了!」
肩膀僵硬,心情盪到谷底,腦袋喋喋不休,重複埋怨自己的粗心大意。彷彿墜落無底深淵,兩旁峭壁寫滿著「都是你!」「活該!」「笨蛋!」「每次都這樣!」「去死好了!」……每一句都是重錘,狠狠把自己擊向深淵的底層。我雙手抱著腦袋,看看能不能讓裡面的叨唸停止。
自責中的聲音,聲音中的自責,萬馬奔騰相互廝殺。好累好累……
「STOP!」我突然間醒過來。
車子被拖吊,已經夠沮喪了,幹嘛還虐待自己?一聲聲責難,層層堆疊給自己施加的壓力,內外夾擊的雙重力道,有誰受得了?
想像腦前額有個粉紅色的「停止鍵」,輕輕按一下,順便跟自己說:「好了,可以了!」
吐一口長氣,鬆鬆肩膀,對自己說:「先弄清楚車子在哪裡。」
地上的粉筆字一行寫著車號,另一行寫著電話號碼。我告訴自己,放鬆,深呼吸,打電話,這應該是保管場的電話號碼。
招了輛計程車,搭車前往「贖」回我的愛車。
天色已黑,保管場有些偏僻,也有些空曠。雖然不怕黑,但環境有點陌生,幽暗中隱約看見一個小亭子。噢,前面還有人呢!一位穿西裝的先生拿著公事包,彎腰對著亭子裡的人比手劃腳。微弱的燈光,沒錯,前面的亭子應該就是辦公室。
他眉頭深鎖離開,輪到我。「一千八!」雖然有點心疼,可是,相較於不斷自責、內疚殺死自己那麼多細胞,該付出的總是要承擔,誰叫我貪快?繳罰款的瞬間還有些自責,同時也如釋重負,不是因為贖回車,而是腦袋終於停止它對我的綁架,內心焦躁的「黑猩猩」可以休息了。
再吸一口長氣,總算還給自己一個平靜的空間。
靜心,給腦袋空間
我們的「腦袋」如同電腦,儲存從小到大每天的生活體驗,經驗慢慢變成信念,因為習以為常,自然不會去懷疑它的合理性,久而久之也無法分辨那些信念到底對自己是利還是弊,是捏造的還是事實。
研讀心理學多年,但真正解決心中的焦慮,是在我心靜下來後,才明白原來總總問題都出自於這顆沒有被好好梳理的腦袋。
靜心,讓我不得不停下來,看看腦袋裡想的內容,跟心裡渴望的方向是否一致。比方說,我看到有人口口聲聲說想要幸福,但面對家人時卻毫無耐心,甚至口無遮攔。這時候我想問,這到底是在爭輸贏,還是在經營幸福?
談起改變,據我多年的觀察,一切必須從認識自己開始,尤其要了解自己腦袋的運作模式。每天最好能花一點時間,即使三、五分鐘,靜下來,看看多半的時間自己是被焦躁的「黑猩猩」挾持,還是被仁慈的「泰迪熊」撫慰。單單如此,生命的翻轉即將開始。
關心自己的起心動念,了解自己的行為模式,同時做出讓自己滿意的調整。
在前作《轉念的力量》中,我選了泰迪熊代表心中最柔軟、純淨和善良的一面。一面培養理性看世界的能力,一面著重發掘事實與真相,一面強調邏輯思考的重要,而最重要的,莫過於發展人性至善、寬容且利他的行為。
書中我曾經籠統描述「執念」是帶給人痛苦的最大主因,該怎麼辦呢?
偏偏人類就是靠著不服輸的執念,才能在面臨各種艱難險阻時成為贏家,存活下來。因此,我想帶入一個觀點,就是前文介紹過的我的「黑猩猩」,她喜歡贏,不喜歡輸。既然贏是身處叢林生態的生存本能,除了壓抑、鄙視和排斥,是否有其他安撫她的方法?答案是,有的!
靜心,讓我跳脫「好強」的輸贏機制,沉靜內觀,聽清楚哪些聲音其實是無意義的魔音。腦袋的碎唸,很多是來自從小被教導灌輸的觀念,我們甚至不曾檢視過它們是否屬實?說不定,只是過往認定為不可動搖的信念,今日無意識的任由「雜音」影響我們現在的情緒和思維,如同「我不夠好」、「都是我的錯」、「我無能」以及「我好可憐」等。
這就是我們的腦袋,如果不主動管理這些聲音,將永遠看不見真相。
「我不夠好。」真的嗎?
「都是我的錯。」真的嗎?
「我無能。」真的嗎?
「我好可憐。」真的嗎?
這些未經檢視的聲音,很多時候只會讓情緒更加低落,沒有任何好處。
給腦袋一些空間,靜心吧!靜心,也是淨心,停下來看看這些腦子裡的聲音,究竟是慣性思維,還是真相?我要說,負面的解讀,通常都是過去負面經驗的累積,現在可以賦予它新的解釋,別讓黑猩猩繼續掌控自己。
簡單來說,左腦關注的是「我」、「經驗值」這類事情,而右腦關注「我們」、「當下」的事情。以繪畫為例,作畫時,左腦注重技巧,擷取經驗值做分析、安排,而右腦專注於捕捉感受,感知當下環境的整體氛圍。傳統腦神經科學曾經用簡單的二分法,來定義我們的左右腦。
然而,人腦的構造非常微妙,難以用二分法講明白。
知名腦神經學家吉兒.泰勒歷經左腦中風的意外後,進一步研究發現,左右腦轄下各有掌管思考與情緒的區塊。根據泰勒的研究,同樣掌管思考,左右腦對訊息的感知與處理方式恰恰相反。
左腦掌管線性思考,注重經驗值、重次序,擅於做分析評斷和推測;右腦為體驗式思考,注重當下、動覺,專注於流動性。情緒方面,左腦的特性是焦慮驚恐小心翼翼,右腦卻是大膽冒險、創意無限,不受經驗值局限。
如果按照泰勒的理論,關掉頭腦的喋喋不休,嚴格來說是關掉左腦人格,將處理訊息的機制交給右腦專注在眼前當下,不受制於過去、不設想未來,不受焦慮驚恐阻礙,以信任、支持、友善對待自己、他人和環境。
「不就好了嘛!比起一早上台做報告,領車是多麼簡單的一件小事啊!」一念之間,就可以把自己從無止境的內在批判深淵拉上來。而事實是:我沒事、車沒事,大不了就折損荷包,換句話說,不就是將來遺產少了一千八百元給孩子而已。
重點在於,能清楚辨別自己的腦海裡,藏有一張既老舊又不斷重複跳針的舊唱片,既然明白了,接下來就必須耐著性子,試圖改寫播放的內容,同時持續培養新的腦神經迴路,才可能在未來有新的行為展現。
清明的活在當下
這一折騰,幾乎忘了身體的疲憊。此時此刻,只想快快回家洗香香、躺平。
坐進車裡,安慰自己,「以後小心一點就好了」,這次學到了教訓,貪快就要付出代價。下次再犯,就要做好被拖吊的心裡準備,沒什麼好囉唆的。
順利開車回家,一路專注留意每個轉彎、下坡,看清楚停車格線,慢慢將車子停進停車位,確定左右格線距離都妥當了,開車門、左腳伸出去踏實踩穩地面,左手扶好,緩緩起身站好,再去後座如數取出該帶回家的東西。然後,鎖好車門,再巡視一遍停車格周邊的情況,確定一切穩妥,怡然上樓。
一個一個動作清清楚楚!平常可能做著眼前的動作,腦袋卻想著另一件事,這樣真的不行。「以後盡量早點出門,不要心存僥倖!」等電梯時,也提醒自己,放鬆,把心思放在眼前的事物上。
禪宗老和尚的叮嚀油然響起:「砍柴即砍柴,擔水即擔水,做飯即做飯。」
回家打開門,望見牆上的時鐘,發現這樣一個動作、一個動作慢慢做,似乎在告訴自己:「我值得,同時也願意給出時間在自己身上。」對呀,慢慢來,為什麼不行?忽然覺得自己賺到了什麼意外之財,嘴角不禁上揚了起來。
臨睡前,把當天發生的事寫了下來。寫著寫著,內心突然湧起一股少有的靜謐祥和。寫完之後重讀一遍,托著雙頰,覺得自己今天過得還可以,有進步,明天繼續,再學著多疼愛自己一些。
我用雙手環抱自己,閉起眼。這時,想起每個人心中都希望有個慈祥的阿嬤。
如實如是體驗生命的開闊
我好渴望從小有個疼我、溺愛我的阿嬤。
不管發生什麼,阿嬤的反應都是,「啊,無要緊啦,來!阿嬤惜惜呼呼!」不過問對錯,不加以評斷,甚至不問發生什麼,一律都是抱抱安慰。緊接在惜惜後面的是,「餓不餓呀?想吃什麼?……」在阿嬤心裡,孫子不開心才是問題,如何讓孫子開心起來,才是阿嬤最在意的事。
阿嬤雖然不懂什麼是「同理心」,卻懂得疼惜,懂得如何無條件愛孫子。學習心理學以來,我發現優秀的諮商心理師角色有如溫暖的「阿嬤」,能接納人的軟弱,以寬容和支持的態度撫慰人心。
好渴望小時候身旁有個像阿嬤那樣能給我無盡寵溺的人。如果真有人能無時不刻給我安慰,心裡就不會傷痕累累吧?
發現車子被拖吊的當下,如果阿嬤在身旁,她會說:「無要緊啦,趕緊找車就好啊!」
對,就是這樣,不就好了嘛!當下,就能清醒的處理眼前的問題,而不陷入內在自我撻伐的深淵。
發現車子被拖吊,腦袋習慣性的即刻蹦出自責,而且相信那些聲音全是真的,因此情緒化的「黑猩猩」開始焦躁不安,不知如何是好。衝擊只是讓我愈來愈沮喪、難過;如果持續緊抓著那些念頭,只會更加強化對「自恨」的認同。
靜心,讓我看清楚事實的真相,不讓無意義的念頭阻礙我去覺知世界還有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的幸福,也因為腦袋的喋喋不休停了,「黑猩猩」才能放鬆下來。
靜心,既幫助我覺察左腦戒慎恐懼機制,又能隨右腦開啟靈性關懷層次,「如實如是」去體驗生命的開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