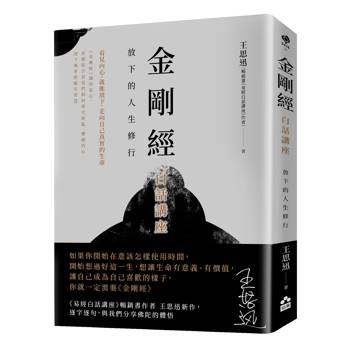第一堂課 譯本、經名及第一分
修行不是做什麼特別的事,
只是用心體會生活,並從中得到提升的力量
《金剛經》與《心經》這兩部佛經的知名度都非常高,也是一般人最常念誦的兩部佛經。
《心經》和《金剛經》的內容,推論可能都是根源自《大般若經》。《大般若經》總共有十四會,《心經》的內容與第二會的內容很接近,尤其是第四二一卷與第四二九卷。《金剛經》則與第九會的內容十分接近。所以,《金剛經》的主題和《心經》一樣,都是在講無上甚深的般若智慧,也就是空的智慧,但是兩者偏重的地方不太一樣。
什麼地方不同呢?我想跟大家分享兩點。第一個不同是:《心經》談「空」不談「心」,而《金剛經》則談「心」不談「空」。
不知大家注意到沒有,《心經》雖然經名出現「心」字,可是經文卻一個「心」字都沒有。相反地,《金剛經》的經名沒有「心」字,但是經文卻經常出現「心」字,總共出現了四十幾次之多。甚至,《金剛經》一開始就以「如何降伏其心」作為全經問答的核心,這等於是用一個「心」字,為我們敲開般若智慧的大門。
至於「空」字,《心經》篇幅極短,卻處處談「空」。開頭第三句,就用「照見五蘊皆空」切入經文的核心。之後又連續用了六個「空」字。這等於是用一個「空」字,為我們敲開般若智慧的大門。
《金剛經》全文五千多字,從頭到尾只出現三個「空」字。這三個「空」字,兩次指空間(東方虛空、上下虛空),一次指沒有(無空過者),這都不是佛教所談的「空」。所以才說,《心經》談「空」不談「心」,而《金剛經》則談「心」不直接談「空」。
第二個不一樣是,說法的對象不同。《心經》是針對智慧已有累積,或修行較深的人而說的法。而《金剛經》則是針對一般開始發願修行的善男子、善女人而說的法。
因此《心經》直接從「空」這個非常抽象的概念入手,其主要論點在「不二」與「無得」。「不二」是指不二分,這是般若智慧的妙用。「無得」則是指一切事物皆不可執著,連般若智慧本身也不可執著。這是《心經》談「空」的方法。它的文字雖然簡潔,但是對一般人來說,內容不是那麼容易懂。
但是,《金剛經》不直接談「空」,而是透過「心」來間接談「空」。因為「心」的所知所見即是五蘊之「相」,所以《金剛經》的主要論點在於「不住於相」。也就是要破我們的「心」對於「相」的執著。
說了這麼多,但是,究竟什麼是「般若」呢?「般若」是梵文的音譯,意思是在智慧之上的智慧。換句話說,它不是普通的聰明智慧,或敏捷巧思,而是高於一切智慧之智慧。
什麼是高於一切智慧之智慧?這好比有一個水池,我們是生活在水池裡的小魚,因為池中食物有限,所以每條魚都要發揮智慧,與其它魚競爭,想辦法吃到更多的食物,變成更大的魚。然而,有一條魚,牠不是想著如何與其它魚競爭,而是彷彿站在水池之外,看著自己所做的事,也看著其它魚所做的事,同時看著大家這樣做的原因,以及這樣做之後,得到的結果。當牠這樣站在局外,這樣站在一切之上,平靜地觀看自己,並不帶好惡地觀看所有事物時,就會逐漸看到一切事物運行的規律,甚至,會看到所有魚的命運,乃至整個水池的命運。在這個不涉入、無所求的觀看過程中,這條魚所領悟到的,必然是一種特別的智慧,一種洞見的智慧。
持續用這樣置身事物之上的角度觀看自己、觀看他人、觀看環境、觀看時空的變化,也觀看自己思維中的一切。這樣的觀看,與這樣的觀看所得到的理解,以及繼續用這樣的觀看來觀看理解,這就是智慧之上的智慧。
智慧之上的智慧讓我們知道,事情為何這樣或那樣發生,也讓我們知道,我們為何會有這樣或那樣的好惡反應。這一份知道,與這一份觀看的能力,讓我們對一切事物的發生與變化,擁有較大的包容與接受的能力。也讓我們對自身一切喜怒哀樂的感受,有較強的平衡與平撫的能力。
*****
在正式講《金剛經》之前,要先說明我們使用的譯本。《金剛經》有好幾種翻譯的版本,我們使用的是鳩摩羅什大師的譯本。但在講解經文時,某些地方也會參考玄奘大師的譯本。
根據鳩摩羅什大師的譯本,《金剛經》的全名是《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不過,根據玄奘大師的翻譯,《金剛經》全名是《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玄奘大師多了「能斷」這兩個字。
所謂的「金剛」,在梵文中是鑽石或閃電的意思。中文的解釋,認為「金剛」是可以摧毀一切,卻無法被一切所摧毀的東西。在古印度神話中,「金剛」也是統領天界的帝釋天所使用的兵器。所以藏傳佛教有「降魔金剛杵」的法器。
鳩摩羅什大師使用「金剛」一詞,是用來象徵般若智慧,表示般若智慧可以破除一切難以破除的無明煩惱。不過,若依玄奘的翻譯,「金剛」一詞反而是用來象徵無明煩惱。指無明煩惱雖然堅硬如「金剛」,但是,般若智慧依然可以將之破除。故稱「能斷」。
前面講過,「般若」是梵文的音譯,是智慧的意思。當然,這個智慧不是一般反應靈敏、思辨力強的那一種智慧。而是在一切智慧之上的智慧,是能解脫一切煩惱的智慧,也是來自我們的本心,人人都具備的智慧。
因為「般若」的含意比世人觀念中的智慧要深遠,所以許多佛法相關書籍中,常常直接使用音譯的「般若」二字,而不用智慧。
大家可能會覺得很奇怪,為什麼《金剛經》、《心經》,還有其它很多佛經,都在講「般若」呢?因為,「般若」思想是佛法非常重要的核心。如果拿掉「般若」,那麼佛法就失去了靈魂,甚至,我們也找不到另一條可以開悟、可以成佛的道路了。
禪宗的法師特別愛說,「佛」與「凡夫」沒有差別,只要「悟」了就是「佛」,若是「迷」了,那就是「凡夫」。而所謂的「悟」,其實就是指打開般若智慧。所謂的「迷」,就是指般若智慧還沒打開。
所以,一切佛法智慧,無論怎麼發揮作用,怎麼應用在現實生活中,怎麼幫助眾生解決問題,最後,這些智慧一定要歸結於能見到本心的般若智慧。至少也要越來越靠近般若智慧才行。如果任何智慧的應用,最後卻越來越遠離般若智慧,那麼這就一定不是來自佛法的智慧。這一點大家一定要分辨清楚。
「波羅蜜」一詞,是指「到達彼岸,得到解脫」的意思。「般若波羅蜜」就是「能讓人到達彼岸,得到解脫的般若智慧」。
但「波羅蜜」在梵文中,也有究竟、圓滿的意思。所以「般若波羅蜜」也可以解釋為「究竟圓滿的智慧」。
《金剛經》在最初剛翻譯成中文時,很多宗派都視之為「不了義經」。當時的人把佛經分為「了義」與「不了義」兩種。「了義經」是指這本佛經以說道理為主,而且把道理說得很清楚、很完整、很透徹,適合根器比較深的人閱讀。而「不了義經」則是這本佛經以說事情、說故事、說譬喻為主,雖然無法把道理說得很圓滿,很深入,卻很適合一般大眾閱讀。例如《阿彌陀經》與《地藏經》等,內容主要是在說故事,所以歸於「不了義經」。很奇怪的,《金剛經》不知是不是情節比較豐富,早期也被視為「不了義經」。當然,隨著時代的發展,這種說法慢慢就被改變了。
一提到《金剛經》,我們很容易就會想到禪宗。因為禪宗向來以《金剛經》為核心經典。例如我們去北投農禪寺,牆壁上刻著的就有《心經》與《金剛經》。還有一面大牆,上面寫著《金剛經》的名句:「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不過,大家要知道,《金剛經》成為禪宗的核心經典,是五祖弘忍與六祖慧能以後的事。在這之前,禪門裡主要讀誦的經典是《楞伽經》。但是《楞伽經》實在太艱深,太難讀了,名相又多,一般人很難讀懂。再加上六祖慧能是因為聽聞《金剛經》而開悟,而且五祖弘忍也以《金剛經》傳法,所以後來《金剛經》在禪門裡的地位,就逐漸取代了《楞伽經》。
因為之前有幾個同學問過如何閱讀《金剛經》,所以在正式講解經文之前,我想先跟大家分享我讀《金剛經》的經驗。有幾點建議,大家可以參考看看。
首先,讀經之前,不必急著明白經文的意思。
我們拿到一本佛經,可以先試著從各個方面跟這本經書結緣。例如仔細看看書的封面、背面,乃至版權頁,看看上面有沒有說明這經書是誰印的,印了多少本等等。也可以仔細撫摸紙面,感受它的材質,觀賞經文的字體,乃至聞聞紙張的味道等等。總之,就是要珍惜這本經,要好好感受,讓我們身體各種感官都與這本經書結緣。這是第一階段。
其次,就是常常讀它,而且要發出聲音讀,一字一句慢慢讀。雖然不必發出很大的聲音,但至少要讓自己的耳朵聽到自己發出來的聲音。每天至少抽出十五分鐘以上,每周至少抽出四天來讀。當然,能夠持之以恆,無一天間斷更好。這屬於第二階段,這階段最好能持續二、三周以上,而且只要念誦和聽自己唸出來的聲音就好,仍不必著急明白字句的意思。
接下來,第三階段,就是在經文中留意是否有一些字句,特別能打動你的內心。例如,我自己剛讀《金剛經》時,對「無實無虛」這四個字,特別有感觸,而且非常強烈,甚至強烈到彷彿全身觸電。之後還曾對「昔為歌利王割截身體」,以及「凡夫之人貪著其事」等字句,很有直覺的身心上的觸動。通常,在兩、三周的誦讀中,我們可能會對經中五到十個地方的字句,留下深刻的印象與觸動。這些地方,也許就是將來我們細讀經文時,負責帶領我們走向更深智慧的伏筆。
第四階段,是尋找適合的參考書,一字一句地理解,一字一句地體會。尤其是像《金剛經》、《心經》這樣的基本佛經,最好每一個字都不要放過。每次專心讀幾句就好,不必貪多,最好能在一百字以內。讀完後,閉目反覆感受,反覆回味五到十分鐘。如果能夠每天這樣讀半小時到一小時,大約二到三個月,就可以把《金剛經》細讀一遍。
第五階段,是每週至少一次,誦讀《金剛經》一遍。能持之以恆最好。如果不能持之以恆,至少也要在特別的日子,誦讀《金剛經》一遍。例如逢年過節,或者對你很重要的親友生日,甚至是身體不舒服的時候,都可以誦讀。當然,機緣合適的時候,能鼓勵別人也一起來誦讀《金剛經》,就更是一件好事了。
現在我們正式進入經文。
法會因由分第一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爾時,世尊食時,著衣持鉢,入舍衛大城乞食。於其城中,次第乞已,還至本處。飯食訖,收衣鉢,洗足已,敷座而坐。
鳩摩羅什翻譯的《金剛經》,全文五千多字(玄奘翻譯的則有八千多字),目前流通的版本,普遍把它分為三十二段,每一段各有一個名稱,例如「法會因由分第一」、「善現啟請分第二」等。有的版本則會寫成「第一品,法會因由分」、「第二品,善現啟請分」等。
此分名為法會因由分,意思就是記述這場說法集會的緣由。
大家要知道,一般佛經的段落與名稱,是原來經文中就有的。例如《法華經》的「序品第一」、「方便品第二」、「譬喻品第三」等。但是《金剛經》的段落與名稱並不是佛經原本即有,而是南北朝時期由昭明太子加上去的。
誰是昭明太子呢?昭明太子就是與達摩大師有一段精彩對話的梁武帝的兒子。梁武帝對中國佛教的影響與貢獻極大,例如漢地寺廟的全面素食,就來自梁武帝「制斷酒肉」的規定。又例如現在拜懺中所用的《梁皇寶懺》,也是梁武帝發起,並請誌公禪師制成的。
讀過中國文學史的人,一定聽過一本書叫《昭明文選》。這是中國第一部收集各種文學形式的選集,而負責主編的人就是昭明太子。《昭明文選》是中國第一本排除經史與諸子百家的觀點,著重於文學的角度所選出來的文集,這也等於表達了昭明太子對於「文學」的看法了。
這位擅長文學的太子,為了方便母親讀誦與理解《金剛經》,所以把經文分為三十二段,並給予名稱。後人覺得這個辦法很好,有助於閱讀,所以沿用至今。不過,也有些人反對這個做法,認為這是竄改佛經,罪過很大。所以,有一個傳言,說昭明太子因為加了這三十二分,死後墮入地獄,至今仍在地獄受苦云云。
雖然有這一則傳說,可是,很多講《金剛經》的法師,仍沿用昭明太子的分法,認為這個分法不但可以幫助初學者理解,也有功於此經的流通普及。由此可見,很多教內人士並不認同昭明太子入地獄的傳說。
講到這裡,我想也順道向大家說一個梁武帝與誌公禪師的有名故事。
有一次,梁武帝請誌公禪師看戲。看完後,問禪師,今天的戲演得如何?禪師回答不知道。武帝又問,那唱得如何呢?禪師仍回答不知道。武帝覺得奇怪,因為看戲時,禪師精神奕奕,並未睡覺,為什麼問什麼都說不知道呢?誌公禪師解釋,出家人時時用功辦道,面對生死,那有時間看戲!又說,陛下若不信,請找一個判死罪的犯人,命他捧一盆水在台前看戲,並對犯人說,等戲結束,若這水未灑出,立刻無罪開釋,若有水灑出,立即斬首。梁武帝便依誌公禪師的意思處理。隔日,看完戲,犯人捧的水,一滴都未灑出來。誌公便請梁武帝問犯人,今天的戲演得如何?唱得如何?結果犯人跟誌公一樣,都回答不知道。梁武帝問何故如此,犯人回說,因為心裡只顧著不讓水灑出來,所以無心看戲、聽戲。梁武帝當下大悟。
原來,修行是要以面對生死之心來修,才能有成就。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
一般佛經在開頭的地方,都有一句「如是我聞」,意思就是以下的經文內容,是「我」親耳聽到佛陀這樣說,然後把它記錄下來的。《金剛經》裡的「我」是誰呢?他就是佛陀十大弟子裡,人稱「多聞第一」的阿難尊者。
據說,阿難尊者的記憶力超越常人,佛陀圓寂之後,弟子聚集於王舍城,阿難把佛陀每一場法會的內容,全部背誦出來,經過眾弟子討論後,記錄成為佛經。當然,這只是傳說。從學術的角度來說,佛經以梵文紀錄,是陸陸續續完成的,中間長達兩三百年的時間(甚至更長),而且版本並不統一。例如《金剛經》現存的梵文版本就有四種之多,可見佛經並非完成於一人、一時、一地之手。
其次,佛經在一開始的時候,還會講述此次法會的「人、地、時、事」等因緣。所謂的「時」,就是時間。但因為古印度人不太重視時間,沒有明確的紀年,所以佛經只寫「一時」,表示有這樣一個時候。有些人認為,「一時」的說法大有深義,因為不特別註明某一年,即表示佛陀所說的佛法有永恆性,不限於任何時空。這個說法,大家也可以參考。
所謂的「人」,就是指在釋迦牟尼佛說法現場的聽眾。在這些聽眾中,有許多是我們肉眼看得到的,例如比丘僧眾、善男子、善女人等。也有許多是我們肉眼看不到的,例如天人、阿修羅、菩薩、各方護法神等等。例如此處說「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這就是看得見的出家人。
一千兩百五十人的場面,在佛陀的法會中,應該屬於中小型場面。例如《法華經》,參與其法會的出家人就有一萬兩千人之多。
所謂的「地」,就是講經的地點。經文說「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這個「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就是說法的地點。
(未完)
修行不是做什麼特別的事,
只是用心體會生活,並從中得到提升的力量
《金剛經》與《心經》這兩部佛經的知名度都非常高,也是一般人最常念誦的兩部佛經。
《心經》和《金剛經》的內容,推論可能都是根源自《大般若經》。《大般若經》總共有十四會,《心經》的內容與第二會的內容很接近,尤其是第四二一卷與第四二九卷。《金剛經》則與第九會的內容十分接近。所以,《金剛經》的主題和《心經》一樣,都是在講無上甚深的般若智慧,也就是空的智慧,但是兩者偏重的地方不太一樣。
什麼地方不同呢?我想跟大家分享兩點。第一個不同是:《心經》談「空」不談「心」,而《金剛經》則談「心」不談「空」。
不知大家注意到沒有,《心經》雖然經名出現「心」字,可是經文卻一個「心」字都沒有。相反地,《金剛經》的經名沒有「心」字,但是經文卻經常出現「心」字,總共出現了四十幾次之多。甚至,《金剛經》一開始就以「如何降伏其心」作為全經問答的核心,這等於是用一個「心」字,為我們敲開般若智慧的大門。
至於「空」字,《心經》篇幅極短,卻處處談「空」。開頭第三句,就用「照見五蘊皆空」切入經文的核心。之後又連續用了六個「空」字。這等於是用一個「空」字,為我們敲開般若智慧的大門。
《金剛經》全文五千多字,從頭到尾只出現三個「空」字。這三個「空」字,兩次指空間(東方虛空、上下虛空),一次指沒有(無空過者),這都不是佛教所談的「空」。所以才說,《心經》談「空」不談「心」,而《金剛經》則談「心」不直接談「空」。
第二個不一樣是,說法的對象不同。《心經》是針對智慧已有累積,或修行較深的人而說的法。而《金剛經》則是針對一般開始發願修行的善男子、善女人而說的法。
因此《心經》直接從「空」這個非常抽象的概念入手,其主要論點在「不二」與「無得」。「不二」是指不二分,這是般若智慧的妙用。「無得」則是指一切事物皆不可執著,連般若智慧本身也不可執著。這是《心經》談「空」的方法。它的文字雖然簡潔,但是對一般人來說,內容不是那麼容易懂。
但是,《金剛經》不直接談「空」,而是透過「心」來間接談「空」。因為「心」的所知所見即是五蘊之「相」,所以《金剛經》的主要論點在於「不住於相」。也就是要破我們的「心」對於「相」的執著。
說了這麼多,但是,究竟什麼是「般若」呢?「般若」是梵文的音譯,意思是在智慧之上的智慧。換句話說,它不是普通的聰明智慧,或敏捷巧思,而是高於一切智慧之智慧。
什麼是高於一切智慧之智慧?這好比有一個水池,我們是生活在水池裡的小魚,因為池中食物有限,所以每條魚都要發揮智慧,與其它魚競爭,想辦法吃到更多的食物,變成更大的魚。然而,有一條魚,牠不是想著如何與其它魚競爭,而是彷彿站在水池之外,看著自己所做的事,也看著其它魚所做的事,同時看著大家這樣做的原因,以及這樣做之後,得到的結果。當牠這樣站在局外,這樣站在一切之上,平靜地觀看自己,並不帶好惡地觀看所有事物時,就會逐漸看到一切事物運行的規律,甚至,會看到所有魚的命運,乃至整個水池的命運。在這個不涉入、無所求的觀看過程中,這條魚所領悟到的,必然是一種特別的智慧,一種洞見的智慧。
持續用這樣置身事物之上的角度觀看自己、觀看他人、觀看環境、觀看時空的變化,也觀看自己思維中的一切。這樣的觀看,與這樣的觀看所得到的理解,以及繼續用這樣的觀看來觀看理解,這就是智慧之上的智慧。
智慧之上的智慧讓我們知道,事情為何這樣或那樣發生,也讓我們知道,我們為何會有這樣或那樣的好惡反應。這一份知道,與這一份觀看的能力,讓我們對一切事物的發生與變化,擁有較大的包容與接受的能力。也讓我們對自身一切喜怒哀樂的感受,有較強的平衡與平撫的能力。
*****
在正式講《金剛經》之前,要先說明我們使用的譯本。《金剛經》有好幾種翻譯的版本,我們使用的是鳩摩羅什大師的譯本。但在講解經文時,某些地方也會參考玄奘大師的譯本。
根據鳩摩羅什大師的譯本,《金剛經》的全名是《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不過,根據玄奘大師的翻譯,《金剛經》全名是《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玄奘大師多了「能斷」這兩個字。
所謂的「金剛」,在梵文中是鑽石或閃電的意思。中文的解釋,認為「金剛」是可以摧毀一切,卻無法被一切所摧毀的東西。在古印度神話中,「金剛」也是統領天界的帝釋天所使用的兵器。所以藏傳佛教有「降魔金剛杵」的法器。
鳩摩羅什大師使用「金剛」一詞,是用來象徵般若智慧,表示般若智慧可以破除一切難以破除的無明煩惱。不過,若依玄奘的翻譯,「金剛」一詞反而是用來象徵無明煩惱。指無明煩惱雖然堅硬如「金剛」,但是,般若智慧依然可以將之破除。故稱「能斷」。
前面講過,「般若」是梵文的音譯,是智慧的意思。當然,這個智慧不是一般反應靈敏、思辨力強的那一種智慧。而是在一切智慧之上的智慧,是能解脫一切煩惱的智慧,也是來自我們的本心,人人都具備的智慧。
因為「般若」的含意比世人觀念中的智慧要深遠,所以許多佛法相關書籍中,常常直接使用音譯的「般若」二字,而不用智慧。
大家可能會覺得很奇怪,為什麼《金剛經》、《心經》,還有其它很多佛經,都在講「般若」呢?因為,「般若」思想是佛法非常重要的核心。如果拿掉「般若」,那麼佛法就失去了靈魂,甚至,我們也找不到另一條可以開悟、可以成佛的道路了。
禪宗的法師特別愛說,「佛」與「凡夫」沒有差別,只要「悟」了就是「佛」,若是「迷」了,那就是「凡夫」。而所謂的「悟」,其實就是指打開般若智慧。所謂的「迷」,就是指般若智慧還沒打開。
所以,一切佛法智慧,無論怎麼發揮作用,怎麼應用在現實生活中,怎麼幫助眾生解決問題,最後,這些智慧一定要歸結於能見到本心的般若智慧。至少也要越來越靠近般若智慧才行。如果任何智慧的應用,最後卻越來越遠離般若智慧,那麼這就一定不是來自佛法的智慧。這一點大家一定要分辨清楚。
「波羅蜜」一詞,是指「到達彼岸,得到解脫」的意思。「般若波羅蜜」就是「能讓人到達彼岸,得到解脫的般若智慧」。
但「波羅蜜」在梵文中,也有究竟、圓滿的意思。所以「般若波羅蜜」也可以解釋為「究竟圓滿的智慧」。
《金剛經》在最初剛翻譯成中文時,很多宗派都視之為「不了義經」。當時的人把佛經分為「了義」與「不了義」兩種。「了義經」是指這本佛經以說道理為主,而且把道理說得很清楚、很完整、很透徹,適合根器比較深的人閱讀。而「不了義經」則是這本佛經以說事情、說故事、說譬喻為主,雖然無法把道理說得很圓滿,很深入,卻很適合一般大眾閱讀。例如《阿彌陀經》與《地藏經》等,內容主要是在說故事,所以歸於「不了義經」。很奇怪的,《金剛經》不知是不是情節比較豐富,早期也被視為「不了義經」。當然,隨著時代的發展,這種說法慢慢就被改變了。
一提到《金剛經》,我們很容易就會想到禪宗。因為禪宗向來以《金剛經》為核心經典。例如我們去北投農禪寺,牆壁上刻著的就有《心經》與《金剛經》。還有一面大牆,上面寫著《金剛經》的名句:「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不過,大家要知道,《金剛經》成為禪宗的核心經典,是五祖弘忍與六祖慧能以後的事。在這之前,禪門裡主要讀誦的經典是《楞伽經》。但是《楞伽經》實在太艱深,太難讀了,名相又多,一般人很難讀懂。再加上六祖慧能是因為聽聞《金剛經》而開悟,而且五祖弘忍也以《金剛經》傳法,所以後來《金剛經》在禪門裡的地位,就逐漸取代了《楞伽經》。
因為之前有幾個同學問過如何閱讀《金剛經》,所以在正式講解經文之前,我想先跟大家分享我讀《金剛經》的經驗。有幾點建議,大家可以參考看看。
首先,讀經之前,不必急著明白經文的意思。
我們拿到一本佛經,可以先試著從各個方面跟這本經書結緣。例如仔細看看書的封面、背面,乃至版權頁,看看上面有沒有說明這經書是誰印的,印了多少本等等。也可以仔細撫摸紙面,感受它的材質,觀賞經文的字體,乃至聞聞紙張的味道等等。總之,就是要珍惜這本經,要好好感受,讓我們身體各種感官都與這本經書結緣。這是第一階段。
其次,就是常常讀它,而且要發出聲音讀,一字一句慢慢讀。雖然不必發出很大的聲音,但至少要讓自己的耳朵聽到自己發出來的聲音。每天至少抽出十五分鐘以上,每周至少抽出四天來讀。當然,能夠持之以恆,無一天間斷更好。這屬於第二階段,這階段最好能持續二、三周以上,而且只要念誦和聽自己唸出來的聲音就好,仍不必著急明白字句的意思。
接下來,第三階段,就是在經文中留意是否有一些字句,特別能打動你的內心。例如,我自己剛讀《金剛經》時,對「無實無虛」這四個字,特別有感觸,而且非常強烈,甚至強烈到彷彿全身觸電。之後還曾對「昔為歌利王割截身體」,以及「凡夫之人貪著其事」等字句,很有直覺的身心上的觸動。通常,在兩、三周的誦讀中,我們可能會對經中五到十個地方的字句,留下深刻的印象與觸動。這些地方,也許就是將來我們細讀經文時,負責帶領我們走向更深智慧的伏筆。
第四階段,是尋找適合的參考書,一字一句地理解,一字一句地體會。尤其是像《金剛經》、《心經》這樣的基本佛經,最好每一個字都不要放過。每次專心讀幾句就好,不必貪多,最好能在一百字以內。讀完後,閉目反覆感受,反覆回味五到十分鐘。如果能夠每天這樣讀半小時到一小時,大約二到三個月,就可以把《金剛經》細讀一遍。
第五階段,是每週至少一次,誦讀《金剛經》一遍。能持之以恆最好。如果不能持之以恆,至少也要在特別的日子,誦讀《金剛經》一遍。例如逢年過節,或者對你很重要的親友生日,甚至是身體不舒服的時候,都可以誦讀。當然,機緣合適的時候,能鼓勵別人也一起來誦讀《金剛經》,就更是一件好事了。
現在我們正式進入經文。
法會因由分第一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爾時,世尊食時,著衣持鉢,入舍衛大城乞食。於其城中,次第乞已,還至本處。飯食訖,收衣鉢,洗足已,敷座而坐。
鳩摩羅什翻譯的《金剛經》,全文五千多字(玄奘翻譯的則有八千多字),目前流通的版本,普遍把它分為三十二段,每一段各有一個名稱,例如「法會因由分第一」、「善現啟請分第二」等。有的版本則會寫成「第一品,法會因由分」、「第二品,善現啟請分」等。
此分名為法會因由分,意思就是記述這場說法集會的緣由。
大家要知道,一般佛經的段落與名稱,是原來經文中就有的。例如《法華經》的「序品第一」、「方便品第二」、「譬喻品第三」等。但是《金剛經》的段落與名稱並不是佛經原本即有,而是南北朝時期由昭明太子加上去的。
誰是昭明太子呢?昭明太子就是與達摩大師有一段精彩對話的梁武帝的兒子。梁武帝對中國佛教的影響與貢獻極大,例如漢地寺廟的全面素食,就來自梁武帝「制斷酒肉」的規定。又例如現在拜懺中所用的《梁皇寶懺》,也是梁武帝發起,並請誌公禪師制成的。
讀過中國文學史的人,一定聽過一本書叫《昭明文選》。這是中國第一部收集各種文學形式的選集,而負責主編的人就是昭明太子。《昭明文選》是中國第一本排除經史與諸子百家的觀點,著重於文學的角度所選出來的文集,這也等於表達了昭明太子對於「文學」的看法了。
這位擅長文學的太子,為了方便母親讀誦與理解《金剛經》,所以把經文分為三十二段,並給予名稱。後人覺得這個辦法很好,有助於閱讀,所以沿用至今。不過,也有些人反對這個做法,認為這是竄改佛經,罪過很大。所以,有一個傳言,說昭明太子因為加了這三十二分,死後墮入地獄,至今仍在地獄受苦云云。
雖然有這一則傳說,可是,很多講《金剛經》的法師,仍沿用昭明太子的分法,認為這個分法不但可以幫助初學者理解,也有功於此經的流通普及。由此可見,很多教內人士並不認同昭明太子入地獄的傳說。
講到這裡,我想也順道向大家說一個梁武帝與誌公禪師的有名故事。
有一次,梁武帝請誌公禪師看戲。看完後,問禪師,今天的戲演得如何?禪師回答不知道。武帝又問,那唱得如何呢?禪師仍回答不知道。武帝覺得奇怪,因為看戲時,禪師精神奕奕,並未睡覺,為什麼問什麼都說不知道呢?誌公禪師解釋,出家人時時用功辦道,面對生死,那有時間看戲!又說,陛下若不信,請找一個判死罪的犯人,命他捧一盆水在台前看戲,並對犯人說,等戲結束,若這水未灑出,立刻無罪開釋,若有水灑出,立即斬首。梁武帝便依誌公禪師的意思處理。隔日,看完戲,犯人捧的水,一滴都未灑出來。誌公便請梁武帝問犯人,今天的戲演得如何?唱得如何?結果犯人跟誌公一樣,都回答不知道。梁武帝問何故如此,犯人回說,因為心裡只顧著不讓水灑出來,所以無心看戲、聽戲。梁武帝當下大悟。
原來,修行是要以面對生死之心來修,才能有成就。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
一般佛經在開頭的地方,都有一句「如是我聞」,意思就是以下的經文內容,是「我」親耳聽到佛陀這樣說,然後把它記錄下來的。《金剛經》裡的「我」是誰呢?他就是佛陀十大弟子裡,人稱「多聞第一」的阿難尊者。
據說,阿難尊者的記憶力超越常人,佛陀圓寂之後,弟子聚集於王舍城,阿難把佛陀每一場法會的內容,全部背誦出來,經過眾弟子討論後,記錄成為佛經。當然,這只是傳說。從學術的角度來說,佛經以梵文紀錄,是陸陸續續完成的,中間長達兩三百年的時間(甚至更長),而且版本並不統一。例如《金剛經》現存的梵文版本就有四種之多,可見佛經並非完成於一人、一時、一地之手。
其次,佛經在一開始的時候,還會講述此次法會的「人、地、時、事」等因緣。所謂的「時」,就是時間。但因為古印度人不太重視時間,沒有明確的紀年,所以佛經只寫「一時」,表示有這樣一個時候。有些人認為,「一時」的說法大有深義,因為不特別註明某一年,即表示佛陀所說的佛法有永恆性,不限於任何時空。這個說法,大家也可以參考。
所謂的「人」,就是指在釋迦牟尼佛說法現場的聽眾。在這些聽眾中,有許多是我們肉眼看得到的,例如比丘僧眾、善男子、善女人等。也有許多是我們肉眼看不到的,例如天人、阿修羅、菩薩、各方護法神等等。例如此處說「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這就是看得見的出家人。
一千兩百五十人的場面,在佛陀的法會中,應該屬於中小型場面。例如《法華經》,參與其法會的出家人就有一萬兩千人之多。
所謂的「地」,就是講經的地點。經文說「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這個「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就是說法的地點。
(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