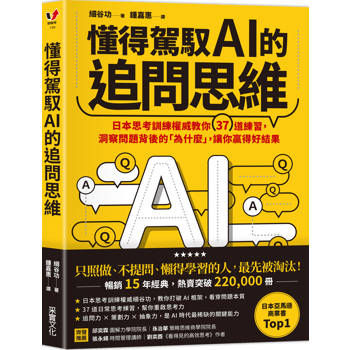洞察世界的「恆變」與「不變」
回顧過去十四年,我們歷經了日本311大地震與新冠疫情(COVID-19)等重大災難。同時,氣候變遷與地緣政治風險日益加劇,從俄烏戰爭到以色列與加薩的衝突,國際局勢動盪不安,進一步強化了我們所處的「VUCA時代」——一個高度易變、充滿不確定、複雜且模糊的世界。
此外,數位科技與生物科技的快速發展,也深刻地改變著全球與我們的日常生活。尤其是以智慧型手機與社群平台為代表的數位技術,透過「數位轉型」悄悄地、一點一滴地重塑著我們的生活方式。如今,不論工作、溝通還是休閒,幾乎一切都圍繞著手機進行。搭乘電車時環顧四周,你會發現幾乎所有人都在滑手機,而其中大多數人正沉浸在社群媒體中。這樣的景象,是自2008年智慧型手機普及以來,在十四年間逐漸形成的日常風景。
如果我們進一步設想未來十五年,今天透過智慧型手機與社群平台進行的種種活動,很可能將逐步轉移至下一個平台——無論是穿戴式裝置、自動駕駛技術,或是虛擬實境(VR)與元宇宙。
而在這些巨變之中,有一項關鍵價值從未改變,反而更顯重要:獨立思考的能力。這也是本書《懂得駕馭AI的追問思維》持續強調的核心理念。過去穩定時期所倚重的,是知識與經驗的累積——一種「被動式學習」的模式;如今面對瞬息萬變的局勢,我們更需要的是靈活應對與主動出擊的「主動思維力」。因此,本書的價值不僅與初版相同,甚至可以說,比當時更加重要。
那麼,這十四年間,真正改變的是什麼?
一項關鍵性的變化是:對獨立思考的最大挑戰,已從「網路搜尋」進一步轉向「人工智慧」(AI)。以 ChatGPT為代表的生成式AI,自2022年底橫空出世後,在短時間內迅速普及至全球數億用戶。
當年搜尋引擎「什麼都能查」的便利,早已讓不少人習慣不再思考;而如今,AI 不僅能查,還能「整理資料並給出答案」。在這個「不必動腦也能解決問題」的時代,思考與不思考之間的差距只會越拉越大。換句話說,那些願意深思熟慮的人與那些放棄思考的人之間,正出現一種殘酷的分化。
如今的兩極化,不再只是貧富差距的問題,更深層的斷裂,來自於「是否還在思考」。在一個由無形的金融與數位科技主導有形世界的社會裡,是否具備掌握抽象概念的能力,將決定我們能走多遠、站多高。
而AI的持續進化與擴散,不僅正在加速這場分化,也將引領人類邁向全然不同的階段。從「什麼都能查」的搜尋引擎,到「什麼都能整理出結論」的AI平台,這場轉變一方面加速人類的思考停滯,另一方面卻也大幅放大那些懂得駕馭技術者的能力與優勢。
不只解決問題,更要發現問題
在這樣的時代,特別重要的,是提出問題的能力。換句話說,就是發現問題的能力。
所謂問題發現,位於問題解決流程的最上游。它關乎我們能否辨識出真正的問題,也就是能否思考:「究竟哪裡出了問題?」當AI逐漸具備回答各式問題的能力,人類若只是被動接收問題並尋找解方,勢必會一個個被AI超越。此時,對人類而言,最需要思考的就變成:「我們希望AI協助解決的是哪些問題?」
這並不是人類與AI能力高低的比較,而是角色分工的重新釐清。
從技術發展的角度來看,也許有一天,連「發現問題」這件事本身,AI也能做得比人類更好。不過,只要AI仍被視為協助人類解決課題的工具,真正該問的問題就不是「誰做得比較好」,而是「AI究竟是為了解決誰的問題而存在」。
如果人類選擇將判斷與選擇交給AI,未來的生活也許就會變成:由AI發現問題、由AI提出解決方案,而人類則照著AI的指示過生活。也許有些人會選擇這樣的方式,但大多數人應該還是希望過自己選擇的人生。
既然如此,「究竟應該解決什麼問題」,就必須由人類主動思考。而這正是需要主動思維能力的時候。特別是能夠不斷反思與探究人生目的的那種思維,也就是本書所提倡的「追問思維」(Why型思考力)。
從具體到抽象:追問與策劃的思考力
除了AI技術的演進,我近年的寫作觀點也有了新的發展,特別是將「具體與抽象」作為理解思考力的主要切入點。
事實上,本書原版所提出的觀念,本就隱含這層脈絡,只是在當時,並未特別使用「具體與抽象」這樣的詞彙。
近年來,我更清楚說明:「Why」(為什麼)是一種能從手段指向目的的提問方式,有助於將具體行動提升到更抽象的理解層次;而「How」(怎麼做)則是從目標出發,回推到具體做法的過程。這兩個提問方向,都是思考中非常重要的起點。
「Why」這類提問,會引導人們進入抽象的思考過程。相較於其他四個W(何時、何地、誰、做了什麼),這類問題更難掌握,但也能帶來更深層的洞察與轉變。
最後,也想提醒一下:本書中有不少描述主管與部屬互動的情節。隨著社會對各種職場不當行為的敏感度提升,過去那些充滿熱情的指導語氣,如今可能被解讀為壓迫式溝通。本書保留了一些這樣的案例,並於相關段落加註說明,請讀者在閱讀時斟酌理解。
用練習,讓思考變成日常
為了呼應這次的新版主軸,我們在原版內容之外,於各章增添了練習題。正文部分則基於當時的結構,盡可能不做更動,而是透過25道題目,明確標示出希望讀者親自思考的段落。
加上新加入的題目,全書共有37題練習題,也因此,我們將書名調整為現在的《懂得駕馭AI的追問思維》。
Why型思考,並不是抽象難解的理論,其實可以應用在每天的生活中,只要你願意帶著意識去實踐,就會發現這套思維方式幾乎處處可用。正因如此,想讓這種思考方式內化為日常習慣,從身邊的話題開始練習是很有效的方式。因此,本書也補充了幾道生活化的練習題,提供你在日常中反覆練習的機會。
那麼,你對AI時代的未來有什麼想像?
有人對這場變革感到期待,有人則感到焦慮。這兩種感受,其實都很自然。但我相信,當你掌握了正確的思考工具,就能將不安轉化為行動,甚至帶著一點興奮,去迎接新的未來。
希望這本書,能成為你邁向明確未來的參考指南,也讓你的每一天都更接近你真正想要的樣子。
你覺得「朝令夕改」是好事,還是壞事?
有人說「朝令夕改」很沒原則,你怎麼看?
有句話叫作「朝令夕改」,意思是「早上才剛下的命令,傍晚就已經改變」,源自中國古代經典《漢書》。
在職場上,這個詞有時帶有正面意涵,有時則帶有負面評價。例如,聽到某位領導者被稱為「朝令夕改型」時,你會聯想到什麼?也許第一個浮現的,是「說話反覆、缺乏一貫性」等負面印象;但也有人會想到「靈活調整、能迅速因應環境」這樣的優點。
這種看似矛盾的雙重印象,其實可以用我們前面提到的觀點來解釋。「朝令夕改」本身就包含了兩個層次:「本質」(Why)與「表象」(What)。
剛才那些正負兩面的說法,正好分別對應到這兩個層次。也就是說,我們可以區分為「本質層次的朝令夕改」與「表象層次的朝令夕改」。
所謂「本質層次的朝令夕改」,指的是對事情的根本理由與思考依據搖擺不定,也就是缺乏清晰的判斷軸心。在這種情況下,即使不斷下指令改方針,其他人也只會被搞得無所適從,不會產生任何正面效果。
相對地,「表象層次的朝令夕改」則是指核心思維保持穩定,在此基礎上根據情勢變化,靈活調整做法與手段。只要本質清楚穩定,行動的調整就不是搖擺,而是策略性的反應。這種應變能力,正是一位成熟領導者不可或缺的特質。
這也可以說是「本質的一貫性」與「表象的一貫性」之間的差別。堅持本質、方向穩定的人,通常被認為是值得信賴的;但如果環境已經改變,卻仍墨守原來的行動模式,那麼這樣的「表象一貫性」反而會顯得固執、不知變通。
此外,有些人重視「誰說的話總是可信」(Who的一貫性),也有些人重視「只要時機對,什麼都可以調整」(When的一貫性)。我們經常說某人「有一貫性」或「沒有一貫性」,但其實,即使被認為反覆無常的人,從他自身角度來看,也未必毫無準則。
只不過,他所堅持的一貫性,是來自本質?表象?還是特定的人或時機?這樣的差異,會造成他人在評價時的不同解讀。
那麼,回過頭來看,你過去口中的「一貫性」,究竟是指哪一種呢?
開發新商品時,該不該聽顧客的意見?
顧客的回饋該當成方向指引?
還是會讓你偏離初心、誤入歧途?
接下來,讓我們來思考在企劃和開發新商品或服務時,「顧客心聲」的表象(照做思維)與本質(追問思維)之間的差異。
長久以來流傳一句話:為了設計出好的商品,要傾聽顧客的聲音。然而,照做思維與追問思維對此的態度截然不同。
開發新商品時,顧客的需求始終是最重要的。技術與創新固然關鍵,但前提是必須能回應某些尚未被滿足的顧客需求。這些需求可分為兩類:可見的顧客要求(照做思維所對應)與尚未說出口的真正動機(追問思維所關注)。本章最後的表格也整理了這兩者的差異。
從基本態度來看,照做型是從「現有的事物」出發;而追問型則從「目前還不存在,但能滿足內在渴望的事物」為起點。所謂「現有的事物」,包括自家商品或競爭對手的商品。照做型的做法包括模仿市面熱賣產品、將其納入自家陣容,或直接依顧客反映進行小幅調整。
相對地,追問型的商品開發不是模仿熱賣商品,而是試圖探究:為什麼這些商品會受到喜愛?從中歸納出背後的共同動機(例如:「平價卻不廉價」、「可以不張揚地展現自我」等),並以全新形式將其轉化推出。這種方法強調忠於核心需求,不僅僅停留在表層。
可見,照做思維偏向延續與改良,是漸進式創新;追問思維則關注根本改變,是更具開創性的方式。
這些差異也可從「顧客的聲音」角度看出。照做型會將顧客表達的內容直接反映於產品中,問題在於顧客往往並非產品專家,因此多數意見都是根據操作經驗提出的反饋,甚至是抱怨。例如:「這個旋鈕太難轉」、「畫面配置看起來不順」等。
另一類照做型的要求,是想補上競品已有而自家缺乏的功能。這些要求多半只是表層的補強,而非真正的創新,也只能讓產品勉強追上對手,仍舊缺乏突破。
而追問思維則重視顧客「未說出口的內心渴望」,這些動機有時甚至與他們口頭表達的需求相反。許多優秀的企劃人會說:「別太相信顧客說的話。」這不是不重視顧客,而是希望設計者能夠看見話語背後真正的渴望。這點與單靠技術導向、忽略市場反應的設計截然不同。
這樣的情況在各公司皆常見。一線業務人員常會全盤接收顧客的反饋,並抱怨:「我們明知道這樣會大賣,為何公司不做?」這類說法的陷阱有兩個:第一,這些要求多半只是表面的照做型需求;第二,正因為是照做型,所以通常已經落後潮流。若貿然依此開發產品,等上市時需求可能早已轉變,結果產品與現實需求脫節。
簡言之,從「目前熱賣的東西」出發,是照做型企劃;而思考「有沒有什麼還不存在但可能會熱賣的東西」,則是追問型企劃。照做型認為要搭上潮流,追問型則致力於創造潮流。
回顧過去十四年,我們歷經了日本311大地震與新冠疫情(COVID-19)等重大災難。同時,氣候變遷與地緣政治風險日益加劇,從俄烏戰爭到以色列與加薩的衝突,國際局勢動盪不安,進一步強化了我們所處的「VUCA時代」——一個高度易變、充滿不確定、複雜且模糊的世界。
此外,數位科技與生物科技的快速發展,也深刻地改變著全球與我們的日常生活。尤其是以智慧型手機與社群平台為代表的數位技術,透過「數位轉型」悄悄地、一點一滴地重塑著我們的生活方式。如今,不論工作、溝通還是休閒,幾乎一切都圍繞著手機進行。搭乘電車時環顧四周,你會發現幾乎所有人都在滑手機,而其中大多數人正沉浸在社群媒體中。這樣的景象,是自2008年智慧型手機普及以來,在十四年間逐漸形成的日常風景。
如果我們進一步設想未來十五年,今天透過智慧型手機與社群平台進行的種種活動,很可能將逐步轉移至下一個平台——無論是穿戴式裝置、自動駕駛技術,或是虛擬實境(VR)與元宇宙。
而在這些巨變之中,有一項關鍵價值從未改變,反而更顯重要:獨立思考的能力。這也是本書《懂得駕馭AI的追問思維》持續強調的核心理念。過去穩定時期所倚重的,是知識與經驗的累積——一種「被動式學習」的模式;如今面對瞬息萬變的局勢,我們更需要的是靈活應對與主動出擊的「主動思維力」。因此,本書的價值不僅與初版相同,甚至可以說,比當時更加重要。
那麼,這十四年間,真正改變的是什麼?
一項關鍵性的變化是:對獨立思考的最大挑戰,已從「網路搜尋」進一步轉向「人工智慧」(AI)。以 ChatGPT為代表的生成式AI,自2022年底橫空出世後,在短時間內迅速普及至全球數億用戶。
當年搜尋引擎「什麼都能查」的便利,早已讓不少人習慣不再思考;而如今,AI 不僅能查,還能「整理資料並給出答案」。在這個「不必動腦也能解決問題」的時代,思考與不思考之間的差距只會越拉越大。換句話說,那些願意深思熟慮的人與那些放棄思考的人之間,正出現一種殘酷的分化。
如今的兩極化,不再只是貧富差距的問題,更深層的斷裂,來自於「是否還在思考」。在一個由無形的金融與數位科技主導有形世界的社會裡,是否具備掌握抽象概念的能力,將決定我們能走多遠、站多高。
而AI的持續進化與擴散,不僅正在加速這場分化,也將引領人類邁向全然不同的階段。從「什麼都能查」的搜尋引擎,到「什麼都能整理出結論」的AI平台,這場轉變一方面加速人類的思考停滯,另一方面卻也大幅放大那些懂得駕馭技術者的能力與優勢。
不只解決問題,更要發現問題
在這樣的時代,特別重要的,是提出問題的能力。換句話說,就是發現問題的能力。
所謂問題發現,位於問題解決流程的最上游。它關乎我們能否辨識出真正的問題,也就是能否思考:「究竟哪裡出了問題?」當AI逐漸具備回答各式問題的能力,人類若只是被動接收問題並尋找解方,勢必會一個個被AI超越。此時,對人類而言,最需要思考的就變成:「我們希望AI協助解決的是哪些問題?」
這並不是人類與AI能力高低的比較,而是角色分工的重新釐清。
從技術發展的角度來看,也許有一天,連「發現問題」這件事本身,AI也能做得比人類更好。不過,只要AI仍被視為協助人類解決課題的工具,真正該問的問題就不是「誰做得比較好」,而是「AI究竟是為了解決誰的問題而存在」。
如果人類選擇將判斷與選擇交給AI,未來的生活也許就會變成:由AI發現問題、由AI提出解決方案,而人類則照著AI的指示過生活。也許有些人會選擇這樣的方式,但大多數人應該還是希望過自己選擇的人生。
既然如此,「究竟應該解決什麼問題」,就必須由人類主動思考。而這正是需要主動思維能力的時候。特別是能夠不斷反思與探究人生目的的那種思維,也就是本書所提倡的「追問思維」(Why型思考力)。
從具體到抽象:追問與策劃的思考力
除了AI技術的演進,我近年的寫作觀點也有了新的發展,特別是將「具體與抽象」作為理解思考力的主要切入點。
事實上,本書原版所提出的觀念,本就隱含這層脈絡,只是在當時,並未特別使用「具體與抽象」這樣的詞彙。
近年來,我更清楚說明:「Why」(為什麼)是一種能從手段指向目的的提問方式,有助於將具體行動提升到更抽象的理解層次;而「How」(怎麼做)則是從目標出發,回推到具體做法的過程。這兩個提問方向,都是思考中非常重要的起點。
「Why」這類提問,會引導人們進入抽象的思考過程。相較於其他四個W(何時、何地、誰、做了什麼),這類問題更難掌握,但也能帶來更深層的洞察與轉變。
最後,也想提醒一下:本書中有不少描述主管與部屬互動的情節。隨著社會對各種職場不當行為的敏感度提升,過去那些充滿熱情的指導語氣,如今可能被解讀為壓迫式溝通。本書保留了一些這樣的案例,並於相關段落加註說明,請讀者在閱讀時斟酌理解。
用練習,讓思考變成日常
為了呼應這次的新版主軸,我們在原版內容之外,於各章增添了練習題。正文部分則基於當時的結構,盡可能不做更動,而是透過25道題目,明確標示出希望讀者親自思考的段落。
加上新加入的題目,全書共有37題練習題,也因此,我們將書名調整為現在的《懂得駕馭AI的追問思維》。
Why型思考,並不是抽象難解的理論,其實可以應用在每天的生活中,只要你願意帶著意識去實踐,就會發現這套思維方式幾乎處處可用。正因如此,想讓這種思考方式內化為日常習慣,從身邊的話題開始練習是很有效的方式。因此,本書也補充了幾道生活化的練習題,提供你在日常中反覆練習的機會。
那麼,你對AI時代的未來有什麼想像?
有人對這場變革感到期待,有人則感到焦慮。這兩種感受,其實都很自然。但我相信,當你掌握了正確的思考工具,就能將不安轉化為行動,甚至帶著一點興奮,去迎接新的未來。
希望這本書,能成為你邁向明確未來的參考指南,也讓你的每一天都更接近你真正想要的樣子。
你覺得「朝令夕改」是好事,還是壞事?
有人說「朝令夕改」很沒原則,你怎麼看?
有句話叫作「朝令夕改」,意思是「早上才剛下的命令,傍晚就已經改變」,源自中國古代經典《漢書》。
在職場上,這個詞有時帶有正面意涵,有時則帶有負面評價。例如,聽到某位領導者被稱為「朝令夕改型」時,你會聯想到什麼?也許第一個浮現的,是「說話反覆、缺乏一貫性」等負面印象;但也有人會想到「靈活調整、能迅速因應環境」這樣的優點。
這種看似矛盾的雙重印象,其實可以用我們前面提到的觀點來解釋。「朝令夕改」本身就包含了兩個層次:「本質」(Why)與「表象」(What)。
剛才那些正負兩面的說法,正好分別對應到這兩個層次。也就是說,我們可以區分為「本質層次的朝令夕改」與「表象層次的朝令夕改」。
所謂「本質層次的朝令夕改」,指的是對事情的根本理由與思考依據搖擺不定,也就是缺乏清晰的判斷軸心。在這種情況下,即使不斷下指令改方針,其他人也只會被搞得無所適從,不會產生任何正面效果。
相對地,「表象層次的朝令夕改」則是指核心思維保持穩定,在此基礎上根據情勢變化,靈活調整做法與手段。只要本質清楚穩定,行動的調整就不是搖擺,而是策略性的反應。這種應變能力,正是一位成熟領導者不可或缺的特質。
這也可以說是「本質的一貫性」與「表象的一貫性」之間的差別。堅持本質、方向穩定的人,通常被認為是值得信賴的;但如果環境已經改變,卻仍墨守原來的行動模式,那麼這樣的「表象一貫性」反而會顯得固執、不知變通。
此外,有些人重視「誰說的話總是可信」(Who的一貫性),也有些人重視「只要時機對,什麼都可以調整」(When的一貫性)。我們經常說某人「有一貫性」或「沒有一貫性」,但其實,即使被認為反覆無常的人,從他自身角度來看,也未必毫無準則。
只不過,他所堅持的一貫性,是來自本質?表象?還是特定的人或時機?這樣的差異,會造成他人在評價時的不同解讀。
那麼,回過頭來看,你過去口中的「一貫性」,究竟是指哪一種呢?
開發新商品時,該不該聽顧客的意見?
顧客的回饋該當成方向指引?
還是會讓你偏離初心、誤入歧途?
接下來,讓我們來思考在企劃和開發新商品或服務時,「顧客心聲」的表象(照做思維)與本質(追問思維)之間的差異。
長久以來流傳一句話:為了設計出好的商品,要傾聽顧客的聲音。然而,照做思維與追問思維對此的態度截然不同。
開發新商品時,顧客的需求始終是最重要的。技術與創新固然關鍵,但前提是必須能回應某些尚未被滿足的顧客需求。這些需求可分為兩類:可見的顧客要求(照做思維所對應)與尚未說出口的真正動機(追問思維所關注)。本章最後的表格也整理了這兩者的差異。
從基本態度來看,照做型是從「現有的事物」出發;而追問型則從「目前還不存在,但能滿足內在渴望的事物」為起點。所謂「現有的事物」,包括自家商品或競爭對手的商品。照做型的做法包括模仿市面熱賣產品、將其納入自家陣容,或直接依顧客反映進行小幅調整。
相對地,追問型的商品開發不是模仿熱賣商品,而是試圖探究:為什麼這些商品會受到喜愛?從中歸納出背後的共同動機(例如:「平價卻不廉價」、「可以不張揚地展現自我」等),並以全新形式將其轉化推出。這種方法強調忠於核心需求,不僅僅停留在表層。
可見,照做思維偏向延續與改良,是漸進式創新;追問思維則關注根本改變,是更具開創性的方式。
這些差異也可從「顧客的聲音」角度看出。照做型會將顧客表達的內容直接反映於產品中,問題在於顧客往往並非產品專家,因此多數意見都是根據操作經驗提出的反饋,甚至是抱怨。例如:「這個旋鈕太難轉」、「畫面配置看起來不順」等。
另一類照做型的要求,是想補上競品已有而自家缺乏的功能。這些要求多半只是表層的補強,而非真正的創新,也只能讓產品勉強追上對手,仍舊缺乏突破。
而追問思維則重視顧客「未說出口的內心渴望」,這些動機有時甚至與他們口頭表達的需求相反。許多優秀的企劃人會說:「別太相信顧客說的話。」這不是不重視顧客,而是希望設計者能夠看見話語背後真正的渴望。這點與單靠技術導向、忽略市場反應的設計截然不同。
這樣的情況在各公司皆常見。一線業務人員常會全盤接收顧客的反饋,並抱怨:「我們明知道這樣會大賣,為何公司不做?」這類說法的陷阱有兩個:第一,這些要求多半只是表面的照做型需求;第二,正因為是照做型,所以通常已經落後潮流。若貿然依此開發產品,等上市時需求可能早已轉變,結果產品與現實需求脫節。
簡言之,從「目前熱賣的東西」出發,是照做型企劃;而思考「有沒有什麼還不存在但可能會熱賣的東西」,則是追問型企劃。照做型認為要搭上潮流,追問型則致力於創造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