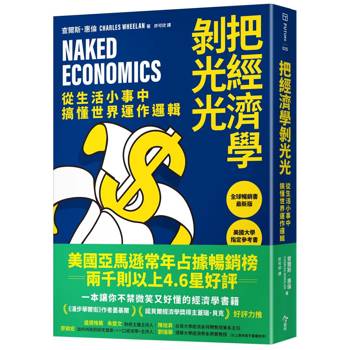第一章 市場的力量:巴黎是誰養活的?
一九八九年,柏林圍牆倒塌時,可口可樂歐洲區負責人道格拉斯.艾維斯特(Douglas Ivester,後來成為執行長),在彈指間做出一個決定。他將銷售團隊派往柏林,告訴他們開始發放可樂,免費。在某些情況下,可口可樂的業務會透過圍牆的洞傳出汽水瓶。他回憶起動盪時期在東柏林的亞歷山大廣場漫步,試圖判斷是否有人認可可口可樂品牌。他說:「我們走到哪裡,都問他們在喝什麼,是否喜歡可口可樂。但我們連名字都不用說!只要用手比出瓶子的形狀,大家就懂了。我們決定要盡可能推銷可口可樂,越快越好,即使還不知道怎麼收費也沒關係。」1
可口可樂很快在東德建立業務,向商家提免費的冷藏櫃,以存放「真正的可口可樂」。這在短期內是會虧損的計畫,當時東德貨幣仍一文不值,對世界其他地方而言,它只是一些紙片,但這卻是一個比任何政府機構的動作更迅速也更聰明的商業決策。到了一九九五年,前東德的人均可口可樂消費量已經達到西德的水準,且西德早已是個強大的市場。
在某種意義上,正是亞當.斯密(Adam Smith)那雙無形之手讓可口可樂穿越柏林圍牆。可口可樂的業務將這種飲品傳遞給剛解放的東德人,算不上什麼偉大的人道舉動,也不是在對共產主義的未來作出大膽的宣示。他們是為了商業,為了擴展他們的全球市場,增加利潤,讓股東開心。這就是資本主義的精髓:市場透過調整激勵機制,讓個人為了自己的最佳利益而行事——發放可口可樂、花費數年讀研究所、種植大豆、設計能在淋浴時使用的收音機——從而使大多數(雖然不是全部)社會成員的生活水準得以改善、繁榮發展。
經濟學家有時候會問:「誰在養活巴黎?」這是一種修辭手法,意在引起人們注意那些讓現代經濟得以運作的複雜多樣、令人眼花撩亂的日常活動。無論如何,適量的新鮮鮪魚會從南太平洋的漁船送到里沃利路的餐廳裡;街坊的水果攤每天早上都能供應顧客所需——從咖啡到新鮮的木瓜——即使那些產品可能來自十到十五個不同的國家。簡而言之,一個複雜的經濟體系每天涉及數十億筆交易,其中絕大多數沒有政府直接干預。而且不僅僅是完成交易,我們的生活在這種過程中也會越來越好。能舒適地在家裡隨時購買電視已經是非常了不起的事;同樣令人驚訝的是,在一九七一年,二十五吋的彩色電視需要一位普通工人花費一百七十四小時的工資;但今日,一台更可靠、能接收更多頻道、信號更好的二十五吋彩色電視,所需的工資不到十小時。
如果你認為更好、更便宜的電視不是衡量社會進步的最佳標準(但我承認這是個合理的觀點),那麼或許你會被以下事實打動:在二十世紀,美國人的平均壽命從四十七歲攀升到七十七歲,嬰兒死亡率下降了九三%,我們消滅或控制了如小兒麻痺、結核病、傷寒和百日咳等疾病。2
我們的市場經濟對這些進步功不可沒。有則冷戰時期的故事,描述一位蘇聯官員參觀美國藥局,明亮的走道上擺滿了從口臭到腳氣的各種藥物。他說:「真令人印象深刻,但你怎麼知道每家藥局都有這些存貨呢?」這則故事之所以有趣,是因為它顯露出對市場經濟運作的全然無知。在美國,沒有像蘇聯那樣的中央集權指示商店應該販售哪些商品,商店販售人們想買的產品,而公司則生產商店想販售的商品。蘇聯經濟失敗的主因之一是政府官僚指導了所有事務,從伊爾庫茨克的工廠生產多少條肥皂,到莫斯科有多少學生攻讀電機工程,最終,這項任務證明過於艱鉅。
當然,我們這些習慣於市場經濟的人,對共產主義中央計畫經濟的理解也很有限。我曾是伊利諾州代表團成員,前往古巴訪問,因為那次訪問有美國政府的授權,代表團每個成員都可以帶回價值一百美元的古巴商品,包括雪茄。由於成長於折扣商店的時代,我們都開始尋找價格最優惠的高希霸雪茄(Cohibas),這樣一百美元零用錢就能獲得最大價值。經過徒勞無功的幾個小時後,我們領悟到共產主義的重點:雪茄價格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樣的。商店之間沒有競爭,因為沒有我們所熟知的那種利潤。每間商店都依斐代爾.卡斯楚(Fidel Castro)所定的價格,販售包含雪茄在內的每個商品,而每個雪茄店店長,都拿著政府規定的工資,這和他們賣了多少雪茄無關。
一九九二年贏得諾貝爾獎的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家蓋瑞.貝克曾經指出(借用蕭伯納的話):「經濟學是充分利用生活的藝術。」經濟學就在研究我們如何做到這一點。所有值得擁有的事物的供應量都有限:石油、椰奶、完美的身材、潔淨的水,能修理卡紙印表機的人等等。我們如何分配這些東西?為什麼比爾.蓋茲擁有私人飛機,而你沒有?你可能會說,他很富有。但他為什麼富有?他對世界有限資源的擁有權為什麼比其他人多?同時,在像美國這麼富裕的國家,一個花三千三百萬美元僱用職業棒球選手克萊頓.克蕭(Clayton Kershaw)打球的地方,卻有五分之一的孩子生活在貧困中,還有些成年人被迫翻垃圾桶找食物?在我芝加哥的家附近,三隻狗烘焙坊只賣狗吃的蛋糕和糕點,富裕的專業人士花十六美元買生日蛋糕給他們的寵物。與此同時,芝加哥無家可歸者聯盟估計,在這個城市的任何一個夜晚,都有一萬五千人風餐露宿。
當我們放眼美國以外的世界時,這種差異更加明顯。中非的查德(Chad)有半數人無法取得潔淨的飲用水,更不用說為寵物提供糕點了。世界銀行估計,全球超過七億五千萬人每天的收入不到一.九美元。這一切是如何運作的,或者在某種情況下,為什麼無法運作?
經濟學從一個非常重要的假設開始:個人的行為是讓他們自己盡可能過得好。用專業術語說,個人尋求最大化自身的效用,這是一個類似幸福的概念,但範圍更廣。我從接種傷寒疫苗和繳納稅款中獲得效用,這些都不會讓我特別高興,但可以讓我避免死於傷寒或進監獄。長期看來,這讓我過得更好。經濟學家並不特別在意是什麼給我們帶來效用;他們只是接受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偏好」。我喜歡咖啡、老房子、經典電影、狗、騎自行車和許多事物,世界上每個人也都有自己的偏好,這些偏好可能與我的有關,也可能完全無關。
事實上,不同個體有不同偏好,這個看似簡單的觀察,有時會被那些通常表現精明的政策制定者忽視。舉例來說,有錢人和窮人的偏好不同,同樣的,我們的個人偏好也可能隨著生命周期而改變,尤其是我們(希望)變得更富有時。「奢侈品」一詞對經濟學家來說有個技術性含義;它指的是當我們財富增加時,購買量會隨之增加的商品,例如跑車和法國葡萄酒。關懷環境則是個比較不明顯的奢侈品。富裕的美國人願意花更多錢來保護環境,這筆支出占他們收入的比例遠高於較不富裕的美國人;同樣的關係在不同國家也成立,富裕國家比貧窮國家投入更多資源保護環境。原因很簡單:我們關心孟加拉虎的命運,因為我們可以。我們有房子、有工作、有乾淨的水,還可以為狗準備生日蛋糕。
還有個棘手的政策問題:對於我們這些過著安逸生活的人來說,將我們的偏好強加於開發中國家的個人,是否公平?經濟學家認為這是不公平的,雖然我們經常這麼做。當我在《紐約時報》周日版上讀到南美村莊砍伐雨林,並破壞珍稀的生態系統的故事時,我驚訝且厭惡地差點打翻我的星巴克拿鐵咖啡。但我不是他們,我的孩子沒有挨餓,也沒有面臨死於瘧疾的風險。如果出現這種前提,而破壞珍貴的野生動物棲息地,可以幫助我養家糊口,買得起蚊帳,我也會磨利斧頭開始砍伐,才不會在乎殺了多少蝴蝶或斑點鼬。這不是說開發中國家的環境不重要,它很重要。事實上,從長遠來看,許多環境劣化的例子會讓貧窮國家更加貧困。砍伐那些森林對其他人也有壞處,因為森林砍伐是導致二氧化碳排放上升的主因之一(經濟學家常常認為,富裕國家應該付錢給貧窮國家,讓他們保護具有全球價值的自然資源)。
顯然,如果已開發國家能更加慷慨,那麼巴西的村民就不必在摧毀雨林和購買蚊帳間做出選擇。目前的問題更基本:將我們的偏好強加在生活情況截然不同的個體上,從經濟學角度來看是不妥的。本書稍後在討論全球化和世界貿易時,這將是非常重要的點。
我再提出一個關於個人偏好的重要觀點:最大化效用並不等於自私行事。一九九九年,《紐約時報》刊登了奧西奧拉.麥卡蒂(Oseola McCarty)的訃聞,這位女士於九十一歲辭世,她的一生都在密西西比州哈提斯堡當洗衣工,獨自住在一個簡陋的小屋裡,屋裡只有一台只能接收一個頻道的黑白電視。讓麥卡蒂女士與眾不同的是,她並不貧窮。事實上,在她去世的四年前,她捐出了十五萬美元給她從未就讀過的南密西西比大學,設立了幫助貧困學生的獎學金。
麥卡蒂的行為是否顛覆了經濟學領域的思維模式?諾貝爾獎是不是要被召回斯德哥爾摩?不,她只是在將錢存下來且最終捐出獲得的效益,要比將其花在大螢幕電視或高級公寓上所得到的更多。
好吧,那只是錢。那麼來看看韋斯利.奧特里(Wesley Autrey)的故事,他是一位建築工人,五十歲,住在紐約市。二〇〇七年一月,他和兩個小女兒在上曼哈頓等地鐵時,附近一名陌生人突發癲癇,然後跌落到地鐵軌道上。如果這還不夠糟糕,那麼一號線的列車已經駛入視野,即將進站。
奧特里先生跳下軌道,用自己的身體保護那名男子,五節車廂差點就要從他們身上輾過去,近到在奧特里的帽子上留下了一道油漬。火車停下來時,他從底下大喊:「我們沒事,但我兩個女兒在上面,告訴她們,爸爸沒事。」3這一切都是為了幫助一個毫無關係的陌生人。
大腦科學——透過觀察人們在做決策時的大腦活動,我們獲得了關於利他主義的新見解。為什麼有人會做出沒有明顯利益,甚至可能讓自己陷入危險的事(例如跳到地鐵軌道上)呢?《經濟學人》解釋道:「根據神經科學的說法,答案是這樣做讓人感覺快樂。」對他人,包括陌生人,表現出友好的行為,會活化大腦的獎勵中心,就像性、金錢、巧克力和毒品一樣。4
演化生物學提供了更詳細的解答。利他行為有助於人類相互合作,而合作有助於物種生存,因此,利他行為並不像它單獨看來那麼不理性。大腦已經演化出會獎勵那些促進群體成功的行為,「利他主義或許比以前想像的更加根深蒂固。」洛杉磯加州大學塞梅爾神經科學與人類行為研究所的科學家於二〇一六年如此宣稱。5
每個人都經常做出利他決定,儘管通常是在較小的範圍裡。我們或許會多花幾分錢購買不傷害海豚的鮪魚、捐錢給喜歡的慈善機構,或是志願參軍,這些不會被認為是自私的行為都能為我們帶來效用。美國人每年捐贈超過兩千億美元給各種慈善機構,我們會為陌生人開門,會做出充滿勇氣和慷慨的行為,這一切都不與基本假設相抵觸:即個人會尋求讓自己過得更好,無論他們如何定義「好」。這個假設也不意味我們總是能做出完美的決定,甚至是好的決策。我們不會。但每個人都會依當時可獲得的資訊,盡量做出最佳決策。
所以,在這些討論之後,我們已經能回答一個深刻且古老的哲學問題:為什麼那隻雞要過馬路?因為牠最大化了牠的效用。
請記住,效用最大化不是個簡單的命題。生活充滿複雜性和不確定性,我們在任何時間點都有無數種可能的行動選擇。事實上,我們所做的每個決定都涉及某種權衡,我們可能在當下和未來的效用之間做取捨。舉例來說,在公司年度野餐會上用划槳敲你老闆的頭,可能會帶來一些滿足感,但那片刻的效用,可能不足以抵消未來幾年牢獄生活所帶來的痛苦(但那只是我的偏好)。更嚴肅的是,許多重要的決定牽涉當下與未來消費價值的平衡。我們可能在研究所吃好幾年的泡麵,因為如此做能大幅提升未來的生活水準。或是反過來說,我們可能在今天刷卡購買大螢幕電視,儘管那筆信用卡的循環利息會減少未來的消費能力。
相似地,我們也在工作和休息間尋找平衡。一名投資銀行家每周辛苦工作九十小時,可以賺取大量收入,但享受那些用收入購買的商品的時間會變少。我弟弟開始他的管理顧問生涯時,薪水至少比我現在的薪水多出一位數,另一方面,他的工時既長又不靈活。有年秋天,我們兩個都興奮地報名參加了由羅傑.伊伯特(Roger Ebert)教授的晚間電影課,我弟連續蹺了十三周的課。
無論我們的薪水多高,都可以將它們花在數不勝數的商品和服務上。當你購買這本書,你隱含地決定不把錢花在其他地方(即使書是你偷來的,你本可以將史蒂芬.金的小說塞進你的外套裡,這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一種讚美)。同時,時間是我們最稀缺的資源,此刻,你正在閱讀這本書,而不是工作、與狗玩、申請法學院、購物或做愛。生活是關於取捨的,經濟學也是。
簡而言之,早上起床和做早餐所牽涉的決策,比一場普通的象棋比賽還要複雜。(那顆煎蛋會在二十八年後殺了我嗎?)我們如何管理這些決策?答案是,我們每個人都在不知不覺間衡量每一件事的成本與收益。經濟學家會說,我們試圖在可用資源的範圍內讓效用最大化;我爸會說,我們努力讓每一分錢發揮最大效益。請記住,為我們帶來效用的不一定是物質商品。如果你正在比較兩份工作——在國中教數學,或推銷駱駝牌香菸——後者薪水幾乎肯定較高,而前者能得到更多的「心理效益」,這是一種文雅的說法,意思就是在過完一天後,你會對自己做的事覺得比較開心。這種效益與較低的薪水成本相比是完全合理的。最終,有人會選擇教數學,有人會選擇賣香菸。
一九八九年,柏林圍牆倒塌時,可口可樂歐洲區負責人道格拉斯.艾維斯特(Douglas Ivester,後來成為執行長),在彈指間做出一個決定。他將銷售團隊派往柏林,告訴他們開始發放可樂,免費。在某些情況下,可口可樂的業務會透過圍牆的洞傳出汽水瓶。他回憶起動盪時期在東柏林的亞歷山大廣場漫步,試圖判斷是否有人認可可口可樂品牌。他說:「我們走到哪裡,都問他們在喝什麼,是否喜歡可口可樂。但我們連名字都不用說!只要用手比出瓶子的形狀,大家就懂了。我們決定要盡可能推銷可口可樂,越快越好,即使還不知道怎麼收費也沒關係。」1
可口可樂很快在東德建立業務,向商家提免費的冷藏櫃,以存放「真正的可口可樂」。這在短期內是會虧損的計畫,當時東德貨幣仍一文不值,對世界其他地方而言,它只是一些紙片,但這卻是一個比任何政府機構的動作更迅速也更聰明的商業決策。到了一九九五年,前東德的人均可口可樂消費量已經達到西德的水準,且西德早已是個強大的市場。
在某種意義上,正是亞當.斯密(Adam Smith)那雙無形之手讓可口可樂穿越柏林圍牆。可口可樂的業務將這種飲品傳遞給剛解放的東德人,算不上什麼偉大的人道舉動,也不是在對共產主義的未來作出大膽的宣示。他們是為了商業,為了擴展他們的全球市場,增加利潤,讓股東開心。這就是資本主義的精髓:市場透過調整激勵機制,讓個人為了自己的最佳利益而行事——發放可口可樂、花費數年讀研究所、種植大豆、設計能在淋浴時使用的收音機——從而使大多數(雖然不是全部)社會成員的生活水準得以改善、繁榮發展。
經濟學家有時候會問:「誰在養活巴黎?」這是一種修辭手法,意在引起人們注意那些讓現代經濟得以運作的複雜多樣、令人眼花撩亂的日常活動。無論如何,適量的新鮮鮪魚會從南太平洋的漁船送到里沃利路的餐廳裡;街坊的水果攤每天早上都能供應顧客所需——從咖啡到新鮮的木瓜——即使那些產品可能來自十到十五個不同的國家。簡而言之,一個複雜的經濟體系每天涉及數十億筆交易,其中絕大多數沒有政府直接干預。而且不僅僅是完成交易,我們的生活在這種過程中也會越來越好。能舒適地在家裡隨時購買電視已經是非常了不起的事;同樣令人驚訝的是,在一九七一年,二十五吋的彩色電視需要一位普通工人花費一百七十四小時的工資;但今日,一台更可靠、能接收更多頻道、信號更好的二十五吋彩色電視,所需的工資不到十小時。
如果你認為更好、更便宜的電視不是衡量社會進步的最佳標準(但我承認這是個合理的觀點),那麼或許你會被以下事實打動:在二十世紀,美國人的平均壽命從四十七歲攀升到七十七歲,嬰兒死亡率下降了九三%,我們消滅或控制了如小兒麻痺、結核病、傷寒和百日咳等疾病。2
我們的市場經濟對這些進步功不可沒。有則冷戰時期的故事,描述一位蘇聯官員參觀美國藥局,明亮的走道上擺滿了從口臭到腳氣的各種藥物。他說:「真令人印象深刻,但你怎麼知道每家藥局都有這些存貨呢?」這則故事之所以有趣,是因為它顯露出對市場經濟運作的全然無知。在美國,沒有像蘇聯那樣的中央集權指示商店應該販售哪些商品,商店販售人們想買的產品,而公司則生產商店想販售的商品。蘇聯經濟失敗的主因之一是政府官僚指導了所有事務,從伊爾庫茨克的工廠生產多少條肥皂,到莫斯科有多少學生攻讀電機工程,最終,這項任務證明過於艱鉅。
當然,我們這些習慣於市場經濟的人,對共產主義中央計畫經濟的理解也很有限。我曾是伊利諾州代表團成員,前往古巴訪問,因為那次訪問有美國政府的授權,代表團每個成員都可以帶回價值一百美元的古巴商品,包括雪茄。由於成長於折扣商店的時代,我們都開始尋找價格最優惠的高希霸雪茄(Cohibas),這樣一百美元零用錢就能獲得最大價值。經過徒勞無功的幾個小時後,我們領悟到共產主義的重點:雪茄價格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樣的。商店之間沒有競爭,因為沒有我們所熟知的那種利潤。每間商店都依斐代爾.卡斯楚(Fidel Castro)所定的價格,販售包含雪茄在內的每個商品,而每個雪茄店店長,都拿著政府規定的工資,這和他們賣了多少雪茄無關。
一九九二年贏得諾貝爾獎的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家蓋瑞.貝克曾經指出(借用蕭伯納的話):「經濟學是充分利用生活的藝術。」經濟學就在研究我們如何做到這一點。所有值得擁有的事物的供應量都有限:石油、椰奶、完美的身材、潔淨的水,能修理卡紙印表機的人等等。我們如何分配這些東西?為什麼比爾.蓋茲擁有私人飛機,而你沒有?你可能會說,他很富有。但他為什麼富有?他對世界有限資源的擁有權為什麼比其他人多?同時,在像美國這麼富裕的國家,一個花三千三百萬美元僱用職業棒球選手克萊頓.克蕭(Clayton Kershaw)打球的地方,卻有五分之一的孩子生活在貧困中,還有些成年人被迫翻垃圾桶找食物?在我芝加哥的家附近,三隻狗烘焙坊只賣狗吃的蛋糕和糕點,富裕的專業人士花十六美元買生日蛋糕給他們的寵物。與此同時,芝加哥無家可歸者聯盟估計,在這個城市的任何一個夜晚,都有一萬五千人風餐露宿。
當我們放眼美國以外的世界時,這種差異更加明顯。中非的查德(Chad)有半數人無法取得潔淨的飲用水,更不用說為寵物提供糕點了。世界銀行估計,全球超過七億五千萬人每天的收入不到一.九美元。這一切是如何運作的,或者在某種情況下,為什麼無法運作?
經濟學從一個非常重要的假設開始:個人的行為是讓他們自己盡可能過得好。用專業術語說,個人尋求最大化自身的效用,這是一個類似幸福的概念,但範圍更廣。我從接種傷寒疫苗和繳納稅款中獲得效用,這些都不會讓我特別高興,但可以讓我避免死於傷寒或進監獄。長期看來,這讓我過得更好。經濟學家並不特別在意是什麼給我們帶來效用;他們只是接受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偏好」。我喜歡咖啡、老房子、經典電影、狗、騎自行車和許多事物,世界上每個人也都有自己的偏好,這些偏好可能與我的有關,也可能完全無關。
事實上,不同個體有不同偏好,這個看似簡單的觀察,有時會被那些通常表現精明的政策制定者忽視。舉例來說,有錢人和窮人的偏好不同,同樣的,我們的個人偏好也可能隨著生命周期而改變,尤其是我們(希望)變得更富有時。「奢侈品」一詞對經濟學家來說有個技術性含義;它指的是當我們財富增加時,購買量會隨之增加的商品,例如跑車和法國葡萄酒。關懷環境則是個比較不明顯的奢侈品。富裕的美國人願意花更多錢來保護環境,這筆支出占他們收入的比例遠高於較不富裕的美國人;同樣的關係在不同國家也成立,富裕國家比貧窮國家投入更多資源保護環境。原因很簡單:我們關心孟加拉虎的命運,因為我們可以。我們有房子、有工作、有乾淨的水,還可以為狗準備生日蛋糕。
還有個棘手的政策問題:對於我們這些過著安逸生活的人來說,將我們的偏好強加於開發中國家的個人,是否公平?經濟學家認為這是不公平的,雖然我們經常這麼做。當我在《紐約時報》周日版上讀到南美村莊砍伐雨林,並破壞珍稀的生態系統的故事時,我驚訝且厭惡地差點打翻我的星巴克拿鐵咖啡。但我不是他們,我的孩子沒有挨餓,也沒有面臨死於瘧疾的風險。如果出現這種前提,而破壞珍貴的野生動物棲息地,可以幫助我養家糊口,買得起蚊帳,我也會磨利斧頭開始砍伐,才不會在乎殺了多少蝴蝶或斑點鼬。這不是說開發中國家的環境不重要,它很重要。事實上,從長遠來看,許多環境劣化的例子會讓貧窮國家更加貧困。砍伐那些森林對其他人也有壞處,因為森林砍伐是導致二氧化碳排放上升的主因之一(經濟學家常常認為,富裕國家應該付錢給貧窮國家,讓他們保護具有全球價值的自然資源)。
顯然,如果已開發國家能更加慷慨,那麼巴西的村民就不必在摧毀雨林和購買蚊帳間做出選擇。目前的問題更基本:將我們的偏好強加在生活情況截然不同的個體上,從經濟學角度來看是不妥的。本書稍後在討論全球化和世界貿易時,這將是非常重要的點。
我再提出一個關於個人偏好的重要觀點:最大化效用並不等於自私行事。一九九九年,《紐約時報》刊登了奧西奧拉.麥卡蒂(Oseola McCarty)的訃聞,這位女士於九十一歲辭世,她的一生都在密西西比州哈提斯堡當洗衣工,獨自住在一個簡陋的小屋裡,屋裡只有一台只能接收一個頻道的黑白電視。讓麥卡蒂女士與眾不同的是,她並不貧窮。事實上,在她去世的四年前,她捐出了十五萬美元給她從未就讀過的南密西西比大學,設立了幫助貧困學生的獎學金。
麥卡蒂的行為是否顛覆了經濟學領域的思維模式?諾貝爾獎是不是要被召回斯德哥爾摩?不,她只是在將錢存下來且最終捐出獲得的效益,要比將其花在大螢幕電視或高級公寓上所得到的更多。
好吧,那只是錢。那麼來看看韋斯利.奧特里(Wesley Autrey)的故事,他是一位建築工人,五十歲,住在紐約市。二〇〇七年一月,他和兩個小女兒在上曼哈頓等地鐵時,附近一名陌生人突發癲癇,然後跌落到地鐵軌道上。如果這還不夠糟糕,那麼一號線的列車已經駛入視野,即將進站。
奧特里先生跳下軌道,用自己的身體保護那名男子,五節車廂差點就要從他們身上輾過去,近到在奧特里的帽子上留下了一道油漬。火車停下來時,他從底下大喊:「我們沒事,但我兩個女兒在上面,告訴她們,爸爸沒事。」3這一切都是為了幫助一個毫無關係的陌生人。
大腦科學——透過觀察人們在做決策時的大腦活動,我們獲得了關於利他主義的新見解。為什麼有人會做出沒有明顯利益,甚至可能讓自己陷入危險的事(例如跳到地鐵軌道上)呢?《經濟學人》解釋道:「根據神經科學的說法,答案是這樣做讓人感覺快樂。」對他人,包括陌生人,表現出友好的行為,會活化大腦的獎勵中心,就像性、金錢、巧克力和毒品一樣。4
演化生物學提供了更詳細的解答。利他行為有助於人類相互合作,而合作有助於物種生存,因此,利他行為並不像它單獨看來那麼不理性。大腦已經演化出會獎勵那些促進群體成功的行為,「利他主義或許比以前想像的更加根深蒂固。」洛杉磯加州大學塞梅爾神經科學與人類行為研究所的科學家於二〇一六年如此宣稱。5
每個人都經常做出利他決定,儘管通常是在較小的範圍裡。我們或許會多花幾分錢購買不傷害海豚的鮪魚、捐錢給喜歡的慈善機構,或是志願參軍,這些不會被認為是自私的行為都能為我們帶來效用。美國人每年捐贈超過兩千億美元給各種慈善機構,我們會為陌生人開門,會做出充滿勇氣和慷慨的行為,這一切都不與基本假設相抵觸:即個人會尋求讓自己過得更好,無論他們如何定義「好」。這個假設也不意味我們總是能做出完美的決定,甚至是好的決策。我們不會。但每個人都會依當時可獲得的資訊,盡量做出最佳決策。
所以,在這些討論之後,我們已經能回答一個深刻且古老的哲學問題:為什麼那隻雞要過馬路?因為牠最大化了牠的效用。
請記住,效用最大化不是個簡單的命題。生活充滿複雜性和不確定性,我們在任何時間點都有無數種可能的行動選擇。事實上,我們所做的每個決定都涉及某種權衡,我們可能在當下和未來的效用之間做取捨。舉例來說,在公司年度野餐會上用划槳敲你老闆的頭,可能會帶來一些滿足感,但那片刻的效用,可能不足以抵消未來幾年牢獄生活所帶來的痛苦(但那只是我的偏好)。更嚴肅的是,許多重要的決定牽涉當下與未來消費價值的平衡。我們可能在研究所吃好幾年的泡麵,因為如此做能大幅提升未來的生活水準。或是反過來說,我們可能在今天刷卡購買大螢幕電視,儘管那筆信用卡的循環利息會減少未來的消費能力。
相似地,我們也在工作和休息間尋找平衡。一名投資銀行家每周辛苦工作九十小時,可以賺取大量收入,但享受那些用收入購買的商品的時間會變少。我弟弟開始他的管理顧問生涯時,薪水至少比我現在的薪水多出一位數,另一方面,他的工時既長又不靈活。有年秋天,我們兩個都興奮地報名參加了由羅傑.伊伯特(Roger Ebert)教授的晚間電影課,我弟連續蹺了十三周的課。
無論我們的薪水多高,都可以將它們花在數不勝數的商品和服務上。當你購買這本書,你隱含地決定不把錢花在其他地方(即使書是你偷來的,你本可以將史蒂芬.金的小說塞進你的外套裡,這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一種讚美)。同時,時間是我們最稀缺的資源,此刻,你正在閱讀這本書,而不是工作、與狗玩、申請法學院、購物或做愛。生活是關於取捨的,經濟學也是。
簡而言之,早上起床和做早餐所牽涉的決策,比一場普通的象棋比賽還要複雜。(那顆煎蛋會在二十八年後殺了我嗎?)我們如何管理這些決策?答案是,我們每個人都在不知不覺間衡量每一件事的成本與收益。經濟學家會說,我們試圖在可用資源的範圍內讓效用最大化;我爸會說,我們努力讓每一分錢發揮最大效益。請記住,為我們帶來效用的不一定是物質商品。如果你正在比較兩份工作——在國中教數學,或推銷駱駝牌香菸——後者薪水幾乎肯定較高,而前者能得到更多的「心理效益」,這是一種文雅的說法,意思就是在過完一天後,你會對自己做的事覺得比較開心。這種效益與較低的薪水成本相比是完全合理的。最終,有人會選擇教數學,有人會選擇賣香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