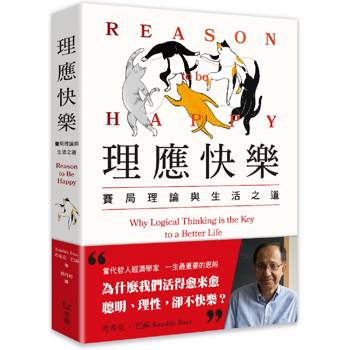推理、幸福與成功
我們一生中大部分時間都在追尋幸福和滿足,同時設法克服障礙和挑戰。然而,這趟人生旅程中最強大,但未被充分利用的工具之一,其實是我們所有人都擁有的工具,也就是推理能力。因此,這本書的書名就有了雙重意義。古代哲學家試圖理解我們周圍的世界,並定義一種有意義的生活方式。本書重新審視這些古老的主題,只不過藉助了現代學科的彈藥,特別是經濟學和賽局理論。在這個過程中,本書也探討了這些學科背後的哲學瑕疵和悖論,以及它們所引起的道德困境,希望能吸引讀者投入這場知識與理解的探索。
這本書的架構是倒金字塔型。一開始的重點在於個人以及日常生活中的理性選擇和推理,從辦公室政治到個人難題。之後書中繼續探討集體福祉和群體的道德責任。最後一章則從個人和集體的角度,聚焦於最宏大的關切,即全球問題,我們將討論,如何解決這個動盪的世界所面臨的一些問題。作為個人,我們能否讓世界變得更美好?如果可以,又該怎麼做?為了開始尋找答案,我想先從展示賽局理論能如何拯救生命開始。
▎如何避免核子戰爭
一九七二年,我來到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求學,幾週後我經過布藍茲維廣場(Brunswick Square)時,有個小孩朝我扔水球。水球擦過我的肩膀,但沒有造成傷害。我當時還很青澀,又是初來乍到,再加上第一次離開祖國印度,所以我猶豫了一會兒,不知道是否值得挑起爭端。我判斷沒有理由這麼做,所以若無其事繼續走。
就在這時,一個身材魁梧的男子大步走到我面前,面上毫不掩飾他的鄙夷(更多的是對我而不是對那個男孩),他說:「年輕人,如果我是你,就會把那個小子痛打一頓。」我當時的第一反應是:「不,你不會,因為正如你剛才看到的,我沒有。」當然,考慮到他傾向於使用武力,我並沒有把這句話說出口。
如果我是你是道德推理的要點,從康德倫理學到福利經濟學和賽局理論都是如此。然而,它卻經常受到誤解。如果真的照字面解讀,那麼一旦「我」看到「你」的行為,就沒有理由再猜測如果我是你我會做什麼。另一方面,如果「如果我是你」的意思是「如果我有一部分像你」,那麼就會出現許多有趣的問題,也會有很多模糊之處,因為在許多方面我都有可能像你。
賽局理論涉及大量這類推理。光是聰明還不夠;你必須能夠將自己置於其他聰明人的立場上,思考她可能會做些什麼——而這反過來又當然是基於她認為你可能會做些什麼。
有鑑於布藍茲維廣場靠近倫敦大學,那名男子很有可能是一名教授。他或許也擅長研究。然而,此時他的情緒勝過了理智。這是常見的人類傾向和許多判斷錯誤的根源,同時也是促成本書的重要動機。
本書旨在闡明我們為什麼有理由感到幸福,以及為什麼我們必須善用推理才能幸福。為了闡明我的觀點,我將借用賽局理論中所使用的推理方法。賽局理論是社會情境中演繹推理的藝術。因此,它在戰爭和外交、制定企業戰略、甚至在我們日常的人際關係中都具有價值。
▎決定人類命運的關鍵賽局
一九六二年十月十六日星期二上午九點左右,甘迺迪總統從國家安全顧問邦迪(McGeorge Bundy)那裡得知,一架美國U-2偵察機發現蘇聯在古巴部署了核子彈道飛彈,這些導彈可以在幾分鐘內襲擊美國城市。甘迺迪的當務之急是決定他和美國該做什麼,而這個決定主要取決於他認為蘇聯總理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會對他的行為做出什麼反應。當時他無疑意識到,赫魯雪夫會採取什麼行動,取決於他認為甘迺迪會如何回應他的所作所為。這是一個經典的賽局理論問題,涉及下棋或打橋牌時所使用的那種推理。這裡的不同之處在於,賭注攸關生死。
接下來的十三天,是歷史記載中人類存亡最危急的關頭之一。全世界時刻關注這場令人毛骨悚然的「賽局」。近一八○架攜帶核武的轟炸機奉命持續滯空,飛抵蘇聯邊境然後返回。訊息很明確:如果美國遭到攻擊,美國也許會滅亡,但俄羅斯也會陪葬。這就是所謂的「第二擊戰略」(second-strike strategy),目的是遏阻任何考慮進行第一擊的人。一旦有國家擁有核子能力,對另一個考慮生產核武的國家來說,第二擊能力被認為是必備的。擁有核彈卻不具備第二擊能力,就等於自尋攻擊。美國公開展示第二擊能力的戰略奏效。赫魯雪夫最終讓步,世界得救了。
但幾乎無人注意到,白宮對戰略和反制戰略進行了多麼漫長的討論,主要是因為這些討論都是祕密進行。事實上,甘迺迪在高度緊繃的情勢下,花了六天才做出回應。經過深思熟慮,美國總統決定在十月二十二日公開告知美國人民他們所面臨的危機,並致信赫魯曉夫詳細說明美國的應對計劃。1全世界都要感謝甘迺迪領導的美國政府在那六天中製定了高超的戰略,使世界從世界大戰和毀滅的邊緣悄然後撤。赫魯雪夫選擇丟臉而不是滅世,也是功不可沒。
甘迺迪之所以能在這場戰局中處理得當,主要是記取了於一年多前豬玀灣事件(Bay of Pigs)慘敗的教訓,當時在美國支持下,古巴流亡人士發動武裝行動,結果被古巴武裝力量迅速擊潰,時間短到令美方顏面盡失。甘迺迪意識到推翻古巴共產主義政府的企圖之所以失敗,並不是因為美國沒有更多的槍支和武器,而是因為他沒有花足夠的時間深思熟慮並制定戰略。
用梅和澤利科夫(May and Zelikow, 1997, p. 14)的話來說,豬玀灣事件的失敗使甘迺迪意識到「他不僅詢問的顧問太少,給予這些議題的時間也太少。」這件事帶來的結果之一是,美國經濟學家謝林 (Thomas Schelling)被要求撰寫一篇關於核子戰略的論文,而他於一九六一年七月五日完成並提交。據國家安全顧問邦迪的說法,這篇論文「給總統留下深刻的印象」。這反過來又在引導國家度過隔年的古巴飛彈危機中發揮了巨大作用。
在我寫這本書時,拜登總統正忙於回應普丁對烏克蘭的入侵。對於他考慮的每一項支持措施,他都必須思考普丁會如何回應。這十分令人憂心,因為普丁的理性堪慮。由時事評論家扎卡里亞(Fareed Zakaria)主持的CNN紀錄片《普丁的內心世界》(Inside the Mind of Vladimir Putin)非常精采。唯一的問題是,看完之後,你還是不知道普丁到底在想什麼。
▎賽局理論的盲點
儘管賽局理論是二十世紀出現的最令人興奮的學科之一,但它也有盲點,所以我們必須利用直覺、心理學、政治和哲學。我們必須接受這樣一個事實:並非所有問題都有解決方案。透過結合這些不同方法的見解,我們也只能希望增加成功的可能性。
人類經過數千年的演化,已經能夠直覺地感受到其他人的想法,這為賽局理論提供了一些基礎。但作為一門連貫而自成一格的學科,賽局理論出奇地年輕。波雷爾(Émile Borel)是法國著名的數學家,後來成為政治家,他在一九二一年發表了一些關於賽局理論的重要著作。賽局理論作為一種分析方法,影響遍及從經濟學、政治學、心理學,到進化生物學、計算機科學和哲學等一系列學科,但它其實是在二十世紀中葉才突然出現——就像菲利普‧拉金(Philip Larkin)第一次的享樂主義邂逅,發生在《查泰萊》(Chatterley)禁令結束和披頭四樂隊發行第一張LP之間。賽局理論的出現大致與原子彈的發明在同一時期,當時跨國公司也開始以全新方式相互競爭並與政府競爭,這也許並非偶然。透過為戰爭、外交和企業戰略提供分析工具,它塑造了現代世界的某些維度。
接下來幾頁將用賽局理論的故事,來說明我們如何面對生活中的挑戰。不過,這本書並非所有內容都是在直接幫助解決特定問題。這本書每次只讀上幾頁,對大腦的作用就如同慢跑對身體的作用。我們慢跑不是因為它有什麼產出或收入,而是為了增進身體健康,以便在做其他事情時可以更有效率。同樣地,邏輯和賽局理論可以鍛鍊我們的思維,好在我們有需要時,能夠更有效地調動大腦。有些讀者也許會希望每天閱讀這本書幾頁,以代替每日數獨或填字遊戲。
在這個心智運動的過程中,本書將向讀者介紹一些重要的難題和悖論。就像慢跑一樣,這些心智運動本身就很有趣,而且對心智有療癒作用。正如早期希臘哲學家,特別是斯多葛學派(Stoics)所意識到的,哲學不僅是一種智性探索,也是一種生活方式。而且,如果在這個過程中,你成功地解開了一個前人未解的悖論,即使你沒有從中獲得快樂,你也會成為史上留名的哲學家,如果這算得上安慰的話。
▎羅素的雞
「如果這算得上安慰的話」這個警語是必要的。就拿法國物理學家達朗貝爾(Jean-Baptiste le Rond d’Alembert)養母的憂慮來說好了。達朗貝爾於一七一七年十一月十六日,被生母遺棄在巴黎聖尚勒朗德教堂的台階上,當時他才出生沒幾天。他以這座教堂為名,一開始在孤兒院長大,後來由養母收養。奇蹟般地,儘管人生開端艱難,他卻成為世界上最偉大的思想家之一,為數學、哲學、音樂理論和物理學做出了重要貢獻。然而,他的養母仍然感到失望,因為他似乎從來沒有做過任何有用的工作。當達朗貝爾向她講述他的一項發現時,她的回應非常出名:「你除了當個哲學家,什麼也不會做——那又算什麼呢?不過是個傻瓜,一輩子都在自尋煩惱,只為了死後還能被人談論。」
確實,哲學以及所有精神追求,都帶有逃避現實的成分。這並沒有什麼害處,而且能幫助人們達到內心的平靜(ataraxia),而這正是皮浪(Pyrrho of Elis)等懷疑論者和芝諾(Zeno of Citium)、狄奧吉尼斯(Diogenes of Babylon)和愛比克泰德(Epictetus)等斯多葛學派所提倡的。同時,對真實和科學的追求有時會帶來智性突破,大大擴展我們對宇宙的理解,並為創造更美好的世界提供要素。
▎人類智性的重大突破
有時人們會說哲學作為一門學科,是始於西元前五八五年五月二十八日。那天出現了日蝕,當然並不是史上第一次。這次的不同之處在於米利都的泰勒斯(Thales of Miletus)已經預言了日蝕的發生。泰勒斯是幾何大師,證明了一條關於圓和直角三角形的美麗定理。在幾乎沒有任何儀器,可以拉近距離觀測天空的情況下,對這次日蝕的預測是透過思考和推測的結果。這是人類一次重大的智性突破,是經年累月追蹤行星和恆星的運動,以及歸納和演繹推理的成果。
歸納推理涉及觀察自然界的模式,並根據這些模式得出有關未來的結論。大多數人都相信明天太陽還會升起,因為我們一直以來,都看見太陽十分規律地升起。這就是歸納推理。
另一方面,演繹則需要根據純粹邏輯的前提得出結論。真實已經包含在前提之中。在直角三角形中,斜邊正方形的面積等於另外兩邊正方形的面積總和。我們不需要收集世界各地的三角形,進行仔細的測量然後才得出結論。這個結論是根據三角形、直角和正方形等概念的定義得出的。它非常透明,原則上任何人都可以看得出來。只不過在畢達哥拉斯之前沒有人看出來,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即使是現在,在畢達哥拉斯之後已經過了二千五百多年,學生也常常因為想看卻看不出來而流淚。
▎科學與迷信比想像中相似
早年讓我迷上哲學的是羅素(Bertrand Russell)在他那本薄薄的專著《哲學問題》(The Problems of Philosophy,p. 98)中,對歸納推理的精彩評論:「那個在雞的一生中每天都餵雞的人,最後卻扭斷了雞的脖子,這代表有關自然統一性更細緻的觀點,對雞會是有用的。」這段話完美地說出歸納法的缺陷,敦促我們採取懷疑論。這是訴諸理性的懇求。我相信其中有很多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
我對羅素唯一小有意見的地方在於規範性(prescriptive)部分。我把這段話稍作修改,改為:那個在雞的一生中每天餵雞的人,最後卻扭斷了雞的脖子,以此向人類展示像雞一樣生活的好處。
畢竟,雞無法改變自己出現在餐桌上的命運。為你無法控制的事情煩惱,只會帶給你不必要的痛苦。去深思可得或「可行」的「行動」或「策略」,以便做出正確的選擇,並最大化金錢、權力、名譽或任何你所追求的東西,當然是值得的。然而,人類卻花了大量的時間在擔心我們無法控制的事情。如果雞對自己的命運無能為力,那麼對餵雞人生氣,只會讓雞的生命更加暗淡。我說我們應該像雞一樣生活,並不是說我們應該自我欺騙,相信未來會和過去一樣。我的意思是,一旦我們明白人無法撼動命運的軌跡,就應該努力把日子過好,就如同未來會像過去一樣美好一般。
羅素的思想實驗讓人們關注歸納法的問題。太陽每天都會升起,但這並不能保證它明天還會升起。當然,我們是靠歸納法過活的。我們觀察自然界中的模式,或者更準確地說,觀察自然並在我們的頭腦中創造模式。然而,這缺少客觀理由。如果有人說,儘管有這麼多科學證據,她還是不相信接種疫苗可以保護她免受新冠病毒感染,那麼就沒有充分的理由能駁斥她的說法。我們所謂的科學與迷信之間的差別,並沒有我們想像的那麼大。而誠實,要求我們抱持懷疑。
▎懷疑與理性是幸福的根源
法國攝影師瓦利(Eric Valli)長期拍攝尼泊爾的古隆族部落(Gurung),部落裡的人會冒險攀爬高樹以採集蜂蜜。他曾經問過其中一人,是否有人從高處摔落。被問及的男子一本正經地回答:「有的,一個人的生命要結束時,他就會摔下來。」我建議讀者不要完全忽視古隆族的觀點。
歸納很重要,但我們需要留意它在發現因果關係方面的缺陷。假設研究人員來到一個社區,想測試給居民注射一種綠色化學物質以改善記憶力的效果。他們進行了大量測試,發現這種注射在每一例中都大幅提高記憶力,並且沒有任何負面副作用。如果研究正確完成,它可能被視為一項重要發現,並將發表在主要的科學期刊上。現在,如果這個鎮上有一名叫夏娃的女子,她沒有接受測試,但渴望增強自己的記憶力。她能否根據這項科學研究做出推斷,如果注射這種藥物,她的記憶力就會提高?歸納法的信徒會自信地回答「是的」。想知道為什麼他們的信心值得懷疑,請容我補充一些上述科學實驗的細節。
假設這個社區裡剛好住著大量蛇、青蛙、老鼠和蝙蝠,而只有一個人,那就是夏娃。因此,實際發生的情況是,實驗者對大量生物(但不包括人類)注射了綠色藥物,並得到了上述結果。顯然,夏娃有理由猶豫是否要注射這種綠色藥物。這種藥物對蛇、青蛙、老鼠和蝙蝠都有效,這一點為真。她是抽取的科學樣本所屬群體中的一部分,這一點也為真,但這顯然沒有什麼安慰作用。
事實上,如果從鄰近的城鎮(那裡所有生物都是人類)傳來消息說,實驗只在當地一名居民身上進行,而她注射了這種藥物後不僅沒有增強記憶力,反而出現劇烈頭痛,那麼我們都能認同夏娃的懷疑態度。6
幸運的是,懷疑和理性也是平靜(equanimity)的關鍵——它們不僅在生活中有用,也是幸福的來源。我上面提到泰勒斯透過長期觀察行星和思考,獲得了令人驚嘆的科學洞見。我相信,這些長時間的思考和推理本身,必定是泰勒斯快樂和平靜的泉源。我希望讀者讀完本書後能認同,追求知識是享樂主義的一種形式。
但我要特別指出一點,在強調理性價值的同時,我無意忽視需要醫療協助的實際精神疾病。在這種情況下,一個人可能無法善用心智,而推理也不會有太大幫助。諷刺的是,美國數學家約翰‧納許(John Nash,1928–2015)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納許是賽局理論領域的重要人物,也是歷史上的偉大思想家,但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時間都因思覺失調症(schizophrenia)而失能,這位理性大師在生病期間無法利用自己的能力來幫助自己。
本書沒有涉及這些深層的心理問題,而是關於如何處理日常生活中的麻煩和困難。基於多年來的經驗,我深信推理是最唾手可得,但未受到充分利用的良藥。
我們一生中大部分時間都在追尋幸福和滿足,同時設法克服障礙和挑戰。然而,這趟人生旅程中最強大,但未被充分利用的工具之一,其實是我們所有人都擁有的工具,也就是推理能力。因此,這本書的書名就有了雙重意義。古代哲學家試圖理解我們周圍的世界,並定義一種有意義的生活方式。本書重新審視這些古老的主題,只不過藉助了現代學科的彈藥,特別是經濟學和賽局理論。在這個過程中,本書也探討了這些學科背後的哲學瑕疵和悖論,以及它們所引起的道德困境,希望能吸引讀者投入這場知識與理解的探索。
這本書的架構是倒金字塔型。一開始的重點在於個人以及日常生活中的理性選擇和推理,從辦公室政治到個人難題。之後書中繼續探討集體福祉和群體的道德責任。最後一章則從個人和集體的角度,聚焦於最宏大的關切,即全球問題,我們將討論,如何解決這個動盪的世界所面臨的一些問題。作為個人,我們能否讓世界變得更美好?如果可以,又該怎麼做?為了開始尋找答案,我想先從展示賽局理論能如何拯救生命開始。
▎如何避免核子戰爭
一九七二年,我來到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求學,幾週後我經過布藍茲維廣場(Brunswick Square)時,有個小孩朝我扔水球。水球擦過我的肩膀,但沒有造成傷害。我當時還很青澀,又是初來乍到,再加上第一次離開祖國印度,所以我猶豫了一會兒,不知道是否值得挑起爭端。我判斷沒有理由這麼做,所以若無其事繼續走。
就在這時,一個身材魁梧的男子大步走到我面前,面上毫不掩飾他的鄙夷(更多的是對我而不是對那個男孩),他說:「年輕人,如果我是你,就會把那個小子痛打一頓。」我當時的第一反應是:「不,你不會,因為正如你剛才看到的,我沒有。」當然,考慮到他傾向於使用武力,我並沒有把這句話說出口。
如果我是你是道德推理的要點,從康德倫理學到福利經濟學和賽局理論都是如此。然而,它卻經常受到誤解。如果真的照字面解讀,那麼一旦「我」看到「你」的行為,就沒有理由再猜測如果我是你我會做什麼。另一方面,如果「如果我是你」的意思是「如果我有一部分像你」,那麼就會出現許多有趣的問題,也會有很多模糊之處,因為在許多方面我都有可能像你。
賽局理論涉及大量這類推理。光是聰明還不夠;你必須能夠將自己置於其他聰明人的立場上,思考她可能會做些什麼——而這反過來又當然是基於她認為你可能會做些什麼。
有鑑於布藍茲維廣場靠近倫敦大學,那名男子很有可能是一名教授。他或許也擅長研究。然而,此時他的情緒勝過了理智。這是常見的人類傾向和許多判斷錯誤的根源,同時也是促成本書的重要動機。
本書旨在闡明我們為什麼有理由感到幸福,以及為什麼我們必須善用推理才能幸福。為了闡明我的觀點,我將借用賽局理論中所使用的推理方法。賽局理論是社會情境中演繹推理的藝術。因此,它在戰爭和外交、制定企業戰略、甚至在我們日常的人際關係中都具有價值。
▎決定人類命運的關鍵賽局
一九六二年十月十六日星期二上午九點左右,甘迺迪總統從國家安全顧問邦迪(McGeorge Bundy)那裡得知,一架美國U-2偵察機發現蘇聯在古巴部署了核子彈道飛彈,這些導彈可以在幾分鐘內襲擊美國城市。甘迺迪的當務之急是決定他和美國該做什麼,而這個決定主要取決於他認為蘇聯總理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會對他的行為做出什麼反應。當時他無疑意識到,赫魯雪夫會採取什麼行動,取決於他認為甘迺迪會如何回應他的所作所為。這是一個經典的賽局理論問題,涉及下棋或打橋牌時所使用的那種推理。這裡的不同之處在於,賭注攸關生死。
接下來的十三天,是歷史記載中人類存亡最危急的關頭之一。全世界時刻關注這場令人毛骨悚然的「賽局」。近一八○架攜帶核武的轟炸機奉命持續滯空,飛抵蘇聯邊境然後返回。訊息很明確:如果美國遭到攻擊,美國也許會滅亡,但俄羅斯也會陪葬。這就是所謂的「第二擊戰略」(second-strike strategy),目的是遏阻任何考慮進行第一擊的人。一旦有國家擁有核子能力,對另一個考慮生產核武的國家來說,第二擊能力被認為是必備的。擁有核彈卻不具備第二擊能力,就等於自尋攻擊。美國公開展示第二擊能力的戰略奏效。赫魯雪夫最終讓步,世界得救了。
但幾乎無人注意到,白宮對戰略和反制戰略進行了多麼漫長的討論,主要是因為這些討論都是祕密進行。事實上,甘迺迪在高度緊繃的情勢下,花了六天才做出回應。經過深思熟慮,美國總統決定在十月二十二日公開告知美國人民他們所面臨的危機,並致信赫魯曉夫詳細說明美國的應對計劃。1全世界都要感謝甘迺迪領導的美國政府在那六天中製定了高超的戰略,使世界從世界大戰和毀滅的邊緣悄然後撤。赫魯雪夫選擇丟臉而不是滅世,也是功不可沒。
甘迺迪之所以能在這場戰局中處理得當,主要是記取了於一年多前豬玀灣事件(Bay of Pigs)慘敗的教訓,當時在美國支持下,古巴流亡人士發動武裝行動,結果被古巴武裝力量迅速擊潰,時間短到令美方顏面盡失。甘迺迪意識到推翻古巴共產主義政府的企圖之所以失敗,並不是因為美國沒有更多的槍支和武器,而是因為他沒有花足夠的時間深思熟慮並制定戰略。
用梅和澤利科夫(May and Zelikow, 1997, p. 14)的話來說,豬玀灣事件的失敗使甘迺迪意識到「他不僅詢問的顧問太少,給予這些議題的時間也太少。」這件事帶來的結果之一是,美國經濟學家謝林 (Thomas Schelling)被要求撰寫一篇關於核子戰略的論文,而他於一九六一年七月五日完成並提交。據國家安全顧問邦迪的說法,這篇論文「給總統留下深刻的印象」。這反過來又在引導國家度過隔年的古巴飛彈危機中發揮了巨大作用。
在我寫這本書時,拜登總統正忙於回應普丁對烏克蘭的入侵。對於他考慮的每一項支持措施,他都必須思考普丁會如何回應。這十分令人憂心,因為普丁的理性堪慮。由時事評論家扎卡里亞(Fareed Zakaria)主持的CNN紀錄片《普丁的內心世界》(Inside the Mind of Vladimir Putin)非常精采。唯一的問題是,看完之後,你還是不知道普丁到底在想什麼。
▎賽局理論的盲點
儘管賽局理論是二十世紀出現的最令人興奮的學科之一,但它也有盲點,所以我們必須利用直覺、心理學、政治和哲學。我們必須接受這樣一個事實:並非所有問題都有解決方案。透過結合這些不同方法的見解,我們也只能希望增加成功的可能性。
人類經過數千年的演化,已經能夠直覺地感受到其他人的想法,這為賽局理論提供了一些基礎。但作為一門連貫而自成一格的學科,賽局理論出奇地年輕。波雷爾(Émile Borel)是法國著名的數學家,後來成為政治家,他在一九二一年發表了一些關於賽局理論的重要著作。賽局理論作為一種分析方法,影響遍及從經濟學、政治學、心理學,到進化生物學、計算機科學和哲學等一系列學科,但它其實是在二十世紀中葉才突然出現——就像菲利普‧拉金(Philip Larkin)第一次的享樂主義邂逅,發生在《查泰萊》(Chatterley)禁令結束和披頭四樂隊發行第一張LP之間。賽局理論的出現大致與原子彈的發明在同一時期,當時跨國公司也開始以全新方式相互競爭並與政府競爭,這也許並非偶然。透過為戰爭、外交和企業戰略提供分析工具,它塑造了現代世界的某些維度。
接下來幾頁將用賽局理論的故事,來說明我們如何面對生活中的挑戰。不過,這本書並非所有內容都是在直接幫助解決特定問題。這本書每次只讀上幾頁,對大腦的作用就如同慢跑對身體的作用。我們慢跑不是因為它有什麼產出或收入,而是為了增進身體健康,以便在做其他事情時可以更有效率。同樣地,邏輯和賽局理論可以鍛鍊我們的思維,好在我們有需要時,能夠更有效地調動大腦。有些讀者也許會希望每天閱讀這本書幾頁,以代替每日數獨或填字遊戲。
在這個心智運動的過程中,本書將向讀者介紹一些重要的難題和悖論。就像慢跑一樣,這些心智運動本身就很有趣,而且對心智有療癒作用。正如早期希臘哲學家,特別是斯多葛學派(Stoics)所意識到的,哲學不僅是一種智性探索,也是一種生活方式。而且,如果在這個過程中,你成功地解開了一個前人未解的悖論,即使你沒有從中獲得快樂,你也會成為史上留名的哲學家,如果這算得上安慰的話。
▎羅素的雞
「如果這算得上安慰的話」這個警語是必要的。就拿法國物理學家達朗貝爾(Jean-Baptiste le Rond d’Alembert)養母的憂慮來說好了。達朗貝爾於一七一七年十一月十六日,被生母遺棄在巴黎聖尚勒朗德教堂的台階上,當時他才出生沒幾天。他以這座教堂為名,一開始在孤兒院長大,後來由養母收養。奇蹟般地,儘管人生開端艱難,他卻成為世界上最偉大的思想家之一,為數學、哲學、音樂理論和物理學做出了重要貢獻。然而,他的養母仍然感到失望,因為他似乎從來沒有做過任何有用的工作。當達朗貝爾向她講述他的一項發現時,她的回應非常出名:「你除了當個哲學家,什麼也不會做——那又算什麼呢?不過是個傻瓜,一輩子都在自尋煩惱,只為了死後還能被人談論。」
確實,哲學以及所有精神追求,都帶有逃避現實的成分。這並沒有什麼害處,而且能幫助人們達到內心的平靜(ataraxia),而這正是皮浪(Pyrrho of Elis)等懷疑論者和芝諾(Zeno of Citium)、狄奧吉尼斯(Diogenes of Babylon)和愛比克泰德(Epictetus)等斯多葛學派所提倡的。同時,對真實和科學的追求有時會帶來智性突破,大大擴展我們對宇宙的理解,並為創造更美好的世界提供要素。
▎人類智性的重大突破
有時人們會說哲學作為一門學科,是始於西元前五八五年五月二十八日。那天出現了日蝕,當然並不是史上第一次。這次的不同之處在於米利都的泰勒斯(Thales of Miletus)已經預言了日蝕的發生。泰勒斯是幾何大師,證明了一條關於圓和直角三角形的美麗定理。在幾乎沒有任何儀器,可以拉近距離觀測天空的情況下,對這次日蝕的預測是透過思考和推測的結果。這是人類一次重大的智性突破,是經年累月追蹤行星和恆星的運動,以及歸納和演繹推理的成果。
歸納推理涉及觀察自然界的模式,並根據這些模式得出有關未來的結論。大多數人都相信明天太陽還會升起,因為我們一直以來,都看見太陽十分規律地升起。這就是歸納推理。
另一方面,演繹則需要根據純粹邏輯的前提得出結論。真實已經包含在前提之中。在直角三角形中,斜邊正方形的面積等於另外兩邊正方形的面積總和。我們不需要收集世界各地的三角形,進行仔細的測量然後才得出結論。這個結論是根據三角形、直角和正方形等概念的定義得出的。它非常透明,原則上任何人都可以看得出來。只不過在畢達哥拉斯之前沒有人看出來,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即使是現在,在畢達哥拉斯之後已經過了二千五百多年,學生也常常因為想看卻看不出來而流淚。
▎科學與迷信比想像中相似
早年讓我迷上哲學的是羅素(Bertrand Russell)在他那本薄薄的專著《哲學問題》(The Problems of Philosophy,p. 98)中,對歸納推理的精彩評論:「那個在雞的一生中每天都餵雞的人,最後卻扭斷了雞的脖子,這代表有關自然統一性更細緻的觀點,對雞會是有用的。」這段話完美地說出歸納法的缺陷,敦促我們採取懷疑論。這是訴諸理性的懇求。我相信其中有很多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
我對羅素唯一小有意見的地方在於規範性(prescriptive)部分。我把這段話稍作修改,改為:那個在雞的一生中每天餵雞的人,最後卻扭斷了雞的脖子,以此向人類展示像雞一樣生活的好處。
畢竟,雞無法改變自己出現在餐桌上的命運。為你無法控制的事情煩惱,只會帶給你不必要的痛苦。去深思可得或「可行」的「行動」或「策略」,以便做出正確的選擇,並最大化金錢、權力、名譽或任何你所追求的東西,當然是值得的。然而,人類卻花了大量的時間在擔心我們無法控制的事情。如果雞對自己的命運無能為力,那麼對餵雞人生氣,只會讓雞的生命更加暗淡。我說我們應該像雞一樣生活,並不是說我們應該自我欺騙,相信未來會和過去一樣。我的意思是,一旦我們明白人無法撼動命運的軌跡,就應該努力把日子過好,就如同未來會像過去一樣美好一般。
羅素的思想實驗讓人們關注歸納法的問題。太陽每天都會升起,但這並不能保證它明天還會升起。當然,我們是靠歸納法過活的。我們觀察自然界中的模式,或者更準確地說,觀察自然並在我們的頭腦中創造模式。然而,這缺少客觀理由。如果有人說,儘管有這麼多科學證據,她還是不相信接種疫苗可以保護她免受新冠病毒感染,那麼就沒有充分的理由能駁斥她的說法。我們所謂的科學與迷信之間的差別,並沒有我們想像的那麼大。而誠實,要求我們抱持懷疑。
▎懷疑與理性是幸福的根源
法國攝影師瓦利(Eric Valli)長期拍攝尼泊爾的古隆族部落(Gurung),部落裡的人會冒險攀爬高樹以採集蜂蜜。他曾經問過其中一人,是否有人從高處摔落。被問及的男子一本正經地回答:「有的,一個人的生命要結束時,他就會摔下來。」我建議讀者不要完全忽視古隆族的觀點。
歸納很重要,但我們需要留意它在發現因果關係方面的缺陷。假設研究人員來到一個社區,想測試給居民注射一種綠色化學物質以改善記憶力的效果。他們進行了大量測試,發現這種注射在每一例中都大幅提高記憶力,並且沒有任何負面副作用。如果研究正確完成,它可能被視為一項重要發現,並將發表在主要的科學期刊上。現在,如果這個鎮上有一名叫夏娃的女子,她沒有接受測試,但渴望增強自己的記憶力。她能否根據這項科學研究做出推斷,如果注射這種藥物,她的記憶力就會提高?歸納法的信徒會自信地回答「是的」。想知道為什麼他們的信心值得懷疑,請容我補充一些上述科學實驗的細節。
假設這個社區裡剛好住著大量蛇、青蛙、老鼠和蝙蝠,而只有一個人,那就是夏娃。因此,實際發生的情況是,實驗者對大量生物(但不包括人類)注射了綠色藥物,並得到了上述結果。顯然,夏娃有理由猶豫是否要注射這種綠色藥物。這種藥物對蛇、青蛙、老鼠和蝙蝠都有效,這一點為真。她是抽取的科學樣本所屬群體中的一部分,這一點也為真,但這顯然沒有什麼安慰作用。
事實上,如果從鄰近的城鎮(那裡所有生物都是人類)傳來消息說,實驗只在當地一名居民身上進行,而她注射了這種藥物後不僅沒有增強記憶力,反而出現劇烈頭痛,那麼我們都能認同夏娃的懷疑態度。6
幸運的是,懷疑和理性也是平靜(equanimity)的關鍵——它們不僅在生活中有用,也是幸福的來源。我上面提到泰勒斯透過長期觀察行星和思考,獲得了令人驚嘆的科學洞見。我相信,這些長時間的思考和推理本身,必定是泰勒斯快樂和平靜的泉源。我希望讀者讀完本書後能認同,追求知識是享樂主義的一種形式。
但我要特別指出一點,在強調理性價值的同時,我無意忽視需要醫療協助的實際精神疾病。在這種情況下,一個人可能無法善用心智,而推理也不會有太大幫助。諷刺的是,美國數學家約翰‧納許(John Nash,1928–2015)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納許是賽局理論領域的重要人物,也是歷史上的偉大思想家,但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時間都因思覺失調症(schizophrenia)而失能,這位理性大師在生病期間無法利用自己的能力來幫助自己。
本書沒有涉及這些深層的心理問題,而是關於如何處理日常生活中的麻煩和困難。基於多年來的經驗,我深信推理是最唾手可得,但未受到充分利用的良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