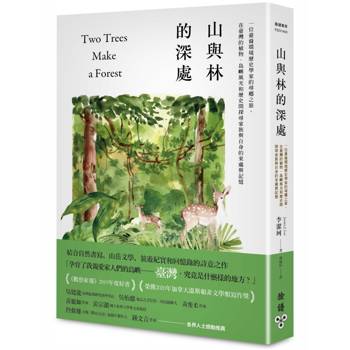上了年紀後,外婆變得性情古怪,反覆無常。外公去世到她離開那十年間,我和媽媽常去探望她。我一邊喝茶,一邊聽她們用中文交談,學到一些抨擊和抱怨的字眼,知道媽媽沉默不語時會換上什麼表情。我時常想起外婆不經意告訴我的一句話:「我對妳媽的批評還不及我媽對我的一半呢。」我忍不住納悶,我們怎麼有辦法控制、無視她的言行舉止這麼多年,認為她只是性格乖僻而已。
幾年前,就在我要搬到德國之前,我們帶她去她喜歡的壽司店吃午餐。席間她突然從讚美我轉向批評我媽媽,連珠炮般罵個不停,緊張氣氛一觸即發。她很氣媽媽認為她需要別人更多的照顧,她不准、也不想要別人幫忙。
回到她的住處後,她的怒火開始轉移到一些沒那麼具體、令人不安又無法控制的事物上。她緊抱著我,抱了好久好久,我能感受到她身體的變化。
外婆緊抓著我的手哭倒在地,力道之大完全超乎我對九十歲老嫗的想像。她用中文尖聲大吼,又說了一串英文:「如果妳走,我也不想活了!我永遠見不到妳了!」她快步奔向陽臺,我立刻傾身向前把她拉回來,動作非常小心,不想傷到她皮膚漸薄、纖細脆弱的四肢。她的力氣怎麼這麼大?
我對媽媽拋了一個求救的眼神;這時,外婆一把抓住我的腳踝,我們雙雙跌坐在地,她站起身,又往陽臺走。我試著穩住她的身體,跟她講道理。「我會回來,我們一定會再見。」
我腦海中閃過外公的身影,想起自己沒見到他最後一面。
救護車來了。外婆的手指像樹根一樣纏繞著我;醫護人員好不容易鬆開她的手,她再度跑向陽臺,不過被他們及時攔住。一根針頭扎進皮膚,她便安靜下來。
抵達醫院後,她躺在病床,臉上掛著平靜的微笑。我開始懷疑自己是不是反應過度,心裡好後悔,不知道這麼做到底對不對。老年醫學專家來了,然後是心理學家。他們說外婆沒什麼問題,沒有失智,也不會對自己造成傷害。事實上,她對所有醫生都很友善。我們想跟社工談談嗎?
我心煩意亂,憤怒、憐憫和悲傷交織在一起,不知道要怎麼跟外婆相處。她躍向死亡邊緣,是我把她拉回來。我想起十多年前的某個午後,她講了一個故事給我聽。
一九二九年,外婆在中國南京嚥氣。那年她五歲。早上九點,她的心跳驟然停止。沒有人察覺不對勁,因為她經常昏倒,上演一系列誇張鬧劇,讓她的母親和家中僕役都很頭痛。可是過了幾分鐘,她依舊毫無動靜,眾人嚇得驚慌失措。
大家捏她的手臂,在旁邊焚香,試圖讓她甦醒過來,可是沒用。他們又按摩她的胸口,揉搓她的腳(我和她第三根腳趾上都有胎記),在驚慌惱怒下替她換上暖和的厚衣,但外婆還是沒反應。到了傍晚,他們決定放棄。她的父親命人把門從鉸鏈上拆下來,擺在地上,將那具年幼的身軀抬上門板安放,準備下葬。
這時,一個廚房伙計跳出來說話。
「夫人,你們這麼快就放手,不救桂林了嗎?」他問道。
「我們不曉得還能怎麼辦。」外婆的媽媽回答。
「你們沒帶她去醫院,也沒叫醫生!」年輕的廚房伙計大喊,「如果覺得麻煩,請讓我來辦。」
他在外婆家人的允許下,於日落前趕到鎮上,帶著一位通曉針灸醫術的拾荒老人回來。楊家認為女兒已經死了,便任憑老人採取他覺得適當的治療方式。老人蹲下來查看外婆的情況,接著把手伸進袋裡,拿出一個裝著針具的木盒。他不發一語,精準地將兩排金針從她頭頂一直插到細瘦的腳跟,並在穴位多加二十根針,直到她的身體看起來像個閃閃發光的洋娃娃造型針墊。老人帶著滿意的神情蹲踞在地,要他們耐心等候。
他們靜靜在屋裡踱步,等了三個小時。十一點,外婆喉嚨裡傳出一陣刺耳的聲響,下一秒,她突然筆直坐起來放聲大叫,金針在燭火下閃爍著亮光。
「媽!」她喊了她的母親。
從鬼門關前走一遭的外婆看起來毫髮無傷,身體也很正常,恢復了以往的生活。雖然她嚐過死亡的滋味,始終擔憂自己孱弱的心臟,但她再也沒暈倒過。
*
崩坍岩壁另一邊,能高步道路緣雲海翻騰,長滿潮溼苔蘚的森林愈來愈濃密。隨著步道爬升,山坡周圍的環狀森林帶從低海拔地區的橡樹和扁柏逐漸變成散發清香的鐵杉和冷杉。各物種彼此交疊,往外延伸,探向微弱的光線。閃耀的地衣爬附於裸露的岩壁,在陰影中靜靜等待雨水降下,整座山岳蒙上一層苔蘚植物的光芒。苔類披垂於樹身,遮住棲息在枝幹上的火冠戴菊鳥。我繼續往前走,步道與能高山峰間的谷壑雲霧繚繞,白松開始越過岩壁,伸向虛無的天空,朝谷間那片蒼茫探去。
登山隊按個人的步調自然分組。攻頂的人於前方疾行,登山杖隨著步態規律擺動;至於我,當然是懶洋洋落在後頭,畢竟比起遠方的險崖,我對地面的細節更感興趣。這條步道橫貫起伏的山脊,直達奇萊山背光側。我細細品味自己徐緩的步伐,另一個健行夥伴腳步漸慢,也與我並肩同行,對方似乎還喜歡花時間慢慢拍照,注意那些只有趴在地上才看得到的小事物。
克里斯多夫來自慕尼黑,雖然我並不想念遠在德國的家,但能用德語為對話增添興味的感覺還是很棒。德文不像中文常用到齒音和唇音,我能感受到字母的音讀和形狀在口腔後方延伸。我們聊了一個下午,將文學和山水詩帶入山間。他跟我分享卡夫卡(Franz Kafka)創作的短篇小說《中國長城》(The Great Wall of China,一部關於帝國、國家認同與長城建築的作品),提到他喜歡的臺灣畫家。身為戲劇系教授的他閒暇時總往山裡跑,如今他的臺灣之旅接近尾聲,島上群峰卻緊緊擄獲他的心。他似乎很不想離開。
我們在岩層裸露的步道上邊走邊聊,突然間,兩人都停下腳步。空氣中瀰漫著杏仁和現烤蛋糕的味道,甜甜的,好像沾滿了糖。我們出於直覺抬起頭,看著附近一棵開花的樹,連忙湊上去聞了聞,結果只換來失望。那棵樹沒半絲氣味。我們發現只有原地才聞得到香氣,無論往前或往後一步都不行。我望向步道邊緣,除了厚實的泥土外什麼也沒有。我沮喪地轉向懸崖附近的溝渠,只見零星幾株灌木和草本植物,有簇植叢帶著紅綠色葉子,點綴著白色小花。我們蹲下身(想像一下克里斯多夫這樣高大的日耳曼人蹲伏在地的模樣),濃濃的香氣撲鼻而來,這些小花散發出非比尋常、不可思議的芬芳。我們倆都拍下照片,想知道這是什麼植物。後來我花了好幾週時間不斷追查才找到答案。這種植物叫火炭母草,別名早辣蓼、烏炭子等。
在臺灣,火炭母草還有一個別稱叫「清飯藤」,花如其名,碧草如茵的步道旁開著許多如米粒般的小白花。這種植物是臺灣和東南亞的原生種,常見於緩坡丘陵上的茶園和村落附近的溝渠。傳到國外的火炭母草被貼上「外來入侵種」的標籤,可是在這裡,在它家鄉山區,是一件洋溢美感的事物。甜蜜的花香讓我有種飄飄然的感覺,一路飛向林線。
一九○○年,早田文藏來臺旅居兩個月,接著返回東京念書。他過去十多年來一直想正式鑽研植物學,如今夢想成真。當時二十六歲的早田一直很想完成學業、進行研究,他從青少年時期就對植物很感興趣,甚至還加入東京植物學會(Botanical Society of Tokyo),但家庭因素讓他不得不延遲進入大學就讀。
讀研究所時,他的導師、臺灣植物學先驅松村任三認為早田應該要將研究重點轉向臺灣植群,而非專注於自己喜歡的苔蘚,就此開拓出他的學術之路與發展方向。早田懷著年輕人特有的熱情與雄心展開專題研究,試圖區別臺灣與東亞其他地域的植物相。他認為,過去那些讓調查行動窒礙難行的環境條件正是臺灣植群之所以獨特的原因。西部平原逐漸擴展,爬升成陡峭又難以到達的群山,隨後地勢再度往下,延伸到東海岸,涵蓋了亞熱帶到高山棲地,形成獨一無二的林相。一旦日本政府成功進入高海拔山區(後來也的確達成這個目標,興建了能高越嶺道),他們便得以為植物考察開闢新路。早田在日本和臺灣進行了幾年研究,後又前往倫敦邱園(Kew Gardens)、柏林達勒姆(Dahlem)、巴黎和聖彼得堡的植物標本館參訪,並於一九一一年正式出版《臺灣植物圖譜》(Icones Plantarum Formosanarum)第一卷。他在序言中簡單勾勒出一個抱負遠大的系列叢書計畫:「我一直很想出版一套福爾摩沙植物志,(中略)應該十五年內就能完成。」事實上,他耗費了十年的時間和心力,進行大量植物研究和採集,編纂出一套十卷的植物志,收錄了近一百七十科、一千兩百屬的維管束植物,共有三千六百五十八種和七十九種變種。
早田的貢獻與遺澤仍蘊存在植物名稱裡,延續至今。根據植物學家大橋廣好的統計,早田在東亞與東南亞勘察植物期間,一共命名了兩千七百多個物種,其中臺灣就占了一千六百多種。然而,他之所以能研究這麼廣的植物相、進行物種分類,部分原因是因為日方成功涉足前朝從未進入的界域。十九世紀的植物學家根本無法到達這些地方。
當然,臺灣有許多植物都是在地居民發現並命名的。一個世紀前,隨著現代分類學的興起和傳播,學界開始記錄臺灣物種、編纂目錄,區分當地與他國物種。西方植物學和地質學一樣,透過探索與殖民擴張來到這座海島。一八五三年,以竊取中國茶株與製茶技術並引進印度,助英國建立茶業基地而聞名的蘇格蘭植物學家羅伯.福鈞(Robert Fortune),就曾對臺灣部分沿海植物進行編目,是臺灣島第一份植物研究紀錄。一八六○年代,英國駐臺領事、生物學家郇和(Robert Swinhoe,羅伯.斯文豪)著手調查臺灣自然史。十九世紀末,愛爾蘭植物學家韓爾禮(Augustine Henry,奧古斯丁.亨利)發表了一份名錄,記載了近一千五百種臺灣植物。
科學標籤承載著許多過往,光從命名法就能一窺歷史的樣貌。比方說,臺灣有許多以斯文豪(即郇和)和早田(Hayata)命名的動植物,前者如斯文豪氏鷴(Lophura Swinhoii,即藍腹鷴),後者如早田山毛櫸(Fagus hayatae,即臺灣山毛櫸)和玉蘭草(Hayatella,臺灣特有的茜草科植物,只有一筆紀錄,發現地為臺灣東部)。此外,臺灣最高峰玉山多年來又稱為摩里遜山(Mount Morrison);摩里遜是一位外國船長,至今仍可在植物名錄中看到此人名字,例如玉山小蘗(Berberis morrisonensis,別名赤果小蘗)、玉山當歸(Angelica morrisonicola)等上百個物種都是以此命名,其中許多都是由早田本人親自記錄。
語言是很棘手的東西,科學標籤無法界定這些形成世界秩序的名謂。我研究臺灣植物時,會對照俗名與學名、中文與臺文名稱。若找不到英譯名,那株植物就只能礙於語言限制的束縛,存在我腦海裡。於我而言,許多臺灣植物名稱被困在兩種語界之間,只有一小部分叫得出名字。我用柏林的華語老師給我的表格,以英文和繁體中文寫下植物名稱,再加上拼音註明發音。例如八角金盤為bajiao jinpan,鞭打繡球則是bianda xiuqiu(後者並沒有通用的英文名稱)。我用拉丁文寫下這些植物名——Fatsia polycarpa、Hemiphragma heterophyllum——感覺這樣好像比較安定、踏實一點。
幾年前,就在我要搬到德國之前,我們帶她去她喜歡的壽司店吃午餐。席間她突然從讚美我轉向批評我媽媽,連珠炮般罵個不停,緊張氣氛一觸即發。她很氣媽媽認為她需要別人更多的照顧,她不准、也不想要別人幫忙。
回到她的住處後,她的怒火開始轉移到一些沒那麼具體、令人不安又無法控制的事物上。她緊抱著我,抱了好久好久,我能感受到她身體的變化。
外婆緊抓著我的手哭倒在地,力道之大完全超乎我對九十歲老嫗的想像。她用中文尖聲大吼,又說了一串英文:「如果妳走,我也不想活了!我永遠見不到妳了!」她快步奔向陽臺,我立刻傾身向前把她拉回來,動作非常小心,不想傷到她皮膚漸薄、纖細脆弱的四肢。她的力氣怎麼這麼大?
我對媽媽拋了一個求救的眼神;這時,外婆一把抓住我的腳踝,我們雙雙跌坐在地,她站起身,又往陽臺走。我試著穩住她的身體,跟她講道理。「我會回來,我們一定會再見。」
我腦海中閃過外公的身影,想起自己沒見到他最後一面。
救護車來了。外婆的手指像樹根一樣纏繞著我;醫護人員好不容易鬆開她的手,她再度跑向陽臺,不過被他們及時攔住。一根針頭扎進皮膚,她便安靜下來。
抵達醫院後,她躺在病床,臉上掛著平靜的微笑。我開始懷疑自己是不是反應過度,心裡好後悔,不知道這麼做到底對不對。老年醫學專家來了,然後是心理學家。他們說外婆沒什麼問題,沒有失智,也不會對自己造成傷害。事實上,她對所有醫生都很友善。我們想跟社工談談嗎?
我心煩意亂,憤怒、憐憫和悲傷交織在一起,不知道要怎麼跟外婆相處。她躍向死亡邊緣,是我把她拉回來。我想起十多年前的某個午後,她講了一個故事給我聽。
一九二九年,外婆在中國南京嚥氣。那年她五歲。早上九點,她的心跳驟然停止。沒有人察覺不對勁,因為她經常昏倒,上演一系列誇張鬧劇,讓她的母親和家中僕役都很頭痛。可是過了幾分鐘,她依舊毫無動靜,眾人嚇得驚慌失措。
大家捏她的手臂,在旁邊焚香,試圖讓她甦醒過來,可是沒用。他們又按摩她的胸口,揉搓她的腳(我和她第三根腳趾上都有胎記),在驚慌惱怒下替她換上暖和的厚衣,但外婆還是沒反應。到了傍晚,他們決定放棄。她的父親命人把門從鉸鏈上拆下來,擺在地上,將那具年幼的身軀抬上門板安放,準備下葬。
這時,一個廚房伙計跳出來說話。
「夫人,你們這麼快就放手,不救桂林了嗎?」他問道。
「我們不曉得還能怎麼辦。」外婆的媽媽回答。
「你們沒帶她去醫院,也沒叫醫生!」年輕的廚房伙計大喊,「如果覺得麻煩,請讓我來辦。」
他在外婆家人的允許下,於日落前趕到鎮上,帶著一位通曉針灸醫術的拾荒老人回來。楊家認為女兒已經死了,便任憑老人採取他覺得適當的治療方式。老人蹲下來查看外婆的情況,接著把手伸進袋裡,拿出一個裝著針具的木盒。他不發一語,精準地將兩排金針從她頭頂一直插到細瘦的腳跟,並在穴位多加二十根針,直到她的身體看起來像個閃閃發光的洋娃娃造型針墊。老人帶著滿意的神情蹲踞在地,要他們耐心等候。
他們靜靜在屋裡踱步,等了三個小時。十一點,外婆喉嚨裡傳出一陣刺耳的聲響,下一秒,她突然筆直坐起來放聲大叫,金針在燭火下閃爍著亮光。
「媽!」她喊了她的母親。
從鬼門關前走一遭的外婆看起來毫髮無傷,身體也很正常,恢復了以往的生活。雖然她嚐過死亡的滋味,始終擔憂自己孱弱的心臟,但她再也沒暈倒過。
*
崩坍岩壁另一邊,能高步道路緣雲海翻騰,長滿潮溼苔蘚的森林愈來愈濃密。隨著步道爬升,山坡周圍的環狀森林帶從低海拔地區的橡樹和扁柏逐漸變成散發清香的鐵杉和冷杉。各物種彼此交疊,往外延伸,探向微弱的光線。閃耀的地衣爬附於裸露的岩壁,在陰影中靜靜等待雨水降下,整座山岳蒙上一層苔蘚植物的光芒。苔類披垂於樹身,遮住棲息在枝幹上的火冠戴菊鳥。我繼續往前走,步道與能高山峰間的谷壑雲霧繚繞,白松開始越過岩壁,伸向虛無的天空,朝谷間那片蒼茫探去。
登山隊按個人的步調自然分組。攻頂的人於前方疾行,登山杖隨著步態規律擺動;至於我,當然是懶洋洋落在後頭,畢竟比起遠方的險崖,我對地面的細節更感興趣。這條步道橫貫起伏的山脊,直達奇萊山背光側。我細細品味自己徐緩的步伐,另一個健行夥伴腳步漸慢,也與我並肩同行,對方似乎還喜歡花時間慢慢拍照,注意那些只有趴在地上才看得到的小事物。
克里斯多夫來自慕尼黑,雖然我並不想念遠在德國的家,但能用德語為對話增添興味的感覺還是很棒。德文不像中文常用到齒音和唇音,我能感受到字母的音讀和形狀在口腔後方延伸。我們聊了一個下午,將文學和山水詩帶入山間。他跟我分享卡夫卡(Franz Kafka)創作的短篇小說《中國長城》(The Great Wall of China,一部關於帝國、國家認同與長城建築的作品),提到他喜歡的臺灣畫家。身為戲劇系教授的他閒暇時總往山裡跑,如今他的臺灣之旅接近尾聲,島上群峰卻緊緊擄獲他的心。他似乎很不想離開。
我們在岩層裸露的步道上邊走邊聊,突然間,兩人都停下腳步。空氣中瀰漫著杏仁和現烤蛋糕的味道,甜甜的,好像沾滿了糖。我們出於直覺抬起頭,看著附近一棵開花的樹,連忙湊上去聞了聞,結果只換來失望。那棵樹沒半絲氣味。我們發現只有原地才聞得到香氣,無論往前或往後一步都不行。我望向步道邊緣,除了厚實的泥土外什麼也沒有。我沮喪地轉向懸崖附近的溝渠,只見零星幾株灌木和草本植物,有簇植叢帶著紅綠色葉子,點綴著白色小花。我們蹲下身(想像一下克里斯多夫這樣高大的日耳曼人蹲伏在地的模樣),濃濃的香氣撲鼻而來,這些小花散發出非比尋常、不可思議的芬芳。我們倆都拍下照片,想知道這是什麼植物。後來我花了好幾週時間不斷追查才找到答案。這種植物叫火炭母草,別名早辣蓼、烏炭子等。
在臺灣,火炭母草還有一個別稱叫「清飯藤」,花如其名,碧草如茵的步道旁開著許多如米粒般的小白花。這種植物是臺灣和東南亞的原生種,常見於緩坡丘陵上的茶園和村落附近的溝渠。傳到國外的火炭母草被貼上「外來入侵種」的標籤,可是在這裡,在它家鄉山區,是一件洋溢美感的事物。甜蜜的花香讓我有種飄飄然的感覺,一路飛向林線。
一九○○年,早田文藏來臺旅居兩個月,接著返回東京念書。他過去十多年來一直想正式鑽研植物學,如今夢想成真。當時二十六歲的早田一直很想完成學業、進行研究,他從青少年時期就對植物很感興趣,甚至還加入東京植物學會(Botanical Society of Tokyo),但家庭因素讓他不得不延遲進入大學就讀。
讀研究所時,他的導師、臺灣植物學先驅松村任三認為早田應該要將研究重點轉向臺灣植群,而非專注於自己喜歡的苔蘚,就此開拓出他的學術之路與發展方向。早田懷著年輕人特有的熱情與雄心展開專題研究,試圖區別臺灣與東亞其他地域的植物相。他認為,過去那些讓調查行動窒礙難行的環境條件正是臺灣植群之所以獨特的原因。西部平原逐漸擴展,爬升成陡峭又難以到達的群山,隨後地勢再度往下,延伸到東海岸,涵蓋了亞熱帶到高山棲地,形成獨一無二的林相。一旦日本政府成功進入高海拔山區(後來也的確達成這個目標,興建了能高越嶺道),他們便得以為植物考察開闢新路。早田在日本和臺灣進行了幾年研究,後又前往倫敦邱園(Kew Gardens)、柏林達勒姆(Dahlem)、巴黎和聖彼得堡的植物標本館參訪,並於一九一一年正式出版《臺灣植物圖譜》(Icones Plantarum Formosanarum)第一卷。他在序言中簡單勾勒出一個抱負遠大的系列叢書計畫:「我一直很想出版一套福爾摩沙植物志,(中略)應該十五年內就能完成。」事實上,他耗費了十年的時間和心力,進行大量植物研究和採集,編纂出一套十卷的植物志,收錄了近一百七十科、一千兩百屬的維管束植物,共有三千六百五十八種和七十九種變種。
早田的貢獻與遺澤仍蘊存在植物名稱裡,延續至今。根據植物學家大橋廣好的統計,早田在東亞與東南亞勘察植物期間,一共命名了兩千七百多個物種,其中臺灣就占了一千六百多種。然而,他之所以能研究這麼廣的植物相、進行物種分類,部分原因是因為日方成功涉足前朝從未進入的界域。十九世紀的植物學家根本無法到達這些地方。
當然,臺灣有許多植物都是在地居民發現並命名的。一個世紀前,隨著現代分類學的興起和傳播,學界開始記錄臺灣物種、編纂目錄,區分當地與他國物種。西方植物學和地質學一樣,透過探索與殖民擴張來到這座海島。一八五三年,以竊取中國茶株與製茶技術並引進印度,助英國建立茶業基地而聞名的蘇格蘭植物學家羅伯.福鈞(Robert Fortune),就曾對臺灣部分沿海植物進行編目,是臺灣島第一份植物研究紀錄。一八六○年代,英國駐臺領事、生物學家郇和(Robert Swinhoe,羅伯.斯文豪)著手調查臺灣自然史。十九世紀末,愛爾蘭植物學家韓爾禮(Augustine Henry,奧古斯丁.亨利)發表了一份名錄,記載了近一千五百種臺灣植物。
科學標籤承載著許多過往,光從命名法就能一窺歷史的樣貌。比方說,臺灣有許多以斯文豪(即郇和)和早田(Hayata)命名的動植物,前者如斯文豪氏鷴(Lophura Swinhoii,即藍腹鷴),後者如早田山毛櫸(Fagus hayatae,即臺灣山毛櫸)和玉蘭草(Hayatella,臺灣特有的茜草科植物,只有一筆紀錄,發現地為臺灣東部)。此外,臺灣最高峰玉山多年來又稱為摩里遜山(Mount Morrison);摩里遜是一位外國船長,至今仍可在植物名錄中看到此人名字,例如玉山小蘗(Berberis morrisonensis,別名赤果小蘗)、玉山當歸(Angelica morrisonicola)等上百個物種都是以此命名,其中許多都是由早田本人親自記錄。
語言是很棘手的東西,科學標籤無法界定這些形成世界秩序的名謂。我研究臺灣植物時,會對照俗名與學名、中文與臺文名稱。若找不到英譯名,那株植物就只能礙於語言限制的束縛,存在我腦海裡。於我而言,許多臺灣植物名稱被困在兩種語界之間,只有一小部分叫得出名字。我用柏林的華語老師給我的表格,以英文和繁體中文寫下植物名稱,再加上拼音註明發音。例如八角金盤為bajiao jinpan,鞭打繡球則是bianda xiuqiu(後者並沒有通用的英文名稱)。我用拉丁文寫下這些植物名——Fatsia polycarpa、Hemiphragma heterophyllum——感覺這樣好像比較安定、踏實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