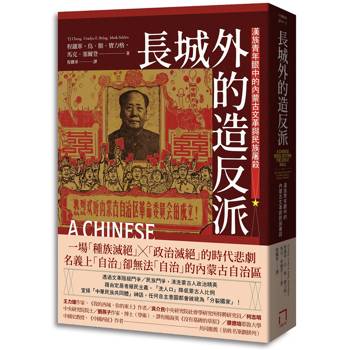【內文試閱】
第一章 華北農家子,隻身赴塞外
一九五八年,對全中國來說,都是一個轉折點,我自己也不例外。那年我十五歲,是河北省饒陽中學國二的住校生。
一九五八年夏天,學校沒放暑假,在物理老師周福田指導下,我們在校園建了三個小工廠:生產焦炭、鋼鐵和水泥。這是我們對席捲全國的「大躍進」所做的貢獻。黨國號召,農村也要生產作為工業標誌的鋼鐵和水泥,以實現所有人快速富裕的承諾。
一九五八年,也是饒陽乃至全國大部分地區夏秋作物將要大豐收的一年,但六月時出現嚴重的勞力短缺。幾乎所有體格健壯的饒陽男性,都被動員到承德縣正在建造的鋼鐵廠和其他工廠。承德是清朝皇帝的避暑勝地和夏都,位於北京東北二百多公里的長城以北。
到了八月,衡水地委發布一項令人震驚的通知:科學研究證明,紅薯(地瓜)產量遠高於玉米,所以,要改種紅薯。當時,玉米已經三尺來高,卻被下令砍倒,改插紅薯秧。以前,黨從未如此直接干預和侵犯農民的智慧。大家都知道,紅薯要在六月種植,才能成熟。村民無視上級命令時,幹部和民兵就直接介入,拉著兩公尺長的繩索,穿過田壟,毀掉玉米。村民的辛苦勞動付之東流,自然,改種紅薯的計畫胎死腹中。
大躍進也承諾大幅擴展全民教育,一九五八年一年內,饒陽縣的中學數量,就從一所增加到六所(每個大公社一所)。一九五八年冬至一九五九年春,我跟三十個男生,搬進縣中一排破舊的紅磚宿舍,十人擠住一個房間,五人合睡一張木板大通鋪。
但隨著工業下馬和飢餓加劇,學校人數大幅削減,部分學校開始關閉。一九五九年六月,校長命令學生站成兩排,大家開始報數:一、二,一、二……偶數學生繼續學業,奇數學生當場解散,被動員回家。當時沒有偏袒或特權,甚至沒有顯示出對地主家庭子女的歧視。當然,也許有,但我們學生沒有意識到。就連一些幹部子弟,也被動員回家。有些學校重複抽籤,每次都減少一半人數。
我的號碼剛好是偶數,但也不容慶幸。一九五七年,我們村小學畢業班的三十五名同學,共有七人考上中學。到一九五九年秋,除三人之外,其他人都回了村莊。一位轉到承德附近某所中專;另一位參軍入伍,最後成為軍官;我是第三個。一九五九年,隨著學校大幅削減規模,母親擔心我的學業和未來希望都會落空,前景似乎一片黯淡。
父親曾多次勸說我,去呼和浩特跟他住,在那裡上學。一九五六年,他又娶了比他小十二歲的第三任妻子。一九五九年初,他曾寫信給我,把貧困的饒陽農業縣與呼和浩特快速工業化的自治區首府做對比,他所描述的美好生活,在饑荒來臨的時刻,變得難以抗拒。
母親說:「我實在不想讓你去跟繼母住,但教育是咱們唯一的希望。」在她說服下,我最終同意,轉學去呼和浩特五中,靠近父親開卡車的呼和浩特運輸公司。依照規定程序,五中需要我的中學轉學證。我多次去公社和饒陽縣城,辦理轉學證和另外兩份重要證件:「戶口遷移證」和「糧油供應轉移證」(簡稱「轉糧證」)。前者將我的合法居住地從河北農村遷到了呼和浩特市;後者則保證,作為國家職工的家屬,我可以獲得政府的口糧供應。中國從一九五八年起,就試圖控制農民進城的機會,但大躍進的瘋狂,壓倒了管控流民的嘗試。從一九五八到一九五九年初,數以千萬計的農民工,在全國新興工業城市,以及受災較輕的農村地區,找到了新工作。一九五九年,是農村人口獲准進城的最後一次機會。到第二年(一九六○年),隨著經濟全面崩潰,大批內地的自發移民,在省際邊界上,即遭收容,並被遣返。
出發那天,母親送我出村,我們朝村北的河岸方向走。我背著一個小包,天一亮悄悄出發,趕在瑞軍醒來之前,因為我擔心他會大哭。母親跟我走在蜿蜒的小路上,叮囑我要好好學習,不要跟繼母衝突。她的話語,多次被肺氣腫引發的咳嗽打斷,肺氣腫是饑荒時期常見的多發病之一。我強忍淚水,懇求她回家。當她瘦弱的身影被晨霧遮擋,咳嗽聲逐漸消失在樹林後面時,我終於忍耐不住,放聲痛哭起來。
這是我第一次獨自離家遠行。告別母親弟弟,去與父親和從未謀面的繼母生活,其前景如何,讓我心情沉重。但我畢竟已經十六歲,期待繼續學習,也準備經風雨見世面。
第一章 華北農家子,隻身赴塞外
一九五八年,對全中國來說,都是一個轉折點,我自己也不例外。那年我十五歲,是河北省饒陽中學國二的住校生。
一九五八年夏天,學校沒放暑假,在物理老師周福田指導下,我們在校園建了三個小工廠:生產焦炭、鋼鐵和水泥。這是我們對席捲全國的「大躍進」所做的貢獻。黨國號召,農村也要生產作為工業標誌的鋼鐵和水泥,以實現所有人快速富裕的承諾。
一九五八年,也是饒陽乃至全國大部分地區夏秋作物將要大豐收的一年,但六月時出現嚴重的勞力短缺。幾乎所有體格健壯的饒陽男性,都被動員到承德縣正在建造的鋼鐵廠和其他工廠。承德是清朝皇帝的避暑勝地和夏都,位於北京東北二百多公里的長城以北。
到了八月,衡水地委發布一項令人震驚的通知:科學研究證明,紅薯(地瓜)產量遠高於玉米,所以,要改種紅薯。當時,玉米已經三尺來高,卻被下令砍倒,改插紅薯秧。以前,黨從未如此直接干預和侵犯農民的智慧。大家都知道,紅薯要在六月種植,才能成熟。村民無視上級命令時,幹部和民兵就直接介入,拉著兩公尺長的繩索,穿過田壟,毀掉玉米。村民的辛苦勞動付之東流,自然,改種紅薯的計畫胎死腹中。
大躍進也承諾大幅擴展全民教育,一九五八年一年內,饒陽縣的中學數量,就從一所增加到六所(每個大公社一所)。一九五八年冬至一九五九年春,我跟三十個男生,搬進縣中一排破舊的紅磚宿舍,十人擠住一個房間,五人合睡一張木板大通鋪。
但隨著工業下馬和飢餓加劇,學校人數大幅削減,部分學校開始關閉。一九五九年六月,校長命令學生站成兩排,大家開始報數:一、二,一、二……偶數學生繼續學業,奇數學生當場解散,被動員回家。當時沒有偏袒或特權,甚至沒有顯示出對地主家庭子女的歧視。當然,也許有,但我們學生沒有意識到。就連一些幹部子弟,也被動員回家。有些學校重複抽籤,每次都減少一半人數。
我的號碼剛好是偶數,但也不容慶幸。一九五七年,我們村小學畢業班的三十五名同學,共有七人考上中學。到一九五九年秋,除三人之外,其他人都回了村莊。一位轉到承德附近某所中專;另一位參軍入伍,最後成為軍官;我是第三個。一九五九年,隨著學校大幅削減規模,母親擔心我的學業和未來希望都會落空,前景似乎一片黯淡。
父親曾多次勸說我,去呼和浩特跟他住,在那裡上學。一九五六年,他又娶了比他小十二歲的第三任妻子。一九五九年初,他曾寫信給我,把貧困的饒陽農業縣與呼和浩特快速工業化的自治區首府做對比,他所描述的美好生活,在饑荒來臨的時刻,變得難以抗拒。
母親說:「我實在不想讓你去跟繼母住,但教育是咱們唯一的希望。」在她說服下,我最終同意,轉學去呼和浩特五中,靠近父親開卡車的呼和浩特運輸公司。依照規定程序,五中需要我的中學轉學證。我多次去公社和饒陽縣城,辦理轉學證和另外兩份重要證件:「戶口遷移證」和「糧油供應轉移證」(簡稱「轉糧證」)。前者將我的合法居住地從河北農村遷到了呼和浩特市;後者則保證,作為國家職工的家屬,我可以獲得政府的口糧供應。中國從一九五八年起,就試圖控制農民進城的機會,但大躍進的瘋狂,壓倒了管控流民的嘗試。從一九五八到一九五九年初,數以千萬計的農民工,在全國新興工業城市,以及受災較輕的農村地區,找到了新工作。一九五九年,是農村人口獲准進城的最後一次機會。到第二年(一九六○年),隨著經濟全面崩潰,大批內地的自發移民,在省際邊界上,即遭收容,並被遣返。
出發那天,母親送我出村,我們朝村北的河岸方向走。我背著一個小包,天一亮悄悄出發,趕在瑞軍醒來之前,因為我擔心他會大哭。母親跟我走在蜿蜒的小路上,叮囑我要好好學習,不要跟繼母衝突。她的話語,多次被肺氣腫引發的咳嗽打斷,肺氣腫是饑荒時期常見的多發病之一。我強忍淚水,懇求她回家。當她瘦弱的身影被晨霧遮擋,咳嗽聲逐漸消失在樹林後面時,我終於忍耐不住,放聲痛哭起來。
這是我第一次獨自離家遠行。告別母親弟弟,去與父親和從未謀面的繼母生活,其前景如何,讓我心情沉重。但我畢竟已經十六歲,期待繼續學習,也準備經風雨見世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