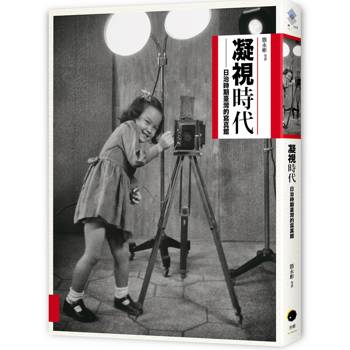第二章 十九世紀臺灣攝影的先行者(節錄)
一八六六,柯林伍德、沙頓與巨蛇號的臺灣踏查
繼郇和之後,英國的博物學家柯林伍德(Cuthbert Collingwood, 1826-1908)也在一八六六年來到了臺灣。他在一八六六、六七年航行中國、臺灣、婆羅洲、菲律賓、與新加坡等地,進行兩年的博物學調查。這段遊歷讓他寫下名作《一位博物學家在中國海域及其沿岸的漫遊》(Rambles of a Naturalist on the Shores and Waters of the China Sea)。當時他搭乘英國皇家船艦「巨蛇號」(H. M. S. Serpent),艦上的輪機長沙頓(Sutton)正是一個攝影師,柯林伍德在書中曾多次描述他們的攝影事蹟。
一八六六年五月,他們先抵達南部的打狗,然後沿著海岸向西北航行,經過馬公、臺南,最後抵達淡水。攝影的記載最早出現在馬公之行,柯林伍德寫道:「我們在馬公停留三天後準備離開,輪機長沙頓先生,一位技術極佳的攝影師,在我們啟行的早晨到城鎮上拍攝了一些景觀。這種情況下要人們避開攝影裝備實在非常困難,他們非常好奇,這使得拍照進行極為不順。一名男子趁我們忙著沖洗底片而疏於注意時,竟然偷偷喝了瓶內的冰醋酸溶液(glacial acetic acid),還好它不具有毒性。另一名男子比他的鄰居更勇敢地接受硝酸銀溶液的挑戰,在他的髭毛、鬍鬚、眼睛等周圍塗上該溶液。可以想見,當我們離開後,它們便會在陽光照射下開始變黑,直到溶液發揮顯影的效果,這時我們這位冒失的朋友肯定會大吃一驚,但非常遺憾,我們雖然可以想像他的難堪,卻沒機會看到他遭無情鄰居白眼的畫面……。」
關於這些民智未開的村民所做的蠢事,柯林伍德的描述雖有點尖酸刻薄,卻令人感到不可思議。文章除了提到拍攝現場沖洗底片一事,對於沙頓所使用的感光乳劑,柯林伍德也明確指出是對紫外線感光的硝酸銀溶液。離開澎湖之後,「巨蛇號」行經臺南、淡水,最後停泊在基隆港。柯林伍德與輪機長沙頓在淡水停留了數日,為了與已經將開往基隆港的布洛克司令(Commander Bullock)會合,五月二十五日他們雇用三名漢人船夫,搭乘舢板從淡水出發,上溯基隆河展開一段內陸的探險活動。這段經歷後來寫成〈橫越福爾摩沙北部的航行〉(A boat journey across the northern end of Formosa),這篇文章後來刊登在一八六七年第十一期的《皇家地理學會》(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一八五一年,英人史考特.亞契(Frederick Scott Archer, 1813-1857)發明了「卡羅酊攝影術」(Wet Collodien Process,簡稱「濕版」),不但影像的階調優於銀版,感度也大為提高,曝光時間從數十分鐘縮短為五至十五秒鐘。但它在操作上極為不便,必須在拍照當下現塗感光乳劑於玻璃版上,並趁乳劑未乾燥硬化前即時顯影,因此外拍時需配備「可攜帶式暗房」。一八七一年,馬德斯(Richard Leach Maddox, 1816-1902)發明了「乾版」(Dry Plate),在一八七七年開始量產,這時攝影才真正具有快速和便捷性,適合戶外、遠距離、瞬間動態的攝影活動。
一八六六年,沙頓的攝影技術還停留在「濕版」的階段,報導日記寫著他們出發當天「攜帶二天的食物、照相機和各式的器材……」。所謂「各式器材」除了整套的攝影裝備,當然還包括戶外用的暗房,顯然早已做好周詳的計畫,準備以攝影作為記錄的工具。第一天舢板行經關渡、八芝蘭(士林),抵達圓山后,受邀上岸拜訪一戶富貴人家,當晚即回到舢板船中過夜。第二天一大早他們便展開攝影活動,這次柯林伍德記錄他們「拍攝了幾處山的風景,捕捉到一些美麗的蝴蝶和甲蟲……」。如前所述,「濕版」攝影的曝光時間長達五至十五秒鐘,相機必須架在笨重的三腳架上,拍攝蝴蝶飛舞的即景畫面是不可能的事,這裡所謂的「捕捉」當然是指昆蟲實體的捕捉而非瞬間攝影。
一八六六年六月十三日,柯林伍德為了繪製更可靠的東北部港口海圖,繼續搭乘「巨蛇號」前往蘇澳。這段航程記載於一八六八年第六期《倫敦人類學協會會刊》(Transactions of the Ethn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的〈福爾摩沙東北海岸蘇澳灣之行〉(Visit to the Kibalan village of Sano Bay)一文中。原文中的「Sano Bay」應為蘇澳灣「Sau-o Bay」之誤。這篇文章記載柯林伍德再次折服於沙頓的攝影技術,對當時的拍攝有非常生動的描寫:「輪機長沙頓先生是一位非常有經驗的攝影師,他在岸上用照相機拍攝這個村莊和居民,並成功取得幾張極好的立體照片(stereoscopic pictures)。當要求他們就定位時,居民很容易就接受了,並且形成幾個完美構圖的群體,少部分照片很成功地被定影下來,當然要讓所有的人保持不動就很困難了,因為我們不可能使他們理解,在關鍵時刻必須絕對的靜止。無論如何,幾個拍攝實例的結果還算令人滿意……。」
使用「濕版」拍攝會動的物件本來就很困難,更何況是一群人的團體照。加上受限於語言溝通的困難,我們很難想像沙頓是如何克服障礙,才能順利完成拍攝工作,也難怪陪伴在旁的柯林伍德一直不斷讚嘆:「他真是一位技術精湛的攝影師!」而且,沙頓在蘇澳拍的竟然是「立體照片」,歐洲在「銀版攝影術」問世時流行立體照片。當時許多攝影師遠赴美洲、希臘、埃及等地,拍攝史蹟、異國風情等照片然後販賣,非常受歐洲人歡迎。
早期來臺的外國攝影師中,沙頓是文獻記載中第一位使用立體相機的人。
一八六○年代之後外國傳教士的身影與足跡
荷蘭人撤離臺灣後的兩百年間,我們很難找到西方教會在臺灣傳道的足跡,直到鴉片戰爭爆發後,在國際條約的保障之下,長老教會才又重新於海外設置傳道會所,在中國展開宣教活動,先後在福建、臺灣、廣東甚至東南亞設立據點。一八六○年代,基督教長老會再度傳入臺灣,當時有英國長老教會馬雅各醫生(James Laidlaw Maxwell, 1836-1921)等人在南部佈道,北部則有加拿大長老教會的馬偕牧師(George Leslie Mackay, 1844-1901)。他們的宣教活動配合著醫療服務與教育同時進行,分別在南北都建有近代化的醫院和學校,不但使長老教會成為基督教在臺灣的主流教派,從文化傳播的觀點來看,他們也為臺灣帶來新知識、新醫療和新教育體系,對民智的啟發與社會變革帶來不可磨滅的影響,間接也促進了臺灣的近代化。
早期到海外宣教的傳教士可能都會使用攝影這項技術,這可從《英國長老教會中國宣教記錄》(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 foreign mission archives, 1847-1950)所刊載宣教地區分類報告書中的圖片得到印證。報告書中對當地政治、經濟、社會情事分析,或世界各地教區之間刊行的《教會公報》(The Monthly Messenger),都會搭配宣教、醫療活動、各地民情風俗等木刻版印刷圖片。
事實上,在目前發現的臺灣攝影史料中,以長老會宣教師馬偕博士來臺初期所留下的攝影資料最為可觀,居所有來臺宣教士之冠。在臺灣宣教、醫療、社會及教育上有深遠影響的馬偕博士,其一生的黃金歲月都奉獻給臺灣這塊土地。二○○一年,臺灣基督長老教會舉辦「馬偕博士逝世一百週年紀念活動」,在臺灣歷史博物館展示這批影像的原版照片,這也是最為國人熟悉的一批早期影像。多數照片顯示馬偕本人都在畫面中,顯然攝影者另有其人,但攝影者不詳。
第三章 日治時期的臺灣攝影(節錄)
一八九四年,中日爆發甲午戰爭,清廷戰敗,隔年簽訂《馬關條約》,割讓臺灣,從此開始五十年日本統治臺灣的時期。領臺之初,掃蕩抗日義勇軍和制定理蕃政策成為當務之急。從統治初期到「始政」(開始治理政治)的三十年間,基本上日本對臺灣採取懷柔開放的態度,尤其是日本在大正年間(一九一二-一九二六)因接受近代文明的洗禮而突飛猛進,臺灣也蒙受其惠。
從政經社會層面來看,「攝影術」在日治時期對臺灣攝影的影響,具有多方潛移默化的作用,特別是攝影藝術的演進。其中,商業寫真館在臺灣攝影的發展中扮演領頭羊的角色,透過鏡像的語彙(如燈光技巧、服飾、布景、拍攝風格等)開啟民風,也間接促成業餘攝影的濫觴。在研究者和相關文獻相當貧乏的情況下,筆者試著以田野調查所得有限的原作與史料,探索日治時期臺灣攝影的發展。
日治時期寫真帖
顧名思義,「寫真帖」是以「寫真」(照片)製作的「帖」(相簿或相冊),泛指官方以實體寫真或印刷模式所製成的相簿,一般私人會社、家族和個人貼製的相簿,也被認定為「寫真帖」的概念。在西方攝影的進程中,攝影術被應用於册集書頁,而使用「Album」一詞的定義,一部分吻合日治時期對於「寫真帖」的廣泛定義。
寫真帖的應用繁多,一個單位的出遊記錄也可以用寫真,委請攝影業者少量製作,留存紀念。而日治時期寫真帖的出版,大都由總督府所屬機關印製或監製,只有少數與總督府關係良好的日本人(當時稱為內地人)所開設的寫真館,才能接受委託攝製或印刷,很少臺灣人(當時稱為本島人)有機會接受委託拍攝製作官方寫真帖。
在日治時期,官方和法人團體(組合)所印製的內容非常廣泛,從軍事政治、人文活動到天然景物,都是鏡頭捕捉的焦點,而拍攝目的有學術研究、活動宣傳、人物紀念、戰事記錄、風景記錄、建設成果等彰顯臺灣總督府的豐功偉業及對天皇的崇敬。
真帖與寫真館
一九○○年,總督府開放民間的印刷事業,從此臺灣攝影便如雨後春筍般地成長茁壯。這些有別於官方監製、以庶民觀點和自主承印的寫真帖,為臺灣人開啟了一扇大門,並看到自身所蘊涵的力量。
臺灣圖書館收藏了不少「遠藤寫真館」所發行監製的寫真帖,如《征臺凱旋紀念帖》、《臺灣蕃地寫真帖》、《蕃匪討伐紀念寫真帖》等。此外,由勝山吉作主持的合資會社「勝山寫真館」,不僅接受晝夜攝影的工作,也兼營十六釐米活動寫真、出版監製「繪葉書」(包含圖像的明信片)等業務。而臺灣人所開設的寫真館,大都以拍攝臺灣家庭照或個人肖像,及外寫出張(外拍)等臺灣人委託的業務為主,很難與日本人競爭。
但也有少數例子,足以說明寫真帖和印刷術如何在民間應用,如小醫院、個人、家庭、小商號、酒家等。在大正年間,臺灣人與日本人一樣享有憲法的保障,是日治時期最安定、富足的時期,從《臺灣始政四十週年博覽會女給篇──花國艶影集》寫真帖便可看出端倪。這本由花國艶影集出版社發行的寫真帖,是黃書樵在醉香樓所編輯的女給影集,除了刊載咖啡店女給和酒室美女之外,也邀請詩人為影集吟詠詩詞,後面還有咖啡(カフエ一)名店、舞廳(ダンスホ一ル)等廣告,在當時頗為時尚。
在眾多日本人監製的寫真帖中,一九三一年(昭和六年)由「ハセシ(林)寫真館」(林得富主持)拍攝和編輯、「臺北共進商會」發行的《霧社事件討伐寫真帖》,最後一頁刊載了編集群合照,最左側站立者為林得富。(作者按:攝影評論者張蒼松在編輯林草紀念集《百年足跡重現》時,曾以為這間「ハセシ(林)寫真館」由林草主持,查明後才知「林寫真館」與「ハセシ(林)寫真館」意思相同但招牌字體不同。)
一九四三年(昭和十八年)十一月,頭份「美影寫真館」的張阿祥(一九一六-二○一三)與關西「真影寫真館」(戰後改名為「珊瑚照相館」)的林礽湖,共同為日本「櫻井組望鄉山制材所」拍攝《拾週年紀念寫真帖》,記錄當時櫻井組開採阿里山山林及製材工業的實況,也是極少數臺灣人接受官方委託的例子。對此,張阿祥曾回憶:「坐流籠很危險,一般都用來搬運大支木頭,人是不允許坐上去的,難怪日本寫真師不敢上去!」
一八六六,柯林伍德、沙頓與巨蛇號的臺灣踏查
繼郇和之後,英國的博物學家柯林伍德(Cuthbert Collingwood, 1826-1908)也在一八六六年來到了臺灣。他在一八六六、六七年航行中國、臺灣、婆羅洲、菲律賓、與新加坡等地,進行兩年的博物學調查。這段遊歷讓他寫下名作《一位博物學家在中國海域及其沿岸的漫遊》(Rambles of a Naturalist on the Shores and Waters of the China Sea)。當時他搭乘英國皇家船艦「巨蛇號」(H. M. S. Serpent),艦上的輪機長沙頓(Sutton)正是一個攝影師,柯林伍德在書中曾多次描述他們的攝影事蹟。
一八六六年五月,他們先抵達南部的打狗,然後沿著海岸向西北航行,經過馬公、臺南,最後抵達淡水。攝影的記載最早出現在馬公之行,柯林伍德寫道:「我們在馬公停留三天後準備離開,輪機長沙頓先生,一位技術極佳的攝影師,在我們啟行的早晨到城鎮上拍攝了一些景觀。這種情況下要人們避開攝影裝備實在非常困難,他們非常好奇,這使得拍照進行極為不順。一名男子趁我們忙著沖洗底片而疏於注意時,竟然偷偷喝了瓶內的冰醋酸溶液(glacial acetic acid),還好它不具有毒性。另一名男子比他的鄰居更勇敢地接受硝酸銀溶液的挑戰,在他的髭毛、鬍鬚、眼睛等周圍塗上該溶液。可以想見,當我們離開後,它們便會在陽光照射下開始變黑,直到溶液發揮顯影的效果,這時我們這位冒失的朋友肯定會大吃一驚,但非常遺憾,我們雖然可以想像他的難堪,卻沒機會看到他遭無情鄰居白眼的畫面……。」
關於這些民智未開的村民所做的蠢事,柯林伍德的描述雖有點尖酸刻薄,卻令人感到不可思議。文章除了提到拍攝現場沖洗底片一事,對於沙頓所使用的感光乳劑,柯林伍德也明確指出是對紫外線感光的硝酸銀溶液。離開澎湖之後,「巨蛇號」行經臺南、淡水,最後停泊在基隆港。柯林伍德與輪機長沙頓在淡水停留了數日,為了與已經將開往基隆港的布洛克司令(Commander Bullock)會合,五月二十五日他們雇用三名漢人船夫,搭乘舢板從淡水出發,上溯基隆河展開一段內陸的探險活動。這段經歷後來寫成〈橫越福爾摩沙北部的航行〉(A boat journey across the northern end of Formosa),這篇文章後來刊登在一八六七年第十一期的《皇家地理學會》(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一八五一年,英人史考特.亞契(Frederick Scott Archer, 1813-1857)發明了「卡羅酊攝影術」(Wet Collodien Process,簡稱「濕版」),不但影像的階調優於銀版,感度也大為提高,曝光時間從數十分鐘縮短為五至十五秒鐘。但它在操作上極為不便,必須在拍照當下現塗感光乳劑於玻璃版上,並趁乳劑未乾燥硬化前即時顯影,因此外拍時需配備「可攜帶式暗房」。一八七一年,馬德斯(Richard Leach Maddox, 1816-1902)發明了「乾版」(Dry Plate),在一八七七年開始量產,這時攝影才真正具有快速和便捷性,適合戶外、遠距離、瞬間動態的攝影活動。
一八六六年,沙頓的攝影技術還停留在「濕版」的階段,報導日記寫著他們出發當天「攜帶二天的食物、照相機和各式的器材……」。所謂「各式器材」除了整套的攝影裝備,當然還包括戶外用的暗房,顯然早已做好周詳的計畫,準備以攝影作為記錄的工具。第一天舢板行經關渡、八芝蘭(士林),抵達圓山后,受邀上岸拜訪一戶富貴人家,當晚即回到舢板船中過夜。第二天一大早他們便展開攝影活動,這次柯林伍德記錄他們「拍攝了幾處山的風景,捕捉到一些美麗的蝴蝶和甲蟲……」。如前所述,「濕版」攝影的曝光時間長達五至十五秒鐘,相機必須架在笨重的三腳架上,拍攝蝴蝶飛舞的即景畫面是不可能的事,這裡所謂的「捕捉」當然是指昆蟲實體的捕捉而非瞬間攝影。
一八六六年六月十三日,柯林伍德為了繪製更可靠的東北部港口海圖,繼續搭乘「巨蛇號」前往蘇澳。這段航程記載於一八六八年第六期《倫敦人類學協會會刊》(Transactions of the Ethn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的〈福爾摩沙東北海岸蘇澳灣之行〉(Visit to the Kibalan village of Sano Bay)一文中。原文中的「Sano Bay」應為蘇澳灣「Sau-o Bay」之誤。這篇文章記載柯林伍德再次折服於沙頓的攝影技術,對當時的拍攝有非常生動的描寫:「輪機長沙頓先生是一位非常有經驗的攝影師,他在岸上用照相機拍攝這個村莊和居民,並成功取得幾張極好的立體照片(stereoscopic pictures)。當要求他們就定位時,居民很容易就接受了,並且形成幾個完美構圖的群體,少部分照片很成功地被定影下來,當然要讓所有的人保持不動就很困難了,因為我們不可能使他們理解,在關鍵時刻必須絕對的靜止。無論如何,幾個拍攝實例的結果還算令人滿意……。」
使用「濕版」拍攝會動的物件本來就很困難,更何況是一群人的團體照。加上受限於語言溝通的困難,我們很難想像沙頓是如何克服障礙,才能順利完成拍攝工作,也難怪陪伴在旁的柯林伍德一直不斷讚嘆:「他真是一位技術精湛的攝影師!」而且,沙頓在蘇澳拍的竟然是「立體照片」,歐洲在「銀版攝影術」問世時流行立體照片。當時許多攝影師遠赴美洲、希臘、埃及等地,拍攝史蹟、異國風情等照片然後販賣,非常受歐洲人歡迎。
早期來臺的外國攝影師中,沙頓是文獻記載中第一位使用立體相機的人。
一八六○年代之後外國傳教士的身影與足跡
荷蘭人撤離臺灣後的兩百年間,我們很難找到西方教會在臺灣傳道的足跡,直到鴉片戰爭爆發後,在國際條約的保障之下,長老教會才又重新於海外設置傳道會所,在中國展開宣教活動,先後在福建、臺灣、廣東甚至東南亞設立據點。一八六○年代,基督教長老會再度傳入臺灣,當時有英國長老教會馬雅各醫生(James Laidlaw Maxwell, 1836-1921)等人在南部佈道,北部則有加拿大長老教會的馬偕牧師(George Leslie Mackay, 1844-1901)。他們的宣教活動配合著醫療服務與教育同時進行,分別在南北都建有近代化的醫院和學校,不但使長老教會成為基督教在臺灣的主流教派,從文化傳播的觀點來看,他們也為臺灣帶來新知識、新醫療和新教育體系,對民智的啟發與社會變革帶來不可磨滅的影響,間接也促進了臺灣的近代化。
早期到海外宣教的傳教士可能都會使用攝影這項技術,這可從《英國長老教會中國宣教記錄》(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 foreign mission archives, 1847-1950)所刊載宣教地區分類報告書中的圖片得到印證。報告書中對當地政治、經濟、社會情事分析,或世界各地教區之間刊行的《教會公報》(The Monthly Messenger),都會搭配宣教、醫療活動、各地民情風俗等木刻版印刷圖片。
事實上,在目前發現的臺灣攝影史料中,以長老會宣教師馬偕博士來臺初期所留下的攝影資料最為可觀,居所有來臺宣教士之冠。在臺灣宣教、醫療、社會及教育上有深遠影響的馬偕博士,其一生的黃金歲月都奉獻給臺灣這塊土地。二○○一年,臺灣基督長老教會舉辦「馬偕博士逝世一百週年紀念活動」,在臺灣歷史博物館展示這批影像的原版照片,這也是最為國人熟悉的一批早期影像。多數照片顯示馬偕本人都在畫面中,顯然攝影者另有其人,但攝影者不詳。
第三章 日治時期的臺灣攝影(節錄)
一八九四年,中日爆發甲午戰爭,清廷戰敗,隔年簽訂《馬關條約》,割讓臺灣,從此開始五十年日本統治臺灣的時期。領臺之初,掃蕩抗日義勇軍和制定理蕃政策成為當務之急。從統治初期到「始政」(開始治理政治)的三十年間,基本上日本對臺灣採取懷柔開放的態度,尤其是日本在大正年間(一九一二-一九二六)因接受近代文明的洗禮而突飛猛進,臺灣也蒙受其惠。
從政經社會層面來看,「攝影術」在日治時期對臺灣攝影的影響,具有多方潛移默化的作用,特別是攝影藝術的演進。其中,商業寫真館在臺灣攝影的發展中扮演領頭羊的角色,透過鏡像的語彙(如燈光技巧、服飾、布景、拍攝風格等)開啟民風,也間接促成業餘攝影的濫觴。在研究者和相關文獻相當貧乏的情況下,筆者試著以田野調查所得有限的原作與史料,探索日治時期臺灣攝影的發展。
日治時期寫真帖
顧名思義,「寫真帖」是以「寫真」(照片)製作的「帖」(相簿或相冊),泛指官方以實體寫真或印刷模式所製成的相簿,一般私人會社、家族和個人貼製的相簿,也被認定為「寫真帖」的概念。在西方攝影的進程中,攝影術被應用於册集書頁,而使用「Album」一詞的定義,一部分吻合日治時期對於「寫真帖」的廣泛定義。
寫真帖的應用繁多,一個單位的出遊記錄也可以用寫真,委請攝影業者少量製作,留存紀念。而日治時期寫真帖的出版,大都由總督府所屬機關印製或監製,只有少數與總督府關係良好的日本人(當時稱為內地人)所開設的寫真館,才能接受委託攝製或印刷,很少臺灣人(當時稱為本島人)有機會接受委託拍攝製作官方寫真帖。
在日治時期,官方和法人團體(組合)所印製的內容非常廣泛,從軍事政治、人文活動到天然景物,都是鏡頭捕捉的焦點,而拍攝目的有學術研究、活動宣傳、人物紀念、戰事記錄、風景記錄、建設成果等彰顯臺灣總督府的豐功偉業及對天皇的崇敬。
真帖與寫真館
一九○○年,總督府開放民間的印刷事業,從此臺灣攝影便如雨後春筍般地成長茁壯。這些有別於官方監製、以庶民觀點和自主承印的寫真帖,為臺灣人開啟了一扇大門,並看到自身所蘊涵的力量。
臺灣圖書館收藏了不少「遠藤寫真館」所發行監製的寫真帖,如《征臺凱旋紀念帖》、《臺灣蕃地寫真帖》、《蕃匪討伐紀念寫真帖》等。此外,由勝山吉作主持的合資會社「勝山寫真館」,不僅接受晝夜攝影的工作,也兼營十六釐米活動寫真、出版監製「繪葉書」(包含圖像的明信片)等業務。而臺灣人所開設的寫真館,大都以拍攝臺灣家庭照或個人肖像,及外寫出張(外拍)等臺灣人委託的業務為主,很難與日本人競爭。
但也有少數例子,足以說明寫真帖和印刷術如何在民間應用,如小醫院、個人、家庭、小商號、酒家等。在大正年間,臺灣人與日本人一樣享有憲法的保障,是日治時期最安定、富足的時期,從《臺灣始政四十週年博覽會女給篇──花國艶影集》寫真帖便可看出端倪。這本由花國艶影集出版社發行的寫真帖,是黃書樵在醉香樓所編輯的女給影集,除了刊載咖啡店女給和酒室美女之外,也邀請詩人為影集吟詠詩詞,後面還有咖啡(カフエ一)名店、舞廳(ダンスホ一ル)等廣告,在當時頗為時尚。
在眾多日本人監製的寫真帖中,一九三一年(昭和六年)由「ハセシ(林)寫真館」(林得富主持)拍攝和編輯、「臺北共進商會」發行的《霧社事件討伐寫真帖》,最後一頁刊載了編集群合照,最左側站立者為林得富。(作者按:攝影評論者張蒼松在編輯林草紀念集《百年足跡重現》時,曾以為這間「ハセシ(林)寫真館」由林草主持,查明後才知「林寫真館」與「ハセシ(林)寫真館」意思相同但招牌字體不同。)
一九四三年(昭和十八年)十一月,頭份「美影寫真館」的張阿祥(一九一六-二○一三)與關西「真影寫真館」(戰後改名為「珊瑚照相館」)的林礽湖,共同為日本「櫻井組望鄉山制材所」拍攝《拾週年紀念寫真帖》,記錄當時櫻井組開採阿里山山林及製材工業的實況,也是極少數臺灣人接受官方委託的例子。對此,張阿祥曾回憶:「坐流籠很危險,一般都用來搬運大支木頭,人是不允許坐上去的,難怪日本寫真師不敢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