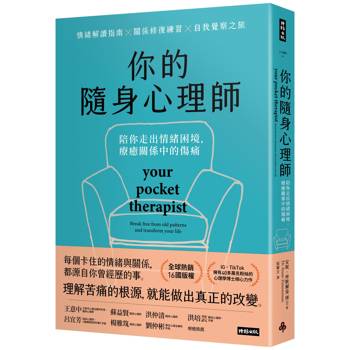童年的傷,用一生治癒
多數人只想過得快樂,艾爾娃(Alva)尤其如此。她一生都在追求快樂,但就是無法如願,她也說不出是為什麼。
她的人生還算順遂,但她每天都過得渾渾噩噩。成天手機滑不停,無時無刻都在玩遊戲。參加家庭聚會時,總在放空發呆,腦中不斷想著自己人生很失敗,做任何事都徒勞無功,一切都毫無意義。有時她會感到快樂,像是與朋友一起跳舞、看好笑的影片或嚕貓,但總終還是會重陷混沌度日的泥淖。
她每天醒來都四肢沉重。還沒睜開眼睛,就在摸找手機,準備再度展開空虛的一天。她用大拇指點開遊戲應用程式,這個動作就像呼吸一樣自然,成了一種反射動作。她看了看時鐘,一小時過了,不但上班遲到,還錯過了她前一天在滿懷希望的妄想中對自己保證一定會去上的健身課。
艾爾娃沮喪地嘆了口氣,將手機扔到房間的另一頭。她心想:夠了!自己必須做出改變,今天就是解決這個問題的日子--她將竭盡所能讓自己感到快樂。
她下了重本投資「快樂產業」。她買了一個新衣櫥,希望能讓自己感到幸福,但根本毫無幫助。她刪掉了手機遊戲,並設定使用其他應用程式的時間限制。頭幾天還算有效,但她後來又故態復萌。她也實行一套新的養生之道,嘗試吃健康的食物與養成慢跑習慣,這讓她有種贏過別人的優越感,但並未真正使她感到快樂。她辭去了朝九晚五的工作,到外地旅遊,在印度、墨西哥與峇里島度假一年。她還開始做瑜珈,身心比以前健康了一點,但悲傷的感覺依舊如影隨形。
也許,她需要尋找更多意義與目的。她轉換跑道,接受教師培訓,期盼與孩子相處的這份工作能帶來滿足感。結果也的確如此,但她仍隱約感受到深沉的悲傷。也許,她需要一段感情,需要有人愛她與支持她。她遇見了賈馬爾(Jamal),一個幽默、性感、野心勃勃又體貼入微的完美男人。她過了好幾個月的幸福生活,每天都心神蕩漾、充滿期待,感覺世界變得美妙。她與賈馬爾在一起時甚至忘了手機的存在。也許這就是她在尋找的快樂,也許她心中那股與生活脫節的莫名感受終於消失了。
之後,熱戀期過了,催產素--所謂「愛的荷爾蒙」--漸漸消退,她內心再度湧現不可名狀的恐懼。她又像從前那樣工作時心不在焉,與朋友相約總提不起勁,經常強顏歡笑,但內心其實感覺糟透了。她又開始玩手機遊戲,搭公車、早上醒來及晚上睡前都在玩,就連跟賈馬爾約會時也是,兩人因此變得疏離且感到孤獨。世界再度變成黑白,而艾爾娃找不到原因。
她為什麼就是無法感到快樂呢?她有努力試著改變啊!
關鍵在於,艾爾娃根本沒有釐清問題的重點。她付出的所有努力都只觸及冰山露在水面上的一角。這裡我要特別說明的是,你的工作、人際關係與生活方式都會對你的心理健康產生重大影響,但它們與你--以及艾爾娃--痛苦掙扎的原因並無太大關聯。
艾爾娃迫切希望生活能有所改變,因此來找我。第一次治療時,我立刻察覺到她非常害怕坦誠以對,也很焦慮。雖然臉上帶著微笑,但似乎並不快樂。她看來心不在焉、與人有疏離感,每句話說到最後都吞吞吐吐,好像不習慣談論自己。她讓我想起自己剛開始接受治療的模樣:一直發呆、感覺害怕,整個人魂不附體。
「我該怎麼辦?」她問,「告訴我該怎麼做。」
人們前來尋求心理治療是為了得到答案,但一開始我往往會丟出更多問題給他們(是的,心理師就是這麼煩人;你看到後面就知道了)。我沒有這些問題的答案。我也希望自己握有人們追求的萬靈丹(倘若如此,我的工作會輕鬆得多),但遺憾的是,這種東西並不存在。所有的答案都在艾爾娃心中,只是此刻她還沒意識到這一點,還沒看到水面下的冰山。而我的工作是,幫助她獲得足夠的安全感去探索答案。
於是,我跟她一起展開這個挖掘的過程。
我做的第一件事是詢問她的童年經歷--這很老套,我知道。
為何心理諮商總在討論童年?
腦部的發展絕大部分發生在出生到三歲這段期間,並在五歲時趨於成熟。這意味著,我們在這段期間經歷的一切,對未來的成長影響深遠。就拿語言學習為例,人在嬰兒時期輕易就能學會新的語言,並在往後的人生中保持一定的流利程度。等過了十二歲,多數人在學習新語言時就會覺得相當吃力。
當我們學習開口說話時,也是在學習情緒的語言。我們對自我、人際關係與世界的認識,大部分都來自童年時期。
不幸的是,人類進化的目的是維持生存,而非尋求幸福。大腦不在乎你對社群媒體上癮而變得如同行屍走肉,也不在乎你因為生活缺乏動力而工作表現差勁。大腦只想保護你不受它認為具有潛在危險性的事物所傷害。
那麼,我們是從何時開始得知什麼樣的事物會危害我們的生存呢?答案是童年時期。
長大成人的你能夠讓自己吃得飽、照顧好自己,但當你還是小孩的時候肯定做不到。相較於其他物種,人類更是如此,因為我們在嬰兒時期脆弱無助。從出生到兩歲的這段期間,我們得完全依靠大人的照顧才能存活,需要有人餵食、扶持與防止我們摔落地上。
寶寶要生存,需要與父母保持連結,需要得到關愛。
因此,寶寶對於會增進或削弱親子關係的事物極為敏感。當父親或母親不在身邊、對我們咆哮或處於神經緊繃的狀態下,我們的大腦會發出恐懼的信號。這種恐懼感告訴我們有事不對勁,還只是嬰兒的我們會使出渾身解數去試著修補問題、讓父母開心。我們需要父母維持我們的生存,因此需要他們的關愛。我們會努力表現更多惹人疼愛的行為,盡量不做會使他們生氣的事情。
即使你的父母懂得控制情緒、不會以批判角度看待你,但你仍會受周遭環境潛移默化的影響,逐漸得知什麼樣的行為才能被社會所接受:男人有淚不輕彈;女人不該有主見;身而為人應該自信而不驕傲,快樂但不自負。這些觀念存在於我們的生活中,依我們所屬的文化、種族、階級與國家而有所不同。社會給予我們無數的訊息,告訴我們應該成為什麼樣的人,應該做出什麼樣的行為舉止,應該從什麼樣的角度去思考。形塑你的不只是你的家人,還有廣大的社會、你所屬的文化、性別、種族、階級、宗教與神經特徵……等。隨著我們長大,生活在這世上得到的所有經驗,都不斷影響我們與他人及自我形成連結的方式。
多數人只想過得快樂,艾爾娃(Alva)尤其如此。她一生都在追求快樂,但就是無法如願,她也說不出是為什麼。
她的人生還算順遂,但她每天都過得渾渾噩噩。成天手機滑不停,無時無刻都在玩遊戲。參加家庭聚會時,總在放空發呆,腦中不斷想著自己人生很失敗,做任何事都徒勞無功,一切都毫無意義。有時她會感到快樂,像是與朋友一起跳舞、看好笑的影片或嚕貓,但總終還是會重陷混沌度日的泥淖。
她每天醒來都四肢沉重。還沒睜開眼睛,就在摸找手機,準備再度展開空虛的一天。她用大拇指點開遊戲應用程式,這個動作就像呼吸一樣自然,成了一種反射動作。她看了看時鐘,一小時過了,不但上班遲到,還錯過了她前一天在滿懷希望的妄想中對自己保證一定會去上的健身課。
艾爾娃沮喪地嘆了口氣,將手機扔到房間的另一頭。她心想:夠了!自己必須做出改變,今天就是解決這個問題的日子--她將竭盡所能讓自己感到快樂。
她下了重本投資「快樂產業」。她買了一個新衣櫥,希望能讓自己感到幸福,但根本毫無幫助。她刪掉了手機遊戲,並設定使用其他應用程式的時間限制。頭幾天還算有效,但她後來又故態復萌。她也實行一套新的養生之道,嘗試吃健康的食物與養成慢跑習慣,這讓她有種贏過別人的優越感,但並未真正使她感到快樂。她辭去了朝九晚五的工作,到外地旅遊,在印度、墨西哥與峇里島度假一年。她還開始做瑜珈,身心比以前健康了一點,但悲傷的感覺依舊如影隨形。
也許,她需要尋找更多意義與目的。她轉換跑道,接受教師培訓,期盼與孩子相處的這份工作能帶來滿足感。結果也的確如此,但她仍隱約感受到深沉的悲傷。也許,她需要一段感情,需要有人愛她與支持她。她遇見了賈馬爾(Jamal),一個幽默、性感、野心勃勃又體貼入微的完美男人。她過了好幾個月的幸福生活,每天都心神蕩漾、充滿期待,感覺世界變得美妙。她與賈馬爾在一起時甚至忘了手機的存在。也許這就是她在尋找的快樂,也許她心中那股與生活脫節的莫名感受終於消失了。
之後,熱戀期過了,催產素--所謂「愛的荷爾蒙」--漸漸消退,她內心再度湧現不可名狀的恐懼。她又像從前那樣工作時心不在焉,與朋友相約總提不起勁,經常強顏歡笑,但內心其實感覺糟透了。她又開始玩手機遊戲,搭公車、早上醒來及晚上睡前都在玩,就連跟賈馬爾約會時也是,兩人因此變得疏離且感到孤獨。世界再度變成黑白,而艾爾娃找不到原因。
她為什麼就是無法感到快樂呢?她有努力試著改變啊!
關鍵在於,艾爾娃根本沒有釐清問題的重點。她付出的所有努力都只觸及冰山露在水面上的一角。這裡我要特別說明的是,你的工作、人際關係與生活方式都會對你的心理健康產生重大影響,但它們與你--以及艾爾娃--痛苦掙扎的原因並無太大關聯。
艾爾娃迫切希望生活能有所改變,因此來找我。第一次治療時,我立刻察覺到她非常害怕坦誠以對,也很焦慮。雖然臉上帶著微笑,但似乎並不快樂。她看來心不在焉、與人有疏離感,每句話說到最後都吞吞吐吐,好像不習慣談論自己。她讓我想起自己剛開始接受治療的模樣:一直發呆、感覺害怕,整個人魂不附體。
「我該怎麼辦?」她問,「告訴我該怎麼做。」
人們前來尋求心理治療是為了得到答案,但一開始我往往會丟出更多問題給他們(是的,心理師就是這麼煩人;你看到後面就知道了)。我沒有這些問題的答案。我也希望自己握有人們追求的萬靈丹(倘若如此,我的工作會輕鬆得多),但遺憾的是,這種東西並不存在。所有的答案都在艾爾娃心中,只是此刻她還沒意識到這一點,還沒看到水面下的冰山。而我的工作是,幫助她獲得足夠的安全感去探索答案。
於是,我跟她一起展開這個挖掘的過程。
我做的第一件事是詢問她的童年經歷--這很老套,我知道。
為何心理諮商總在討論童年?
腦部的發展絕大部分發生在出生到三歲這段期間,並在五歲時趨於成熟。這意味著,我們在這段期間經歷的一切,對未來的成長影響深遠。就拿語言學習為例,人在嬰兒時期輕易就能學會新的語言,並在往後的人生中保持一定的流利程度。等過了十二歲,多數人在學習新語言時就會覺得相當吃力。
當我們學習開口說話時,也是在學習情緒的語言。我們對自我、人際關係與世界的認識,大部分都來自童年時期。
不幸的是,人類進化的目的是維持生存,而非尋求幸福。大腦不在乎你對社群媒體上癮而變得如同行屍走肉,也不在乎你因為生活缺乏動力而工作表現差勁。大腦只想保護你不受它認為具有潛在危險性的事物所傷害。
那麼,我們是從何時開始得知什麼樣的事物會危害我們的生存呢?答案是童年時期。
長大成人的你能夠讓自己吃得飽、照顧好自己,但當你還是小孩的時候肯定做不到。相較於其他物種,人類更是如此,因為我們在嬰兒時期脆弱無助。從出生到兩歲的這段期間,我們得完全依靠大人的照顧才能存活,需要有人餵食、扶持與防止我們摔落地上。
寶寶要生存,需要與父母保持連結,需要得到關愛。
因此,寶寶對於會增進或削弱親子關係的事物極為敏感。當父親或母親不在身邊、對我們咆哮或處於神經緊繃的狀態下,我們的大腦會發出恐懼的信號。這種恐懼感告訴我們有事不對勁,還只是嬰兒的我們會使出渾身解數去試著修補問題、讓父母開心。我們需要父母維持我們的生存,因此需要他們的關愛。我們會努力表現更多惹人疼愛的行為,盡量不做會使他們生氣的事情。
即使你的父母懂得控制情緒、不會以批判角度看待你,但你仍會受周遭環境潛移默化的影響,逐漸得知什麼樣的行為才能被社會所接受:男人有淚不輕彈;女人不該有主見;身而為人應該自信而不驕傲,快樂但不自負。這些觀念存在於我們的生活中,依我們所屬的文化、種族、階級與國家而有所不同。社會給予我們無數的訊息,告訴我們應該成為什麼樣的人,應該做出什麼樣的行為舉止,應該從什麼樣的角度去思考。形塑你的不只是你的家人,還有廣大的社會、你所屬的文化、性別、種族、階級、宗教與神經特徵……等。隨著我們長大,生活在這世上得到的所有經驗,都不斷影響我們與他人及自我形成連結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