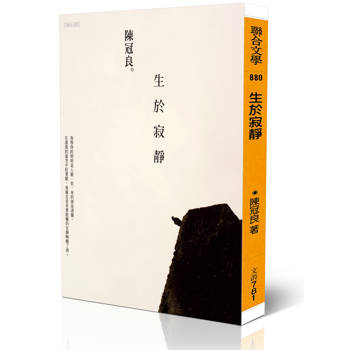玩房子還是被房子玩?
2020.03.18,天氣晴好
生於寂靜
以前並不知道自己是會打鼾的。
一個人的房間,獨眠,即便響鼾堪以夏午蟬唧、春夜貓吟分庭抗禮,我也不會有所覺知。但透天厝同住一層樓的老弟,本來就是呼吸道過敏的體質,加之長年戒之不卻的喫菸小酌,且不說平常其鼾之驚天地、泣鬼神,當鼻炎發作,鼾聲變得崎嶇破碎,偶然大鼾忽熄,我便會心上一悚,豎耳膽戰起他是否窒息,斷了呼吸。每每拿來說嘴笑鬧,老弟一臉窘之外,也沒能反脣相稽我還不是一樣。而與朋友們出遊外宿,同樣沒有聽過抱怨我擾人好夢,現在推想,大概是認床的關係,所以淺眠而釀不成鼾了。
後來,交了戀人,同床共枕時有之。起初兩個人半生不熟,彼此尚有許多陌生留待探聽,我連睡覺都下意識維護著矜持形象,睡不酣,當然也就不鼾了。
戀人怕吵。
他是一個敏感的人。而他的敏感便是體現在「怕吵」一事上。怕吵,不純粹指音量大小,也包括了感官上任何細瑣的紊亂煩雜。
每晚就寢前,眼罩耳塞是必不可少的基本配備,窗簾更得一絲不茍地嚴密遮掩,好像除了預阻晨曦刺目,夜空裡那盞曖曖月光也是干擾。然而,市廛擾攘,工地趕進度,大車轟隆小車噗噗,鄰戶在午夜時分啟動的洗衣機……外面的世界自有其節奏,甚或無秩序,想方設法降低被影響程度,有一回盡人事了仍不得一番清靜,乾脆另覓巢穴搬家。
戀人千防萬堵,怎樣也沒料到最大噪音源多年前就潛伏在耳邊。可謂機關算盡,百密一疏,哭笑不得。當他苦著臉哀怨陳訴事實,我本能反應地否認,深覺誣賴。被我回譏幾次口說無憑,他竟拿手機錄下證據反擊。百口莫辯的我,聽著那彷彿什麼外星語的聲頻,腦中迴播起那些老弟鼾聲伴奏的夜晚,以及原形畢露的赤裸感……各種尷尬攪和一氣,澈底惱羞成怒,我板起冷面冷戰,他感覺無辜,我卻一時半刻只能以不可理喻來掩飾自己。
我會打鼾已是無以轉圜,換了枕也罔效,為了不加重他的黑眼圈,也內疚地提議過不如就各睡各的,但他一口否決,還啐我荒謬。長久下來,他嘀咕從窗隙門縫滲漏入屋的喧擾如故,卻鮮少在我面前嗟歎夜難安眠。無論是顧全我顏面,圖個相安無事,抑或者頹然放棄掙扎,我知道都是他的體貼。可是,嘴上不說,呼嚕嚕的鼾息並不因此滅絕,實在受夠了,他還是會試探地、小心地企圖將我推挪成側臥,求個暫且安寧。
戀人的怕吵其來有自,在一次機緣下,我意外發現了那個算不上祕密的原由。
戀人成長於靠近赤道的馬來西亞半島。有一年,他帶著我,一起回家。
在檳城停留一夜,剛破曉,我們便搭上巴士,展開了數小時的長途跋涉。車外熾陽猛烈、黃沙飛揚,繁鬧街衢、阡陌田野,風景輪流轉,車內乘客全像搖籃裡的嬰孩,瞌成一片與世無爭的沉寂。停經幾處如廁需要付費的公路休憩站之後,我們抵達了金馬崙高原。
溫度切換成舒爽模式,五月的暑熱被遠遠遺棄在幾百里之外的城市裡。
戀人的老家坐落被勃勃蓊鬱綠意環抱,得爬上一段微喘緩坡的山丘處。聚居多戶並共用一條走廊的組屋,四方框起的設計形式,圈出井字中庭,自成面面相覷、聲息相聞的小社區,類似香港的公共屋邨。
父母辛勤務農,胼手胝足攢下一廳二房的小單位,不大,卻是三口人遮風避雨,安穩度日的最好的家。屋裡一切清簡,沒有多餘什物,一如樸素生活,就算粗茶淡飯,三餐溫飽已是豐足。若要說最貴重的,也許就是母親那台噠噠噠縫製、補綴過無數布匹衣料的老裁縫車了吧。戀人直至十二歲負笈寄宿學校前的記憶,便全是在這屋子裡的每個晨昏,乖巧搗蛋、獎勵挨罵,還有那香氣彷彿仍留在舌尖,餐桌上自家種育的特別甜美的高麗菜。
正午過兩點,無絲風,懸吊出柵欄外晾曬的短褲汗衫也聲色不動。廊道上遇見住在隔壁,剛散步返來佝僂的印度老嫗,親切如昔,戀人說孩提時代受她許多照顧。梯間拐彎的水泥地上不知是誰恣意揮灑的藝術創作,一簇簇妖嬈盛放的花朵在默默燦爛。一牆整齊列隊的木釘郵箱沒有信件或半張廣告傳單,清爽得像裝飾用似的,幾輛三輪的娃娃腳踏車挨擠在幾何圖形鏤空的磚牆邊,像是被幾個小兔崽子為了追貓追狗追蟋蟀而匆忙撇下的……樓上到樓下,整座組屋像是盹著了,搭好的日常生活布景,空著,靜悄悄的,沒有演員從帷幕後出來亮相走位。
陽光柔煦,金馬崙年均溫介於攝氏十五至二十五度之間的高地氣候,軟化了半島始終火爆的脾氣。
小鎮大街上,旅館小吃店、茶鋪雜貨店一應俱全,來自世界各地,卻步履同樣慵懶的旅人時不時錯身而過。雖是著名避暑旅遊之地,這普通日子裡,一爿爿店鋪門前大多空落落,待售的商品貨物,與陷在藤編躺椅裡神遊的老闆相看兩不厭,偶然盲飛亂竄的蟲蠅才稍稍攪動了連塵灰都浮不起來的空氣。而類似「網咖」可以付費上網,擺著遊戲機的「娛樂場所」倒是不意外地人氣熱絡些。街道盡頭,連綴著一排食檔,已過午餐時刻,簷下整列藍色桌椅不見食客。緊鄰在旁賣炸香蕉的小販,簡陋搭起的攤子像是占在馬路邊的違章建築。
飲著一袋涼水晃悠,離開了街區,高低綿亙的田地山坡與樹林大片鋪展,遠方山不修邊幅的稜線靜靜伏臥著,其間錯落砌有煙囪的英式風格屋宅外,還拔地而起一式的龐大樓群,戀人嘆那些都是逐年增蓋的觀光飯店,開發是不會停止的了,約莫再幾年就會像南投的清境農場一樣,不再是清境,小時候印象裡的家園模樣將蕩然無存。一路慢慢走逛,戀人導覽般細數自己曾在這裡那裡發生的點點滴滴,遇見一些熟悉的,或喊不出名字的花草,最讓我驚奇的就屬隨地漫生、隨手可摘的龍鬚菜了。盤旋而上的路旁,一段一段略顯凌亂的不規則形狀石梯,以四十五度或六十度角斜切、橫跨,成為坡道與坡道間的捷徑,省了不少腳勁。來到英殖民時期遺存的老教堂,時光洗過的磚石黯淡,木門漆面微微斑駁。教堂局部如今用作小學校園。不上課的週末下午,孩子們的嬉戲是遙遠的餘波,正喧騰的是那近在眼前髹得鮮黃的牆柱,張貼垂掛的學生們色彩大膽繽紛的美術作品。
向晚,風躡著手腳而至,讓人雞皮疙瘩地抖索。白日的清涼轉而清冽。
若不是舟車勞頓,就是半山夜色有催眠效果,似乎才剛晚飯過,睏懶便偷偷摸摸上了眼瞼。
梳洗過,窩進通鋪上的碎印花被褥裡,好整以暇地閉上澀澀雙眼。
我等待的明明是入眠,但,來的卻是清醒。
在漆黑的虛空中眨著眼,我確定是未曾經驗的安靜喚醒了我。沒有蛙鳴蟲唧,沒有塵世窸窣,萬籟俱絕,那透澈的止息,是宇宙,是真空,是失去磁場,沒有引力,深深沉澱,無一絲絲懸浮。我像被拓印在一張平面的圖稿紙,而寂靜是一個俯看我的觀賞者,立體而巨大,完完全全籠罩,將我包裹進他無垠的瞳眸銀河裡……我從小就家住繁忙的嘈雜街市旁,房裡凹凸格紋的落地窗也沒裝窗簾,所以練就既不怕吵更不畏光的金剛不壞之體,不得不承認,過去雖可以理解但卻無法體會戀人何以那麼嚴重,近乎誇張地排斥,甚至恐懼吵雜的環境,然而那當下一刻,我真正明白了他—到底,他是被這樣的靜寂餵養長大的孩子呀。
喜歡在睡前說說話的戀人,像怕誰偷聽似地,細細飄飄的聲音貼在我耳畔:明天我帶你去茶山看一看。
親愛的老傢伙
有時從舊物的價值才體認了新事的意義,反之亦然,拍照於我,便是如此。
初初與一夥友人瘋拍照,直逼癲的程度,像中了什麼巫術蠱咒。每到週末,我們整裝出發,駕著M老當益壯的二手車,城郊鄉鎮,半山或臨海,遠近跋涉,用相機記景留影。其時雖不確定那樣的遊走拍照,究竟是發洩生活的苦悶,或想為蒼白的青春暈染顏色,但我們無疑是耽溺的。
我的第一臺相機是數位單眼,入門款的入手價格,如同十分膠感的輕巧機體,不算負擔,需要計較的只有記憶卡容量與電池續航力。彼時拍照不假思索,視感一如數位平面的冰涼,沒有立體的縱深。若拍照是一個自我與外在的對話過程,那麼我只是一昧地想說,無心傾聽。數位單眼的拍攝設定一切便利,唯一變數是我的眼睛與環境條件之間的平衡,或抗衡。便利意味著輕易,即拍即看,賞心悅目的暫存,不中意的垃圾立馬刪淨,不過眨眼功夫,上一秒的新紀錄,下一秒就成了遺忘殆盡的舊廢棄。
數位相機的新鮮感與低操作門檻,貧弱了拍照行為的「作品」意識,每幅畫面力求清晰呈現,忠實反應現場所見細節,美麗與否,但憑運氣就是。我與相機的互動直來直往,不必時刻認真,即便我的態度隨性,它依然可以把持自己的精準原則。而志不在於專業攝影師,對那般淺薄的關係並沒有什麼惋歎,也就缺乏進一步改善的動機與心思。似乎這樣,我與拍照之間就長期友達以上,而戀人未滿了。
應該是注定的緣分,我才會在已然遭到主流淘汰的時代裡,與底片(亦稱作菲林或膠卷)相遇。
初見銀鹽影像的悸動,猶如乍見夜穹劃過一抹碎星、安眠中忽聞奔落的春雷。如果數位是敏銳的神經系統,底片就是噗通跳躍的心臟。數位可以細緻地陳述現實,底片粗糙的顆粒卻有更大的張力容納歧義。透過35mm的菲林,我看見一個何其普通的畫面,竟催化出黑洞引力般的厚度層次。截然不同的溫度、質地與情感稠度,甚至略帶瑕疵的不完美都教我驚豔,儘管熟稔於拍照,仍不由自主地對之產生了另一種嶄新而嚮往的情懷。
父親有一臺,也是唯一一臺日本製造的P牌底片單眼相機。雖是老機子,錚亮如新的品相表明了聊備一格、極低的運用率。在家裡角落塵封多年,兩顆不同焦段的寶貴鏡頭早已受潮生霉,重出江湖之前,先付了白花花五千鈔票清潔除霉。因為陌生,舊物也成了新玩意。旁的姑且不說,僅僅第一關,開片匣、裝底片,既小心翼翼怕太粗魯扳壞精細零件,又誠惶誠恐擔憂底片排孔沒咬住齒輪,捲軸空轉,導致在路上追逐的繁華景色全淪為一覺醒來就船過水無痕的黃粱夢。
包裹黑色皮革箍銀邊的機身,優雅內斂,掂在手裡沉甸扎實,都不曉得那重的是歲月,抑或自疑沒有能耐將它淋漓盡致發揮的壓力?全機械手動的底片機,從決定拍攝主體,調配光圈快門,算焦距對焦、找光測光,到一格一格轉片軸,每個步驟,無論疾緩,總得耗上點時間,拍照的動作於是顯得特別慎重其事。常常,屏住呼吸,斟酌構圖,穩定水平,瞄準目標,看似一切就緒,也並不保證順利壓下快門鍵—可能凝注時莫名多了一縷思慮,也許疏忽捲妥下一格空白膠卷……而踟躕而錯失某個心動瞬間的最佳時機。重來的,都已非原來。那些來不及拍的,是否比拍下的更值得?我無從確知。然而,但凡懸念的,必不放棄,繼續走在有風景的路上,我總會在觀景窗裡再遇見似曾相識的一些什麼。
用底片拍著拍著,倏忽也逾十載有餘。
父親的老相機不堪操練,在頭幾年內澈底故障退役,永遠地成為象徵舊時光的裝飾品。如今與身邊生於七○年代的二手相機早也過了磨合期,我們一起這島那陸相伴過許多遠方,它無可避免地添了點新傷,我在生活裡、旅途上快照慢拍的興致如昔。每次快門清脆鏗鏘一聲的同時,停在視窗內的片刻便已舊去,待底片沖掃出來,因視角與預期的落差,出乎意料的奇幻景象、斑斕光影,甚或模糊失焦,竟又彷彿未曾邂逅了。菲林無法完全掌控的特性,像是與一個若即若離的人的曖昧戀情,在朦朧的浪漫中患得患失—有驚喜的亢奮,也不乏想像之外的錯愕與失落。但情不自禁的,如何反覆的折磨都是甜美的呵。
再也回不去,也不想回去。這會兒,不斷推陳出新的數位相機幾乎被攝影功能日益進化的智慧型手機取代了,我卻仍獨獨偏愛那低調穩重的老傢伙。
這個世界總是匆忙,好像稍慢了,文明就要面臨瓦解。但老傢伙故我地,不徐不疾地去解讀每一次的相逢與經過。我眷戀且依賴地跟隨它,悠悠緩緩,與躁鬱的世界保持一點距離,以三十六張底片的餘裕,在一場西北雨、一陣三月南風;一次次的迎面而來、擦身而過中暫佇流連之後,靜靜等待不可預知的,新的詮釋,浮現。
南下月台
再五分鐘,列車就要進站了。
幼年牙牙學步時,易摔,每每號啕不止,到醫院檢查何以如此卻誤遇庸醫,我右踝的一點小症狀被矯枉過正成永久性的骨骼傷害。以後的日子裡,我嫌拐杖麻煩,行走時,左腳都只好半屈膝地配合搆不著地的右腳。姿態是特異了點,但頂多一些少見多怪的視線跟隨。我到底不願隨身一雙拐杖累贅。
星期六。剛過午,金烏灼度正熾。
我沁著薄汗,略有不耐地佇候南下車次。即便右腳懸空,我照樣穩當當金雞獨立在高鐵月台上。好像功底深厚的俠客,氣沉丹田,如僧入定。
我察覺,來回巡邏的警衛迂迴地愈靠愈近,終於幾步路外踟躕不去,顯然有話。既然那廂按兵未動,我這廂便也暫時不動聲色。在狀況幾乎發生僵持嫌疑之際,他畢竟率先有所表示了。
他一臉明顯天生的憨愣氣(就像臺語形容的孝呆),笑起來時,裸露過多的齦肉,凌亂參差的黃板牙,絲毫不羞赧於示人:「你要不要坐下來?」伸直的手臂指向旁邊一排空著的銀白座椅。「不用,沒關係,一下子而已。」揮擺著手,我用溫煦的微笑感謝他的好意。
他點著頭,像是不勉強卻又似乎意有未竟地沉吟著,半晌,他不期然蹦出了一句:「你……你都這樣子生活喔?」
「……對啊。」雖不覺得唐突冒犯,我仍是些許尷尬地把微笑的嘴角撐得更開一些。說不上揉和他神情裡的詫訝與敬佩,也可能是惋惜或同情⋯⋯哪種成分比例高一點,我猜他腦海裡大概是閃過了「人活著可真的是不容易呵」諸如此類的念頭罷。但,誰知道呢,或許他其實不過為了自己沒有被接納的善意而感到失望罷了。
頷頷首,始終沒有斂收笑容的他,踏起微微顛晃的步態,繼續執行長長月台上巡視的勤務去了。
到底沒有什麼礙事的。只不過,在列車即將進站的半分間,方才他那不假修飾的模樣,率真直性的幾句話,卻讓一點輕淡的、軟暖的什麼觸上了心尖
2020.03.18,天氣晴好
生於寂靜
以前並不知道自己是會打鼾的。
一個人的房間,獨眠,即便響鼾堪以夏午蟬唧、春夜貓吟分庭抗禮,我也不會有所覺知。但透天厝同住一層樓的老弟,本來就是呼吸道過敏的體質,加之長年戒之不卻的喫菸小酌,且不說平常其鼾之驚天地、泣鬼神,當鼻炎發作,鼾聲變得崎嶇破碎,偶然大鼾忽熄,我便會心上一悚,豎耳膽戰起他是否窒息,斷了呼吸。每每拿來說嘴笑鬧,老弟一臉窘之外,也沒能反脣相稽我還不是一樣。而與朋友們出遊外宿,同樣沒有聽過抱怨我擾人好夢,現在推想,大概是認床的關係,所以淺眠而釀不成鼾了。
後來,交了戀人,同床共枕時有之。起初兩個人半生不熟,彼此尚有許多陌生留待探聽,我連睡覺都下意識維護著矜持形象,睡不酣,當然也就不鼾了。
戀人怕吵。
他是一個敏感的人。而他的敏感便是體現在「怕吵」一事上。怕吵,不純粹指音量大小,也包括了感官上任何細瑣的紊亂煩雜。
每晚就寢前,眼罩耳塞是必不可少的基本配備,窗簾更得一絲不茍地嚴密遮掩,好像除了預阻晨曦刺目,夜空裡那盞曖曖月光也是干擾。然而,市廛擾攘,工地趕進度,大車轟隆小車噗噗,鄰戶在午夜時分啟動的洗衣機……外面的世界自有其節奏,甚或無秩序,想方設法降低被影響程度,有一回盡人事了仍不得一番清靜,乾脆另覓巢穴搬家。
戀人千防萬堵,怎樣也沒料到最大噪音源多年前就潛伏在耳邊。可謂機關算盡,百密一疏,哭笑不得。當他苦著臉哀怨陳訴事實,我本能反應地否認,深覺誣賴。被我回譏幾次口說無憑,他竟拿手機錄下證據反擊。百口莫辯的我,聽著那彷彿什麼外星語的聲頻,腦中迴播起那些老弟鼾聲伴奏的夜晚,以及原形畢露的赤裸感……各種尷尬攪和一氣,澈底惱羞成怒,我板起冷面冷戰,他感覺無辜,我卻一時半刻只能以不可理喻來掩飾自己。
我會打鼾已是無以轉圜,換了枕也罔效,為了不加重他的黑眼圈,也內疚地提議過不如就各睡各的,但他一口否決,還啐我荒謬。長久下來,他嘀咕從窗隙門縫滲漏入屋的喧擾如故,卻鮮少在我面前嗟歎夜難安眠。無論是顧全我顏面,圖個相安無事,抑或者頹然放棄掙扎,我知道都是他的體貼。可是,嘴上不說,呼嚕嚕的鼾息並不因此滅絕,實在受夠了,他還是會試探地、小心地企圖將我推挪成側臥,求個暫且安寧。
戀人的怕吵其來有自,在一次機緣下,我意外發現了那個算不上祕密的原由。
戀人成長於靠近赤道的馬來西亞半島。有一年,他帶著我,一起回家。
在檳城停留一夜,剛破曉,我們便搭上巴士,展開了數小時的長途跋涉。車外熾陽猛烈、黃沙飛揚,繁鬧街衢、阡陌田野,風景輪流轉,車內乘客全像搖籃裡的嬰孩,瞌成一片與世無爭的沉寂。停經幾處如廁需要付費的公路休憩站之後,我們抵達了金馬崙高原。
溫度切換成舒爽模式,五月的暑熱被遠遠遺棄在幾百里之外的城市裡。
戀人的老家坐落被勃勃蓊鬱綠意環抱,得爬上一段微喘緩坡的山丘處。聚居多戶並共用一條走廊的組屋,四方框起的設計形式,圈出井字中庭,自成面面相覷、聲息相聞的小社區,類似香港的公共屋邨。
父母辛勤務農,胼手胝足攢下一廳二房的小單位,不大,卻是三口人遮風避雨,安穩度日的最好的家。屋裡一切清簡,沒有多餘什物,一如樸素生活,就算粗茶淡飯,三餐溫飽已是豐足。若要說最貴重的,也許就是母親那台噠噠噠縫製、補綴過無數布匹衣料的老裁縫車了吧。戀人直至十二歲負笈寄宿學校前的記憶,便全是在這屋子裡的每個晨昏,乖巧搗蛋、獎勵挨罵,還有那香氣彷彿仍留在舌尖,餐桌上自家種育的特別甜美的高麗菜。
正午過兩點,無絲風,懸吊出柵欄外晾曬的短褲汗衫也聲色不動。廊道上遇見住在隔壁,剛散步返來佝僂的印度老嫗,親切如昔,戀人說孩提時代受她許多照顧。梯間拐彎的水泥地上不知是誰恣意揮灑的藝術創作,一簇簇妖嬈盛放的花朵在默默燦爛。一牆整齊列隊的木釘郵箱沒有信件或半張廣告傳單,清爽得像裝飾用似的,幾輛三輪的娃娃腳踏車挨擠在幾何圖形鏤空的磚牆邊,像是被幾個小兔崽子為了追貓追狗追蟋蟀而匆忙撇下的……樓上到樓下,整座組屋像是盹著了,搭好的日常生活布景,空著,靜悄悄的,沒有演員從帷幕後出來亮相走位。
陽光柔煦,金馬崙年均溫介於攝氏十五至二十五度之間的高地氣候,軟化了半島始終火爆的脾氣。
小鎮大街上,旅館小吃店、茶鋪雜貨店一應俱全,來自世界各地,卻步履同樣慵懶的旅人時不時錯身而過。雖是著名避暑旅遊之地,這普通日子裡,一爿爿店鋪門前大多空落落,待售的商品貨物,與陷在藤編躺椅裡神遊的老闆相看兩不厭,偶然盲飛亂竄的蟲蠅才稍稍攪動了連塵灰都浮不起來的空氣。而類似「網咖」可以付費上網,擺著遊戲機的「娛樂場所」倒是不意外地人氣熱絡些。街道盡頭,連綴著一排食檔,已過午餐時刻,簷下整列藍色桌椅不見食客。緊鄰在旁賣炸香蕉的小販,簡陋搭起的攤子像是占在馬路邊的違章建築。
飲著一袋涼水晃悠,離開了街區,高低綿亙的田地山坡與樹林大片鋪展,遠方山不修邊幅的稜線靜靜伏臥著,其間錯落砌有煙囪的英式風格屋宅外,還拔地而起一式的龐大樓群,戀人嘆那些都是逐年增蓋的觀光飯店,開發是不會停止的了,約莫再幾年就會像南投的清境農場一樣,不再是清境,小時候印象裡的家園模樣將蕩然無存。一路慢慢走逛,戀人導覽般細數自己曾在這裡那裡發生的點點滴滴,遇見一些熟悉的,或喊不出名字的花草,最讓我驚奇的就屬隨地漫生、隨手可摘的龍鬚菜了。盤旋而上的路旁,一段一段略顯凌亂的不規則形狀石梯,以四十五度或六十度角斜切、橫跨,成為坡道與坡道間的捷徑,省了不少腳勁。來到英殖民時期遺存的老教堂,時光洗過的磚石黯淡,木門漆面微微斑駁。教堂局部如今用作小學校園。不上課的週末下午,孩子們的嬉戲是遙遠的餘波,正喧騰的是那近在眼前髹得鮮黃的牆柱,張貼垂掛的學生們色彩大膽繽紛的美術作品。
向晚,風躡著手腳而至,讓人雞皮疙瘩地抖索。白日的清涼轉而清冽。
若不是舟車勞頓,就是半山夜色有催眠效果,似乎才剛晚飯過,睏懶便偷偷摸摸上了眼瞼。
梳洗過,窩進通鋪上的碎印花被褥裡,好整以暇地閉上澀澀雙眼。
我等待的明明是入眠,但,來的卻是清醒。
在漆黑的虛空中眨著眼,我確定是未曾經驗的安靜喚醒了我。沒有蛙鳴蟲唧,沒有塵世窸窣,萬籟俱絕,那透澈的止息,是宇宙,是真空,是失去磁場,沒有引力,深深沉澱,無一絲絲懸浮。我像被拓印在一張平面的圖稿紙,而寂靜是一個俯看我的觀賞者,立體而巨大,完完全全籠罩,將我包裹進他無垠的瞳眸銀河裡……我從小就家住繁忙的嘈雜街市旁,房裡凹凸格紋的落地窗也沒裝窗簾,所以練就既不怕吵更不畏光的金剛不壞之體,不得不承認,過去雖可以理解但卻無法體會戀人何以那麼嚴重,近乎誇張地排斥,甚至恐懼吵雜的環境,然而那當下一刻,我真正明白了他—到底,他是被這樣的靜寂餵養長大的孩子呀。
喜歡在睡前說說話的戀人,像怕誰偷聽似地,細細飄飄的聲音貼在我耳畔:明天我帶你去茶山看一看。
親愛的老傢伙
有時從舊物的價值才體認了新事的意義,反之亦然,拍照於我,便是如此。
初初與一夥友人瘋拍照,直逼癲的程度,像中了什麼巫術蠱咒。每到週末,我們整裝出發,駕著M老當益壯的二手車,城郊鄉鎮,半山或臨海,遠近跋涉,用相機記景留影。其時雖不確定那樣的遊走拍照,究竟是發洩生活的苦悶,或想為蒼白的青春暈染顏色,但我們無疑是耽溺的。
我的第一臺相機是數位單眼,入門款的入手價格,如同十分膠感的輕巧機體,不算負擔,需要計較的只有記憶卡容量與電池續航力。彼時拍照不假思索,視感一如數位平面的冰涼,沒有立體的縱深。若拍照是一個自我與外在的對話過程,那麼我只是一昧地想說,無心傾聽。數位單眼的拍攝設定一切便利,唯一變數是我的眼睛與環境條件之間的平衡,或抗衡。便利意味著輕易,即拍即看,賞心悅目的暫存,不中意的垃圾立馬刪淨,不過眨眼功夫,上一秒的新紀錄,下一秒就成了遺忘殆盡的舊廢棄。
數位相機的新鮮感與低操作門檻,貧弱了拍照行為的「作品」意識,每幅畫面力求清晰呈現,忠實反應現場所見細節,美麗與否,但憑運氣就是。我與相機的互動直來直往,不必時刻認真,即便我的態度隨性,它依然可以把持自己的精準原則。而志不在於專業攝影師,對那般淺薄的關係並沒有什麼惋歎,也就缺乏進一步改善的動機與心思。似乎這樣,我與拍照之間就長期友達以上,而戀人未滿了。
應該是注定的緣分,我才會在已然遭到主流淘汰的時代裡,與底片(亦稱作菲林或膠卷)相遇。
初見銀鹽影像的悸動,猶如乍見夜穹劃過一抹碎星、安眠中忽聞奔落的春雷。如果數位是敏銳的神經系統,底片就是噗通跳躍的心臟。數位可以細緻地陳述現實,底片粗糙的顆粒卻有更大的張力容納歧義。透過35mm的菲林,我看見一個何其普通的畫面,竟催化出黑洞引力般的厚度層次。截然不同的溫度、質地與情感稠度,甚至略帶瑕疵的不完美都教我驚豔,儘管熟稔於拍照,仍不由自主地對之產生了另一種嶄新而嚮往的情懷。
父親有一臺,也是唯一一臺日本製造的P牌底片單眼相機。雖是老機子,錚亮如新的品相表明了聊備一格、極低的運用率。在家裡角落塵封多年,兩顆不同焦段的寶貴鏡頭早已受潮生霉,重出江湖之前,先付了白花花五千鈔票清潔除霉。因為陌生,舊物也成了新玩意。旁的姑且不說,僅僅第一關,開片匣、裝底片,既小心翼翼怕太粗魯扳壞精細零件,又誠惶誠恐擔憂底片排孔沒咬住齒輪,捲軸空轉,導致在路上追逐的繁華景色全淪為一覺醒來就船過水無痕的黃粱夢。
包裹黑色皮革箍銀邊的機身,優雅內斂,掂在手裡沉甸扎實,都不曉得那重的是歲月,抑或自疑沒有能耐將它淋漓盡致發揮的壓力?全機械手動的底片機,從決定拍攝主體,調配光圈快門,算焦距對焦、找光測光,到一格一格轉片軸,每個步驟,無論疾緩,總得耗上點時間,拍照的動作於是顯得特別慎重其事。常常,屏住呼吸,斟酌構圖,穩定水平,瞄準目標,看似一切就緒,也並不保證順利壓下快門鍵—可能凝注時莫名多了一縷思慮,也許疏忽捲妥下一格空白膠卷……而踟躕而錯失某個心動瞬間的最佳時機。重來的,都已非原來。那些來不及拍的,是否比拍下的更值得?我無從確知。然而,但凡懸念的,必不放棄,繼續走在有風景的路上,我總會在觀景窗裡再遇見似曾相識的一些什麼。
用底片拍著拍著,倏忽也逾十載有餘。
父親的老相機不堪操練,在頭幾年內澈底故障退役,永遠地成為象徵舊時光的裝飾品。如今與身邊生於七○年代的二手相機早也過了磨合期,我們一起這島那陸相伴過許多遠方,它無可避免地添了點新傷,我在生活裡、旅途上快照慢拍的興致如昔。每次快門清脆鏗鏘一聲的同時,停在視窗內的片刻便已舊去,待底片沖掃出來,因視角與預期的落差,出乎意料的奇幻景象、斑斕光影,甚或模糊失焦,竟又彷彿未曾邂逅了。菲林無法完全掌控的特性,像是與一個若即若離的人的曖昧戀情,在朦朧的浪漫中患得患失—有驚喜的亢奮,也不乏想像之外的錯愕與失落。但情不自禁的,如何反覆的折磨都是甜美的呵。
再也回不去,也不想回去。這會兒,不斷推陳出新的數位相機幾乎被攝影功能日益進化的智慧型手機取代了,我卻仍獨獨偏愛那低調穩重的老傢伙。
這個世界總是匆忙,好像稍慢了,文明就要面臨瓦解。但老傢伙故我地,不徐不疾地去解讀每一次的相逢與經過。我眷戀且依賴地跟隨它,悠悠緩緩,與躁鬱的世界保持一點距離,以三十六張底片的餘裕,在一場西北雨、一陣三月南風;一次次的迎面而來、擦身而過中暫佇流連之後,靜靜等待不可預知的,新的詮釋,浮現。
南下月台
再五分鐘,列車就要進站了。
幼年牙牙學步時,易摔,每每號啕不止,到醫院檢查何以如此卻誤遇庸醫,我右踝的一點小症狀被矯枉過正成永久性的骨骼傷害。以後的日子裡,我嫌拐杖麻煩,行走時,左腳都只好半屈膝地配合搆不著地的右腳。姿態是特異了點,但頂多一些少見多怪的視線跟隨。我到底不願隨身一雙拐杖累贅。
星期六。剛過午,金烏灼度正熾。
我沁著薄汗,略有不耐地佇候南下車次。即便右腳懸空,我照樣穩當當金雞獨立在高鐵月台上。好像功底深厚的俠客,氣沉丹田,如僧入定。
我察覺,來回巡邏的警衛迂迴地愈靠愈近,終於幾步路外踟躕不去,顯然有話。既然那廂按兵未動,我這廂便也暫時不動聲色。在狀況幾乎發生僵持嫌疑之際,他畢竟率先有所表示了。
他一臉明顯天生的憨愣氣(就像臺語形容的孝呆),笑起來時,裸露過多的齦肉,凌亂參差的黃板牙,絲毫不羞赧於示人:「你要不要坐下來?」伸直的手臂指向旁邊一排空著的銀白座椅。「不用,沒關係,一下子而已。」揮擺著手,我用溫煦的微笑感謝他的好意。
他點著頭,像是不勉強卻又似乎意有未竟地沉吟著,半晌,他不期然蹦出了一句:「你……你都這樣子生活喔?」
「……對啊。」雖不覺得唐突冒犯,我仍是些許尷尬地把微笑的嘴角撐得更開一些。說不上揉和他神情裡的詫訝與敬佩,也可能是惋惜或同情⋯⋯哪種成分比例高一點,我猜他腦海裡大概是閃過了「人活著可真的是不容易呵」諸如此類的念頭罷。但,誰知道呢,或許他其實不過為了自己沒有被接納的善意而感到失望罷了。
頷頷首,始終沒有斂收笑容的他,踏起微微顛晃的步態,繼續執行長長月台上巡視的勤務去了。
到底沒有什麼礙事的。只不過,在列車即將進站的半分間,方才他那不假修飾的模樣,率真直性的幾句話,卻讓一點輕淡的、軟暖的什麼觸上了心尖